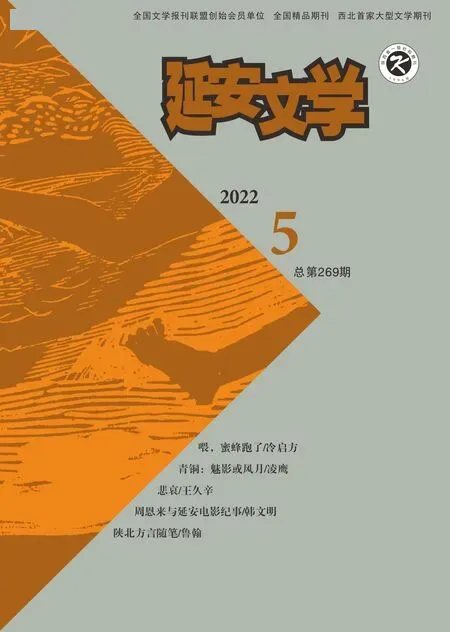陕北方言随笔
鲁 翰
出门人
陕北的“门文化”渊源深厚,也自异彩纷呈。门是宗族家庭标志性的尊严和象征。“门第”“门神”“高门槛”“开门红”“没门儿”“邪门儿”“倒插门”“门三户四”“风门水口”“门里出身”“扰门沓户”“门圪崂立五尺着嘞”“锁门锁君子”“善门难开,扇门难闭”……围绕着门真是有数不清的讲究和说道儿。
陕北民间把离家较长的时间、较长的旅程,常常说“出门”,把背乡离土的人是叫“出门人”,短时间逗留、寄居或者长期异地落户的也是中人。外乡人来当地生活、工作和行旅,比如当年从外地分配来的下放干部、落户知青和异地亲戚,都道“门外人”或“外路人”。出门到他乡自己也便成了人家地皮上的“外路人”了。普通话是“说洋话”“咬京腔”,听不懂的外地口音称“嘴里噙个羊卵卵”“操古兰音”。邻邻近近出去散活走动,只算串玩,串门儿,走亲戚,赶亲事,坐娘家和赶集遇会,活动天地也就三五十里不过。
官家逍遥坐轿,富人拉骡扬马,自轻省三分,普通人家骑驴跨鞍出门,也算得上有“枵xiao 架”,而没牲灵咣当流星的穷汉只得干赲干步行。搭伴儿说“相xi跟”,徒步说“步勷”,快走说“紧走”,跑叫“頏”,也说“跑頏”“瞎跑乱頏”,抄近路说“捷径路”,走长途说“上长路”,形容出门艰辛是说“远路风尘”。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锅头。”受传统农耕思想的影响,陕北人多守旧,守家,守摊摊,“走十处不如守一处”,但凡有个几垧几嶵山地,春种秋收,自食其力,除过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谋算到“生地方”出门闯荡的。
上长路,出远门,通常是外出求学留洋,做官行医,探病投亲,和尚行脚,道人访山,工匠“谋营生”,戏班子撵庙会和生意人“闹买卖”等等的情形。另外一种特殊情形则是实在走投没路时流离转徙的“逃荒”和流亡。或没远没近,单个儿挨门沿户讨乞,也说“行吃讨叫”,或举家抛乡离井寻活路。前者那是“情意愿”,后者则是“没办法”。旧庚儿,真正旅行意义上“走三山四码头”的游山玩水绝无仅有,即便是达官贵人、纨绔子弟,恐怕也只偶尔为之。
“离家三丈远,另外一重天。”“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因此,有家人出远门对于陕北人大多数家庭来说可是一件不寻常、不简单的事情。事先仔细焙炒面、烙饼子须备足干粮,缝新补烂,加棉添衣,捲捆铺盖,打发盘缠等等事无巨细。临行前一老碗热热辣辣的“菜汤滚水”权作饯别。这样,每家每户的“大门道”,既是出门人的动身地儿,也是亲人们的送别地儿,其实脱不得就是伤情地儿。父母相送,夫妻惜别,捋发衿巾,抚手扯衣,揩眼抹泪,千安万顿,万顿千安……怕山高路远,怕圪塄防畔,怕挨冻受饿,怕露餐风宿,怕豺狼当道,怕土匪打劫……总之,走前一百个不放心,别后白日黑地操尽了心。
有一首陕北民歌就唱叹到大门道送别的情景:
人人都说出门人好,出门人恓惶谁知道。
妻儿老小都大撇了,死活交给老天爷了。
哥哥起身妹妹我照,眼泪滴嗒在大门道。
“出门万容难,谁说天地宽。”人在路上,心盼远方。翻不完的沟圪梁,走不完的黄土路。遥遥途程,不分冬夏。十冬腊月,眉毛胡子上凝结的都是“霜呵子”“冰渣渣”,手背上脚后跟是冻伤的皴口子、血裂子。七月流火,嘴唇干裂,喉咙冒烟,烧炼得急忙探不上一口井泉水,寻不见个背荫地。饱一顿,饥一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所谓“客子饥寒多,行旅衣装薄。”
黑了明了,明了黑了。漫漫长路上,无论独行人或者赶着牲灵,人熬煎,心孤寂。无法排遣孤独寂寞,只便肚子里瞎盘滥算,想亲人,念婆姨,思邂逅的“相好儿”。那些爱恋欢喜,那些别恨离愁丝丝缕缕都在拐肠子里纠结转腾。一人一马半夜里走,脚夫不唱怕杆毬?
终于曲曲溜溜,张嘴即来,走哪儿唱哪儿,想起甚唱甚,想唱甚就唱甚。
七十二行当最数赶脚忙,走路啃干粮坐下补鞍帐。
叼抢个空空巴屎又尿尿,黑天半夜起来添草拌料……
无聊解闷,嘶声壮胆,更是释放难怅的情怀。想来,所多的“脚夫调”无疑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于是李治文、张天恩和柴根等等等等无师自通的天才的脚夫歌手,名驰四方,歌传遐迩。
尤其经典的“脚夫调”要算《好婆姨出在张家畔》:
说四十里(那)长涧——哎羊羔(就)山,
说好婆姨出在了我们张家(呀)畔。
张家畔那个起身儿刘家峁站,
说峁底里下迲我把朋友哟看。
说三月里的太阳红又红,
我们赶牲灵的人儿咋就这样苦命。
不唱了(那个)山曲儿我不好宬,
我唱上了(那个)山曲儿哟,我就想亲(呀)人。
我唱上了(那个)山曲儿哟我就想亲(呀)人。
自清代中晚期以降陕北人群体性出门主要还是以商旅为主,大致为“走西口”“跑草地”“过黄河”。“滚南路”算得上是特例,而奔“天(津)北京上海”那可是大海势,惟有极少数名字号、大东家“撑盘”起,办得到。
“走西口”是讨生活。“口”就是长城关口,从沙圪堵一直到包头,“西口”既模糊又清晰,既笼统又具体。因着“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出门在外,搭伙揪柴,伙场伙种,踅摸生意,养家糊口,这是秦晋老百姓山穷水绝、穷猿投林的一场滴滴续续了二百多年的人口大迁徙。
《走西口》就唱道: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唉小妹妹泪常流。
送出来就大门口,小妹妹我不丢手,
有两句的那个知心话,哎——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拉话话解忧愁。
“跑草地”,是指榆横绥米佳吴包括鱼河堡、镇川堡的商贾小贩在漠南漠北跑荡来回生意,贩来牲口、皮毛、大盐、药材和砖茶等等,而粜卖的多为米面、陶瓷、烧酒、烟糖和铜铁制品等,总的“上至绸缎,下至葱蒜。”陕北人闹买卖常见的是“朋股股”,多小打小闹,多“走碎销”,其规模和繁盛尽管比不上“山西帮”,口话说“做不过‘老西脑子’”,但是天长日久,贩贱鬻贵,“一个一个上串,十个十个上万。”毕竟也自腰缠硬货,钵溢盆满。有一首小调反映旧庚儿“走夷方”(南面人叫“跑草地”)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旅途艰辛的《出门调》如是唱叹:
驾脚落地照四方,时时念想我爹娘。
人家是人我是人,人家在家我出门。
人家出门人服侍,小哥出门服侍人。
白天吃得燎灶饭,黑地草当栽绒毡。
“过黄河”其实说的是秦晋通商之路。神木府谷过保德走的是忻代二州,佳县米脂走螅蜊峪(陕北人讹音为“孙驴儿”),到碛口,走离石、汾阳、孝义一路。绥德吴堡则过军渡,走柳林,到侯马交口。
值得一提的“螅蜊峪”(口音为“孙驴儿”),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古镇是清代和民国最大的舟行渡口和最有名的河西“水旱码头”,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当时流传的民谣就有“拉不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孙驴儿。”而对岸“九曲黄河第一镇”的碛口码头,凭借黄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商贸重镇。那些从包头、宁夏等地沿黄河顺流而下一直到碛口,水路因二碛跌潲戛然而断,所有堆山积塄的货物非得需要经过这个唯一的中转枢纽改走旱路,而后再行四到五处运往各地。
“——撂碛嘞!”“碛里放下迲嘞!”这些个针对船覆货淹的说叨、疼惜及叹惋,至今顽强地留在陕北人寻常的口话里。
“滚南路”逃荒则是最为悲惨的一场出门。
陕北人的逃荒史那可是要命三官的饥饿史,那可是死里逃生的逃亡史。或许历史太习惯于轻描淡写了,以至于后代的人们往往对于“饥荒”的情景和涵义,仅仅停留在诸如“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描述的词汇本身。
在不到140年的时光里,陕北先后经历过几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劫洗。每一次遭灾时都历经三五年,每一次劫难陕北地皮都要活剥一层皮。
第一次是光绪三年(1877)史称“丁戊奇荒”。据光绪二十五年《靖边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大旱。越明年,荒甚。民齿草根,继食树皮叶俱尽;又济之以班白土,土柔无沙,掘地得之,老稚毙于胀,壮者苟免,黠者又往往割肌莩臂以延残喘,甚有屠生人以供餐者。”新编《清涧县志》录有:“光绪三年,春至六月无雨,秋禾绝,饥民鬻男弃女,不计其数,人互食,道殣相望,死者大半,十有七八家破人亡。”真是骇人听闻,不忍卒读……
第二次是始自民国十七年,1928—1932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饥馑”。据1929年2月8日张季鸾先生主笔的《大公报》报道:“陕北23 县,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由于灾情,大多数人口悉以逃亡……”据统计,“灾民人数查有55 万至59 万,如一两日内不得救助,则大多数当必死矣。”又据《陕西赈务会刊》不完全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全省灾民535万,死亡250 万,逃亡外省40 多万,很多人栽倒在逃荒路上。加之1930-1932年鼠疫大害,陕北人得病的14591 人,死亡13285 人。
第三次当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1944年,井泉干涸,树木枯萎,秋田严重歉收,饥民无数,逃荒者众。
而“滚南路”则是第三次“大饥荒”时期,榆林各县民众在饥寒交迫,困顿无奈的状态下寻求生存出路,再不跑路“一眼看下往死饿”,于是纷纷偷明暗使,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向南逃亡。像当年359 旅一样,在延安后山的老梢林里筚路蓝缕,垦荒种地,券窑安土,生儿育女。北面各县来的“外来户”逐渐地就成了地道的延安人了。近日余翻检资料,捉句一阕《走南路》,权补以记。
陕北榆林延安,旧庚二十三县。
半个世纪之前,灾祸活命艰难。
只因地广人罕,逃荒滚南老山。
大致应到洛川,落户垦荒不堪。
绥米清佳若干,人口上面泰半。
先辈扬棍讨饭,人挪比树活泛。
码头好养穷汉,如今金银满罐。
回望历史云烟,慨喟如此这般。
“年成”指一年中农作物的收获情况。因遭灾收成少叫“跌年成”,颗粒无收,说“跌下黑籽(种子也留不下)老年成”。至今陕北人把欠债说成“跌饥荒”。
旅途中在客店吃饭休息,是说“打间儿”。清代福格写的《听雨丛谈》中这样解释:“今人行役,于日中投店而饭,谓之“打尖”。皆不晓其字义。或曰中途为住宿之间,乃误‘间’为‘尖’也……”
就是脚夫跟大牲灵之间的交流也饶有意思,“嘚驾”是提示扬蹄开拔,——“吁!”是煞车口令。而一声催促警告的“待抽!——”那意思可是“等得挨打呀!”的文言呢,异样的是那懵痴痴的驴骡居然也听得懂这句蹩脚的古汉语哦。
关于“出门”陕北地皮依旧孑遗下众多的口话俗语。譬如,“走州过县”“穷家富路”“少依无靠”“门槛han 大王”“半路空中”“人生两地”“不走得路走三回”“望山跑死马”“六月天出门还要拿腊月的衣嘞”“赶早不赶晚”“干粮,干粮,撧断心肠”“家穷不算穷,路穷穷死人。”“好汉(岀门)问酒嘞,慫汉(岀门)问狗嘞。”“吃米不如吃面,投亲不如歇店。”“岀门看天色,进门看成色。”“出门门坎低,进门门坎高。”“强龙不压地头蛇”“出门人不说在家话”“在家是条龙,在外是条虫。”“在家不学好,出门圪疤脑”“出门人低耷三辈着嘞”“外来的沙子还把本地土给压住嘞?”“攀伴儿攀个强的,柱棍柱个长的。”“老乡当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耤地让畔,走路让担。”“隔河不算近,隔山不算远。”“树挪死,人挪活。”“人不能在一卜树上吊死”。“官修衙门客修店”“到什嘛站,歇什嘛店。”“风中的沙蓬,刮得哪落哪。”“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地。”“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陕北谣歌《出门人儿难》唱曰:
出门人难,出门人难,伞不离人来人不离伞。
出门人难,出门人难,揪上皮袄背上毡。
出门人难,出门人难,热身身睡在荒草滩。
出门人难,出门人难,连皮皮筷子重茬茬碗。
出门人难,出门人难,难癨没人改心宽。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水浒》里神行太保戴宗日行千里的神奇已然不再是什嘛传说和梦想了。如今陕北人出门“简单得跟一也似”,出门的方向路径更是“枣核子乱开花”了。出国旅行,会议考察,度假观光,驴友出游,跟工去乡,真个走南闯北,海迸天飏,出得门去全然是乐山乐水的心境了。
“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说到底出门人的难,其实难得无疑是远离生身的本乡田地,无法排遣怅然的魂牵梦绕的乡愁以及无处安放的拳拳在念的桑梓情怀喔。
味 气
有很多很多的词,陕北人通常多是逆序表达的,两个词可前可后、可正可反随意调整,土话叫“打颠倒儿”或者“打嘚尦儿(调的分音)”,意思却一点儿也没变,有时侯反倒有着重强化和弱化某一头儿,感觉上又还别开生面呢,现代汉语是叫逆序词。譬如,竞争与“争竞”,煎熬与“熬煎”,手脚与“脚手”,蔬菜与“菜蔬”,熟惯多说“惯熟”,劐huo 开多说“开劐”,损失也说“失损”,力气也说“气力”,气味陕北话是说“味气”……
人在感受一件东西时总离不得要调动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类感觉里,嗅觉应该是数得上的微弱和飘忽。而陕北话里用打比方来表述人物和情景俯拾皆是,哪怕是些细碎末节,极其不容易逮住的渺渺意思,陕北人常常想方设法总会往细法里说说咂咂。
就拿感受“味气”来说,陕北人自是拥有着令人异样的嗅觉和诗人一般的敏感神经。比如寻常“五味”,类似就说庞臭、焦酸、汹甜、噬咸、饤苦……再譬如,碎娃娃身上幽幽淡淡的味儿,是叫“奶腥气”。身上散发的汗水味是“汗腥气”。“老人气”一是说老人身上细胞老化代谢缓慢沉积物所散发的异味,一说是显摆老资格,如“老人气圪慉慉吤”。“气呵呵”形容的是弱不禁风的人和事物。如若有人家不爱好,邋遢“日赖”,家里有股“恶遢子气”,一进门里那就熏得臭得“閟bi 气”。道臭之极是“庞臭(庞,大且杂落)”“庞骨子老滥臭”。说香,香得喷香,“香烂人脑脑”。陕北酸曲就有:“砂糖冰糖雪花糖,比不上二妹妹的唾沫香。”这么摄人心魂的味道,究竟唱叹出了难以言说的神来之妙啊。
有个哄娃娃歌叨“水萝卜”的老谜语:“吃个香,咬个脆,嗝噜上来股大粪味”。食物放久的味儿叫“陈气”。怪味是说“味儿不正”或者“不是味儿”,有时间也形容内心难过的感受。旧以前陕北苦焦穷困,连放坏的“馊si 气”吃食都不舍得撂去,于是留下了“生臭熟不臭,熟臭没解救”的俗谚。
“一气”是指一阵儿、不间断的时段或者一股劲。“好得一个鼻窟窿里出气”,常用来形容亲密知心的关系。“心气”照例指志气、心劲儿和气量。“泰(tǎi,大)气”形容展拓、大气和慷慨等气派。“顺气”是说气性和顺,称心遂意之意。“活气”指的是生活的生机、活力和顺遂的氛围。为人宽滔叫“大气”、大道。而知心人、好拜识那自须“脾味相投”。“慑气”,是说因受委屈或受恐吓的憋气。“输气”指代承受失败之后的丧气。“穰气”形容人脾性和软,窝囊容易受气,受人欺负。无由头受的气是叫“闲闲气”。“寻气”是专故意找麻瘩或闹别扭。
民间广为流传的《嫑生气》顺口溜如是道:
人生就像一场戏,今世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人人都该去珍惜。
为点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
人家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没人替。
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
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
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而拿味气论品行道德,应该是陕北话尤其精细、尤其稀罕、尤其了得的路数。例如在吃食及为人处世方面幼稚的不成熟的味道那是“嫩腥气”。比如有强烈刺激味儿的芥末等,是说“呛”“冲”“圪冲冲”“冲得人脑仁儿疼”,也用来形容暴躁性情。把生气形容为“害气”“毬气”“气戆戆gang”“一冒两弽she”的“毬脾气”。腥臭气是叫“骚气”,如尿骚气;也暗指无关痛痒的某种侮慢,所谓“尿脬打人,疼唣不疼,骚气难闻。”“跑味”也叫“走味”,既指吃食泄气也会引申到说人的做派。人的面色神态的“气色”也说“色气”;贬义说的“毬色气”,是形容人猥琐、不上进、“没态骸”等等。“气数”,一般指气运、命运。“气长”意思是葆有的活力和生命力延续而久长。“气团”“气圪泡”“气包蛋”,是指不争气、惹人生气、没出息的人。“看那也不是蒸糕的气”,这是成不了气候的预测和料想。“一肚子兀的气”,意思是无处发泄的窝囊气。而“臭得出味嘞”一句,一边是说东西腐败恶臭至极,一边却是指作事手段糟糕以及人品“日脏”卑劣的行径。
在描状和揭示负面人性方面陕北话是极具批判精神的,类似“小里小气”“小家寒气”“圪酸小气”“浪里浪气”“淘声斗气”等等熟语,盖为以气言人,言微旨兴。
“人味”,这是陕北人创造的一个意味深长、惊世骇俗的表述。既直指仁风礼至的“人情味”,同时又褒贬分说有没有“人味”,“人气行不行”“算个人”与“不够个人”,这一道德山峁峁上的岔路口。
在平常生活中,我们无妨偶然会闻见布头儿烧燎的味气,那是一种不见火头,只煨火燎烫,“焦糊涂烙”“燎毛凅癴”,刺鼻咳呛的难闻气息。陕北绥米一带的老百姓生乍生就套用“烧布味”来刻画和讽刺那些在点点丝丝、不值当的“小节意思”上龌龊作事、尴尬为人。往往沾酱醋的光,落下打瓷坛的名声。即便只是些不甚检点的零敲碎打的毛病和没情形的出格和丢丑,居然使唤如此辛辣和严厉的修辞手段,其道德评判的尖锐可见一斑。
好像柳青曾说过,他就最讨厌有“烧布味”的文人。那些在名利和处世等方面“细细丝丝”,那些“想吃油糕怕油嘴”,那些“水腥塌气”“毬毛鬼态”,那些“鬼溜乞势”“偷私圪搲”……凡此种种不地道的“恶水”人事,黄河畔长大的硬气的刘老汉,自必小看和恶臓到忿忿不消。
“不寒不热神荡荡,东来西去气绵绵。”陕北人凡事会品,每每细发品验、玩味以至于确认,居然并不过分依赖眼睛去看,只相信和依靠感觉,因此经年累月使得在烟火生命里熬煎的心灵变得更透彻、更纯粹,如此使得他们的人生也更有滋味,更多彩,更囫囵可见。在陕北人的理性世界里,人是似乎由各色各样独特的气味组成的,穿过芸芸众生若隐若现、如云似雾一样的“味气”,通过抬举和赞誉或者不齿和鞭挞,以图直解人心。
难 癨
吃五谷杂粮,人活一辈子没有不生病的。人生无常,任何一个生命自降生之日起,生老病死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七病八难依旧是每一个生命在所难免必经的“山水圪岔”。
那么病这东西,究竟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陕北人说病的成因有自己的理解和说道,“胎里带的”,是指先天遗传;“染上的”,这是外部环境“作造”的。内在病因一是说“病是吃出来的”,少吃没喝和瞎吃瞎喝都在份内;再是“气下的”,这一条条正符合古中医理论:“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素问·举痛论》)。
“疾病”,在陕北人口话里不见有说,惟留有一个“病病疾疾”的熟语。《玉篇》说疾,患也。病在《说文》解释,“疾加也;疾甚曰病”。我们常说的疾病原来是有所区别的,疾是不适小恙和“残气”,病为身体郁积下来的较大的麻瘩、痛苦和熬煎。
陕北人常把生病叫“害病”,害病的不适和疼痛是说“难癨”。除了流行性瘟疫等传染疾病,多数是因积劳成疾所致。千百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概称自己是“受苦人”,日月恓惶,看天吃饭,费辛费苦不算,主要须得养家糊口,又少有口粮,积劳成疾在所难免……“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经年累月一条条壮汉几掺凑、几圪榄子免不下便挼(ruá)成些弯腰背锅的“病罐罐”、“病佬佬”了。
“树有圪节长疤,人有头疼脑热。”旧庚儿,陕北人把因招风的感冒发烧叫“风发”“风冒”“风头脑发”“一吷二念三风发,四吃好的五挨打。”是根据打喷嚏次数来推断是否生病。眼睛近视叫“近觑觑”,耳朵失聪是说“耳背”,聋得厉害那就“十叫九不应”;手脚受凉抽搐叫“鸡爪风”。伤寒疟疾叫“打摆子”;拉痢疾叫“跑肚”“拉稀”,把腹泻尤其严重的流行病“霍乱”是叫“忽喇症”,所谓“好汉怕得三泡屎”。胃酸反流说“烧心”,消化不好是“生食气肚胀”;气管炎叫“喉痨”,盲肠炎说“拐肠子疼”,“痉挛”是说“鬼抽筋”。西医的动手术多说“开刀”;相思病是说“害心病”,“性病”是说“脏病”。“要命病”,如癌症一般说“起瘤子”,食道癌旧以前说“噎倾”。最多只说“赖病”“不好的病”,这是老百姓留心注意着的“口德”。
“生疮害病不由人”,自然,普遍认病也认吃狗屎命。缺医少药,所多的病通常是靠“对敷”和“抗”。“病串着命”,抗过了,枯木逢春;若实在抗不过则无奈任随病入膏肓以至于呜呼哀哉,米脂俗话里有一句:“艾崇德(晚清本地名医)的药子也贴不过迲嘞”,那意思暗示家属去抹捋“棺木老衣”。
陕北口话说“小娃娃不藏情”。“娃娃不蹦,肯定有病。”碎娃娃尚是“水泡泡”“气呵呵”,又不会言传,一但患病自便上抓铙搲、圪檛檛啼哭闹阵。特别是“怀抱抱”娃娃,易惊风,易发热,易夜哭,防水痘,防麻疹,防蛔虫,怕吐泻,怕咳嗽,怕得小儿麻痹症……总之任病都“怕得咬指头”。若是家里小娃娃得病,汤水伺候,冷热无措,昼夜难宁。大人且忌讳言病,只委婉着说“变狗”“不乖”。而各自有病只说“憋合”、恶心、发软、“不应自”或者谑称“照窑顶着嘞”。婆姨们妊娠期怀身带肚“难癨”的一串子反应,陕北人叫“害娃娃”,不以为病,只道“嫌饭”,盖言“有喜”;“坐月子”遭下的病病疾疾笼统称“月地病”。“当梁”的男人和年迈的老人诉病多说“脑疼病”“肚子里的病”和“腰腿病”。有一种浑身发软的布病是叫“趴场病”;寒邪出疹、心腹绞痛的羊毛痧,叫“羊毛疔”。而说不清,道不明因由的怪病一般是以“邪病”来疗治或禳镇。过去,陕北人往往把精神失常的“精神病”都说成“神经病”,狂躁的又叫“癔病”,而按现代西医理论,两者完全是两码事。
“看病先看脸”,陕北人多从眉脸和气色上察看,如眉脸蜡黄、两眼无光、肿眉膖(pang)脸、痴槑圪呆、黑干憔悴、棉圪咳咳、蔫头耷脸、没精没神、病病怏怏等等都是形容“容颜不好看”“容颜也下来了”的验兆。
若是家里人得了重病可是天大的事,即便再穷得咣噹响的人家,“挽锅卖风匣”“破心沥肝”也得寻医问药,以求药到病除,妙手回春。
“大病要养,小病靠抗。”不像富实人家“得病乱投医”,寻常人家一般的小病小灾,总不以为然,对对付付,强忍硬抗,熬煎延日以期烟云消散。
“肠肚勤涮,滚水一碗。”老陕北人“解(hai)不开”养生这档子事,也没类似的概念,当然主要是没条件。含糊的、下意识的保健,常常也是来自上辈子人避凶趋吉的身体经验总结,比如流传在民间的一些常识性的防病口歌和理念:
“少吃多香”“心宽体胖”“气大伤身”“吃药不顶息病”“吃要暖,穿要宽。”“先睡心,后睡眼。”“冬睡不蒙头,夏睡不露肚。”“水怕脏,人怕黄。”“苗靠粪长,人凭气活。”“大蒜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饭前一碗汤,胜过好药方。”“饭吃八成饱,活得寿数高。”“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头对风,暖烘烘,脚对风,请郎中。”“休管伤风不伤风,三片生姜一根葱。”“人是铁,饭是钢,不吃不喝没‘抗障’。”“一碗饭三滴血,三滴血一滴㞞(song成年男子精液)。”“恼一恼,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笑口常开,百病不来。”……陕北婆姨即便思谋着心疼一下家里的“顶梁柱”,“窝大十口”,实在拿不出东西给男人“吃偏食”滋补,到底还是“有心怕个没有的”。于是就有心眼聪明的捏造些许的“忌须”出来,例如有点精气的饭皮子(米脂),安顿小孩子不能吃,谁吃谁长大就是“虚说鬼”(说谎者);猪羊的腰子(肾脏),小娃娃万不可动嘴,吃了就会“懒腰”。想想,这是何等的良苦用心哦。
陕北人祖祖辈辈心里圪念着,口上提调着,日常留心着。开窗通风,洒扫洗涝,豁晾铺盖,除鼠灭蝇,吃斋念佛……每年正月十六黑地的打烟火“燎百病”,开春宬人窑洞里的“打醋坛”,无不体现着消毒祛邪的卫生意识。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受苦人”那里,“动弹”(劳动)跟锻炼的概念几乎是同步的,他们断然再没有剩余的精力和心劲格外去跳弹勏劽(bulie),但甩胳膊扬腿,搓手跺脚,咳浠噡嗽总是有的。得空踃起脚尖站在硷畔上心旷神怡眺望一回,算是“眼亮”,赶集遇会一天平添“散活”,庄前地头走走串串不叫散步,居然称为“散心”。
小时候的印象中,冬末寒天一群扯皮露肉、憨说憨道的碎娃娃在烂窑前的圪台上“晒太阳”,纷纷抢占阳光充足的地场。
“久病成医生”。除了警觉的预防疾病意识,同样的,陕北人一般性的医疗知识也多是出自上辈子口传心授的“医谚”“偏方”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病患品验和警训等途径。
譬如:“小窟窿不补,大窟窿得尺五。”“夜里磨牙,肚里虫爬。”“消肿头,趁热揉。”“牙疼不是病,疼死没人问。”“风冒不是病,不治要老命。”“泻肚子不用医,困饿到日沉西。”“背无好疮”“是药三分毒”“十人九腰疼”“十老九病”“伤筋动骨一百天。”“针灸拔罐,病去一半。”“好话怕的冷水浇,好汉怕的病缠倒。”“气不走成病,血凝住成疮。”“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男怕脚肿,女怕脑大。”“老怕伤寒少怕痨。”“病怕没名,疮怕有名。”“丑病不妨医生”“三肿三消,预备铁锹。”“病人炕上卧,死人满街跑。”“医不自治”“紧病慢医生”“名医不治心病”“聋子治成哑子嘞”“好药难治冤孽病”“偏方治大病”“药要用对,不一定要贵”“泻药轻煎,补药浓熬。”“看病般般大,药量分高下。”“三分治,七分养。”“中医问屎,西医听屁”“人有四百病,医有八百方。”“炕上有病人,地上有难人。”“久病床前无孝子”“忙人事多,病人心多。”……
《书经》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的终命。”病的后顾之患是折寿,而“善善从长”依凭的正是一颗无微不至的“佛心”。
“谁家也不挂那无事牌”。兵来将挡,水来土坉,生命跷过病的“山水圪岔”,自便就是大路,是坦途。纵使有个“七灾八难”,只要不讳疾忌医,寻根疗治,把心放宽,用心将养,无妨平复如故,柳暗花明。天有木火土金水,人有肝心脾肺肾;天人合一,顺应四时,平衡阴阳,气血和中,以至神清气正,祛病延年自不在话下。
“无病不知有病苦,有病方知无病福。”人啊,往往病好后才知福惜福。“无病一身轻”,这样反观生命之重,竟是一场举重若轻的跋涉流浪与修行怡养呢。
穷通生死不惊忙——陕北人说“生死”
生命,是一个可大可大、关天关地、没边边没沿沿的话题。
花有凋落,潮有涨落,宴有消散,月有圆缺。生命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看起来包含着活着和死去两厢意义,其实拢共还是一个问题。生命诞生的偶然和玄秘、成长的周折和神奇以及归宿的迷惘和无奈,加之到底还是因为心有不甘,于是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活着的追问和对死亡的反思从未有过歇息和停止。往往从社会的、宗教的、哲学的以及艺术的方方面面的角度来解读,来感悟,来启蒙,来劝谕,以期企图慰藉困惑、不安或恐惧的灵魂。
古人论生死很早,深深浅浅,真真幻幻,也形形色色。最看得开、最超然的当然要数庄子了,这老汉汉就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意思是说大自然给我身体,用生教我操劳,用老教我清闲,用死教我安息;所以称善我能活着,也同样称善我的死去。
当代人谈得最精到的,我个人以为当数曾经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著名作家史铁生。记得先生在他的《我与地坛》里是这么说的:“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荣销枯去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生老病死,虽说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和无法抗拒的规律,虽说悦生恶死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无论如何死总是哀伤的、阴暗的、凄冷的、晦气的、沮丧的,到底比不得生的明丽、祥和、自在和喜悦,不会因为你喜欢或不喜欢,意愿或不意愿,论谈或不论谈就没这么一回事了。
《西藏生死书》上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通常时候,国人很忌讳好端端着来谈论死的问题,尤其杜绝牵扯到亲近的家人,要是涉及到各自那更是讳莫如深了;就好像一张口说叨一个死字,冥冥之中立马会有什嘛不测在悄悄凑近。说生道死,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毕竟是心存忌讳和不安的。
“油尽捻子干,人死如灯灭。”这是我们陕北人固有的一种死亡基本认知。透过这一观念,我们照例可以从老百姓现存的习俗俚语中,依稀可以寻找到陕北人生寄死归的生命态度和生命觉悟的一些端倪,并且衍生出这一方土地上好些深情底理的东西。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兵燹杀戮,瘟疫疾病,饥寒困苦……千百年来无以数计的天灾人祸曾经毁荡和洗劫过的苦焦的黄土地,祖祖辈辈的陕北人历经了多少生死存亡、生离死别的烤炼和洗礼。如何看待和面对死亡,恐怕在陕北老先人们的血液和神经里,已然流淌和根植处变不惊的冷峻从容和哀死事生的遗传基因。
对死亡的表述陕北话有很多委婉的说法,最多的是说“殁了”。通常采用隐语来暗示和隐晦以此回避直白直道。一是表示对“死者为大”的尊重,再则是顾就其亲友的哀恸之情。
常听的表达有,走嘞、去嘞、过世、下世、人过迲(ke)嘞、人不在嘞、咽气嘞、合上眼嘞、归天嘞,升天嘞等;小口少亡多叫老千、冥故儿、夭折、短折,也说失脚嘞。意外亡故常是说碰坏嘞、跌坏嘞;自行了断的是说寻短见、寻无常、自造不祥。类似以上两样突发性、不寻常的死于非命的罹难,陕北人总称为“冷事”。老年离世则多说老嘞、老溘嘞、百年嘞、成仙嘞等。也有少数带有轻巧的戏谑色彩的一些说法,譬如不出气嘞、瞪眼嘞、展脚嘞、蹬腿嘞、撒手了、停当嘞、命尽嘞、天数尽嘞、回老家嘞、不再遭罪嘞、阎王请走嘞、见阎王爷迲嘞、解脱嘞、上山嘞、入土嘞等等等等。
记得,对死亡有一个最为异样的说叨,不粘扯任何伦理情感、多少有点隔岸观火的意思,当然有时候偶尔用来自嘲,就是这个“挃故儿”,其中的挃居然是收割的意思。而对宿有“过结”、恨怨或者刁蛮黑痞的死掉,给出的说法自就忿然了,是说“死殄下嘞”“孽罐子满嘞”“害不成人嘞”“老天爷睁眼收得迲嘞”“沤粪嘞”……
老人弥留之际是称“回首”,所谓“好回首”,说的是临终时不受罪、无痛苦的安详,自然也包含着满堂儿女伺奉在侧的放心和安然。不少上了一定岁数的人,甚至早早便事先打好了墓葬,备好了棺木老衣,安妥后事,备而不用。“来吤我嚎人,走时人嚎我。”举行丧葬祭祀是叫办“白事”“白羊肚手巾红腰带”“女要俏,一身孝。”陕北人信崇象征干净纯洁、超脱凡尘和至高神圣的白色,传说那是春秋之前的白狄部落孑遗下来的一种习尚。
“清水河看到底”“百年换尽满城人。”“人吃土一辈,土吃人就一回。”道出的是人跟自然的休戚与共的依存关系和终极辩证。
“生老病死”“生、旺、死、绝”“先注死,后注生。”“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至。”“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尽人事,安天命。”……一切生死福禄什嘛的都是交盘给老天爷做决定的,这是陕北人较为普遍的认命和平和心态。
“命数是个定数”“人活一口气”“人瞎活着嘞”“黄泉路上无老少”“病人炕上卧,死人满街跑”“好汉死得马上,艄公死得水上”“好人不长寿,害祸一千年。”“无常一到万事休”“养儿为防老”……这是陕北人对充满变数的世事无常、生命无常的思想预备和认忍心理。
“活人活熬煎嘞”“活人一世麻烦一场”“活不成个人”“死迲容易活迲难”“不到大限命不尽”“多会儿死了就轻省了”“死了就了了”“早死早托生”“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人活得就是个盼儿”……这些俗话无疑反映了“活气不好”的人们沮丧、无奈和彷徨,祈死逃避求以解脱和拯救,“走哪算哪”,随波逐流。
“死,是一步涩路”“宁教世上磨,不教土下沤。”“蚂蚁也贪生嘞”“好死不如赖活着”“八十佬梦见办老伴——死心不尽。”“谁哪能撂下这花花草草、红火烂灿?”“怕也怕死嘞”“怕又怕不下?!”……贪生怕死自然是万有动物的本能,而不屈不甘、只争朝夕就是活着最大的人权。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抑郁的是人生短促而无奈。“来如春梦几时多?去似朝云无览处。”白居易纠结的是人生的美好如梦幻泡影。自然,朴朴实实的陕北人不会像写文弄诗的古人那样慷慨陈词、刚巴硬正说话,他们也不会细思极恐地发出“有今儿没明儿”无谓的长吁短叹,也不会死搬硬套儒学的安生,佛家的轮回,道教的长生那些谈玄说妙。面对时光的迅逝,生命的虚幻,常常轻描淡写着形容为“眨眼放屁,一忽时儿,一辈子其实也就一忽时儿。”在他们以为死是生的大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关口,无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官庶富贫,只有死这事情,才“天公地道”。“赤叾(du)子来,浑圪溜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自然本然地秉持一颗乐道安命从容不迫的“平常心”。
陕北话里创造出“一死二活”这样一个神奇无比的词句,强烈表达出与命运争竞的不屈不挠的坚决意志。有时候甚至敢于豁达地轻蔑和自嘲死亡,“命在骨殖里嘞”“死无非就是睡了个长觉”“大大划个圐圙,命交给老天。”“发了个谁?活了个谁?”“土埋到半截上来嘞”“生死看淡,毬也不蛋。”……
看清事情不过是取舍,看懂情爱不过是聚散,看穿活人不过是名利,看透生命不过是无常……
“惜生”,对啊!就是“惜生”这个词,诠释了陕北人对于追寻生命意义最为妥切、最为温暖、最为通彻的定义。“觉悟无量生死行,逮得不退智慧门。”珍惜身寿福报,自救自赎,正是如此的向死而生、悦生恬死的生死观念,折射出了陕北人无畏豪爽的胆气、盎然天趣的雅量和远望无遮的情怀。毋庸置疑,照例也彰显了他们口喋莲花的语言智慧和熠熠闪光的生命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