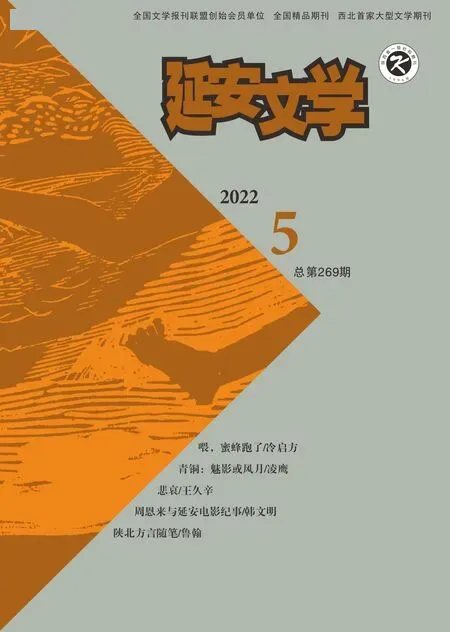乡村生活也多彩
杜海瑜
乡村的生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单调寡味,日出而作,扛镢种地,日入而息,抱头大睡。并不是只有人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生活还是丰富多彩,值得回忆的。
听古朝
乡间的“说古朝”,就是讲古朝古代的故事,而听这些故事,叫“听古朝”。有人总结它:不是相公招姑娘,就是奸臣害忠良。农村忙,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各有活计,说古朝只能在农闲夜晚进行。村人的聚集场所一般是大队部和人缘好的人家里。说古朝的场所一般在说者自己家里。听古朝的人男女老幼都有,农村人没有条件也不讲究卫生,脚汗味臭气冲天,咳嗽吐痰,或旱烟锅子嗒吧嗒吧,或大喇叭旱烟卷吞吞吐吐,烟雾缭绕,呛得人嗓子疼、眼睛酸。众人一走,得开门开窗通风放烟,打扫通炕脚地,不挣钱,光出力,谁愿意这般让蹂躏?但自有人愿意,说者愿意,他肚子里有货要往出倒,不往出倒,会憋得难受,所谓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且听众会给他尊严,得到敬仰。
论理,说者是付出,听者是收获,听者应该相应地贡献出与说者相适应的付出,可是就现实情况而言,这说古朝者的地位比较尴尬。说者,讲也,讲者或坐前,或居中,若在前,听者在后拥坐,若在中间,听者团团围坐。讲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侧耳倾听,如痴如醉。
其实说古朝的人基本都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角色,能看书认得字就算有文化了,多数大字不识,只靠听得别人讲来就热蒸现卖,讲张飞大战程咬金,讲关公大战尉迟恭,驴唇安到马嘴,还讲得唾沫星子乱飞,能记清关口将名就算有水平了。
记忆中在村子里听过三人说古朝。
这三人中当数当庄的刘廷岐讲得好。他在西安上过技校,在大饥饿时回村,开过手扶拖拉机,会修发电机,戴一副比瓶底圈还厚的眼镜。据说他珍藏着一些古书,但秘不示人,这些封资修的黄书当然见不得人。他讲古朝小范围,听众是在本村有些档次的人,大队队干或在外工作的本村人,那些懒汉二流子偷鸡摸狗之徒难进他门。我与他儿子延平、候平是小学、初中同学,故得以在他的新砖窑里享受殊荣,听了几次古朝。他讲得抑扬顿挫,四六句子随口而出,故事有根有蔓,村人们称赞他“好钢口”。
我的一个堂大伯在青化砭战役致残右眼失明。他嗜爱讲古朝,但不识字,为此他便借来古书,请来我们这些学生诵读,他侧耳倾听。他的记性甚好,每集都去给人讲古朝,为吸引听众,提高积极性,还备香烟散发。不知咋的,他被小偷盯上,连续几个月领下的残疾金在讲古朝时被摸走,为此家人颇有怨言,但他痴心不改,逢集还是直奔街上。
还有一个是张三的丈人。他住在东川永坪镇,离我们村翻山走小路二十来里地。张三老婆是青光眼,见光流泪,干不了活计,光景过得恓惶,老子便隔三差五送粮送钱。听说他来,张三的土窑里便挤满了人。在昏暗的窑洞,我们盯着跳跃的小油灯,全神贯注听张三丈人讲古朝。老汉也有眼疾,不知是眼泪还是鼻涕,过一会儿拧一把,抹到土墙上。
我听他们讲了《五女兴唐传》《大小八义》《瓦岗寨》,以及唐代薛家三代《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古朝。
我至今记得他们讲的战斗场面:
里三层,外三层,一气围了十八层,刀枪剑戟一片明,一家打马向西行,一家打马向东行,回头回来见输赢。
杀杀杀,战战战,杀杀战战不停缓,直杀得人仰马又翻,直杀得天昏地又暗。
讲姑娘的容貌:
粉嘟脸,红口唇,满口白牙碎纷纷,眼又花,鼻又正,一对黑眉爱死人,越看越爱越称心,不由得指甲抠手心,不由得眼睛瞪得瓷钉钉,不由得憨水淌下一大楞。
讲武将:
头似柳斗,眼赛铜环,拳头一捏炒菜盆,脚片一顿像门墩。
讲相面:
前胸饱满后心平,两耳垂肩有官形,不是宰相是总兵。
左肩高,右肩低,家中必定有贤妻。
还有描述快步:
七踏踏加一踏踏,扑踏踏。
说古朝的三人早已作古,但我们同村的人到一块,谈起童年的趣事,便想起历史上那些文臣武将陪伴我们度过的漫漫长夜……
听 书
听书是每个陕北人都熟悉的事。那时的听书是集体活动,书匠(我们都这样称呼说书先生)都有眼疾,通常是在春秋两季进行。每次都由邻村人或以驴车或以自行车,完后再由本村送到下一村。
春夜,大队部窑面上的电灯雪亮,村人们拿着大凳小凳在院里依次坐下,虔诚地盯着书匠。秋夜,寒风透心,书场搬在窑洞,窑洞容积有限,待不了五六十人,故而有人便早早地进窑占位,免不了有铁杆书迷在院里边跺脚边侧耳倾听。
书匠坐在高板凳上,给膝盖上绑上竹板,晃动腿部,弹起三弦,敲响竹板,三弦便绷绷响起,歌声便也随之响起:
弹起三弦定起音,
见了乡亲我心欢喜;
开口说书见真情,
我今天来到刘家坪;
刘家坪人有水平,
我说的不好多担承。
这个开场白是必有的安客程序。哪个山上不长几棵歪脖树?哪个村里没有几个难缠人?说了上述话,谁还抹开脸面砸场子。而后便言归正传:
我不说三国刘关张,
不说大唐乱辈分
不说精忠岳家军
大败强敌金兀术……
这是引子。而后书归正本,说到一个钟头时光,说书先生口干舌燥,听众也有的尿急,需要中途歇息时,唱曰:
高高山上有一棵麻
两个老鼠往上爬,
左爬右爬你慢慢爬,
我停住三弦喝一杯茶。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说的一个段子叫《刮大风》,超现实的浪漫,夸张,摄人心魄:
哎——昂——
春天刮风暖融融
夏天刮风热烘烘
秋天刮风凉森森
冬天刮风冷死人,
儿马风,叫驴风,
崖崖洼洼母猪风,
刮倒大树一摆溜,
刮得小树无影踪,
刮得碌碡耍流星,
刮得碾盘翻烧饼,
啊呀呀——
好大的风!
他们说唱结合,绘声绘色,根据书中故事人物说话不时变换声调。男人说话则愣声愣气,女人说话则细声细语,笑起来声振寰宇,哭起来悲天恸地。婆姨声,女子气,惟妙惟肖,幽默风趣,引得一阵阵哄堂大笑。
由于是公派,他们说的都是歌颂新社会、移风易俗的段子,如歌颂新社会的《翻身记》,鞭挞包办婚姻的《小女婿尿床》,针砭时弊的《懒汉种田》……由于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所以深受群众喜爱。
说书人在我的印象中永远是肩背三弦袋,手拄打狗棍的形象。听大人们说有个叫韩起祥的说书匠给毛主席说过书,还说当时延安的说书匠大多是他的徒子徒孙。有一个说书匠是蟠龙镇老庄村刘家的女婿,来村里说过几次书。有一年说书匠来说书,遇到连阴雨,天留人不留,他住在大队部,一日三餐吃派饭,由派吃的接去送回,晚上我们沾光多听了几本书,可白天听着滴答滴答的雨声寂寞难耐,说书匠便拿出一盒扑克,邀我们玩,那扑克上有针扎的小孔。当时我们并不懂这是盲文,还以为他有特异功能,对他佩服之至。
看 戏
我们看戏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公家的各种庆祝活动,一个是庙会上的传统折子戏。
记忆中那时各种庆祝集会不是很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节日,我们在学校的舞台上或学校或公社举行纪念活动,程序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先是领导讲话,而后或独唱或合唱革命歌曲,接着为活跃气氛,增加趣味性,会表演“三句半”或唱一段“眉户戏”。“三句半”是四人一组,持鼓、钹、锣、镲在台上气宇轩昂地转一圈,然后在中央站定,开场白依次:
鼓者:锣鼓咚咚敲起来,
锣者:我们四人来上台,
钹者:学的说个三句半,
镲者:试试看——
而演的眉户戏通常是《四老汉学毛选》。同学们扮演的四个老汉弯腰驼背,右手拿着吊着荷包袋的旱烟锅,左手背腰,头拢三道道蓝的白羊肚手巾,留着山羊胡子,穿对襟上衫,大裆甩裤,打绑腿,蹬圆口黑便纳鞋,活脱脱四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诙谐的对话、夸张的表演,总逗得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我也曾上台表演过一场戏。那是我上初二的时候。这是一出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开门办学的戏。我脸上被涂脂抹粉,扮作考生,坐在桌上没发一言。
民间的看戏是庙会。从我们蟠龙川到子长安定方圆二百里供奉的是黑虎灵官,由周边固定庙会轮流执事。轮值地派四个身强体壮的后生到几十里甚至百里之外的上届庙会去请,用老轿毕恭毕敬地抬回,这叫“请神”。庙里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神像,戏台。这大概是自古神仙皆寂寞,众生想让神仙开心,敬神就要想神所想,故而有庙必设戏台,每年都要给神唱戏,取悦于神,好让神降福这方田地,庇荫这方田地。当然,忠实的信徒们便也在服侍神神之时,可以物质精神双重享受,放开肚皮吃喝,放松心情看戏。就是有些不轨行为,不雅举动,比如三只手挤来挤去偷人钱包,比如光棍汉摸了人家小媳妇的奶子,青皮后生与姑娘在夜幕里投怀送抱……神仙也慈悲为怀,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一概不予计较。
庙会必定要唱戏,一般请的是山西的晋剧团或关中的秦腔剧团。这些剧团较之本地剧团有一个共同点:民营、价格低、好侍应、戏本多、灵活。
庙会实行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办会人员和看戏的免费吃喝,当然没有山珍海味,一日三餐大烩菜白馍绿豆汤。吃喝和包戏的费用来之于庙会范围内的群众,也可谓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庙会有总会、分会,会长负总责,分会长负责自己附近村的布施收交,故而分会长基本是三四个自然村有点名气且热心服务之人。上布施实行自愿的原则,但积极主动的少而又少,所以需要分会长受累腆脸挨家上门收交,数量不限,半升一碗粮食也可,三两块现金也行。神仙普渡众生不嫌穷富,敬神要心诚,心意到了,喝凉水也暖心。
看电影
我们看电影有两种:一种买票,一种免费。
买票看电影只在镇上。起先在公社大院,大人一毛,小孩五分,自带板凳。由于环境影响,音像效果不好,管理比较困难,窑洞顶上站一圈人,管理人员撵下去,一会儿又爬上去,“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要闹到剧终人散。后来镇上盖起了宽敞的封闭电影院,并配备了木花椅,凭票进场,无票靠边。
免费看电影是在驻镇厂矿企业和各村。我们当地驻有三家国有单位:蟠龙煤矿、贯屯煤矿和孙台水库。一般情况下,只要公社放映室回来新影片,首先要先在这些单位放映,而后才在各村轮流放映。我记得第一次看《洪湖赤卫队》是在距我们村五里路,还要翻越当地最高的柏树山的孙台水库。从此我们开始学会《洪湖水,浪打浪》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并唱到如今。有一次看电影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那年我12 岁,随村里的大孩子到二十里外的下坪去看电影,谁想一阵狂风暴雨迫使电影中断,我随大孩子们向回一路狂奔,临近孙台水库坝梁时,有一处塌方堵住了路,我们在虚土中艰难攀行,瓢泼大雨将土和成了泥,我丢了只鞋也不敢停留,在漆黑的雨夜追赶他们,手脚并用翻过柏树山,待后半夜回到家雨停云散,我却成了个泥人。
贯屯煤矿邻近子长,是千人大矿,有专职电影放映员,几乎每个周日晚上都要在煤矿广场放映电影。春夏秋天气适宜,我们去的多,虽然二十五里路不算近,但由于总是怀着迫切的心情,并不觉得遥远,也不觉得苦累。
蟠龙煤矿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较之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贯屯煤矿,也算历史悠久。它的矿部设在蟠龙粮站旁边,有刘坪、西洼、拓家沟和四咀四个矿井。其中刘坪矿井就在我们村,也有三四百名矿工,占地足有上百亩。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从记事起,每月至少在这里看一场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就是从这里镌刻在我的脑海。
我们村每年都要放映三五次电影,但由于距公社五里路,按路程有近十个村子近于我们村,加之村里的经济和名声尽皆不佳,轮到我们村放映的几乎都是旧片。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充满着期望,心情激动着。村里派手扶拖拉机去接电影放映员和放映机,有时先在别村放映,大家直到夜里十点多,甚至十一点还都在等待着。
在本地,可以不知道公社书记是谁,但没人不知道电影放映员是谁。放映员享受着非同一般的殊荣,车接车送,当然手扶拖拉机也是车,自行车也是车。放完电影还有一顿让人垂涎的晚餐,或鸡蛋柿子揪片面,或烙饼粉条肉烩菜。在那个年代,这就是龙肝凤髓,普通人一年也吃不上一顿。然后,安排暖窑热炕新被新褥就寝。唯恐得罪,下次不来,就断了全村人的电影梦。
行门户
亲朋过事情,相关人员行门户。门户的原意是正门、房屋的出入口,后来引申为派别、宗派,门第,或者是婚俗伦理婚配观念。在我们陕北更进一步,先引申为参加婚庆宴席,后演变为一切红白事的宴席,顾名思义,行门户,就是参加红白宴席聚会。我们还把举办红白事宴席叫做事情,把办宴的过程叫过事情,当然,中国是礼仪之邦,来而不往非礼也。赴宴不可空手而去,需带馈赠礼物,后来发展到或将物折钱,或现金馈赠。今人呢,撇开古人还要拱手推让的繁文缛节,干脆摊开账本,请君出钱。
传统行门户的目的应该比较纯粹,是参与、见证亲友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一种形式。维系感情的是亲情,传宗接代来之于血缘,与亲友欢聚一堂,把酒言欢,何其乐也!可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人闻听亲朋过事情邀请行门户便心如鼓捶。本是好事,但变了味。有的人爱过事情,家中有事必过,甚至没事,不惜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创造条件也要过事情。正月孙子满月、三月迁埋老坟、五月暖窑、七月自己过生日……以过事情敛财,坑了亲朋好友,鼓了自己腰包,大家虽不胜其扰,却碍于情面,慑于陋习,只得如此。有人看别人以此牟利,便也效仿,于是,家贫亲戚多者便难以承受,只好能躲则躲,能溜则溜,有的干脆记“主收”,意谓主人收去。来而不往非礼也,便为此变脸,老死不相往来。
门户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红事、白事。
红事是指红火热闹喜庆事:结婚、满月、过寿、合龙口;白事则指披麻戴孝的丧事。结婚门户须事情主家邀请,贸然赴宴有些唐突,主人恐有不便。亲朋诞下儿女,须先送喜汤,名曰汤,实为乳妇在月子可食的鸡蛋、挂面,一般非嫡亲,不送汤不请赴满月宴。按风俗,上七十岁方可过寿,过寿来客比较杂乱,一般来者不拒。在陕北,起楼盖房是人生大事,为感谢工匠及亲朋鼎力相助,主家遍请亲朋四邻,行合龙大吉,给工匠披红,爆竹声声,笑脸盈盈,庆祝房屋建成。这与城里人暖窑,庆贺乔迁之喜同为一理。
闻知有丧,便蒸白馍送去,后进化为携带香纸到灵棚前烧香叩头。按风俗,若主家把香纸收下,说明这个事情待他,他可来行门户。若不收香纸,说明这个事情不需他参与。主家一般会委婉解释,户小人单,一切从简,谨请体谅。尽管如此,风俗使然,被拒者亦不尴尬难看。
乡里的事情是早晚两顿饭,若在十里开外的外村行门户,是需第一天动身,在主家过夜。若在本村或邻村行门户,当日才去,早上油糕饸饹面,中午是正席,俗称八碗。传统八碗有软硬之分。软八碗是将烧肉、酥肉、丸子、羊肉等八种肉置在一个碗中,每人一碗,各吃各碗,吃不完还可打包带走。本是贫困所致,想不到却是最卫生、最经济、最科学的吃法。硬八碗呢,耗材费功,八碗八种,块大肉肥,还后加一碗红烧肉,吃者绝对自由,筷子可如蛟龙在碟盘里面搅江翻海,各瞅所需,各挟所爱。不管软硬八碗,后上一盆添菜,其实是烩菜,因是八碗之余添加的菜,故称添菜。对八碗我倒不觉什么,但对添菜情有独钟。将所用蔬菜全部开水焯过,加猪肉腥汤杂烩一起,白的洋芋片,褐的炸豆腐,黄的大豆芽,青的宽粉,黑的木耳,再加一把绿油油的蒜苗,洒几撮红艳艳的辣椒丝,看得眼馋,吃得肚圆。就是到八十年代经济好转,奢靡之风日盛,宴席菜品暴涨一倍,已达八荤八素两汤,而添菜还是一道长青不老的压轴菜。
吃完宴席,事情便告结束,门户便也行完。说一声慢走,道一声留步,或远路亲戚,或本村庄客皆甩手抹嘴打道回府,一切归于原位,但事情过得歪好,主家是否大气,这些老生常谈又在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中相互谈论,这倒不是人们好事,生活在这条亘古不变的川道里,总要在静止凝滞的空气中咂摸出点不同味道吧。
听古朝去,说书的来了,看庙戏去,今夜看电影走,今儿赶集去,我行门户去……这些熟悉的话语,或喜悦,或无奈,但俱是干旱的季节雨点在黄土窝窝里砸下的印痕,真实而清晰,真诚地伴随着我们度过春夏秋冬四季更替。花儿开了又谢,果子青了又红,坟上的草绿了又枯,父老们在这片碧空下,面朝黄土背朝天,吆着牛扬着鞭吼着信天游,悠扬苍劲的歌声引逗得崖娃娃不歇气地接尾学唱。那弯弯曲曲深浅不一的犁沟里的种子,在不经意间便发芽、冒头,焕发出毛头柳树般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