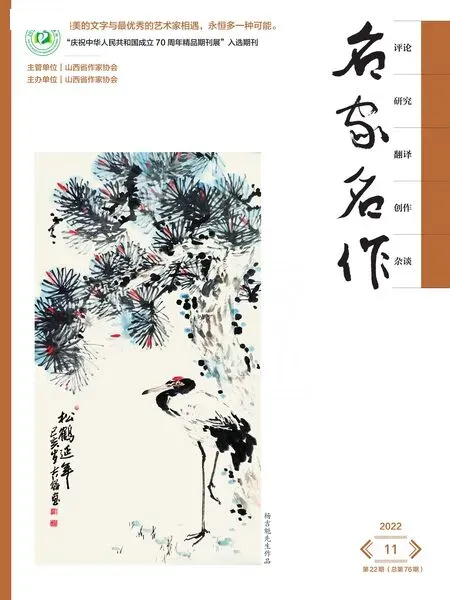假面与迷失的自我
——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下的《他人的脸》解读
韩星鹭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3年)是20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其于1936年在马林巴德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提出镜像阶段理论,并将之变迁为1949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并选入其著作集中,指出镜像阶段是主体由于接受了视觉上带来统一性的镜像,结果反被夺取自我的戏剧。
在文学界,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对于分析都市人自我定位的迷失问题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与拉康生活在同一年代的安部公房(1924—1993年)是日本战后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人的脸》(1964)作为其都市失踪三部曲之一,以手记、附录、信件的形式,记录了在从事高分子工作时因液态气体爆炸而毁容的主人公与其制作的假面之间一场关于自我认同及归属的博弈。本文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以小说《他人的脸》为例,分析该小说通过假面这一载体,反映人从意识到他人到认识自己的过程,以及镜像阶段中主体、镜像、自我三者的关系在其中的影响和体现。
一、认同
突然对方起身,以一副诧异的神情走过来窥视我。就在这一瞬间里,我被一种情感严实地裹挟住了。这情感犹如服用过量的安眠药开始生效一般,带着强烈的冲击性,但却又滑溜通畅,尖锐剧烈,但却又令人陶醉,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和谐。或许在那一时刻,我的外壳出现了裂纹吧。彼此面面相觑着,首先是对方笑了,在他的带动下我也笑了。最终我不加抗拒地一股脑儿溜进了对方的面孔中,并很快一分不差地黏合在一起,我已经彻底地变成了他。[1]96-97
在“白色手记”一章中,主人公成功制造出足以仿真人皮的假面,并尝试着戴上假面在镜子前享用晚餐。这一场景可以被视为拉康所描述的镜像阶段典型情境的一个变体。主人公如同六至十八个月大的婴儿,在第一次面对镜子时自发地倾身融入,“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于己”[2]84,并通过对假面的认同,使得一个完备、调和的自我在镜像环境中被构型。
在拉康看来,“镜子阶段的功能就是意象功能的一个殊例。这个功能在于建立起机体与它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2]86。假面作为主人公的镜像,以格式塔方式补足了主人公残破、缺失的面部,令其在镜子中呈现出一个“统一整体的视觉形象”[3],与此同时,又“给‘我’这一不确定实体的主体穿上衣装,将主体隐藏起来”[4]45。当主人公因试戴的顺利而重获信心,怀揣着“恢复与他人之间的通道”[1]64的愿望走出房门时,他发现人们不再如他用绷带蒙面时一般有意识地避让,使其前方总“像瘟疫地带一样预留空间”[1]63。与之相对的,因为假面的缘故,主人公得以大胆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下,自由穿行于人群中且“什么也没有发生”[1]100。这一点变相体现出假面得到了他者的承认,承认他的普通、他的正常,并将其划归为同类。然而,主人公亦隐约意识到,在这一场景中,他是“不在场”的[1]100,正是其本质的缺席使其获得了社会层面的认同,“那使我垂头丧气的虚脱感,与其说是围绕着新的面孔所产生的困惑,不如说是好像看见自己的影子在隐身蓑衣下面渐渐淡化隐没了一般的那种对消亡的忧虑”[1]92。
归根结底,假面这一完整形式终究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致的,正如拉康所言,“在这种外在性里,形式是用以组成的而不是被组成的,并且形式是在一种凝定主体的立体的塑像和颠倒主体的对称中显示出来的,这与主体感到的自身的紊乱动作完全相反”[2]85。镜像并非对主体的单纯复制,一方面,空洞的主体不足以对镜像作出能动反应,相反,是镜像将主体从迷人的幻象中召唤而出。假面先于主人公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用视线吸引主人公的视线,以表情带动主人公的表情,从一开始便掌握了主动权。另一方面,镜像与主体之间的关联是异质性的。主人公自认为假面“容易支配”[1]93,以为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出于自己本意,实却被假面投注在其身上的欲望所驱使,如福原泰平所描述的,“在如同对镜内部的世界里,自己与他者在镜中相互映照,产生了只能相互认同的自己与他者融合的状态”[4]59。因而当主人公取下假面,面对自己的真面,脸上“水蛭窝”形状的瘢痕也失却了绝对的现实感。在主人公眼中,“假面已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东西,就如同水蛭窝是现实的一样。”他甚至自问,“如果将假面作为一种虚假的表象,那么,水蛭窝不也同样是虚假的表象吗?”[1]102可见,主人公已将与己有别的假面误认为是内在的、对等同一的形象,深受身边众人“个人主体‘应该’成为的形象之镜”[5]135和“非言传的意会行为之镜”[5]141的影响,不仅未能意识到二者因镜像的对称属性而天然相隔的鸿沟,反而以假面为中心将一切合理化,自此踏上自我疏离的单行道。由此应验了拉康的观点,镜像格式塔“象征了我在思想上的永恒性,同时也预示了它异化的结局”[2]85。
二、嫉妒
拉康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中指出,“我的形成是以一个营垒甚至一个竞技场来象征的。从内场到边墙及外缘的碎石地和沼泽,这个竞技场划分成斗争的两个阵营,主体在那儿陷在争夺遥远而高耸的内心城堡的斗争中”[2]87-88。自我借助镜像的反射作用而生成,必然是一个“依赖而非独立的建构”[6]63。但同时,自我亦是一种误认的功能,一种想象的功能,使得破碎的主体在镜中照见完整,并维持着主人性可以被占有的幻象。为此主体不得不通过长久持续的争斗,一次次将其从镜像的阵营暂时性地拉扯过来,自我却“只能以渐近线的方式重新加入主体的生成中,而不能与之完全同一”[6]63。
就小说的主人公而言,这场自我争夺战的枪声自其戴上假面的那一刻起便已打响,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推进“恢复与他人的联系”[1]179这一计划,主人公为假面以“弟弟”的名义支付了房租,从眼镜到服装皆依照假面的审美进行搭配,且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增加假面的自信,确认其实际存在。随着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断增强,一种拒斥着主人公的接近,不对主人公“言听计从的独立意志”[1]111逐渐在假面上显现了出来。主人公觉察到,“看来,假面已抛开我的想法而不顾,开始了我行我素”,但主人公并未因此提高警惕,反而“仿佛我自己也加入其中瞎折腾了一番似的”[1]103,沉浸于帮助假面所带来的满足感。直到一次出行中,假面“把我的惊恐抛在一边”[1]117,执意向玩具店店主购买了一把瓦尔沙气手枪,主人公方才意识到:我只不过是打算一边犒劳他,一边在旁边拉他一把罢了。但自从玩具店发生事情以来,已经完全是主客颠倒。哪里是我在拉他一把,相反,倒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惊讶之中勉强跟随在了这如同刚刚释放出来的囚犯般饥肠辘辘的灵魂后面。[1]118
不知不觉间,假面已深入主人公的内部,但这并非主人公所预想的恢复或找回自我,相反,这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充斥着尖锐对立的入侵。镜像哗地拉开竞技场的帷幕,显示出破坏性的本质及足以凌驾于主体的力量,劫持了自我,彻底背叛了主体的信任。然而,主人公拒绝接受失势的真相,坚持认为“假面的人格绝不是像从魔术师的高筒礼帽中蹦跳出来的兔子之类的东西,而应该是由于被真面的门卫严格地控制着进出,以至于只有在没有被意识到时才能跑出来的我的一部分”,盲目地自我安慰道,“无论此时的我与真面的我有多么不同,但我毕竟就是我”[1]119。在主人公的纵容下,假面“越发增加了他的厚度,最终发展到了像是把我团团围住的混凝土要塞一般”[1]141,而主人公将那混凝土视作镜像阶段中“把碎片化的身体包裹起来并加以保护”[7]的盔甲,过早放弃了抵抗,任凭假面恣意行动,无形间交出自治权。在拉康的观点中,“主体这时也不能说自己最亲近的人是外部的人。主体确认自己为外部的他者的像会将自己暴露在无的危险下,但顽固地不承认这一点,也就迷失了自己的本质”[4]47。
于是当假面在与妻子之间“恢复通道”[1]86的计划中又一次不听指挥,将欺骗与复仇的愿望掺杂其中时,主人公已无权干涉更多。由主人公依照心理形态学上“外向的、非和谐的或者具有行动力的意志型面孔”[1]51制造的假面,在潜移默化间早已在主人公的内心刻上了“猎人的面孔”,使得把箭搭在弓弦上向其妻子瞄准的姿势也成了“司空见惯的日常场景”[1]86。在“灰色手记”一章中,主人公戴上假面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对妻子进行诱惑,原是想揭开妻子“菩萨相”[1]50般沉默的、过分宽容的“假面”,却不料妻子欣然接受并与假面开始了长期的肉体关系。面对深爱着的妻子“出轨”的现实,嫉妒最终使主人公堕入流氓化的陷阱,完全沦为被假面所操控的“复仇的俘虏”[1]179。
三、异化
假面将我平稳的日常生活无情地抖搂出来,彻底打碎的残酷举动固然是可怕的,但返回那种没有面孔的、被囚禁的日子却更加可怕。[1]186
主人公将自我交付假面,任其困锁于假面之笼,明知受着囚禁,却认为相较于以真实面孔示人时耸立在四周被命名为“异类”的高墙,当下的处境要好过得多。凭借这一副假面,主人公成功建立了与他者,乃至与妻子的通道,即便方式如此扭曲,从某种程度上却是达成了主人公的预期。然而,主人公意识到,因自我本源性的失落,通道所通往的已是一个陌生的、遥远的他处。“好容易戴上假面,打开了通道,把你邀请了进来,可你却逾越了我,迅速地消失在了某个地方,而我就和戴上假面之前一样,被孤独地留在了原地。”[1]188主人公在手记中对妻子写道:“即使剥去了你的伪善,可你的假面却多达一千张或一万张,依旧会源源不断地拿出新的假面来,而我却只有一张假面,除此之外,甚至连一张普通的真面也没有剩下。”[1]196无论主体如何扮演,都无法改变他人所沟通、触碰的皆是假面这一事实,而作为“我”的主人公,始终不过是一个休假的同事,一个出差的丈夫。因而,当主人公久违地返回家中,他发现卸下假面的自己完全是“一种淡淡的梦幻般的存在”[1]196,无论如何都不能与家这一坚固的实存相融。主人公不禁在内心发出呼喊,“怎么着都行,反正我想赶快游回到可靠的陆地上。原以为是自己的家,可实际上却只是一个临时客栈,我甚至觉得只有假面——不仅不是“假”的面,反而唯有他才能治愈我的晕船——才是真正的陆地”[1]196-197。主人公因得不到他者的认同而无法证实自身存在,如今仍是一片孤独的虚无,甚至由于假面的不正当掠夺,连妻子所在的家亦成为无法回归的寓所。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的悲剧性在于“对于受空间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策动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形形式的种种狂想——直达到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2]87。主人公陷在自我异化的深渊,终生无法抹去假面于脸上烙下的奴隶印记。然而,主人公的异化并非单纯由他人、假面所致,正如妻子在回信中质问的,“难道不是你自己拒绝了自己吗?”[1]213控诉他人将脸当作尺度,却不顾一切逃离自己的脸,甚至不惜戴着假面睡觉,以祈求假面替换了自己的真面。“一面说着脸是人与人之间的通道,一面却像海关的官吏那样只想着自己这道门,如同海螺似的你。”[1]215
可以说,正是主人公画地为牢囚禁了自己,在假面这一天然掩体的遮蔽下,一步步追寻着打破戒律与禁忌的快感,放任“野兽般”[1]227原始的欲望驱动自己的身体。因而当主人公发现妻子从一开始便识破了他的伪装,“变成没有意识到滑稽的丑角”[1]216一般的耻辱感彻底将他淹没。他最终戴上假面,拿起手枪,走上大街,准备向出走的妻子、一个陌生女人,抑或她们身后一个用脸或是别的什么规约人、异化人的社会秩序发起袭击。
四、结语
在安部公房笔下,都市人自我存在的迷失一直是其关注的主题。面对这一困境,不同的主人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如《砂女》中仁木顺平以出走对抗妻子的压力,《箱男》中的箱男栖身在纸箱中以获得窥视别人而不被人窥视的特权。在小说《他人的脸》中,主人公采用的是变脸这种比较特别的变形方式,因为变脸而获得的社会认同一度让他以为自己就是变脸后的人物,并企图操控戴上假面的自己去满足自己的幻想,如同拉康镜像理论中婴儿对镜中影像的认同和着迷。小说中主体因事故而造成的形象缺失满足了镜像认同的前提条件,此后当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对身体的掌控只是一个错觉,自己反而被假面掌控时,他一方面心生妒忌,另一方面又乐得享受假面构建的自己与外界扭曲的沟通,最终无法避免地异化成了镜像。主体已彻底遭到了镜像的吞噬,连其自身也清楚这一点,“只有假面留在了原地,而我却消亡了”[1]227。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