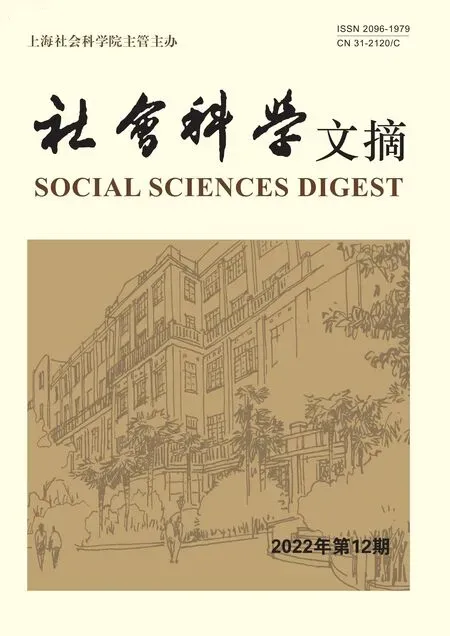身心一体与性命论主体的确立
文/吴飞
本文是对性命论主体建构的哲学探讨。建构性命论主体的一个关键,是破除心物二元论。现代中国哲学接受唯物论,并非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因为以儒、道为主流的中国哲学本就有唯物论因素,即强大的气论传统。不过,正如熊十力和刘咸炘两位先生意识到的,中国的性命论哲学传统并非建立在心物二元基础上,因而其唯物论亦非机械唯物论。若将传统性命论哲学做一创造性转化,以面对现代问题,我们首先需要破除二元论,在身心一体的基础上建构性命论主体。
从心物二元到身心一体
主体性二元论哲学源于古代西方哲学传统,经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与主体性哲学而确立。前者奠定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并划定了现代人文与科学研究的边界,后者为现代自由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两方面结合起来,便是一种以认知主体为出发点的现代哲学: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将精神定义为思想,物质定义为广延,而又认为,自我就是一个精神。
中国哲学和宗教传统都没有发展出这样的二元对立,虽有诸如身心、阴阳、理气之类的二分,但与西方式的二元论模式都有巨大差别。突破二元论传统,理解身心一体,以建构性命主体,这是性命论哲学要做的工作。
严格说来,中国并不存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心物”问题,而只有身心问题。中西哲学皆以心为身之主宰,区别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这种关系被理解为精神性存在对物质性存在的优越和主宰。而在中国哲学中,心首先被当做脏腑器官当中的一个来看待,它和所有其他脏腑一样,有自己的职分和功能,但它的功能比其他脏腑的功能更重要,因而作为君主之官,统领着身体中所有其他部分,但其又和所有臣民一样,都是整体的成员。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告子上》)耳目为小体,心为大体。耳目没有思的功能,所以会蔽于物;而思考正是心的功能,所以人要先用心来思考,这便是先立乎其大。
中国传统之所以如此看待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所有脏腑、器官都是维持与提升人的生命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心脏。心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君臣关系,并不是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大学》中对八条目的次序安排尤其展现出这种身心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四条都是修身的功夫,通过格物、致知、诚意做到正心,而正心是修身的关键,修身是齐家的关键,齐家是治国的关键,治国是平天下的关键。作为最要害的环节,所谓“修身”,并不是针对肉体性身体的锻炼,而是以正心为最核心内容的自我修养。身即自我之总体,而心是这个自我的主宰,通过正心才能做到修身。以正心、修身建构起来的自我,与笛卡尔通过“我思—我在”构建起来的自我非常不同。中国哲学中这种身心结构,在《大学》中已经有一种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推扩,即由身而家,而国,而天下的推扩,“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心以修身,被理解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同基础。
性命论主体
性命论主体既非认知主体,亦非意志主体。我是一个以心御身的性命体,心虽为主,仅有心却无法构成自我,因为身、心并非相互独立的两种存在物。身是自我生命之全部,心是生命之主宰与精华,理性的心对此一生命的反思、主宰与调整,即构成性命论主体。无论欲望、认知,对种种工具的使用,都是自我生命活动的一部分。这个主体,便是性命论哲学的出发点。我和其他生命体,乃至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生、被生、共生的关系,认知、欲求、使用,都是其次的。
性者,生也,但“性命”不同于完全生物性的生命,而是对有生有灭之物的哲学理解。自我之性命,是我一切生命活动的出发点,但我仅仅是世界上众多生命中的一个,我并没有绝对的优先性。如何平衡文明与自然,是以二元论建构的主体性哲学的巨大困难,也是性命论哲学最大的优势。以外物为认知对象、欲望对象或使用工具,最终都无法将他人当做和我一样的主体看待,因为在自我面前,他人和所有其他物体一样,也是被对象化的物,我无法将他当做和我一样的精神主体。这也正是现象学之交互主体性试图克服的难题。而在性命论的主体哲学中,各正性命的任何一个主体都处在相对的中位,但没有一个中位是绝对的。
每个人只能以自己为中心观察外部世界,无论是时空架构、声音色彩气味、茫茫太空,还是草木禽兽,乃至我的五脏六腑。但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灵魂对外物的认知,而在于我的生命与外部世界的交汇。我在世界中生活这个常识性的事实,是一个给定的前提,既然在生活,我就不是完全孤立的,因而必须从我所在的主体出发,与他人和万物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主体的尊严不是通过封闭自我、无视其他主体获得的,而是通过反思自我、推己及人、观照万物、体察天地,尽可能从全局的视角看待我的生活世界而逐渐达成的。
我们由此可以确立性命论主体的哲学意涵。性命个体是因为生生而在天地之间有一席之地。他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力和理性思考,确立自己所处的这个中位,牢牢地立足于中位的主体,要认识自己周围其他的性命体与万物,把他们当做同样的性命体来对待,理解自己所在的这个生生共同体。
气论宇宙观
气构成天地万物,是宋明理学各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共识。对理、道、心的讨论,只是在这一共识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通常所谓的气论学派,并非不讲其他概念,更不是机械之物质对精神实体的反抗或取消。而无论理学还是心学,也都不会在西方二元论的意义上讲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实体,而是在接受气构成宇宙万物的前提下,在确立性命主体与认识生生共同体之时,尤其强调理或心等概念。
性命论哲学并不假定能绝对客观地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构成。气,是性命主体反思生命之成立与其生活之世界而形成的哲学概念,而非科学概念。气的基本特点都是流动不居、生生不已。孟子已经将自己生命中的浩然之气与塞于天地之气联系起来,庄子认为生死是气之聚散。张载、王船山之气论,实接续此一传统而来:以构成我之生命的气理解天地万物;复以天地间氤氲之气理解我之生命。气聚而为生,并非气体凝结为固体;气散而为死,也不可理解为固体升华为气体。我们必须抛开以哲学附会物理学的思路,才能真正理解性命论传统中的气论哲学。
从性命主体的角度观察世界万物,理解宇宙万物与我之生命类似,有其聚散,有其生灭。我与万物也是生、被生、共生的关系。这一态度并非否定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从哲学上,以流动不息、生生无穷的气之聚散来理解有生有灭的万物。没有一种永恒的存在者,亦无绝对的创造者,更没有完全超越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精神实体。然而死生相继,聚散无穷,各种生命体共同构成始终充满生机、活泼泼的世界。
性命论的理解与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可以协调,而不必设定一个永恒的存在者。传统哲学中的“理”和“心”都不是精神实体。说理在气中,就如同说心在身中。朱子一直坚持“理是纹理”的定义,将天理解释为道理、规律和规则,虽然也会强调理相对于气的优先性,但始终不会将理当做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正如心是身的主宰,也可以说天地之心或天理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然而这个主宰既非精神实体或神,亦非形式或样式,而是内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生生之仁或是人。
人为天地心
在性命论主体与气论宇宙观的哲学图景下,我们才可以尝试理解《礼运》“人为天地之心”与张载“为天地立心”之语的宏阔哲学图景。在这一哲学模式中,天地间的万物是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万物都有其存在之理与生生之道,也在相互影响中各正性命,组成一个永远变动又维持大致平衡的生生共同体,而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万物之上的绝对至善的精神实体,来制造、设计、安排。
作为有理性、有智慧的性命体,人类不仅像所有其他生命体一样生生死死,而且可以反思、认识,从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所在的这个生态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可以参赞化育,也因而才能更自觉地成为《礼运》中所说的“天地之心”。
理性而智慧的人类,以自己的理性认知成果诠释天地,这便是“为天地立心”。某种超出人类文明之上的超越性力量,都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放大,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随着人类文明的积累与发展,人类已经越来越不用借助于宗教性来源,来强化其理论的力量。我们并不否认有人类之上的自然规律和天地生生之德,但这种生生之德不会以人类理性和逻辑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只会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不可言说的整体。人类可以用自己的智慧不断地去改造自然世界,但始终应该对这种自然而然的整体心存敬畏。这是“参赞化育”的智慧中的应有之义。
性命论的角度,展现出与二元论存在论传统差别很大的问题域。善恶皆以性命为标准,我们并不把天地总体当做至善或超越性的神,天人关系不会呈现出善恶二元的形态,但仍会蕴含巨大的张力,这在先秦儒、道两家的争论中呈现得相当尖锐,也与当代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息息相关。
西方主体性哲学一直在真切地面对这一问题,但也在推动着天人张力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境地。由于根深蒂固的二元论传统,西方思想要么将希望寄托于人类文明之上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和引导本质上自私的人类走向美好的天国,要么以善恶二元的尖锐对立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将明明是人义的运动自我神化。
性命论哲学基于“参赞化育”的立场,认为人类仍然必须以文明创造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个角度有些类似于海德格尔批判技术化时代的态度:虽然深切意识到现代文明的种种问题,但必须接受这个文明处境,在内部对它做出修正。在这个意义上,性命论哲学虽深具古典思想气息,却也有十足的现代精神的历史担当。
在二元论架构之下,“不朽”就是精神实体的永远存在。但性命论不朽观的三种形态:立德、立功、立言,都不是字面上的永远存在。性命论的哲学态度相信,身心一体,有生必有死,身体死去则没有灵魂独活的道理。不朽,要依靠历史的忠实记载和永远延续。中国的史学传统高度发达,并不是基于一种先天的线性历史和发展规律,而是人类制礼作乐与参赞化育的传承不绝。
结论
性命论哲学试图挖掘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精神,以面对现代性的种种问题,其要害是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张力,它可以成为毁灭性力量,但也可能成为文明进步、创造历史的动力。二元论传统使这对张力呈现为激烈的心物、圣俗、神人之争。
从性命论角度统合自然与文明两个方面,方能更全面看待中国文明的精神。在人的性命中,心虽为身之主宰,但身为性命之全体,所以不能脱离身体,将精神当做性命的实质。将此智慧扩展到天地宇宙之间,是同样的道理,理虽然是万物之条理,把握了天理就可以把握物之根本,但物毕竟由气组成,岂有脱离气单论理的可能?要在自然与文明之间寻求中道,并不是刻意去放弃什么、勉强什么,而是应该始终着眼于性命本身,这是自然与文明的交汇点。人类文明的各种悲剧常常是,以生命中的一偏妨害生命之全体,以局部的生命妨害总体的生命。要突破这些偏见与狭隘,人类不应放弃文明的创造性活动,因为文明的创造也是内在于人之性命自然的。人类只有不断扩大自己对天地自然的理解,由偏入全,由局部入全体,才可以在越来越大的整体范围内,把握自然规律和生命走向,创造出更适宜生命及其延续的秩序。
性命主体应当深入认识自我,把握自己的心性结构与身心平衡,才能做到修身;再以性命主体为中心和出发点,去认识其所在的家庭,在主体和其他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思考和安排,使各方面尽可能各得其所,才能做到齐家;再进一步,能够在国家的范围内,在性命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参酌远为复杂的关系,不失自己的主体之位,却又能悬置主体,尽可能客观、辩证、平衡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使其中的性命体各安其位,才能做到治国;而若是能更进一步,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范围内,乃至在不同文明体系、不同政治诉求的政治群体之间,做到更加多层次、更加多利益的辩证与平衡,使各个国家中的性命体都可以各正性命,才能做到平天下。
以此思路,我们还可以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地推扩,抽象的“天下”概念可以无限推展出去,及于人类之外的各种生命体,乃至地球之外的广阔宇宙。差序格局,是人类文明不断认识自己、不断为自己在世界中定位,同时也不断承担起参赞化育之责任的无限过程。文明拓展的范围越大,对自然的认识就越全面,因而以文明毁坏自然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不断推扩、不断拓展知识的过程中,人类勇敢地面对和化解天人张力,不断地实现自己作为天地之心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个给定的事实,更是基于天人之间的哲学关系给出的文明理想。人类并不是任凭自然力量的摆布,就可以做到天人合一,反而是要在不断拓展知识、扩大生活领域的过程中,通过“制天命而用之”,才能尽可能地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的过程中,天人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我们正是生活在这对张力当中,靠它的推动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乃至改造自然,从而创造人类的文明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