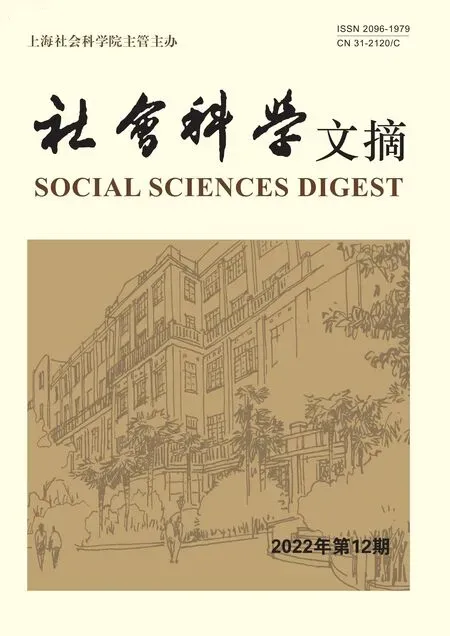哲学中的教条及其扬弃
文/杨国荣
以抽象的归约为进路,构成了哲学领域教条形成的一般趋向。将“所与”视为“神话”,在强调感觉经验渗入概念的同时否定感觉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认识意义,表现为当代认识论的一种教条;以强化命题性知识与非命题性知识、活动与真理的相分为前提,拒绝承认“知道如何”(knowing how)之知包含命题性内容,是认识论中的另一教条。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作为不相容的两个方面,在质疑积极自由的同时推崇“消极自由”,呈现为政治伦理领域的教条;与之相关的是将正义原则永恒化,它构成了政治、伦理领域的另一教条;以“天下主义”或“天下模式”为形式,“天下”观念被奉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救世”教条。在心物、主客、天人关系方面,则呈现更普遍意义上凡“合”皆好、凡“分”皆坏的教条。
以上诸种教条的形成,与抽象的知性思维方式存在难以分离的关联;克服这类教条,则以回归具体的存在、扬弃独断和抽象的思维方式为前提。
一
作为抽象的观念,哲学上的诸种教条呈现多重偏向,在认识与变革世界的过程中,都难以提供合理的规范。从其形成的根源看,这种教条的发生,又有自身的缘由,后者首先表现为知性的思维方式。哲学教条的共通趋向在于片面强化存在及其关系的某一方面,忽略或漠视其他相关规定,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比较典型的知性特点。
从康德开始,德国古典哲学便区分了感性、知性与理性。这里所说的理性与通常所说的认识论意义上区别于感性的“理性”有所不同,它既以超验的理念为形式,又具有扬弃分离的辩证趋向。同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表述,知性也有二重品格:在超越感性这一层面,知性与通常认识论视域中的理性有相通之处;然而,就其把握对象的方式、过程以及所指向的存在规定而言,知性又不同于前述意义上的理性。
区别于感性和理性的“知性”首先与思维方法相关。在思维方式这一层面,知性的特点在于“丢掉具体事物所具有的一部分多样性”,而抽取其相同的方面。从逻辑上说,这一思维趋向侧重于“分”或分析。然而,在以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同时,知性未能引入综合和关联的视域,与之相联系,区分与划界构成了知性思维的基本特点。上述方式运用于思维过程,便展现为以下趋向:一是截止运动,即把对象的变迁过程裁割为不同的断层,然后对各个横断面加以研究;二是分解整体,即把完整的统一体分解为不同规定而加以考察。前者主要撇开事物的纵向联系而把各个断面抽引出来加以分析,后者则悬置事物的横向联系而把统一体的各种要素分离出来进行考察。
从把握存在的过程看,知性思维无疑有其意义。相对于感性直观的外在性与混沌形式的整体性,知性既通过截止、分解等活动而深入到了对象的内在层面,又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由此扬弃了感性的混沌性。正是基于知性的思维,认识开始摆脱感性直观的外在性与混沌性,从而为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定以及再现理性的整体提供必要的前提:把过程加以截止,将整体加以分解,构成了把握真实对象的条件。
然而,知性思维诚然扬弃了对象的外在性与混沌性,但自身又以抽象性为主导品格,如上所言,后者主要表现为执着各个规定的自身同一而撇开其相互联系。在知性的形态中,对象的各个规定往往彼此分异,其现实的联系则被悬置,这样,如果停留于知性思维,将其视为终极的认识形式,便难以避免各种负面的思维后果。
事实上,在前述各种哲学的教条中,便不难注意到执着于抽象规定而形成的片面趋向。在以批评“所与的神话”这一形式出现的教条中,仅仅强调感觉经验渗入概念性规定,由此否定感觉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认识意义,呈现的即是知性思维的抽象性。同样,拒绝承认“知道如何”之知包含命题性内容这一教条,也以单纯强化命题性知识与非命题性知识、活动与真理的相分为前提。推崇“消极自由”的教条,即以强调消极自由、疏离和责难积极自由为前提,后者在逻辑上以仅仅侧重于自由的一个方面而排斥相关的另一方面为特点。与之相关的是将正义原则永恒化的教条,其前提既表现为个体权利的片面突出,又呈现为正义这一价值原则的抽象化。在心物、主客、天人关系方面,凡“合”皆好、凡“分”皆坏的教条,与心物、主客、天人关系中“分”与“合”内涵的抽象理解相关,在这一视域中,心物、主客、天人之间合一的不同形态被搁置,统一本身被抽象化为理想之境,其具体性、历史性品格则被消解。从以上方面看,哲学中的诸种教条的形成,与抽象的知性思维方式存在难以分离的关联。
由此做进一步考察,便可注意,哲学领域的教条同时关乎更广意义上的学术趋向。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界而言,附和所谓热点,从众以及跟风式的“研究”,往往成为各种教条生成的温床。梁启超在谈到学术衍化时,曾指出:“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这里虽主要涉及学派流变,但其中也关乎学风上的消极趋向,而“希附末光”“陈陈相因”,则可以视为附和、从众、跟风之类“研究”方式的概述。在人人讲“天下”的时风中,“天下主义”或“天下模式”逐渐被奉为“救世”教条;以个个谈“消极自由”为学术“前沿”,消极自由本身也开始获得了教条的性质,如此等等。这里既渗入了抽象的知性思维方式,也折射了人云亦云、追随学术时尚的浮泛学风。与之相关,时下往往好谈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种表述本身似乎已成为陈腐的套语:在实质上的“陈陈相因”之后,以上标榜更多地呈现某种反讽意义,而其背后,则常常是思想的贫乏和观念的空洞与抽象。事实上,虚华的学风,本身也可视为抽象思维的体现,而不同形式的哲学教条,则表现为其逻辑的结果。
二
以上所述表明,哲学的教条首先与知性化的抽象思维及其衍化形态相涉,这一关联同时规定了克服各类教条的可能进路。概要而言,超越哲学教条的途径表现为以具体的分析、综合的考察扬弃抽象的归类和抽象的分析。
就“所与的神话”这一概述所内含的教条而言,其克服或扬弃既与肯定感觉经验的认识论意义相关,也以具体地分析“所与”的内涵为前提,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这里需要将“所与”放在具体的关联中,避免对其作孤立的考察。在引申的意义上,可以把“所与”和“感觉材料”联系起来。按其实质的规定,“所与”侧重所知(认识对象),可以视为对象的直接呈现;感觉材料更多地与能知(认识主体)相关,主要表现为主体把握的认识质料。将“所与”仅仅理解为外在的、对象性的规定,而否定其与主体(包括概念形式)关联,无疑是一种偏向;把感觉材料主要归结为主体性的主观规定,认为它只是存在于内而与对象无关,这种看法同样有其片面性。作为认识的现实出发点,“所与”只有与概念形式相关才有意义;感觉材料则唯有包含关于对象的内容,才构成认识条件。
真实的认识条件表现为“所与”和感觉材料的结合:二者无法截然相分。与之相联系,感觉经验或感觉材料可以视为对象在一定条件(与人相关的背景)下呈现的属性,从而,在获得感觉材料的同时,人也同时达到了对象本身。以批评“所与的神话”为形式的教条仅仅肯定概念对经验的渗入,基本上忽视了“所与”是“客观”的呈现。事实上,作为认识的质料,感觉材料既关乎对象性,而非纯粹的概念投射,又渗入了概念形式,从而不同于光溜溜的实在规定;以对象在能知之中的呈现为形式,感觉材料具有个体性,但与概念的关联又使之具有普遍性(可以在共同体中交流、讨论)。关于经验材料,不应简单地否定其认识论上的存在和意义,而是需要指出其中所与(对象的呈现)和所得(语言、概念形式)的结合、感性与理性的相涉、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相关等品格。
否定“知道如何”之知包含命题性内容,构成了认识论中的另一教条,解构这一教条,需要从广义的视域考察认识过程。从现实的层面看,人类认识不仅关乎认知与评价,而且涉及规范,后者以引导人的观念活动和实践活动为内在指向。规范性的认识或认识的规范之维主要与“知道如何”相联系,如果对认识过程作具体的考察,便可以注意到,作为广义认识的重要方面,“知道如何”与“知道是何”并非截然相分:与抽象地划界相对,作为对象性认识的“知道是何”与体现于人类活动的“知道如何”具有相互关联性。事实上,所谓命题性知识并不仅仅限于对事物的把握(“知道是何”),以规范性(“知道如何”)为指向的认识形式,也同样包含命题性内容。这里,重要的是超越“知道是何”与“知道如何”的分离以及命题性知识与非命题性知识的对峙,这种分离和对峙体现的是抽象的知性思维形态,其逻辑结果是形成否定规范性认识的命题意义这种教条,而回到现实的人类认识过程则是扬弃以上教条的前提。
在政治与伦理领域,拒斥积极自由、推崇消极自由成为一种教条。从理论的层面看,其中关乎如何理解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现实关系。积极形式的自由取向如果片面发展,固然可能导致独断与强制的偏向,但消极形式的自由则由于缺乏价值的承诺及忽视规范的引导而容易走向虚无主义。这里,可以关注儒家所提出的“忠”与“恕”的为仁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内在的趋向是由己而及人,将自己所接受和追求的价值理想作为自我与他人共同努力的目标;“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尽管这一取向也以自我为出发点,但其中又包含不强加于人的旨趣。“忠”所展示的是积极的意向,但一味地向他人推行自己的理想,不免走向独断。相对于此,“恕”蕴含的则是消极或有所节制的意味。对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取向可能引发的负面结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观念似乎具有某种抑制的意义,但以后者为唯一的原则,则容易消解一切价值追求。儒家兼容“忠”与“恕”,将其作为实现仁道的必要方式,无疑有助于扬弃“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各自的价值偏向。从价值原则看,相对于“忠”与“恕”的以上统一所体现的具体视域,排斥积极自由、仅仅强化消极自由的教条无疑呈现了抽象的进路,克服这种抽象教条的前提,则是关注并置身于现实的存在过程。
将正义视为至上甚至永恒的价值原则,表现为政治与伦理领域的又一教条。正义以确认个体的权利为核心,将正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原则的背后,是个体权利的强化。如所周知,个体之间的权利并不一致,其间存在不同形式的冲突,仅仅以基于权利的正义为原则,固然可以在得其应得的层面形成某种社会秩序,但既难以避免个体之间分化或对立,也无法使这种秩序建立在实质层面的价值和谐之上。在社会领域,首先应当关注的是人不同于其他存在的内在价值,儒家的仁道观念,便以肯定人的这种内在价值为其实质的内涵。相对于“礼”之侧重于社会层面的“度量分界”,“仁”更多地表现为超越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差异而指向人自身的价值。无论是儒家的人禽之辨,抑或其仁者爱人的思想,都可以视为仁道观念的展开,而其内在之旨,则是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人所具有的这种价值赋予人以内在的尊严,并使尊重人的存在价值成为基本的伦理要求;较之以个体权利为中心的正义,仁道更多地体现了对人的这种存在价值的确认,在此意义上,仁道既高于权利,也相应地高于正义。
以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仁道趋向于对群体的普遍关切。对儒家而言,“仁民”是仁道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观念既蕴含着对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肯定,也意味着走出狭隘的自我,以仁道的方式处理群己关系。从内在含义看,“仁民”所指向的主要不是基于个体权利的应得,而是群体的关怀。仁道观念的以上内涵,在儒家那里进一步引向万物一体论。对儒家而言,仅仅关注个体权利,并以个体之间的利益计较为出发点,往往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离和冲突。相对于此,注重正义与仁道的互补和互动,则既为扬弃正义原则的教条化提供了前提,也有助于克服这种价值取向的非历史和抽象性。
同样,“天下”观念以及心物、主客、天人关系中的诸种教条,其超越也需要基于现实的存在形态。以“天下”而言,作为历史中的观念,“天下”有具体的内涵,无论以大同理想的形态呈现,还是表现为现实的政治格局,都有其特定所指,唯有联系不同的历史背景,才能把握其实际内涵,避免将它泛化为现代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救世良方”。作为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下”观念多少呈现乌托邦的性质;作为与一统和正统以及夷夏之辨相关的政治形态,“天下”观念则有历史的品格,将其抽象为普遍的政治教条,显然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背景。与之相近,心物、主客、天人之间既有相分的一面,也包含内在统一,离开统一谈其相分或离开相分谈其统一,都难以避免抽象的形态。这里,重要的是注重心物、主客、天人关系的具体内涵,并在切实地把握其不同规定的同时,不断在既分之后重建统一。笼统地批评其相分、无条件地礼赞其统一,总是难免引向抽象的教条。
宽泛而言,哲学中的教条并不限于以上所论的各种,从广义的所谓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到中西关系上的以中释中,等等,哲学领域的教条呈现多样形态。尽管取向各异、内涵不同,但前述各种教条在独断性、抽象性等方面,又呈现相通之处,后者同时构成了哲学中一般教条的普遍特点。克服哲学中的这类教条与回归具体的存在、扬弃独断和抽象的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