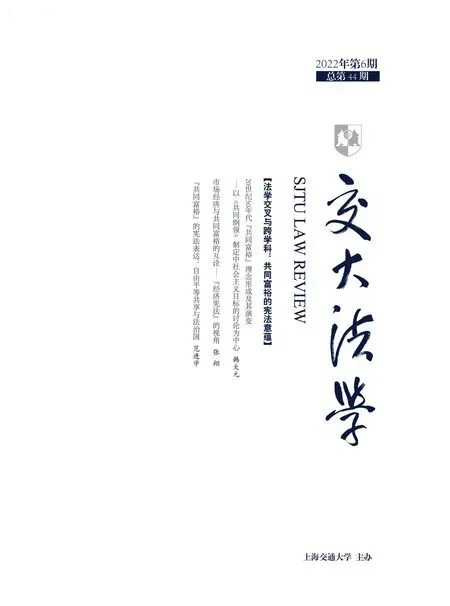中国和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演进:法律传统的趋同?
曾元君
目次
一、引言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澳两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发展
(一)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由控方证人转变为诉讼参与人
(二)中国刑事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转变为当事人
三、中澳两国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结构条件
(一)澳大利亚对抗制审判的结构限制
(二)中国审问制审判的结构兼容
四、不同法律传统的趋同
(一)重视被害人权益
(二)区分公私利益
(三)趋同因素
五、结语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英美法系对抗制刑事司法传统因边缘化被害人而饱受诟病。随着19世纪现代警察以及公诉机构的诞生,作为正统“冲突所有者”(owner of conflict)的被害人正式将起诉控制权让渡给国家,〔1〕Nils Christie,Conflicts as Property,17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1(1977).仅在控辩双方有需要时出庭作证。西方诸国自20世纪70年代踏上了刑事被害人权利发展的新里程。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开始推广一系列旨在帮助被害人脱离被害困境的措施,包括改善信息服务、提供国家补偿、升级法庭设施,以及给予多样化援助以满足被害人医疗和心理咨询等需求。另一方面,被害人逐渐回归对抗式刑事诉讼程序,角色从控方证人转变为拥有少量参与权的诉讼“参与人”。〔2〕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The Role of Victims of Crime in the Criminal Trial Process,Final Report(2016),p.29-30.相较而言,拥有强职权主义刑事司法特征的中国自1979年《刑事诉讼法》起便赋予被害人较多诉讼参与权,并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2012、2018年《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诉讼规则、程序规定等文件则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并完善信息提供、作证保护、国家司法救助等服务。以此为背景,本文认为中澳两国在被害人权利演进方面呈现出分歧与趋同,而趋同成为主要趋势。为论证该观点,文章首先考察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和澳大利亚被害人权利的演进路径,关注两国在改善被害人困境方面取得的进展。〔3〕澳大利亚共九个司法区,包括六个州、两个领地和联邦。在刑事司法领域,只有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保留了普通法传统。其他各州和领地颁布了刑法典,普通法用于解释制定法。本文主要聚焦上述三个普通法司法区的被害人权利发展。其次,剖析中国审问制和澳大利亚对抗制刑事审判在容纳被害人方面的结构条件,解释两国赋予被害人不同诉讼地位、参与权的缘由。最后,探究被害人参与两国刑事诉讼的实践情况,指出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程度并非仅由诉讼结构决定,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而分析推动两国被害人权益发展趋同的因素。
文章聚焦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关被害人权利的法律及政策框架,并适当结合与中国、澳大利亚17名检察官、律师的访谈、问卷数据加以论证。文中使用编号代替参与者姓名:中方检察官为CPP1(Chinese Public Prosecutor 1),CPP2,以此类推;中方律师为CL1(Chinese Lawyer 1),CL2,以此类推;澳方检察官为ACP1(Australian Crown Prosecutor 1),ACP2,以此类推;澳方律师则为AS1(Australian Solicitor 1)和AS2。〔4〕17名参与者包括北京市4名执业律师和A、B两区人民检察院的7名检察官,以及新南威尔士州公诉办公室的3名检察官(Crown Prosecutor,均为barrister)、1名已退休检察官(Queen's Counsel)、2名事务律师(Solicitor,含一名法律援助律师)。研究采用访谈和问卷两种方式,除5名中国检察官通过填写问卷参与、已退休检察官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外,其余所有参与者均以访谈方式参与。数据收集时间为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本研究已获笔者所在单位“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需要说明以下三点:其一,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少数保留“警察公诉人”(Police Prosecutor)角色的国家。“警察公诉人”负责在基层法院(Magistrates'Court/Local Court)起诉简易罪行(Summary Offence),而公诉办公室(ODPP)的检察官则负责在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County Court)及州最高法院起诉可检控罪行(Indictable Offence),具体由Crown Prosecutor代表公诉方出席法庭审判。由于访谈以性侵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为主题,而性侵犯罪在澳大利亚是严重的可检控罪行,故访谈对象选择的是有着十年以上办案经验的Crown Prosecutor,而非Police Prosecutor。其二,问卷和访谈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1.被害人权利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情况和存在问题;2.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需求;3.被害人对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其三,即使澳大利亚各州、领地在被害人权利发展方面步调不一,但方向大体一致,司法实践也大同小异(经由参与研究的澳方检察官和律师证实)。另外,本文仅仅是借助访谈、问卷数据对相关论点加以论证,故而特此强调本文论证“适当结合”实证数据。本文弥补了目前欠缺的刑事被害人权利比较研究,可丰富学界关于不同诉讼结构的国家就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路径选择、改良思路的认识,有助于从保障被害人权益的角度构思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澳两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发展
(一)澳大利亚刑事被害人:由控方证人转变为诉讼参与人
1.20 世纪70年代:被害人服务权的产生与发展〔5〕本文“服务权”和“参与权”的概念借鉴了英国学者安德鲁·阿什沃斯(Andrew Ashworth)对被害人权利的划分。根据阿什沃思的类型学,被害人权利可分为服务权和程序权。前者旨在帮助减轻犯罪对被害人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预防或降低刑事程序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而后者允许被害人影响刑事司法决策程序。目前,阿什沃思关于服务权的界定已经取得了国际被害人学界的认可,“服务权”概念也被广泛采用。See Andrew Ashworth,Victim Impact Statements and Sentencing,Criminal Law Review 498(1993).
作为被传统对抗式刑事司法“遗忘”的人,〔6〕Brian Dickson,The Forgotten Party—The Victim of Crime,18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Law Review 319,319(1984).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面临的困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呼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运动浪潮。〔7〕See Marie Manikis,Contrast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Victims'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 and Wales,9 Societies 35,36(2019).在被害人活动家及女权主义者的号召下,澳大利亚被害人运动顺势蓬勃发展。〔8〕Michael O'Connell,The Evolution of Victims'Rights and Services in Australia,in Dean Wilson&Stuart Ross eds.,Victims and Policy:International Contexts,Local Experiences,Palgrave Mc Millan,2015,p.243-247;Tyrone Kirchengast,The Victim in Criminal Law and Justice,Palgrave Macmillan,2006,p.166-169.被害人服务机构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权利维护等方面的支持,并推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改良。这一时期的被害人运动以完善被害人服务为主要内容,响应了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帮助的福利国家理念。〔9〕Tyrone Kirchengast,Victims and the Criminal Trial,Palgrave Mc Millan,2016,p.34.自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被害人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被害人权益的发展。最初的被害人学以被害人同犯罪人之间的动态联系为研究焦点,关注被害人就犯罪发生存在的过错及责任,〔10〕Stephen Schafer,The Victim and His Criminal:A Study in Functional Responsibility,Random House,1968.故而具备些许谴责被害人的色彩。随着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者等“草根”权利活动家对此的批判反思,被害人学逐渐转向关注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的困境,为被害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同时,消费主义理念的兴起为理解社会关系开辟了全新视角,被害人与刑事司法系统开始被解读为“消费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关系。〔11〕Paul Rock,Constructing Victims'Rights:The Home Office,New Labour,and Victims,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2012,p.133;Renée Zauberman,Victims as Consumer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in Adam Crawford&Jo Goodey eds.,Integrating a Victim Perspective within Criminal Justice:International Debates,Ashgate Publishing,2000,p.40.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刑事司法机构应向作为消费者的被害人提供符合其需求的服务。在该背景下,澳大利亚开始着力健全被害人服务体系以改善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艰难处境和减轻犯罪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
刑事被害人能够获得专业、全面的服务。这些服务主要包括:获知有关被害人权利、刑事程序、案件进展、自身在诉讼中的角色等方面的信息,人身和隐私保护,获得被害人支持服务、国家补偿、有尊严的待遇等等,〔12〕See Stuart Ross,Victims in the Australian Criminal Justice System:Principles,Policy and(Distr)action,in Wilson&Ross,supra note〔8〕,at 218-224.一般涉及财务援助、心理咨询、诉讼支持、医疗服务等领域。服务提供者为州政府专门设立的被害人服务机构,例如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社区与司法部”下设的“被害人服务”(Victims Services),以及与州政府订立代理协议的民间组织。此外,各州在20世纪90年代还相继在公诉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中设立了专门服务于证人出庭作证的机构,例如新州的“证人援助服务”(Witness Assistance Service)。该机构为被害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告知被害人法庭程序和被害人在其中的角色、组织审前法庭参观、安排翻译人员、在被害人有需要时安排工作人员陪同支持其出庭作证等。办案机关在接触被害人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害人有需要援助的情况或需求,应当主动联系相应援助机构或者告知被害人专业援助机构的联系方式。〔13〕ACP2,ACP3,AS1 and AS2.办案机关同民间组织的密切合作,为方便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减少二次伤害提供了全方位的协助。另一方面,这些协助有利于确保被害人证言质量,因此间接服务于公诉。然而,这也表明刑事司法机构所提供的服务并非完全建构于被害人需求之上,可能倾向机构利益和功利考虑,被害人真正需求与政府服务供给之间存在潜在冲突。〔14〕See Joanna Shapland,Jon Willmore&Peter Duff,Victim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Gower Publishing,1985,p.2,178.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完善被害人服务为内容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被害人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割裂状态,甚至进一步将被害人从刑事司法领域引向获取国家福利的行政法范畴。〔15〕See Kirchengast,supra note〔8〕,at 206-210.
2.20世纪80年代: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新时代
(1)诉讼参与权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公众的注意力逐渐从完善被害人服务转向帮助被害人重新融入刑事诉讼程序。被害人需求与刑事司法系统供给之间的差异以及被害人游离于司法程序外的事实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大量研究发现,被害人认为他们“在刑事程序中不应仅仅充当证人角色”,其关于犯罪处置的观点应当得到决策机构的考虑;〔16〕Jo-Anne Wemmers&Katie Cyr,Victims'Perspectives on Restorative Justice:How Much Involvement are Victims Looking for?11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259,262-264(2004);Joanna Shapland,Victims,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Compensation,24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131,133-135(1984).并且,服务权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诉讼参与需求,忽视了被害人与犯罪行为的密切联系。〔17〕See Kirchengast,supra note〔8〕,at 201-213.在过去四十年间,澳大利亚赋予了被害人下列诉讼参与权,使其以超越证人的身份回归刑事诉讼程序。
第一,被害人有权向量刑法庭提交书面“被害人影响陈述”并当庭朗读陈述内容。1988年,南澳大利亚州(以下简称“南澳”)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将“被害人影响陈述”引入量刑程序的州,其他司法区也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初期在刑事法中明确赋予被害人此项权利。新州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允许性犯罪和因犯罪遭受实际身体损害、暴力或暴力威胁的被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家庭成员(如果被害人本人因犯罪去世)参与量刑程序。上述人员可以在被告人获罪到量刑之间通过检察官向法庭提交书面陈述,详细说明犯罪对其造成的人身损害(包括身体、精神、心理伤害),以及感情、人际关系、经济方面的影响等,被害人或其代理人也可以当庭朗读被害人影响陈述。法庭必须考虑该陈述。在犯罪致死的情况下,如果检察官要求及法官认为合适的,该陈述将明确成为量刑考虑因素。〔18〕Crimes(Sentencing Procedure)Act 1999(NSW)pt 3 div 2.“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在各州、领地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由于陈述内容的主观性,反对者认为适用该制度将导致量刑差异,有损法律适用平等的原则;其次,被害人影响陈述可能使被害人产生不当量刑期待,当期待未能得到满足时,可能加剧被害创伤且降低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满意度。〔19〕Edna Erez,Victim Impact Statements,33 Trends&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1,3-4(1991).目前澳大利亚各司法区(北领地除外)确立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不允许被害人就量刑、被告人品格进行评价。
第二,澳大利亚各州、领地的《被害人权利宪章》和公诉政策赋予了被害人在某些公诉决定做出前获得咨询的权利。在新州,警察或者检察官变更、撤销性犯罪或者其他导致人身损害的犯罪指控之前,以及检察官在决定接受被指控人就一项较轻指控的认罪答辩前,应当征求、考虑被害人意见。新州《1999年犯罪(量刑程序)法》更是要求检察官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提交由检察长或特定官员签发的证书,以证明已咨询被害人;如果该咨询并未发生,则应载明理由。〔20〕Crimes(Sentencing Procedure)Act 1999(NSW)ss 32,35A.该证明限于这样一种情形的控辩协商:在被告人因某项犯罪被量刑的程序中,检察官向法庭提交列明被告人已被正式指控,但还未定罪的其他犯罪,请求法庭在对主犯罪量刑时,考虑这些其他指控。根据新州的司法实践,一般由公诉办公室中的事务律师(solicitor)会见被害人,听取其关于变更指控、撤销指控、控辩协商等决定的意见。事务律师向负责此案的出庭律师(Crown Prosecutor)提请上述处置方案的报告中必须说明是否听取了被害人的意见。如果被害人不同意,则这些决定最终须由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或者副检察长(Deputy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做出。〔21〕ACP2 and ACP4.目前,咨询式参与已成为被害人参与审前程序的主要形式。〔22〕See Ian Edwards,An Ambiguous Participant:The Crime Victim and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Making,44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967,972-976(2004).
第三,性侵被害人享有通讯秘密(心理咨询记录)特权。作为首个确立“性侵通讯秘密特权”保护制度的司法区,新州在立法中明确赋予性侵被害人在控/辩方申请调取或者引证涉及性侵被害人同心理医师的咨询记录时出庭反对此项申请的权利。〔23〕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NSW)s 299A.此外,各司法区皆允许性侵被害人聘请律师或者申请法律援助,代理被害人参与该决定程序。新州的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如果发现控辩双方举证可能涉及性侵被害人通讯秘密特权,会主动联系法律援助机构为被害人提供相关协助。〔24〕AS1 and AS2.被害人可以向法庭提交“通讯秘密损害陈述”,具体说明法庭允许获取或使用特权通讯记录将给被害人带来的损害。
第四,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可以在假释机构对被告人进行假释、降低特定安全分级的决策程序中发表意见。为减轻被害人在人身安全方面的顾虑,澳大利亚各司法区都确立起了被害人登记制度。尽管对可以申请登记的被害人资格条件规定不一,〔25〕例如在南澳,罪犯如果被判处监禁或社区监管,被害人有资格获得登记。而在维州,登记制度只适用于谋杀、过失致人死亡、性侵等十种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各司法区皆允许获得登记的犯罪被害人或者(在被害人去世的情况下)其家庭成员代表知悉有关被告人被判处刑罚、服刑地点、越狱情况、假释资格等方面的信息,并允许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就罪犯是否符合假释条件发表意见,供假释机构考虑。
第五,2017年12月,澳大利亚《皇家委员会关于机构应对儿童性虐待的最终调查报告》建议各州建立有效机制,允许被害人就关键公诉决定申请复议。根据该建议,维多利亚州(以下简称“维州”)公诉办公室在2018年设立内部复议机制,要求检察官在撤诉决定做出前,必须征求被害人意见和经过内部复查程序。〔26〕检察官撤诉的初步决定须由(其他)高级检察官复议,如果复议检察官不同意该决定,须提交检察长最后决断。该机制将撤诉决定的审查程序常规化,增强了被害人在撤诉决定程序的参与角色。2021年7月,新州公诉办公室建立两级复议机制,明确赋予被害人针对不诉、撤诉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27〕ODPP New South Wales,Victims'Right of Review Policy(26 July 2021),https://www.odpp.nsw.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1-08/Victims-Right-of-Review-Policy_1.pdf.
由此可见,目前澳大利亚的刑事被害人仅享有少量诉讼参与权,且各州在赋予被害人参与权方面步调不一。但总体而言,立法和公诉政策正逐步促进被害人融入刑事决策程序。一方面,被害人有限的参与权揭示了以控辩对抗为中心的澳大利亚传统刑事司法同被害人参与之间的潜在矛盾;另一方面,逐渐增加的被害人参与权标志着被害人已从控方证人转变为刑事诉讼的参与者,其程序利益得到认可。
(2)从虚幻的承诺到可行使的权利
1985年联合国发表《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受害者宣言》),澳大利亚各司法区紧随其后,纷纷出台《被害人权利宪章》。与《受害者宣言》一致,宪章普遍要求州政府为被害人提供信息、援助、补偿等服务,以及适当的程序参与机会。然而,这些宪章却因缺少明确的执行程序和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而不尽人意。在批评者眼中,《被害人权利宪章》仅仅是为了暂时安抚国内被害人权利活动家以及应对要求改善被害人待遇的国际准则带来的压力。〔28〕See Kirchengast,supra note〔9〕,at 268,286.相同的问题也存在于同时期的英国、美国等国家。See Douglas E.Beloof,The Third Wave of Crime Victims'Rights:Standing,Remedy,and Review,2005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255,256-261(2005);Jonathan Doak,Victims'Rights,Human Rights and Criminal Justice:Reconceiving the Role of Third Parties,Hart Publishing,2008,p.25.其贡献在于逐渐引起相关文化转变并促进政策发展,而非为刑事司法机构与被害人服务机构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29〕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supra note〔2〕,at 16;Victims'Charter Act(Vic)s 22;Victims of Crime Act 2001(SA)s 5.2000年左右,澳大利亚各州、领地开始制定专门的被害人法案,将《被害人权利宪章》纳入其中,同时设立“被害人权利专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mmissioner of Victims'Rights),负责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实现。在新州,“被害人权利专员办公室”确立了专门的投诉机制,允许被害人向其报告任何违反《被害人权利宪章》的行为。专员应当调查并解决投诉,在不能妥善解决时,应建议相关机构向被害人道歉,或者将该情况制作成特别报告递交司法部长,由司法部长向议会反映。〔30〕Victims Rights and Support Act 2013(NSW)ss 10,13.然而,在新州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专员”的作用主要在审查、批准被害人援助申请(含特定小时的免费咨询、经济资助)方面。南澳在维护被害人权利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除采纳和新州相同的投诉机制外,南澳允许被害人任命一名法庭官员、被害人权利专员、被害人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等作为其代理人行使权利。〔31〕Victims of Crime Act 2001(SA)s 32A.然而,目前澳大利亚各司法区不允许被害人因宪章规定的权利受损而对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提起民事、行政或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救济的途径限于该机构内部的纪律制裁程序以及向“被害人权利专员办公室”投诉。
(二)中国刑事被害人:由诉讼参与人转变为当事人
1.1979—1996年: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的被害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篇章。在刑事司法领域,首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继颁布。1979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参照1963年《刑事诉讼法草案(六稿)》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提议,〔32〕参见吴宏耀、种松志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典百年(中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6—720页。而将被害人列为诉讼参与人之一,赋予了一些程序性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就不立案决定申请复议、对人民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决定进行申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参与庭审并在法庭调查结束后发言和参加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向被告人发问、在法庭上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对已生效裁判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虽然立法并未赋予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却明确将“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列为律师的主要业务之一。然而,直至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委托代理人以及代理人应享有何种诉讼权利问题的批复》颁布,被害人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才得以明确。据此,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到法院查阅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在庭审过程中,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在法庭调查时提问和回答问题,向法庭陈述被代理人的意见,参加辩论,发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等”。可见,诉讼代理人的权利囿于审判阶段。尽管这一时期的被害人被赋予了超出证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性权利,但国家补偿、被害人援助、作证保护等服务欠缺,也缺乏明确依据、程序规则来保障被害人知悉诉讼流程、案件进展、其权利义务等信息。
2.1996年至今: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
1996年《刑事诉讼法》首次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以及广泛的诉讼权利。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得益于我国自80年代中期开始蓬勃发展的被害人学。国内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被害人有限的诉讼参与权,并就被害人应享有诉讼当事人地位形成多数意见。〔33〕参见赵国玲、常磊:《中国犯罪被害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1、85页。同时,强化被害人诉讼地位和权利也顺应了国际上呼吁关注被害人困境的浪潮,符合联合国《受害者宣言》的精神。具体而言,除原先当事人具有的诉讼权利,例如申请回避,申请通知新证人到庭、调取新物证、重新鉴定、勘验外,1996年《刑事诉讼法》新增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知晓鉴定结论并申请补充或重新鉴定的权利、申请立案监督的权利、公诉转自诉的权利。该法也正式确立诉讼代理制度,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检察院有义务在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告知上述人员该权利。
2000年以后,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进一步强化。首先,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等指导意见的陆续颁布,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权利和对量刑的影响逐渐明确。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和理由。〔34〕《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20〕38号)第10条、第21条。对故意伤害、强奸等常见犯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案件,被害人谅解和获赔情况成为法官量刑时减少基准刑一定比例的重要依据。〔35〕《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发〔2021〕21号)。其次,诉讼代理人权利的完善促进了被害人诉讼参与。尽管诉讼代理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仍以人民检察院许可为前提,并且介入诉讼的时间在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后,但在其他方面,其权利得到了扩展。例如,2012年《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申请复议驳回回避之决定的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应当将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记录在案或附卷。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5条则取消了审理阶段诉讼代理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需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前提条件。再次,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将部分犯罪案件被害人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的影响由量刑阶段延伸至审查起诉阶段。对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和解的,公安机关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从宽处理,并且如果犯罪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刑罚的,检察院可以决定不起诉。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突出被害人在案件审前程序分流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被害人诉讼话语权相对缺失的状况,彰显恢复性司法理念。最后,2018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不仅应当听取被害人和其诉讼代理人意见并将情况记录在案,而且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罚”要重点结合被害人谅解、赔偿损失等因素。〔36〕《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需要指出的是,与澳大利亚控辩协商相似,被害人异议不能决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否适用。两国的被害人在此程序中,仅享有表意权。然而,在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害人谅解和获赔情况可以成为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重要依据之一。这点与澳大利亚控辩协商制度存在明显差异。以新州为例,尽管检察官在决定接受被指控人就一项较轻指控的认罪答辩前,应当咨询被害人;被害人不同意的,决定应当由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做出,但被害人意见无法影响量刑。实际上,澳大利亚检察官仅享有极为有限的量刑建议权。通常,检察官在量刑程序中的作用仅限于向法官提供三种信息:1.量刑所依据的事实;2.相关量刑原则;3.类似案件中所判处的刑罚。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在Barbaro v.the Queen案中明确表示不支持检察官提供量刑幅度建议,更排斥确定刑建议。在其看来,应当严格区分检察官角色与法官角色,量刑是法官独有的一项权力。不过,目前澳大利亚各州、领地通过制定法不同程度地限制了法官量刑权,以鼓励被告人认罪。比如,根据新州实施的“法定量刑折扣方案”,可检控犯罪(indictable offence)的被指控人可获得三档量刑折扣:25%(在预审程序中认罪)、10%(被移交审判后,在正式审判之前至少14天认罪)、5%(其他情况下认罪)。综上,在澳大利亚,被害人除了可以就控辩协商发表意见之外,对控辩双方达成认罪协议以及被告人量刑,一般无实质影响。Barbaro v.the Queen(2014)253 CLR 58,73-76;Crimes(Sentencing Procedure)Act 1999(NSW)s 25D.
另一方面,被害人服务缓慢起步。第一,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初步建立。2009年中央政法委等八部门联合颁发的《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因严重暴力犯罪造成死亡、严重伤残,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依靠其生活的近亲属,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请援助。2014年《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进一步增加援助对象,将因犯罪遭受重大财产损失而无法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及因犯罪危及生命而需紧急治疗又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被害人,纳入救助范围。同时,明确规定办案机关告知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被害人申请救助的义务。201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赋予因犯罪遭受严重心理创伤且因不能及时获赔而生活困难的未成年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的权利。第二,办案机关在提供信息方面有所改善,突出的表现为:实行立案、破案、命案工作进展回告;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向被害人送达权利义务告知书;实行办案流程、时限、进展、结果公开;规定公安机关在撤案决定做出后的三日内通知被害人等方面。〔37〕《关于实行“办案公开制度”的通知》(公刑〔2005〕1228号);《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年)第189条。第三,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被害人因在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请采取保护措施。〔38〕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第64条。第四,被害人法律援助服务扩展。2021年《法律援助法》不仅确认了此前《法律援助条例》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并明确“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益”而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39〕《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2021年)第29、32条。此外,该法规定“当事人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或者决定提出申诉或者申请再审,人民法院决定、裁定再审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40〕同上注,第33条。
然而,目前我国在为被害人提供社会援助、心理辅导,由公安司法机关为其提供转介服务等方面存在不足。〔41〕这点可从笔者与检察官、律师关于性犯罪被害人获得心理援助的交谈中确认,CPP1明确表示在其办案过程中,往往不会考虑为被害人联系心理援助机构,而且也未曾听过被害人表达该需求。尽管对于某些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案件,办案机关通常会联系妇联、学校、民政部门、心理辅导机构,为被害未成年人提供较为全面的帮扶,但这并未在实践中成为普遍性做法,成年被害人也往往被排除于服务对象之外。此外,民间专业的被害人服务机构数量稀少,且分布不均(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其发展面临资金、人员不足等障碍,无法为被害人提供全面、持续服务。〔42〕作为本文访谈对象的其中三名中国律师便来自专业的民间被害人法律援助机构。三名中的两名律师确认了此类机构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包括CL2。据CL2的体会:“这种民间层面的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它的生存和发展确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和挑战。政府层面至少没有给与任何政策、技术、资金方面的倾斜性支持,所以完全靠自己的一腔激情或者机构创始人、领导层在默默无闻、自愿地去从事公益法律服务,所以它的可持续发展是个很大问题。”服务的缺失不但无法满足被害人的创伤治愈需求,而且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在刑事诉讼中遭受二次伤害的风险。
同澳大利亚被害人权利救济路径相似,我国立法并不认可侵犯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构成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事由。除办案机关工作人员严重违法以致构成犯罪而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外,一般侵犯被害人诉讼权利的行为经由办案机关内部纪律处分程序处罚。被害人对于侵犯其诉讼权利的司法工作人员,有权向其主管机关控告、投诉。为增强救济,被害人可以向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后者经审查,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出纠正意见或者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办案机关纠正违法行为。〔43〕《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19〕4号)第552—554条。
三、中澳两国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结构条件
中澳两国被害人诉讼权利及地位的演进路径存在差异。承继英格兰对抗式司法传统的澳大利亚早在19世纪上半叶便设立了包括总检察长和现代警察在内的国家公诉机构,正式代替被害人追诉犯罪。〔44〕Christopher Corns,Public Prosecutions in Australia:Law,Policy and Practice,Tomson Reuters,2014,p.64-82.随着20世纪80至90年代初公诉办公室在各州、领地的确立,国家巩固了对控诉权的垄断。如今的澳大利亚,虽然保留了自诉的普通法传统,但制定法限缩了可自诉犯罪的范围,并且自诉启动受到严苛的程序性限制。〔45〕被害人须向司法常务官(court registrar)申请签发出庭通知,该通知应当符合实质要件(充分的理由)与形式要件,否则司法常务官有权拒绝。Criminal Procedure Act 1986(NSW)ss 49,174.此外,公诉办公室如果认为有必要,可随时接管自诉。因此,被害人沦为刑事司法的边缘人物,仅在控辩一方有需要时履行作证义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这一情形有所好转。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渐增,角色由证人转变为诉讼的参与者。反观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被害人是拥有超出证人诉讼权利的诉讼参与者。1996年《刑事诉讼法》更是正式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以及申请立案监督、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等诸多程序性权利。尽管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具有从属性,即协助公诉机关履行控诉职能,被害人所享有的广泛参与权使其能够对案件实体争议解决产生一定影响。具体就刑事审判阶段而言,两国被害人分别承担证人和辅助当事人角色。
(一)澳大利亚对抗制审判的结构限制
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英美法系国家,控辩对抗式刑事审判结构无法容纳被害人以超出证人的身份参与审判程序。传统理论将审判视为处于平等地位的公诉方与被告方为寻求刑事争议解决,在消极中立的法官、陪审团前,积极主张各自版本的“事实”并破坏对方“事实”的激烈竞技活动。〔46〕Nico Jörg,Stewart Field&Chrisje Brants,Are Inquisitorial and Adversarial Systems Converging?in Phil Fennell ed.,Criminal Justice in Europe:A Comparative Stud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42;Jill Hunter et al,The Trial:Principles,Process and Evidence,The Federation Press,2nd edition,2021,p.3-4.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被害人不得提出独立于公诉方的主张并进行举证、质证,而只能在控辩双方有需要时,出庭履行作证义务。同时,本质为对抗的刑事审判不具备处理被害人情感创伤和私人冲突的能力。〔47〕Jonathan Doak,Victims'Rights in Criminal Trials:Prospects for Participation,32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94,297(2005).尽管当前的刑事审判为性犯罪被害人、未成年或认知能力受损被害人等脆弱群体提供了诸如视频作证、陪同作证等特殊保护措施,以及禁止律师在交叉询问中采用误导,过度重复、骚扰、压制,或者仅基于成见等不当问题和贬低、侮辱性的发问方式,〔48〕Evidence Act 1995(NSW)s 41.带有浓厚竞技色彩的审判仍然可能加剧被害人的被害创伤。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通常被置于“零和游戏”的语境加以解读,增强被害人在刑事审判中的参与即意味着削弱辩护力量,故而损害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澳大利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石在于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其程序和证据规则主要以维护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为目的。正如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High Court of Australia)在Rv.Carrol案中所言,刑事审判的大量规则反映出两个明显的主张:其一,国家作为控方所享有的力量和资源远远超过被告人;其二,被告人面临的定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49〕R v.Carrol(2002)213 CLR 635,643.而在控辩对抗的两造诉讼结构中,被害人往往被归为控诉一方,与公诉方形成天然同盟。如果增强被害人参与,可能强化指控,使控辩失衡,增加被告人获得不公正待遇的风险。
这一担忧普遍存在于澳大利亚司法界。例如,维多利亚律师与刑事律师协会(Victorian Bar and Criminal Bar Association)强调,必须平衡促进被害人参与诉讼的改革和其对审判公正性的影响。〔50〕See 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supra note〔2〕,at 28.检察官作为“司法大臣”(Minister of Justice)应当独立、公正、公平地开展公诉活动。〔51〕Whitehorn v.the Queen(1983)152 CLR 657,663-664.一方面,检察官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应维护包括被害人利益在内的广大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其负有公正客观义务,须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因此,维州公诉办公室也明确反对被害人积极参与,认为如果允许被害人在审判中提出独立主张,将造成控辩失衡以及公诉方和被害人合作的表象,有损公诉独立性。〔52〕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Vic),The Role of Victims of Crime in the Criminal Trial:Submission to the 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p.9.被害人利益与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紧张关系还体现在判例法中。以维州最高法院Rv.Dupas案为例,针对这起谋杀案件,检察官直接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了公诉而未经预审程序。高德瑞(Coldrey)大法官认为,在决定是否许可被告人以预审程序的缺失损害了其公正审判权为由,申请暂停审判程序而先进行预审程序时,不仅应当保障被告人公正审判权,还应当考虑审判迟延将给被害人家属带来的痛苦。〔53〕R v.Dupas(2006)14 VR 228,230-233.经综合衡量被告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以及被害人家属的利益、证人证言质量等情况,高德瑞大法官驳回了被告人的申请。〔54〕Ibid.高德瑞大法官经结合州最高法院的Barton v.R一案,强调预审程序对于公正审判而言并非必要;而且,本案此前已经经过死因裁判程序,只剩两名证人需要交叉询问。因此,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并不会损害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由是观之,在被害人(包括因杀人案去世的被害人家属)无法直接参与审判的情况下,其程序利益与被告人公正审判权尚且存在潜在冲突,何况赋予被害人作证以外的庭审参与机会。鉴于对抗制诉讼传统以及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学者布劳恩(Braun)旗帜鲜明地指出,现阶段更大的好处在于完善被害人作证保护,而非赋予其积极的审判参与角色。〔55〕Kerstin Braun,Victim Participation Rights:Variation Acros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9,p.9.在这场控辩举证能力悬殊,唯有通过正当程序限制来尽力维持双方“平等武装”的较量中,被害人要以第三方当事人的身份融入刑事审判举步维艰。
从诉讼经济和效率的角度,被害人作为第三方当事人参与审判将增加审理时长与成本,并且提高审判组织、安排的难度。审判延迟目前已经是困扰澳大利亚刑事司法的一大难题。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的数据显示,2017—2021年经由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办理的案件,从逮捕犯罪嫌疑人到审判结束所耗费的平均时间为728.6天。〔56〕NSW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Government Website,17 June 2022),New South Wales Criminal Courts Statistics Jan 2017-Dec 2021,https://www.bocsar.nsw.gov.au:443/Pages/bocsar_publication/Pub_Summary/CCS-Annual/Criminal-Court-Statistics-Dec 2021.aspx.通常,从犯罪嫌疑人被正式指控到预审程序(Committal Proceedings)需要的时间在半年到一年,〔57〕Committal Proceedings也译作“移交审判程序”。在澳大利亚,地区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审理的可检控罪行(indictable offence)应当首先由基层法院通过预审程序查明是否存在足够的证据支持公诉,以确定是否将案件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如果被告人被移送审判且保释,则最终的审理日可能又要排在一年后。〔58〕ACP2.无疑,被害人作为第三方当事人参与预审程序和正式庭审,将进一步增加举证、质证环节的复杂性,加剧审判迟延,不利于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进而影响其公正审判权的实现。
在过去三十年中,澳大利亚的被害人诉讼参与权虽然逐渐兴起,增加了警察、检察官等司法工作人员对被害人的通知、咨询等义务,但这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检察官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为被害人提供当事人地位以至于颠覆对抗式刑事审判传统。〔59〕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The Role of Victims of Crime in the Criminal Trial Process,Consultation Paper(2015),p.54.
(二)中国审问制审判的结构兼容
相较而言,我国的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缺乏强烈的控辩对抗,在理论结构上可以接受被害人以超出控方证人的身份参与其中。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对抗元素引入审判的举证、质证环节,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和1979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的审问制审判结构。追求实质真实是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在其引导下,事实发现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主要靠控方举证、合议庭核实刑事案卷内包含的证据以及庭审中提出的证据。审判人员仍然享有讯问被告人、询问被害人的权力,合议庭也保留了独立调查权。尽管随着以庭审实质化为目标的司法改革的推进,在试点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辩护律师庭审参与度有所提升,庭审对抗性得到一定程度强化,但辩方在事实发现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十分有限,“庭审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60〕参见左卫民:《地方法院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17—119、124—125页。我国证人出庭率依然非常低,辩护律师往往无法当面询问相关证人。〔61〕参见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效、瓶颈与出路》,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159—160页。即使在证人出庭的场合,由于缺乏以“证伪”为目标的交叉询问机制,辩护律师通过“轮替询问”这一相对温和的方式来促进事实发现的难度较大。〔62〕参见龙宗智:《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第25页;郭彦:《理性 实践 规则 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的成都样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144、153、177页。由此,我国的事实发现路径并非构建于以控辩双方激烈交锋为特征的两分式审判结构,控辩双方对抗性之不足和交叉询问规则之欠缺突出了国家权力在事实发现方面的中心地位,同时也相对减少了刑事审判给被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再者,对实质真实的追求和合议庭的独立调查权,使得事实发现可以突破控辩双方的举证范围,获取不同来源的证据信息。即“为查清真相,法院依职权应当将证据调查涵盖所有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材料”。〔63〕施鹏鹏:《“新职权主义”与中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基本路径》,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85页。作为法定证据来源的被害人在审判中不仅可以作为广义上的“证人”接受控辩双方和审判人员询问,还能作为当事人具备一些有助于发现实质真实的庭审参与机会,包括: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的权利;在审判长准许下,就公诉人讯问的犯罪事实向被告人补充发问;申请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申请调取新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参与法庭辩论等。不仅如此,被害人的诉讼代理律师也享有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调取新物证等诉讼权利,能够积极推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协助合议庭查明案件事实。其角色进一步体现了我国刑事审判以发现实质真实为基本任务,与审问制审判结构兼容。
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允许因犯罪遭受直接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民事争议应当与刑事案件一并审判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刑事审判在结构上可以容纳私人利益的事实。因此,从理论和立法的角度,我国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结构下的审问式法庭程序较澳大利亚的对抗式刑事审判更能包容被害人利益,允许其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刑事审判。
四、不同法律传统的趋同
(一)重视被害人权益
过去四十年间,中澳两国在改善被害人困境方面进行了大量立法、政策改革。如今,澳大利亚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角色不能再简单归作证人。尽管被害人诉讼参与权的进路保守,司法机关逐渐重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意见,使其以诉讼参与人的崭新身份回归刑事司法程序。被害人权利框架的完善和“权利专员办公室”的建立,表明被害人参与对抗式刑事司法程序的能力得以提高,也说明传统的对抗式诉讼结构与关照被害人利益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各司法区为脆弱证人提供了一系列旨在减少二次伤害的保护性措施,包括性侵被害人通讯秘密特权、性侵被害人作证时禁止公众旁听、允许脆弱被害人通过视频作证和在支持者陪伴下作证、突破传闻证据规则从而允许采纳脆弱被害人在侦查阶段接受警察询问时的录音录像资料来代替主询问等等。〔64〕Criminal Procedure Amendment(Sexual Offence Evidence)Act 2004(NSW);Criminal Procedure Amendment(Evidence)Act 2005(NSW);Criminal Procedure Further Amendment(Evidence)Act 2005(NSW);Criminal Procedure Act 2009(Vic)pt 8.2,s 389F;Evidence Act 1929(SA)ss 12AB,13A.另外,被害人能够获得专业性和全面化的服务,既享有利于其回归正常生活的专业心理咨询、财务援助服务,也可获取与刑事诉讼相关的信息服务和作证保护。在中国,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引入了加强控辩双方对抗性的当事人主义诉讼元素,但它也同时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以及一系列诉讼参与权。同时,随着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和作证保护制度的确立,以及信息服务的改善,被害人在诉讼中面临的困境有所缓解。因此,从立法、政策所构建的被害人权利框架角度,中澳两国在促进被害人利益和优化其诉讼参与方面展现出一定趋同。
(二)区分公私利益
1.澳大利亚犯罪追诉中的公私利益区分
除对抗式司法传统固有的结构限制和对被告人公正审判权的顾虑外,公私利益区分也是英美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抗拒被害人积极参与诉讼的一大原因。阿什沃思和加尔卡威(Garkawe)等学者在认可被害人对刑事司法存在固有利益的同时,认为应当严格区分追诉犯罪的公益与被害人的私益。在其看来,犯罪主要是针对国家的行为,故而应由国家机关通过追诉、惩罚犯罪来实现维护公共秩序的公益;尽管被害人也因犯罪受到了损害,其个人利益不应介入属于公共领域事项的犯罪处置。〔65〕Andrew Ashworth,Victim's Rights,Defendants'Rights and Criminal Procedure,in Adam Crawford&Jo Goodey eds.,Integrating a Victim Perspective within Criminal Justice:International Debates,Ashgate Publishing,2000,p.200.刑事审判被视作国家与被告方之间去私人化的较量,被害人只能参与“合法关切的事务”,即限于损害弥补方面,而不得“外溢至公益领域”。〔66〕Ibid.阿什沃思甚至认为,赋予被害人在检察官决策前获得咨询的权利也并无必要,而应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对被害人的尊重,包括告知并解释起诉决定,以及确保检察官就赔偿令而向法庭提交的陈述具有坚实的基础。〔67〕Andrew Ashworth,The“Public Interest”Element in Prosecutions,Criminal Law Review 595,598(1987).加尔卡威主张,被害人的利益可以通过构建和谐的被害人—公诉人关系实现,具体途径为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受)咨询权,并且咨询以事先筛除被害人不当法庭言论为目的,无需赋予被害人实质性诉讼参与权。〔68〕Sam Garkawe,The Role of the Victim during Criminal Court Proceedings,17 UNSW Law Journal 595,609-611(1994).
澳大利亚的公诉政策和公诉实践坚持公私利益有别的基本立场。检察官如果发现公私利益存在冲突,必须服务公益而非被害人个人利益。就追诉性侵犯罪而言,基于被害人可能遭受严重二次伤害和其通常是最重要或唯一的控方证人的现实考虑,被害人放弃追诉的请求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公诉人的起诉、撤诉决定。笔者与新州检察官的访谈揭示,性侵被害人是否愿意继续追诉往往是影响检察官起诉、撤诉决定的“头号原因”,〔69〕ACP 4.检察官很少违背被害人的意愿继续追诉。〔70〕ACP2,ACP3 and ACP4.ACP2更是表示,其很少在性侵犯罪被害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被指控人的认罪答辩。一项违背性侵被害人意愿的决定,包括撤诉、接受认罪答辩、变更指控罪名必须最终由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做出。〔71〕ACP2 and ACP4.即便如此,如果被害人为未成年人或者认知能力受损之人、被告人为惯犯、犯罪情节严重等案件,检察官往往决定起诉,不受被害人意愿的限制。〔72〕ODPP New South Wales,Prosecution Guidelines(March 2021),https://www.odpp.nsw.gov.au/sites/default/files/2021-08/Prosecution-Guidelines.pdf,Chapter 5.近年来,公诉政策尤其对涉及家庭暴力的性侵犯罪十分强硬。在这类案件中,即使被害人不愿追究,检察官为了公益也很可能追诉;极端情况下,检察官甚至会申请强制被害人到庭作证。〔73〕ACP2 and ACP3.再者,有些检察官在性侵犯罪被害人请求不继续追诉时,可能要求被害人提供正当理由,比如精神健康状况恶化。〔74〕ACP3.ACP3认为,性侵被害人对检察官裁量决定的影响应视决定类型而定。如果是关于是否继续追诉,被害人的影响通常特别大;而若是关于指控本身,比如变更指控、接受认罪答辩等事项,被害人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不仅是因为检察官凭其职业素养和经验,更有能力做出正确的指控决策,也是出于对检察官裁量权以及裁量权之基础——公益的维护。ACP1与其他三位检察官相比,对被害人影响检察官起诉裁量的态度较保守。其再三强调检察官决策的基础为法律、公诉政策和证据。ACP1认为,检察官就起诉决定和指控咨询被害人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是为了获得被害人的指示,而是为了告知其将要采取的程序,使被害人参与后续程序,获得被害人意见以及评估被害人意见对决定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被害人的意见并不会对检察官的裁量决定产生太大影响,它们和其他任何可能合法影响决策的事项都将获得考虑”。〔75〕ACP1.总而言之,检察官虽然必须考虑性侵被害人的意见且往往尊重被害人不继续追诉的意愿,但为了某些公益的实现仍会做出与被害人所愿相悖的决定。对被害人证言依赖性极强的性侵犯罪案件尚且如此,更不必说一般证据相对较多的其他类型犯罪案件。
公益与私益的区分还体现在量刑阶段。首先,被害人虽然可以向量刑法庭提交一份书面影响陈述,但该权利的行使受制于公诉机关的裁量。一方面,法庭只接受通过公诉人递交的被害人影响陈述;〔76〕Crimes(Sentencing Procedure)Act 1999(NSW)s 30A.另一方面,公诉人经咨询被害人可以修改陈述内容,并最终决定是否向法庭提交。〔77〕ODPP New South Wales,supra note〔72〕.其次,尽管量刑法庭通过签发赔偿令来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的做法在维州依然可行,但在其他司法区,被害人通常不直接从被告人处获得经济赔偿,而是从州政府机构,例如新州的“被害人服务”,申请经济补偿和心理辅导等援助。由此,被害人的“私益”从刑事司法领域被引向行政法范畴,从而维护刑事司法的公共性质。
2.中国犯罪追诉中的公私利益区分
我国学界关于被害人应然诉讼地位存在观点分歧,但一般认为被害人参与审判应当受到一定限制。学者肖波主张,被害人在审判阶段仅应充当证人,因为积极的被害人参与可能扰乱公诉和恶化本就弱势的辩方处境,而且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违背了犯罪须由国家公力救济的历史趋势。〔78〕参见肖波:《被害人庭审权利的退与进》,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1期,第82—85页。龙宗智教授则从追诉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承担者并非被害人、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将导致控辩审三角诉讼结构失衡、被害人的当事人身份同证人角色冲突等方面来论述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不可取。〔79〕参见龙宗智:《被害人作为公诉案件诉讼当事人制度评析》,载《法学》2001年第4期,第31—33页。另有学者从国家追诉模式角度论证被害人诉权的不完整,认为其不享有起诉权、上诉权、处分权等核心权利,因此应当处于协助公诉的从属地位,并且被害人诉讼权利不应广泛扩张。〔80〕参见张泽涛:《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8—122页。更有学者认为被害人应作为特殊诉讼参与人,虽不享有直接参与庭审就定罪量刑发问和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应当保障其知情权、有限制地允许被害人旁听案件审理,且允许其通过公诉人在庭上表达意见和主张。〔81〕参见胡铭:《审判中心与被害人权利保障中的利益衡量》,载《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68—72页;马贵翔、林婧:《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化的反思与制度重构》,载《河北法学》2020年第1期,第59—64页。
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效果有限。笔者与北京市A、B两区人民检察院4名检察官(共7名)就性侵害犯罪公诉办案情况的访谈、调查数据表明,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的意见并不会影响检察官起诉决定,其中一名检察官更是直言:“刑事司法和被害人无关。”〔82〕CPP5.4名中的3名检察官强调案件证据决定了其批捕、起诉决定。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关注被害人的证据价值,“欢迎被害人有价值的参与”,而该价值体现于“被害人提供有用信息,协助办案”方面。〔83〕CPP2.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部分检察官眼中,被害人的角色和证人无异。其余3名表示在决策时会考虑被害人意见的检察官则认为,被害人的意见是众多参考因素之一,并不能仅凭被害人意愿决定是否批捕、起诉和影响量刑建议。CPP1强调,被害人的意见可能影响批捕决定与量刑建议,但不能影响起诉与否的决定。再者,实践中虽然有被害人、诉讼代理律师与公诉人就罪名认定存在分歧的情况,并且被害人和诉讼代理律师可以在法庭中提出不同于公诉罪名的主张,但是根据CPP1多年的办案经验,这样的分歧不大可能出现在其承办案件的正式法庭审理中。这是因为在此之前,CPP1会向被害人“释法说理”,尽量减少双方分歧。CL2和CL3认为,当前立法虽然逐渐完善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但书面上的法律与行动中的法律仍存在较大差距,部分检察官、法官的“官本位”思想阻碍着被害人有效行使诉讼权利。另有学者发现,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更多限于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而在其他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很少听取被害人意见;部分法官为了防止拖延庭审时间和确保庭审有序进行,通常不愿意通知被害人出庭。〔84〕刘玫:《论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善及保障》,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41页。尽管2018年《刑事诉讼法》和《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时听取被害人意见,但实践中该意见听取情况不尽人意。比如,一些法院因注重诉讼效率而忽视被害人参与,或者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未给予充分重视。〔85〕张素敏:《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H省Z市两级法院司法适用现状为样本》,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34页。
其次,诉讼代理律师作用受限也导致被害人不能有效参与刑事审判。CL2和CL3指出,目前实践中,部分检察院和法院不允许诉讼代理律师阅卷,并且副卷从不允许律师查阅。而副卷因可能包含法院内部领导批示等文件,故其意义往往大于正卷;在庭审程序中,某些基层法院法官不让诉讼代理律师就刑事争议发问,将其参与限定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CL1认为,当前某些基层法院的法官由于习惯思维,往往认为被害人诉讼代理律师的作用在争取民事赔偿方面。因此,如果即将开庭审理刑事争议,法院在电话通知诉讼代理人开庭时,往往预判代理律师不打算参加——“明天我们开庭审理刑事部分,你不用来了吧?”〔86〕这一点也可从其他学者开展的研究得到印证,通常法院只通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出庭。见前注〔84〕,刘玫文,第141页。在庭审中,法官有时也不会意识到被害人和诉讼代理人想就刑事部分发言。此外,受访检察官也一致认为诉讼代理律师的主要作用在于为被害人争取民事赔偿。这与立法所确立的诉讼代理律师角色有相当差距。受访诉讼代理律师一致主张,其角色不应囿于帮助被害人获得民事赔偿方面,而也应参与定罪、量刑的审理。然而,当被问及诉讼代理律师在定罪、量刑部分的具体作用时,三名诉讼代理律师认为其应当扮演辅助性角色,通过提供线索、补充信息,达到“补强公诉”的作用。〔87〕CL1,CL2 and CL3.
由此可见,起诉的控制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公诉人手中,并未因被害人享有当事人地位和诉讼代理律师帮助而受到威胁。即便被害人在立法层面享有提出不同于公诉主张的权利,实践中对公诉的影响甚微,并且参与刑事争议解决的作用因部分检察官、法官的权利意识淡薄、习惯、态度等因素而难以发挥,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主张个人权益的实际能力有限。因此,我国的强职权主义刑事诉讼虽然在理论上缺少被害人参与审判的结构性限制,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见得欢迎被害人积极参与。司法官员在严格区分公私利益的同时,可能忽视对被害人诉讼权益的尊重和保护。
(三)趋同因素
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程度并非单纯由各国诉讼结构这一内因所决定,应当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理解为在外部因素作用下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放眼世界范围内英美法系国家和欧陆国家被害人权利演进的一般路径,推动被害人融入刑事诉讼的外因主要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区域人权公约和组织对各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88〕Doak,supra note〔28〕,at 28-33;Tyrone Kirchengast,Victimology and Victim Rights: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Routledge,2017,p.72-75.各国被害人、女权草根组织运动;拥有相同或不同法律传统国家之间的法律移植、政策借鉴;〔89〕Jo-Anne Wemmers,Victim Policy Transfer:Learning from Each Other,11 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121,121-122(2005).学界对刑事司法制度的反思,刑事审判应当考虑“利益三角”(triangulation of interests),即关照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并且应当灵活适应变化中的社会需求。〔90〕Terese Henning&Jill Hunter,Finessing the Fair Trial for Complainants and the Accused:Mansions of Justice or Castles in the Air?in Paul Roberts&Jill Hunter eds.,Criminal Evidence and Human Rights:Reimagining Common Law Procedural Traditions,Oxford Hart Publishing,2013,p.351;Tyrone Kirchengast,The Criminal Trial in Law and Discourse,Palgrave Macmillan,2010,p.5-6.
澳大利亚被害人权利框架的形成受到上述外部因素的极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被害人权利运动浪潮以及1985年联合国《受害者宣言》促进了各州、领地《被害人权利宪章》的出台与被害人服务的完善。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美国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被引入南澳,为被害人提供了参与量刑程序以获得疗愈和影响量刑的机会。被害人权利也逐渐从被害人作为证据来源的工具性价值转向其生而为人应享有的尊严待遇之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欧洲人权法院等等公约和组织为澳大利亚被害人权利的发展带来了如下启示和发展:第一,公正审判权不再被认为是被告人独有的一项基础权利,被害人作为审判参与者同样应当获得公正待遇。〔91〕Victor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supra note〔2〕,at xiv.出庭作证的被害人,尤其是性犯罪、未成年、认知能力受损等脆弱被害人有权获得特殊作证保护措施,从而更好地参与法庭审判。第二,人人享有免受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这不仅意味着办案机关应改善对待被害人的态度,也同时禁止辩护律师在交叉询问被害人时采用过度压制、恐吓、骚扰等问题和以贬低、侮辱或其他不当方式发问。第三,生命权和人身安全权要求保释、假释机构在决定是否保释、假释时,允许被害人提出安全顾虑并予以考虑。第四,隐私受尊重的权利要求法庭不公开审理性犯罪被害人出庭作证部分,保障其通讯秘密特权,并且法庭可以依职权或申请签发抑制令(suppression order)或禁止发布令(non-publication order)以保护作证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推动我国与被害人相关法律、政策改革的因素不同于澳大利亚。我国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路径尤其强调高层的政策统筹和最高司法机关的引领地位。高层在改善被害人困境方面最直观的作用表现为:由中共中央政法委引领、协调国家司法救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作为司法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最高司法机关通过颁发司法解释、诉讼规则等指导性文件,落实被害人权益,包括规定司法机关应告知符合条件的被害人可以申请国家司法救助、对部分未成年被害人开展特殊帮扶、纠正办案误区从而减少谬见对事实认定的影响〔92〕例如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发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该文件纠正了部分基于对被害人的性别偏见而形成的强奸谬见,要求办案机关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认定强奸罪不能以被害妇女有无反抗表示作为必要条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对被害人的公平性。等方面,学界对被害人权利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兴起的被害人学研究以及早前关于被害人地位和诉讼权利的学术争鸣为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持。国际被害人权利运动和人权公约对我国被害人权利演进的直接影响较小。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在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保障被害人权利成为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对被害人权利的完善渐渐向《受害者宣言》确立的标准看齐,比如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和倡导恢复性司法理念。
虽然中澳两国刑事被害人权利发展的驱动力存在差异,但也存在促进两者趋同的客观因素。首先,由于两国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面临某些相似问题,例如信息欠缺、〔93〕以新州为例,尽管“证人援助服务”(WAS)及时为被害人提供了有关其权利、诉讼流程、开庭日期、可用服务等方面的信息,但ACP3、ACP4表示,检察官为了确保被害人法庭证言不被污染,通常不会告知被害人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信息,包括DNA证据。有时候,部分检察官甚至不会告知其指控的罪名。二次伤害等,两国都承受着改善被害人处境从而化解纠纷、节约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压力,故具有一致的改革内在动力;其次,频繁的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法律移植和政策借鉴营造了良好的理论环境;再次,联合国《受害者宣言》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人权公约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国被害人权利框架的构建,成为改革的共同参照。〔94〕Kirchengast,supra note〔88〕,at 75.最后,一致的司法价值观是具有不同法律标签或司法形态国家间趋同的关键因素。〔95〕PJ Schwikkard,Convergence,Appropriate Fit and Values in Criminal Process in Innovations,in Paul Roberts& Mike Redmayne eds.,Evidence and Proof:Integrating Theory,Research and Teaching,Hart Publishing,2007,p.338.对公平、正义和人权保障等基本价值理念的追求应成为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被害人权利发展趋同的共同基础。
五、结 语
中国与澳大利亚赋予了刑事被害人迥异的诉讼地位。两国被害人权利框架的构成并不相同,前者以诉讼参与权为核心,知情权、国家司法救助和作证保护等服务权则发展滞后;而后者主体为服务性权利,被害人提交被害影响陈述、获得咨询、对不起诉和撤诉决定申请复议等诉讼参与权数量较少,位于权利框架的外缘。中澳两国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分布于不同阶段,前者参与权存在于审判(定罪量刑)之前与审判阶段,而后者限于定罪程序前后阶段。两国被害人权利框架的构成差异可归因于对抗制与审问制诉讼模式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设置的不同结构性限制。澳大利亚对抗制审判结构与被害人以第三方当事人身份参与并不兼容,而本质上缺乏竞技对抗性的中国审问制审判能够包容私人利益,允许被害人以超越证人的身份参与其中。然而,同我国检察官、律师的访谈和调查数据表明,严格的公私利益区分存在于我国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学界、实务界普遍对被害人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持谨慎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部分检察官、法官缺少被害人权益保障意识,致使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律师的诉讼权利难以充分行使。实际上,被害人融入司法程序的程度并非仅由诉讼理论结构所决定,它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包括实践中司法官员对公私利益界线的把控、对被害人参与的态度和保障被害人权利的意识,也包括法律和政策改革背后的多元动力。毋庸讳言,中国和澳大利亚被害人权利框架形成的动因有明显差异,但却客观促成了当前两国在被害人权益方面一定程度的趋同。
本文从中澳两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害人权利演进切入,试图探索拥有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在完善被害人权利方面存在的分歧与趋同。分析适当结合了实证研究方法,但因研究样本较小且限于北京市和新南威尔士州,故无法全面论证分别采纳(强)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结构的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利益的包容度和差异性。未来相关研究可延续实证研究思路,采用访谈、问卷调查、法庭观察等方法,充分探讨两种诉讼结构在容纳被害人利益、允许被害人参与方面的实际限度。
应当强调的是,在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关注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尤为必要。首先,要推动庭审实质化、提高证人出庭率,强化控辩双方平等对抗,需进一步思考被害人应以何种身份适应变革中的庭审程序、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的合理限度。并且,需明确作为证据的被害人陈述的形式、当庭询问被害人的适当方式和顺序等,确保司法改革在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同时,不致损害被害人权益。其次,应当重视刑事诉讼给被害人带来的二次伤害。这是目前我国学界、立法和司法相对忽视的一个问题。除了司法机关针对性侵儿童案件颁布了一些办案指南以及极少量的可适用于性侵成年被害人的规则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分类并规定区别对待。这导致某些脆弱被害人群体,例如性侵成年被害人、认知能力受损被害人,容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一步遭受创伤。在这方面,澳大利亚预防和减少二次伤害的各项举措,包括:提供全面和专业的被害人援助、保持办案机关同服务机构的密切合作、区分被害人类型从而为脆弱被害人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作证保护、适当限制辩护律师交叉询问脆弱被害人的方式等等,可供我国学习和借鉴。最后,应当强化我国司法官员对被害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意识。具体可通过长期、定期教育和培训的方式来促进法律职业文化转变,树立良好的为民服务理念。改善司法工作人员办案过程中对待被害人的习惯和态度,才能有效减少刑事诉讼给被害人造成的二次伤害以及真正落实法律所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