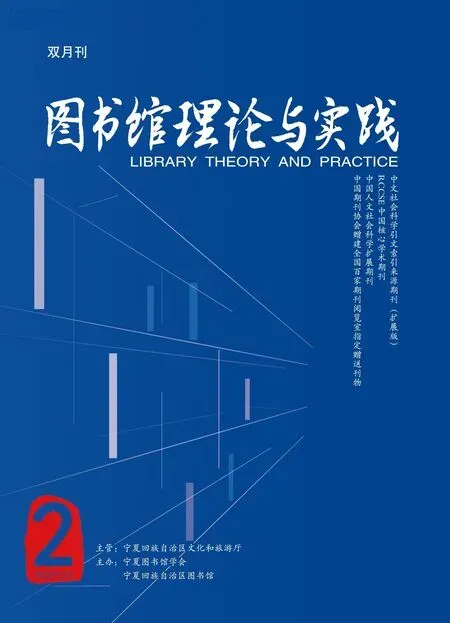关于智慧图书馆建设的几点思考
——专访吴建中先生
吴建中,郭生山(.澳门大学图书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郭生山:建中先生,您好!请益有日,诚邀已久,今天欣获良机,就教于先生,一慰所愿。先生无论在图书馆实践管理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建树丰硕,贡献良多。先生于业界之引领、担当,学术涵养与文人风度,素所为业界学界同人敬重。今天机会难得,我抱着将所有疑问一股脑儿抛出来的想法,大胆向先生求教,意在廓清迷雾,直见真章,实为罕遇之契机。提问不当之处,还请先生见谅。
吴建中:郭主编,您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无论在理论导向还是在实践探讨上一直都很有特色,是业界认可度较高的一份专业刊物。虽然最近有较多机会参与研讨和发言,但总觉得对一些问题阐述得还不深,探讨得还不够,期待有一个对自己的想法再整理再补充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更应感谢贵刊给我提供的这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就一些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做深一步的研讨。
郭生山:好,我就斗胆直接提问了。寻踪先生理论研究脉络,举凡图书馆发展新的动态,先生均有新论,能够由高屋建瓴的视角予以阐论,廓清迷氛,点题朗晰,足资业界之认识和取法。当下图书馆发展又面临着新的态势,那就是智慧图书馆的蓬勃兴起,隐约展现着图书馆发展的美好前景,令业界怦然心动。有关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已呈喷涌之势;业界各种探索的触角不断延展,亦各有所呈。但在一切浮出水面之前,当下的智慧图书馆尚不明朗。跟许多同行一样,我也怀着许多的疑问,借此契机,请先生予以指点。智慧图书馆如何从理念上来理解?智慧图书馆可以简单地理解为Smart Library吗?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业态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智慧图书馆显在的方面是引入和借用大量的现代技术,那么图书馆对技术的追逐,会没有尽头吗?智慧图书馆是不是就是技术主导下的图书馆?
吴建中: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常有同行抱怨说,智慧图书馆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一直说要启动,但不知道从何入手,总觉得这是技术活,是技术人员的事。因此大家对我提出的智慧图书馆不是一件技术活的观点很感兴趣,也很有同感。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智慧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的关系。有人以为我们又要搞一个类似数字图书馆的大规模项目了。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文化行业相比,属于比较亲近和拥抱技术的行业,国外从几十年前就开始从事数字图书馆的工作了,国内稍晚一些,但从世纪之交开始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在这些年里,各地建设了无数个数字图书馆或数据库,基本完成了精品馆藏数字化复制的工作,成效很大。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数据库之间缺乏联系,利用率也不高。所以,大家开始重新评价数字图书馆利弊的问题,如果说数字图书馆仅仅是为了将已有纸本馆藏数字化,那它的使命已经到尽头了。智慧图书馆的指导思想,其一是改变以藏为主的传统思维,将使用和增值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像传统图书馆到现代图书馆转型时从“以藏为主”到“以用为主”的认识过程一样;其二是为什么说智慧图书馆不是一个技术导向的工程?数字图书馆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发挥现代通信技术应有的长处,而是迁就了传统图书馆以藏为主的思维。智慧图书馆不能简单地翻译成“Smart library”,似乎只要我们使用智能技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这样我们又会走回数字图书馆的老路。智慧图书馆不是一项具体业务或技术工程,它是一种高度智慧化的知识服务体系,它强调的是全媒体、平台化和新业态,我在《建设智慧图书馆:我们准备好了吗?》一文中已经详细提到这个问题,这里不再赘述。
郭生山:听先生阐述,不禁有一种恍然而现的开悟。去年以来,新文科建设蔚然而兴,再加之学界长期以来助推的图情档一体化建设,似乎在学术领域酝酿着一种变革,我不敢判断是不是根本性的,但其影响确为巨大,那就是图书馆学科改名和学科重组。表象之下,是不是深层隐藏着对图书馆再认识的问题?是不是新的一体化后的学科要超越图书馆学?或者淡化和稀释图书馆学?能够诞生或者形成新的学科体系吗?这种学科发展与智慧图书馆建设如何对接?如何在新的学科发展现状下理解智慧和认识智慧图书馆?
吴建中:这个问题的角度选择得很好,涉及图书馆学本原的问题。学界不少人对图书馆学这门学科感到过于传统了,所以老是想着改名。但数字图书馆也好,智慧图书馆也好,这些高度现代化的东西都与图书馆三个字有关,不少名人纪念馆明明是档案馆,人家也喜欢借用图书馆的名称。图书馆是人类文明最美好的伴生物,我们为什么要嫌弃它呢?
我在博客中这样说过:图书馆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物理形态的存在,当博尔赫斯描述或想象图书馆的时候,透过一个个连着的六边形的小图书馆,他看到的是无限延展的宇宙,所以他认为,图书馆就是宇宙,宇宙就是图书馆。很多建筑设计师想表达他们对博尔赫斯的敬意做了一些有趣的设计和模型,包括我国的王树,说明人们仍然把图书馆看作人类最美妙的存在。在这方面,从事图书馆或图书情报学的同人们是应该有点愧疚感的。图书馆学科改名不是一个学科建设的问题,而是对“图书馆”认识的问题[1]。在智慧图书馆大规模建设时,我们需要对图书馆有一个再认识。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时,整个学界错过了从理论上对数字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关系的探讨,把它仅仅看作技术问题。现在,大规模展开智慧图书馆建设之前,学界和业界需要联手对此做一个共同探索。新文科建设的兴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探讨图情档一体化,而不是图情档再分工的问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即图情合并,全球不少国家级图书馆或省市级图书馆将图书馆与档案馆合并,即图档或图情档合并,这两件大事国内都没有跟进。以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为例,它管辖着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26个公共图书馆。在其《2025图书馆档案馆蓝图》(2025)中,该局提出了四个战略:学习超市(Learning Marketplace)、市民素养(Informed Citizenry)、狮城寻根(Singapore Storytellers)和消除鸿沟(The Equaliser)[2]。该蓝图将图书馆和档案馆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讲得很透,如图书馆打破围墙走向社会、为提升民众素养服务、民众与图书馆和档案馆一起讲好新加坡故事、全社会携手共同消除信息鸿沟等。该蓝图是根据新加坡“智慧国家2025”计划制定的,这不就是一个智慧图书馆规划吗!四个具体的战略哪一个不需要用到智能技术啊!之所以用“智慧图书馆”,而不是“智能图书馆”,内涵上差别很大,“智能”侧重以智能设备取代人,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的作用,而“智慧”强调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同时,注重知识共有和分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智慧图书馆建设从一开始就要强调“以人为本”。
郭生山:我们都熟悉先生的“三代图书馆”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科学地准确地阐述了图书馆史,对于认识图书馆发展历程、厘清图书馆不同阶段的业态,具有提纲挈领的价值,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图书馆史研究方面发凡起例式的学术建树。这里想请教先生的是,智慧图书馆属于先生理论的第三代图书馆序列吗?还是超越了第三代图书馆,或者能说是“第四代”图书馆形态?
吴建中:关于第三代图书馆,就好比智慧图书馆一样,讲的是一种理念。第一代图书馆是以收藏为中心的;第二代图书馆是开放型图书馆,但仍以书为主体;第三代图书馆是前两代图书馆的超越,突出“人”和“知识”这两大要素。我们现在正在转型的过程之中,绝大部分图书馆目前仍处于第二代。第三代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最高境界,即“以人为主体的全媒体知识库”,这是相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的特征而言的。今后再进步的话,我们可能会换个说法了,因为整个场景不一样了,但“以人为主体的全媒体知识库”是一个理想状态,估计十年、二十年之内是完成不了的。
智慧图书馆与第三代图书馆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就像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的《2025图书馆档案馆蓝图》一样,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智慧图书馆项目,它是一个大平台,读者在商场电梯内与图书馆进行知识对话也好,市民讲述狮城故事也好,都涉及民众的参与,读者通过获取信息、发表意见、合作研讨、生产知识等,为平台、为他人也为自己增加价值。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智慧图书馆,而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孤岛”的再现。
我国知识消费旺盛,社群参与踊跃,智能技术发达,相信智慧图书馆一旦做起来,一定会更精彩,但这是需要顶层设计和精心策划的。目前这一阶段,取得共识、统一步骤是当务之急,千万不能无谓地争论下去了。
郭生山:智慧图书馆预示着图书馆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是毕竟目前还未有建成的样板。我想业界肯定都和我一样,存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想要急切一睹智慧图书馆面目。就我们当下的理解,肯定是由目前实体图书馆状况出发的,无法超越实体羁绊。那么,未来智慧图书馆还需要建筑吗?还需要实体资源吗?它的资源组成是单一的还是多类型的?智慧图书馆肯定面临着更加浩瀚的资源,如何组织这些资源,如何发展出更先进的检索手段,才能实现检索的精准化?
吴建中:您的提问就像一篇文章的归纳,可能会重复已经讲过的内容,就当作一个全面梳理吧。首先,从建筑的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是一个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新业态,图书馆空间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部分,但过去那种阅览室围绕书库转的传统模式肯定要改变了,图书馆本身就像一个大平台,读者既可以获取信息、交流信息,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和创造价值。澳门大学图书馆建了一个媒体实验室,虽然空间不大,但老师和学生都愿意来制作自己的东西,这也是平台化的一部分啊。图书馆不仅提供文献,而且也提供工具,让读者参与创意和创造。有人曾说,创客空间是一阵风,这说明我们没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创客空间是让读者走进图书馆、与别人合作、参与价值创造的空间,我觉得这不是一阵风的问题,而是图书馆没有设计和组织好,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其次,是否还需要实体资源的问题。在纸张发明之初,上流社会对印刷品是不屑一顾的,在《大风歌》这部讲述西汉故事的电视剧里我们看到上流社会用的是竹简,而普通大众用的是纸张,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上下层对印刷品的态度。其实,纸质出版物成为主体资源以后,图书馆也没有丢弃手稿,反而把手稿珍藏了起来。智慧图书馆关注的是全媒体资源,就像《建设智慧图书馆:我们准备好了吗?》一文中所提到的四位一体藏品,我们过去只重视前两项即实体资源和实体资源的数字化,而对原生数字资源和创新型数字资源的关注度不高,所谓创新型数字资源,就是可检索的诸如研究成果和社交媒体等的资源[3]。今后,实体资源会更加稀缺,更有文物价值,很多图书馆都在做原有善本库的“提善”工作,像澳门大学图书馆,已经开始珍藏民国早期的出版物了。再次,是资源组织化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智慧图书馆来说不算是个问题,因为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精准组织和使用信息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在实际运行中难度很大。以前文献是分开管理的,今后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一个大池子里,然后各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开发资源,并开展各种服务,那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图书馆组织架构的问题。以前组织架构是跟纸本资源走的,先有采编部,再有阅览部,再有流通部、保管部等。网络文献出现以后,图书馆在原有组织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网络服务部,然后与网络有关的部门一个个增加,形成了“两张皮”现象。也有不少图书馆开展了机构重组,按知识流重新组织,将数字和网络服务融入图书馆整个服务体系之中。对于大型图书馆来说,将所有资源放在“大池子”中的设想不容易实现,而这正是智慧图书馆的要求,而且要在目录体系中完整地体现出来。
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是对涉及智慧图书馆问题的延伸性探讨,而且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思路再整理的过程。我相信,如同图书馆是永恒的一样,我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和探讨也是无止境的。
郭生山:向先生请教,颇为惶恐,深恐自己的理解与研究流于庸肤,问题提了不少,但不知是否切中了先生的学术兴趣点,能够引发先生的娓娓道来,得到一场尽兴的学术传授。不过随着先生的阐述,我逐渐释然,先生的学深养高,总能于我的提问触绪而发,随机而应,切中问题窾要,吐属大雅,足以解颐。在这里深谢先生之稠情古谊,唯愿再觅良机,得以请益。谢谢!
吴建中:客气了,有机会再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