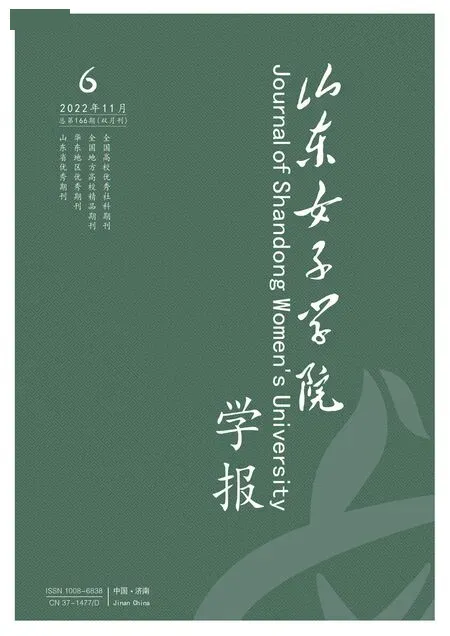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
雷瑞鹏,邱仁宗
(1.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102)
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在《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导论》[1-3]等书中已经有多次论及。美国试图通过司法判决来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撕裂社会的有关人工流产(我们应该使用“人工流产”这一正式的学术术语,而不用“堕胎”这一通俗的但有误导作用的词)伦理问题的争论,有些律法主义(legalism)的味道,律法主义是指试图用立法、司法程序解决社会问题,而缺乏对其根本性伦理问题的研讨。本文扼要地介绍一下人工流产的伦理问题。
人工流产的理由归纳起来有多种。人工流产争论的焦点在于:人工流产在伦理学上是否可以得到辩护?与这个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胎儿是否已经是人?胎儿的道德地位是什么?胎儿有没有生的权利?以及妇女有没有身体权,即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自主决定的权利?这种身体权是否包括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人工流产的权利?人工流产手术涉及孕妇、胎儿(产前生命)以及社会各方的利益,如何在各方价值之间进行合适的权衡?等等。
在伦理学上,我们首先要解决人工流产在伦理学上的可辩护性问题。我们说这个行动在伦理学上可得到辩护,这是指这个行动能得到伦理学的论证,能得到伦理学的论证要求:(1)在伦理学论证中为该行动提出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例如人工流产使孕妇健康受益,避免严重疾病甚至死亡,胎儿还不是人未构成对人的伤害,使家庭和社会受益或至少伤害不大等);(2)所提出的理由作为推理的前提,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人工流产可得到伦理学辩护的结论。例如下列的论证形式:
前提1:凡挽救患病孕妇生命的人工流产均可得到伦理学的辩护;
前提2:孕妇甲患有癌症,继续怀孕将危及她的生命;
结论:因此,对妇女甲实施人工流产可得到伦理学辩护。
人工流产的主要伦理问题如下。
第一,对孕妇实施人工流产必须符合医学适应证。在历史上,由于缺乏安全有效的人工流产方法,伦理学的关注点在于人工流产手术对孕妇的安全性。20世纪下半叶医学已经发明了安全、有效、简便的人工流产方法,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使用。但我们仍然要关注孕妇对人工流产手术是否有医学适应证。要求有医学适应证是为了使人工流产手术达到有益于孕妇、防止可能的伤害或将不可避免的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亦即人工流产的风险—受益比(risk-benefit ratio)对孕妇健康有利。这是实现生命伦理学的第一原则:有益(beneficence)。然而在有了安全、有效、简便的人工流产方法后,伦理学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胎儿的道德地位上。
第二,胎儿的道德地位。人工流产的结果必然是胎儿的死亡。更不幸的结果是人工流产术之后,这个胎儿还是活的。这个特殊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说一个实体的道德地位,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实体的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行动涉及这个实体的死亡问题。在某些表达中,人工流产是一个杀死胎儿或胎儿被杀的问题;在另一些表达中我们说人工流产终止了胎儿的生命。在胎儿的道德地位问题上经典的论证有两个:一个被称为“人类生命论证”(human life argument),认为胎儿是一个活着的无辜的人类生命,其结论是我们采取人工流产技术就是杀死了一个生命,这就是“杀人”,因此人工流产这种行动是得不到伦理学辩护的。另一个论证被称为“人格论证”(personhood argument),认为胎儿还不是人(person),其结论是我们采用人工流产技术终止胎儿这个不是人的生命,就不是“杀人”,这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4]。
我们用逻辑学的公式来表示这两个论证如下:
人类生命论证:
杀人是错误的;
胎儿是人;
因此利用人工流产杀死胎儿是错误的。
人格论证:
杀人是错误的;
胎儿不是人;
因此利用人工流产终止胎儿生命不是错误的。
我们从这两个逻辑公式可以看到关键的分歧在于小前提:胎儿是不是人?这两个论证在各自论证它们的论点时都存在困难。
人类生命论证的困难:人类生命论证既存在理论困难,也存在范围过宽的困难。理论上的困难在于人类生命活着的生物学特性与享有生命权的道德特性之间的联系,任何实体只要拥有胎儿也具备的那些生物学特性也就拥有生命权。这种联系是否成立不是不证自明的,需要进行哲学的和伦理学的论证。单单引用宗教的或政府的权威论述或人们直觉的论述,在理论上都是不充分的。这包括某宗教经书或宗教领袖的言论,或某个强大国家总统的言论,或根据对老百姓的调查,他们都认为从受精卵开始那个实体就是人,这种引述或调查结果都只是描述性叙述,不是论证,不是经过严密论证的规范性结论。关于人类生命论证也面临着范围过宽的困难:因为它似乎把太多的终止人类生命的案例都视为错误的了,因为它们都涉及“杀害人类生命”。例如有意结束那些永远不会有意识的人类生命(如无脑新生儿和处于永久性植物状态者),甚至有意结束一个精子或一个未受精的卵子的生命(它们也是活着的、无罪的“人类生命”)是错误的,因为这也是“杀人”。因此这种人类生命论证在理论上不够充分,而且范围过于宽泛[4]。
人格论证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玛丽·安·沃伦(Mary Ann Warren)[5-6]认为,人格论证最核心的是,一个人(person)或者一个具有人格的生命的特征是意识,特别是感受痛苦的能力、推理的能力、自我激励活动的能力,以及社会交流的能力和自我概念的存在。根据沃伦的说法,一个没有意识的人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沃伦看来,杀人(killing)的错误在于受害者是一个人(person)。由于胎儿显然不是人,人工流产在道德上应该是允许的。
人格论证的困难:沃伦的人格论证也面临理论困难和范围过大的困难。沃伦论证的理论问题是对关于定义人格的心理特征与享有生命权的道德性质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充分的论证。无论是沃伦仅仅断言有这种联系,还是人们普遍认为有这种联系,都不足以确定二者之间存在着实际的联系。沃伦的人格论证也有范围过大的问题。因为胎儿不是人而缺乏生命权的说法似乎也可适用于新生儿。新生儿不拥有意识以及她列出的那些特征。我们可以根据新生儿不具有沃伦所列出的那些特征而杀死那些新生儿吗?再者一个暂时失去意识的人(例如一时性的昏迷)丧失了意识,不能显示沃伦列出的那些特征,那么杀死这个人是否也应该被允许?这显然是荒谬的。人格论证似乎会导致允许太多的这种错误地结束人生命的事件,而人类生命论证似乎会导致将结束本不是人的生命实体都说成是错误地“杀人”[4]。
鉴于人格论证的困难,沃伦于1997年提出胎儿缺乏完全道德地位(full moral status)的论证来为人工流产作辩护[7]。地位(status)这个术语本来是描述性的,例如经济地位(economic status)、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但道德地位是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面前的实体才是正确的。这句话可以有以下多种意义:一个实体的地位是,由于该实体拥有的地位,这个实体在我们作出道德决策时理应得到认真的考虑;问一个实体是否有道德地位就是问他人是否应该考虑这个实体的福祉、利益、价值观;也是问这个实体是否有道德价值(moral value or worth),如果某一实体有道德价值,那就应该加以特殊的对待;也是问这个实体对他人是否能提出道德诉求;当一个实体拥有道德地位时,那么我们对待它就有一个我们的对待是否正确还是错误的问题。例如,你把海滩上的卵石随意扔进水中。这些上万亿卵石在几十亿年来被潮水冲来冲去,它们没有道德地位,虽然有些人愿意收集其中一些颜色和形状特别的卵石。我们对卵石做什么,对它们本身不存在对错问题。如果我们将卵石扔在某个人脑袋上使人受到伤害,那是对那个被你用卵石砸伤的人做了错事,而不是对卵石做了错事。因为卵石没有道德地位,它没有内在价值,只有工具性价值。但在海滩上洗海水浴的人就完全不同了。肆意将卵石扔进海里就是一种不道德、应备受责备的行动。因为人拥有利益和权利,这使人们有义务对他们的福祉高度关注。那么,沙滩上的孩子、狗、珊瑚、海草等这些实体,哪一个有道德地位?根据什么标准来判定?一旦根据标准确定下来,这是不是绝对的?或可随情况或互相冲突的利益而有异[8]?人们发现,除了这些卵石没有道德地位外,沙滩上的其他实体拥有的道德地位有程度的不同。人拥有最高的道德地位,狗则次之,哪些海洋植物是否有道德地位以及拥有多大程度的道德地位可能有不同意见。伦理学家将人(person)拥有的最高程度的道德地位称为“完全道德地位”。说一个实体具有完全道德地位是包括:“一个非常严格的道德推定,即不受各种方式的干涉,包括无故伤害该实体,未经同意或代理同意用该实体进行实验,无故毁灭该实体,等等;一个强的但不一定严格的理由提供援助;一个强的理由对该实体公平对待。”[8]
沃伦援引完全道德地位概念来为她主张的人工流产辩护,并试图解决她的人格论证理论上的缺陷,结果引发了胎儿是否拥有人那样的完全道德地位问题。由于妇女拥有控制她们身体的优先权利,如果胎儿有一些道德地位,但低于完全道德地位,那么胎儿的利益就不会强到可以压倒妇女的利益,毕竟妇女拥有完全的道德地位。仅当胎儿拥有像人一样的完全的生命权的时候,它才能赢过一个怀孕妇女的优先权利。为此她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人拥有完全道德地位,而胎儿却不拥有这种完全道德地位。于是,她提出了一个“行动者的权利原则”(the agent’s rights principle),根据这个原则,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拥有完全和平等的道德权利,包括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一个道德行动者是“一个能够利用理性来辨别和遵循普遍道德规律的人”[7]。
但我们认为沃伦这一补充论证并没有摆脱她人格论证的困难:因为新生儿和处于失智状态的人不是一个“能够利用理性来辨别和遵循普遍道德规律的”人。我们认为,人之所以出生后才成为人,是因为:(1)他出生后具备了一个相对完备的人类有机体,这是他之所以为人的物质基础或条件;(2)更重要的是,胎儿的脑原是一块“白板”,唯有胎儿出生成为新生儿后他的脑才能与他自己的身体及其外界环境产生互动,才能在他脑中建立独特的神经和心理结构,这才形成一个独特的自我,也才具有利用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的潜能。同样,一时性昏迷的人,他仍然拥有这种利用理性来思考和行动的潜能,因此他并没有丧失完全道德地位。
第三,妇女的身体权。我国的《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身体权。即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所有权。简言之,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不是任何人的身体。相应地,《民法典》规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死后自愿捐赠器官的权利,以及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在其身上进行临床试验的禁令。那么除了上述规定外,身体权是否包括一位妇女选择是否生殖、何时生殖、生殖多少孩子的权利呢?是否包括自己选择妊娠、终止妊娠的权利呢?我们认为身体权应该包括这些选择的自由。“终止妊娠”就包括选择人工流产使妊娠终止,结果是胎儿死亡。但同时这个身体权又不是绝对的。即使人工流产,也要求必须在有资质的医院实施,而且要按医学适应证和禁忌证行事。
第四,女性主义对人工流产的看法。人工流产在女性主义的政治学和哲学中一直很重要。第二波女性主义尤其与生殖权利有关。然而,在人工流产问题上并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立场;事实上,在人工流产问题上将“支持选择”(pro-choice)的立场算作女性主义的观点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在寻求为人工流产辩护的女性主义径路的支持者中,裘迪斯·汤姆森(J.Thomson)[9]采取了基于权利的径路。然而,即使在这里,对于胎儿的道德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母亲对她自己身体的权利的相对重要性,女性主义者之间也存在分歧。此外,维护人工流产的其他女性主义的径路则试图将辩论的焦点从个人权利的概念和胎儿的道德地位上转移,至少就认为这取决于胎儿的内在属性而言是如此。相反,有些女性主义者强调的是怀孕的关系性质,以及一个特定的女性对某一特定的妊娠作出决策的情境(contextual)特征。苏珊·舍温(Susan Sherwin)[10]说,妇女个人对人工流产的深思熟虑涉及由情境界定的考虑,这些考虑反映了她们对相关的每个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承诺,包括她们自己、她们所怀的胎儿、她们家庭的其他成员等等。因为没有单一的公式来平衡这些遍及所有可能情况的复杂因素,至关重要的是女性主义者要坚持保护每个妇女得出自己结论的权利,并抵制其他哲学家和道德家为这些考虑设定议程的尝试。同理,伊丽莎白·哈曼(Elizabeth Harman)论证说,早期胎儿的道德地位或者说对胎儿的义务,取决于孕妇对待自己妊娠的态度。根据哈曼的说法,孕妇所作的决定将决定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她选择人工流产,那么这个胎儿在道德上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她选择继续怀孕,那么胎儿就是她孩子的开始,她对这个胎儿有爱的义务。
同样,胎儿的道德地位也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它取决于妇女是否选择与胎儿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对哈曼来说,这有助于说明在失去想要的怀孕和终止不想要的怀孕时,在情感和道德上都可能采取的不同立场。虽然同一阶段的胎儿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相同的内在属性,但它不具有相同的关系属性,因此也就不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
尽管许多女性主义者会维护妇女选择人工流产的权利,然而无论是基于自决的理由,还是基于母亲和胎儿之间独特关系的理由,并非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认为人工流产是没有问题的。对许多人来说,人工流产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正是因为它是女性回应和反击男权社会压迫结构的一种手段。然而,有人声称,胎儿和母亲一样,都是一个脆弱的存在,理应受到保护而免受压迫。妇女受压迫的事实并不能免除她们对其他脆弱生物的道德责任,也不能以此为无视胎儿道德地位问题辩护。在某种程度上,对怀孕和人工流产更加微妙的关系性的解释可被视为处理不同意见的一种尝试。在这方面,妇女人工流产的权利可以被视为行使她道德的自主性也是她个人的自主性的权利,只要她有义务就其特定情况的道德特征作出决定[11]。
第五,在人工流产问题上的价值冲突。人工流产问题涉及胎儿父母、家庭、社会、后代等多种价值的交叉和冲突。过去,人工流产术原始而危险,往往不是夺去母亲的生命,就是危害她的身心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权衡的天平容易倾向禁止一切人工流产,至多允许个别例外。自从有了安全、简便、有效的人工流产方法后,情况就不同了。天平的一端是父母、家庭和社会,而另一端只留下胎儿一方。胎儿还不是人,但毕竟是人类的生命,所以仍然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这个价值不足以赋予其与成人乃至婴儿同样的权利,尽管成人的权利也不是绝对的。当胎儿与父母、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其不得不服从于后者。这一点不是哪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所以,当一个社会人口过度膨胀,像中国以前那样,已经大大影响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会牺牲一些胎儿,但留下来的胎儿可以有更好的照料和更好的前途。反之,在目前的发达国家,人口不但出现零增长,而且出现负增长,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和人口异常老化的情况,这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威胁,这种情况下,胎儿的价值就会因社会的理由而大为增大。另一方面,胎儿虽然还不是人,但毕竟也是人类的生命,其与以后的发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也应给予必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