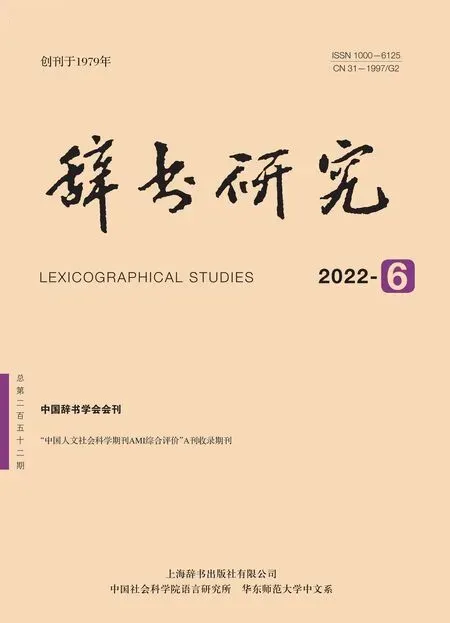汉字发展中的类成字化现象探讨*
董宪臣
“类成字化”是齐元涛和符渝(2011,以下简称“齐文”)基于“成字化”所提出的一个概念。根据齐文:成字化指汉字发展过程中非字构件转变为成字构件的现象;类成字化指一些形体在发展过程中变成了与成字构件同形的形体,但这些同形形体不提供成字构件的音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字构件;成字化的含义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成字化专指非字构件转变为成字构件,广义的成字化还包括饰笔的成字化、低频构件高频化及类成字化三种情况。
关于类成字化现象,齐文仅以“耑”“要”“肩”“犀”等七字为例进行了列举性阐释,未展开讨论。我们认为,类成字化是汉字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和趋势,在近代俗字领域的表现也十分突出,值得重新审视和深入考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隶楷书阶段的类成字化现象为考察重点,主要结合中古碑刻、墓志[1]及近现代字书中的字例,对类成字化的表现形式、特点、与其他文字现象的关系及认知机制等问题做进一步探讨,以期对这种现象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
一、 类成字化的演变指向与表现形式
从本质来说,类成字化是一种字形讹变现象,指在汉字使用过程中,将既有字形或字形的某些部分误写或改造为形近的其他构形要素,这些构形要素形式上表现为成字构件或成字构件组合体,但在新字中并不提供标音或示义功能,与全字音义缺乏关联。为表述方便,本文称这些与成字构件同形异质的构件为“类成字构件”及“类成字构件组合体”。与通常意义的字形讹变不同的是,类成字化具有明确的演变指向,即原有形体向形近的高频构件或构件组合体靠拢。正如张涌泉(2010)85-86在讨论唐佛经中“”(“擾”的本字)右旁或俗写作“憂”时所指出的:“其实这与写字的人厌生喜熟的心理有关。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字的偏旁构件看起来比较陌生,俚俗往往会把这种陌生的偏旁改为相近的比较熟悉的偏旁……据《说文》,‘夒’释‘贪兽也。一曰母猴’,所指本来就含糊不清,并且文献中也没有实际用例,所以这个字对普通人来说显得很陌生;而‘’字恰恰从这个让人讨厌的‘夒’字,称说书写都不方便,于是写字的人便把它写成了形近的‘憂’。”即是说,人们在书写、识记汉字的过程中,每遇到“不成字”或陌生的构件,便倾向于将其改造为“成字”或熟悉的构件,以便记写。
结合文献和字书字例,依据转变前后原形与新形的不同属性和对应关系,大致可将类成字化的表现形式概括为拆分式、黏合式及转写式三种。
(一) 拆分式
独体字或单个构件拆解为类成字构件组合体,新形中各构件均不表音义。这是一对多的转变,在隶变过程中相对常见。齐文所举“→耑”即是其例。又如:
(二) 黏合式
字内位置临近的几个构件(可能分属不同构字层级)黏合成单个类成字构件,该构件通常作为整体直接参与构字,但不提供音义信息。这是多对一的转变,在今文字形体演变过程中相对常见。齐文所举“→履”、[2“]犀→”、“靈→”皆是其例。又如:
“嗣”,《说文·口部》:“诸侯嗣国也。从冊,从口,司声。”构件“口”“冊”的组合与“扁”形近,故全字或从“扁”作“”。北魏孝昌二年《于纂墓志》作(《北图》5/51)、北齐天保四年《崔頠墓志》作(《北图》7/26)。
“席”,《说文·巾部》:“籍也。从巾,庶省声。”[3]字内构件“廿”“巾”的组合与“带”形近,故全字或从“带”作“廗”。该形碑志常见,如北魏正光元年《元譿墓志》作(《北图》4/84)、隋开皇三年《寇奉叔墓志》作(《隋汇考》1/58)。
“莽”,本义指丛生的草。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一引《说文》:“木丛生曰榛,众草曰莽也。”构件“犬”与“廾”(“艸”的变体)的组合与“奔”形似,故该字或从“奔”作“莾”。北魏武泰元年《元宥墓志》作(《北图》5/100)。《字汇·艸部》:“莽,俗作莾。”
“懿”,《说文·壹部》:“嫥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声。”段玉裁注:“‘从恣省声’四字,盖或浅人所改窜,当作从心从欠,壹亦声。”按:依段说,则《说文》字形有误,字本当作“㦤”。碑志“㦤”“懿”二形皆见。构件“壹”“欠(或次)”的组合或讹作形近的“鼓(皷)”形。东魏武定八年《关胜碑》作(《北图》6/161)、唐显庆五年《姚弟墓志》作(《北图》13/181)。
(三) 转写式
全字的某个构件或构形成分讹为单个类成字构件,或构件组合体讹为类成字构件组合体。这是一对一或多对多的对应性转换。主要包括如下情形:
2. 单个构件讹为高频类成字构件。齐文所举“蕤”的声符“甤”讹作“麸”即是其例。又如:
“裔”,《说文·衣部》:“衣裾也。从衣,㕯声。”俗或讹从“商”作“”。北魏建义元年《元彝墓志》作(《北图》5/90)、太昌元年《元文墓志》作(《北图》5/171)。《干禄字书》:“裔:上俗下正。”考其缘由:一则“衣”作为构件参与组字时,通常位于文字下部,如“装”“裂”“裘”“袭”等,“裔”之“衣”符下移应当是受到了这种习惯性组合模式的影响;一则“㕯”字罕见,故在书写时将其改为形近且习见的“商”。
3. 构件组合体重组为高频类成字构件组合体。齐文所举“要()[4]”讹为“西”“女”的组合即是其例。又如:
“勖”,《说文·力部》:“勉也。从力,冒声。”俗书或讹作“勗”,变为“曰”“助”的组合。《正字通·力部》:“勗,俗勖字。”
“滿”,从水㒼声。声符“㒼”构形不明,文献未见单独成字用例。《说文· 㒳部》:“㒼,平也。从廿,五行之数二十分为一辰。㒳,平也。读若蛮。”其说备考。北魏太昌元年《元恭墓志》作(《北图》5/172)、唐开元六年《严识玄墓志》作(《隋唐汇编》陕西卷1/94),将“㒼”变为“艹”“雨”的组合体。
二、 类成字化的特点
通过上述字例不难发现,类成字化的结果往往导致汉字构意的部分或完全丧失。从汉字构形系统的角度看,它也是造成汉字系统偏旁讹混、异体字及俗讹字形大量滋生的原因之一,因此无理性是它的基本特点。此外,类成字化还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
(一) 类推性
某些构件极少独用为字,对人们来说比较冷僻,于是经常被改造为某个形近高频构件。这种改造有时具有类推性,可以类推包含该构件的一批字,使它们产生同类讹形。
“夗”,《说文·夕部》:“转卧也。从夕从卩。”“夗”虽然经常参与构字,但极少单独成字使用。隶楷书“夗”与“死”形近。相较而言,“死”比“夗”更为常见,故从“夗”的字或改从“死”作。唐天宝五载《侯方墓志》“苑”作(《隋唐汇编》洛阳卷11/74)、天授二年《陈崇本墓志》“鸳”作(《北图》17/153)、大中十三年《张昱墓志》“宛”作(《隋唐汇编》洛阳卷14/83)。
“冋”,古同“冂”,构字时常讹作“向”。北魏熙平三年《宇文永妻韩氏墓志》“扃”作(《汉魏校注》4/367)、建义元年《寇慰墓志》“迥”作(《北图》5/75)、正光六年《李超墓志》“炯”作(《北图》4/179)、太和二十三年《元彬墓志》“垧”作(《北图》3/42)。
(二) 多向性
如果一个“不成字”构件拥有多个与之形近的高频构件,这时对该构件的类成字化改造则可能呈现多向性的特点。
“策”,从竹朿声。声符“朿”即“刺”的初文,极少独用为字,人们对它的意义和写法相对陌生,于是或将其改造为形近的“宋”“夹(夾)”“宗”“束”等。北魏永安三年《元液墓志》从“宋”作(《北图》5/136)、孝昌元年《元宝月墓志》从“宗”作(《北图》5/14)、东魏天平元年《张瓘墓志》从“夹”作(《北图》6/23)、唐开元十一年《执失善光墓志》从“束”作(《昭陵碑石》85页)。
(三) 渐次性
部分类成字化改造并不是通过新旧字形成分的直接代换而一步到位的,而是旧形经历了若干连续讹变环节,逐步与新形趋于近同,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渐次性的特点。
例如“屬”,俗作“属”,“尸”下讹从“禹”。清顾蔼吉《隶辨·烛韵》引《尧庙碑》“”字下注:“《说文》:‘屬,从尾从蜀。’[5]碑则省蜀为,他碑或作,亦作。转转相变,并上尾,止存尸头,而下遂为禹字矣。”结合碑志字例分析其字形演变过程:“属”,小篆作;唐开元二十二年《张休光墓志》作(《北图》23/136),此依小篆构造隶定;东汉中平二年《曹全碑》作(《北图》1/176),“蜀”之下部省变近“禸”;东汉建宁元年《杨统碑》作(《汉魏校注》1/269),“罒”省居中二竖笔作“口”形,“ ”之竖笔向下贯通“口”形;唐大中十年《张茂弘墓志》作(《北图》32/134),“ ”之二横笔合并。综上,这个脉络大致是
此外,类成字化改造完成之后,流俗可能还会基于对讹形的错误解读而进一步改造字形。如“能”,当是“熊”的初文。金文作,象熊形。《说文·能部》小篆作,头、口、足离析。隶楷书作“能”,皆承小篆而来,前后足讹为纵排之二“匕”,与“長”之草体“长”(如东晋王羲之《此事贴》作、三国吴皇象《急就章》作)形近,故“能”或作“”,碑志常见。如北魏神龟二年《慧静墓志》作(《汉魏校注》5/15)、唐开元十四年《崔淑墓志》作(《隋唐汇编》洛阳卷9/157)等。“长”或又错误还原为“長”,如北魏太延年间《嵩高灵庙碑》作(《北图》3/5)。
(四) 通俗性
俗字是流行于民间而未取得正体地位的俗写汉字。俗字产生和流通环境相对宽松,使得具有无理性的类成字化改造在俗字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也成为俗字生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曾列举当时流通的一些“鄙俗”的字形:“亂旁为舌,黿、鼉从龜,席中加带,惡上安西,鑿头生毀,離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为獦,靈底着器……”
这些俗字形体的产生可以说都是类成字化的结果,也不难在碑志文献中找到实际字例。如北魏永安二年《元继墓志》“鑿”作(《北图》5/124),此所谓“鑿头生毀”;延昌二年《元显儁墓志》“壑”作(《北图》4/7),此所谓“壑乃施豁”;正光六年《元茂墓志》“獵”作(《北图》4/180),此所谓“獵化为獦”;永安二年《山徽墓志》“靈”作(《北图》5/125),此所谓“靈底着器”等。
三、 类成字化与其他文字现象
作为一种文字现象及字形演化通例,类成字化与成字化、记号化、繁化、简化等其他文字现象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它们协同作用于汉字发展的各个时期,促动汉字系统的发展演进。
(一) 类成字化与成字化
类成字化与成字化都是基于形近而对既有字形做出的调整或改造,在表现形式上极为接近,故齐文将类成字化纳为广义成字化的一个类型。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改造后的新字形是否具有理据性:类成字化是无理改造,新字形丧失或局部丧失构字理据;成字化是有理改造,新字形依然保留构字理据或经重新分析而获得构字理据(有时表现为俚俗理据),其间往往包含着构件声化或义化的过程。如“㱃”,甲骨文作,象人俯首吐舌捧尊就饮之形,后因“㱃”字与“今”字音近,与“今”形近的舌形演变为表音部件“今”;“老”,甲骨文作,象老人持杖之形,小篆讹作,六朝在篆形基础上产生从“先、人”会意的俗体“”,[6]全字理据重构。
当然,类成字化与成字化同属于形近变异的范畴,[7]都是造成汉字形体和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一方面,两者可能表现在同一字形的不同演化阶段。如“憂”,《说文·夊部》小篆作,隶楷书承袭小篆结构,但声符讹作“㥑”,“頁”之底横与“八”形黏合为“冖”,全字作“憂”。或作,见东汉熹平元年《吴仲山碑》:“孤慙亡父,在夙夜。”(《隶释》卷九)《隶辨·尤韵》引注碑字:“即憂字,变頁为,移夊于中。”构件“”“夊”黏合为“夏”,与全字音义无涉,这是个类成字化的过程。或继而作“”。之上部构件“”与“百”形近,余下部分粗看与“念”相近,于是干脆将全字改造为“百”“念”的上下组合。《颜氏家训·杂艺》所谓“百念为憂”,即指“”字。“憂”本是形声字,“”则变为会意字,全字构造理据重解。这可视为一个成字化的过程。
另一方面,两者可能表现在同一构件的不同演变方向。如“夗”在参构时或被改写为“死”,这是一种类成字化改造;也可能被改写为“宛”,这是一种成字化改造,大概是因为在书写者的心目中,“宛”比“夗”更为熟识,更像一个“字”的缘故。如北魏神龟二年《元祐墓志》“苑”作(《北图》4/61)、武泰元年《元举墓志》“怨”作(《北图》5/79)等。又如“遷”的声符“䙴”,在汉代实际上已经极少使用,一般人很少知道它的音义,于是人们将其下部改作“升”,“遷”全字变作“”,凸显了升高义,(赵平安 1999)这是一种成字化改造;另一条路线是将“䙴”改造为形近的“零”,北魏太昌元年《元恭墓志》“遷”作(《北图》5/172)、隋大业十年《鲍宫人墓志》“僊”作(《隋汇考》5/94),这是一种类成字化改造。
(二) 类成字化与记号化
记号指汉字形体中不能解析的部分,记号化指汉字在演变过程中构造理据完全或局部丧失,沦为记号字或半记号字。裘锡圭(2013)42认为记号字和半记号字的逐渐增多是汉字结构的发展趋势之一。
显然,类成字化属于记号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类成字化的结果来看,新产生的字形属于记号字或半记号字。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明确的演变指向:类成字化通常有明确的演变指向,即原有形体向形近的高频构件或构件组合体靠拢;而记号化的成因则比较多样,如构件的讹变、粘连、合并等,其结果也未必以“成字”为最终指向。例如隶楷书“春”“奏”“秦”“奉”“泰”等字的小篆形体互异,它们共有构件“”的产生是各字内部不同构件粘连的结果,产生途径不一,“”是个记号构件,但本身并不“成字”,很难说它是一个类成字构件。
(三) 类成字化与繁化、简化
张涌泉(2010)85-87、李荣(2012)60-61两位先生都认为“把不常见的偏旁改为常见的偏旁”会导致字形的繁化,并分别结合敦煌写本、明刻本小说列举了“鐡→䥫”“叫→呌”“萼→蕚”等例加以说明。实际上,如果原字中被替换的成分比新成分形体复杂的话,类成字化也有可能造成字形的简化,例如前文所举的“屬→属”。又如:
“膝”,本作“厀”。《说文·卪部》:“厀,胫头卪也。从卪桼声。”段玉裁注:“厀者在胫之首。股与脚间之卪也。故从卪。”因表示人体部位的字多从“月(肉)”,“厀”受优势构件的影响产生了从“月”的异体“膝”,并逐渐取代了原字,成为通行字体。声符“桼”或简作与之形近的“來(来)”。东汉延熹元年《郑固碑》作(《北图》1/113)、唐天宝元年《崔君妻朱氏墓志》作(《北图》25/9)、乾符三年《支䜣妻郑氏墓志》作(《北图》33/147)。
“盜”,会意字。《说文·㳄部》:“盜,私利物也。从㳄,㳄欲皿者。”碑志多见从“次”作“盗”者。如北魏正光五年《檀宾墓志》作(《北图》4/178)、永安二年《元继墓志》作(《北图》5/124)等。考其缘由,一方面固然与“氵”“冫”形近相乱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次”较“㳄”更为人们所熟习有关。“㳄”即表口水义的本字,文献通常以后起字“涎”代之,故“㳄”颇不见经;而“次”则是极为常见的字。从“盜”到“盗”,字形得到了简化。类例如“羨”,本从“㳄”,但常省作“羡”。
四、 类成字化的认知动因及探讨价值
(一) 类成字化的认知动因
从汉字心理学的角度看,构件的分析和称说是识记汉字的关键。(何九盈等 2009)81齐文将成字化的动因归结于它能够满足人们的称说需要和理据追求。上文已指出,类成字化与成字化虽然表现形式相同,但彼此隐含着无理与有理的对立,因此如果单独讨论类成字化的动因,那就应该与构件称说和书写需求密切相关,而与人们对字形理据的追求关系不大,甚至是有所相悖的。类成字构件虽与全字音义无涉,但显然具有极强的可称说性。因此在俗文字流通领域,普通民众日常拆字大多采取成字优先而不论其理据的做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人们把用作姓氏的“楊”说成“木易楊”、把“俞”说成“人則俞”,主要是“楊”的声符“昜”比较罕见、“俞”的“人”符以下部分不成字,不如形近的“易”和“則”便于称说的缘故。至于民间以“尺二”称说“尽”字、[8]以“丘八”称说“兵”字[9]等,似乎都属于无理拆分,所得构件与全字理据缺乏明确的关联。
文字是思维的表征形式之一,人们书写、识记汉字的过程离不开认知因素的参与。如果从认知层面考虑类成字化的深层动因,我们认为至少与以下两种认知机制的参与和促动密切相关:
第一,完形感知。“完形”是西方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派基于审美经验提出的一个概念。完形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当人们在知觉一个不规则、不完满的形状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在头脑中填补“缺陷”,使之成为完满的形状(即所谓“完形”或“格式塔”),从而达到内心的平衡。汉字作为一种可以“目治”的视觉符号,人们对它的识读和书写不可避免地受到“完形压强”[10]的影响:那些为人们所熟识的字或构件就是一个个“完形”,而那些“不成字”或罕见的构件或形体在记写过程中就倾向于被识别或改写为某个“完形”。例如隶楷书中等字所包含的构件“田”,分别源自各字小篆中所包含构件的类成字化改造。(董宪臣2018)98
此外,整体性观念也是完形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完形比它的构成要素在认知上更简单,更容易识别、记忆和使用。(沈家煊 2020)11这可以很好地解释黏合式类成字化现象何以发生。例如前文列举的“→履”“席→廗”“莽→莾”等,都是字内位置临近的几个构件黏合成单个类成字构件,这种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全字的认知层级,增强整体感知性,便于记写。
第二,重新分析。汉字的重新分析是指对同一个汉字所做的又一种符合汉字系统的形体分析。(齐元涛 2008)这种重新分析可能是有理的,也可能是无理的。无理的重新分析通常会造成汉字的形义割裂,导致类成字构件的产生。如“章”本由“音”“十”构成,构字理据清楚。《说文·音部》:“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但用作姓氏时常被称为“立早章”,全字被重新分析为“立”“早”的组合,构字理据丧失。
徐彩华(2010)119指出:“汉字在视觉上是一种平面图像刺激,字形的可分解是汉字知觉属性的重要特点。”隶变中所发生的笔画拆解、变形及构件移位、离析、重组、讹变等造成了大量汉字的形义割裂,对汉字的记写造成了不小的困难。为了明确一个字的构形与写法,流俗倾向于将其分解为便于称说的类成字构件,而往往不论其真实理据。这可视为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如称说姓氏的“口天吴”“双口吕”“干勾于”“草头黄”等,都包含对字形的无理拆解。对构形更为模糊难识的草书,这种拆解可以说触目皆是,如“六手宜为禀”“七红即是袁”“寿宜圭与可”等。(万业馨 2012)212
(二) 类成字化的探讨价值
在汉字发展进程中,类成字化既是客观而普遍存在的文字现象,也是文字改造的重要手段。对类成字化的深入认识和探讨,在汉字理论的完善、俗字研究的开展、汉字的民俗阐释等方面都颇具启发意义。
首先,类成字化改造增强了汉字系统性。汉字发展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构件偏旁归并的过程。在完形感知及重新分析等认知机制的驱动下,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完成了对大批构件的类成字化改造。这个过程在客观上消解了一部分基础构件,促进了基础构件的归并整合及汉字系统性的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汉字系统的整体面貌。例如隶楷书中“口”“田”“日”“罒”“覀”等高频构件的产生,很大程度是类成字化改造的结果。王贵元(2014)从经济性的角度阐述了个中原理:“就一个系统来说,只因一个字而多出一个构形成分是不经济科学的,正因为如此,构件的改造遵循的是类化的方式,即把不常见构形成分改造成形体近似的常见构件。”
其次,类成字化改造推动了现代汉字部首体系的确立。东汉许慎作《说文》,坚持“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据表义形符将9353个小篆归入540部。而在隶变过程中,大量形近、义近部首发生了进一步的归并,使得汉字部首总量逐步减少,从而也使汉字的构形系统更加简化、明晰,至明代梅膺祚《字汇》214部确立,标示着现代部首体系的最终确立。部首归并的总体趋势便是构字能力强、出现频率高的强势部首兼并、取代,或淘汰构字能力弱、出现频率低的弱势部首。在这个过程中,类成字化改造无疑起到了促动作用。
再者,类成字化改造是异体字、俗讹字产生的重要途径。形近变异是引发汉字形体、结构变化的原因之一,而高频出现、为人们所熟悉的字或构件为这种变异提供了可参照的“完形”,诱导字形的演变或改造向这个方向发展。这种现象发生于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导致了大量异体字的产生。在隶楷书为代表的近代汉字中,类成字化改造表现尤为活跃,是俗讹字产生的一大渊薮。张涌泉(2010)85将“把罕见的、生僻的偏旁改为常见的偏旁”所产生的俗字归纳为俗字的一个类型。李荣(2012)61也将“把偏旁改成常见的”视为俗字改造的手段之一。
最后,类成字化拆分为汉字的民俗阐释提供了土壤。黄德宽等(1994)指出:“从阐释角度看,在单纯观照那些陌生的汉字形体时,人们常常无法完成由字形到字义的正确转换,而且汉字构形及其发展也越来越背离其早期构成的形义统一性原则。”对于字形演变过程中所造成的形不表义的情况,后世往往结合所见字形结构进行主观性拆分阐释,赋予其流俗理据,以弥合形义关系。《说文解字·叙》[11]及《颜氏家训·书证》[12]都曾举证批驳过这种近乎游戏的解字法。裘锡圭(2013)41-42也指出:“为了尽量使偏旁成字,往往不得不在字形的表意方面作些牺牲……有时为了使偏旁成字,甚至不惜完全破坏字形的表意作用。例如:(射)字象弓箭的部分后来改成形近的(身),跟字义就完全失去了联系(《说文》“䠶”字下以“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说“䠶”字从“身”之意,是牵强附会的。“䠶”即“射”字异体)。”民间流行的“千里为重”、[13“]二山为出”、[14“]同田为富”等说法,其实都属于这种情况。
总之,传统文字学认为形义统一性是汉字构形及其运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当汉字丧失理据时,往往会通过围绕字音、字义进行改造(如加注形符、声符或构件声化、义化等)的方式进行理据重构。但类成字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却与上述观念相互乖违。可见,汉字的发展演化是复杂而多途的,类成字化改造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尤其在世俗用字层面,很多时候人们似乎更注重汉字记写的便捷性,而不以理据性为最终诉求。这值得我们对汉字发展问题进行重新审视。
附 注
[1]本文所引碑志字例均注明出处,斜线前的数字表示册数,后表页数。为求行文简洁,部分文献采用简称:《北图》指《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汉魏校注》指《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毛远明 2008),《隋汇考》指《隋代墓志铭汇考》(王其祎,周晓薇 2007),《隋唐汇编》指《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5]依各本《说文》,“屬”当从尾蜀声。
[6]《颜氏家训·杂艺》:“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憂……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所谓“先人为老”,正指“”字。
[7]张素凤(2012)244:“形近变异是指汉字书写者在书写过程中将汉字的某个部件写成与它形体相近而意义不同的其他部件,从而造成字形理据的丧失或重构。”
[8]“尽”是“盡”的草书楷化俗字。宋孙奕《履斋示儿编》卷九《文说》“声画押韵贵乎审”条:“诚斋先生杨公考校湖南漕试……先生见卷子上书‘盡’字作‘尽’,必欲摈斥。考官乃上庠人,力争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传以为场屋取得个尺二秀才,则吾辈将胡颜?’竟黜之。”后因以“尺二秀才”讥讽写俗字的书生。
[9]“兵”可析为“丘、八”二字,故俗以“丘八”为“兵”的隐语。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四《轻薄鉴》:“太祖问击棆之戏创自谁人。大夫对曰:‘丘八所置。’”
[10]赵平安(2020)66:“心理学实验证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格式塔’,人们面对着那些不尽完善、不尽美观的‘格式塔’,往往会产生一种改变它的强烈愿望,即所谓‘完形压强’。”
[11]《说文解字·叙》:“今之诸生竞说字解经……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
[12]《颜氏家训·书证》:“《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泉货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