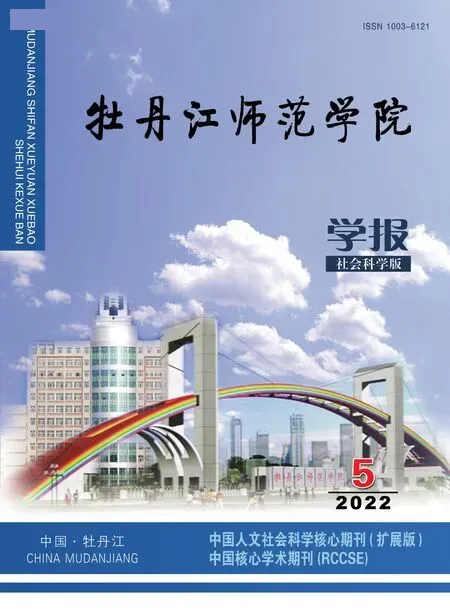浪漫幻想与现实生存:《另一个巴黎》中离散人群的身份异化
黄芙蓉,卢静静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梅维斯·加兰特(Mavis Gallant)是加拿大真正具有国际背景和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常年侨居在法国,著有《玛德琳的生日》(“Madeline’s Birthday”)、《从第十五区》(From the Fifteenth District)等。加兰特以创新的叙述形式、敏锐的语言和细腻的心理刻画描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的人生的孤独和受环境所迫的失败感和失落感,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有加拿大文学女皇之称的阿特伍德齐名。[1]293由于加兰特的侨居身份,她在加拿大受到了不公平的忽视,错失了许多奖项,但她的短篇小说选集Home Truths:Selected Canadian Stories于1981年获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之英文小说奖。
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兰特作品中离散人群的身份构建、战争反思等主题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策略、历史背景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等方面。例如,加兰特小说中的加拿大民族和世界公民身份探究(Von Baeyer);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梅维斯·加兰特和艾丽丝·门罗的后现实主义小说的女性话语分析(Melanie Sexton);分析她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探讨无政府状态以及反法西斯主义话题(Tamas Dobozy)等等。国内学者对加兰特作品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从空间理论探究离散移民的个体异化(黄芙蓉)以及对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杜立霞)或身份构建(耿雨佳)。总之,国内外对加兰特作品的关注度还不足够,缺乏对她作品和主题的多重解读,仍需进一步探究。
《另一个巴黎》发表于1956年,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十年。曾经被称为世界浪漫之都的巴黎,二战之后,失去了早年艺术之都的风采,仍然处于惨败经营、缓慢恢复的状态。同样,巴黎底层的人民处于战争创伤和物质生活匮乏的双层压力之下,对未来生活充满迷茫。这一时期,为扩大冷战时期的盟友阵营和牵制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势力,美国对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援助。杜鲁门倡议的《1947年对外援助法》中提出“对法国等国家提供食品和能源等援助”,并提供了超过2.8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来促进欧洲复兴。[2]38像女主卡洛尔(Carol)这样的美国青年在全球移民潮流和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的号召下远赴巴黎,试图在新土地上寻找人生目标。然而,战后巴黎的萧条状态以及社会文化同质化现象使得离散群体在后工业时期对浪漫巴黎的幻想破灭,陷入了自我困惑和身份迷失之中。
本文从文化冲突和身份异化的角度出发,结合霍尔的文化身份理论,分析主人公卡洛尔面对浪漫幻想和残酷现实的对立冲击,丧失了自我身份归属感,走向个体异化的过程,借个体的异化窥探战后巴黎实用资本主义精神下离散群体的社会性创伤和巴黎人民穷困的生活状态。
一、异国幻想:法国民族文化的追寻者
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群体或族裔群体迫切地想要融入“他者”的文化中去,尽快建立新文化的身份,避免成为文化统一体中的边缘人物。[3]50作为离散者,移居到巴黎的卡洛尔也对法国民族文化充满幻想,她试图在对统一社群的幻想中寻求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以求在巴黎寻找到生存方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一)对高雅艺术的幻想
“浪漫”是巴黎的代名词,也是许多离散人群对巴黎的刻板印象。以卡洛尔为代表的异国人对巴黎充满了天真的向往与渴望,在其心中,“巴黎作为文化之都的形象根深蒂固”,会始终保持着以往的风采,充满着古典贵族情调和浪漫主义情怀。[4]110二十一岁的卡洛尔满怀期待来到了国际都市巴黎,渴望在巴黎发现美丽与浪漫,并期待在巴黎能有一段与爱情的邂逅。这种虚无的幻想使她陷入了与现实对立的自我矛盾之中,她竭力保持着对浪漫主义的追求,沉溺在自己对巴黎的虚假幻想之中,积极探寻巴黎浪漫文化的踪迹。卡洛尔表现出对巴黎社会贵族浪漫情调的极大热情和关注,幻想自己能够成为法国浪漫民族文化的体验者。浪漫主义小说中描述的巴黎都市给她带来了最初的幻想蓝图。“高雅华贵的女人”和“英俊放荡、哼唱着轻快歌曲的男人”应当是巴黎街头常见的风景线,美好的天气,人们漫步在阳 光 之 下。[5]18尽 管 来 到 巴 黎 后 现 实 的差距给予她较大的打击,但卡洛尔仍试图寻找巴黎浪漫主义的痕迹。她不断去探寻巴黎都市的街道、参加可能会充满高雅气息的音乐会和聚会。想要尽快融入到法国本土文化的迫切心理使得卡洛尔寄希望于结交法国本地朋友,尽管霍华德(Howard)的法国人秘书奥迪尔(Odile)的傲慢和讽刺使得卡洛尔深感受伤,但孤独的卡洛尔仍然愿意与她保持着相对亲密的朋友关系,试图借助本地人的帮助尽快融入到巴黎群体之中,并期待从奥迪尔身上寻找到巴黎人浪漫与高贵的影子。当卡洛尔收到参加奥迪尔家庭音乐会的邀请之后,她满心期待,希望能从奥迪尔的叔父——生于上世纪的落寞贵族伯爵——身上见识到巴黎贵族伯爵的风采与文雅。为了迎合和融入奥迪尔家族,卡洛尔甚至买了一顶贵重的“白色皮毛帽子”,还学了几句“优雅的”法语。[5]23像许多刚来到巴黎的异国人一样,卡洛尔积极探寻着巴黎都市的美好与浪漫,期待感受到巴黎以往的荣耀和光彩,试图融入到法国民族文化中去。
(二)对浪漫爱情的追求
同样,与浪漫爱情的邂逅也是卡洛尔对巴黎浪漫文化幻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巴黎被视为“浪漫之都”,所有完美的 浪漫 和求婚 都在 这里萌 芽。[6]218她与霍华德三个月的相识相爱在她自己的幻想里被定义为“一见钟情”,习惯于别人对她的订婚如此“罗曼蒂克”的讽刺性评价;在卡洛尔的爱情幻想之中,她与霍华德的求婚背景应当是集“埃菲尔铁塔和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包含“塞纳河、月光、小山似的紫罗兰和金合欢花朵”所有浪漫元素为一体。[5]16尽管她意识到自己与霍华德的订婚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但她始终坚信“只要天气不再阴雨绵绵,她就会和霍华德相爱了。”[5]17她的天真之处在于将对爱情的发生看作是条件适合之下的自然发展,将爱情寄托于美好的氛围。不以真爱为基础的婚姻似乎与卡洛尔的浪漫幻想相违背,但对于卡洛尔来说,与霍华德的婚姻是她用来满足浪漫幻想的一个爱情资本,她并未放弃对爱情的追求。
卡洛尔在现实生活和婚姻中,保留了自己对浪漫巴黎的刻板幻想,这种幻想使她竭力想要融入巴黎文化之中,在巴黎社会中尝试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在对法国民族文化的追寻中,卡洛尔将巴黎所代表的法国民族文化放在一个神化和崇拜的地位,同时鄙夷甚至想要撇弃自身本民族文化。她在描述现实差距时总是会与纽约做对比:人们在拥挤的地铁站里表现得“与纽约人一样粗鲁”,到处充满“可口可乐。”[5]18她对巴黎现实的不满转向对美国文化深远影响的攻击上。在她的潜意识里,低俗、粗鲁的美国文化冲击了高雅浪漫的巴黎文化,造成了法国民族文化的堕落和毁灭。对于卡洛尔来说,她在巴黎文化的神话幻想里无法得到满足,便将矛头指向自身文化,体现出了一种不平等的文化观念。这样一种不平等的文化观念使卡洛尔陷入巴黎文化幻想之中,无法真正认清法国民族文化日益衰落的事实,沉迷于追寻法国民族文化的残辉和踪迹。现实的巨大差距终将打破她的幻想,使她认清楚战后巴黎早已不复荣光,充满了战争遗留下来的残败和破乱。
二、现实重审:文化创伤中的“他者”
尽管离散人群对巴黎本土文化充满浪漫想象,但现实沉重打击了他们想要融入到巴黎文化的期望,致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巴黎社会。战后创伤、民族主义以及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影响对离散群体造成了精神创伤和生存压力,他们成为了巴黎文化共同体中的“他者。”“他者”是指以自身文化为主体,指称具有文化差异的其他对象,而“他者”被一般认定为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和被动地位。”[7]63美国人卡洛尔以及来自奥地利或是捷克的难民代表菲利克斯(Felix)都是现实冲击的受害者和文化冲突中的“他者。”
(一)美国移居者:卡洛尔
?
沉迷于幻想的卡洛尔最终要面对的是对现实的重新审视。巴黎街道的破败和荒凉、底层群众的困苦生活、以及神圣爱情的现实价值都一步步冲击着卡洛尔的幻影之梦,使她不得不重新认识到,巴黎早已无法给离散人群提供任何浪漫的想象空间,其排外和实用主义的大众意识让离散人群有了创伤性文化体验,无法真正在巴黎获得认同感,成为文化对立中的边缘群体。
二战之后的法国狼狈不堪,不得不接受美国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援;而美国也借机拉拢友国、扩大联盟,试图在美苏争霸的冷战局面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根据美国总统签发的9914号行政命令,为“美国海外任务招聘和培训人员到受援国”这一条例也被包括在对外 援 助 计 划 内。[2]39在 这 一 政 策 的 号 召下,许多像霍华德和卡洛尔一样的美国青年怀抱梦想来到法国,期待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处在中下阶层的巴黎人如何在资本压迫下在萧条破败的战后巴黎社会艰难生存:拥挤的地铁站、昏暗难吃的餐馆、黑心的出租车司机、裹着雨衣的女子、亟需理发的男子…这一切都让她的美好憧憬急速破灭,让她不禁感叹:“巴黎已不再是那个五十年前人们随时歌颂的城市了。”[5]22但是,由于当时美法同盟关系升级,身为美国人的卡洛尔只能小心翼翼地不对巴黎做出任何抱怨或是诋毁性评价。
卡洛尔在法国民族文化的神话与美国文化侵入的现实的对立中,陷入了被排斥、被“他者”化的身份危机之中。卡洛尔被“他者”的文化创伤主要表现在卡洛尔对巴黎文化同质化的失落和对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无奈。战后本土文化的没落让卡洛尔无法追获幻想中的高雅艺术,巴黎社会显现出的同质化特征又让她深感失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不断接受美国经济政治支持,同时也不得不接受美国在巴黎的公共外交宣传。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及“文化巡展”等多种方式对法国进行公共宣传,提高法国民众对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工业生产先进性”的认同感,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2]44这种宣传让巴黎曾经的贵族文化和高雅的审美艺术被美国快餐文化和资本阶级所替代,显现出与美国同质化的社会特征。拥挤的地铁站、随处可见的快餐、昂贵的消费品牌等都让卡洛尔感觉像是在纽约,丝毫反映不出巴黎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实用主义思想正逐渐控制巴黎人民的生活行为方式,文化的同质化特征让处在异国的美国人卡洛尔丧失对法国民族文化的神化推崇,在对本民族文化摒弃或是复归的文化抉择中陷入尴尬境地。另一方面,这种以宣扬美国生产生活方式为重点,努力塑造美国在法国民众心中的正面国家形象的外交方式促使法国的左倾和右倾的政治势力逐渐产生“反美主义”的立场以期寻求国家认同和威信,许多法国群众也开始对生活在 法 国 的 美 国 公 民 产 生 敌 意。[2]50遭 遇战争创伤的本地人奥迪尔将她的创伤性群体体验转移到了异国人卡洛尔身上,表现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这无疑又是对卡洛尔的又一打击。即使战争摧残了巴黎社会正常的运转秩序,巴黎人民也受到了萧条的经济形势和战争创伤的双层打击,身为本土人的奥迪尔仍旧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高傲,对美国人卡洛尔充满不屑。她讽刺卡洛尔“一见钟情”的虚假爱情观、对卡洛尔出借礼服的好意置之不理,其刻薄排斥的态度让卡洛尔深感失落,成为文化统一体中不被接受和认可的一类。其次,同样带给她冲击的还有未婚夫霍华德对感情的实用倾向。大萧条戏剧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理想追求,高离婚率的现实压力下年轻人不再将对爱情的浪漫追求作为婚姻的前提,他们“凑合着结婚”,将人人都要结婚并组建一个“男性养家式”的家庭视作一种文化 共识。[8]251霍华 德作为 那一代 年 轻人的代表,也透露出这一“传统的”婚姻观念,这与卡洛尔的美好幻想背道而驰。她幻想的求婚仪式并未发生在浪漫的巴黎铁塔旁,而是面对着午餐时的金枪鱼色拉,并且霍华德将求婚成功的喜悦心情化作物质消费:“额外点的一瓶香槟酒。”[5]16霍华德的呆板、平凡与实用主义思想冲击了卡洛尔对浪漫爱情的美好想象,将她拉回到现实世界。爱情的种子始终没有受到美好天气的培育,两人多次努力的尝试却最终都以失望而告终,这使卡洛尔开始质疑两者的亲密程度。
伴随着萧索街道和残败建筑的是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这也为巴黎都市的前景蒙上一层阴霾。卡洛尔不得不重新审视巴黎真正的现实世界,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陌生化和身为离散者的孤独感。卡洛尔这样的现代人,缺乏对传统教义的信仰和忠诚,以现代“非理性”的教义生活,缺乏了精神信仰上的支撑和满足,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现实逼近时,必然会产生“个人内心一种空前的孤独感。”[9]46总之,浪漫之都的同质化、本地人的讽刺与排斥以及未婚夫的实用主义思想都给卡洛尔造成了创伤,巴黎幻想的现实冲击使她作为异国人而无法产生对巴黎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认定这是“另一个巴黎。”幻想与现实的对立使卡洛尔感到被排斥和孤立,对自己在巴黎文化身份也产生了迷茫与质疑,一度想要回美国。
(二)难民代表:菲利克斯
同样受到战争创伤和生存打击的还有来自奥地利或是捷克的难民代表菲利克斯,他处在巴黎社群的边缘,是法国民族文化与自身民族文化中的“他者。”二战结束后,波兰与德意志的领土划分矛盾升级,波兰疆域“整体大幅度西移”,由此引发了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潮。[10]26临近德国的奥地利或是捷克国家也受到了不小影响。不少难民为了谋职求生,来到法国和英国。父母在战争中身亡、无依无靠的菲利克斯也是难民群体的一员。由于难民身份的影响,他只能非法滞留在巴黎。在这里,他无法以公民身份从事劳动工作。残酷的巴黎社会并未对这类的非法难民提供有效救助或生存机会,菲利克斯整天无所事事,流浪在街头上,做着一些疑似非法的“其他事。”[5]20社会淘汰机制下,他如同灰色的老鼠,苟活于巴黎的阴暗背景里,寄生在奥迪尔身上,无法与巴黎本土群体产生真正的交集。同时,不合法的身份、悲惨的身世和年龄差距无法让奥迪尔的家人接受他作为奥迪尔男朋友的身份存在。战争和异国文化的拒绝对他所造成的创伤不仅仅表现在他无所适从的社会行为上,还有他孤僻绝望的心理状态。他厚颜无耻地依附于奥迪尔,对于从女性那里获得金钱的行为从不感到羞愧,对未来生活也毫无打算。他看清了美国报纸对欧洲生活的虚假宣传,早已经对这个国家和未来充满绝望,对他来说,在战争中死去或消失才是最好的解脱。面对着无法回归的本土身份、巴黎社会的排斥,拿着美国香烟的菲利克斯被孤立在一切社会秩序和群体存在之外,作为异乡人的孤独感和不适应感让他放弃了生活的希望和独立的信心,他展现着自己的另类与孤僻,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身份定位和人生方向。他既无法回归自己本土的文化身份,也被巴黎文化所拒绝。像菲利克斯这样的移民群体,身处两种文化的夹杂和边缘,失业率高,“多数仍保留着来源国的文化宗教传统,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是巴黎社会中容易被边缘化而受到歧视的“问题移民”和另类。[11]10
幻想破灭之后,离散群体在重新审视战后巴黎的真正面貌之后受到了社会现实的创伤性打击。离散群体在经济资本的打压下被讽刺、被排斥、不被理解和关注,无法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产生了自我定位危机。这种身份危机演化而来的则是他们内心无所归依的寂寞与痛苦,同时也经历着异化和精神的沉沦。
三、个体异化:实用主义的复归者
浪漫巴黎的幻灭和实用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冲击对离散人群产生了创伤性打击,为了应对这种巨大偏差和对新文化的不适应,他们不得不更正自己的行为习惯,通过“调整自我甚至不惜屈辱地忍耐”以维持和改善现实生存,主动适应巴黎社会的新形态来掩盖自己的失落和痛苦,接受西方文化中实用功利主义的思想来满足自身欲望。[12]463在这一过程中,离散群体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身份的转变和个体的异化。
(一)战后巴黎现实爱情的刺激
战后的巴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经济体系下,其参与者“不得不顺从市场的规范”,“自发地”形成了适合资本主义特征的生活态度。[9]32这种生活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大众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以及“获取、追求利益的冲动”已经被“道德上”肯定了,[13]13他们更愿意追求“清醒、勤奋的职业生活。”[13]31它通常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威廉·詹姆斯提到的实用主义哲学相契合。詹姆斯将实用主义的方法定义为“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并且这个态度是指在对待事物时要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14]31而资本主义精神也通常被解释为一种理性经济主义,以财富的积累为最终目的,这种实用资本主义精神塑造了当时青年一代的精神信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体现了美国精神的核心。这类人中最鲜明的代表就是同为美国人的卡洛尔的未婚夫霍华德,一个典型的资本经济实用主义的代表。他将婚姻视作是解决孤单以及满足传统社会伦理需求的调节,认为与卡洛尔的“婚姻生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霍华德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者,其外在行动极有“系统和效率”,以现代意义下的理性计算为出发点进行行为判断。[9]43因此,在经济主义思潮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霍华德认为婚姻不再被视为神圣的爱情发展,而是双方利益平衡的结果;在物质基础合适的情况下,为了消除现代人潜在的孤独感和精神空虚以及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婚姻关系的建立成为了他们经济关系的一种特别形式。功利实用主义实际上已经渗透到霍华德和卡洛尔的婚姻关系之中。
一开始沉溺在巴黎文化憧憬中的卡洛尔,受到巴黎现实的创伤打击之后,异化成了一个彻底的美国实用主义精神贯彻者。这一彻底醒悟的瞬间发生在对菲利克斯暗恋的失败结局中。受到创伤的卡洛尔被有相同境遇同年龄的欧洲难民菲利克斯吸引,她认为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惺惺相惜,都在这个异国他乡里同病相怜,有着不可掩盖的孤独感。对菲利克斯的暗恋也使卡洛尔发狂。她强迫自己忽视奥迪尔和菲利克斯的年龄差距和不平等的经济交往,努力接受两人的爱情关系;但对菲利克斯的爱恋使她陷入不可控制的嫉妒之中,尤其是在看到奥迪尔与菲利克斯的亲密行为之后,她联想到了自己与呆板的霍华德之间的感情。相比较于年轻的她与霍华德的婚姻关系,她嫉妒老女人奥迪尔与年轻的菲利克斯之间的相依相靠,这让她产生了不平衡感。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好胜心,她试图以功利实用主义的思维为自己辩解,贬低奥迪尔与菲利克斯之间的不切实际的爱情关系。她认为,奥迪尔与菲利克斯存在于肮脏房间的爱不足以支撑他们度过债务危机,她和霍华德才是最好的伴侣,“没有人能够批评他们。”[5]32卡洛尔不再相信纯粹的不以物质和年龄为基础的爱情的存在,说服自己与霍华德经济匹配的婚姻才是最浪漫的,这种自欺欺人的实用主义想法给了卡洛尔慰藉和满足。她不再幻想有浪漫主义爱情,反而更加以经济实用主义的角度分析自己婚姻的可行性,迎合了时代背景下现代青年对“男性养家式的婚姻”文化准则指导下的传统婚姻关系的文化认同。故事最后,卡洛尔“以病态的自我陶醉为粉饰”的“石化现象”已经造成了她对生活意义的完全麻木不仁,她已经彻底异化成为现代实用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成为现代“新新人类”的一员,成为现代社会和婚姻关系中“没有情感的享乐人。”[9]87至此,卡洛尔彻底放弃了对法国民族文化的崇拜,选择复归到主流文化之中,并异化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
(二)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回归
事实上,卡洛尔向实用主义身份的异化并不是与爱情的偶然碰撞猝然形成的,成长在美国社会中的她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用主义的精神种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用主义就已被美国大众广为接受,成为美国人生活方式和求生手段的重要思想基础。她的行为判断和处事准则被禁锢在实用主义浅意识之中。例如,卡洛尔的早期浪漫爱情幻想之中隐晦地暗示了她潜在的实用主义的思想。二战后,社会出现了对大萧条和战争时期“所积压的延期婚姻”的临时调整,空前的结婚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发生。[8]252这种结婚浪潮使得卡洛尔也面临着婚姻的压迫感。尽管卡洛尔年仅二十一岁,她不得不尽早做出迈入婚姻殿堂的决定。她保持着传统主义心态,遵循着传统社会中对女性价值观念的设定,将婚姻视为适龄女性成长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带着标准的传统主义心态,与霍华德的婚姻关系是她陷入“大龄剩女”的紧急避险,她担心“老得没人再问她”,所以即使霍华德没有按照幻想进行求婚,即使她还不爱他,卡洛尔“立马接受了。”[5]16她与霍华德的爱情观念是基于两人相似的经济背景、财产担保和宗教背景,她“有效率地”开始实施“陷入爱情的生意。”[5]17由此可见,爱情的存在与否并不是两人的婚姻关系的必然条件,卡洛尔仍然选择以实用主义的角度对待两人的婚姻缔约。
同样,在她对巴黎社会的浪漫幻想中,她渴望看到的是巴黎表面的物质丰富,忽视了对于艺术浪漫美感的追求。即使她满怀期待去参加奥迪尔家族的音乐会,但她的失望仅仅表现在对音乐会的破旧装潢和人们服装的简陋,并没有表现出对艺术的整体感知。因此,卡洛尔的浪漫幻想是停留在巴黎物质层面,她并没有真正了解到巴黎都市的艺术浪漫。另外,面对自己对菲利克斯的情愫,她以阶层和经济上不对等的理由试图扼杀“与菲利克斯亲密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行为实际上表现出卡洛尔在身份探寻阶段已经陷入“自我摧毁”,也暗示了她实 用主 义的内 涵。[15]97卡洛尔 以浪 漫主义的思想表达了对实用物质层面的幻想和追求,这也暴露出她实用主义的潜意识。直到最后,她受到现实和爱情的双重冲击之后,才真正完成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的身份异化。
浪漫主义和西方实用主义的拉扯与对立给卡洛尔这样的异乡人造成了精神上的折磨和文化身份探寻上的打击。他们的文化幻想受到异国现实世界的冲击,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孤立感。为了避免陷入身份危机,他们不得不做出文化选择,调整更正自己的行为来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卡洛尔接受了巴黎社会现实,认清功利主义的现实需求,异化成为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
四、结语
加兰特在《另一个巴黎》中借美国人卡洛尔在巴黎幻想破灭、遭受现实打击的身份异化经历,折射出战后巴黎本地人民的社会性群体创伤和资本分化的阶层压迫,以及异国人群所遭受的文化冲击。战后巴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冲击,呈现出与美国社会同质化的特征,使得以卡洛尔为代表的异国青年们难以在此满足自己的浪漫主义情怀,只能被动接受实用主义观念;以奥迪尔为代表的中下阶层青年一代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群体创伤,他们不得不在资本压榨之下担负起赚钱养家的重任。他们的艺术情调被窘迫生活所磨灭,被美国资本的流入所冲击,被实用主义思想所占据;同样,以菲利克斯为代表的难民群体处于文化社群的边缘地带,陷入异国文化排斥和本国文化丧失的两难境地,以漂泊孤独的生存状态在巴黎底层苟延残喘。这些群体的生活状态都折射出战后巴黎经济萧条、新教伦理冲击、实用主义主流思潮、青年一代迷茫和精神空虚的惨淡社会背景。加兰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离散群体在巴黎遭受的文化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体异化,呈现了巴黎后工业社会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另一个巴黎》展现了加兰特对异国群体文化身份的关注,对战后巴黎社会创伤的揭露和思考,体现了她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