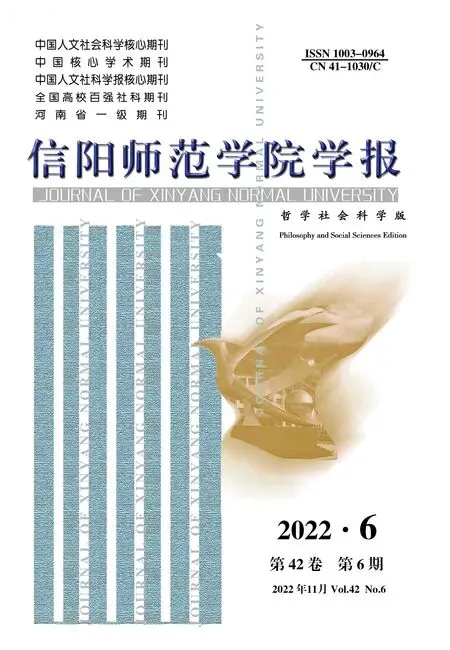作为见证的责任
——《辛德勒方舟》中的大屠杀记忆书写
徐阳子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最多产和最杰出的“国宝级”作家,迄今已经出版了30多部小说、戏剧、电影剧本和非小说书籍。他曾2次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4次入围布克奖,最终凭借《辛德勒方舟》(Schindler’sArk)摘得1982年布克奖桂冠。这部杰作后来被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成了享誉国际的电影《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1993),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7项奥斯卡奖。直至今日,这部小说及其改编电影仍在世界范围内长盛不衰,引发了全世界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注与反思。
一、大屠杀记忆的文学表征:犹太人被大屠杀
《辛德勒方舟》讲述了一个关于一种文明在6年内销声匿迹,以及一个人如何通过努力改变小群体命运的故事。小说以纪实手法再现了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的真实经历,出色地描绘了主人公在“极端邪恶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德国投机商人奥斯卡·辛德勒是个纳粹党党员,善于利用关系攫取最大利润。在被占领的波兰,犹太人是最便宜的劳工,因此辛德勒的工厂只使用犹太工人。他通过阴谋诡计、贿赂和黑市交易,不仅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且使自己备受纳粹官僚们的青睐。然而,纳粹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使辛德勒越来越不满,尤其是1943年纳粹对克拉科夫犹太人的残酷血洗使辛德勒对纳粹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从那时起,辛德勒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来保护他的犹太劳工,辛德勒的工厂从此成了犹太人的避难所。1944年底,战争接近尾声,所有幸存的犹太人都被驱逐到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辛德勒历经千辛万苦说服当局将他的工厂及其“重要工人”转移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家乡布伦利茨。一份包括1 100名犹太人的名单——“辛德勒的名单”——已经准备就绪,这是一份“生”的名单,谁的名字进入这份名单,谁就能逃脱毒气室的灭绝厄运。当战争结束时,辛德勒的角色也结束了,他被认定为纳粹战犯不得不连夜出逃。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婚姻和商业投资均宣告失败,生活在贫困潦倒之中,但他在二战期间英勇无畏的行动赢得了犹太幸存者及其后代的无尽感激。1956年,在以色列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博物馆(Yad Vashem Museum)附近的国际义士大道上,人们为他种下了一棵角豆树。1974年10月,辛德勒在法兰克福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到以色列,埋葬在耶路撒冷的天主教墓地。彼得·皮尔斯尤其赞叹基尼利对辛德勒的描写,称“基尼利对辛德勒的描述是鼓舞人心的……他避免陷入哗众取宠的陷阱,以坚韧细腻的态度来处理几乎无法忍受的事情”[1]33。
《辛德勒方舟》是大屠杀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2]116。基尼利聚焦二战中德国惨绝人寰的种族清洗——犹太人被大屠杀,汇编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并将其改写为一部小说,为大屠杀历史做了有力的注脚,引起了学界对大屠杀小说的广泛兴趣。小说通过对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艺术呈现,将个体对于大屠杀的灾难记忆放入集体叙事中加以考量,艺术地再现了后现代语境下记忆、历史与话语交互渗透的大屠杀记忆现状,也传递出基尼利对于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承担起为大屠杀作见证的责任。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纳粹大屠杀无疑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一次最为残忍的杀戮,但这段创伤记忆在二战结束后长期处于被压抑和遗忘的状态,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①打破了犹太群体对于大屠杀的集体沉默,促使越来越多的幸存者鼓起勇气,将尘封的痛苦记忆呈现给世人。同时民族解放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也使少数族群和亚文化群体基于自身历史的特殊诉求开始受到正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新定义及讨论大屠杀历史的术语进入公共知识空间,如战争罪、反人类罪、种族清洗、种族灭绝、大屠杀、创伤、见证等,标志着人们对既有秩序和体制的深刻反思以及在历史认知方面出现的重大变革。
学界用“大屠杀”(Holocaust/Shoah)一词专指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欧洲犹太人以及其他群体实施的极端残酷的集体迫害和种族灭绝事件。虽然这场灭绝人寰的种族灾难发生在欧洲,但其所带来的创伤记忆属于全人类,自发生之日起它就从未停止过对人类良知的拷问。丹·迪纳指出,“如今公共话语中无所不在的大屠杀记忆的出现应该追溯至上世纪70年代末,其影响力到80年代已日趋显著,90年代开始对普遍的历史意识及道德准则产生重大意义”[3]67。托尼·朱特在谈及大屠杀记忆时认为,21世纪的欧洲人必须首先接受“一份颇为沉重的遗产——灭绝(extermination)”,承认大屠杀的罪行是当今欧洲走进未来的“入场券”,而对大屠杀的否认或轻视则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文明、文化的公共话语之外”[4]803-804。关于大屠杀的苦难叙事与创伤记忆已经超越犹太种族的局限而汇入全球公共议题,演变成一种全球遭遇种族屠杀创伤的群体共同享有的普遍化的记忆隐喻。
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随着大屠杀亲历者的逐渐去世,有关大屠杀的鲜活记忆也逐渐消亡,文化记忆研究者便聚焦于大屠杀记忆在不同媒介、形式、文化及地理空间中的代际传播问题。大屠杀记忆已经溢出历史事件本身,成为一种带有普世意义的记忆符号,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丹尼尔·利维和纳坦·施耐德首次将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全球记忆形式加以全面透彻地分析,认为记忆的全球性与本土性之间存在持续性碰撞与交融,并指出这种“双向过程催生出一种基于全球化记忆的跨国符号”[5]13。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公共符号已经从政治及政治伦理领域延伸至记忆与集体身份认同范畴。正如亚摩斯·戈尔德伯格所言,大屠杀记忆有助于形成一种共同身份或共同归属感,从而催生一种“地球村”一般的大型想象共同体[6]5。大屠杀记忆的普遍化使作为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所有群体都在道义上获得了身份言说的空间,也为其他类似记忆形式的扩展开辟了道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开始正视和反思历史上的种族屠杀事件。
大屠杀记忆的全球化跨越了地域与文化的藩篱,使特定群体的受难经历成为一种超越民族或国家范畴的集体记忆形态。不同学科、文类、媒介、形式都从各自的视角对人类历史悲剧及其后遗症进行解读与反思。其中以大屠杀为主题的文学、影视、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促进了大屠杀叙事。正如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言,我们的社会试图通过纪念大屠杀事件创造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世界,“在每个大屠杀纪念馆里,犹太人的命运都充当了阐释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和种族相似遭遇的隐喻性桥梁,其目的显然不是把大屠杀作为历史早期的重要事件加以‘推广’,而是为当今世界实现多元主义与公平正义的可能性做出贡献”[7]257。大屠杀纪念馆成为全球记忆的圣地以及历史见证的中心,并与世界上其他大屠杀记忆中心形成紧密合作的网络,共同推动公共话语对大屠杀记忆的认知与传承。
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奥斯卡·辛德勒
《辛德勒方舟》被基尼利称为“纪实小说”(faction),这是“一种新闻类型的小说,大量依赖并引用事实,提供可供核实的场景,一般涵盖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8]503。据基尼利本人的叙述,198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遇到了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Leopold “Poldek” Pfefferberg),并首次听到有关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普费弗伯格是基尼利为小说创作所采访的50位“辛德勒犹太人”(Schindlerjuden,或Schindler’s Jews)中的第一位,正是他向基尼利提供了关于辛德勒的事迹。基尼利将辛德勒形容为“一位锦衣玉食的德国人,一位投机商,一个魅力四射的男人,一个矛盾的化身……他在那个如今通称为大屠杀的年代里,拯救了一个被诅咒种族中的男男女女”[9]1。针对这一主题所带来的挑战,基尼利选择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形式,把小说与纪录片相结合。通过小说的形式,能够更好地勾勒出历史人物辛德勒的正确形象,因为“小说的技巧似乎适合于表现像辛德勒这样一位如此含混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9]2。与此同时,基尼利又利用纪录片式的技巧,通过大量现存文字、口述历史和照片材料来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基尼利采用的叙事策略赋予了该书小说的虚构魅力以及纪录片的真实感,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获得成功。
《辛德勒方舟》不仅仅是对普费弗伯格记忆的转述,同时也是对辛德勒惊人历史的记录。基尼利有充分的理由为其创作的历史性与真实性作担保,他的资料来源包括对50名“辛德勒犹太人”的采访,对故事主要地点的实地探访,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提供的大量证词,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辛德勒朋友提供的辛德勒本人的文件和来往书信。这些都是可以核实的真实信息,暗示着如果读者有好奇心和精力,可以自己去寻找,就像基尼利可以在阿根廷拜访辛德勒的遗孀一样。想象虽然是“虚构”的,却可以讲述“非虚构”难以描述的真实。作者一再强调,“我一直着力避免一切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像辛德勒这样的伟大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我则一直力图将事实与神话区分开来”[9]2。
基尼利笔下的辛德勒并非一个十全十美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有缺陷的”英雄,一个道德上模棱两可的人,他成功地塑造了辛德勒这个“是人而非圣人”的普通人形象。小说中的辛德勒有血有肉,凡人的弱点和美德集于一身:他生活放浪,花天酒地,并非不爱妻子,同时又拥有若干情妇;他酗酒成性、善于投机和交际,花钱如流水,具有商人的狡黠和冒险的品性;他是一个战时的德国投机商人,却并不崇尚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屑与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恰恰相反,他倾尽全力去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辛德勒此举并非刻意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也根本不求回报,仅仅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正因为是一个普通人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非凡的壮举,两者之间构成的强烈反差才令人震撼和感动,更加凸显人性的伟大。
基尼利深刻分析了辛德勒的痛苦挣扎、思想动荡和行动轨迹。他从一个冷漠的人蝶变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却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使得笼罩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神话色彩更加浓厚。基尼利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辛德勒吸引他的原因是,“你无法说清楚机会主义在哪里结束,利他主义在哪里开始。我喜欢这种颠覆性的事实,即好的东西总是会从不可能的地方出现”[10]27。被辛德勒拯救的大屠杀幸存者们也对此感到困惑,他们通常的回应都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身上一定有“对人类的野蛮行为感到愤怒并对其做出反应的能力”。对辛德勒自己而言,他目睹犹太区数千人惨遭屠杀的那一天是他思想和行为的转折点,“从这天起”,他声称“任何有思想的人都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决心尽我所能来击败这个体系”[9]322。实际上,辛德勒拯救犹太人的义举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他与身边的犹太人一起长大,对犹太人甚至有一种崇敬和尊重之情[11]14。辛德勒的英勇故事很多,围绕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寓言、传说和神话。正如帕特里克·怀特笔下的沃斯多次被比作上帝,辛德勒也成为大屠杀中非犹太救援者的一个总称,成为犹太人的一种宗教象征。一位幸存者多年后回忆道,“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母亲,他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他从未让我们失望”[9]391。基尼利这样看待关于辛德勒的神话,“神话不在于它是否真实,也不在于它是否应该真实,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比真理本身更加真实”[9]3。
基尼利对辛德勒人物形象的刻画主要通过另一位主要人物阿蒙·葛斯(Amon Goeth)完成,他把葛斯称为辛德勒的“黑暗兄弟”[9]192。葛斯是纳粹党卫军军官,一个死忠的纳粹分子,第三帝国暴行及其“最终解决方案”的化身。与辛德勒一样,葛斯也是一个既复杂又矛盾的人,两人在小说中形成了饶有趣味又意味深长的对比。这“善恶的两端”[9]482不但家庭出身、外貌特征、兴趣爱好都基本类同,甚至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无相同之处,但两人最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救世主,另一个是作恶者。作家将葛斯作为检视辛德勒的一面镜子,迫使读者认同纳粹的权力,而不仅仅记录他们的残忍。基尼利对葛斯的塑造着力反映其人性的复杂,他倾向于用一种“技术中立性”的手法来描述人物,向读者提供人物内在与外在生活的完整画面,从而让读者自己做出判断。对读者而言,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救世主或作恶者,并且这两种人都没有先决条件。正如基尼利所言:“你仍不免会将葛斯视作辛德勒的黑暗兄弟,如果辛德勒的性情不幸颠倒一下的话,他也极有可能成为葛斯这样的暴君和狂热的刽子手。”[9]192辛德勒并非注定会成为英雄,葛斯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恶魔。辛德勒不惜倾家荡产、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1 000多名犹太人,从而成就了传奇英雄的“本质”;葛斯“杀起人来就像一个职员每天上班一样冷静”,“上绞刑架的时候丝毫没有悔恨的表现,死前还敬了个国社党的举手礼”[9]192,由此造就了他的恶“本质”。
基尼利跨越了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的界限,在真实性和虚构性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虽然基尼利撰写的是一部小说作品,但它是基于对世界各地“辛德勒犹太人”的深入研究与采访而写成,这是其他学者都无法企及的。但作为作家的基尼利也深知:真相只可接近,永无抵达的可能。“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虽由无数真相组成,那些真相却定格在过去,没有人能像上帝一样客观地见证事件的全貌。基尼利的非虚构叙事以历史和记忆为背景,并按照时间顺序逐渐展开,再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即一个德国人在战争期间无私帮助犹太人的故事。基尼利可能编造了小说中人物的交流和对话,但却忠实于他们的行动和意图。历史上真实的辛德勒86岁的前妻艾米莉·辛德勒(Emilie Schindler)如此评价道:“这部小说是纯粹的真相。它展示了一些丑陋的东西,但当你意识到这是真相时,它变得更有力量。真相甚至比小说中所讲述得更加糟糕。”[12]23
三、奥斯维辛之后:大屠杀的记忆伦理
大屠杀发生于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理性社会,大屠杀记忆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总是处于无法言说却又不得不说的伦理困境之中。面对这一惨痛的过去究竟是应该记忆还是应该忘却一直是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大屠杀这一极端事件的悲惨程度远超人类语言所能言说的范围,它体现出道德伦理的无力与生命意义的虚无,基尼利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对这一人类悲剧的诗意再现,恰恰使西奥多·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命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阿多诺在《文化批评与社会》一文中说:“文化批评发现自身面临着文明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我们对如今为什么不能写诗的理解。”[13]34在阿多诺看来,人类在经历了这场超乎道德底线的残暴屠戮之后,所谓高贵的诗歌已经暴露出自身的空洞虚伪,“写诗”也构成了对野蛮人性的苍白掩饰。阿多诺的命题一经面世便引起广泛论争,遭到了诸多反驳,促使阿多诺重新思考“苦难意识”这一重要议题,继而指出,“日复一日的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就像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权利尖叫一样”[14]363。事实上,对人性灾难的反思一直都是文学的基本职责之一,苦难一旦汇入艺术,艺术便负有唤醒人性之责,只不过如何在真实史料的基础上,重新书写人类的血腥历史,使其具有文学的审美意蕴,仍旧是对作家能力的一种考验。
基尼利勇于承担起唤起记忆与纪念的责任,对敏感议题和历史问题进行书写及探讨,在继承世界文学主题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当下性的思考。小说标题《辛德勒方舟》源自“诺亚方舟”,极具宗教隐喻色彩及救赎意味。“方舟”一词寓意“希望与重生”,正如辛德勒的“方舟”,实为纳粹大屠杀时期辛德勒全力庇护下的犹太人工厂,进入辛德勒的工厂即登上了隐喻重生的方舟,逃离了死亡境地,驶向生之彼岸,使随时面临灭族之灾的犹太人得以幸存,乃至繁衍生息。小说的美国版及电影版标题被易名为《辛德勒名单》,真实的“名单”取代了“方舟”,虽失去了宗教隐喻意义,但却暗含了拯救和救赎的双重意蕴。辛德勒的“名单”拯救了1 000多名犹太人,但小说中其实还有一份事关生死的名单,也就是获得拯救的全体犹太人签名作证的名单。辛德勒的名单把犹太人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而犹太人的名单又使辛德勒后来免遭盟军追捕与战后审判。两份名单交替的那一刻,双方的角色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这种回报性的彼此拯救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救赎过程,彰显了“名单”的救赎力量与人性的本善之力。
《辛德勒方舟》讲述的不仅是辛德勒救助1 000多名犹太人的故事,更呈现出正统派犹太教文化及其身份认同从丧失到重建的痛苦历程。小说中德军入侵波兰后迫害犹太人的第一个场景,不是搭建犹太人隔离区,不是强制佩戴大卫之星,而是废止犹太人的一切律法与习俗,即从文化表征上消灭犹太人的痕迹。这些习俗来自希伯来圣经及后世犹太拉比对《圣经》的解释,是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的重要身份标记。书中详细描述了正统派犹太男子被割去垂发的段落,垂发是正统派犹太教徒男性的标志性发型,这意味着大屠杀从剥夺犹太律法的合法性开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辛德勒出于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与理解,表现出对犹太文化重建的热情,他在将工厂搬到老家捷克苏台德区后,鼓励勒瓦托夫拉比带领其他工人一起守周五安息日,“每到星期五下午辛德勒就会对他说,‘您不该待在这里,拉比,您应该去准备过安息日了才对’”[9]243。由此可见,辛德勒拯救的不仅是犹太人的物质生命,而且是他们作为文化载体的生命。德国投降后辛德勒被迫连夜出逃,在最后的告别仪式上,辛德勒提议为死难同胞默哀,勒瓦托夫拉比带领大家用希伯来语唱歌表示哀悼。此时的希伯来语歌声具有无与伦比的抚慰作用,同时也象征着犹太文化的重建与大屠杀幸存者恢复文化尊严的开始。
伦理学家阿维夏伊·马各利特曾说:“人类到底应该记住什么?简单来说,人类应该记住那些根本之恶以及反人类的罪行,比如奴役、驱逐平民和大规模灭绝。”[15]78这里所说的“根本之恶”,就是那些“足以动摇道德根基的行径”[15]78。接着马格利特展示了两种对待过去创伤的范式:记忆或忘却,是选择记忆以留存过去,还是选择忘却以放眼未来。徐贲②接受了玛格利特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记忆不只是“知道”,而且是“感受”,被忘却是一种人在存在意义上的可怕的惩罚,因而他强调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个体应该通过叙述的途径让记忆在公共空间中自由交流,分享他们的记忆,才能形成集体的共同记忆[16]7。在这种意义上而言,《辛德勒方舟》具有文学治疗和见证历史的双重意义。小说中所展现的大屠杀创伤记忆,不仅涉及具有相同创伤经验的犹太人群体,同时涉及犹太人幸存者及其后代子孙之间关于大屠杀记忆的代际传递。对于当代犹太人群体而言,大屠杀记忆蕴含着征服、暴力、绝望、遗忘与纪念的复杂情绪;对于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这一记忆造成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而对于那些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犹太人后代而言,大屠杀记忆是犹太历史与文化的浓缩,是整个族群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渠道。在这种记忆的历史化过程中,大屠杀的创伤成为一代人或某个集体共同拥有的记忆对象,并成为文学写作、电影等再现和塑造过去的基础,它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传递使其进一步融入民族或集体的文化记忆中。
四、结语
通过在世界记忆语境中对大屠杀记忆及其文学表征的考察可以看出,基尼利致力于将犹太人群体的战争创伤从个体苦难上升为集体危机,从文学主题演变为哲学、伦理或道德主题,从身体、精神及社会创伤深化为“文化创伤”。正如亚历山大所说:“通过文化创伤的建构,社会群体、民族社会,有时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在认知上辨认人类苦难的存在及根源,还会就此担负某些重大责任。一旦他们确认了创伤的根源,并由此担负起道德责任,集体成员便能界定彼此的团结关系,并在原则上分担他人的苦难”[7]1。然而,实际情况是,社会群体成员往往拒绝承认他人创伤的存在,借此推卸自身对他人苦难的责任,甚至将自己苦难的责任投射到他人身上。因此,在集体层面上对大屠杀记忆的保存、传播及反思不受个体、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而是以人性的道德责任为基础,以人类对文明和未来的共同愿望为支撑,这也许是基尼利着力书写大屠杀记忆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高官,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二战后艾希曼一直流亡海外,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部门逮捕。1961年2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类罪名等15宗罪名起诉。这次审判因不少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而引起国际注目。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② 旅美学者徐贲曾以玛格利特的《记忆的伦理》为基础写作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并以之作为“序”收入其同名著作,使其在大陆知识界得到初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