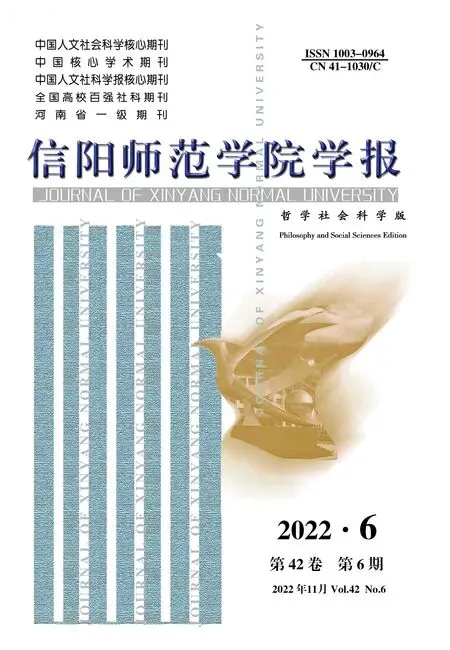清末民初小说话中“典型化”理论的探讨
李军辉,乔 丹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典型”一词虽未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出现过,但关于典型化问题的讨论在古代文论中却多有涉及,如叶昼在评析《水浒传》中诸人物时指出,“同而不同处有辨”[1]196,金圣叹也指出,《水浒传》中的众人物“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相识”[2]83,但人人又不同,每个人物都有区别于他人的典型气质、性格、形状等[3]20。这些典型化问题的讨论,虽然尚属粗浅阶段,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但对于晚清民初小说话作者们有着很大的启发,并逐渐进入创作界和理论界的视野,成为重大热点话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发掘并理清晚清民初小说话中有关典型问题的论述,以便更好地把握现代小说典型化理论建构的内涵演绎。
一、关于“人物性格典型性”的早期论析
追溯小说话的缘起,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首先进入了当代文论学家的视野,可作为中国小说话的发轫[4]5。统揽小说话的发展,其所承载的内容,对于历代小说人物性格的评析是一个热点话题。经久不衰的讨论热潮体现着小说话作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特别关注,也体现着小说话作者们的价值判断与审美追求。
佚名在小说话《西游记窾言》中对《西游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进行了点评,如“八戒之呆状可笑,行者之尖态可喜,沙僧之冷语可味”等,用“呆状”“尖态”“冷语”等词描摹,一语中的地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亲切可感。尤其是在评析孙行者这个人物形象时,强调用“猴”字之妙,“猴”的动物特性在行者的身上得到完美体现,而行者的行为处事又符合“猴”的动物属性,使人与动物达到和谐共生。再如,八戒的形态与猪的憨态也是完美的结合,“行者耍处、八戒笨处,咄咄欲真,传神手矣”[5]72-73。张其信在《红楼梦偶评》中也指出:“湘云之豁达,迎春之昏懦,探春之英敏,凤姐之悍妒,以及紫娟之忠,平儿之贤,翠缕之呆,大姐之傻,无不口角如生,始终一丝不走,真写生大手笔也。”[6]957这里已经若隐若现地注意到了“人物与性格”以及“性格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于人物的个性化及性格的多重性问题,在早期小说话中也多有论述。例如,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水浒传》中诸人物同是“粗鲁”的性格,却表现各异,“鲁达的粗鲁是性急,史进的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的粗鲁是蛮,武松的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的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的粗鲁是气质不好”等,他认为同一性格也有不同类型,因为人人有不同的气质、形态和言谈举止,只有形神兼备才能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形象。对于人物的个性化问题的探讨,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概括得较为传神,“宝钗外静而内明”“王熙凤,胭脂虎也”“尤氏者,以其人为尤物也”等,尤其对贾府中的几个“色鬼”,概括得最为精辟,“贾赦色中之厉鬼,贾珍色中之灵鬼,贾琏色中之饿鬼,宝玉色中之精细鬼,贾环色中之偷生鬼,贾蓉色中之刁钻鬼,贾瑞色中之馋痨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7]272-281,同为“色鬼”,而又色中不同、鬼中各异。对于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金圣叹也是较早发现这一问题的。他在评析《水浒传》诸人物时,指出武松不但“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小七之快、李逵之真”,而且还具有“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2]83。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对于大部分小说,看过一遍就弃之一边,唯独对《水浒传》印象深刻,其原因就是书中一百○八人都写活了,写出了每个人的性格特征。这种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振聋发聩的,首次明确地将人物“性格”的刻画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再者,早期小说话作者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展开人物批评,揭示性格与命运的关系问题。例如,西园主人在《红楼梦论辩》中指出,林黛玉与众女子相比,“宝钗有其艳而不能得其娇,探春有其香而不能得其清,湘云有其俊而不能得其韵,宝琴有其美而不能得其幽,可卿有其媚而不能得其秀,香菱有其逸而不能得其文,凤姐有其丽而不能得其雅”,通过比较使林黛玉的“娇”“清”“韵”“幽”“秀”“文”“雅”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再如,晴雯与袭人共事宝玉,通过二人的行为处事的不同比较来揭示其性格特征,“袭人之事也用柔,而晴雯则用刚;袭人之事宝玉也以顺,而晴雯则用逆;袭人之事宝玉也纯于浓,而晴雯则全于淡;袭人之事宝玉也竭力争先,而晴雯则偷安居后;袭人之事宝玉也或箴或劝,终日无不用心;而晴雯则一喜一怒,我身似不介意”。由此可观出晴雯的“性刚、气逆、情淡、甘居人后”的性格,袭人的“柔顺、争胜、用心”的特征。晴雯“刚直”性格在群芳汇集的大观园中,注定“傲与矜并起,亦妒与谗俱来”[8]650-652。
总之,早期小说话在人物形象及性格的批评上,虽未直接点明“典型化”问题,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进行“典型化”问题的探讨,涉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人物性格的个性化”“人物性格与命运和行为的关系”等问题,与后来的典型化理论在内涵上有诸多一致,完成了典型化理论的早期探寻。
二、关于“典型”意义与方法的争论
承接早期小说话关于人物性格的批评理论探讨,进入近代以来,创作理论的视野发生转移,不再过多地讨论人物的评析,而是转移到了对典型化理论的探讨上,即由单个的人物批评转型到对理论体系建构的批评。较早论及典型化问题的当属王国维和蓝公武。王国维早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就谈到了关于典型化问题的论述,王国维指出,美术(作品)创作的本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人类全体的性质而不是个人之性质;故在作品创作中要把全体之性质集于个人之一身,透过个人之性质来窥测人类全体之性质[9]76,犹如画家画人之美一样,“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9]80。通过对人之共性的撷取、加工,展现人之个性之美。蓝公武在小说话《红楼梦评论》中对《红楼梦》中的诸人物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宝玉,宗教家也,故无往而不用其情,其情为至情,为纯粹无私之情。黛玉,哲学家也,不同流俗,超然高攀,不能与世推移。宝钗、凤姐,政治家也,才具可爱。妙玉,才子也,才高遗妒,过洁受嫌,不仅当时大观园中人嫌之,即至今读者亦多嫌之。史湘云,文豪也,跌宕可爱。惜春,大师也,独具慧眼。探春,英雄也,有任事才。宝琴,君子也,守身如玉。”[10]146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蓝公武所分析的每一个人物形象,“举其大者”,已经具有了类的属性,具有了“代表”的初始意义,“亦各合社会中一种人物而足以代表之也”。代表着社会中的一种人物类型,已经具有了人物“典型意义”的味道。后来成之的《小说丛话》就是在此基础上详细地分析了《红楼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代表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典型意义”的理论。总而论之,小说人物典型化的意义与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人物塑造要具体,即人物要具体可感,有血有肉;二是强调人物形象的“代表”性,即透过个人之性质来窥测人类全体之性质。正所谓“写一人,窥全体”“虚写一家,实乃百家”,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艺术的典型意义正在于此。
关于塑造典型的方法和技巧问题,小说话的作者们也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观点和思路。例如,侠人提出“明著一事焉以为之型,明立一人焉以为之式”。这里的“型”就是故事情节构筑的定例,“式”即人物塑造的示范,其实上就是讲怎样塑造典型的问题,但过于笼统。对于如何实现这一“典型”的塑造,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总结,他认为典型化要从“小”处和“深”处入手,何为小?就人物描写而言,则选取生活中普通常见者为代表;就事件描写而言,则选取简单明了之小事为代表。比如,描写侠烈壮健之人,则写三军统帅可也,写匹夫之勇可也,但毋宁写匹夫之勇;写缠绵悱恻之情,写忠君爱国、忠臣义士可也,写贾宝玉、林黛玉可也,毋宁写宝黛私情。因为前者事大而难见,后者事小而易明;前者或令人难以想象,后者则多属于耳濡目染,正所谓“以小见大”。何为深?“是指凡写一种事实、一种人物,必加重数层。比如,写一善人,必尽其善;写一恶人,必尽其恶;写一侠烈之人,则无丝毫柔情”[11]2797。深入挖掘出人和事中的内里层面,才能写出与众不同来,写出个性来,这里作者对“典型化”的认识,凸显出了“最突出”的原则。
以小见大是典型艺术最突出的特征,也是进行典型塑造最重要的方面。以小见大就是通过个人之事实来窥视人类全体之性质,具体到人物形象本身,就是说塑造的人物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有着区别于他人的鲜明个性,如此才能称之为“典型”。但是个性并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人物只写一种性格,成之所谓的“深”就是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要熔炼好人物性格的方方面面,写出“深”意来,才能写出这一类人的本质。其实,在此之前的小说话作家对此也有深切的认识,如曼殊在比较《水浒传》《红楼梦》两书中的人物形象时说:“唯《红楼》所叙之人物甚复杂,有男女老少贵贱媸妍之别,流品既异,则其言语、举动、事业,自有不同,故不重复也尚易。若《水浒》,则一百○八条好汉,有一百○五条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儿,等也;其事业同是强盗,等也;其年纪同是壮年,等也,故不重复也最难。”[12]1197“不重复”皆因挖掘出了人物的本质属性,写出了人物的深层性格,成为“类”的代表。对此石庵在《忏空室随笔》中品评《七侠五义》诸人物时也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艾虎之忽而粗豪,忽而精警,似从《水浒传》中武松、石秀二人融化而出;白玉堂之纵意径行,恃能傲物,似从《水浒传》中卢俊义、鲁智深二人融化而出;蒋平之处处精细,举动神速,似从《水浒传》中之吴用、时迁、阮小七等诸人融化而出”[13]1583。这里作者已经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的熔炼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矛盾性等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典型化概括。后来的小说话作家更有体悟,并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如冥飞、海鸣、著超、玄甫、太冷生等5人撰写的小说话《古今小说评林》中论及曹操人物形象时,指出曹操形象使人毁誉参半、褒贬不一,这正是成功塑造的明证。书中刻画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所以,“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有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4]3290-3291。胡适对于典型人物的刻画和典型环境的书写,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写人要举动、口气、身份、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15]55。胡适强调对于个性化的处理,要从细微处入手,如对人的一个举动、一个表情、一个语气等的刻画,就能显示出与众不同来;从小处着眼,如对典型环境的描写,一山一石皆可着墨,一草一木皆可下笔,且此山之石非彼山之石,此处之草木也绝非彼处之草木。这样的塑造和描写,就写出了独特性和个性,其实也是典型化处理的基本路径。
三、关于“典型化”过程的商榷
关于典型化的过程,近代文论及小说话有相当多的论述,不过他们大都把典型化的塑造过程等同于“美”的制作过程。例如,鲁迅先生在《拟播美术意见书》中指出,美术(作品)创作需要借助于自然界中的事物作为素材,然而自然界中的素材或过于华丽,或过于荒秽,或过于枯槁,未必尽合创作者之意,在进行创作再现时,作者势必要削高补短、添枝加叶,使其完美呈现,这一过程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对客观事物的美化过程。所以,鲁迅先生对“美术”进行了这样的定义,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强调了天物、思理和美化作为美术的“三要素”[16]50。可以看出鲁迅所说的天物即“天赐之物”,就是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也可延伸至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所谓的思理就是创作者对美术(作品)的创作构思;所谓的美化就是作者对外物的加工与提炼过程,即对天物的“削高补短、添枝加叶”。美化的加工过程,就是先做到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即“眼中之物”,再做到对“眼中之物”的消化、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即“心中之物”,最后就是经过加工、提炼,创作出新的事物,即“手中之物”,这也就是人物与环境的典型化过程。正如解弢在《小说话》中所说的那样,“施耐庵之作《水浒》也,先图一百八人之象,黏之屋壁,顾其面貌,揣摩其言行,然后落笔,故能一丝不走。是诚作小说之妙诀也”[17]3172。全面描述了典型化的整个过程。
对于典型化的过程,成之的观点与鲁迅先生的观点高度一致,都指出了典型化的过程就是“美”的制作过程,就是“祛除不美以美补之”,进而塑造出“纯美”的典型[18]2766。显然这个“纯美”的塑造过程也即典型化的过程。但对于“美”的制作过程,成之在其小说话《小说丛话》中把它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模仿,所谓模仿就是对美的事物的效仿,面对美的东西人人都有察辨不美事物之缺陷的能力,必然会产生对美的趋同和对不美的疏离,对美的趋同过程就是对美的对象的模仿过程,使自己的情感与价值无限接近或等同于美的本身,这也是一个“物化”的过程。但人人又有不同,尤其是美的观念,面对不同的美要加以比较、甄别和筛选,选出自己认为的美,这就是成之所谓的“美的制作”的第二个阶段——选择,在选择中要“去物之不美之点而存其美点之谓也”,即选择出最理想的美。能模仿、能选择,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的想化。所谓“想化”就是作者完全跳脱自然界中实物的干扰,调动全部的经历、阅历、审美,甚至于知识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参与,生出一个“美的想象”,也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意化”。对于这个“想化”过程,成之曾举例进行了说明,如对一个美人的塑造:当前之美,已尽态极妍,但因作者创作之需要,嫌其丰则减、嫌其瘦则增、嫌其高则缩、嫌其矮则长,经过作者这种繁复的减、增、缩、长之后,创作出来的美人,已经与原来的大相径庭,这种新的美人的制作过程就是“想化”过程[18]2761。这一过程,完成了创作者独特审美理想的再造,实现了由客观事物到美的生成的“意化”过程。剩余的就是把作者脑海中想象出来的美的事物,付诸笔端,就是所谓的创造[18]2761。
对于整个“美的制作”过程的四个阶段,成之曾用鲜明具体的语言进行过这样的描述:作者在进行“美”的创造时,必取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然客观事物良莠不齐,必进行选择;选择结果未必符合创作者之需求,需要进行删减增补的想化;最后实现重造一新物的创造。这一过程中,在选择基础上的“想化”,是对原有事物基础上的删减增补,即把不美之处用其他美来代替,或臆造一部美来填补,是各种美的混合,新造之物的美蕴含着原有美的一部分,并非如水中投盐,化合于无迹[18]2768。通过这一过程的完成,作者“造出第二之社会”,最终“别造一新物”,这一新物,既有原物(天然景物、客观世界)之一部分,又有作者的臆造掺杂其中,形成了“混合物”,而非“化合物”。成之认为,文学即为“美的制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原有美的模仿层面,而是要尽力创造出代表“人类之美”的新美。这其实就是后世典型化理论中的“对生活的艺术加工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成之的典型化论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后世影响很大。
其实,典型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上述内容论述的仅仅是作品自身在创作过程的典型化塑造,是从创作主体的愿望出发,寄希望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环境皆是典型,那么作者是否能够如愿,最终还是读者说了算。所以,经典化的过程离不开接受群体的认可和接纳,接受群体在经典化的过程起到巨大的外部推动作用。对于这一问题,小说话作者们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如蛮在《小说小话》中评点侠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时,指出古今以来人们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最熟于人口者,为《三国演义》中之诸葛、关、张,其次则唐之徐敬业、薛仁贵,宋之杨业、包拯,明之刘基、海瑞,偶一征引,辄不胜其英雄崇拜之意”。为什么呢?皆因这些人物不但具有英雄的鲜明气质,而且经过代代相传、口耳相授,已经在民众心中生根发芽,成为英雄的典范,成为衡量一个人物是否是英雄的比照参考的标准。人们在行为处事时会与英雄的品质直接对接,来检验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也需要具有广泛的接受基础。作者在文中还进一步阐释道:一个英雄人物成为“典型”有三个原因促成,“一、宗教。如崇拜关羽之为无上上人物,庙社遍天下,其由历代祀典之尊崇故。二、平话。平话别有师傅秘笈,与刊行小说互为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三、演剧。平话仅有声而已,演剧则并有色也。故其感动社会之效力,尤捷于平话”[19]1477。这里作者罗列的三个原因,其实概言之就是思想上的认同,宗教导之;接受上的广博,尽人可解;精神上的感化,声色并茂。不论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以何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接受群体的接受和认可使之成为“经典”的必要前提。针对蛮在《小说小话》中论及的关于“典型化过程”的问题,觚庵在《觚庵漫笔》中也进行了论述,他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余谓得力于毛氏之批评,能使读者不致如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下,绝未注意于篇法、章法、句法,一也;得力于梨园子弟,如《凤仪亭》、《空城计》、《定军山》、《火烧连营》、《七擒孟获》等著名之剧何止数十,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足使当场数百十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二也;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三也。有是三者,宜乎妇孺皆耳熟能详矣。”[20]1513比较蛮与觚庵两位小说话作者的观点,蛮强调人物的“典型化过程”,由“宗教、平话、演剧”三者推之;而觚庵则强调作品的“典型化过程”,由“批评、演剧、平话”三者助之。其实无论人物的典型化,还是作品的典型化,都有异曲同工之法,觚庵在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强调了“批评”在“典型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大大丰富了后世典型化理论的内涵。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以诗文为中心的创作理论强调的意行合一、“道文”统一,追求的是形式美、言辞美、意象美、意境美,通过意象的摄取,意境的营造来实现“道文”统一的创作目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占据了古代创作理论的话语中心。小说话的出现,一改古代创作理论的窠臼,把批评的目光聚焦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开始了对小说人物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批评。虽有传统文论的印记和历史时代的束缚,但对小说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审美批评,却跳脱了传统的局限,涉及诸多问题,成为典型化问题讨论的前驱和基础。近代以来,小说话作者们在承继前期小说话论述成果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究“典型化”的理论问题,并逐渐建构了“典型理论”的轮廓。总之,“典型化”理论的探讨及建构过程,是中国小说创作理论现代转型的重要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