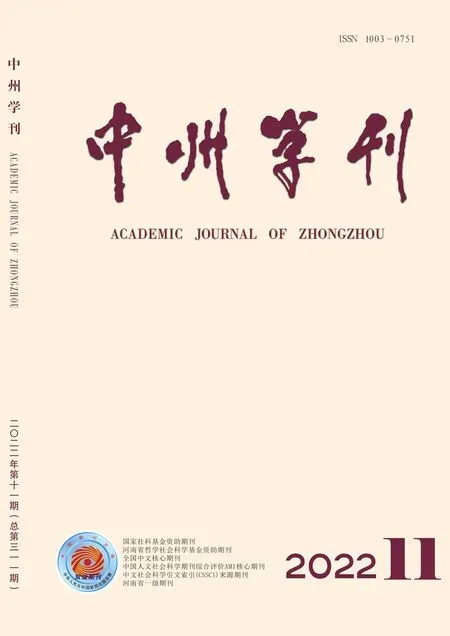从“《诗》本事”到“诗本事”:古代诗歌本事批评的传承与发展
杨 柳 青 过 常 宝
“本事”在先秦大多指农桑之事,例如《管子》云:“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1]本文所说的“本事”指诗歌创作的背景和缘起,与之接近的含义最早出自《汉书》:“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2]2737这里的“本事”指《春秋》微言大义背后的历史事实。本文讨论的“《诗》本事”是指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诗歌本事,“诗本事”则指后世广泛的诗歌本事。
有关本事的渊源,清人毛奇龄《西河集》云:“自祈招止王,左丘志始;墓门负子,屈氏更端。于是韩婴有记实之文,刘向得征情之序,此即后人本事之所自昉矣。”[3]毛氏将本事的源头系于《韩诗外传》以及刘向《列女传》《说苑》等作品,可谓真知灼见。余才林在《唐诗本事研究》中继承这一理念,他认为:“《诗序》和《韩诗外传》对唐诗本事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显明的,本事中诗与事的结合方式及文本结构均部分源出这两部汉代诗学著作。”[4]这些看法基本已为学界共识,但不够全面,仍存在诸多局限。事实上,除了上述文献,先秦的史传及诸子散文中也包含不少《诗》本事,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诗》的创作背景。汉代经师在解《诗》过程中力图追溯诗歌的创作背景,除了《毛诗小序》《韩诗外传》以及刘向等人的作品,散佚在典籍中的三家《诗》说中亦不乏《诗》本事。我们在探讨本事的起源和发展时,不应忽视这些文献。本文结合以往被忽视的材料,围绕狭义的“《诗》本事”如何泛化成为广义的“诗本事”,纵向梳理“《诗》本事”和“诗本事”的发展历程,揭示古代诗歌本事批评理论形态的传承与发展,以期对《诗经》的阐释和诗歌本事批评的发展做一些深入思考。
一、从“《诗》本事”到“诗本事”
1.先秦:“《诗》本事”的滥觞期
先秦时期《诗》本事的主要来源有三个:
一是《诗》文本。《诗经》文本中的本事较少。例如《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诗句明确此诗为周宣王时期的大臣尹吉甫送别申伯所作。又如《大雅·烝民》“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仲山甫欲前往齐地,尹吉甫作《烝民》相赠。
二是史传著作。史传中的《诗》本事较多,其中《左传》包含的最多。比较典型的有《卫风·硕人》《鄘风·载驰》的本事,《左传·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5]30-31《左传·闵公二年》:“卫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5]267《左传》还记载了《清人》《黄鸟》《常棣》《武》等诗篇的本事,不再赘述。《国语·楚语上》记载了《大雅·抑》的本事:“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6]500韦昭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6]502另《国语·周语下》云:“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6]503明言《昊天有成命》一诗乃道文王、武王能成其王德。《左传·昭公十二年》还记载了周逸诗《祈招》的本事:“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5]1297
三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如《孟子》《墨子》《荀子》中含有不少《诗》本事。《孟子·告子下》:“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7]5996-5997尹伯奇为仁人,其父尹吉甫虐之,故作《小弁》抒发幽怨之情。高子认为伯奇抒发怨亲之情有过,故为小人,孟子直指其陋,认为诗人之意乃抒发亲亲之悲怨,故《诗》曰“何辜于天”。
上述《诗》本事多为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称为史本事,不属于有意识的本事解《诗》,这些内容或指出创作者或记录作诗之由,已初步具备本事的要素,但仍处于零碎的状态。这一时期可视为《诗》本事的滥觞期,推动着汉代用本事解《诗》的诗学观。
2.汉代:“《诗》本事”的重要积蓄期
两汉时期的《诗》本事尤为典型,汉代经师上承“以事明义”的传统,沿用先秦《诗》本事的模式。与之不同的是,他们多有意识地运用本事解《诗》,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或故事情节来阐释诗篇。此外,这一时期以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本事也有明显的发展。
汉代史书也包含大量《诗》本事。《史记》中包含《秦风·黄鸟》《邶风·击鼓》《豳风·鸱鸮》《小雅·采薇》《大雅·公刘》等诗篇的本事。例如《史记·秦本纪》:“秦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黄鸟》之诗。”[8]
汉代经师解《诗》时多涉及《诗》本事。齐、鲁、韩三家《诗》在汉武帝时被立为学官,到了东汉,作为古文经学的《毛诗》独领风骚,三家式微,于魏晋之后渐次亡佚,而《毛诗》独存。三家《诗》的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清代是集大成时期,使我们得以比较全面地看到散落在纷繁古籍中的三家《诗》原貌。《毛诗小序》近乎全用本事说《诗》;《鲁诗》派代表学者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以及蔡邕的《琴操》《独断》等作品都含有大量《诗》本事;《韩诗外传》多采史事或杂说解《诗》。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鲁说不限于刘向、蔡邕的作品,《礼记·坊记》:“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郑玄注:“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定姜无子,立庶子衎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献公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正义》云:“此是《鲁诗》。”[7]3514该段内容为《邶风·燕燕》的本事。韩说不独有《韩诗外传》,经疏史注等典籍所引的《韩诗薛君章句》及《韩诗》中也包含不少本事。例如《文选·辩命论》李善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曰:“芣苢,泽写也。诗人伤其君子有恶疾,人道不通,求己不得,发愤而作,以事兴。芣苢虽臭恶乎,我犹采采而不得已者,以兴君子虽有恶疾,我犹守而不离去也。”[9]2348《韩诗》认为该诗的本事为一女子的丈夫有恶疾,她坚持不改嫁并作诗以明志,这一本事与鲁说《列女传·贞顺篇》所载的“蔡人之妻”①基本相同。《齐诗》也不应被忽视,《汉书·儒林传》云匡衡从后苍学《齐诗》,其本传载匡衡上疏云:“臣窃考《国风》之诗……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应劭注曰:“《黄鸟》诗所为作也。”[2]3335-3336这里所记与《史记》所载《黄鸟》本事同。
汉代《诗》本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目的明确。汉代经师往往通过叙说创作背景来揭示诗旨,这与先秦无意识的《诗》本事已截然不同,是汉代《诗》本事最典型的特征。先秦史传中的《诗》本事大都基于史实,诸子散文中的《诗》本事则是诸子阐述己说的工具。而汉代无论是今文学派还是古文学派,都采用本事解《诗》,有明确的解经目的。二是所叙本事更具体,情节更丰富。以《鄘风·载驰》为例,先秦《诗》本事出自《左传·闵公二年》:“卫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5]267这里只有三十多字,叙事非常简练。而刘向《列女传·仁智篇》经过加工润色后,扩充为二百余字,故事更加具体,情节大大丰富,感情生动饱满,许穆夫人远识仁惠的形象跃然纸上。三是结构趋于完善。汉代《诗》本事不似先秦《诗》本事那样零碎,集中表现为两种结构模式,一种是以《诗序》《琴操》为代表的“主旨+事”模式,另一种是以《列女传》《韩诗外传》为代表的“事+诗”模式。前者一般先列篇名,再以一句话概括主旨,后述本事,如《毛诗序》:“《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7]630《琴操》:“《白驹》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贤居任也,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成风,谏不见受。国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长歌。”[10]后者往往先详叙本事,结尾引具体诗句,如《列女传》所引《载驰》本事。
汉代除了《诗》本事更加成熟,以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本事也有一定的发展。乐府诗本就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色,其背后往往有明晰的历史事实或故事情节。最典型的如《孔雀东南飞》,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而为此辞也。”[11]序中详细叙说了该诗的创作背景,后接诗句。又如,《汉书·礼乐志》收录《郊祀歌·天马》二首也包含简短的本事说明,第一首为“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第二首为“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2]1061,虽然简练,亦涵盖了创作时间、创作者、创作缘起等多个本事要素。需要指出的是,乐府诗本事只是来源于诗歌中的叙事特色,尚未体现出自觉的本事批评意识。从中可见,汉代本事已经突破经学的藩篱,开始由“《诗》本事”向“诗本事”泛化。
3.魏晋南北朝:“《诗》本事”到“诗本事”的过渡期
在汉代经学的影响下,《诗》本事无论在数量还是内容上均达到巅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较为沉寂,几乎没有突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诗本事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著作、史书、杂记等均涉及诗本事,诗本事一改先前的附属地位,超越了《诗》本事。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中均有诗事结合的描写。志怪小说如南朝任昉《述异记》:“相州栖霞谷,昔有桥、顺二子,于此得仙,服飞龙一丸,十年不饥,故魏文诗曰:‘西山有仙童,不饮亦不食。’”[12]曹丕的《折杨柳行》一诗正是化用这一本事。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含有大量说诗故事,如著名的“七步成诗”:“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13]该段描写为一则要素齐全的诗本事,具备创作者、情节和创作缘由等要素。
魏晋南北朝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发展时期,代表作钟嵘《诗品》中有数处诗本事。例如《中品·宋法曹参军谢惠连》引《谢氏家录》云:“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称‘池塘生春草’。”[14]124这则本事亦见于《南史·谢惠连传》。又如《下品·宋监典事区惠恭》:“惠恭本胡人,为颜师伯干。颜为诗笔,辄偷定之,后造《独乐赋》,语侵给主,被斥。及大将军修北第,差充作长。时谢惠连兼记室参军,惠恭时往共安陵嘲调,末作《双枕诗》以示谢。”[14]185《双枕诗》今不存,该诗的本事因《诗品》留存下来。
史书和杂记类著作中也记载一些诗本事。沈约在《宋书·乐志》中对晋宋吴歌杂曲的本事做了记录,涉及《公莫舞》《杯盘舞》《白纻舞》等。以《公莫舞》为例,《宋书》这样记载:“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15]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记载了大量乐府诗本事,涉及《雉朝飞》《走马引》《淮南王》《武溪深》《吴趋曲》《箜篌引》《平陵东》《陌上桑》《杞梁妻》等乐府诗。例如:“《平陵东》,翟义门人所作也。王莽杀义,义门人作歌以怨之。”又如:“《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越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乃作《陌上桑》以自明焉。”[16]这些诗本事结构统一,先点明创作者,后叙述具体的背景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本事的文本形态已较为成熟。从内容上看,本事类型丰富,各类作品所引本事涵盖史实、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从结构上看,志怪、志人小说以及《诗品》均先叙事后引出诗句,即采用“事+诗”的模式;《古今注》中的诗本事则先点明创作者后叙事,即采用“作者+事”的模式。这两种结构模式直接影响了唐代的诗本事。“事+诗”模式上承汉代《诗》本事,而汉代“主旨+诗”的模式在魏晋南北朝已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作者+事”模式。究其原因在于,汉代经师的目的是解经,把握《诗》的主旨是其本义,而到了诗本事,对象不再是经学,而是文学作品,故对诗歌主旨的探究不再那么重要。从性质来看,魏晋南北朝的诗本事与汉代乐府诗本事相似,同样不属于自觉的本事批评,属于诗事结合的创作手法或诗歌叙事成分的引申,为唐代本事批评的确立积蓄了重要力量。
4.唐代:“诗本事”的成熟确立期
唐代是诗本事的成熟确立期,具体表现为大量本事专著问世,其中孟启《本事诗》、范摅《云溪友议》、卢瓌《抒情集》三者最为典型。除了专书,唐代大量作品中都记载有诗本事。
“本事”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概念最早由孟启提出,他的《本事诗》是第一部专门的本事批评著作,将本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其《序》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17]该段文字为本事批评的重要理念,孟启认为诗者乃触事之兴咏,事引发情,情形于言。《本事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本事有玄宗宫人制袍藏诗、贾岛因诗不第、刘禹锡题诗玄都观、崔护叹“人面桃花”等。在孟启之前,如上文所述历朝历代均不乏《诗》本事或诗本事,然而多为旁引曲述,或附见史文,或彰于诗品,迄无成本,故《本事诗》的出现是本事批评成熟的重要标志,为《诗》本事泛化成为诗本事提供了理论支撑。
《云溪友议》记录了大量与诗人唱和有关的杂事,《四库全书总目》云:“诗话居十之七八,大抵为孟启《本事诗》所未载。”[18]1186该书“因事录焉”的记录方式与孟启的“触事兴咏”一脉相承,其《序》云:“每逢寒素之士做清苦之吟,或樽酒和酬,稍蠲于远思矣……摅昔藉众多,因所闻记,虽未近于丘坟,岂可昭于雅量。或以篇翰嘲谑,率尔成文,亦非尽取华丽,因事录焉。”[19]
《抒情集》收录了众多诗人的抒情作品,胡应麟《诗薮》云:“《抒情集》亦本事诗类也。”[20]《太平广记》中的“李廷璧妻”“曹生”“薛宜僚”②等诗事都出自《抒情集》。
除了上述三种诗本事专书,唐代《隋唐嘉话》《大唐新语》《明皇杂录》《唐摭言》《国史补》《杜阳杂编》《唐阙史》《玉泉子》《酉阳杂俎》《北梦琐言》等作品均载有大量诗本事。试举两例,《隋唐嘉话》记上官仪《入朝洛堤步月》本事云:“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侍郎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晓,蝉噪野风秋。’”[21]《唐摭言》记薛能诗本事一则:“薛能尚书镇彭门,时溥、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22]
唐代诗本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创作实践丰富,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本事类型也极为多样,更有专书问世,整理诗本事已成为一种自觉。二是理论总结完备,孟启《本事诗·序》及范摅《云溪友议·序》均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支撑,本事批评这一文学批评形式也在唐代独立出来。三是文本结构基本固定,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均有至少两种本事结构,到了唐代基本统一为“事+诗”模式。
自此,经过先秦两汉“《诗》本事”和汉魏六朝“诗本事”的创作实践,加之唐代本事批评的理论总结,创作和理论两大要素齐备,狭义的“《诗》本事”正式泛化成为广义的“诗本事”。
5.宋至清代:“诗本事”的继续发展期
宋以后诗本事继续发展,主要有三个表现。
一是续作频出。宋代出现多部《续本事诗》,今可考者有处常子、罗隐、聂奉先所作三种,三书均失传,目前仅能从古人议论中略窥其貌。《宋史·艺文志》著录《续本事诗》二卷,未题撰者,马端临《文献通考》云:“《续本事诗》二卷。晁氏曰:‘伪吴处常子撰,未详其人。’自有序云:‘比览孟初中《本事诗》,辄搜箧中所有,依前题七章,类而编之,皆唐人诗也。’”[23]该书完全接续孟启《本事诗》,同样七题分类,明代毛晋《汲古阁书跋》对其颇有微词,批驳处常子画蛇添足:“比览初中缘情、感事七类,皆叙事夹诗句……或病其卷帙太简,曾见蟹鸽臛罗列方丈者耶?犹觉伪吴处常子未免蛇足云。”[24]刘肃《大唐新语》著录宋代聂奉先《续广本事诗》五卷,《直斋书录解题》云:“《续广本事诗》五卷,聂奉先撰。虽曰广孟启之旧,其实集诗话耳。”[25]虽然古人针对这几部续作的评论贬多于褒,但不可否认,大量续作的问世体现了本事批评发展之迅速。清人徐釚的《续本事诗》为续作中的翘楚,该书以诗歌为主体,本事附于题序,无论内容还是体例都继承了“诗本事”的传统,内容更加审慎,体例更加完备,吸收前代的经验并改善不足,可视为古代本事批评的总结之作。
二是诗话勃兴。北宋诗话继承唐诗本事,多记诗事。陈振孙认为聂奉先的《续广本事诗》虽名为比览《本事诗》,实则为诗话总集,从中可见唐诗本事直接影响了宋人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首次以“诗话”命名,内容大部分以作家或作品的背景故事为基础,说诗28则,其中有21则叙述诗事。需要指出的是,诗话虽然在内容上继承唐本事,但二者仍有区别,在后续发展中诗话逐渐与本事疏离。正如余才林所云:“(宋代)诗话逐渐偏离本事的体式,证事变异,议论提升,诠事扩展。”[26]南宋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代表的诗话更是以议论为主,诗事不再是记述的重点。
三是纪事诗学发展。纪事体诗学著作与唐诗本事更是一脉相承,以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为代表,是书采摭繁富,《四库全书总目》云:“于唐一代诗人,或录名作,或纪本事,兼详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18]1785清代有厉鹗《宋诗纪事》、陈衍《辽宋金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当代有钱仲联《清诗纪事》,纪事体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学范式,可谓影响深远。
此外,《诗》本事在泛化为诗本事后没有完全沉寂,二者相辅相成,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并行发展。从宋代开始,学者普遍疑《序》,自宋讫清的大量解《诗》著作中均言诗事。如欧阳修的《诗本义》和苏辙的《诗集传》均创发新说,二人亦尝试从史书记载中挖掘《诗》本事,以此作为根据探寻诗之本旨,实与汉代经师说《诗》一脉相承。清末学者马振理搜集历代典籍,撰有《诗经本事》,该书可谓一部“《诗》本事”专著,依次对《国风》160首诗歌的本事进行梳理和评议。他认为“诗之作,其必有本事矣”[27],将《诗经》视为“《春秋》未作前之史”[27]。
二、“《诗》本事”泛化为“诗本事”的内在理路和外缘影响
“《诗》本事”在唐代正式泛化成为“诗本事”,这一转化是在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和文学批评发展进程的双重作用下引起的,前者是内在理路,后者是外缘影响。
从内在理路来看,《诗》本事既是一种经学阐释手段,也是一种文学解读方法,具有文学批评的内在因素,故有条件转化为广泛的诗歌本事批评。汉代经师广泛用本事注《诗》,这与先秦时期运用故事解说经典的方式相似。以事解经的传统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汉书·艺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2]1715依班固之言,《左传》乃用本事注《春秋》。运用故事解说经典的方式不仅仅出现在《诗经》和《春秋》中,《韩非子·喻老》也采用了数则历史故事和传说解释《老子》。这些注解方式可统称为一种“本事注经”模式,其后转化为更广泛的“本事注诗”,即本事批评。这说明从“《诗》本事”到“诗本事”也正是从“以事解经”到“以事解诗”,二者的转化有其内在合理性。
从外缘影响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评论著作的相继问世,文学批评发展逐渐成熟,这一时期被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受此时代风尚的影响,魏晋时期“《诗》本事”相对沉寂,“诗本事”则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获得较大发展,学术性有所降低,文学性得到提升。此外,由于魏晋时期著作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诗本事”还呈现出“作者+事”的结构模式,强调创作主体。唐代因理论体系的完备被视为诗本事的正式确立期,唐代以后,“诗本事”进一步影响了诗话、纪事等文学批评形式。所以,“诗本事”的发展历程与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外部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促进了“诗本事”的泛化。总的来说,从“《诗》本事”到“诗本事”,是文学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从《本事诗》续作看“诗本事”理论形态的传承与发展
唐代以后,文学批评继续传承并发展着诗歌本事批评。宋代处常子、罗隐、聂奉先的三种《续本事诗》早佚,据古人议论可知,处常子本完全比览孟启《本事诗》,而聂奉先本被陈振孙总结为“虽曰广孟启之旧,其实集诗话耳”[25],可知该书应兼具诗话的理论内涵,诗话的典型特征即论诗,聂书很有可能加入了议论部分。清代徐釚《续本事诗》的理论内涵较前作有了大幅提升,可视为古代本事批评的总结之作,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突出诗歌主体。本事属于诗歌批评的范畴,理论的主体应是诗歌文本。而孟启在《本事诗》中多断章附会,摘取部分诗句,将诗句置于事中,破坏了诗歌的完整性。徐釚的《续本事诗》录诗完整,将本事置于诗题、诗序或诗注中,在录事的同时保留了诗歌原貌。
二是强调本事。孟启“触事兴咏,有所钟情”的理论明确知诗事才能体诗情,落脚点在情,徐釚《续本事诗》继承并引申了这一理论。徐釚亦重视情,自云“因传《本事诗》,愿续断肠句”[28]1。但他更强调本事批评的核心是“事”,其《序》云“其事有足征述者,萃为一编”[28]1,可见“事”是徐釚选诗的主要标准。例如汤显祖《遥和诸郎夜过桃叶渡》一诗,题后注“汤自注云有本事”,该诗情感并不浓厚,亦被选入。
三是众体兼备。《续本事诗》汇集了诗选、诗话、诗评等众多诗歌批评形态。首先是诗选,徐釚将选诗标准明确为“其事有足征述者”,据此汇集了元末至清初的相关诗作;其次是诗话,其《略例》云“间采诸家诗话”,例如王佐《宫怨》一诗,徐釚引《梦樵诗话》《竹垞诗话》之语论诗;最后是诗评,徐釚在记录本事之余,还阐述了诗歌风格特征,对诗歌进行品评,例如唐时升《观妓戏作》,徐釚后注:“今录其对酒听歌之作,觉松圆诗老,情致宛然。”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本事批评发展到清代,批评的主体“诗歌文本”和批评的核心“事”都得到了强化,更是体兼诗选、诗话、诗评,融合了唐以后众多诗歌批评理论形态,理论内涵大大完善。
四、“《诗》本事”和“诗本事”的异同
“诗本事”在理论内涵上仍遵循“《诗》本事”的阐释思路和方法,因而二者呈现出一些相通之处。
一是本事类型丰富,内容相通。无论是经师解《诗》还是文人论诗,对本事的探求就是对作品创作背景的挖掘,本事类型不外乎历史事实、名人轶事、神仙故事、传奇故事、民间逸闻等内容。
二是文本结构形式相通。《诗》本事在先秦时期结构较零散,到了汉代基本稳定在“主旨+事”和“事+诗”两种形式,诗本事先是呈现出“事+诗”和“人+事”两种形式,到了唐代基本统一为“事+诗”的形式。
三是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诗》本事”和“诗本事”的来源之一就是史实,这部分材料具有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此外,说本事者往往征引广博,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得以保存。
四是内容往往虚实参半。有些《诗》本事杂以臆说,牵强附会,例如《列女传·贞顺篇》记载《王风·大车》的本事为息夫人作诗明志后自杀,这与《左传·庄公十四年》的记载有出入。又如《列仙传》和《韩诗外传》记载的《周南·汉广》本事为郑交甫与江妃二女的人神之恋,这些都是附会诗篇的杜撰。而诗本事从内容上看也包含传奇类和志怪类,这些本事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传闻性,亦为杜撰,最典型的如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的本事,女子死而复生的情节富有传奇色彩。明人胡震亨云:“唐人作诗本事,诸稗说所载,资解颐多矣。其间出自傅会,借盾可攻者,盖亦有焉。”[29]
然而,“《诗》本事”和“诗本事”毕竟是两种不同的阐释路径,它们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二者的性质不同。“《诗》本事”是一种治经行为,陈说本事是为了阐释《诗》义,目的是治经,偏重学术性;“诗本事”则是一种文学行为,带有文学色彩,目的是品评诗作,偏重文学性。《诗》本事是经师解经的手段,通过解《诗》使其成为一种作用于政教的经典;诗本事则是以文学的手段涵泳诗篇。
二是二者辨伪的意义不同。针对《诗》本事的辨伪意义不大,对“诗本事”的辨伪则需要重视。有些《诗》本事真伪难辨,无当史裁,但这些本事是经师在《诗》本义基础上的引申和发挥,对解经和《诗》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资料,而且能折射出特定时代的《诗》学风貌,因而这些本事具有积极作用,片面地辨正意义不大。以《召南·行露》为例,《列女传》和《韩诗外传》记载的本事中描绘了一位守礼有节的女子形象,该女子因夫家礼义不备而誓死不嫁,宣扬“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志贞理,守死不往”。类似的还有刘向《列女传·贞顺篇》记载的《邶风·柏舟》及《邶风·式微》两诗的本事,均宣扬了女子从一而终恪守夫妇之道的品行。这些本事于史无证,其真伪不可考,但其中蕴含的礼制教化作用十分明显,符合当时的伦理规范,也反映了汉代的诗学风貌。正如陈寅恪所言:“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30]虽然《诗》本事中不乏强以附史、刻意索隐的描写,但由于其治经的特殊性,积极意义较为明显。
而“诗本事”崇尚征实,自唐迄清的本事批评著作中均强调这一原则。学者多从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等文献中搜集本事,在选取材料时往往略去失实的材料。孟启《本事诗·序》云:“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事实者,则略之。”[17]徐釚《续本事诗》云:“小说家所记事多失实……总无明证,并不混载。”[28]44虽然在实际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辑本事者也不免疏漏,亦有悖谬和附会之处,然而他们对这一原则的重视不可否认。针对这些“诗本事”,整理者往往认真钩稽史料以作辨正,这种辨伪具有重要价值。例如《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云:
武年二十三,为给事黄门侍郎,明年,拥旄西蜀,累于饮筵,对客骋其笔札。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馔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琯亦微有所忤,忧怖成疾。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母则可谓贤也,然二公几不免于虎口矣。李太白为《蜀道难》,乃为房、杜之危也。略曰:“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19]36
该段本事描写《蜀道难》为李白因房琯、杜甫厄于严武而作,并云诗句“化为狼与豺”乃谓严武之酷暴。元代萧士赟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中对此本事进行了驳难,认为这首诗是为唐玄宗在安禄山攻占长安后仓皇幸蜀而作,后世大多采此说。然而这一说法也有误,殷璠《河岳英灵集》选录了开元二年(714年)至天宝十二年(753年)的作品,该书收录了《蜀道难》,而安禄山攻占长安的时间为天宝十五年(756年),萧士赟之说不攻自破。由此可见,对于“诗本事”的辨伪很有必要。
小 结
从“《诗》本事”到“诗本事”,本事批评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先秦为《诗》本事的滥觞期,这一时期的《诗》本事可以视为史本事,较真实地还原了诗歌的历史背景,但比较零散。汉代为《诗》本事的重要积蓄期,汉代经师多采本事解《诗》,本事内容更具体,情节更丰富,结构也趋于完善,这一时期以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本事也有明显发展,本事已突破经学的藩篱。魏晋南北朝为“《诗》本事”到“诗本事”的过渡期,各类文体均包含诗本事,这些本事类型丰富、结构成熟,《诗》本事则较为沉寂。唐代为诗本事的成熟确立期,创作实践丰富,理论总结完备,文本结构固定。宋代以后为诗本事的继续发展,续作频出,诗本事也促进了诗话的勃兴以及纪事体诗学的发展。
“《诗》本事”泛化为“诗本事”,是在文学内部规律和外部进程的双重作用下引起的。《诗》本事是一种文学解读方法,具有文学批评的内在因素,而本事批评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与文学批评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诗本事”发展到清代,批评的主体和核心进一步强化,又融合了众多其他诗歌批评形态,理论内涵得到发展。“《诗》本事”和“诗本事”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具体而言,二者在故事类型、文本结构、史料价值和材料虚实等方面均有相通之处;但二者的性质不同,《诗》本事是一种治经行为,诗本事是一种文学行为,前者的辨伪意义不大,后者对史料的辨伪值得重视。
注释
①《列女传·贞顺篇》:“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虽其丑恶,犹将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参见刘向:《列女传》,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②《李廷璧妻》:“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著骨黏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曹生》:“卢常侍鉟,牧沪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薛宜僚》:“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榇,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参见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146、215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