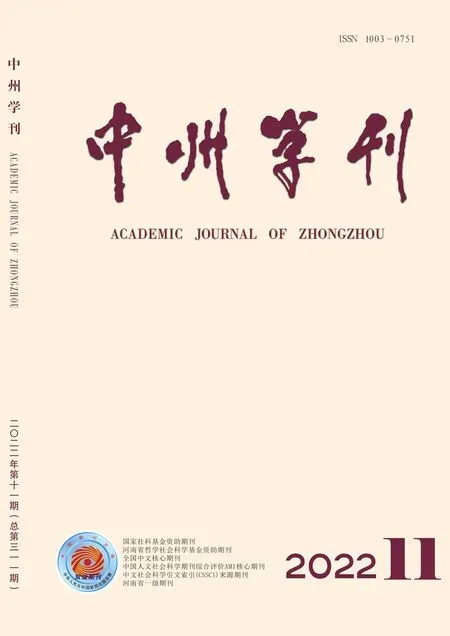求真实以黜名辩*
——《论六家要指》名家论之哲学分析
李 若 晖
中国哲学的真实建立之途,唯有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哲学分析。有论者以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其语言之精炼,议论之透辟,均可独步千古。说它是天地间少有之文,是一点也不为过的”[1]。本文即尝试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之名家部分为例,探索由文献分析通往哲学建构之途。
一、现代名学研究之反思
曹峰先生在其近著《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书中,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名学研究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总括性地指出了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名学研究之根本问题:“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名家’研究在中国一度极为兴盛,成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百年之后,我们回首这一研究领域,发现在取得许多重要学术成果的同时,其实也不无偏颇之处。可以说,‘名家’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方向性的错误,表现为不顾‘名家’所生存的思想史环境,将西方逻辑学概念、框架、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有削足适履之嫌。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逻辑意义上的、知识论意义上的‘名’,有时甚至曲解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将其当知识论、逻辑学材料来使用。自从将‘名’、‘辩’与西方逻辑学相比附后,只要谈到‘名’,似乎就只能从逻辑的角度出发。这样使很多看上去与逻辑学无关的‘名’的资料被轻视,被闲置,甚至被曲解。特别是那些伦理学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虽然是中国古代‘名’思想中不可割裂的、有机的、重要的成分,却因为西方逻辑学研究的思路而得不到正视和客观的研究。”[2]9
曹先生的确目光如炬,洞烛幽隐。20世纪的所谓“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找相同”的文字游戏。冯友兰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中,将其构造“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阐释得很清楚:“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245冯先生还进一步阐释道:“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3]249对此,景海峰先生批评道:“很明显,这样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本然面貌,不但在形式构成上是属于人为加工、有意造作的仿制品,就是具体内容也因经过有色眼镜的选材和西方观念的处理而变得难以辨识了。”[4]
基于对20世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反思,曹峰先生进而提出:“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讨论极为活跃,是当时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伦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名’与知识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名’。前者在中国古代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学术背景下形成的先秦名学研究,却只重视语言、逻辑意义上的‘名’,未对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展开过系统研究,有时甚至曲解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将其当语言、逻辑材料来使用,这使名学的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有必要拨乱反正,对各种‘名’思想重新作出客观地、全面地梳理。”[2]74作为例证,曹先生举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于名家的论述,认为:“虽然司马谈没有明确指出他心目中的‘名家’是谁,但是从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做相应的推测,即这里有两种名家的影子,正面的是司马谈所推崇的,将‘名’思想运用于政治场合的政治思想,反面则是被否定被批判的,执着于概念、名辞分析的,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2]77
本文将通过对于《论六家要指》的哲学分析,揭示出无论是司马谈的文本中,还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都没有所谓“语言、逻辑意义上的‘名学’”,而只有“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学’”。
二、《论六家要指》文本疏证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载《论六家要指》:
经: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5]3965
传: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5]3969
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在引用了《论六家要指》和《汉书·艺文志》的名家部分之后,评论道:“汉朝的历史家对于先秦思想的‘六家’的分法,本来就是不很科学的。他们所说的‘名家’的内容是很混乱的。司马谈所说的‘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是法家所讲的统治术。刘向、刘歆所说的‘正名’是孔丘的‘复礼’的方法。前者属于法家思想,后者属于儒家思想,两者正是相反的。司马谈所说的‘苛察缴绕’,刘向、刘歆所说的‘钩釽析乱’同法家所讲的‘控名责实’,儒家所讲的‘复礼’,既没有逻辑的关系,也没有继承的关系,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些历史家们仅看到一些现象,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就混为一谈,一概称之为‘名家’。这是很不科学的。”[6]376这可谓极其严厉的批评了。但是太史公对于名家的批评是否果真如此错乱?本文将通过对《论六家要指》名家部分的哲学分析,来揭示其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论六家要指》对每一家的评论,可以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司马谈作经,司马迁作传①。
司马迁叙乃翁作《论六家要指》之意为“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5]3965,《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颜注:“悖,惑也。各习师法,惑于所见。”[7]2710这是比附于汉代经学以作解,故《史记正义》引作“师书”以严分经子②。李笠《广史记订补》则曰:“师悖者,谓以悖为师也。小颜说未是。”又曰:“此‘师’字与‘师心自用’之‘师’同,作动词用,犹言效法也,‘师悖’犹言效法于悖。颜注释‘悖’为‘惑’,甚是。”[8]李说是。故此文论道德家之外的五家,都是分为“达意”与“师悖”两个方面。
我们先澄清几个争议之处的意义。
第一,“俭”。司马贞《索隐》:“刘向《别录》:名家流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家知礼亦异数,是俭也。”[9]3966小司马如字,其意盖谓礼既异数,则严禁僭越,于是在下者不得奢靡,此即是俭约。凌稚隆《史记评林》引董份曰:“墨者俭,是矣。若名家言俭,似不可晓。盖此乃检字,因上有俭字,写者遂误耳。解曰,检者,法也。又曰,检者,束也。下文苛察缭绕,即检束之意也。”[10]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董、梁说是也。名家出于礼,不得云使人俭,且与上墨者俭义相犯。盖检即敛也,《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赵注:‘检,敛也。’班书《食货志》作‘不知敛’。名家以绳墨检察人,使各约束于礼,而不得肆,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11]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庆长本标记引刘伯庄云,俭当作检,谓拘检人。愚按:俭检通用,下文所谓苛察是也。”[12]王叔岷《史记斠证》:“《长短经注》引俭作检,《金楼子·立言篇》同,与刘、董说合,检取拘检、检束义。”[13]3466张大可《史记新注》:“俭,通‘检’,咬文嚼字。这句是说名家纠缠在概念上打圈子,把人们的思想弄糊涂了,而不能掌握实际。”[14]2130此皆以“俭”为“检”,取束缚、纠缠之义。唯马持盈《史记今注》:“俭:同‘检’,检验,分析。”[15]3346将“检”释为“检验”,再转义为“分析”,理解过于现代。要之,《索隐》释“俭”平实可信,不必改读。蔡伯铭《评两汉对先秦名辩的评论》释作“言辞贫乏”[16]22,语言学意义不错,但是对文句的理解不妥。
第二,“失真”。司马贞《索隐》:“受命不受辞,或失其真也。”[9]3966“受命不受辞”见《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何休注:“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设,故云尔。”[17]97这是指处置事情要依据事态的变化灵活应对,如果死抠文辞字面不放,反而会导致偏离命令的真实意图。其他诸家的解释,如马持盈《史记今注》:“名家使人注重分析,反而很容易失去了事物的真象(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5]3346王汉民《太史公自序注译》:“受名词概念的束缚而脱离实际,所以说‘善失真’。”[18]11这是直接基于字面将“真”理解为“真象”。杨燕起《史记全译》:“名家使人拘束而容易失掉真情。”[19]4492韩兆琦译注:“由于名家过于讲究循名责实,讲究名分与实际的相称,结果就使人们被虚名、迂礼所束缚,从而违背人的真实情感。”[20]7638这是联系“传”中对应的“失人情”一语进行解释。
第三,“苛察缴绕”。《集解》引服虔曰:“缴音近叫呼,谓烦也。”又引如淳曰:“缴绕犹缠绕,不通大体也。”[21]马持盈《史记今注》:“苛察:毛举细节,反复推敲。缴绕:纠缠不止。”[15]3348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苛察’就是指对问题作过细的分析考察。‘缴绕’就是缠绕。所谓‘苛察缴绕’,就是指缠绕在某一问题上,作过于细致的繁琐论证。”[22]3蔡德贵、侯拱辰《道统文化新编》:“名家的学者都很精察,对周围的事物有精细的观察,一些平常人不能注意到的事情,他们也都注意到了。但他们的精察有时又太过分,因此而不必能如实,往往会繁琐支离而徒乱人意。”[23]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苛察’是指名家对各种概念的严格辨析,如公孙龙把现象世界与语言世界细分成‘物’、‘实’、‘名’、‘指’,论‘白马非马’的理由是‘形(马)非色(白),色非形’。‘缴绕’是指名家纠缠于语言概念,事实上,公孙龙的论辩就非常像绕口令……这种缠绕的结果,并未阐明有意义的理论问题,或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现象世界,而纯粹成为一种辩论的技巧。依中国传统学术来看,这就是所谓‘不通大体’,有‘术’而非‘道’。”[24]
第四,“反其意”。“反”有四种解释。一,推论。王汉民《太史公自序注译》:“反其意,推想它的用意。反:推及;推论;推想。”[18]19杨燕起《史记全译》:“反:反复,琢磨。”[19]4496由“反”作为复合词“反复”的语素,不能推论“反”就有“反复”之义。至于“推想”“琢磨”更乏根据。二,反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使人不能反省思考明白它的旨意。”[25]“反”是“反省”的语素,表示“反省”需要在思维中重复原过程。但是“反”并无“反省”的“省察”之语义。三,同“返”。马持盈《史记今注》:“使人没有可能恢复其本心诚意。”[15]3348韩兆琦译注《史记》:“不能回归各自的真实情性。”[20]7645这是将“反”读为“返”,但是又觉得“返其意”似乎讲不通,于是只能将下句之“情”引入。四,反驳。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解此句说:“名家的理论难以理解,艰深而不易为人反驳。”[22]3将“反”解释为“反驳”。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也注曰:“反驳他们的言论。”[26]344蔡伯铭《评两汉对先秦名辩的评论》:“令人不能违反‘名’的本意。”[16]22按“反其意”的“其”显然应当指句首的“名家”而非“名”,但是将“反”释为“违反”,所取的语言学意义与许先生的“反驳”相同。这里的“反”是“反对”“反驳”之意,不是“返回”的意思。譬如“白马非马”这样一个命题,虽然违背经验常识,但我却很难反驳名家对这个命题的论证,“白马非马”也从而成为一种悖经验的诡辩,这就是“使人不得反其意”。至于什么是悖经验的诡辩,以及为何会造成这种诡辩,都是后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五,“专”。高步瀛《古文辞类纂笺》:“《汉书》‘专’作‘剸’,颜曰:‘剸读与专同。’步瀛案:《说文》无‘剸’,‘专壹’之‘专’本作‘嫥’,经传借‘专’字为之。”[27]
第六,“而”。王念孙《读书杂志》:“而、时声相近,故字相通。《贾谊传》:‘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记·保傅篇》‘而’作‘时’。《聘义》曰:‘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大戴记·朝事篇》‘而’作‘时’。《史记·太史公自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汉书·司马迁传》‘而’作‘时’,是其证。”[28]
第七,“失人情”。王汉民《太史公自序注译》:“指惠施的‘合同异’,公孙龙的‘离坚白’之类,专从名词概念上来决定事物的属性,而违反人情。”[18]19马持盈《史记今注》:“完全玩弄名词而失却了人的本性。”[15]3348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解为“与人们的常识不符”[22]3。蔡伯铭《评两汉对先秦名辩的评论》:“一切取决于‘名’而不顾人们在使用‘名’时的思想感情。”[16]22祝捷《论刑名之学》:“纯粹的形名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专注于纯粹逻辑学探讨而忽视了对于人类社会实际状况的考虑。”[29]郭桥《立破之间——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说理分析》:“‘失人情’,即失弃人们的一般看法——常理。”“在司马谈看来,‘人情’即‘真’;违背了‘人情’也就意味着违背了‘真’;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有悖于人之常情(人之常情是‘白马马也’),所以失其情,不应当被接受。”[30]
第八,“控名责实”。《史记集解》引晋灼曰:“引名责实。”[5]3969张大可《史记新注》:“即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14]2132将“控”释为“引”是有根据的。《说文》:“控,引也。从手,空声。《诗》曰,控于大邦。匈奴名引弓控弦。”[31]252韩兆琦译注《史记》:“即‘循名责实’,按其名而求其实。控,按照。”[20]7645虽然不失文意,但是在“控”的语言学意义上并无着落。
第九,“参伍”。“参伍”一词历来有三种解释。一,《史记集解》引晋灼曰:“参错交互,明知事情。”[5]3969王汉民《太史公自序注译》:“参伍:错综复杂。失:乱。是说名家据名以求实,使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既有其名,又有其实,虽然关系复杂,但不错乱。”[18]19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参伍,参错交互,此谓即使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不使名实相违。”[26]344此皆读“参”为“cēn”,义为“参错”。并据“参”以释,而未顾及“伍”之词义。二,《说文》:“伍,相参伍也。”[31]164段玉裁注:“参,三也;伍,五也。《周礼》曰:‘五人为伍。’凡言‘参伍’者,皆谓错综以求之。《易·系辞》曰:‘参伍以变。’荀卿曰:‘窥敌制胜,欲伍以参。’韩非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史记》曰:‘必参而伍之。’《汉书》曰:‘参伍其价,以类相准。’此皆引伸之义也。”[32]段说确有所本。《易·系辞传》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孔颖达《疏》:“参伍以变者,参,三也;伍,五也。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略举三五,诸数皆然也。错综其数者,错谓交错,综谓总聚,交错总聚其阴阳之数也。”[33]此读“参”为“sān”,义为“三”。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司马谈所说的‘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是法家所讲的统治术。”[6]376所谓“法家统治术”,就是韩非的“参验”。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十三章《战国时期最后的理论家韩非的哲学思想》中说:“韩非说:‘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备内》)这就是说,要知道一个人所说的话(‘陈言’)是不是合乎实际情况,还需要用‘参伍之验’的方法。下文说:‘众端以参观。’这就是说,要想了解事情真象,不能专从一方面看,必须把许多方面的情况(‘众端’)搜集起来,排一排队(‘伍’),加以比较研究(‘参’),看这个人所说的话是不是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证实(‘验’)。如果能够得到证实,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是合乎实际情况,就是真的;如果不能证实,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是虚假的。韩非的这些话的认识论的涵义就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关于它的命题不一定都是真的;要断定命题的真假,须从各方面的情况加以研究,看其是否合于事实。”[6]646-647这是读“参”为“cān”,义为“参考”。三说相较,以段说最为有据。至于杨燕起《史记全译》:“参(cān)伍:错杂比较,加以验证。”[19]4496韩兆琦译注《史记》:“参,错杂;伍,排列。错杂排列,即参照比较,以定是非优劣之意。”[20]7645当用冯说,却将“参验”混同于“参错”。
第十,“使人俭而善失真”。一般都将此句理解为“而”字前后为因果关系。王叔岷《史记斠证》标点为:“使人俭,而善失真。”[13]3466则当是理解为转折关系。
三、名与真
《论六家要指》中,“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以及“使人俭而善失真”是对名家的批评,而“正名实”与“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则是对名家的赞许和改造。下文将具体分析《论六家要指》对名家的这两部分评述。
经“使人俭而善失真”以及相应之传“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是《论六家要指》对名家最为核心的两句批评和评论,且这两句之间的“故曰”二字暗示着两句在语义上的对应关系。“专决于名”与“俭”之间虽然存在着语义理解上的前后对应关系,但如何能建立起两者之间的必然性逻辑联系呢?
何谓“专决于名”?徐复观《先秦名学与名家》曰:“名家之所以为名家,乃在于他们是‘专决于名’。他们之所谓实,乃是专从名的本身去认定实。例如公孙龙的‘离坚白’,乃是从‘坚’是一名,‘白’又是一名,因为推论坚为一实,白又另为一实,坚与白,虽由与石或其他物结合而为人所拊所见,但未与石或其他物相结合时,坚与白仍潜伏(藏)于客观世界(天下)之中而为各自独立之存在。在其他各家,对名与实之是否相符,乃是以观察等方法,先把握住实,再由内外经验性的效果以证明实,看名是否与此实相符,这是‘专决于实’而不是‘专决于名’。换言之,诸家是由事实来决定名,而公孙龙这一派则倒转过来成为由名来决定事实,他们是以语言的分析来代替经验事实,而成为玩弄语言魔术的诡辩派。司马谈乃至许多人对他们的批评,皆由此而来,所以把他们特称之为‘名家’,以与其他主张‘正名’各家的思想作一区别,并无不当。”[34]徐先生看到了名家是“玩弄语言魔术的诡辩派”,但是仍然跳不出“正名”的窠臼,说“公孙龙这一派则倒转过来成为由名来决定事实”。“专”为何意?由多元变为一元,即是“专”。王凤阳指出,“专”的“引申义有专一、集中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上》‘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又《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术),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专’都是专一而不杂、集中而不分散的意思。用在独占意义上,‘专’也同样表示独自占有,不分散给别人的意思。《左传·庄公十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和独自占有相对的是以之分人;《汉官仪·上》‘每朝会,与司隶校尉、御史大夫、中丞,皆专席坐’,‘专席’是独占坐席,不与人共坐;白居易《长恨歌》‘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专夜’是独占过夜之权,不分给其他嫔妃”[35]。循此以进,可知“专决于名”之解。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认为:“本来名、法两家所持的‘控名责实’之说,在古代逻辑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到了辩察者们的手里,就变成专用名字作行为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实’可责了。”[36]许抗生《先秦名家研究》:“‘专决于名’是指什么呢?‘名’就是指概念名称,‘专决于名’就是专门从抽象概念与名称的分析中来下结论。”[22]3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谓专从名词上来判断一切,以致违反人情。”[26]344儒家的“正名”是名实合一的。例如孟子所说的“诛一夫”:弑君不可为而诛纣则可为,就是因为儒家把纣的“名”正为“一夫”,而这是与经验事实相对应的,因为当时的纣的确是不得民心、孤立无援的“一夫”。而名家类似“白马非马”的命题则不是名实对应的,它取消了“实”,从而变为“名”的一元统治,这就是“专”。
如何理解“俭”?亦即经之“俭”与传之“专决于名”如何对应?或者说,如何在“专决于名”的意义上来理解“俭”?高华平《先秦名家及楚国名辩思潮考》说:“当然,这个‘俭’并非道家的老子和墨家的墨翟之所谓‘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又说:‘治人事天莫若啬。’(第五十九章)《论六家要指》说:‘墨者俭而难遵。’王弼注《老子》的‘俭’说,俭,乃指‘节俭爱费’,即不奢侈、养生不浪费,保啬而爱精,而墨子的‘俭’则是‘节用’、‘节葬’。可见道、墨的‘俭’都有‘节俭’义,但名家的‘使人俭而失真’,则是说名家过于纠缠于‘名’,只精于事物的概念而忽视了事物之‘实’。因为只‘苛察’事物的‘名’,于事物之‘实’就会有所忽视。这既是‘俭’,也是‘俭’可能‘失其情’、‘失其真’之处。”[37]“俭”可以理解为对“物”的最少使用,“专决于名”就是对“实”的最少使用,且这种“最少使用”已经到了“无实”的程度,“无实”而只剩下“名”。这也可以在“俭”与“专决于名”之间建立逻辑关系。
如何理解“真”?“专决于名”导致割裂名实,纯“名”的考察是无法进入实践的。“真”即名实相符。“专决于名”,割裂名实,自然失真。我们不妨看看与司马谈约略同时的董仲舒是怎样理解“真”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38]562所引《春秋》见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17]139先听到有陨物于地之声,到坠落处去看,发现落下的是石头,再一数是五颗,所以记述的次序是“陨石五”。先看到有六个东西在天上飞,等飞近了仔细看,才发现是鹢鸟,知道是鹢鸟之后,才觉察到鹢鸟的头部朝向与其飞行方向是反的,这才能断定鹢鸟在“退飞”,所以记述的次序是“六鹢退飞”。由此可知,董仲舒所理解的“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名实相符,而且包含着“名”与“实”如何得以相符的认知过程。董仲舒更进一步论及“名”与“真”的关系,《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返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也,犹绳之审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38]562
拒绝经验事实介入,单凭“名”就解决问题,也就是“专决于名”。“俭”是对“物”的最少使用,对“物”的最少使用即无“物”。“专决于名”是对“实”的最少使用,对“实”的最少使用即无“实”。正是在此意义上,司马谈认为名家丧失了名实相符的可能性,亦即“失真”。至于传之“失人情”,当先明“人情”究何所指。《管子·心术》上:“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39]《文子·上仁》:“礼因人情而制。”[40]《史记》卷二十三《礼书》:“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5]1365这都表明“人情”是礼的根基。《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郑玄注:“称情而立文,称人之情轻重而制其礼也。”《释文》:“称,尺证反。”[41]义为合适、相应。“称情立文”即“缘情制礼”,也就是说,礼仪节度必须与人情轻重相适应。《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7]1737谓名家出于礼官,实即认为名家的“名”“实”相符系由礼官的“名位”与“礼数”的对应转变而来。因此当名家“专决于名”,导致有“名”无“实”,相当于礼官有“名位”而无“礼数”,于是“人情”亦无从表达了。
我们可以举一个名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的例子。《庄子·天下篇》记辩者论题有:“孤驹未尝有母。”《释文》:“李云:驹生有母,言孤则无母,孤称立则母名去也。母尝为驹之母,故孤驹未尝有母也。”[42]“孤”之名的意义就是“无母”。因此,既称“孤驹”,就是指“无母之驹”。正是在这一步,“名”与“实”分道扬镳:如果我们顾及实际经验,将“孤驹”放入生活经验中,就必须承认,“孤驹”也曾有母,这样“孤”就不是绝对的,“名”受到了经验(“实”)的限制。名家则毅然挣脱经验(“实”)的束缚,将“名”绝对化,“驹”既称“孤”,就是绝对地无母,就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母——这就是所谓“专决于名”,并且显然违背了日常经验,导致“失人情”。
四、俭与真
《论六家要指》名家部分最值得探究的是“使人俭而善失真”一语。
一般将此句理解为因果关系,但正如此前所言,王叔岷先生标点为“使人俭,而善失真”[13]3466理解为转折关系,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
转折,即前件判断的逻辑要素为后件判断所取消。在此,即后件判断“失真”取消了前件判断“俭”的要素:“真”。于是这一逻辑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便是,“真”如何作为“俭”的要素。
在一个名实对应的逻辑体系中,有名无实的“俭”是一种极端状况:“名”也是一“物”。比如《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43]52,即把有“名”无“实”之“道”也称为“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弼注:“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43]117此注本于《庄子·内篇·齐物论》:“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44]而当“名”自身也是“物”时,此时的“名实相符”就是“名”与“名”自身的对应,“名”既作为名又作为物,自身与自身百分之百地对应和相符。所以,在名家那里,所谓“从‘俭’推到‘真’”或“‘真’作为‘俭’的一个逻辑要素”就是指,“俭”是“专决于名”,仅仅有“名”,“名”既是名又是物,名与名自身形成一种百分之百的名实对应,而“真”就是指名实对应,故曰“俭”包含“真”。但是,此处之“真”或“名实相符”是名家所建构的或说是司马谈笔下的名家所建构的另一种“真”,这种“真”并不符合“人情”,因为它没有考虑经验事实。这种“真”不是后文司马谈所说的“失真”之“真”,所以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成功地从“俭”推到“真”。这里存在两个“真”:“真”即名实相符,而在名家看来,“真”是指“名作为物”的一种“名”与其自身的名实相符;在司马谈看来,“真”是指“名不作为物”,名实区分的一种名实相符。
我们回到先前的问题,即“从‘俭’怎样推出‘真’”。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名实相符”:从“俭”推出名实相符,而名实相符又是“真”,所以“俭”包含“真”。但是,通过之前对两个“俭”和两个“真”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个关键的“名实相符”却被理解成了两个不同的意义,即名家建构起来的“名作为物”的一种自身与自身的名实相符,以及“名不作为物”的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名实相符。我们要从“俭”推出“真”,就是说要在从“俭”到“真”之中建立起逻辑上的必然性联系。但是,前文所说的“两个‘真’”“两个‘俭’”“两个‘名实相符’”都意味着这里存在着偷换概念的可能性,比如:前文“俭”是司马谈对名家观点的论述,是名家的观点,因此这个“俭”是“‘名’作为‘物’”的“俭”,由这个“俭”推出来的“真”也就是“‘名’作为‘物’”的“‘名’‘实’相符”;而后文“失真”是司马谈对名家的批评,是司马谈的观点,这里的“真”是“‘名’不作为‘物’”的名实相符。所以,前文“‘名’作为‘物’”的“俭”与后文“‘名’不作为‘物’”的“真”只具有语义上的对应关系,而两者实际上却因概念的偷换而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联系。
“俭”若是与“真”构不成必然性逻辑联系,那么“俭而善失真”就构不成转折。所以,既然从“俭”推到“真”已经失败,那么就应该尝试从“真”推到“俭”。这里的“真”是“失真”之“真”,从司马谈的角度来说的一种日常的、名实区分的“名实相符”。而“俭”虽然具有在前文提到的两种理解方式,但无论“名”是否作为“物”,“俭”的含义都可以归结为“对于物的最少使用”。之前从“俭”推“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遇到了日常之“真”和名家之“真”两种“真”导致概念被偷换,而现在从“真”推到“俭”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的“真”就是司马谈所说“失真”的“真”,可以确定是司马谈所认为的日常生活经验之“实真”,而“俭”也可归结为单一的“对物的最少使用”这一定义,因此这里并不存在概念的混淆或偷换,而是可以把“从‘真’推到‘俭’”这个问题直接归结为:“从日常意义的‘名’‘实’(‘实真’)相符如何推出‘对物的最少使用’?”
我们可以把“名”定义为“物的形式规定”,而把“实”定义为“物的存在形式”,因而“物的形式规定”(“名”)与“物的存在形式”(“实”)相符,即是“实真”。那么,这两者的相符合为什么能推出“对物的最少使用”?理由在于,用“物的形式规定”来规定“物的存在形式”,就必然会有“物的形式存在”(形式性存在)。未被规定的“物”也有它自己的存在形式,但这种存在形式未被限定和规定,因而还不能算是形式性存在。反之,具有形式性存在的物因其具有规定性而一定会导致使用此物的精确性,而所谓精确性使用就是对“物”进行不浪费的、必要性的使用,因而也就是对“物”的最少使用。所以,由“真”推到“俭”可以归结为这样一条路径:
“真”→日常的“名”“实”相符→“物的形式规定”与“物的存在形式”相符→“物”的形式性存在→使用“物”的精确性→对“物”的最少使用→“俭”
由此,“俭”与“真”之间就建立起了逻辑上的必然性联系,两者之间具有共通的逻辑要素,而这也是“俭而善失真”这句话之所以能构成转折(前件判断的逻辑要素为后件判断所取消)的前提条件。
但是,如何继续整体性地构造“俭而善失真”的转折性仍然是一个问题。
名家通过把“名”作为“物”,取消了真正物质之“物”的位置,从而无法指导经验。因此,名家所理解的“俭”是不含有日常生活经验之“实真”的,而名家所理解的“真”也是不包含物质之“实物”的。于是,司马谈对名家“俭而善失真”的这句评价之所以构成转折,就是因为司马谈想表达这样一个逻辑:(司马谈所认为的)“俭”应当是包含(真实的)“真”的,而名家的“俭”却不包含(真实的)“真”。(真实的)“真”本来是包含“实物”的,而名家的“真”却不包含“实物”。这都是前件判断的逻辑要素(“实真”,“实物”)为后件判断(不含“实真”,不含“实物”)所取消,因而构成转折。总之,司马谈是想对名家说这样一句话:
“真”应含“物”,汝“真”无“物”;“俭”本含“真”,汝“俭”失“真”。
五、司马谈对名家的改造
司马谈在对名家进行批评之后,是怎样对名家进行纠正和改造的呢?
在司马谈改造下的所谓名家学说已经不是真正的名家学说了,而是司马谈对名家思维模式的工具性应用。司马谈赞同名家的“控名责实”或“正名实”,是指在“名”“实”合一的情况下(类似“诛一夫”的情况),名家在方法论意义上是有贡献的。但实际上这是司马谈对名家的改造,是在“如果名家为我所用”这种语境下的赞许。名家自己并没有把方法运用好,导致“名”“实”割裂。因此在司马谈看来,名家学说自身不可能成为一个内在自洽的独立王国,而只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种工具而已。
司马谈具体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实行改造的?总的来说,他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引入来改造名家学说的。
例如,名家“白马非马”的辩题是一种悖经验的诡辩,这与非经验的悖论有所不同:“非经验”是完全脱离经验的,悖论的矛盾在于逻辑上的矛盾,但不一定悖经验;而名家的“悖经验”则在逻辑上不一定有矛盾,但一定与经验相矛盾,且同时又是一定不脱离经验的,因为一旦完全脱离经验则不可能与经验产生矛盾。名家“专决于名”,排除物质之“物”,所以,其实名家是要竭力排除日常经验的,这也可以视为中国早期的唯理论倾向。但是问题在于,名家构造的“白马非马”学说就算再怎么悖经验,它还始终是基于经验、不脱离经验的,我们是基于经验中的“白马是马”才会认识到“白马非马”的悖经验性。再以“孤驹未尝有母”来说,如果我们将其改造为合经验的辩题,可以是“孤驹曾经有母”或“孤驹之母已死”。这两个辩题因为太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了,以至于让人感受不到逻辑的存在。反之,“孤驹未尝有母”正因其悖经验性,令人不由自主地进行批判质疑,由此引发的辩论,恰恰可以引出辩题之中潜藏的逻辑推理。正因为此,名家乐此不疲地构造了一系列悖经验辩题来突显逻辑推理的重要性。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名家陶醉于悖经验辩题而无以自拔之时,也就无力构造超经验的纯逻辑命题,而这也正是名家最终没有发展出完整的唯理论或逻辑学的原因。
名家竭力寻找却最终没有能够找到摆脱经验的有效方法,这也导致了司马谈对名家的批评:想要处理经验却悖离了经验。因此,名家自身在经验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摇摆性:一方面,有非经验倾向(但未达成非经验),有唯理论倾向;另一方面,有政治性,想要指导经验实践。名家兼具这两方面,因此名家的理论是兼有经验性与非经验性的,即:
非经验性概念+关联经验事实的推理=悖经验性结论
如此一来,则名家不免在经验性和非经验性两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从逻辑的方面来说,由于“白马非马”这类悖经验辩题仍然牵涉经验,所以无法用逻辑上的、非经验的“真值”来判定“白马非马”是否为“真”;从经验上来说,由于名家采取的是“‘名’作为‘物’”的特殊的一种“名”“实”相符,从而造成“名”与“实”之间的割裂,所以我们也就无法从在经验上是否“名”“实”相符来判断“白马非马”是否为“真”。所以,司马谈对名家“失真”的批评除了可以理解成“不真”或“‘名’‘实’割裂”之外,还可以理解为“无真”,即根本没有判断真假的标准,根本无法辨别真与不真。这是对名家的一种非常深刻的内部批评。
总之,名家在经验问题上的摇摆性使得名家既在经验方面失“实”、失“真”,又在逻辑方面未离经验、不够纯粹,以致无“真”。这可以用一句话来归结:名家既无“真实”,又无“真值”。
司马谈从这种“非真实”入手,加入经验事实,把经验还原入概念之内,把名家改造成这样一个模式:
经验性概念+经验性推理=正经验性结论
也就是说,司马谈的改造方案中“控名责实”的“名”已然是经验性概念了。这一方面是把名家学说改造成了可以指导实践的学说,但另一方面却彻底毁灭了名家学说的灵魂,仅仅留下了工具性的框架和躯壳。
后人若要重新建构名家学说,重新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不妨从“非真值”这一角度入手,试着去剔除那些古人所摆脱不了的经验性牵绊,建构起中国古代思想的纯逻辑运演。
注释
①罗焌《诸子学述》曰:“上六节,盖古人之言而太史公述之。以下六节则太史公之说明语也。”罗焌:《诸子学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即已洞悉其经传之别与作者非一,唯株守作者当为司马谈,故只能以上六节为古人之言。罗书初版为商务印书馆,1935年。张大可《司马迁评传》曰:“《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另可参阅:赵吉惠:《〈史记·论六家要指〉的文本解读与研究》,《人文杂志》1997年第6期;[日]楠山春树:《〈六家要指〉考》,[日]增野弘幸等:《日本学者论中国古典文学——村山吉广教授古稀纪念集》,李寅生译,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61页;周桂钿《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兼论思想方法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2期。但诸家皆为推测之辞。李若晖发现,杨雄《法言·寡见》云:“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汪荣宝:《法言义疏》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2页。对应于《论六家要指》儒家之传“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可证汉人确知《要指》之传为司马迁所作。李若晖:《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08—111页。②张守节:《正义》,司马迁:《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65页。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作《集解》,误。王先谦:《汉书补注》第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