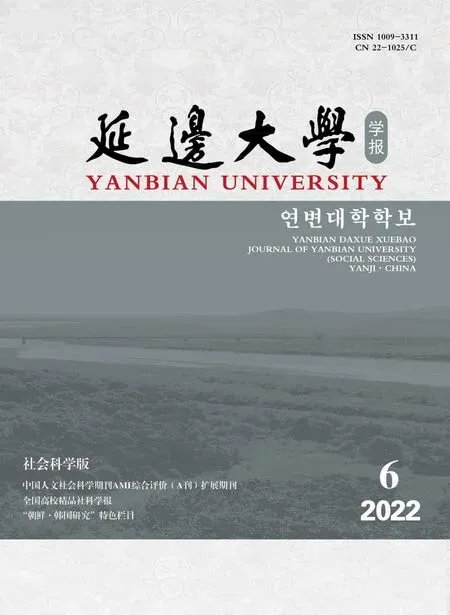跨文化交际视阈下“口罩”的多重隐喻
钱 娟
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遭遇危机,克服危机,不断前进的过程。危机及其伴随的破坏、灾难和浩劫,一直是人类力求解决的问题,而关于危机的表现类型、后果、实质、原因及防范措施,各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探索。
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意猖獗时,作为技术物品的“口罩”,已然不局限于医用范畴,它更多地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必须品。新冠肺炎疫情下,“口罩”作为技术物品在中西方人们的“戴”与“不戴”之间,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差异。它“反映了个人、团体或国家之间文化接触和关系结构生成的过程”。(1)王宏涛:《口罩隐喻:人类学视野下的礼物互惠与身体边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98页。疫情期间,“口罩”作为一个重要的物品,对其认知更多地体现出中西方医学、价值观和文化等方面的多重隐喻表达,对此进行一定的诠释,将有助于人们突破异质文明之间的藩篱,加强彼此的交流与理解。
一、隐喻的基本含义
隐喻(metaphor)作为一种语言学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以隐喻为基础。”(2)[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隐喻也是一种比喻,常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比如“疫情防控是一场持久战”,所以西方修辞学最早把基于相似性的比喻叫作隐喻,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灵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意味着对相似的一种领悟”。(3)Aristotle,Poetics,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Heath,London:Penguin,1996,p.10.但隐喻不仅仅是对某些词汇、事物的领悟,今天“对隐喻的认识,已摆脱了修辞学的传统理论,把隐喻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4)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自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理查兹的隐喻理论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譬如里德提出隐喻起源于对世界认知信息的共鸣。“基本隐喻最显著的特点与其起源有关:它们源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关联。这说明了该理论相对先前观点的一个变化,即隐喻的起源不是某种感知的相似性,而是共现的概念。”(5)孙毅、李学:《基本隐喻理论发端:肇始与演进》,《外文研究》2021年第4期,第1-9页。隐喻不仅仅是对外在世界的身体感知,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对事物的思维过程、心理活动都具有隐喻性。但“当语言由口头语言发展到书面语言时,人类进入了有史文明的阶段。由于不同语言社团使用不同语言,对世界的认知不尽相同”。(6)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可见,语言、文字和符号对人的心理暗示具有极大的作用,词语的联想往往在潜意识影响与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口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社会生活中传染病疫情代言者的工具性表达。分析“口罩”的象征意义,不仅因为它可以强调个人身体区隔边界的重要性,以及逼近与打破这边界的危险性,还因为它是社会、文化与自我相互作用的前线。”(7)王宏涛:《口罩隐喻:人类学视野下的礼物互惠与身体边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99页。正因如此,对“口罩”在医学、价值观以及文化等层面多重隐喻式的认知与表达,已然成为疫情下,人类对世界的探索与发现,人际间开展交往的一条重要途径。
二、“口罩”的医学隐喻
就其起源而论,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意识到了口鼻飞沫的危害,所以常常侧着头以避免口鼻飞沫的污染,以示尊重。《礼记·曲礼上》记载:“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8)戴圣编、贾太宏译注:《礼记》,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孟子·离娄》也有“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的记载。(9)孟子:《孟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而最初的“口罩概念”不论是侧头、掩口还是掩鼻,始终停留在保持个人卫生的原始状态,既不卫生,也不方便。直到13世纪初,中国最早医学意义上的“口罩”在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初现雏形——“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10)金芷君、张建中编著:《中医文化掬萃》,上海:上海医药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蒙住口鼻的绢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次具体物化性的“口罩”,它的出现表明中国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具备了个人防护的意识。从古时起,中国人民在同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逐步积累了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和经验,产生了预防疾病的思想。古人也早已认识到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发生跟外界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保护和改善环境因素、保障人体健康和预防疾病的措施,诸如凿井而饮、杼井易水、洒扫除虫等。在几千年的中药治疗理念传承的亚洲国家认为,戴“口罩”是防微杜渐,为了防止被患者感染,所以健康者和患者均应佩戴“口罩”。
纵观早期西方历史,不难发现传染性疾病的防控手段主要采取的是“隔离”而非佩戴“口罩”。自2019年至今,一段时间内,“隔离”无疑已成为热门词汇。而所谓的以隔离检疫(quarantine)方式来阻遏传染病蔓延,被西方文明用于防止疾病传播由来已久。
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当时威尼斯执行了一项规定:船只必须锚定40天后,船员和乘客才能上岸。在西方,一个著名的隔离范例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德比郡(Derbyshire)的伊姆村。1666年,该村遭到鼠疫肆虐,不断有村民死亡。在新上任的教区长威廉·蒙佩森(William Momperson)带领下,村民们自愿隔离、封锁村子,遏制了病毒向外扩散。随着时间推移,病例数下降,疫情消失,从而免除了附近村庄遭受同样的厄运。这一次隔离可以说是非常奏效的,并且这个防控方法仍然是西方各国用来限制疫情恶化的关键手段。
然而,作为口鼻覆盖物的“口罩”这一防控疾病技术物品,进入西方的现代医学领域的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之交,但认可度与接受度一直较低。西方媒体报道过的一些照片,再现了西方现代早期的医学专业人员,穿着黑色斗篷,戴着黑色帽子,戴着喙状“口罩”治疗患有腺鼠疫的患者的情景,并由此产生了“喙医生”一词。(11)Byrne J.,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Westport:Greenwood Press,2006,p.25.但这样的恐怖的形象一度被认为是中世纪致命流行病的象征,并且当时医生们的“口罩”仅仅是被视为保护自己免受“瘟疫”的“面罩”。1897年,卡尔·弗里德里希·弗吕格和约翰·冯·米库利茨合作出版了医学著作,记录了医生戴着“口罩”进行手术。在书中,米库利茨将“口罩”描述成了一种由纱布制成的单层“面罩”。(12)Mikulicz J.,Das operieren in sterilisierten Zwirnhandschuhen und mit Mundbinde,Stuttgart:Centralbl f Chir Press,1897,p.7.1914年,外科医生弗里茨在一本全科医生外科手册中写道:“……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口罩”)——顺便说一句,很烦人——完全没有必要使用”。(13)Christiane Matuschek,Friedrich Moll,Heiner Fangerau,et al.,“The history and value of face masks”,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09199/.之后,在外科手术和综合医院中,纱布制成的双层口腔保护装置应用并不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德国和美国的手术室中,“口罩”被弃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不同厚度的“口罩”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研究。尽管如此,“口罩”仍然不被普遍接受,医生在手术的所有阶段都拒绝戴“口罩”和橡胶手套,因为它们“令人恼火”。(14)Adams L.W.,Aschenbrenner C.A.,Houle T.T.,Roy R.C.,Uncovering the History of Operating Room Attire through Photographs,Philadelphia:Anesthesiology,2016,p.9.西方文明史历经中世纪的黑死病、西班牙的大流感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等严重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却没有形成戴“口罩”防疫的传统,究其缘由,与西方医学对“口罩”的认知及长期隔离防疫经验不无关联。
在西方观念看来,“口罩”是医生的标配,是特定职业的象征;在其认知中,患者佩戴“口罩”不能阻断病毒传播,而应遵循历史的经验,采取居家隔离防疫。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说道,“任何一种被作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惧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15)[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第7页。因此,从医学专家到政府部门以及到普通民众,都认为只有生病的人员才需要戴“口罩”,而生病的人应该采取的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与自我隔离,而健康者佩戴“口罩”无非是多此一举。比如,英国首席医疗官克里斯·威蒂就表示,戴“口罩”不会停止感染,美国外科医生杰罗姆·亚当斯也通过推特网呼吁人们停止购买“口罩”。政府也一直对外宣传“口罩”没用,西方老百姓出门无需戴“口罩”,如果有人戴了“口罩”,就会受批评与嘲讽,“戴‘口罩’等于生病”这一医学认知在西方社会是普遍存在的。
如果从跨文化角度来辨明中西方医学对于“口罩”的认知,其差异的根源将更加清晰。荷兰社会心理学家盖尔特·霍夫斯泰德(Hofstede)在其著作《文化的后果》中提到不确定性规避原则(UAI),即不同文化对不可预测性的容忍程度的差异。霍夫斯泰德(Hofstede)曾提到,“这里的根本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应对未来永远不可能被知晓的事实:我们应该设法控制它,还是让它发生?”(16)Hofstede,G.,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2nd ed.),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pp.79-123.具有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背景的社会试图将未知和异常情况的发生降至最低,并通过规划和实施法律、法规逐步进行仔细的改变。相比之下,低不确定性避免社会更倾向于接受非结构化环境或多变环境,并感到舒适,故而较少制定规则。避免不确定性最需要处理的领域是技术、法律和宗教,技术通过新的发展帮助解决自然界的不确定性,法律用既定的规则来保护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宗教通过教化来安慰人们无法得到保护的不确定性。对于高度避免不确定性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则倾向于使用严格的规则——佩戴“口罩”,这将更有助于他们确定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方式。而对于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的人们更关心让未来在没有控制或计划的情况下到来,他们的压力小和焦虑率低,“在医学领域,人们对不确定性事物会深感不安,并用‘面具’一词来比喻医学中过度简化而造成的不清楚的现象,以及医生强加决策的欲望,所以不会主动或自愿佩戴口罩”。(17)Lindsey Grubbs,Gail Geller,“Masks in Medicine:Metaphors and Morality”,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Vol.19,No.2(2021),pp.103-107.
简而言之,对于亚洲人而言,“口罩”就是“防护”,可以有效防御外界病毒侵害,人人皆可佩戴;而西方人则认为佩戴“口罩”等同于患了“疾病”,居家隔离才是正确之举。种种差异性主要存在于东西方两种根深蒂固的不同医学理念,以及围绕“口罩”的象征含义之间的跨文化误解中。
三、“口罩”的价值观隐喻
价值体系是理解文化如何表达自身的基础。价值观是人们深刻感受到的,往往是指导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的原则。价值观是后天习得的,大多是潜意识的,深藏在周围社会的语言和传统中。共同的价值观形成习俗,指导行为,塑造态度。因此,分析价值观是理解文化之间基本差异的有效方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口罩”突显了新的紧迫性,人们不仅仅会思考“口罩”在医学上的隐喻作用,将会更加关注其在中西方价值观层面的重要意义。
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的。价值观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作为理想的最终状态,还是作为一个人的特征。另一方面,道德规范是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在道德基础上行为的指导方针。简单地说,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是重要的信念,而道德规范是支持和表明这些价值观的行为和态度。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演变与发展来看,众多先进思想都在春秋战国时期激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最终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我们不能给病毒找理由》一文中提出,东亚抗疫卓有成效得益于东亚传统“儒家思想”中“依顺”与“服从”。(18)[韩]韩炳哲:《我们不能给病毒找到理由》,《世界报》2020年3月23日。
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我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即“爱”人,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基本的道德规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基本思想,而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强调君臣、父子以及夫妻之间都要遵守一定的人伦关系。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因此,中国人一直秉持五常之道,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疫情当下,中国人能够听从国家和政府的各项安排,自觉自愿地佩戴“口罩”,各尽其能、各安其位遵守社会秩序与规则,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几千年的教化与规训作用功不可没,在这一层面上,佩戴“口罩”是“服从”、是“团结”,更是“集体主义”的充分体现。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一直重视礼仪教育与规范。“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礼仪是有关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礼仪教育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礼仪教育,引导共鸣自觉遵守当代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不断提升公民素质。在疫情未现之时,“口罩”常被作为中国人在冬日面部保暖,空气污染严重时的防护,明星在公共场所的遮掩等。疫情期间,为加强防范意识,杜绝将病症传染给他人,同时也避免被传染,全体公民需具有“防微杜渐,而禁于未然”的防患姿态,戴“口罩”成为了一种疫情期间文明社会一项基本而又重要的“礼仪”,“口罩”被赋予“礼貌”“礼节”以及“公共道德”等含义。正如英国医学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林特瑞斯所说“将戴“口罩”放入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你就会明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意义远大于简单的个人感染防护”。(19)刘玲玲: 《疫情之下,要不要戴口罩?看看东西方纷争背后的故事》, https://view.inews.qq.com/k/20200327A0SJRS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反观西方,“《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美利坚的新教徒是通过《圣经》团结起来的”。(2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齐心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05页。《圣经》以使人的灵魂获得救赎为目的,其影响渗透于文学、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净化心灵、劝善惩恶、凝聚人心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对美国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宿命论的人生观以及消费主义的价值观等局限性。在面对自然环境的考验时,西方人首先想到的是“自我拯救”,如《圣经》中关于诺亚方舟的描述: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时,诺亚选择带着家人,以及为未来生活所必须的一些生物躲进方舟以逃避洪水。西方一直遵循着“适者生存”的丛林生存法则,同理,疫情下,大多数西方人依旧认为戴“口罩”无用,以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态度自持,认为必然安然度过并且以“逃避”的态度拒绝佩戴“口罩”,“口罩”无形中被贴上“道德”标签,“口罩将道德伦理问题提上了台面,为思考道德方面的考虑提供了一个更微妙的元概念,比如真实和信任的沟通,医疗环境内外潜在的不平等”。(21)Lindsey Grubbs1,Gail Geller,“Masks in Medicine:Metaphors and Morality”,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Vol.11,No.5(2021),pp.103-107.作为一种隐喻,医学上的“口罩”暗示了一种二元状态,即造成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空间的隔离与交流的障碍,抑或是医学中不确定性的容忍与治疗能力的期望。对于社会道德中的“信任”与“诚实”皆采用“口罩”加以描绘,这赋予“口罩”隐喻一种更为突出的特征。1975年,戈罗维茨和麦金太尔鼓励医生们承认医学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从而摘下“绝对正确的面具”。他们把这种“面具”归因于医生的信念,而不是傲慢,他们认为“戴口罩”这种“确定的姿势”可以保护病人免受焦虑。同时也认为,在现实中,由于对混乱的现实的误解,“口罩”让患者对医疗护理产生了不合理的期望,最终加剧了医患的冲突。摘掉“口罩”这个面具,需要医生和病人接受新风险而采取新的沟通方式,它是诚实的,却又会令人不安。(22)Gorovitz,Samuel,Alasdair MacIntyre,“Toward a Theory of Medical Fallibility”,Hastings Center Report,Vol.5,No.6(1975),pp.13-23.可见,“口罩”的出现加剧了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的“障碍”、产生了信任的“危机”。
由“口罩”引发的“信任危机”不仅仅存在于医学领域,更存在于经济或政治范畴。《纽约时报》在2020年1月的一篇报道指出,阴谋论人士相信,盖茨之所以早就预先知道会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是因为他本身也许参与酝酿了这一场危机。之后的社交媒体和电视节目反复中指出,将比尔·盖茨与新冠病毒联系在一起是阴谋论。而且这些阴谋论在传播过程中,又不断被添油加醋,也就有了“口罩”里有监视芯片、疫苗里有病毒或窃取DNA等说法。戴与不戴“口罩”,对于更多的西方人士来说,已然成为了“虚假”与“信任危机”的代名词。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于国教的对抗,以及英国光荣革命中的辉格党人声称人们拥有选择君王的权力,可以视为宣扬人民主权的先驱。不过,一般到了启蒙时代这些运动才开始被认定为真的“自由主义”。“整体看,西方是理性主义的象征。然而在美国,对它的崇奉几近狂热,甚至都未真正理解它的本意:自由主义。在美国,从未出现一个“自由主义运动”或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政党”:只有美国的生活方式。”(23)[美]路易斯· 哈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赵旭东、齐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因此,西方国家长期大力宣传与标榜的民主、自由、隐私等,已形成思想意识形态的民众则会对于一些集体主义和公共安全的需要而限制个人行为的事情极端排斥。例如,欧美人士就非常抵制街道上安装摄像头,认为其侵犯了个人的隐私,以致于导致其产量在欧美的市场很小。因此,政府无法通过政策监管或道德调节使民众佩戴“口罩”,只能靠个人的自觉自愿。“口罩”已然成为了“约束”或“限制”的代名词,疫情严重期间,西方人宁愿“自由”而不惜抛弃“生命”,开着狂欢派对,观看各种比赛。
美国为更多渴望平等的白人移民提供了广阔的愿景,这是在出生即拥有权力的贵族制度的欧洲无法想象的,也无法实行的。在这片“新大陆”,几乎任何一个移民只要想握有土地,就唾手可得。正是这种对平等的自然意念,使其坚定不移地“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实上,美国黑人一直在为“平等”呐喊、斗争。从19世纪30年代初,要求彻底废除黑人奴隶制的群众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争取非裔美国人民权非暴力的抗议行动,美国人一直在寻找“平等”之路。
今天,无处不在的“口罩”又一次唤醒了一系列与价值观相关的挑战。在美国,戴“口罩”也可能加剧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加布里埃尔·菲利克斯表达了他的恐惧,作为一名黑人医生,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可能会威胁到生命。他知道很多人对黑人持怀疑态度,这可能导致他们与执法人员发生致命的冲突。(24)Gorovitz,Samuel,Alasdair MacIntyre,“Toward a Theory of Medical Fallibility”,Hastings Center Report,Vol.5,No.6(1975),pp.13-23.因此,尽管“口罩”被视为一种保护公共健康的机制,但由于美国种族主义的现实,“口罩”的佩戴可能会适得其反地增加黑人受到伤害的风险,“口罩”无疑成为了“危险”的标志,变成了“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代名词。
“囚禁动物用牢笼,而囚禁人类用什么?”这个问题,哲学家帕斯卡尔给人类做了最好的回答:真正囚禁人类的是思想牢笼。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真正让全人类缩手缩脚、瞻前顾后的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差距、是道德的分歧、是伦理的差异。
四、“口罩”的文化隐喻
“口罩”作为文化的一种符号化象征,其渊源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物件——面具。原始居民赋予面具的最初的功能是实用性。因为在狩猎过程中,原始居民发现佩戴兽头、兽皮能够麻痹猎物,或轻易捕获它们,或吓跑凶猛食人的野兽。渐渐的,在“万物皆为神”的意识支配下,不自觉地赋予了面具以法术和神力的外衣。“这些原始形态的器物的面具,大多是原始宗教、原始巫术的产物,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精灵和偶像崇拜的产物。它们蕴含着原始人、先民、古人对图腾、神鬼、精灵的敬畏,对祖先的怀念,以及驱使或祈求它们发挥超自然的威力,克服和战胜自然(如瘟疫、灾难)和人为的(战争)的威胁与灾难,保护人类的生存和人种繁衍。”(25)曲六已:《面具·宗教祭祀·原始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53页。在我国殷商时期,有“蒙熊皮”、戴“黄金四目”的驱逐鬼疫的方相氏和从事巫术活动三星堆的青铜面具,而玛雅早期原始居民则在宫殿外镶满了超过300个雨神恰克的面具用以祈雨,埃及法老佩戴着代表鹰神奈克贝特和蛇神瓦吉特的黄金面具,以及藏族地区流传至今的狩猎祭神面具、狩猎巫术面具、跳神面具、供奉面具和丧葬面具。从英语的语境来看,“面具(mask)”无论是名词含义或者是动词解释,都有着重合之处,常指“遮面”“隐瞒”“伪装”之意。在世界各地,面具被广泛用于喜剧和悲剧表演艺术中,似乎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的表达。在许多戏剧传统中,包括古希腊的戏剧、日本的古典能剧、印度尼西亚的托彭舞以及中国的京剧等,所有的表演者通常都戴着面具,不同类型的面具用于不同类型的角色,这似乎形成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一份更神秘的吸引力。以至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社区内特定群体的宗教和社会生活重要的活动中,面具几乎被普遍使用。但在欧洲宗教改革期间,许多戴面具的狂欢节习俗开始在新教地区消失。如今,随着欧洲国家自觉的“民俗”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了舒适性,人们通常会把面具换成颜料涂于脸上。
“面具”这一独特的符号,在东西方历史的演变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更替,刀光剑影中,有着一群佩戴“面纱”或“面罩”的英雄侠士们。侠客,通常指有丰富的精神追求和超凡的品格的人。从春秋战国起,王纲解纽,列国争霸,旧的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历史上开始出现一个被称为“士”的阶层,各诸侯大夫为了各自的利益纷纷招募以武为生的“武士”,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侠客”或“刺客”,如《史记·游侠列传》中刻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虽然在秦汉时期便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说法,并对民间游侠进行过镇压,但是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墨道法等思想均有深厚渊源的“侠文化”,总是能不断催生出一代代英雄侠士。民间也喜编和流传各种侠客的故事,以排解现实生活的不平之忿。由此可见,无论是古时“谅简精锐数百骑”戴的“幕篱”、还是“女子出门,必拥其面”(2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84页。的“面纱”或“帷帽”等并未受到社会与民众的强烈抵触与摒弃,反而承载了一份千年的“侠客”情怀及“侠义”精神。
陈独秀曾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27)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915年第4期,第4页。因此,中国有侠客,西方多骑士。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基本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但两者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英雄往往是背负“宿命论”,以悲壮的结局收场。从为人类带来幸福而牺牲自我的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到娶母弑父的俄狄浦斯,为国家、人民和家人而壮烈牺牲的赫克托儿,以及中世纪谋求苏格兰独立的华莱士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抗争、挑战命运。英雄主义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文化典型特征,强调个人的力量和利益,具有强烈的自由奔放思想,这深深地扎根于西方人心中。因此,在西方,“男性比女性更不可能戴口罩”,(28)Haischer,M.H.,Beilfuss,R.,Hart,M. R.,Opielinski,L.,Wrucke,D.,Zirgaitis,G.,et al.,“Who is wearing a mask? Gender-, age-, and locationrelated difffferenc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40785.因为他们更可能认为“口罩”是“可耻的,不酷的,软弱的标志”。(29)Capraro,V.,Barcelo,H.,“The effect of messaging and gender on intentions to wear a face covering to slow down COVID-19 transmission”,https://psyarxiv.com/tg7vz/.此外,“男性不愿意戴“口罩”也与新冠肺炎的易感性较低有关,但后一项发现具有讽刺意味,因为男性更容易受到这种疾病的严重后果的影响”。(30)Bwire,G. M.,“Coronavirus:why men are more vulnerable to Covid-19 than women?”,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838138/.由此可见,在西方的“英雄们”的眼中,早已将“口罩”视为“示弱”和“没有男子气概”的表现。
在对“口罩”的描述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隐喻事实除了存在于英雄文化层面外,还来源于不同的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层面。同样是戴“口罩”,亚洲人感觉可以对自己或别人起到安慰作用,但在西方却截然相反——戴“口罩”常常让人产生焦虑与紧张。究其缘由,从深层次讲,是西方社会对蒙面法规的顾忌。众所周知,西方喜欢聚会、喜欢游行,这是古代西方人流行的狂欢文化遗留的传统,比如在希腊的酒神狂欢和狄俄尼索斯崇拜中,人们戴上了面具,暂时停止了对行为的常规控制,抛弃等级或地位尽情狂欢。但高密度人群聚集,易于滋生犯罪行为,这就是《禁蒙面法》由宗教性走向法治性的根源。在西方,《禁蒙面法》的颁布已有百余年历史。制定之初,很多欧洲国家是针对女性戴面纱头巾的习俗,但目前国际上的大部分《禁蒙面法》已悄然将执法焦点转向有意遮掩个人特征而进行的违法行为,这其中就包括在非法游行或暴乱中遮挡面部的行为。佩戴“口罩”和面罩很有可能会被暴力犯罪分子利用,这也会使守法的公民处于危险边缘,甚至遭到人身伤害。
自20世纪中期开始,欧美国家先后订立法案以对抗在集会中通过蒙面隐藏身份、实施暴行者,违反者通常面临监禁与罚款。由此可见,“口罩”已成为一种十分难以忍受的文化禁忌,“口罩”往往和“抢劫者”“恐怖分子”“犯罪”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固化思维十分严重,以至于西方从普通百姓到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对“佩戴口罩”有着强烈的心理敌视,对他们来说,如果能有别的办法控制疫情,他们是绝不会选择戴“口罩”的。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对欧美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程度是东亚文化圈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尽管“口罩”是抗击空气传播病原体的主要工具,但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期间,“口罩”的使用却频频遭遇滑铁卢。美国学者马库斯(2021)基于跨文化心理学理论框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紧密—松散框架以及美国荣誉文化和政治取向作为预测因素,对来自美国45个州的633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调查了戴“口罩”的行为、“口罩”的感知效用、对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口罩”的社会意义。“调查结果表明,在较为宽松的州,戴‘口罩’被认为是一种公民义务;而在美国的荣誉州,戴‘口罩’则被视为破坏公众形象”,(31)Markus Kemmelmeier,“Mask Wearing as Cultural Behavior: An Investigation Across 45 U.S. Stat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Front Psychol,Vol.12,No.5(2021),pp.2-5.甚至戴“口罩”一度被认为是在配合民主党人渲染疫情的严重程度,戴“口罩”是“政治作秀”。除了不愿接受“口罩”作为一种价廉、普遍可得、有效的抗感染工具外,西方政治人士将新冠病毒和戴“口罩”描述为在选举年使用的“骗局”。(32)Egan, L.,“Trump Calls Coronavirus Democrats’ New Hoax”,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calls-coronavirus-democrats-new-hoax-n1145721,2020-3-21.在美国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口罩”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迅速适应了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戴“口罩”的人被怀疑是某一政党的反对者,反之亦然。可以说,“口罩”成为了区分政党的独特“标志”。(33)Malka,A.,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in Adam B.Cohen,Culture Reexamined: Broad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and Evolutionary influences,Washington,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14,pp.129-153.
尽管在各自的文化层面上,“口罩”的隐喻存在些许差异,但在对抗疫情方面却有着一致的认知。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全球引发了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不足,医疗卫生物资保障缺位诱发了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失灵,以及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尚未完善导致了政府失灵等状况下,(34)秦立建、王烊烊、陈波:《全球战疫背景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基于公共经济学视阈》,《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6-27页。“口罩”已然是疫情下的“刚需品”,也成为了亚洲、欧洲乃至全球各国最为紧俏的“战略物资”。当公共卫生问题已从传统的医学问题演变为威胁人民、国家、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问题时,(35)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路径分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225-229页。医疗机构正在优先考虑克服“口罩”供应有限的战略。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人们关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口罩”短缺的问题,并解释造成这些短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世界各地的氢氯化物对“口罩”的需求增加,以及中国(医疗级“口罩”的主要生产国)出口大幅减少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36)Ranney M.L.,Griffeth V.,Jha A.K.,“Critical supply shortages-the need for ventilators an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Vol.382,No.2(2020),pp.41-43.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之时,勇挑大国责任,将“口罩”作为重要的“物资”和“礼物”援助各国、回馈世界,“通过口罩来界定或表达物的文化符号,建构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生产的意义”。(37)王宏涛:《口罩隐喻:人类学视野下的礼物互惠与身体边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99页。中国抗疫纪录片《武汉24小时》在法国、哈萨克斯坦、安哥拉等国家以当地语言播放,展现了中国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建筑工人等在战“疫”中的担当与奉献。国际哲学学会联合会主席鲁卡·马里安·斯卡兰提诺在《危机是文明互鉴的机会而非强化偏见的借口》一文中写到:“普通百姓和国家领导人都会愈发感知到世界的现实关联性。较之宏观经济、文化和环境问题,健康危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引发我们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来一次深刻的改变。简言之,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会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把危机看作是一个进一步了解其他文明的机会,而不是又一个强化现有偏见与成见的借口,那么我们可以从这场危机中学到很多。”(38)[意]鲁卡·马里安·斯卡兰提诺:《危机是文明互鉴的机会而非强化偏见的借口》,http://opinion.people.com.cn/BIG5/n1/2020/0427/c1003-31689909.html。由此可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生动阐释,“口罩”无疑汇聚成后疫情时代摒弃国家的界限、种族的区别、利益的纠葛,共同抗击疫情的一面面闪亮的“旗帜”。
五、结语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制于自然,人类在征服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展示了无穷的力量,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的信念。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暴发愈加突显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共处于一个统一共同体中,只有和谐平衡、共同生长才能实现生态持续性发展。面对全球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人类只有秉持“共命运同呼吸”的思想,坚持以“至真”为社会共识的价值追求,以“至善”为伦理基础的价值尺度,以“至美”为道德核心的价值诉求。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戴口罩”与否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疫情之期,灾难之中,它已然变成了医学、政治和文化的多重问题。此外,“口罩”这一抗疫技术物品所发挥的力量却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反而引发了诸多方面的误解。因此,面对疫情引发的灾难,人类的探索与思考不能仅仅驻足于生态危机的阐释上,也应该充分理解“口罩”在不同领域、不同视野和不同层面中蕴含的多重隐喻,摈弃中西方在医学、价值观与文化中的傲慢和偏见,真正实现跨文化间的交流、交往、交融,真正做到全人类团结一致抗击疫情,共建人类卫生健康与命运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