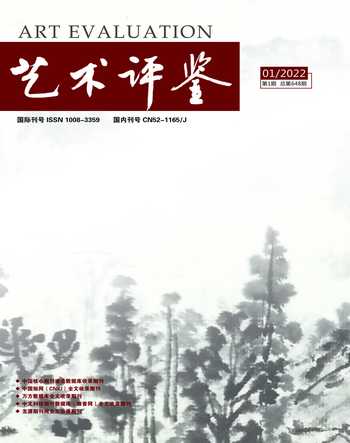拼贴、挪用与重组
侯丹丹
摘要:自处女作伊始,集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贾樟柯便有意持续关注同一社会群体,聚焦有着鲜明区域特色的地域空间,敏锐捕捉当下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叙事母题,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贾氏电影美学。贾樟柯在作品中有意拼贴、挪用和重组其他媒介信息产生巨大“互文”能量的同时,更是拼贴、挪用和重组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时空以及情节主题,这一创作上的自觉在电影《江湖儿女》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至此“贾樟柯导演作品”系列得以建构起了贾樟柯的“电影宇宙”。
关键词:贾樟柯 电影宇宙 建构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2)01-0150-04
2018年公映的电影《江湖儿女》,是贾樟柯导演的作品中获得票房最高的电影,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对于贾樟柯有着双重的意义:从商业角度看,《江湖儿女》使贾樟柯从“地下”攀升到了导演生涯阶段性的“高峰”;从艺术创作角度看,《江湖儿女》是其电影美学实践的阶段性“硕果”。在访谈中贾樟柯提到“要完成自我电影的完善,形成一个自己的电影宇宙”,这一“电影宇宙”说法的提出,为梳理分析贾樟柯的作者身份以及贾氏的作者电影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贾樟柯在作品中有意拼贴、挪用和重组其他媒介信息产生巨大“互文”能量的同时,更是拼贴、挪用和重组了自己作品中的时空、人物以及情节主题,这一创作上的自觉集中体现在了电影《江湖儿女》中,至此“贾樟柯导演作品”系列得以建构起了贾樟柯的“电影宇宙”。
一、拼贴:叙事空间的裁剪嫁接
空间,一直是贾樟柯导演创作最看重的元素之一,他指出“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个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的联系。”除《站台》中多次出现的城墙、《山河故人》中的黄河等地理标示式的空间展示方式以外,贾樟柯电影中更多通过方言和其他媒介声音来标示具体的空间——《小武》中宣传严打公告的高音喇叭循环播放“汾阳县公安局……”,《任逍遥》结尾段落中斌斌被抓的派出所电视上播放着“山西高速公路……”等,这种方式不仅扩展了画面的叙事空间,更巧妙地与故事情节产生了“互文”效应。
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中,贾樟柯的故乡汾阳无疑是最核心的叙事空间。《小武》中正拆除的汾阳县城已成了20世纪90年代北方县城的空间“标本”,《站台》中的崔明亮和尹瑞娟一次次從家乡汾阳出发又一次次回到汾阳家乡,《天注定》中的小玉以及《山河故人》中的涛同样在外“流浪”之后最终回到了故乡。在贾樟柯电影中,“汾阳”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空间标识,或者山西地域空间的代言,它已是贾樟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空间,是贾樟柯“站在故乡看中国看世界”的精神“发源地”,同时与鲁迅笔下的“未庄”、梁鸿反复书写的“梁庄”一样,成为大众通过电影媒介观察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大同和三峡,是贾樟柯电影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叙事空间,这两个在地理特征上有着巨大反差的空间,串联起了贾樟柯“电影宇宙”的叙事空间系统。这里的“宇宙”可被理解为一个超文本(Hyper Text),连接多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副文本(Para Text)。《任逍遥》中的大同以及《三峡好人》中的三峡作为“副文本”被“裁剪”之后,“嫁接”到了《江湖儿女》中,使得这三部电影的空间叙事形成了前后呼应。大同公路旁的公交车停靠站,作为重要创作空间第一次出现在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中,而后在电影《任逍遥》中又多次以不同的角度参与到叙事中,这些经过强化的空间标识再次出现在《江湖儿女》中被“辨认”时,出现在这个空间里的演员赵涛所饰演“巧巧”的角色属性便被激活。同时,观众对熟悉空间的认同,也使得导演通过新的摄影机设备拍摄模拟出的DV质感的影像,与此前留存的DV素材的融合达到水到渠成的效果。在《三峡好人》中出现的游轮,同样是《江湖儿女》中千里寻夫的巧巧出场的重要叙事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三峡好人》中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现场演出声音素材,搭配新近创作的巧巧看演出的画面,形成了《江湖儿女》对《三峡好人》同一空间的精准复刻,达成了时空的“艺术真实”,接续了《三峡好人》中的叙事节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文本可以作为“副文本”的前提,是其已经成为了观众(读者)的观看(阅读)经验储备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看过《任逍遥》和《三峡好人》的观众来说,导演意欲在《江湖儿女》中做的时空“嫁接”自然是失效的。
此外,在《任逍遥》中斌斌父亲看表演的剧场空间同样再次出现在《江湖儿女》中,同属一个空间,《任逍遥》里呈现的是剧场的“舞台”空间正面,《江湖儿女》对准了这个剧场的“后台”背面,构建出了一个麻将馆和剧场二合一的场所,它不仅是大众娱乐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是斌哥“话事”的私人空间,而这个空间作为《江湖儿女》叙事元素的不变量和“参照物”,它“见证”了叙事的推进,是斌哥眼中“江湖”的隐喻,也是巧巧口中“时代”的象征。在电影《江湖儿女》的尾声,麻将屋的里外都与时俱进的架起了摄像头,而这一意象使得这个场所可能成为贾樟柯新“电影宇宙”中的又一个新的空间地标。
二、挪用:人物组合的穿插编织
从《小武》中的“手艺人”小武到《江湖儿女》中的情侣斌斌和巧巧,贾樟柯逐步为自己电影中的角色树立了几个符号化的人物“坐标点”,并围绕这些角色搭建起了多向度的人物“坐标系”,从而以此为核心虚构出了一套具有映照现实意义的人物谱系。
电影《小武》在创作之初,贾樟柯为他的长片处女作起了一串长长的片名《靳小勇的哥们、胡梅梅的傍家、梁长有的儿子:小武》,片名概括了一个男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这显示出贾樟柯从导演生涯初期便以展现个体的“人”为中心,演员王宏伟饰演的小武塑造了戴着宽边框眼镜、穿着肥大西装、走路左摇右晃的县城混混的生动形象。被称为“小武哥”出现在电影《任逍遥》中的,依然是那个整日在大街上无所事事游荡的无业游民,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的他质问卖光碟的斌斌,“《小武》有没有,《站台》有没有”,贾樟柯用这样直接挪用的方式刻意完成了“小武”这个角色在其电影中的第二次登场。
贾樟柯电影中另一个人物“坐标点”是韩三明,贾樟柯的表弟,现实生活中他的身份是一名矿工。在电影《站台》中,韩三明以真实姓名出场,本色出演了一名煤矿工人,在有限的叙事段落中展现出较为完整的朴实形象。《站台》中作为配角的韩三明,在《三峽好人》中以主角身份出场,他独身一人到奉节寻找离家出走多年的妻子无果,此后韩三明在贾樟柯电影中确立了木讷少言、重情义、知礼节的北方汉子形象。韩三明第三次出现在贾樟柯电影《天注定》中时,依然是不变的矿工身份,要和其他工友一道去奉节接他的老婆回家过年,贾樟柯在这里也给此前电影埋下的伏笔做了了结,韩三明显然和奉节的老婆达成了和解,至此韩三明的角色在贾樟柯电影中有了一条清晰完整的人物叙事线。
作为贾樟柯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主角,演员赵涛担纲了除《小武》之外的其他所有贾樟柯电影的女主角,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电影《站台》中的尹瑞娟和《任逍遥》中的巧巧,而其他男性角色与这两个角色的“组合”,构成了贾樟柯电影中多向度的人物“坐标系”。
其一,巧巧和斌哥的“情侣”组合。巧巧和斌哥的形象都是首次出现在电影《任逍遥》中,又同时在《三峡好人》中得以叙事的延续,然后再次在《江湖儿女》中得到全新的扩展,套用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宇宙”系列电影的命名方式——《三峡好人》是《任逍遥》的后传,《江湖儿女》是《任逍遥》的前传和《三峡好人》的后传。这三部电影中,导演以巧巧造型的“不变”来反衬斌哥经历的复杂变化——在《任逍遥》中在大同风生水起、意气风发的斌哥,同样是《三峡好人》里悄然离开妻子到三峡做生意的稍显低落的斌哥,也是《江湖儿女》中起初翻云覆雨到后来无颜面见巧巧再到后来落魄归乡的斌哥。此外,在《天注定》中作为煤矿老板贴心助理出场的也是另一面的斌哥,在《山河故人》中短暂出现的在煤矿看场的同样是在场的斌哥。
其二,尹瑞娟与父亲的“父女”组合。在电影《站台》中,20世纪80年代的尹父是一位“车站几百号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坏人”的警察,他正值壮年,血气方刚,在“谈对象”的问题上与女儿产生争执;展现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小武》中,这位警察父亲依然是一名被小武尊称为“郝老师”的铁面无私的民警;电影《山河故人》中,他再次与赵涛扮演父女,最后在去往战友聚会途中火车站候车室的座椅上安详离世。他与尹瑞娟的“父女”组合,使得这一“父辈”形象在贾樟柯电影中得以完整的呈现。
其三,尹瑞娟与张军的“故人”组合。电影《站台》中作为尹瑞娟好友的张军亲手剪掉自己的长发以明志,他们的关系延续到了《世界》中,《山河故人》中的男主角梁建军和女主角涛的关系依然可以看作是这种“故人”组合的扩展。
三、重组:情节主题的变奏升华
《江湖儿女》的片名高度概括了贾樟柯电影中表述最多最核心的主题,即江湖(世界)和儿女(情长)。《小武》中小武和小勇之间的兄弟瓜葛以及小武同梅梅间若即若离的爱情,直接指向了《江湖儿女》的原英文名字《Money And Love》。《小武》之后的电影,贾樟柯不断用“变奏”的方式来诠释这两个主题,在不同角色设置的叙事语境中尝试对这两个主题做不同层面的注脚。
贾樟柯电影中的“江湖”——侠义、出走、抗争、回归。侠义,是众多武侠类型电影中的叙事核心,贾樟柯曾多次提到自己对武侠电影的迷恋,同时他提到“‘江湖’是我浪漫想象的世界,更是我真实体验的世界。”在《天注定》和《江湖儿女》之前的贾樟柯电影中,没有出现“刀枪拳脚”的硬派武林江湖,也没有直面表现过因“闯荡江湖”带来的“命丧天涯”。贾樟柯的电影更多的是“隐性”地追问狭义精神在当下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展现坚守侠义的普通个体遭遇的尴尬——小武为了兑现曾经对兄弟的承诺不惜顶风作案因而被捕,少年小济和斌斌为了完成“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的浪漫夙愿甚至去抢银行,千里寻妻的韩三明一踏上异乡的船就碰到形形色色“江湖规矩”的侵扰。这些现实世界遭遇的不满,使得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不得已一次次出走,到“花花世界”里寻找更多的可能——《站台》里的崔明亮和张军、《世界》里的小桃、《三峡好人》中的沈红皆是如此。而当寻找无果时,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抗争,或回归,《天注定》里的四位主角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惨烈的抗争,而贾樟柯电影中的更多人物选择了回归——崔明亮和尹瑞娟最终放弃抗争回归到了家庭日常,韩三明领着工友回到了家乡。
贾樟柯在电影《江湖儿女》里对自己前作中出现的“江湖”和“儿女”的主题进行了“集大成者”式的变奏和升华。正面展示的北方小城里的“地下江湖”世界——请关二爷塑像见证“正义”的判决,集体“观摩”港台黑帮题材电影,用大瓷盆同喝“五湖四海”酒,这些看似直接套用的类型电影叙事程式的段落,很快在电影后段得到了消解,电影转向“儿女”叙事主题,有情有义的巧巧外出寻斌哥的过程陷入生存危机,而为了生存又不得不混迹在更复杂更微妙的“江湖”,导演的用意不言而喻,对于奔波在外寻求生活的普通大众而言,生活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儿女》交代了《任逍遥》中动机模糊的斌哥与巧巧的关系,扩充了《三峡好人》里巧巧寻找斌哥的前因后果,同时用巧巧的女性视角观照,使二人的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斌哥对所谓“江湖中人”深深迷恋而之后背叛了“侠义”,巧巧主动出走“寻找”和斌哥被动出走“归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斌哥消极地抗争和巧巧积极的争取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尽管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回归,但仍旧回到了不一样的境地。巧巧/女性从无意识地依附斌哥/男性,到之后的被动独立,再到主动地解救斌哥/男性,巧巧/女性通过一系列的外界刺激以及自身内在的反思觉醒,最终达成完全的自主自立,而在男性世界里曾经处在主导地位的斌哥不得不再次出走,这是《江湖儿女》比贾樟柯前作主题的超越之处。《江湖儿女》填补了《任逍遥》和《三峡好人》叙事留白的同时,又空出了新的叙事缺口:斌哥重返故地前遭遇了怎样的落魄?拄着拐杖再出走的斌哥会不会有东山再起后的又一次荣归?这种无穷尽可以追问下去的延续情节,使得贾樟柯未来作品中“电影宇宙”的建构升级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自处女作伊始,集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贾樟柯便有意持续关注同一社会群体,聚焦有着鲜明区域特色的地域空间,敏锐捕捉当下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叙事母题,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贾氏电影美学。持续地关注和表现同一主题和群体,不代表是对自我固步自封式的重复,对于年近知天命的贾樟柯,《江湖儿女》可看作是其创作的分水岭,《在清朝》的古装题材全新尝试之后,意味着贾樟柯所提到的“电影宇宙”系统在未来或许会有着更大空间的延伸和拓展。
参考文献:
[1]贾樟柯.贾樟柯的电影宇宙[DB/OL].2018-09-03.
[2]贾樟柯.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1996—2008)[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尹一伊.作为文本空间的“电影宇宙”:故事世界与跨媒介叙事[J].艺术评论,2021(06):79-93.
[4]贾樟柯.“江湖”就是人情[DB/OL].2018-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