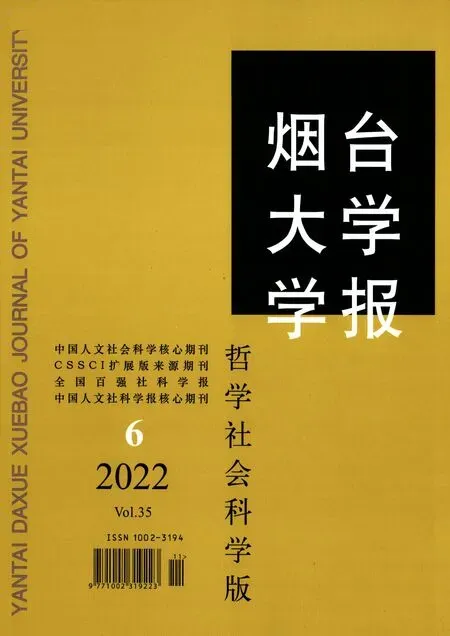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的观念史考察
牛玲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李大钊(1889—1927)生活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关键时期(1895—1925),(1)1895至1925年为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代,五四以后新主义登场,将晚清新文化运动以来多元气象逐渐收归于一。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4期。又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和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其中华民族观生成发展脉络值得深究。学人多重视李大钊1917年所提出的新中华民族主义民族观,视其为李大钊中华民族观之典型,但对中华民族观在李大钊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整个发展脉络,鲜有问津。李大钊思想注重实际,正如其挚友章士钊的评价,“彼凡持一理,必先视此理是否合于当时环境,及己是否能实行以为断”。(2)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7页。身处被瓜分豆剖、内部四分五裂的中国,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以再造新中华国家为目标和指向,受不同时期救国思想影响,呈现出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面相和曲折的发展脉络。笔者借助观念史工具,利用李大钊留下的全部文字,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生成和演进脉络。只有将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置于时代思潮和他本人思想体系的坐标系中,确立一个整体性定位,方能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给出恰当的评价,亦可从中窥见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端倪。
一、革命共和:辛亥前后的“吾华”观念
既有研究多重视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观,对其早期的中华民族观却少有关注。实则一个观念在初始时往往蕴含着决定它发展走向的重要历史基因,应给予足够重视。清末革命党人将国家内忧外患归咎于“满洲人”统治,由此产生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思想。如章太炎就主张“满洲之政敌,非自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3)章太炎:《满洲总督侵吞赈款状》,《民报》1908年第22期。还有人提出,君主是满洲人,很容易专私满洲一族,不驱满洲,就难以实现(各族)人民平等的宪政民主。(4)蛰伸:《论满洲虽立宪而不能》,《民报》1905年第1期。汪精卫也提倡只有先行民族革命,才能达到民主革命的目标。(5)精卫:《民族的国民》,《民报》1905年第1期。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及革命派报刊大量宣传“黄汉民族优越论”和“汉族中华正统论”,指向革命建国。
李大钊青年时期的中华民族观,就是在革命派和立宪派救国思想相互激荡背景下形成的。如他在1919年捐给北大图书馆的书目中就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邹容《革命军》等。(6)《捐赠北大图书馆书刊》,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第193页。李大钊受过较完整的传统教育,堪称儒士典范,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又主动投考清廷为仿行立宪招揽人才而设的法政专门学堂(天津)。李大钊上述入仕求学行为,可以看作是认同清政府统治合法性的重要体现,本无反满思想。他思想上发生反满的转变,是受革命派所宣传的革命以建立共和国家为目标的政治理念影响的结果。他在1923年母校周年庆讲演时亦透露了其倾向革命的原因。当时清廷承诺实行宪政民主,却一再推延行宪时间,引发了各省“请开国会运动”,仅在1910年全国就爆发了4次请愿热潮。李大钊及其法政学校同学参加了第四次,但以失败告终。李大钊回顾道:“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介绍”,同学、教员中亦不乏为革命奔走甚至牺牲者。(7)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1923年12月30日,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6、497页。
受革命派思想影响,李大钊这段时间内常在满汉相对意义上看待中华民族,用传统表达胡汉对立思想的语辞如“吾华”“汉家”“吾少典子孙”“吾四千余载声华明盛之族”等称中华民族,与胡(即满洲)相对,希望驱逐满洲,还政汉家,建立民主共和国。他同样用这种胡汉对立观念表述中华与俄、日等列强之间的关系,表达反帝思想。
1909年李大钊首次表露了反满思想。如他在一首寄友诗中写有“九世仇堪报,十年愿为违。……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8)李大钊:《岁晚寄友》,1909年冬,见《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09页。所寄之友是李大钊永平府中学同学蒋卫平,当时他正在东北跟随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后遇沙俄进犯我国北边,曾参与中俄交涉事。(9)杨琥:《李大钊年谱》上册,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35页。李大钊常与蒋卫平书信往来,得知中俄事,又在《登楼杂感》诗中称:“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10)李大钊:《登楼杂感》,1908年,见《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07页。显然,前诗中“驱漠北”“树汉家旗”说法与革命党人所主张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义相近。后诗以“胡马”喻沙俄,是反帝思想的写照。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国初建,李大钊在一段时间内仍基于胡汉对立思想表述中华民族。如他在一篇政论《隐忧篇》中称“民国之兴”是“吾华之幸”,亦是“吾民之幸”。这里“吾华”指汉族,如其在后文中列举“吾华历代”党争事,有意识地未举元、清两朝之例。(11)李大钊:《隐忧篇》,1912年6月,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页。1912年11月浙江省报载迎明遗臣朱舜水骸骨回国事。(12)《廿二日亥刻杭州专电》,《时报》1912年11月23日,第2版。朱舜水为反清复明曾辗转日本,终生以复国为念。李大钊连续撰文三篇,对朱舜水“义不媚清”飘零异域仍以恢复中原为念,称颂不已。(13)李大钊:《覆景君函》,1913年5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6-57页。同时,从字面意义上看,李大钊似乎视日本和满洲同样为异族。如当时有日本学人宣称朱舜水已归化日本,李大钊反对此说,指出舜水遭“国亡种夷”之大痛,若有归化之心,“满洲与日本奚择”?(14)李大钊:《筑声剑影楼纪丛·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1913年5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51页。意思是如果舜水甘心屈于异族,直接臣服满洲即可,何必舍近求远,跑去日本归顺他族呢?李大钊受革命党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曾寄希望于以反满方式来实现共和。质言之,反满是手段,实现共和对内惠及民生、对外自强御辱才是目的。
然而,民初共和未成和备受列强侵辱的现实,让李大钊认识到民主共和、国家自强实现与否,和由哪一民族主政并无必然关联。当他看到昔日革命党人拔剑击柱、各省都督专权、政治派别之争导致暗杀成风等国内政治乱象时,指出“国势之危,倍于前清”,在清末“吾人犹有共和之希望”,而民初政俗愈下,真使人万念俱灰。(15)李大钊:《原杀》,1913年9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82页。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所受外辱之程度,亦是有增无减。如1913年李大钊在昌黎火车站亲历日本驻屯兵枪杀中国五路警事件,他在《游碣石山杂记》中谴责日本军人“昂首阔步于中华领土”滥杀无辜,呼吁设昌黎为国仇纪念地,提醒“中原健儿”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16)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1913年11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149页。此处出现旧词新义的现象值得注意。虽然李大钊仍使用“中华”“中原”和“倭奴”等旧词,其词义已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即用旧词指中、日两个现代国家之间对立关系,不再局限于王朝国家下胡汉种族观念了。
李大钊青年时期未曾有过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专门论述。他最初的中华民族观受革命派思想影响,是在支持反满革命和追求共和目标中表露出来的,即用胡汉对立的传统观念和词汇表述中华民族,表达反满和反帝思想。民国初年,李大钊在表达上仍用胡汉相对词汇指称中华与满洲和列强,但这些旧词已获得了一定新义,狭隘的种族观念淡化,有时也用以表述国与国之间关系。民国初年,李大钊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视汉、满、蒙、回、藏为一家,认为“蒙藏离异”是事关国基巩固的最大隐忧,(17)李大钊:《隐忧篇》,1912年6月,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1页。称“吾华自共和以后”五族平等。(18)李大钊:《一院制与两院制》,1913年9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93页。同时,“中华”“中原”与“倭族”等旧词亦用以指中、日两国家之间关系。可见,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并非凭空生成,而是时代思潮影响、思考现实政治问题的产物。他对民初政治失望,为寻求挽救之法“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19)杨琥:《李大钊年谱》上册,第92页。李大钊受进步党人汤化龙、孙洪伊等资助赴日留学。在异国语境下结合新的思想资源探求再造共和之法,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亦有了新发展。
二、再造青春中华:“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
目前李大钊新中华民族观相关研究,往往重视它所蕴含的经由融各族人民血缘、文化等因素构成国民全体的观点,(20)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6、127页;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而对他之所以提出的再造共和国家的政治目标、具体语境及其相互矛盾之处,未予足够重视。
李大钊1917年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时所阐述的新中华民族之“新”,对外与当时极具侵略性的大民族主义相对,要中华民族做亚洲民族主人翁,振兴亚洲民族,与欧美民族相竞争;对内“新”与旧相对,不但是融合了汉、满、蒙、回、藏、苗、瑶等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而且是生活在自由民主政体下的现代国民,即“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这较此前满汉相对意义上的“吾华”观念,更具现代性和包容性。新中华民族主义是李大钊再造青春中华的政治蓝图,是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所习得宪政民主思想,是参与反抗“二十一条”运动和反袁复辟活动的产物,其新中华民族观便是基于这一思想背景形成的,并且从属于再造青春中华的政治目标。
(一)新中华民族观形成的政理基础
李大钊留日期间接触的人物和思想繁多,与新中华民族观形成有关者,择要有二:一是国家是由人民创造,是全体人民意志集合的宪政民主精神。李大钊留学期间正值日本拥护宪政运动高涨之际。早稻田大学是倡导英国式立宪政治理想的重镇,该校注重实证研究学风,教员讲义里充满了自由民主主义精神。(21)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第107页。李大钊深为这种思想氛围所感染,也在相关课程如福田和民讲授的国家学原理和近代政治史等,取得了较好成绩。(22)《李大钊大正四年度进级成绩表》显示,李大钊该年度所修课程平均分是66.9,而文中所提两门课成绩分别是77分和70分。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1889—1927)》,第104页。二是集国内全体国民组成的国族观念。李大钊的国族观念与早稻田大学颇有渊源,黄兴涛先生曾洞见此点,但未予深究。(2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126页。张君劢、光昇、吴贯因等有早稻田留学经历的进步党人,曾在天津《庸言》等刊物上鼓吹合五族国民为一国族的主张,如在张君劢编译的《代议制政府》中就有明确的国族概念,国族是指相互间有共同之感情而受制于同一自主政府之下的人们。(24)立斋:《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1906年第18期。据章士钊回忆,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时“谈政臭味,与进步党相近”。李大钊可能在出国前就从进步党刊物中接触到国族概念,只因未遇现实需要,在其脑海中处于隐而未发的状态。以上两点结合,为李大钊形成中华民族(即国族)是由中华民国内全体国民构成的认知,奠定了政治理论基础。
首先,国族、国民全体和国家三者同构关系是新中华民族观形成的政理基础。1915年2月,“二十一条”事引发留日学生抗议活动。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首次用“国族”一词取代“吾华”,作为与“日本”相对的称谓。文中称倭族乘机(指一战)“逼我夏宇”,以奴役非洲黑人之法施于“我中华”,“其夷视我国族于何等”,旨在唤醒国人反抗意识。他也讲明国家与个人生命财产关系犹如皮之于毛,“国社为墟,种族随殄”,“中国乃四万万同胞之中国”,只要国民不甘心亡国,政府也没有权力“命我国民曲顺于敌”。(25)李大钊:《警告全国父老书》,1915年2月初,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11、219页。
其次,国家是由人民所创造并为人民所有的宪政理念,为中华更生再造提供了可能性。袁世凯政府对日妥协,被迫签订“二十一条”,这使当时的中国爱国青年中出现灰心丧志的情绪,甚至不少青年产生放弃国家的念头。李大钊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中劝说青年,国家是由人民创造的,当有人为恶国家时,人民应该“改进立国之精神,造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而非弃之。(26)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1915年8月10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49、250页。此时李大钊心里的国家观念和在国内时已有所不同,更多是抽象意义上即作为全体国民意志集合之国家,而非只是领土、人口等实体意义上的国家。因此,根据立宪政治逻辑,国家是由全体人民让渡出自己生命、财产保护等权力集合而成,人民是主权者,政府代替人民行使主权,若国家不能体现人民意志,则主权者可以收回所让渡的权力,推翻现有政府,再集合民意造一个新国家。这些新理念为李大钊再造青春中华理想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
最后,新中华民族是传统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李大钊本以为,对于类似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等行为,只要“改进立国之精神”,实行宪政民主政体即可解决。但袁氏复辟帝制一事后,他才认识到,要拯救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光有宪政政体还远远不够,还要更新国民之思想。李大钊在《青春》和《民彝与政治》中提出了“再造青春之中华”理想,指出与世界新兴民族和国家相比,“吾之国族,已阅尽长久之历史”,“桎梏其生命”,对于中国来说,民族问题是青春中华再生问题,而非为白首中华续命的问题,而再造青春中华的使命主要靠青年人承担。(27)李大钊:《青春》,1916年4、5月,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12、313页。同时,李大钊指出专制思想是中华衰敝的根源,而代议政治“葆有绝美之精神”,恰好可以增进人民德智。我们读《青春》一文时,往往只把它当作表达青春中华再生的美好愿望。在笔者看来,综合此前政治思考,李大钊在《青春》和《民彝与政治》中,基本勾勒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可行思路,即中华维新依赖于国民自新,需改造专制之国民为立宪之国民,使之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2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271、282、286页。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李大钊为这一理想绘制的政治蓝图,新中华民族观则是以蓝图的实现为目标的思考。
李大钊回国前有关国族、国家、全体国民同构性和再造新中华民族的途径等思想,主要是着眼于国与国间的关系而从民族和国家整体上看问题,尚未遇到现实契机让他思考多种族因素,提出新中华民族概念。
(二)新中华民族观的提出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仍以再造青春中华为政治理想,如他在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创刊号重申了这一理想。(29)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1916年8月5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31-332页。两个政治事件构成他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现实契机:一是重开国会制宪法(30)1913年4月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1914年1月袁世凯复辟时解散。。二是新亚同盟党创始人黄介民回国,力倡联合被日本压迫的东亚各民族,再造新亚细亚民族。
李大钊是在参与孔教入宪提案讨论中,注意到国民全体在种族上的多样性。本次制宪是以《天坛宪法草案》为摹本再行讨论。(31)《祝九月五日》疏证,李继华:《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2页。宪草第三章国民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第三章第三、四和十一条又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在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别,有信仰宗教自由。第十九条又有“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规定。(32)《天坛宪法草案》,1913年10月31日,冯学荣:《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第94、95页。李大钊针对孔教一条指出,中华民国国民由五族人民组成,其“族性不同,宗信各异”,宪法应当是全国国民共同遵守的信条,不能以其中一个“小社会”(指汉族)之法替代之,(33)李大钊:《孔子与宪法》,1917年1月30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4页。况且这里也和宪草本身“信仰宗教自由”条款内容自相矛盾。(34)李大钊:《制定宪法之注意》,1916年10月20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70页。当时,李大钊视孔教为专制思想根源,当然反对它入宪,但他不以反专制为名,而是以揭示宪草文本内在矛盾的方式提出质疑,此点颇耐人寻味。但李大钊正是在这次耐人寻味的提案讨论中,认识到构成中华民族的全体国民是分为多个种族的,再造青春中华须将其考量在内。
再造新亚细亚民族需要中华民族在亚洲乃至世界民族之林中定位自己。李大钊参与宪草讨论之际,新亚同盟党创始人黄介民从日本回国,在北京和李大钊商议,如何联合东亚民族摆脱日本的压迫,再造新亚细亚。(35)黄介民:《三十七年游戏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第122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5、169页。这促使李大钊思考再造青春中华方案时,要考虑整合国内各民族为一个民族以及中华在亚洲乃至世界各民族中的定位问题。1917年2月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提出新中华民族观。
新中华民族观密切关联三方面内容。首先,中华民族应做亚细亚“主人翁”,担起兴亚责任。李大钊反对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36)《新中华民族主义》疏证,李继华:《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第123页。主张以中华民族为主导的大亚细亚主义,就人口、文化、血缘等文明体量而论,中华民族才是亚洲当仁不让的“主人翁”,能够引领亚洲民族走向复兴。其次,完成兴亚使命首先要自新,将多种族打造成一个新中华民族。李大钊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同一之人种,如磁石之相引,不问国境、国籍之如何,而遥相呼应、互为联络之倾向”。它既能使“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也能让“殊异国中之同一民族有联系之情”。要将民族主义用于中国,李大钊取其凝聚之功而防其崩离之势,于是引入“新”字,即新中华民族既是传统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也是历史上多种族的冶融为一。他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加之全体人民都生活在“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以前满、汉、蒙、回、藏乃至苗、瑶等,只是残留的历史名词而已,是时各族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最后,新中华民族将带领亚洲崛起,与欧美民族相比肩。(37)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77、478、479页。
前人多以《新中华民族主义》中的新中华民族观作为李大钊代表性观点,并未注意到,1917年的新中华民族观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如上文所述,李大钊在讨论孔教立宪问题上强调五族“个性不同,宗仰各异”,但几乎在同一时期,却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中宣称五族“早无是界”。李大钊在中华民族内部是否存在民族多样性问题上,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也许是建成宪政民主国家的迫切性使他过于专注推进立宪政体(即再造青春中华),如他称制宪会议为“再造之中华新纪元”,(38)李大钊:《祝九月五日》,1916年9月5日,见《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360页。同样,新中华民族主义则是他再造青春中华的基本蓝图,从而导致在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整合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质言之,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观主要是为再造青春中华宪政国家服务的,不免在其他方面出现歧义和矛盾等情况。这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型期特有的一种“思想的复合性”现象,即在思想混杂多变的时代,思想者往往把相互间有出入或矛盾的思想叠加或嫁接并置于一个结构中,而他本人却视其为一个逻辑一贯的有机体。(39)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73页。李大钊思想中亦不免有这种情况,但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思想先驱,后来他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中对1917年新中华民族主义作了进一步完善。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合汉、满、蒙、回、藏熔铸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实现这一目标“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而后在同一宪政民主国家内“自由以展其特能”实行自治,与异民族相抵抗。(40)李大钊:《雪地冰天两少年》,1918年7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39页。正如迈斯纳发现的那样,再造一个新的中华国家,始终是李大钊整个世界观的真正核心和情感寄托,(41)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85页。但对实现理想道路的探索,可谓历尽艰难曲折。
三、民族解放:“历史文化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
当李大钊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再造新中华国家有了新方案。李大钊围绕中华民族解放或复兴目标,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中华民族观,笔者暂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
(一)马克思主义的发现、研究和传播
1917年接连发生制宪会议流产、张勋复辟等事件。李大钊指望官僚政客开国会、制宪法等再造共和的希望逐渐破灭,亦使其青春中华理想一度陷入迷茫。如他在国庆日望着“飘飘国徽”,感于新中华诞育艰难,又担心它会因先天“病惰种子”有流产的风险,不得不承认凡新生命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前路茫茫,非旦夕之间所能竟此大任”。(42)李大钊:《此日——致〈太平洋〉杂志记者》,1917年10月10日,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54、255页。
1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加入新文化阵营,不久公开倾向俄国革命的想法。(43)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67页。但他并未直接模仿俄国经验,而是探其成功背后的理论渊源,由此发现布尔什维克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其宗旨是打破作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劳工自己的组织,自己做主。(44)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62、368页。
李大钊把1918年以来各国学者批评和介绍马克思的“零碎资料,稍加整理”,将马氏“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撰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6号“马克思主义研究号”专栏。他自谦说,“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硬想谈马克思主义“僭越的很”。(4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9月、11月,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2页。1920年3月,李大钊等创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组织翻译德文、法文、英文和俄文等原著,分小组讨论和授课等形式,有组织地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又与第三国际建立联系,(46)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文教师安德烈找到李大钊。获得研究所需资料和革命所需经验。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除了1924年5月《人种问题》讲演时提及一句“台湾的人民虽现在隶属于日本政府,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47)李大钊:《人种问题》,1924年5月13日,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72页。未再有过中华民族专门论述,以至于许多学人认为1917年新中华民族主义是李大钊中华民族观的典型。仔细梳理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文献,发现较之于新中华民族,他这段时间的中华民族观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散见于民族解放和唯物史观等论述中的中华民族观,是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影响的产物,笔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
五四以前,李大钊提倡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继而世界各民族应在平等基础上联合起来。1919年,孙中山提出以汉族之血统同化其他民族,造成一个民族的“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该主张与李大钊上述“以汉族文化开发其他各民族”观点相近。然而,李大钊却不再赞同孙中山的这一观点。他指出,应该以“联治主义”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即“今后中国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哪)一族的隶属”,须采用联治主义办法整合蒙藏边域,还建议“杂民族”的新俄也可尝试这一办法实现统一。李大钊解释说,联治主义源于解放的精神,即“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还特别强调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而是个性解放的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要重新组成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个性不受他方侵犯,同时结成一种平等的组织,完善其共性,达互助的目的。(48)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1919年2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95-400页。同时,李大钊还提倡在世界实行联治主义。如他反对大亚细亚主义时,不再强调中华民族做亚洲的主人翁,而是要亚洲各民族,为摆脱日本压迫,应该和“日本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实现民族自决,再建成亚洲联邦,最终和欧美民族一起结成世界联邦以增进全人类幸福。(49)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年元旦,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79、381页。但这只是巴黎和会前李大钊的民族和国家观。
巴黎和会的结果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大同团结理想与弱肉强食世界的现实出现了严重矛盾。如他责备威尔逊不退出和会和日本侵占山东行径,却反复强调这不是“狭隘的爱国心”作祟,只是反抗强盗世界的侵略行为。(50)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1919年5月18日,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57页。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李大钊便由唯物史观得出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这一结论。他指出国内的工农业受国外工业压迫,“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而赴欧美国家的华工却又受到外国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双重压迫。李大钊称这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51)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1日,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89页。李大钊从唯物史观角度解释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实际上从世界大同又回到了东、西国家民族竞争的立场。从整个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也很容易得出中华民族反抗西方压迫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结论,这与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宗旨不谋而合。
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反帝纲领,受共产国际指导,践行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1924年1月,李大钊赴粤参加国民党一大并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起草。他提出“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5月,李大钊在北大政治学系《人种问题》讲演时提出了新的中华民族观。
首先,他指出中华民族是历史和文化共同体,不受国籍限制。李大钊对国民、民族和种族概念作了辨析:国民是在同一政治下共同生活的人们,民族是在相同历史和文化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而人种只是生物学上的概念。其中,他特别提到台湾人民虽然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然其历史、文化都与我国相同,故不失为中华民族”。李大钊不再以国籍限定民族,而在相同历史和文化等较宽泛意义上定义民族,结合宣言中国民族反帝自决纲领看,是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自决提供合法性依据。这里李大钊将国民与民族区分开来,还有另一层用意,即多民族共处一国,并不必然出现“同一国内之各种民族有崩离之势”。
其次,他指出反抗压迫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是“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他指出,人种与民族性质不同,近代大多数民族冲突与人种差异的“异视”关联不大,主要是白种人以世界文明主导者自居,视有色人种为低下阶级,从而使人种问题成为世界的阶级问题。因此,中国人民觉醒、反抗列强压迫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将来要在民族舞台上彰显我们的民族特性和精神。他强调,民族复活的机运自五四时就已开启了。(52)李大钊:《人种问题——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的演讲》,1924年5月13日,见《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72、577、578页。
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在五四前后亦有明显变化。五四之前,李大钊基于解放精神提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互不隶属即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出路是在世界联邦体系中实现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平等和互助。五四以后,为了反帝,李大钊由唯物史观得出在世界经济关系中全中华民族都是无产阶级,于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就是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要义联系起来。这种观念也是为了反帝,让英治下的香港和日治下的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实现中华民族自决。李大钊打破了新中华民族以国籍界定民族的限制,强调拥有我国历史和文化者便是中华民族,这暗示了香港和台湾人民反帝和民族自决正当性,同时,亦为多民族共处一国提供合法性。
简言之,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以再建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国家为指向和目标。受民族解放和世界主义双重影响,最初力图以先破后立的方式再建新中华民族国家,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国民革命集中反帝建国目标指引下,他的中华民族观突破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界限,对内为多民族共处一国提供合法性,对外为被列强侵占的殖民地以中华民族自决方式回归祖国赋予了正义性。
四、结 语
我们讨论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应将其放到历史语境中,做动态的系统的考察,厘清其民族观在当时思想潮流中的脉络和特点,唯此方能获得整体性认知,并对其历史意义给出应有的评价。
李大钊终其一生为探求和践行救国救民真理(即“主义”)奔走呼号,直至牺牲生命。他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受立宪派、辛亥党人、进步党人和国民党人救国思想的影响,然而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并与陈独秀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对中华民族的看法,隐含于探寻再造中华国家的全过程,是与当时政治现实相碰撞、与其他思想派别相论辩的产物。正如前文所述,其中华民族观经历了满汉相对意义上的狭隘汉族观、五族平等国民意义上的汉族中心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观的演变。他的这一早期的理论探索,突破了清末以降旧党派以西方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在理论和多民族国家构建现实中遇到的困境。在打破一族一国民族主义窠臼,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辱,再造新的中华国家等探索中,李大钊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对此前中华民族观做了重新甄别和完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民族观,为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正是在民族观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创新,为中国共产党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此外,我们也可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先驱是如何走出时代和思想幽暗地带,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难求索过程,也许正是选择时的慎重、艰难和曲折,才造就了今天道路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