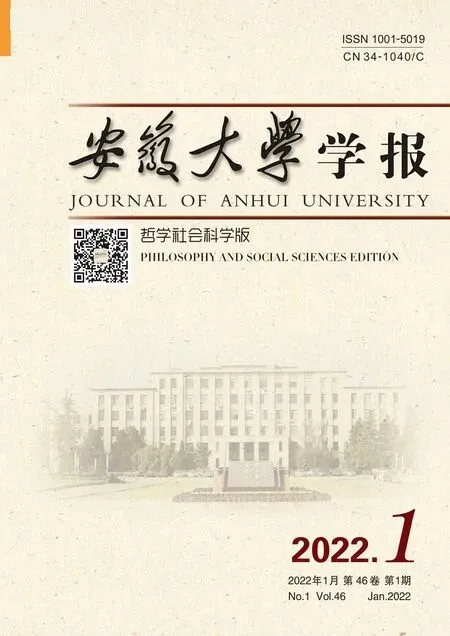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杨小雨,曾庆香
一、引 言
己亥猪年岁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在我国的突然爆发与蔓延,导致确诊人数与死亡人数不断递增,新型传播方式的接续发现,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时刻提醒人们病毒传播能力之强、传播速度之快。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形势,政府制定的政策,媒体汇聚各方的声音,以及公众所曝光并热议的人和事,都在争相设置疫情的实时走向,试图在社会情绪失控的边缘占据舆论引导的主场。学界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可主要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定量研究。学者们多采用回归分析、可视化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工具进行研究。二是舆论引导分析框架。学者们基于议程设置理论、危机理论等探讨了微博、微信及新闻报道的内容及特征,为舆论引导提供有价值的相关建议。三是舆论引导策略及相关传播效果的研究。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危机传播策略及政府、媒体、意见领袖应分别如何有效引导舆情走向。为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政务微博作为政务新媒体的“主力军”,应在此次重大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中将官方微博与个人微博的差异化特征转化为互补优势,实现“和声共振”(1)邓喆、孟庆国等:《“和声共振”:政务微博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舆论引导协同研究》,《情报科学》2020年第8期。。在重大疫情面前,主流媒体应发挥领军作用,加快提升网上传播能力,进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运用互联网思维热忱满足公众需求,不断改进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使公众喜闻乐见(2)丁柏铨:《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提升》,《中国出版》2020年第18期。。学者李小平建立了传播效果综合评价模型(3)李小平:《一种社会网络知识传播效果综合评价模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总体看来,在研究视角上,已有不少文献研究了政府、媒体与意见领袖三者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但从分析三者在实际案例中的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特性着手,建立同频共振的联动机制方面尚无涉及,即使将三者结合研究,也只在结论部分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如“政府部门作为高位舆论引导主体应积极发挥主动作用,弥补事件发生时的信息不对称;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建构和舆论表达也制约着突发事件的发展;公众作为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客体,其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满足与否,最终决定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效果”(4)焦俊波:《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研究的过程与得出的结论尚浅。
选取此次新冠肺炎作为案例,由于疫情涉及时间长、数据量大,因此研究无法进行全样本分析。为保证样本的有效性,研究依据疫情爆发的阶段性特征提取2019年12月30日、12月31日,2020年1月1日、1月2日为第一阶段,2020年1月23日、1月24日为第二阶段,2020年2月6日、2月7日为第三阶段,2020年2月13日、2月14日、2月15日为第四阶段作为抽样数据。之所以选择上述四时段,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发展的过程存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疫情初现,由于认知本身需要过程,政府与媒体前期对疫情认识不清,无法确切告知公众疫情情况,导致谣言愈演愈烈,加之李文亮等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惩戒,公众舆情产生;第二阶段疫情重灾区出现,政府加大力度对人群进行管控,对武汉实施封城,公众舆情达到第一个小高峰;第三阶段疫情直逼顶峰,伴随李文亮的去世,公众舆情瞬时爆发;第四阶段度过疫情顶峰,此时,政府与媒体在疫情防治和舆论引导上取得一定成效,公众舆情逐渐平息,民众生活趋于正常。
对于样本的选取,在政府通告内容的选择上,由于此次新冠肺炎属于公共卫生事件,又首发于湖北武汉,国家卫健委站在国家高度指挥疫情防控,湖北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作为疫情重灾地落实疫情防治措施,最具有代表性。同时,因为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可选信息较少,官方微信公众号与微博所发内容类似,所以按上述四个时段选取国家卫健委官网所有关于疫情的18篇“通知公告”和官方微博“健康中国”所有关于疫情的185篇博文(排除重复内容)。武汉卫健委官网疫情通告从2020年1月22日起由省卫生健康部门发布,并且由于湖北卫健委和武汉卫健委没有官方微信公众号,因此选取武汉卫健委和湖北卫健委官网所有关于疫情的23篇“通知公告”以及武汉卫健委官微“健康武汉官方微博”所有关于疫情的44篇博文(排除重复内容)。以上共计270篇。
在媒体报道内容的选择上,因研究无法穷尽全部媒体样本,考虑到与选取的政府媒介类型并置研究的合理性,在此次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在业界享有的独特地位等因素,将与此次疫情及公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官方媒体和都市化媒体官微报道作为媒体报道内容的择选对象,以保证数据的全面性与结论的可信度。基于此,研究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级权威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官微、疫情中心湖北地方政府报刊《湖北日报》官微、武汉当地具有影响力的都市化报刊《武汉晚报》官微以及以敢于说真话、大胆批评和言辞犀利著称的《南方周末》官微作为样本,按上述四个时间段得到《人民日报》官微124篇、《湖北日报》官微171篇、《武汉晚报》官微98篇以及《南方周末》官微29篇,共计422篇。
在公众关注内容的选择上,选取了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互动平台微博,以“新冠”“武汉肺炎”以及“新型冠状”为关键词在高级搜索平台上按上述四个时间段每天抽取点赞量、转发量以及评论量总和数排名前十的个人微博(除去不相关和蹭话题微博),共计110篇。政府、媒体和公众总计802篇样本。在研读所有样本的基础上归纳议题,完成对802篇样本的编码。
为进一步直观地展现政府通告议题、媒体报道议题与公众关注议题间互动的情况,研究将三者在不同阶段本身议题(议题主要所议的对象和事件)和勾连议题(议题在议论主要的对象和事件时连带议论的其他对象和事件)进行属性归纳,并计算各议题出现频次,以此作为权重采用Gephi图呈现三者议题呼应程度。此外,还分别统计了每一阶段三者的议题来源并制作各来源占比图。通过重点分析各阶段政府、媒体与公众在本身议题和勾连议题中的呼应度,以及三者议题来源的占比度,还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者是怎样争相设置议程进而引导舆论走势全过程的。其中凸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存在的重要问题是最后建立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的事实依据。
二、疫情初现: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
Kasperson等人指出,“风险事件与心理的、社会制度的和文化的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增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度并形塑风险行为”(5)转引自汤景泰、巫惠娟《风险表征与放大路径:论社交媒体语境中健康风险的社会放大》,《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这在新冠疫情初现时得到了很好的演绎。
2019年末,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在微信群里透露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情况,并勾连SARS议题,在网上引发关注。虽然政府和媒体迅速进行了辟谣,但由于医生的身份和病例的真实存在,导致网民对疫情的关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发增加。如图1中本身议题Gephi图所示,公众这一阶段关注议题迅速升为20个。但政府与媒体在辟谣之后回应公众热议的话题较少,前者只有病毒源头、出现病例和散布谣言3个,后者仅有散布谣言和出现病例2个。在公众有众多信息需求下,政府和媒体这种语焉不详,必然导致流言的产生,正如奥尔波特的流言公式所显示的:流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图1显示(6)图示中数字代表出现频次,箭头粗细程度与数字大小正相关,政府、媒体与公众在某一议题上箭头重合,代表政府与媒体回应了公众关注的这一议题,三者在议题设置上形成呼应,后续Gephi图同理。,政府与媒体未重视对公众勾连议题的回应,即疫情解释得不到位,会使得“谣言得到公众的信任,唤起了存留人们心底的,凝聚着情绪与情感的原型或集体记忆”(7)曾庆香、李蔚:《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与政府应对》,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第103页。——我国2003年SARS疫情,被勾起的恐慌焦虑心理使得公众风险感知度提升,对于获知信息和情绪抚慰的需求感增强。此后,除了信息本身的传播外,还伴随着情绪、情感的传播与感染,甚至发展到后来,作为导火索的事件本身信息已经不重要,或不完全得知,只剩下情绪、情感或信念本身的传播,这种弥散式的传播,将会以异常的速度在群体中蔓延开来,公众迅速聚集争夺议题框架设置权,疫情风险被放大。
SARS事件让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及时公布疫情的重要性,但在此次疫情初现时,地方政府由于对疫情的认识不到位、不知怎样定性疫情等客观因素,导致信息发布未能跟上疫情的发展速度。此时政府仅以疫情程式化通报和病毒可能性溯源为议题设置框架(由图1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无法满足公众获知信息、抚慰情绪和指导行为的需求。风险信息缺失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疫情防控信任度,提升了公众的风险感知度,疫情风险被放大。如图2所示,无论是公众议题来源还是政府议题来源,都是公众占据这一阶段疫情的议题框架设置权,引导舆论的大体走势。

图3 第一阶段媒体议题来源占比
现阶段,4A属性的专业媒体在为谣言传播、舆论聚焦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也为政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9)祝哲、彭宗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角色厘定:挑战和对策》,《东南学术》2020年第2期。。在疫情初现期,无论是信息的综述还是新闻事实的求证,专业媒体倾向于在新闻报道中呈现官方或权威来源(10)Duru, A. V., Narratives of death: Systemic determinants of the coverage of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15, No.4, 2019, pp. 215-232.。如图3所示,媒体这一阶段高度复制了政府问题界定和因果阐释的议题框架(由图1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但在疫情初期,在政府风险信息缺失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专业媒体如若只复制政府政策,而忽视公众诉求,则会勾起群众的愤怒情绪(11)UK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3,“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http://www.hse.gov.uk/research/crr_pdf/2001/crr01329.pdf.,“由此引发相关的次生风险”(12)张志安、冉桢:《“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下危机事件的风险沟通研究——以新冠疫情中的政府新闻发布为例》,《新闻界》2020年第6期。,更不利于风险事件的解决。
三、疫情爆发: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
疫情出现时,政府的辟谣策略暂时平息了公众舆情的蔓延,武汉当地民众便信以为真地认为这场即将大规模爆发的疫情只不过是“散布谣言者”制造的恐慌,疫情仍旧“可防可控”。 此时武汉市民并未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于2020年1月18日如期举行了“著名”的万人宴。仅隔两天,在国家卫健委记者会上,钟南山便证实新冠病毒确存“人传人”的现象。公众舆情复燃并迅速蔓延,开始热议武汉万人宴的种种后果。之后武汉封城随即引爆舆情。如图4中本身议题Gephi图所示,此时,面对公众关注的15个议题,政府仅回应了感恩故事和驰援武汉2个,媒体只回应了研发进展、在线问诊、感恩故事、驰援武汉和康复过程5个。这一阶段公众除了有对疫情的恐惧焦虑外,还存在着对部分相关部门事件处置的不满,认为在疫情可控阶段存在隐瞒行为。此时政府和媒体不仅未对公众关切的追责问责议题作出回应,反而在疫情阐释时频频提及SARS,如图4中勾连议题Gephi图所示。这既对引导舆论走势无利,还会加剧公众的焦虑与恐慌,使得由恐慌与焦虑的公众组成的群体迅速升级为发泄型群体,“即在群体中的个人认为自己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由此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法不责众或无人知晓的心理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13)莫伟民:《另一种政治哲学:福柯的“生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5日,第009版。,随着武汉拉开疫情“封城”防控战后,引发大批公众在封城前夜出逃武汉的种种非理性行为。

图4 第二阶段政府、媒体与公众本身议题与勾连议题呼应度
“封城”防控战,实质上是“通过专家知识来把某类人归入风险人群而隔离起来,以保证社会秩序处于正常化状态中;或是赋予某一类事项以风险属性,通过延缓或终止的方式来保证社会利益的最大化”(14)韩宗生:《风险社会理论范式的批判性阐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在此期间,前期从“未见明显人传人”,到 “已证实人传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的信息权威度,点燃了公众愤怒的非理性情绪。这一时期政府仅运用解决对策的框架对疫情进行救治防护、物资保障以及传播形势等主流议题建构(由图4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虽然暂时占领议题框架建构的主导位置,及时稳住公众进行自我议题建构的趋势,却实质上没有满足公众情绪抚慰和行为指导的需要。当疫情爆发时,信息呈井喷式增长,如果此时公众信息流不畅、政府与媒体的影响流有限,会出现噪音流强化的现象,影响正常的信息传播。“一般来说,危机传播流是由信息流、影响流和噪音流三部分组成,危机传播围绕相应的控制、引导、消解展开”(15)邓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因此,公众本身建构的议题仍旧占据这一阶段公众议题和政府议题的主要来源,引领当下议题建构的大趋势,政府舆论引导效果并不显著,如图5所示。

图5 第二阶段公众与政府议题来源占比
福柯在其“治理性”中提出社会稳定秩序的正当性来源于“生命政治”和“安全配置”。“生命政治”即“以安全社会的名义,致力于布置、调控和干预环境问题以实现合理治理的政治技术和设想”(16)莫伟民:《另一种政治哲学:福柯的“生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5日,第009版。。“安全配置”应该包括行为指导和情绪安抚,即强调事实上的稳定。只有在治理中寻求二者的相容相配,这种“治理术”才会换来疫情期间社会总体秩序的稳定。此时,政府的封城策略虽能抑制公众的非理性行为,却不能换来事实上的稳定。因为现代社会是工具理性与世俗政治的集合体,而社会的稳定秩序需要建构二者之间的相容性。福柯强调,“管理人不是强迫他人做管理者要求的事,而是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保证强制权的技术与自我建构间存在着某种互补和冲突的动态平衡”(17)转引自徐晓霞《简析福柯的“治理性”概念》,《文化与传播》2013年第6期。。因此,这一阶段政府的防疫策略应将权力规训下的限制人口流动硬政策和目标共识下的舆论引导软策略进行融合。如此,才能真正取得社会的总体稳定。

图6 第二阶段媒体议题来源占比
传媒是公共话语资源,其建构和定义现实的功能使其能够反映社会的权力结构(18)王斌、胡周萌:《媒介传播与社会抗争的关系模式:基于中国情境的分析》,《江淮论坛》2016年第3期。。在实际中,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扮演着公开宣传角色和内部监察角色,前者引导舆论、生产共识,后者代表上级对下级开展调查的报告(19)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第1期。。特别是在疫情的爆发与对病毒尚不可知的情况下,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想要规避政治风险、及时对公众有关政府的意见作出回应非常难。因此,媒体但凡对公众有回应,就必须集中回应公众最关注的议题,否则无法扭转舆论走势。如图6所示,这一时期,媒体依旧高度复制政府解决对策等议题,将政府议题作为主要议题来源。可以看到,与上一阶段相比,媒体略微增加了本身议题设置的比重,但这一略微增加的比重因为没有回应公众热议的议题(由图4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而不足以颠覆公众对媒体复制政府信息的刻板印象,媒体与公众之间信息仍旧互通不畅,影响舆论引导的效果。
四、疫情蔓延:公众信任占半·政府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风险类型的划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爆发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逐步转向“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或者是“外部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20)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随着武汉的封城、李文亮医生的离世和公众情绪的频频失控,这已不再单纯地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具有多重社会后果的社会信任危机。
2020年2月7日,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于凌晨去世。此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后立即引爆公众舆论。几小时后,各种自媒体博主有关“哀悼李文亮”的博文被公众疯狂转发。此时,公众对个别疫情处置不当者的愤怒和对疫情恐慌的情绪因李文亮的去世而达到顶峰。在极度愤怒与恐慌心态的驱使下,公众会产生寻求情绪抚慰与责任归因等需求,以及表达自身价值观念的强烈愿望。如图7中本身议题Gephi图所示,公众主动介入议题框架建构,除了向政府与媒体寻求信息,要求调查病源、关注疫苗进展外,还充斥着谴责个别失职官员的声音和哀悼李文亮的悲伤情绪。这一阶段,虽然政府与媒体减少了对SARS议题的勾连,如图7中勾连议题Gephi图所示。但面对公众着重关注的12个议题,政府仅回应了哀悼李文亮、加油鼓劲2个议题,媒体只回应了哀悼李文亮、方舱医院和研发进展3个议题,如图7中本身议题Gephi图所示。在公众舆情处于谴责与信任两端极化的边缘阶段,政府与媒体会因没有及时给出解释并负起相应责任而无法引导舆论走向理性,由此产生社会信任危机。正如卢曼所说:“风险问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各功能系统是如何有效处理风险的,而是各功能系统如何依据其自身的条件对因果关系作出归因的过程。”(21)Luhmann, N., Albrow, M.,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p.25.

图7 第三阶段政府、媒体与公众本身议题与勾连议题呼应度
“风险社会学认为,任何灾害风险都具有联结效应(combination effect),都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紧密联结的复合系统”,“很多情况下,这种因风险的复合性而带来的联结效应所产生的风险影响和社会后果甚至都超过了风险灾害本身”(22)Zimmermann, M., Glombitza, K. F., Rothenberger, B.,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rogram for Bangladesh 2020-2012, Switzerland: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2010, pp.61-74.。病毒肆虐夺走亲人、疫情管控下民众陷入经济困境,这些因素让公众对李文亮的去世格外关注,甚至一度超过疫情本身。如图8所示,虽然公众议题在政府议题来源中占比有所提升,但此时政府仍以解决对策为主和道德判断为辅的框架进行疫情进度的阐释和情感的引导,在联结效应带来的影响之下,导致地方政府与公众自说自话,舆论引导效果并不可观,公众依然占据这一阶段议题框架设置的主导权。

图8 第三阶段政府与公众议题来源占比

图9 第三阶段媒体议题来源占比
作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理应实践其兼顾多方、上传下达的社会责任。但在全球化语境下,在智能化进程中,社交媒体的普及加剧了“真相还在路上,谣言早已登场”的局面,“人人都有麦克风”导致“众声喧哗”,群体传播的圈层又加剧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这都加大了专业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难度。然而在疫情的蔓延阶段,即使被“谣言”环绕,“谣言”又被社交媒体大量转发导致公众的不理性发声,专业媒体仍旧能克服困难并审时度势,以道德判断为主、解决对策为辅,主动建构哀悼李文亮和处理失职干部等议题(由图7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回应公众情绪抚慰和行为指导的需求。虽然这一阶段政府议题依旧占据媒体议题的主要来源,如图9所示,但媒体提高了回应公众议题的比例。相较于上一阶段,在提高回应公众议题比例的这部分中,媒体增加了追责问责议题(由图7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虽不算及时,但也能平复一部分公众愤怒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公众的信息恐慌,营造出后续政府联合媒体占据议程设置主导权,进而扭转舆论走势的有利环境。
五、疫情衰退:政府、媒体安抚情绪·公众信任、鼓劲
2020年2月8日,武汉封城过去半月,疫情防控、社会和百姓生活,都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前三阶段政府、媒体与公众对议程设置权的争夺与舆论引导走势的探索,可知“早期的风险沟通,仍然着重‘单向告知’,重在向公众提供事实,认为只要提供准确的事实和统计数据,公众就能作出‘正确’的决定”(23)邓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呈现出明显的精英导向,舆论引导效果并不可观。
在疫情衰退的这一阶段,政府吸取上一阶段媒体报道的策略,紧跟其设定的议题,以道德判断为主、解决对策为辅,积极主动进行医护关爱、感恩故事等议题框架建构。同时,在提供疫情防控等强关联议题基础上,扩展至财税政策、社会影响、复工复产,以及教育、就业等衍生议题(由图11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与媒体报道形成合力,有力回应了公众在疫情后阶段情绪关照、防控行为指导和生产生活等信息的需求。此时,“通过转换站位、多频共振,基本实现了‘政府议题-媒介议题-公众议题’的融合效应”(24)Fischhoff, B., Risk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plugged—20 years of process, Risk Analysis, Vol. 15, No.2, 1995, pp.137-145.。三者议题的融合恰恰是“风险沟通进入到了加强沟通双方的对话参与,考虑各方参与者能动性的阶段”(25)张洁、张涛甫:《美国风险沟通研究: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传者不仅要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还要以受者的需求为导向提供信息和进行反馈,是动态的对话”(26)苏婧、张镜:《从危机传播到风险沟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播转型》,《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4期。。同时,“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和相关职能政府部门多次对疫情防控进行指挥和布置,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开始降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7)赵耀、王建新:《基于多元主体共在与信息即时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舆情的思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第2期。。
如图10所示,虽然政府议题仍旧占据媒体议题的较大部分比重,但媒体此时以对话式的方法、负责任的态度回应公众切实所需(由图11中本身议题Gephi图可知),占据了公众议题来源的绝对比重,这是媒体抢占议程设置主导权的胜利,也是媒体成功扭转舆论走势的胜利。这一阶段性胜利亦预示着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提升,因为这是以政府紧跟媒体回应公众议题为策略在舆论引导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突出表现。

图10 第四阶段媒体、政府与公众议题来源占比
这一阶段,公众议题开始重新与SARS有勾连,与疫情初始因恐慌而产生的勾连不同,此时“多次与2003年‘非典’进行比较,是因民众高度关注疫情过后中国经济承受能力以及国际社会连锁反应”(28)邓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此时政府和媒体敏锐地察觉到公众对疫情防控关注取向发生的改变,主动为公众解决后顾之忧,并及时给予公众反馈。因此,这一阶段三者议题重合度较高,如图11中本身议题Gephi图所示,在公众关注的17个议题中,政府与媒体虽共回应8个议题,但其中公众关注度高的感恩故事、日常防疫、研发进展、康复过程等议题均和政府或媒体回应的议题相呼应,显示出政府与媒体从单向的“告知信息”到双向的“舆论引导”策略的转变,其二者与公众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对话式风险沟通模式。此后,公众热议的议题也随之转向加油鼓劲、祈求平安等正面议题上,政府与媒体舆论引导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舆情开始回落,民众生活逐渐回归正常。
六、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在风险社会中,任何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都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风险事件只要发生了,就必然会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众多领域发生关联,并产生一种社会放大效应(29)Kasperson, R. E., Renn O., Slovic, P., et al,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 Conceptual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Vol. 8, No.2, 1988, pp.177-187.。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停留在灾害的表面,而是深入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的压力、经济秩序的影响、持久的心理感知度以及难以修复和重构的文化困境等。政府应对这种疫情灾害的管理经验基本都是 “临时介入—适度改进—再临时介入”(improsive,improve and improvise)(30)Puig, M.E., J.B. Glynn, Disaster Responders: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to Recovery and Relief Work,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Vol. 30, No. 2, 2003, pp. 55-66.。而这种传统的方式存有明显的单一性、线性的特点,会对风险管理带来一定的局限,并收效甚微。

图11 第四阶段政府、媒体与公众本身议题与勾连议题呼应度
在以往案例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议程设置、框架建构、范式订定及舆论引导等方面既存在着政府主导、专业媒体主导、公众/意见领袖主导,也存在着政府与媒体共同主导四种情况,从而出现舆论甚至谣言倒逼“真相”的状况。
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严重水污染。人们通过互联网知晓水污染消息,市民疯狂采购并陷入恐慌,政府、媒体未对水污染事件及时通报,导致哈尔滨地震、出逃哈尔滨等谣言愈演愈烈。经过激烈的商讨,政府决定发布公告承认停水系中石油吉化公司爆炸所致,媒体也主动对上进行深度调查、追责问责等监督报道,对下进行科普与行为指导等防控报道,赢得了公众的谅解。公众主动与政府和媒体一道共同应对挑战并战胜了困难。
又如2008年9月,石家庄爆发三鹿奶粉危机。此前,有网友曾在天涯社区发布帖子质疑三鹿奶粉质量,后来此帖发布者被三鹿公司“封口”,媒体并未对此事有深挖报道。之后三鹿奶粉被检测出三聚氢胺,三鹿集团虽出面解释但推卸责任之意却远远多于主动承认错误,这一阶段政府和媒体都未跟进,一时舆论沸腾。直至9月12日,一位自称三鹿公关普通员工在网上揭露三鹿集团公关解决方案才使得媒体纷纷出面追责三鹿。随后9月13日国务院启动机制处置乳业危机。但食品安全、政府管理、媒体报道以及“中国制造”,乃至包括人权状况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一度遭到社会的质疑。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和媒体在舆论引导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可推卸的职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并不是政府、媒体各自单独在唱的“独角戏”,或是政府与媒体一起合唱的“双簧戏”,而是需要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的协同应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发生后,最应该率先建立的就是一种应对疫情风险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1)文军:《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共同体防控——基于风险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实现从原来政府单一负责向社会集体负责转变,从“一主多辅”向更具凝聚力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转变。
具体而言,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初现期,公众曝光疫情并传播流言,政府及时预警并向媒体和公众发布疫情,媒体主动对公众发布疫情并回应公众需求,同时对政府进行疫情预警并回应政府;在爆发期,公众因为疫情会在舆论监督时伴随着情绪的发泄,政府对媒体和公众进行防控通报和疫情阐释,媒体为公众设定疫情阐释和解决对策的议题框架,同时对政府实施新闻监督和深度调查;在蔓延期,公众信任权威并予以情感支持,政府继续进行防控通报的同时修正自身行动,媒体以道德故事和解决对策引导公众,并引导政府追责相关人员;在衰退期,公众增强对政府和媒体的信心和信任,政府在建构自身形象的同时进行权威科普,媒体为公众提供科普知识并设定典型报道的议题框架,与此同时对政府进行深层的反思和经验的梳理。三者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疫情,在实施此流程和实践反馈基础上调整或强化舆论引导机制,形成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如图12所示。

图12 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互联网时代,本身就伴随着众多不确定性信息的出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对舆论引导作用与机制的构建拥有较大的形塑力量。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学界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案例观照此类议题,案例的不同却并没有得出明显的差异性结论,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和媒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回顾过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看到,公众/舆论领袖总在政府和媒体对突发问题处理不当时存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舆论走势的情形。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舆论领袖又在一定阶段成为掌控议程设置和引导主流舆论的重要力量。鉴于此,公众/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中的主观能动性显得更加可贵。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不仅要着眼于危机舆论引导的问题所在,更要纵观全局,以民众的诉求和社会的稳定为目标,三者合力形成协同一致的良性互动机制,共同应对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