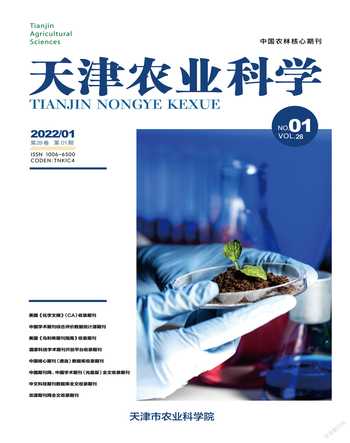“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
聂淼 余超 董照锋


摘 要:建设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已成为公认的解决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总结了猪肉质量安全与可追溯体系的概念和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现状,提出了“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构想,分析了“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优势与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推进可追溯体系改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引导宣传、试点先行逐步推广、持续发展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等建设建议,以期为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思路。
关键词:猪肉;可追溯体系;质量安全;“宰销一体”模式
中图分类号:TS201.6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22.01.014
Construction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under the "Integrated Slaughter and Sales" Mode
NIE Miao1, YU Chao2, DONG Zhaofeng1
(1.Shangluo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Center, Shangluo,Shaanxi 726000, China; 2.Shangluo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Center, Shangluo, Shaanxi 726000,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has become a recognized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cept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my country, which highlight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under the "integrated slaughter and sales" model. In addi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problems it faced in the establishment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constructio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which include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publicity, gradually promoting by pilot firs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and standardized breeding, etc.. This article would provide referenc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ork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pork; traceability system; quality and safety; "Integrated Slaughter and Sales" mode
我國是世界猪肉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62%,其质量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1]。建设猪肉等畜产品可追溯体系逐渐发展成为控制猪肉等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并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立健全追溯体系,是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重要举措。我国政府和企业在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和推广应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追溯信息不可查、不全面、不可信等诸多问题长期存在,难以实现有效溯源,极大制约了可追溯体系在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方面的效果[2-3]。从生猪养殖到屠宰加工,最终以猪肉形式到消费者餐桌,经历了复杂的交易和流通环节,给猪肉质量安全信息的采集、储存、溯源等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任何环节出现漏洞或虚假,都直接影响猪肉质量安全追溯效果。生猪屠宰环节是活猪到猪肉再到消费市场的过渡环节,是控制猪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是建设猪肉可追溯体系核心环节。目前,我国猪肉从屠宰环节到销售市场,涉及的经营主体繁多,且各主体素质差异较大,是猪肉可追溯体系难以规范有效运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在总结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构想,分析了该模式下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优势与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建议,以期为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思路。
1 猪肉质量安全与可追溯体系的概念
1.1 猪肉质量安全
猪肉质量安全可从三层面理解,一是猪肉产品安全,猪肉对人类身体健康和生命无危害,其感官、理化、微生物等各项技术指标和卫生标准均达到国家或国际质量标准;二是猪肉相关活动安全,猪肉在生产、屠宰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免受有害物质污染,使猪肉有益于人体健康;三是猪肉品质在销售过程中真实,不弄虚作假,不欺骗消费者。饲料原料污染或养殖场饮水不达标,非法使用禁用抗生素或未严格实行休药期等使猪肉药物残留,售卖过期猪肉、病死猪肉、注水肉等都会直接影响猪肉质量安全。
1.2 猪肉可追溯体系
可追溯是通过记载的识别,追踪实体的历史、应用情况和所处场所的能力,具有跟踪和溯源双向性的特点[4]。猪肉可追溯体系是指对生猪养殖、流通、屠宰加工、冷藏、猪肉销售等产业链各关键环节的相关质量安全信息进行跟踪记录,并可实现全程追溯或追踪的保障体系,对有效控制猪肉质量安全、增强消费者信任度和满意度、加强猪肉质量安全监管、提升猪肉国内外市场竞争力等有着重要意义[5]。猪肉可追溯体系能够实现从养殖到屠宰再到消费等各个环节点追溯检查相关产品,一旦发生猪肉质量引发的安全事故,可通过追溯体系迅速准确找到危害元,杜绝事故的大范围辐射,以确保安全。猪肉可追溯体系的溯源难度由低到高可分为追溯到销售门店、屠宰加工企业、养殖场户、养殖饲料和兽药使用情况等四个层级,结合我国国情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目前,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应以追溯到养殖场户为目标[6]。
2 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现状
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疯牛病”事件[7]。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相当完善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及运行机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通过环境监测、气候模拟、卫星跟踪、成像分析等技术,畜禽产品全程质量安全追溯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8]。
早在2002年,我国就开始探索建设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并逐步纳入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9](表1)。猪肉作为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肉类产品,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始终是我国畜禽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重点。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主要由农业农村部及商务部共同推动,包括农业农村部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及商务部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2017年6月,农业农村部首先在四川、山东、广东3个省开展国家农产品追溯平台试运行,2018年9月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各地加快落实已有追溯平台与国家平台的对接融合,持续优化平台,稳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2010年开始,商务部分五批支持58个城市建立城市级肉类蔬菜流通追溯平台,对畜禽屠宰、加工、批发、零售、超市、团体消费等环节的流通信息和责任主体进行追溯,初步实现试点范围内肉类蔬菜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有效提升了流通领域的肉菜安全保障能力。
可追溯体系建设前期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我国以企业为主导的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较少,代表性的有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吉林精气神山黑猪肉质量安全溯源查询系统”和山东徒河黑猪食品有限公司建立的“山东绿源新食品徒河黑猪溯源查询系统”[10]。前者消费者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查询到批次屠宰、分割、检疫、包装等生产信息以及饲养、放牧、运输等养殖信息,企业还将追溯系统与京东智慧养殖系统相结合,运用猪脸识别、AI管理、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消费者可实时、精准了解到每头山黑猪的全部生长、生产、流通信息。后者系统还处于进一步建设过程中,暂时不能实现追溯信息查询。
随着我国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不断发展,相关政策法规、监管体系和技术框架基本建立,可追溯的理念逐渐被社会了解和认可[11]。但认为可追溯体系“效果不显著”、“形同虚设”的看法也是客观存在的[12]。高额的运营成本付出并没有给经营者带来销量和利润增加,经营主体执行追溯制度的积极性不强[13-14]。
3 “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构想
猪肉从养殖场到餐桌需要经历养殖、流通、屠宰、销售及消费五大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对应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养殖环节有规模猪场、养殖合作社、家庭农场、散养户等经营主体,销售环节有大型连锁超市、小型超市、专营门店、农贸市场、自营门店、流动商贩等经营主体。经营主体繁多和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一给可追溯体系建设及规范有效运行带来极大困难。基于屠宰环节经营主体单一易管控特点,作者提出“宰销一体”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构想(图1),其基本原理是以屠宰场负责制统一销售环节,即屠宰场建立猪肉品牌,对其质量安全直接负责,并以直营店或与其他销售主体合作统一挂牌连锁经营,且销售主体只能与单一屠宰场建立合作关系,消费者无论选择在哪个经营主体消费,通过品牌名称,不用扫码操作就可知道所购买的猪肉源自哪家屠宰场,扫码后可进一步查询销售门店、冷链运输、屠宰分割、批次检疫以及养殖档案等信息。
4 “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优势与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4.1 “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體系优势
(1)减少信息不对称,强化市场作用和公众监督作用。信息不对称被认为是猪肉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生猪产业链链条长短成正相关[14-15]。“宰销一体”模式缩短了消费环节与屠宰环节距离,通过猪肉品牌名称消费者就可判断所购买猪肉来自哪家屠宰企业。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购买更信任的屠宰企业品牌猪肉,同时对屠宰企业起到直接监督作用。
(2)增加生猪屠宰企业参与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建设猪肉可追溯体系意义重大,但如果没有较高的收益回报,企业只会在政府强制推行下实施可追溯体系,参与积极性不高。“宰销一体”模式下,屠宰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较好的可追溯体系有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竞争力,促使屠宰企业积极规范参与可追溯体系建设与运维。同时,市场激励机制可促进企业不断创新可追溯体系建设,使可追溯体系更优发展。
(3)规范屠宰行业秩序,极大避免私屠滥宰违法行为发生。“宰销一体”模式下,豬肉都是以单一品牌形式连锁经营售卖,禁止私自售卖猪肉,市场上所售猪肉全部是屠宰企业品牌猪肉。私屠滥宰没有了消费市场,也就没有了违法动机。
(4)猪肉销售环节统一经营,追溯体系运行更加规范。“宰销一体”模式下,所有销售主体都必须和唯一屠宰企业合作经营,一方面避免了一个经营主体售卖两家品牌猪肉,减少追溯误差,另一方面,经营主体必须按照屠宰企业统一要求进行猪肉售卖,按要求建立购销台账、主动提供购物小票,有利于可追溯体系的规范运营。
(5)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销售环节猪肉质量安全。研究表明,反复冻融会严重降低猪肉的食用品质,冻融次数越多猪肉品质越差[16]。目前,我国猪肉销售模式下反复冻融售卖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甚至售卖过期猪肉。“宰销一体”模式下,屠宰企业可根据自营店或其他合作经营主体日销售情况,应用大数据分析,合理安排屠宰批次,统一冷链运输,科学布局冷库,最大限度减少猪肉冻融次数,实现“集中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市”的目标。
(6)可实现现场分割售卖要求,满足大众消费习惯。现阶段,发达国家和我国已有的可追溯猪肉都是把生猪胴体按照不同部位分割成小块猪肉独立包装后贴上追溯条码,消费者只能选择已包装好的可追溯猪肉,往往很难选择合适部位、合适重量大小的猪肉。而我国消费者习惯在购买猪肉时现场分割,选择好部位后要多少割多少。同时部分消费者对提前分割包装好的猪肉品质存有疑虑,这也是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17]。“宰销一体”模式下,屠宰企业可直接将带有编码的生猪胴体冷链运输到销售门店,销售门店可现场分割猪肉并对其进行续码售卖,最终消费者可通过扫描购物小票上的追溯码对猪肉信息进行溯源。
4.2 “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
(1)需大量的资金投入。“宰销一体”模式下,屠宰企业既要负责屠宰环节又要兼顾销售环节,需要较大资金支持,同时因销售环节主体较多,屠宰企业管理压力较大。
(2)政府监管责任不明晰。目前我国生猪养殖到屠宰环节属于农业农村部门分管,销售环节属于商务部门分管。“宰销一体”模式合理运营需要两个部门联合监管,往往会出现管理漏洞和监管空白。
(3)易形成地方垄断。“宰销一体”模式下,猪肉消费市场竞争很容易演化为屠宰企业资金实力竞争,往往会形成区域性企业垄断。
(4)现代化屠宰企业不足且布局不合理。据统计,2017年全国有屠宰企业2.07万家[18],但很多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装备不足,机械化率低,开工率不足30%。生猪主产区屠宰能力不足,主销区屠宰企业产能过剩。
(5)冷链运输系统不健全。“宰销一体”模式对猪肉冷链物流有极高的依赖性。目前我国猪肉冷链物流主要是地区性分布,冷链企业散、小、乱问题突出,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冷链网络互联互通不足[19]。
5 “宰销一体”模式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建议
5.1 推进可追溯体系改革
(1)建立可追溯官方监控体系。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是一项全国性的系统工程,政府应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方面,建立一支从国家到地方专门的监管机构,明确各级职能职责,创新运行模式,开展跨区域、跨部门、跨系统合作,确保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监管不留空档,提高监管执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增强猪肉质量安全监管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建立全国性统一的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平台,生猪养殖、流通、屠宰、销售等环节全程覆盖,各环节经营主体、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监管机构负责可追溯平台总体运维,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环节信息快速高效收集并形成巨大的数据库,最终上传到公众信息平台,消费者可通过平台追溯到购买猪肉的来源,真正做到全程监管。
(2)完善可追溯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积极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牧法》等修订完善工作,严格违法责任承担,明确各经营主体第一责任,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合理设置罚款金额,提高违法成本。细化地方政府及监管机构管理责任,实行问责制度,增强执法监管能力。规范生猪养殖、屠宰、运输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适时淘汰落后标准,配套质量标准检测检验方法,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5.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优化屠宰企业和销售点布局。非洲猪瘟疫情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背景下,各大区应平衡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屠宰产能,尽快调整优化大区内屠宰企业布局,促进生猪就地就近屠宰。生猪主产区应抓紧时机适当加快现代化屠宰场建设。新建屠宰场,选址必须符合《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从方便监管、有利流通、提高质量安全等方面,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合理规划布局。对已饱和地区不再新建生猪屠宰场,实施标准化改造工程,提高机械化率、现代化水平和屠宰完成后的保鲜率[18]。生猪主销区应淘汰落后产能和整合过剩产能,保留少量现代化标准屠宰企业即可,鼓励屠宰企业转型升级为专门化冷链物流中心。另外,“宰销一体”模式下,屠宰企业还应综合考虑区域消费量、方便群众、优化企业效益等方面,合理布局品牌肉销售网络。
(2)完善冷链物流体系。猪肉冷链物流对车辆规范、温度控制和生物安全等有其特殊要求。加快制定冷链物流体系相关规程标准,对冷库结构、冷藏运输车温控、生物安全防控等进行规范[20]。加强生猪运输和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屠宰企业自建冷库和购置冷藏运输车,支持第三方猪肉冷链物流企业发展,对原有落后冷库实施改造提升工程,建立冷鲜肉品流通和配送体系,逐步构建产销高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加大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冷链物流体系中的应用,提高流通效率,保证猪肉质量。
5.3 加强引导宣传
政府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官方媒体,加强猪肉可追溯体系宣传力度,提高大众对可追溯猪肉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和额外支付意愿。加大对猪肉追溯体系各经营主体培训指导,增强法律和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作为企业信用背书的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执行可追溯制度。另外,充分调动消费者日常监督作用,努力实现市场起主导作用、消费者、企业和政府共同参与猪肉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良性运作机制。
5.4 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建设“宰销一体”模式豬肉可追溯体系前期资金投入较大,涉及利益主体较多,政府应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切忌一刀切,选择具有一定实力的现代化屠宰企业和基础条件较好、大众对可追溯猪肉认可度较高的发达城市和区域,先进行试点运行,优化完善运行机制,理顺监管流程,总结建设成功经验,全国逐步推广。
5.5 持续发展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
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可从源头对猪肉质量安全进行有效控制,提升猪肉质量安全水平,是实现我国猪肉有效溯源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生猪产业仍存在规模养殖比重低、标准化水平不高等问题。要以生猪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为抓手,以规模化带动标准化,以标准化提升规模化,加强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规划布局,建立健全生猪标准化生产体系,强化先进科学技术培训与指导,加快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完善与推广应用步伐,不断提升生猪标准化规模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1] 李慧.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态势逐步向好[N]. 光明日报. 2019-03-02(3).
[2] 刘增金, 乔娟, 张莉侠, 等. 消费者对可追溯猪肉的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495位消费者的问卷调查[J]. 上海农业学报, 2016, 32(3): 126-133.
[3] 黄胜海, 陆俊贤, 张小燕, 等. 我国畜禽产品追溯体系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8, 20(9): 23-31.
[4] 张驰, 张晓东, 王登位,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7, 19(1): 18-28.
[5] 高迎春, 薄永恒, 杨林, 等. 畜禽产品安全生产信息化和质量追溯系统研究进展[J]. 山东农业科学, 2015, 45(3): 127-130.
[6] 乔娟, 李文祥, 刘增金. 加快完善我国猪肉可追溯体系顶层设计的思考[J]. 猪业科学, 2017, 34(8): 50-51.
[7] 陈娉婷, 罗治情, 官波, 等. 国内外农产品追溯体系发展现状与启示[J]. 湖北农业科学, 2020, 59(20): 15-20.
[8] 代晓凝, 刘丽莉, 孟圆圆, 等. 河南省肉类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体系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J]. 肉类工业, 2018, 37(10): 38-42, 45.
[9] 谭利伟, 王应宽. 发达国家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的发展与启示[J]. 肉类研究, 2016, 30(12): 54-63.
[10] 刘增金. 基于质量安全的中国猪肉可追溯体系运行机制研究——以北京市为例[D].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11] 李玉红, 李宗泰, 李华, 等. 猪肉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J]. 黑龙江畜牧兽医(下半月), 2019, 18(9): 29-32.
[12] 辛盛鹏, 王慧敏, 谭智心, 等. 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可追溯体系运行机制及优化对策研究[J]. 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2017, 14(5): 8-14.
[13] 秦雨露, 孙晓红, 陶光灿. 我国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推广应用难点及对策研究[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20, 22(1): 1-11.
[14] 何德华, 史中欣. 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研究与应用综述[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9, 21(4): 123-132.
[15] 张小允, 李哲敏, 肖红利. 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探析[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18, 20(4): 72-78.
[16] 常海军, 牛晓影, 周文斌. 不同冻融次数对猪肉品质的影响[J]. 食品科学, 2014, 35(15): 43-48.
[17] 孟晓芳, 刘增金, 张莉侠, 等. 信息源信任对消费者可追溯猪肉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上海市和济南市1009份消费者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上海农业学报, 2019, 35(2): 107-114.
[18] 张喜才, 汤金金. 非洲猪瘟背景下生猪供应链重塑及其对策研究[J]. 中国畜牧杂志, 2019, 55(9): 143-146.
[19] 牛小娟.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J]. 科技信息, 2011(29): 159-160.
[20] 刘如意. 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江苏农业科学, 2020, 48(22): 311-316.
收稿日期:2021-08-27
作者简介: 聂淼(1991— ),女,陕西山阳人,农艺师,硕士,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董照锋(1976— ),男,陕西洛南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