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忠诚
刘文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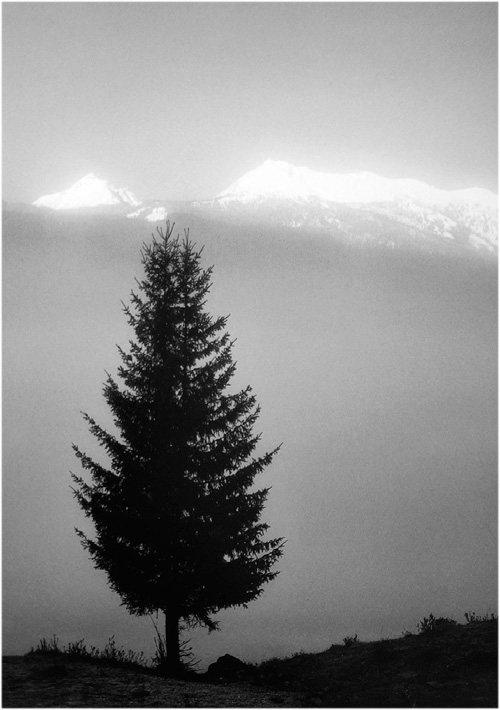
父亲叫刘吉如,虽说只是个农民,但曾是温州地区的劳动模范,虹桥镇上大名鼎鼎的老黄忠。又因他与中国共产党同岁,对党就有特别的感情。他有一句名言:“都说祖国是娘,我说共产党是大(父亲)。共产党让我们吃饱穿暖,就是大,我们要孝顺。”
父亲对于“大”这个名号,看得比山还重,他有很深的父亲情结。
父亲是个遗腹子,他出生前,我爷爷就死了,他一出生就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我父亲前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他十来岁,一家三口靠祖母帮人洗衣缝衣赚点零碎钱过活,经常吃不饱穿不暖。每当一家人饿得、冻得发抖时,祖母总抱着我父亲哭,说:我儿命苦冇大,才吃不饱穿不暖啊……由此,父亲就认定,大就是让他吃饱穿暖的人;谁能让他吃饱穿暖,谁就是他的大。十四岁那年有一天,父亲看到镇上在招兵,说当了兵有饭吃有衣穿还有津贴,就认定军队是大了,就想投军。招兵的见他年少,不要他。他看到边上有个人双手抖抖地、吃力地在举石锁,就过去,单只手把石锁举了三举,他就当了兵了。当兵后,他让人给祖母带信,说:“娘!儿找到大了,军队管吃管穿,你甮愁!”
可不久,国民党的军队就让父亲灰了心。他的部队是乌合之众。父亲作为新兵,非但发不到枪支,还拿不到饷银。一些兵还胡作非为,以掳掠百姓为能事。一次父亲上街,看见四五个兵端着枪在洗劫一家商铺,便上前阻止。可是,那四五个兵的几条枪却立马调过头来对准他。他从小练过武,不怕这架势。其时天热,父亲肩背上搭着脱下来的军衣。这时就随手将军衣一挥,身子一转,四五条枪就被军衣绞在一起,挂到了父亲的背上了。父亲就背着这四五条枪到兵营告状,却反被当官的骂了一通,说他多管闲事。父亲一恼之下,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正值我大伯去世,大伯母也脱身到县城做保姆去了,留下两儿一女由我祖母抚养。我祖母正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父亲就担起家庭这副重担。可他没田没地,只能给人帮长工,累死累活还养不活一家五口人。每当我的堂兄堂姐饿得冻得发抖时,我祖母总抱着他们哭,说:“我娒命苦冇大,才吃不饱穿不暖啊……”父亲就想,还得找个管吃管穿的大呀。
父亲就拜师学做道士。
道士好啊,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道士先生做道场。做道场收入也好啊,除了工钱,每次回家都能带些做供品用过的鸡、肉、年糕,一家人吃得热闹。父亲早年读过半年书又肯自学,又练过三脚猫的功夫,当然比别人做得好。于是,虹桥山圈底没人不知鼎鼎有名的道士刘吉如。由此,我父亲以为道士这个大找对了。可正在父亲给我大堂兄娶亲、堂姐出嫁的时候,我的二堂兄却被国民党部队拔壮丁当担夫吐血死了,还要我父亲拿钱去领尸体。待到东借西凑弄足钱把二堂兄的尸体赎回来安了葬,父亲这个家庭又被打烂了。
就在一家人走投无路、前途无望的时候,1949 年,共产党来了,全国解放了。
共产党带来的是个怎么样的好日子啊!斗地主,分田地,分房屋;家家吃饱饭,人人穿暖衣。那日子真如歌里唱的:“嗨啦啦啦嗨啦啦!天空出彩霞啊,地上开红花呀……”那一天,父亲把我堂兄领去交给土改工作队,对他说:“当年我娘老说我们冇大,才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新中国来了,共产党让我们吃饱穿暖了,新中国就是娘,共产党就是大!要孝顺娘、孝顺大啊。”
就这话,我堂兄当了十几年的村党支部书记。
父亲这样说,他自己也这样做。父亲认定跟共产党走,对党忠诚,前途有希望,就事事争先进。那几年,他做出许多看似平常实则不平常的事:比如向工作组提出自己不要分房,把地主的房子让给更穷更需要的人;比如把道冠、道袍一应做道士的器物上交工作组,从此金盆洗手;比如每年都给政府纳全村最多的田粮,自己没粮瓜菜……
父亲表现得更积极,他做了两件轰动全村、大义灭亲的事:一是他一堂侄在农业社的养鱼塘里钓鱼,父亲劝阻不听,一气之下把他扔入鱼塘中,结果房族人都骂父亲不认姓族不认亲。二是父亲的另一个堂侄在背后骂农业社,被父亲打了一巴掌。结果他们家人来闹,说他把侄子耳朵打坏了,讹去100 元钱的医药赔偿费(那时的钱,100 元钱能买一间屋)。这事虽说让父亲在族里受气,却让他在外面声名大震。
父亲更受领导器重了。当年莫区书(虹桥区委书记)一家就租住在我家新建的屋里,和父亲很讲得来。农活上的事,总找父亲商量。父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无论犁田耖田耕田,村里数第一。插田更不用说,别人用绳牵,他不用绳牵也插得笔直,一天还能插七分田,虹桥全镇无人可及。农活上的事,父亲当然是活字典。莫区书推广新技术、推广新品种等等,也让父亲先试验。比如新中国成立前都种间作稻,就是先种早季稻,再在早季稻中间插晚稻。这样稻的间距大,两季稻的产量都不高,一季稻亩产一二百斤。新中国成立后推行一季一季种的連作稻,产量可翻番。可许多农民不习惯、不接受。莫区书就让父亲队里先种,种好了再号召全区农民代表来参观。农民们从未见过这么密的稻秆、这么粗的稻穗,一下子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了,连作稻一下子就在虹桥全区推广开了。又比如号召选种、推广水稻新品种,也叫父亲先试验。父亲就经常下田捋谷种,又把这些谷种分门别类地装在玻璃瓶里,贴着标签,到时候分田试种。小时候,我经常帮着做这些事,觉得很神秘。
就这样,父亲成了全区的农业科技带头人。经常和县(区)农技站的干部联系,逢年过节,都有区干部、农技站干部来我家拜年、送对联。有一副对联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任劳任怨,甘为群众当牛马;老实忠诚,愿做党的好儿郎”。那一年,虹桥区评三大英雄,即:少将罗通,老将黄忠,女将穆桂英。父亲被评上“老将黄忠”,他的光荣头像与“少将罗通”“女将穆桂英”一起被画在虹桥镇西横街的一面大墙上。父亲的头像下面写着:老黄忠刘吉如。
老黄忠的大号,就在虹桥镇上传开了。别人说我父亲的名字,只说老黄忠,谁都知道是刘吉如。
后来,父亲的待遇也变了,被区里抽调到钱家垟镇农场当技术员,且准备转为行政脱产干部,已报上面审批。可不久,父亲却把这个机会给弄丢了,原因是不肯讲假话。
事情得从县现场会说起。
那次会议是在虹桥区的某个乡里开的。县领导带全县(区)、各乡来的代表参观了该乡的仓库丰实(稗谷堆的)、稻谷丰收(几亩田合并的)现场后,要各地报当年的水稻产量。那是地地道道的“放卫星”啊。产量越报越高,从每亩五百斤、一千斤加到一千五百斤、二千斤……到场的县领导大喜,问莫区书,虹桥区的总产量几千斤?莫区书沉吟半天,说:“产量这么高,恐怕有问题。”县领导不爽,点父亲的名,说:“吉如同志,你是土专家,你说一亩田能打几千斤?”父亲此时早已对各乡各队昧着良心唱高调心中不安了,这时惴惴地说:“我看,我看……能保证亩产七百斤……就好。”
县领导当场变了脸,拳头在桌上一捶,说:“想不到你老黄忠也说落后话,当大跃进的绊脚石嘛!”当场,我父亲和莫区书一起被拔了白旗。会上还宣布,除名刘吉如的农场技术员职务,回村当农民去。
快到嘴的鸭子却飞了!
父亲于上世纪80 年代末去世。去世后,我在他的衣柜里掏出一个布包。包里有两件东西:一件是1959年温州专区公署颁发给他的地区级劳动模范证书。另一件,是1951 年土改工作队写给他的证明书,证明书写着:“收到刘吉如道冠、道袍、道靴各一件,罗盘、铜剑、锣鼓各一副,手抄本《道德经》一本。证明刘吉如已与迷信职业划清界限,是个忠诚老实的农民……”
哦,这是一位农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的忠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