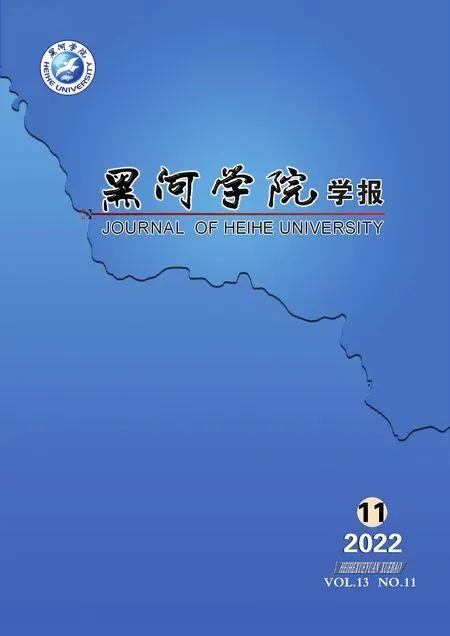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超时代性“典型”
——以《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为阐释中心
赵书豪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典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方法论之一。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在文学批评史上对“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概念界定与关系阐述一直是言人人殊。旷新年对“典型”概念的变迁史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指出“典型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来自西方”,但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早直接使用“典型”和“典型人物”这个概念的是鲁迅”[1]。而典型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发展要到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胡风、周扬等文艺理论家对其进行了再表述,将典型放于个性化、特殊性以及阶级性的范畴内进行考察。20世纪40年代,典型理论被纳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探讨中,文学作品要凸显英雄典型,进入到革命叙事中去。十七年时期,典型理论从革命叙事走向阶级评定,周扬提出“典型是代表一个社会阶层,一个阶级一个集团,表现他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把典型问题,当作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党性问题,不创造典型就是政治不行”[2]。阶级化之外,还有以群的典型之“个性与共性”论,李希凡的“典型新论”,何其芳的“共名说”。到了新时期,随着文艺思想的调整,“两结合”和“三突出”等创作方法受到否定,对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进行了再次思辨,其中李陀提出“以一个恒定不变的定义去解释、限定、约束处于无限生动活泼的发展中的现实主义,显然是不适合的,是违反历史的辩证发展的”[3],以及吴亮的“新典型观”,刘再复的“二重性格组合”对“典型”概念进行解构。
立于足下,我们当以历史的意识与发展的自觉将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放于文学发展的坐标中重新探讨,试图打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也‘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从开始到发展、深化阶段也是‘走俄国人的路’”[4]的圭臬,构建融入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借“创”的担当,“美”的指向,发掘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并以之催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且不囿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当代文学史中,提到现实主义作品创作,“陕军”创作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沿着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路遥、陈忠实、陈彦等人逐渐将现实主义深化,不论是“民族的秘史”,还是“为小人物立传”皆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空间的文本叙述中呈现出超地域、超文化、超阶层、超性别、超时代的历史变革期的矛盾对立统一以及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生命自觉。《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所承载的社会历史不同,所反映的现实矛盾冲突不一,所塑造的青年斗争形象各异,关照文本看到异中之同的是《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中历史变革期引发的社会矛盾均具有超时代性“典型环境”特征,具体的社会矛盾有别,但基于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反映体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同样,在这种超时代性的“典型环境”中活跃着超时代性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依于其“典型环境”展示出人性的某种稳定特质与恒常态势。以二者文本中的历史断层期与变革期矛盾对立统一、青年一代生存平衡的构建为中心,具体阐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超时代性,从而呈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互渗互构中所达成的现实主义大书写。
一、历史变革期人类生存矛盾的对立不统一——超时代性的“典型环境”
历史的变革期与断层期最突出的主题之一是新与旧的对立冲突,外在环境的突变对个体及群体造成较大冲击。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集中的两次新旧对立思想迸发期是“五四”思想大解放时期及“二次思想解放”,“二次启蒙”的新时期。事实上,历史变革期是带有觉醒意识的悲剧时期,“当新方式逐渐显露, 旧方式还仍然存在着。面对尚未消亡的旧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内聚力,新方式的巨大突进最初便注定要失败。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5]。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进程中前进的每一小步,都势必要经历拔毛断喙的阵痛,遵从马哲范畴的矛盾对立统一。相对而言,从文学文本来看,恰恰是这种“拔毛短喙”阵痛引发人类情感的对立冲突成为每个历史变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大书写。个体短暂的生命历程沉浮在历史进程中,似一叶扁舟,历经一浪又一浪的对立冲突延续其生的可能性。
处在历史变革期的伟大现实主义书写会将这种“典型环境”“再现”到文本当中,“典型环境”的现实记忆事实上是指向未来的,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认识,也表达了我们所希冀的未来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典型环境”是超时代性,现实主义作品是背负历史朝向未来的大书写。《白鹿原》文本的时间坐标是20世纪上半叶,《平凡的世界》的时间坐标是1975—1982年,时空范围大小有异,相同的是二者分别切中了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集中的两次历史变革与思想迸发期。从三秦大地上的乡土刻画中,我们析读现实主义作品中“典型环境”的超时代性特征。
《平凡的世界》百万字的卷幅“全景式”表现了文革结束前后双水村一带农村社会生活的变迁。社会主义艰难曲折的探索期,“公社”的生产方式带给人的莫属“饥饿记忆”。孙少安、孙少平以及双水村的大部分人是拥有“饥饿记忆”的一代人。少平求学时,“菜分甲、乙、丙三等”,“主食也分三等”[6]4,当然,可以分等级的不只有饭菜,“饥饿记忆”里是“阶级记忆”。双水村的生存层次是以阶级划分的,双水村外的城里也具有阶级划分层,每一个阶级层之内,一个阶级层与另一个阶级层之间均有着较为统一而稳固的秩序,几乎没有跨越阶层的可能性。在历史的长河里,阶级紧束型的社会环境并不陌生,近在一个世纪前,鲁迅指出“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一级一级制驭着,不能动弹”[7]。阶级性在任何一个现有的社会形态中均是普遍性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阶级性开始紧收,阶层固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变革因子,社会变革因子大量汇聚引发历史变革期。从社会主义探索期的“公社”,“农业学大寨”到文革结束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阶级叙述由紧束状态逐渐开放,呈相对自然状态,阶层开始流动。以历史的意识来看,历史变革期是社会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动态平衡。放入文学文本中看,社会的矛盾对立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典型环境”,这种环境中所塑造的矛盾冲突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公社”“农业学大寨”是具有唯一性的时代符号。但其促生的“饥饿记忆”与“阶级记忆”是超越时代的。“饥饿记忆”与“阶级记忆”在人类发展史上勾连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由此使得关注社会现实的“典型环境”文本能够跨越历史的长河常谈常新。
紧随《平凡的世界》之后的《白鹿原》同途同归,在80年代的“方法年”与“观念年”浪潮之下,陈忠实延续着陕军的现实主义笔法,竖起了当代文学的一座高峰。关照文本,我们会发现《白鹿原》不同于《平凡的世界》的是,“陈忠实比其他作家更早就意识到把现实主义的批判反思引入对历史的思考”中去[8]。宗法秩序统治下的白鹿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前后经历了清朝的终结、袁世凯的复辟、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发动政变、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这半个世纪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半个世纪,是历史的断层期。顺着近代革命史,可以发现,我们的革命在一次次失败与摸索中迂回前进,在整个大的历史图景上,社会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呈现动态平衡的态势。而陈忠实的着笔点是这一场场大大小小战乱,种种社会矛盾对立冲突期原乡秩序的瓦解,一次次政权更替下原乡三代人的生死叛离。从“交农运动”的鸡毛信到掀起“凤搅雪”的“农讲所”到天福贤与黑娃的“鏊子”戏台再到白孝文胡乱处死“反革命”黑娃的临时戏台,这种动乱的、断层的“典型环境”中有一种较为突出的记忆,即“战乱记忆”。“鏊子说”“风搅雪”“农讲所”是白鹿原的战乱记忆符号,而这个“战乱记忆”如何构得上“典型”呢?纵观人类发展史,历史断层期与社会动荡期大概率是滋生伟大作品的温床,在社会矛盾剧烈对立时,整个社会环境在主要社会矛盾冲突时是被立体凸显出来的,“白鹿原”就是那个被画了高亮的立体凸显环境。当然,白鹿原之为“典型环境”不仅仅因它具备“这个”的唯一性,构成它超时代性“典型环境”的最大一个原因是历史断层期的“战乱记忆”是一种背负历史朝向未来的大书写,它立于当下而不束于当下,具有永恒阐释的生命力。
二、历史变革期人类“求变”“求新”的生命自觉——超时代性的“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依托于“典型环境”而存在,如上论述,现实主义中的“典型人物”概念在发展中被持续阐释。不论是怎样的“典型人物”,典型阶级代表,典型性格代表,典型类型代表,最终的落脚点要归为“人”。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莎士比亚与巴尔扎克以高度评价,认为“在他们阅读过的欧洲历代文艺作品中,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艺术掌握世界的卓越高度”[9]。存在于莎翁作品中的人物“典型”绝非单一的阶级代表、性格代表、类型代表,而是“已经穷尽整个人性的方方面面,已经做过最高、最深的发掘”[10]的“典型人物”,这种“典型”特征既呈现出时代性的印记,又具备超越时代性的特质,其本质上包含了具有一定稳定性、恒常性、遗传性的人性力量。当然,迄今为止,不论从自然科学角度还是社会科学角度,人性的丰富性表达均无法被穷尽。正因此,文学的长河里接续活跃着无数鲜活灵动的人物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不囿于文本所依托的时代的,它以超时代、超地域、超文化的丰富人性担当“典型”。
在《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群体是引人注目的存在。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青年群体在面对历史变革期社会矛盾的对立冲突时,显示出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绝对意志,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生命自觉。事实上,青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一个背负“历史”朝向“未来”的群体。这里的“历史”当指其背负的文化遗传因子、阶级遗传因子、环境遗传因子等,这个“历史”是不可控的,源自祖辈的,源自社会的影响合力。而青年所朝向的“未来”当为人类生存平衡构建的生命自觉。通过细读两部作品,体味历史变革期一代青年人“求新”“求变”的生命自觉,以及拥有这种“生命自觉”的“典型人物”的超时代性特征。
《平凡的世界》在读者群热度远远高于在评论界热度现象的出现,多源于少安少平兄弟的“求新”“求变”精神契合了任一时代青年人的精神旨归。少安身为长子,需挑起长兄的担子,“帮助父亲养活一家人,而且要对少平和兰香的前途负起责任来”。生活的重负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四下铺盖,家里一穷二白的一间土窑,姐夫王满银“走资”被拉去改造,对青梅竹马的润叶求不得。重压之下,少安有着青年人固有的倔强与“求变”本能,他相信“一旦有了转机,他孙少安还会把这个家营务得更好;他在这方面雄心勃勃……”[6]145。改革开放后,少安率先领导生产队实行责任联产,随后进城拉砖建窑烧砖,凭借勤奋与冒险精神成为公社的“冒尖户”。同少安不同,少平是在艰苦的生苦条件下接受完高中教育的青年,是一位具有“混合型的精神气质”的年轻人。他有两个系列的精神思想:一个是“农村的系列”;一个是“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6]391。这种混合型精神气质与较为全面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不再像哥哥少安一样认定阶层的不可跨越性,追求县改革委副主任田福军的女儿田晓霞,“不安分”的渴望外边的世界,从漂泊的揽工者到正式的建筑工人再到一名优秀的煤矿工人。少平始终在“求新”“求变”的内在驱动力下,企望构建属于他这一代青年人的生存平衡。于青年人而言,这种精神是“生命自觉”,这种“典型”是可跨越时代而存在的,这也是《平凡的世界》在当下仍然被人作为奋斗者经书的合理性之所在。
将时间的坐标向前滑动六十载,关中白鹿村那些原上儿女亦上演了一番可歌可泣的“求新”“求变”的大胆“叛离”。宗法秩序与革命现代性的对立冲突,使得白鹿村里的第三代人无法接续父辈的生存方式继续生活,他们需要在承继与叛离中构建新的生存平衡。白鹿原上的第三代人中,有不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白灵与鹿兆鹏,接受过革命现代化教育的二人在宗法传统与革命现代性的冲突夹缝间毅然决然走到革命中去,以决绝的态度叛离宗权,叛离父权。有不束缚于阶级性的“造反者”黑娃,黑娃不似白灵与鹿兆鹏,未接受过正规的革命现代性的教育,从小以寄居者身份游离于白家上下的记忆,使得黑娃自小便反感于白嘉轩“挺得笔直的腰”,“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情”以及那“使人联想到庙里神像”的“眼泡皮儿”[11],对压制者的反叛,对主仆等级关系的反抗源于黑娃个体生存的生命自觉。还有挑战宗法妇道观的大胆女性田小娥——“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12],拨开男女性别场域的划分,单从人的本能来讲,田小娥是在面对宗法规约与人的本能情欲的冲突对立中,释放出人类构建生存平衡的生命本能。在原上第三代人中还有一位彻底的“离经叛道”的“逆子”——白孝文,这位白家长子,白鹿宗族的继承人一反父亲白嘉轩的宗法规约,经历了“野狗分尸”的生死之感后,成为以左右逢源为生的历史投机分子。历史的断层期,一代白鹿儿女以青年人“求新”“求变”的生命自觉探索着变革时代的生存道路,演绎着一场浩浩汤汤的生死叛离。“白鹿儿女”不仅仅是20世纪前半叶那片原上的儿女,在过去的某场历史变革中出现过,也具备出现在未来的某个变革期的可能,故这一“典型”具有超时代性的特征。
三、不囿于时代性的现实主义大书写——两个“典型”的互渗与互构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将文学作品放于现实主义创作范围内,置于欧洲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论述的,两个“典型”的塑造主要针对无产阶级文艺创作。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开始纳入中国元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胜利,使得“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被赋予新的阐释意义。其中,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有关于两个“典型”关系的表述,认为两个“典型”之间是辩证关系,“典型环境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人物对环境又可以有反作用”[13]191-192,且典型环境“逼迫着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13]192。其两个“典型”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但将“典型人物”表达为“典型性格”进行阐述,这里的“典型人物”与“典型性格”可否对等,还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江守义基于文史论与文学创作解读“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关系时指出“在恩格斯那里,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内部问题,而是一个与作品的现实品格和历史品格息息相关的问题”[14],从这个层面上讲,两个“典型”之间的关系应在现实与历史两个坐标维度中进行考察。当下,我们谈论“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及二者间的关系均是将其置于现实主义创作之下进行讨论的,现实主义文本之外的其他创作中不能绝对说没有两个“典型”的存在,只是本文暂且不做论述。回归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具有超时代性特质的,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互渗与互构促生了超时代的现实主义大书写,体现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立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艺术魅力。
现实主义书写中,“典型人物”的存在须依托于“典型环境”,同样“典型环境”的意义须“典型人物”来赋予,两个“典型”不可割裂。我们谈两个“典型”具有超时代性的特质,并不意味着《百年孤独》的两个“典型”可以约同《白鹿原》的两个“典型”,这样降低了两个“典型”的包容度,也抹杀了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如果说,人的存在无法剥离环境而求得纯粹的个体独立,那么小说人物亦不可从文本环境中抽离出来单独作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多的是体现两个“典型”的互渗与互构,现实主义大书写里的“典型”该是并置关系,而不是前后或上下的位置关系,如“阿Q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而非“阿Q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或“阿Q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但归根到底是中国的”,不可偏颇,现实主义的胸怀当为构建立体环境中的人性永恒而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掘现实主义作品的超时代性特质,但不可否定其时代性印记,正是从这种时代印记中体味人类经历不同社会变革期的丰富性表达以及超越时代的“遗传性”记忆。
《平凡的世界》中,有两个主要的“典型环境”,社会层面上的“典型环境”是历史变革期,个体生存层面的“典型环境”是陕北乡野。历史变革期的“公社”与“农业学大寨”“城乡融合”是现代化进程探索期的印记,这种印记为少安、少平留下深刻的“饥饿记忆”与“阶级记忆”,陕北乡野的生活生产方式、礼俗习惯影响了少安、少平二人的行为方式与性格性情。少安少平一代人的“求新”“求变”,对未来生活的大胆想象与虔诚信仰,脱离历史变革期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场域是找不到落脚点的。
《白鹿原》的历史图卷较《平凡的世界》更为宏阔,一片原三代人半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与生死叛离。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白鹿原》中两个不同的“典型环境”所催生的两个不同的“典型人物”,一个“典型”是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原上第二代人,宗法秩序下崇于“耕读传家”的“仁义白鹿村”子民;另一“典型”是以白孝文为代表的原上第三代人,革命现代性中的“叛离”青年,“叛离”祖宗之法,“叛离”父母之命,“叛离”宗法妇道,“叛离”主仆阶级,可以说,这里的环境“典型”塑造了人物的“典型”,人物的“典型”又赋予环境“典型”以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相建构的,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无法“立”起来,而任何一方的不真实,都会出现文本内容及结构的牵强附会,这也正是现实主义书写的一个难题,因其“典型环境”本质的真实性是决定“典型人物”塑造成功与否的前提和必要条件”[15]。兼顾两个“典型”的“真实性”及二者之间的契合,实为不易,可贵的是,“陕军”现实主义作品极为注重“典型环境”的立体性考察与“典型人物“的丰富性表达,柳青的《创业史》如此,《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亦是如此。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需要被持续阐释,以往附着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中的阶级性导向已然不能满足当下的文艺需求。我们不能将两个“典型”钉上阶级性的木板上置于历史的角落,而是要看到两个“典型”内含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生命力。现实主义创作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立于时代而又超越时代的书写,对人性的丰富性表达以及对环境的立体性考察是两个“典型”的突出特质。同时,两个“典型”之间互渗、互构促进文本的“真实性”表达,催生现实主义大书写。关照当下现实主义创作,似乎缺少一种现实主义大书写的力量,可能“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仍然未走出去革命化叙事后的再阐释困境与书写者禁忌,但对现实主义作品评论而言,现实主义创作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之间是需要持续阐释的一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