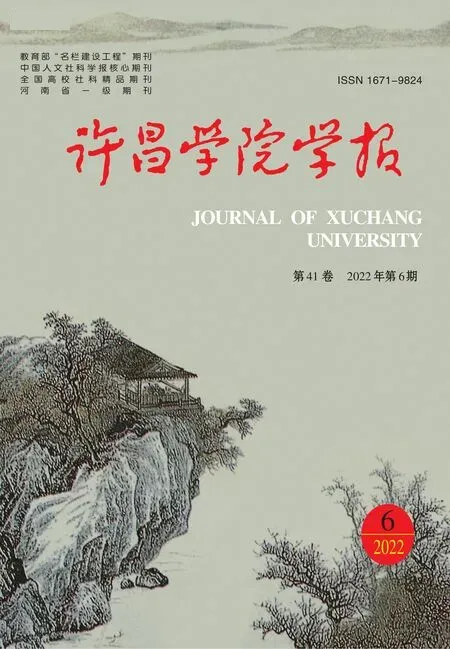《乡村医生》与《药》的意象分析兼及启蒙困境
谢 占 杰
(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鲁迅,其国际性文学大师的地位和影响都是公认的,对他们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成果亦汗牛充栋。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刘小枫在其专著《拯救与逍遥》[1]、高旭东在其专著《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参见第五章“中西文学与哲学的个案研究”)[2]中,都从宏观角度涉及了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有诸多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对二者思想上、艺术上的异同做了深入探讨,也有就二者单个作品开展的比较研究。以上数量颇多,难以一一统计。但尚未见到把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与鲁迅的《药》放在一起进行的比较研究,这是选择此论题的一个缘由。
就对人类生存的关切而言,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发展、文明的提高从来都不是直线式的,愚昧总是与人、与人类相伴,而在不同时代,也总有先行者走在前列,为人类的幸福、尊严、善和正义不懈追求、执着探索。无论是卡夫卡还是鲁迅,可以说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像医生一样,探讨社会的病源,寻找良方。依此来看,在《乡村医生》与《药》这两个短篇中,“疾病”“医生”和“药”等意象的内涵指向、人物带有悲剧性意味的遭遇,都体现着两位作家对生存困境的关切,内在构成了两位作家的精神实质以及整个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底,有着深沉的启蒙意味。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对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够,这是选择此论题的另一个理由。
本文拟通过平行研究,对两部作品中出现的相似意象的内涵展开分析,在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两位作家的精神实质及整个文学创作的思想根底,并对启蒙困境等问题略陈浅见。
一、“疾病”“愚众”意象及其意蕴
无论是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还是鲁迅的《药》,故事都很荒诞,色调都很灰暗。《乡村医生》写一个乡村医生在天寒地冻的时日到十里外的村子里去给一个孩子看急诊,结果没有治好孩子的病,自己却迷失在雪原上,再也回不到家了。《药》采用双线叙事,一条明写华老栓迷信“人血馒头”能治肺痨,于是花干家中积蓄为儿子华小栓换来“灵丹妙药”,结果儿子吃后还是死了;一条暗写觉醒者夏瑜为救治愚昧、唤醒国民而奋斗,却反被出卖遭砍头,鲜血被制成“人血馒头”。两部作品含有大量意象,广泛运用象征手法,由此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尤其是“医生”和“夏瑜”两人作为“觉醒者”的悲剧令人深思。在意象的选择上,两部作品有相似之处,本文主要讨论那些指向启蒙困境的意象,它们涉及“疾病”“愚众”“启蒙者”,他们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内涵有着较强的一致性。
(一)与“疾病”相关的意象
与“疾病”相关的意象主要是《乡村医生》中的“美丽的伤口”和《药》中的“痨病”。二者作为疾病有着表面的相似性,内涵上又具有相关性,两者都属“身体疾病”,但都另有所指,即“精神疾病”。
在《乡村医生》中,医生发现孩子的伤口脓肿严重,上有蛆虫蠕动,认为这孩子要毁在这朵“奇葩”上;而孩子则说:“我带着一个美丽的伤口来到世上;这就是我的全部装备。”[3]109如何理解“美丽的伤口”这一“疾病”的意象,是进一步探讨如何进行救治的关键。不妨把孩子的“美丽的伤口”看作人与生俱来的通病——“欲望”的象征,这就为我们理解小说中孩子的“病”提供了线索。在医生看来,人人都是带着“美丽的伤口”来到世上的,人人都有对生活的强烈欲望,尤其是生的欲望。这欲望包含了诸多可厌的丑恶,就像那些蠢蠢欲动的蛆虫,但它也包含着善和美,像盛开的花朵,因此医生说欲望是一朵“奇葩”。人身体上有疾病,医生可以想方设法救治,但人若失去活下去的信心,失去了信仰,一心想死,就不是一个医生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医生感到无力拯救这个病孩,就是因为他想死,想死意味着他对生失去了希望,而这才是他真正的病。
《药》中华小栓的疾病是“痨病”。在过去“肺痨”是不治之症,是疾病中的重症、恶疾。华小栓身患“痨病”,表面意思是患上了难以救治的身体疾病,象征的意思是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精神痼疾。文本写到华小栓的病况:他吃饭时也大汗不止,连“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起,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4]14,还经常不住地咳嗽。人的求生欲望是天生的,即使是孩子也能意识到这种病的严重危害,因此华小栓乖乖吃下了父母为他烤好的“人血馒头”。作为孩子他不知道如何救治,他的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但作为父母,已经是成年人,却选择让孩子吃“人血馒头”来治病,其愚昧无知便不可原谅。那么,孩子的病怎么治,谁来治,便成为问题的症结。文本重点是写那些大人的所作所为,由此来揭示“愚众”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精神“恶疾”“痼疾”——愚昧迷信、麻木自私、冷酷残忍。
(二)与“愚众”相关的意象
两部作品中“愚众”的意象是“无名的众人”,都重点揭示了“无名的众人”的“疾病”。在《乡村医生》中,孩子是无名的,他的父母、姐姐、村子里的长老、合唱队的学生及带队老师、牧师等,都没有名字。这暗示了这些人人数众多,且都是“病人”,他们患的“疾病”也都一样。首先是互不信任。医生自称是在这个地方行医多年的老医生,但当他要出急诊时,村子里却没有人愿意借给他马;他给孩子看病时,孩子不信任他,他认为孩子没有病,孩子的家人极为失望,认为他没有尽到职责;最后,家人以及村里的长老们扒掉医生的衣服,把他抬到病孩的床上,逼他非得给孩子诊治,这期间一位老师还带着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在房前唱歌。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场景,暗示着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因而无法沟通,陌生感、疏离感使人陷入孤独、痛苦的处境之中。其次是信仰的丧失。而这一点才是病根。文本中医生说,这地方人们“已经失去了旧信仰;牧师坐在家中,撕着一件又一件弥撒服”[3]109。显然,人们包括圣职人员都已经失去了对信仰的坚守。特别是牧师,他们的职责是通过让人树立信仰不断克制欲望,获得生存的精神支撑,但他们却放弃了自己的职责。而周围的人,因为信仰的丧失,失去了爱心,竟要求一个世俗的医生去完成不属于他,他也不能完成的工作。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上帝的信仰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借助信仰他们才能相互信任,相互帮助,从而团结在一起,在对苦难的忍耐中克制欲望,等待救赎。而这些“无名的众人”恰恰因为丧失了信仰,才彼此互不信任,因而带来了生存的痛苦。文本中老师带学生合唱队唱歌的场景非常富有讽刺意味,歌词是:
脱掉他的衣服,他就会治病,
他若不治,就把他处死!
他不过是个医生,不过是个医生。[3]109
这显然是对教堂中祭司(或者拉比)带唱诗班孩子唱圣歌的一个戏仿。教堂的肃穆庄严、圣歌的神圣美妙在此成了病床前的滑稽表演,卡夫卡借此透露出对人们失去信仰的嘲讽。
在鲁迅的《药》中,“无名的众人”这一群体同样人数众多,尽管他们身份各异,但“精神痼疾”却相同——愚昧迷信、麻木自私、冷酷残忍。他们和《乡村医生》中的“愚众”一样,没有具体的姓名,都只有某种代指,包括在镇子上开茶馆的华老栓一家、常来茶馆闲聊的客人、观看杀人的看客、杀人并卖“人血馒头”的满脸横肉的康大叔、告密出卖亲人换取利益的夏三爷、一心想着从狱囚身上榨取油水的红眼睛阿义等。在《药》中,鲁迅不是要揭示吃“人血馒头”治病是否科学,而是要通过这一事件展示那些参与其中的人的作为和心理,进而揭示在那个时代还有那么多的底层民众如此愚昧无知。更可怕的是,“病人”所吃的“人血馒头”蘸的是觉醒者的血,而这一觉醒者恰恰是想救治他们的病,让他们摆脱非人的生存处境,过上人的生活。然而,这些“无名的众人”没有“人之为人”的基本认知,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也没有同情心。华老栓愿意花干积蓄去买“人血馒头”,自然就有人去做卖“人血馒头”的勾当,而那些看客把看杀头当成平庸生活中可以热闹一回的大事件。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都与己无关。更典型的是康大叔、红眼睛阿义、夏三爷之流的人,不仅愚昧无知,还阴暗狠毒。“无名的众人”这个群体,陷入“被吃”与“吃人”的恶性循环里,身处悲剧之中而不自知。
从卡夫卡和鲁迅的关注点来看,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卡夫卡关注的焦点在个体,核心是信仰问题和对家园的追寻。医生救不了病孩,救不了那些患病的“愚众”,连自己也救不了。有病的不只是他人,医生自己也是病人。“猪圈”作为医生潜意识的象征,暗示着他的欲望有着多重矛盾。那里有“非尘世的马”,也有“胆大无耻亲吻女人的马夫”。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非尘世的马”是他的“超我”人格。马的出现帮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完成了大雪天也必须出急诊的愿望。马夫是他的“本我”人格,马夫的出现代表着他的“欲望”中还有着“性意识”。潜意识中的“马”——超我,按照理想原则带他去治病,而本我——“马夫”,按照快乐原则让他不想离开女仆罗莎,并在治病的过程中仍对她念念不忘。超我与本我构成了强烈的冲突,撕扯着医生的“自我”,使他深陷痛苦却无力自拔。这种无力救他人也救不了自己的景况,还暗含着医生深深的负罪感。
与此不同的是鲁迅的关注点,既有个体性,也有社会性,核心在社会的变革和人精神的觉醒。小说借助象征手法揭示现实人生的种种悲剧,促人警醒。除了揭示“愚众”的悲剧,《药》也揭示了社会的悲剧。可以说,有病的社会造就了有病的人,而有病的人又成为有病的社会延续的根基,这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在《药》中,有病的众人这一群体不仅数量大,而且范围广。他们没有是非善恶之分,没有信仰,愚昧、麻木而又凶残,只是卑贱地苟活着。他们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新思想,把新思想的传播者视为“疯子”。他们看似不是“恶”的制造者,但却是“恶”的帮凶,因此实质上恰恰是在制造“恶”。作品并没有对“病”的成因进行展示,然而我们不难理解“愚众”绝非自然形成。鲁迅深知,中国的历史上所谓行“仁政”的王道是从来没有的,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恶性历史循环中,普通民众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5]31(《灯下漫笔》)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统治者采取的大都是弱民、贫民、愚民政策,人民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奴役压迫,民众的愚昧是不容争辩而又令人痛心的事实。在此期间,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而传统的教育内容又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还有专门用来驯服和束缚民众的礼教文化,这些导致了民众物质上的贫困、精神上的匮乏、心智上的不健全和行为上的自私卑劣。因此,产生这样一个人性扭曲的社会是必然的。
两个文本中的“疾病”与“愚众”意象,有着紧密的相关性。表面上患病的是孩子,深层次来看,真正患病的是“愚众”,进一步说是社会及其文化。个人有病是无法避免的,但众多的人都患上了“精神疾病”则是危险的。两个文本揭示的正在于此,由此就有了启蒙的必要。
二、“启蒙者”意象及其蕴含的意义
与“启蒙者”相关的意象主要是“医生”和“药”。韦勒克、沃伦在谈到象征这个术语时说:“希腊语的动词的意思是‘拼凑、比较’,因而就产生了在符号及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进行类比的原意。”[6]203借助象征物与被象征物之间的类比关系,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加以论说:一个层面是把文本中的医生和夏瑜看成“启蒙者”;另一个层面是把现实生活中“医生—诊断病情—开药方”与“作家—揭示人、社会、人类的错误、缺点—探索出路”相类,从而把卡夫卡和鲁迅看成启蒙者。
(一)人物“启蒙者”——医生和夏瑜
在《乡村医生》中,“医生”既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又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身份,不妨说他也是救治社会病的“医生”,一个“启蒙者”。表面上,他作为区里委派的医生,恪尽职守,即使在雪原莽莽的大冬天也要外出看急诊;实质上,他深刻意识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并没有多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变得互不信任,误把精神疾病看成身体疾病,却非要一个世俗医生完成不属于他的使命。面对“愚众”,他认为:“开处方是件容易的事,而除此之外,还与这些人沟通就很困难了。”[3](108)医生的认知使他超越了“愚众”,成为“启蒙者”。作为“启蒙者”,他在思想上是信仰的坚守者,但在行动上却有着消极倾向。“非尘世的马”作为医生的“超我”,代表他的理想、对上帝的信仰。文本中,马的嘶鸣被医生看作“上天安排的”,这嘶鸣声正是医生心中理想、信仰的回响,透过来自上帝的声音,他透彻认识到世人的苦难,认识到世间信仰的丧失。在他打算自救时,两匹马忠实地站在原地,暗示着医生从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但他觉得无力救人,也无力自救。
《药》中的夏瑜形象,不同于《乡村医生》中的“医生”。“医生”是以“我”这一叙述者的身份进入到文本中的,是故事的当事人,“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有叙写,形象相对明晰完整。《药》中夏瑜的形象塑造是通过他人的叙述完成的,因而这一形象塑造得比较简单。但从文本要表达的内涵来看,夏瑜这一形象又极具分量。如,满脸横肉的康大叔说他:“这个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老头造反。”他对狱中牢头红眼睛阿义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4]17他遭到毒打却不怕,还对包括红眼睛阿义在内的人说可怜可怜。最终读者才明白,华老栓买的人血馒头,被杀的人就是夏瑜。夏瑜一句简单的话——“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足以说明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的进步性,说明他是有觉醒意识的“启蒙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怕挨打,不怕牺牲,他对愚昧的民众心怀悲悯,他要救治他们,救治社会。然而在有病的“愚众”中和社会里,他的思想、言论和作为反被人嘲笑,人被视为“疯子”,成了专制社会的刀下鬼,鲜血成了愚众用来制作“人血馒头”的材料。文本对夏瑜的侧面塑造,包含着深深的悲哀和同情,对“愚众”包含着深深的愤怒,也使我们对启蒙的困境产生深深的思考。
(二)作家启蒙者——卡夫卡和鲁迅
“医生”这一意象,不仅是文本中“医生”和“夏瑜”形象的象征,还可以看作所有有良知的伟大作家的象征,它也自然适用于卡夫卡和鲁迅。对两位作家来说,“医生”是他们所具有的决定性和根本性的精神特质,也构成了他们整个文学创作的思想底色。
就鲁迅而言,作为救治社会的“医生”,他诊断出社会的病根是国民精神的贫弱:愚昧迷信、麻木自私、冷酷残忍,由此构建出他“立人”的核心思想。“立人”思想成为他改变人、改变社会的良方,成为他批判愚众、批判社会的尺度,也成为他整个文学创作的根底。他弃医从文,就是想成为改变病弱社会的“医生”。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健全的精神,无论体格如何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深刻认识到,“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性,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立矣,则邦国亦以兴起”[5]291(《文化偏至论》)。正如钱理群所说:“对于鲁迅,以争取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反对对人的一切奴役为内涵的‘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为他的终身不渝的理想,以至信仰。”[7]12-13更为可贵的是,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他的眼光是国际性的。他对比审视了中西文明的发展之路后认为,之所以欧美发展强盛而中国却积贫积弱,根源在于前者做到了“立人”。他明确提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位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尊个性而张精神。”[5]298在鲁迅看来,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奴役抹杀了人的个性,导致人精神的缺失,从而奴性十足,没有个性。没有精神的独立,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只能盲目从众,最终成为麻木不仁、冷漠自私、是非不分的旁观者。《药》(包括《阿Q正传》《示众》)中那些观看杀人以自娱的“看客”、那些“无名的众人”都是此类。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荣,就没有精神上、思想上的创造和发展。在当时许多人寄希望于通过物质救亡图存之际,鲁迅看得更远,也更深刻,他认为只有“立人”才是根本。他所希望的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5]298在那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探求中国未来的出路,鲁迅无疑是其中思想较为深刻、影响甚为巨大的一位。或许对怎样“立人”,鲁迅并没有“灵丹妙药”,但他的“立人”思想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巨大的启蒙意义。人与制度是一体两面,人对制度的建立和运转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制度一旦建立,人又受制于制度,不同的制度塑造着不同的人。一方面,新制度的创立离不开有新思想、新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国民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特定的制度等多重因素造就的。因此,培育、造就新国民离不开以上重要因素的改变。或许,“立人”与文化创新、与体制变革、与生存条件改善同时兼顾而并行不悖,才是真正的路径。需要注意的是,鲁迅对国民性中那些丑陋一面的揭露,并不代表他对国民性中优秀一面的否定,他对那些愚昧、自私、自欺、无个性、无精神性的人的批判,也不代表他对国民中优秀的人的否定。他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赴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失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5]214(《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鲁迅真正担心的是那些觉醒者被遗忘的悲剧不断地重演。
作为象征意义上的“医生”,卡夫卡既在为那个时代诊断,审视人类、他人的病,也在审视自己的病。他看到人们失去了信仰,互不信任,甚至充满仇恨。从“开药方”的角度来说,卡夫卡感到无能为力,他不能为社会、为他人、为人类找到出路,连自己也觉得无路可走;但实质上,他和文本中的“医生”并不一样,他从未放弃对出路的追寻。作为个人,面对荒诞的生存处境,他体会到深深的孤独、恐惧和不安;作为犹太人,他体会到犹太人生存的艰难、痛苦;作为普通人,他体会到可能无缘无故就会遭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就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突然变成甲虫,或《审判》中的约瑟夫·K,一觉醒来遭到逮捕。但作为社会“医生”的卡夫卡仍然思考着关于“救赎”的沉重话题。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但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使犹太人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标识的族群。然而,生存环境的险恶迫使许多犹太人改信基督教。不管是因投机改变信仰,还是被迫改变信仰,都让卡夫卡感到愤懑。在他看来,信仰的丧失导致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导致犹太人之间发生分歧、分裂,也导致不同民族之间产生仇恨乃至仇杀,使人们生活在痛苦之中。他借助自己的创作,让人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谬丑恶,认识到自身的罪恶。他“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手法,将他作品中的世界描写得陈旧、腐朽、苟延残喘、积满灰尘。……这个世界的堕落触目皆是……上层权力和下层权力一样,都在残酷而恶毒地戏弄着它的牺牲品”[8]343。在一个信仰丧失的时代,“神恩”还会降临吗?人还能得救吗?卡夫卡受犹太教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尽管这个民族遭受了漫长的流离之苦,他们始终相信上帝会拯救他们,但前提是必须信上帝的义。但是,人生来有罪,人无法改变来自始祖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带来的“原罪”。“由于人自身罪性的局限性,不可能实现自我拯救,而须向上帝呼求,以得到上帝的救赎。”[9]237只有到了上帝“末日审判”降临之时,这一切才会有答案。但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犹太教与后来的基督教对此看法不同。基督教认为,救世主已降临人间,耶稣就是上帝派往人间的救世主。犹太教认为,当充满苦难、黑暗、混乱、疯狂、是非颠倒的现世终结以后,上帝赏罚善恶的时刻就会到来,一个新时代,由弥赛亚永远统治的光明国度终将建立。换个说法,基督教的救世主已在人间,而犹太教的救世主却永远在路上。卡夫卡的精神核心是以神恩之爱救赎世人,包括他自己。《乡村医生》及卡夫卡的其他小说如《城堡》《审判》等,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绝望、灰暗、丧失信仰、没有正义仁慈的世界,但对卡夫卡而言,他展示这样的世界恰恰是为了否定它。本雅明把卡夫卡的文学世界视为一面反射的镜子,在那里,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似乎变了形,怪模怪样,无法理喻,充满着丑陋破败,气氛压抑沉闷,对人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但同时,这镜子也是在警示世人,未来要远离里面被颠倒的一切[8]340。
要之,尽管卡夫卡和鲁迅对社会诊断出的病情不同,开出的药方也不同,但深厚的人文情怀及启蒙的精神实质却是内在相通的。
三、启蒙困境——启蒙者的“罪与罚”
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始终离不开人类思想的变化,离不开人的思考与探索。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代往往会出现一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或觉醒者,他们往往不遗余力地想去改善人的生存处境,启迪人们摆脱愚昧,走向光明。但他们的思想即使具有革命性、指导性,也不意味着能被人理解接受,相反他们常常遭遇到误解,不被信任,甚至常常受到威胁,遭到迫害,最终成为牺牲品。这种觉醒者面对“囚徒”、有知面对无知、无路可走而又坚韧前行的景况就是启蒙困境。这种困境常常导致“先觉者”悲剧。这种悲剧,苏格拉底之死是最好的说明。苏格拉底一生“坚定地追求真理,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为确定的知识寻找基础。他也试图发现善的生活的基础”[10]28,但他最终却被那些无知的、误入歧途的人审判和杀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洞喻”也做出了预言[11]358-413。最早挣脱束缚来到洞外的“囚徒”,最早认识到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但当他们返回洞中去告诉那些一直处在“囚徒困境”中的人真相时,其结果并不是大受欢迎,而很可能受到惩罚。他们受到惩罚并非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他们以“有知”面对“无知”,这“有知”就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文本中,作为先觉者的“乡村医生”和“夏瑜”,遭遇的正是这种困境。尽心尽责的“乡村医生”明白,孩子也好,众人也罢,他们真正的疾病是丧失了信仰。他知道他也许能够医治人身体上的疾病,但却治不了人精神上的病,他不被信任,不被理解,最后落得个流浪雪原无家可归的下场。而那个告诉众人“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夏瑜,想救治那些无知的愚众,却被众人视为疯子,最后被害、被吃、被遗忘。那些数量巨大的“愚众”,就像洞中的“囚徒”,他们已经习惯了“黑暗”和“幻影”,对“光明”和“真实”无法接受。而那些不愿接受真知真相的“囚徒”,他们的所作所为便会产生出一种“恶”,这种“恶”就是一种“平庸的恶”。汉娜·阿伦特曾对“平庸的恶”做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在阿伦特看来,“平庸的恶”反映的既是一种人性的恶,又是一种体制的恶,恶的平庸性是专制政府对良知的扭曲,是极权社会对罪恶的麻木。极权社会把每一个人视为齿轮、螺丝钉,“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可报废的,而这又不会改变整个系统”[12]24。这种体制之恶造就“无个性的”“没脑子的”人,迫使并让他们习惯于按照命令、规范或律法去行事,无须对所行之事的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长期的规训、惩罚、奴役,使众人逐渐习惯于将自己视为齿轮、螺丝钉,从而失去良知,放弃责任,没有了判断力。体制之恶扭曲了人性,也埋下灾难和悲剧的祸根。极权社会塑造出的庸众,其特征就是麻木盲目、卑鄙怯懦、冷酷自私。他们常常为自己能够为这个极权社会服务并得到肯定、获得利益、得到升迁而欣喜满足。即使犯下了罪,他们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有罪,而是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无辜的,自己仅仅是执行人,有罪的是领头者或社会。他们对“恶行”的容忍使“恶行”蔓延,导致社会成为一潭死水或一盘散沙,极具危害性。这种庸常的人性之恶常常不那么为人所憎恨,因为人们对这种恶的危害没有足够的认识。当体制之恶和平庸之恶结合在一起时,灾难、浩劫将无可避免。汉娜·阿伦特以希特勒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那些被审判的战犯为例对此做了极为深刻的思考[12]185-207。卡夫卡和鲁迅所揭示的这种人性的灾难、文化的灾难、体制的灾难,与汉娜·阿伦特所揭示的一样,这种灾难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不断上演,特别值得人们警惕深思。
作为“觉醒者”,鲁迅和卡夫卡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都想救救孩子,救救大人,救救自己,救救世界,并常常为自己不能兑现救人救世的承诺而深感痛苦。他们都对人、对世界充满着深厚的爱意,却在孤独寂寞中前行。他们不被人理解,不是因为他们有错,而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光芒让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觉得太刺眼。尽管二人探索的出路、开出的良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5]63(《记念刘和珍君》)的猛士。对卡夫卡而言,改变个人和人类尴尬而险恶的生存处境,没有什么比确立对上帝的信仰更为重要的。尽管他对未来感到失望,甚至有些绝望,但他“为了这个世界”,依然“可笑地给自己套上了挽具”[13]119。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被判决了,那么我并非仅仅被判完蛋,而且被判处抗争到底。”[13]52他以自己的作品向荒诞世界提起了诉讼。而对鲁迅来说,除旧布新、兴邦立国,没有什么比“立人”更为迫切和重要的。正如高旭东所言:“在他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改造国民性。”[2]110为此,他呐喊过,彷徨过,但从未放弃希望,也没有停止战斗。他希望“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17(《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正因为鲁迅的清醒与坚守,王富仁把他称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14]自序三。
无论是鲁迅还是卡夫卡,或者其笔下的清醒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他们都是有良知的“医生”,都在努力探索社会、人生的出路,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他们都想开启民智,也都可能遇到无罪而遭处罚的悲剧困境。由此启示人们,无论是减少还是消除体制之恶和平庸之恶,道路都极为漫长、极为艰辛,也常常带有悲剧意味。但无论如何,促使个人、社会或人类生活迈向更好,“医生式”的启蒙者将永不可少,也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