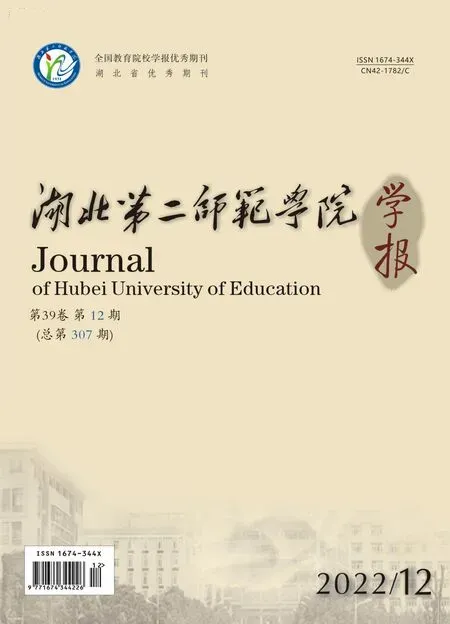《长生殿》“情在写真”的实现策略
戴 峰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院,武汉 430205)
《长生殿》传奇是清代戏曲的双峰之一,晚清曲论家梁廷楠认为:“(《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起俯首。”[1]《长生殿》主要表现安史之乱前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与离合之事。在洪昇之前,正史之外,无论是诗词,还是小说、戏曲,相关主题的作品可谓屡见不鲜。但在洪昇看来,这些作品对李、杨情感的处理都不能令人满意,因此,洪昇决定重新演绎这一“帝王家罕有”的“情缘”(《长生殿·例言》),使之更为合理和动人。梁氏所谓“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即是对此而言的。而《长生殿》取得成功的关键,用洪昇的夫子自道来概括,就是《长生殿·例言》中所说的“义取崇雅,情在写真”八字。
一、千回万转情难灭
《长生殿》是洪昇“盖经十余年,三易稿而始成”的心血之作(《长生殿·例言》)[2],在《长生殿》的第一出《传概》和最后一出《重圆》中,他非常清晰,也非常郑重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旧《霓裳》,新翻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无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长生殿》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化“长恨”为“长生”。在剧情的构思上,洪昇明确采用艺术虚构的方法,吸收了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的民间传说,给予了李、杨二人一个“仙圆”的结局。而这种安排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突显李、杨二人穿越生死的真情。在洪昇心中,这种可以长留万古的真情,与《牡丹亭》中“至情”的内涵是极为相似的。
在洪昇看来,天宝遗事虽然是传奇作家的“绝好题目”,但此前表现李、杨情缘的作品都至少存在两大缺憾:一是情节存在明显的硬伤。但凡处理不好马嵬之变中李隆基、杨玉环二人的表现,那么,他们此前的恩爱和此后的思念就都缺乏有力的支撑。此即《例言》中所说的“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元杂剧《梧桐雨》,在该剧中,当将士们要求处死杨贵妃时,且看李隆基和杨玉环二人的对话:“(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大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正末云)卿休怨寡人!”[3]人物性格前后的割裂非常显眼。而这也直接引出了第二个缺憾:“曲终难于奏雅。”(《自序》)由于马嵬之变的痛楚和伤心无法抹平,不仅使整个故事难以圆满收场,而且李、杨的爱情传奇也无法升华,只能在无尽的悔恨和伤感中结束,浪漫之调不得不转为变徵之声,“情在写真”的初衷自然也无法实现。
有鉴于此,洪昇大胆地摆脱历代史料和文学作品的限制,以更深刻的同情之心和更完整的艺术构思来重塑人物形象,极力突出李、杨爱情的至纯至美,并充分借鉴《长恨歌》后半段的艺术想象,赋予全剧一种浪漫的气质。
在洪昇笔下,杨玉环完全是一个才艺双全、单纯多情的女子。《长生殿·例言》说:“史载杨妃多污乱事。予撰此剧,止按自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而中间点染处,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若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览者有以知予之志也。”在《长生殿》中,杨玉环也像大多数女子一样,为爱情和命运担忧,“瞬息间,怕花老春无剩,宠难凭。……若得一个久长时,死也应;若得一个到头时,死也瞑。”(第二十二出《密誓》)剧中即便涉及杨妃与梅妃、虢国夫人争宠的情节,作者也明确将其定义于“情深妒亦真”(第十九出《絮阁》)。尤为重要的是,在马嵬之变中,她的表现真可谓勇毅坚强、情真意切。面对军士的威逼和君王的慌乱,她甘愿就死,以保君王和社稷:“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第二十五出《埋玉》)此后,杨玉环虽重登仙籍,但最大的心愿还是想与唐明皇重续前缘,“位纵在神仙列,梦不离唐宫阙。千回万转情难灭。”(第四十七出《补恨》)这样一来,作为艺术形象的杨玉环,其情其性不仅前后一致,其言其行也是感人至深。
同样,《长生殿》中李隆基的形象也非常完整、生动。他起初用情并不专一,虽钟情于杨玉环,但和虢国夫人有私情,也曾暗召梅妃,然而当杨玉环愤而自请斥放的时候,他幡然醒悟,甚至当面认错:“总朕错,请莫恼。”(第十九出《絮阁》)经此风波后,他用情日深。到长生殿七夕盟誓时,其情已臻真纯之境,连天上的牛郎和织女也忍不住赞叹。在马嵬驿,其拼死保护杨玉环的态度也非常坚决:“妃子说那里话!你若捐生,朕虽有九重之尊,四海之富,要他则甚!宁可国破家亡,决不肯抛舍你也!”“若是再禁加,拼代你陨黄沙。”(第二十五出《埋玉》)更为感人的是,杨妃死后,李隆基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哀思之中,他说:“是寡人昧了他誓盟深,负了他恩情广,生拆开比翼鸾凰。”“我当时若肯将身去抵搪,未必他直犯君王;纵然犯了又何妨,泉台上,倒博得永成双。”“如今独自虽无恙,问余生有甚风光!只落得泪万行,愁千状!”(第三十二出《哭像》)这就不仅完全避免了像《梧桐雨》那样的割裂,还不断升华了他的情感,显得愈发的真诚和浓烈,为最后的重圆做好了铺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剧作的后半部,李、杨二人已然卸去了皇帝和宠妃的身份,再无需担承过多的国家重任和指责议论,他们与普通人的身份差别几乎消失殆尽,原来的帝妃之情已悄然转换成了通常的男女之恋,作品通过《冥追》《闻铃》《哭像》《见月》《改葬》《雨梦》《觅魂》《补恨》《得信》等出的铺陈,反复渲染了二人天上人间的思念之情,他们的悔恨、悲伤、怀想和期盼,都显得极其真切和自然,每个普通的受众在细细地品味之时,都不难生出一种由衷的认同感和同情心。作品最后,李杨二人终偿夙愿,在月宫中永为夫妻,正如第一出《传概》中所言:“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庄子》有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4]或许这就是洪昇想要传递的万古情:唯其精诚,方能“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第一出《传概》)唯其朴素,才能“情留万古无穷”。就这一层面而言,《长生殿》的构思和策略无疑是巧妙和成功的。
二、别离生死同磨炼
但是,洪昇还清醒地认识到:“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自序》)因此,“情在写真”不能仅在相思言情、浪漫唯美上着力,而应更进一步,将演绎爱情传奇与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用“兴亡梦幻”来突显“长生”的艰难与独特,这也是《长生殿》实现创作初衷的第二个策略,即“乐极哀来,垂戒来世”。
在创作《长生殿》时,洪昇并没有忽略“天宝遗事”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特殊性,也没有回避唐明皇、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应负的责任。毋宁说,洪昇心中的万古情绝不是建立在虚幻缥缈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将李、杨爱情置于安史之乱的现实背景之下,用大量的笔墨表现了唐明皇种种失范的行为。剧中借郭从谨、李龟年、李謩等百姓之口,直接道出了对唐明皇的批判:“宠爱了贵妃,朝欢暮乐,致使渔阳兵起。”“弛了朝纲,占了情场。”“误任边将,委政权奸,以致庙谟颠倒,四海动摇。”(第三十八出《弹词》)此外,剧中还着意描写了贵戚的奢靡、权臣的骄横以及献果使臣的狂暴,对安史之乱的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刻画。
客观而言,洪昇对这段历史的反思还远未达到制度批判的高度,对李、杨二人也多有回护之处,但其传达出来的“兴亡梦幻”却别有一种沉郁动人的力量:一是非常契合清初广大汉族民众普遍的伤感和失落情绪,二是为李、杨的爱情传奇铺设了多灾多难的背景。后者尤为重要,因为在洪昇看来,李、杨二人既是安史之乱的引发者,又何尝不是安史之乱的受害者。堂堂的帝王和贵妃,在巨大的动荡中也无法自保,曾经朝欢暮乐的情侣,也不得不面对生离死别的痛楚。“可怜一对鸳鸯,风吹浪打,直恁的遭强霸!”“堂堂天子贵,不及莫愁家。”(第二十五出《埋玉》)面对这种巨大的反差,无论是当局者,还是旁观者,都不能不遽然梦醒,对“弛了朝纲”的恶果有了直观的认识。因此,一方面,洪昇发出了“古今来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长生殿·自序》)的感叹,意在总结“乐极哀来”的教训,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戏剧结构上,洪昇又巧妙地借助这一惊天的变故,使男女主角实现人格的净化和情感的升华,并推动剧情转向至纯至美的天上人间之思。因为经过“安史之乱”的劫难之后,李、杨二人可谓繁华落尽,心碎神伤,为曾经的“乐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天人两隔的唐明皇与杨贵妃,就像无数历经沧桑的普通夫妻一样,绵绵相思和重圆期盼就成为了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寄托。这种情愫也因沉郁动人而逐渐显出了典重和本真的意味,超越了一般“言情之文”的俗套,这恰如剧末所言:“把别离生死同磨炼,打破情关开真面,前因后果随缘现。”(第五十出《重圆》)
当然,为了使剧情的发展更为严谨、合理,也为了使人物性格的转变不显突兀、生硬,作者还多次安排了李、杨二人深深自责和忏悔的情节,二人情感之真诚和态度之谦卑,让天上的织女、嫦娥也颔首嘉许,这就是“一悔能教万孽清”(第三十出《情悔》)。于是,最终的月宫重圆就是理之必无,而情之必有了。对此,时人梁清标就曾明确赞许《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亭》”,洪昇深感欣慰,“以为知言”。(《长生殿·例言》)这说明,洪昇在创作和反复修改《长生殿》时,是有意接续汤显祖戏曲重情的浪漫主义传统的。不过,仔细辨析的话,二者的侧重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在汤显祖《牡丹亭》中,‘至情’的基础和前提是超越社会伦理规范的感性欲望,是作为本能的生命原动力,它可以超越‘理’的拘囿;洪昇《长生殿》则将‘情’的重点落实为夫妇之间的相互忠诚,以及‘臣忠子孝’这样的纲常人伦、社会规范。”[5]换言之,《牡丹亭》的“至情”,重在表现内心情欲的自由;《长生殿》中的“至情”,则重在揭示真心相守的可贵。前者偏重于文化启蒙,使人茅塞顿开;后者则落脚于人之常情,更容易让人感同身受。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洪昇之所以采取“乐极哀来”的编织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彰显生旦“离别生死”的曲折和痛苦,并为“终成连理”的结局服务的。这从洪昇对《牡丹亭》的解读中也可得到有力的佐证,他说:“(《牡丹亭》)肯綮在死生之际。记中《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自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能使赫蹄为大块,隃靡为造化,不律为真宰,撰精魂而通变之。”[6]这里的“赫蹄”“隃靡”“不律”分别指纸、墨、笔,而所谓“为大块”“为造化”等等,都是出神入化之意。可见,洪昇认为,《牡丹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情节的“死生之际”对生旦二人“灵根”“情窟”的张扬。因此,在《长生殿》中,洪昇将表现李、杨二人生死离别的《埋玉》一出,作为上下两卷的分割点,显然是刻意为之的。
三、两情坚如金似钿
追根溯源,洪昇之所以醉心于对李、杨情缘的演绎,十余年间乐此而不疲,是因为他认为,若以有情之眼观之,就能发现李、杨情事足够新颖特别。这种独特性,洪昇只是用“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一句来概括,所指还不甚清晰,而其好友吴舒凫则作出了精当的阐释,他说:“数百年来,歌筵舞席间,戴冕披袞,风流歇绝……汉以后,竹叶、羊车,帝非才子;《后庭》《玉树》,美人不专。两擅者,其惟明皇、贵妃乎!倾国而复平,尤非晋、陈可比,稗畦取而演之,为词场一新耳目。”[7]由此可见,《长生殿》的“情在写真”既非摹写一般的帝妃传奇,也不是描绘常见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演绎令人耳目一新的爱情奇缘。而为了突显这种独特性,洪昇所采取的第三个策略就是“专写钗盒情缘”,使之成为纷繁复杂剧情中的一条红线。
《长生殿》长达50出,以杨贵妃之死为上下卷的分界线,上卷重在写实事,将李、杨二人的遇合、定情与安史之乱的发生发展相结合,给人以跌宕生姿之感;下卷重在写幻境,对安史之乱的结局和影响只稍作点染,而主要表现李、杨人间天上的相思之情,舒徐婉转,凄恻动人。洪昇巧妙地用金钗、钿盒的合——分——合作为李、杨爱情发展的象征,将所有的情节贯穿起来,达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吴舒凫在评点《长生殿》时也敏锐地发现了洪昇的这一匠心,他在《重圆》一出的批语中说道:“钗盒自定情后,凡八见:翠阁交收,固宠也;马嵬殉葬,志恨也;墓门夜玩,写怨也;仙山携带,守情也;璇宫呈示,求缘也;道士寄将,征信也;至此重圆结案。大抵此剧以钗盒为经,盟言为纬,而借织女之机梭以织成之。呜呼,巧矣。”[8]虽然《长生殿》中金钗钿盒出现的次数远不止此,如《密誓》《冥追》《哭像》《改葬》等出中都有提及,但吴舒凫的见解无疑是精辟的,他所点到的《定情》和之后的“八见”也确实是李杨情感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
《定情》《絮阁》是剧中的第二和第十九出,金钗、钿盒在此期间出现了合——分——合的小循环,整体可视为李、杨爱情发展的开始。在《定情》中,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喜欢主要还是容貌,即“德性温和,丰姿秀丽”。他将钗盒赐予杨玉环时,虽然说是“与卿定情”,但其实是君王赏赐嫔妃的惯常做法,尚不是他的肺腑之言。而杨玉环则是喜忧参半,一方面“谢金钗、钿盒赐予奉君欢”,另一方面又“只恐寒姿,消不得天家雨露团”。这表明二人并非同心,也预示了二人的矛盾不可避免。果然,此后便接连出现了唐明皇与虢国夫人有染和暗中召幸梅妃的事件,杨玉环难抑伤心、悲愤之情,将金钗钿盒交还给唐明皇,“把深情密意从头缴”。而唐明皇也越来越感受到了杨玉环的真情和深情,也认识到了爱情的排他性,便连忙抛弃君王的高傲,真心地向杨玉环道歉,并请她“将钗盒依旧收好”,“重把那定情时心事表”。至此,李杨二人才真正成为心意相通、平等相待的爱侣。随后的《密誓》就成为非常自然的延伸,对二人“世世生生,共为夫妇,永不相离”的愿望进行了确认。
从第二十五出的《埋玉》开始,到第四十七出《补恨》,都可视为李、杨爱情发展的转折。在此期间,金钗、钿盒几乎不离杨玉环的左右,而由于人、鬼、仙的分隔,它们也成为了唐明皇苦苦思念的对象。当然,它们更是李、杨二人情比金坚的见证者。吴舒凫所说的“写怨”“守情”“求缘”等等,都是对杨玉环心境的准确揭示。在《冥追》《尸解》《仙忆》等出中,杨玉环不论为鬼为仙,都不忘将金钗、钿盒随身紧守,“定情之物,身不暂离;七夕之盟,心难相负。”在《补恨》一出中,当织女看到杨玉环将钗盒朝夕佩玩、念兹在兹时,这样说道:“你如今已证仙班,情缘宜断。若一念牵缠呵,怕无端又令从此堕尘劫。”而杨玉环则立即回应道:“倘得情丝再续,情愿谪下仙班。”“只求与上皇一见,于愿足矣。”精诚之情,可谓感天动地,使得织女也明确表达了成全之意。
从第四十八出《寄情》到第五十出《重圆》,是全剧的结尾,也是李、杨爱情发展的高潮。在道士杨通幽面前,杨玉环将金钗、钿盒各分出一半,请他交给唐明皇,“半边钿盒伤孤另,一股金钗寄远思。”当李隆基猛然看到当日的定情信物时,竟忍不住涕泗横流,“执钗盒大哭介”。最后,二人在月宫中重聚,钗盒情缘以团圆收场,“收拾钗和盒,旧情缘,生生世世消前愿。”可谓前后照应,似断实连。
从上可见,洪昇“专写钗盒情缘”的策略,既充分展现了人物情感的发展演变,也深化了全剧“要使情留万古无穷”的主题思想。正如洪昇的同学徐麟所说:“(《长生殿》)或用虚笔,或用反笔,或用侧笔、闲笔,错落出之,以写两人生死情深,各极其致。”[9]诚哉是言。
四、结语
《长生殿》传奇问世于清康熙年间,一经脱稿即轰动京城,“一时梨园子弟传相搬演,关目既巧,装饰复新,观者堵墙,莫不俯仰称善。”[10]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在评价此剧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其与《琵琶记》《西厢记》《牡丹亭》等名剧相提并论,认为其“藻思妍词,远接实甫,近追义仍;而宾白科目,俱入元人阃奥。”[11]但相关评析大多集中于结构、排场、音律等方面,而对其创作思路的发掘有所忽略。其实,《长生殿》之所以能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后出转精,卓然绝伦,在很大程度上是洪昇要通过李、杨情缘着意写出自己对“万古情”的独特理解。如果说,《长生殿》化“长恨”为“长生”主要是为了在剧情上翻空出奇,并突显李、杨情缘的纯度,而“乐极哀来,垂戒来世”主要是为了彰显真情的艰难,以增加李、杨爱情的厚度。那么,“专写钗盒情缘”则是对前面两点的具体化,并体现李、杨爱情的独特程度。三者相辅相成,融浪漫和现实于一体,从而使“情在写真”的主旨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使《长生殿》得以跻身于中国第一流爱情文学作品的行列,在精神上堪与《西厢记》《牡丹亭》等名剧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