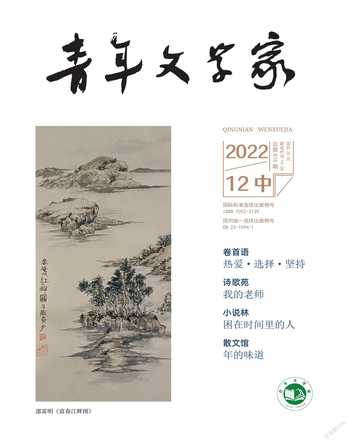用布鲁姆“诗的误读”理论探析宋诗的新与变
韩新一


“唐宋诗之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对宋诗的成就,各家说法迥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宋诗对唐诗进行了传承和突破,别开一路,展现了独特的风采。
江西诗派面对的情况是严峻的,唐诗种类众多,名家辈出,各类诗体、诗法已备极。“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姜夔《白石道人诗集自序》)宋诗一产生就处于唐人的阴影下,突破唐人的影响和包围成了江西诗派的首要目标。作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将诗歌引向前人的诗歌和书卷中,力图通过对前人作品的再创造获得新意。这使宋诗难掩其书卷气与苦寒气,使得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专于小处琢磨、下功、出新,使诗狭窄逼仄。但无论如何,他们终究突破了唐人的风格,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他对文学界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阐述了“诗的误读”理论。一方面,他着重于“前驱诗人”对“迟来者诗人”的压抑和影响,后进诗人总是被传统,即“前驱诗人”所支配,如何摆脱传统的阴影,减少自己的诗歌与前驱诗人的联系,另立新峰,便形成“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他认为,文本意义同作者写作文本的初衷未必完全吻合,由作者阅读时产生,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阅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写作也是创造意义。“诗的误读”的精髓所在,后进者对前驱诗人的诗歌进行再阅读,故意使意义偏离前驱诗人的本义,把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加以强化,使之形成自己的风格。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出了六种抵御前驱诗人影响的方法,称为“修正比”,包括“克里纳门”“苔瑟拉”“克诺西斯”“魔鬼化”“阿斯克西斯”“阿波弗里达斯”,其中部分观点与江西诗派求新求变有相同之处。
一、克里纳门与杜甫
克里纳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原指原子的偏移,布鲁姆用它借指后人对前人诗歌的有意偏移。宋朝诗人作诗多取法于唐朝,或白居易、李商隐,或贾岛、姚合,但值得注意的是,对诸如李白、王昌龄等盛唐诗人取法较少,反而对杜甫青睐有加。杜甫成为江西诗派甚至大部分宋诗诗人的学习对象,正是“克里纳门”中所说“诗人给前驱诗人定下这样一个位置,然后从前驱的诗的位置上偏转方向”(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唐诗流派众多,诗人如云,而选择杜甫,显然是对唐诗传统的有意偏移。“‘克里纳门’必须永远被视为仿佛同时具有‘有意的’和‘无意的’属性的一种行为。”(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无意的”便是制约诗人的各种客观条件,如理学思想的影响、造纸术的发展、言论的禁锢等等,这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诗人的主观想法。“有意的”便是诗人突破前驱诗人的意志和偏好,如江西诗派对唐诗的故意曲解,以及对老杜的喜爱。与此相反,宋人对其他诗人的认可则远远低于杜甫。“王荆公常谓‘太白才高而识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杜甫《杜诗详注》),苏辙便直接批评李白“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杜诗详注》)。偏爱杜甫便是第一次偏移。杜甫的诗,风格多样、变化多端,“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杜甫《杜诗详注》)。在体裁上,既有五言七言,又有连章排律;在题材上,既有抒不遇之悲、感国家之乱、叹百姓之苦,又有喜景色之丽;在作法上,既讲究炼字炼句,又追求情景交融。江西诗派对杜甫的学习是有选择的,在题材上多抒发个人感慨,少叙述民间疾苦;在作法上多炼字炼句、活句活典,少关注诗歌整体的内容和意蕴。正如钱锺书先生说的“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钱锺书《宋诗选注》)。这便是江西诗派的第二次偏移,重新定位杜甫的诗歌地位,从而使自己与杜甫分离。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补充道:“发现是一种限定,重新评价是一种替代,重现瞄准是一种表现。”(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通过这两次偏移,江西诗派对唐诗进行发现和重新评价,并对杜甫进行重新瞄准,对唐诗和杜甫有意误读,选取杜甫的部分特色进行自我强化,形成了新的诗歌风格。
二、苔瑟拉与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苔瑟拉,即对偶式续写,指的是迟来的诗人以续写的方式对前驱诗人似乎未完成作品所进行的补写,并使其臻于完美的艺术创造方式。“‘苔瑟拉’代表任何一位迟来者诗人的一种努力—努力使他自己相信(也使我们相信):如果不把前驱的语词看作新人新完成或扩充的语词而进行补救的话,前驱的语词就会被磨平掉。”(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后辈阅读前驱诗人的诗并保留原诗的词语,但使这些词语具备其他的含义,以突出自己的特色,让人反觉前驱诗人的诗不够独特。同样对前人诗歌的保留,这无疑与黄庭坚首创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暗合。黄庭坚旗帜鲜明地主张向杜甫学习,“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杜甫《杜诗详注》)。“点铁成金”是师前人之言,而“夺胎换骨”是学前人之意,但无论是“点铁”还是“夺胎”,都不是对前人诗歌的照搬照套,而是强调“活用”,表现为创造新意或与旧意相逆。
(一)用典
黄庭坚好用典,他的用典特点有两种。第一种:用典偏。例如,《戏答陈季常寄黄州山中连理松枝二首》中末两句“金沙滩头锁子骨,不妨随俗暂婵娟”(黄庭坚《黄庭坚全集》)便用了《传灯录》中的典故—一個菩萨偶化为荡妇的故事。这个典故又偏又怪,但黄庭坚用来形容苍劲挺拔的松树结连理枝的情况异常贴切。第二种:用典新。例如,《寺斋睡起二首》其一:“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退食归来北窗梦,一江风月桃李船。”(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前两句都用了庄子书中的比喻,其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义一般指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顾自己的安危;黄庭坚此处用典意义则指向第四句,巧诈智愚,相互争斗,和虫子有何区别,不如乘着渔船远离名利争夺之处。
(二)用句
江西诗派诗人熟读前人诗歌,将其巧妙地融入自己的诗歌中,是对前人诗歌改写和重新诠释。陈与义的《伤春》写于金兵大举过江之时,自己流落湖南,面对艳丽春色却生黍离之悲。在诗歌的颈联“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陈与义《陈与义集》)中,他化用了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李太白全集》)及杜甫的“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杜甫《杜诗详注》),既形成了完美的对偶,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超越了李白、杜甫原诗的意义,表现了作者悲怆凄凉的心境。吕本中《兵乱后自嬄杂诗》其二十四中颈联“报国宁无策,全躯各有词”(吕本中《东莱诗词集》),从杜甫《有感五首》其五颈联“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杜甫《杜诗详注》)中脱胎,与杜诗句式相仿,意义却不相关,加强了杜诗的对比成分,相较于原诗显得更加痛切、更加有力。
(三)用意
“夺胎者,因人之意,触类而长之”,“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惠洪《冷斋夜话》),对前人所表达过的意义,江西诗派便对其进行补正、修订、完善,抑或是因旧意生新意,甚至与前人的观点针锋相对。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其一中三四句“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吕本中《东莱诗词集》),是对杜甫“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杜诗详注》)的改写。杜诗为死者哀悼,在痛苦之余尚有一丝无奈,吕诗反用杜句,死者因死去而轻松,生者因存活而受累,想偷生却不可得,更写出了生者处境之艰难,苦难背后是更深的苦难,情感无疑比杜诗更激烈。曾几《苏秀道中》的第三句“不愁屋漏床床湿”(曾几《茶山集》)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床头屋漏无干处”(杜甫《杜诗详注》),杜诗意在表現房屋败破,曾诗字句虽同,写的却是对凶猛雨势的欣喜。第六句“五更桐叶最佳音”则旧调新唱,将“梧桐雨”这个凄苦的意象翻新,听见雨打桐叶,就想起得到滋润的庄稼,是作者对农事的殷切期望。
在《误读图示》中,布鲁姆用“提喻”来形容“苔瑟拉”,意在体现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前驱诗人是影响的施加者,后来诗人是影响的承受者,但是后来诗人通过主动地对前驱诗人诗歌改写,将关系颠倒过来,反成了动作的主体,前驱诗人的“部分”经过转换成了后来诗人的部分,而部分又消融于整体。最终,“自我修正和自我再生产成为一个整体,影响则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用典、用句、用意是江西诗派对前人的“部分”的吸纳,而正用、反用、新用是对意义域的扩展、延伸和修改,然后巧妙地穿插在自己的诗歌中,使诗歌看起来自然、不突兀,重新成为一个浑然的整体,如此便完成了苔瑟拉,即对前辈,尤其是唐代诗人的续写。
三、克诺西斯与以俗为雅
克诺西斯是“发生了一种与前驱有关的‘倒空’或‘退潮’现象”(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通过把自身的天赋和灵感毁灭,使得隐藏在天赋和灵感中的前驱诗人的影响也消失殆尽,达到从前驱诗人的姿态中分离出来的目的。后来,诗人无法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因为“诗人父亲已经被吸收进了‘本我’,而不是被吸收进‘超我’”(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诗人的创作始终沾染前人的色彩。连续性,即传统的连续性,历史上不同作家、不同流派之间的影响、延续和发展,对诗人的创作进行束缚和压制。唐诗是高雅的、饱满的,它的词句体例对宋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使宋人难以超越。江西诗派用“以俗为雅”的方式,破除了唐诗向“雅”方面发展的连续性,牺牲自身在“雅”上的才华,放弃“雅”,而堕入“俗”。
(一)江西诗派中的俗字俗句
江西诗派一方面用俗字,使句子浑如口语闲谈,另一方面用俗句,使诗歌在整体结构上显得突兀。杜甫写过《喜雨》,“南国旱无雨,今朝江出云。入空才漠漠,洒迥已纷纷。巢燕高飞尽,林花润色分。晚来声不绝,应得夜深闻”(杜甫《杜诗详注》)。杜诗使用的是诸如“漠漠”“巢燕”等典雅的词语,使得诗句情景交融,生成一种浑厚的意境美,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曾几同样写过的《苏秀道中》:“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全诗意思通俗易懂,所使用的是诸如“不愁”“且喜”等常用词,不难认,不拗口。末尾两句“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更像作者欣喜之余,脱口而出的自白。在黄庭坚的《寄黄几复》中,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黄庭坚全集》)隽永流丽,很有唐韵的风采,但接下来“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风格突变,与上句产生鲜明对比,使人感到不协调。陈衍评论说:“三四为此老最合时宜语,五六则狂奴故态矣。”(陈衍《宋诗精华录》)
(二)江西诗派的拗字拗律
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即云:“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例如,《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胡仔所举的例子正是一个拗句,传统五言诗的正格是上二下三,而“利欲食之既”则是二二一,与上句又不对仗,读起来便成了拗句。又《题落星寺》其一:“星官游空何时落?著地亦化为宝坊。诗人昼吟山入座,醉客夜愕江撼床。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星宫游空”连用四平声,“著地亦化”连用四仄声,“封侯王”又是三平尾,犯了律诗的大忌,反而与古体诗的格律更为接近。
江西诗派大量使用俗字俗句和拗字拗句,破坏了中国诗歌传统的连续性,放弃追求唐朝已至极致的浑然圆满之美,而使诗歌显得怪异俗气。“曾经有前驱者出现的地方就会出现新人—但其出现的方式使以不连续方式倒空前驱本人的神性,虽然表面上似乎是在倾倒自己的神性。”(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江西诗派正是以“倒空”的方式,主动放弃了传统诗歌的典雅特点,同时也放弃了自身可能在此的灵感与天赋,“有意识地利用在连续性中的故意失败去破解前驱的模式”(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回到原点,反而与传统分离开来,以此完成了克诺西斯。
四、魔鬼化和议论为诗
魔鬼化将前驱诗人更彻底地融入前驱的传统,以此消解前驱诗人的独特性,同时“接受这种他认为蕴涵在前驱的诗中但并不属于前驱本人而是属于稍稍超越前驱的某一存在领域的力量”(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后来诗人通过这种力量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在具体的创作中,便是一边夸大在更早的传统中便存在的,前驱诗人继承的特性,一边开创自身的特点。议论为诗是江西诗派也是宋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尽管争议不断,但议论为诗确实是宋人开创的一条新路。
诗歌的抒情传统在宋代得到了继承,宋人继续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走下去。陈师道《示三子》:“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抒发儿女归来的喜悦,极尽表现之能事,不仅“不得语”,还流了眼泪,甚至因過于欣喜担心这只是一场梦,使读者与之心意相通、感同身受。这首诗与杜甫的风格接近,似乎受杜甫影响,但“魔鬼化的功能恰恰就是增强这种压抑,将前驱更彻底地吸入传统,甚至比他自己勇敢的个性化所允许的更为彻底”(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
同时,宋人好议论,但不是在诗中直接讲演道理,而是对比、交融等方式使读者自生理趣,这在唐诗及更早的诗歌中间有出现,但直至宋朝才形成了气候。例如,陈师道的《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喜欢的书很快就看完,等待的客人却迟迟没有到来,世间不顺事多而顺心事少。这既是对人生道理的揭示,又是自我的无奈感慨。陈与义《襄邑道中》:“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陈与义《陈与义集》)后两句“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写人与物之间的相对关系,天上的云彩未动,只因“我”躺在船上与它一起动。
“魔鬼化”的挺进方向是逆崇高,“当新涌现出来的强者诗人转而反对前驱之‘崇高’时,他就要经历一个‘魔鬼化’过程,一个‘逆崇高’过程,其功能就是暗示‘前驱的相对弱化’”(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江西诗派继续保持抒情的特点而使前驱诗人尤其是唐朝诗人归于一般化,同时将议论融入诗中,张扬自己的独特性,“把前驱得来不易的一切胜利交回到‘魔鬼化’世界,从而削弱前驱者的人性光荣”(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
“‘影响的焦虑’产生了误读、修正和再现,从而推陈出新,有所创意。这给我们研读文本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让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去审视、评价文本和互文性。”(张龙海《哈罗德·布鲁姆论“误读”》)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诗的误读”是对传统诗学中“继承”“发展”的颠覆,他更加注重创新的一面,“诗的影响—从启蒙运动至今一直是一种灾难,而不是福音”(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误读”的六种修正比,对于后来诗人的创新有重要的帮助,只有真正的强者诗人才能突破传统的阴影,树立自己的威名。布氏的理论可以解释宋诗发展的一些现象: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人对唐诗的影响有着极大的焦虑,他们“误读”前人并殊死一搏,尽管付出惨痛的代价,但终于自成一路,形成了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格。宋诗的突围不是个例,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而又厚重,“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袁枚《续诗品》)诗歌如何打破前人的风格,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些问题依然有着经久不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