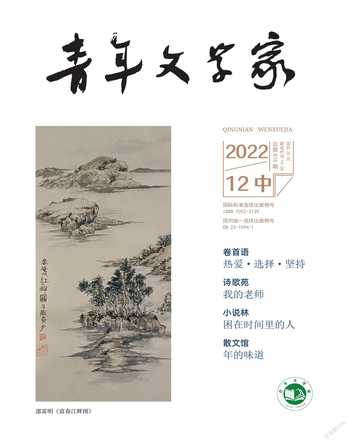爬在记忆深处的那几只鳖
一愚
我之上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先后在十岁左右夭折。十岁那年,我又得了重病。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祖母(祖父早年去世)和父亲、母亲心急如焚。一方面,写信向远在四川工作的我唯一的大哥求救,让他无论如何也要弄些救命药;另一方面,寻了一个土方子—肉炖冬虫夏草,一天一碗,三个月一个疗程。
好在当年的冬虫夏草没有现在金贵,一元钱一大包,将就吃十天。当时父母一天共挣不到两个工分,二角钱一个工分。肉就吃不起了,于是父亲打起了鳖的主意,用针穿了蚯蚓在村后池塘钓鳖。通常是头天傍晚下钩,第二天早上去收。开始两次都没有收獲,第三次,父亲下狠心买了点儿猪肝,用针穿了猪肝去钓。这一次钓了一只五斤多重的大鳖。父亲用网袋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小脸盆大的甲壳上好像长着青苔,针别在脖子上还没取,四只脚乱蹬。可怜的大鳖,贪那一口猪肝,成了我的药引。可能它临死都没有明白,当时人们是不吃龟鳖的,怎么就遇到了这一家不讲规矩的呢?祖母悄悄地对我说,鳖有灵性,平时是不能吃的,现在为了救命,不得已吃它,你将来一定要报这段恩情。那只鳖我吃了七天,每次端起碗吃冬虫夏草的时候,都感觉有两只小小的鳖眼在看着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害怕。
父亲、母亲好像知道我心里害怕,以后又寻了别人家的胎盘,杀了家里仅有的两只鸡,也买过几次猪肉,但还是不够,只能以鳖肉为主。祖母几次三番买了香烛,替我祷告鳖神和灶君,以求它们谅解。
一年之后,我大病痊愈,功劳主归野生鳖和冬虫夏草。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一种极为奢华的疗法,要用现在的市价计算,恐怕几百万元钱都拿不下来。当然,兄长寄回的西药也起了大的作用。
后来,我外出读书又回到家乡教书的时候,冬虫夏草已等同黄金,论克买卖,实在吃不起了。家乡的鳖又和我续了一段缘分。我教书的学校在一处集市上。集市早市,有附近老乡零星提了野生鳖来卖,一元二角一斤。我当时月工资三十四元五角,起初每月吃一两次,后来发现鳖壳值钱,就买鳖吃肉,把壳卖掉。卖壳的收入与买鳖的支出几乎等值,这等同发现了新大陆,但我还是刻意控制了吃鳖的频次。
一次,我买了一只大鳖,五斤多重,就像父亲当年用猪肝钓的那只一模一样。我把它放在一个大水盆里,准备赏玩几天,让其吐尽脏物后再吃。有人时,它把头和脖子都缩到鳖壳里,趴在盆里不动;看不到人时,则在盆里爬得吱吱响。有一次,它还下了一窝蛋,像十几颗晶莹的白玉石。第二天夜晚,它就离奇地失踪了。门窗完好,没人进来过,只能推断它从厨房砖砌的下水道逃走了。一只刚产过卵的母鳖,为了活命,屈尊从肮脏的下水道夺路而逃。我突然记起了祖母关于鳖有灵性的叮嘱,记起了自己是靠吃鳖活下来的。下水道有迹可循,只有下过大雨,积了大水,鳖才能真正脱险,就把机会留给它吧。这件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过去了,如果那只鳖有幸逃出,且还活着,现在应该有五十多岁了吧。
此后,我搬到县城居住,与鳖接触的机会减少了许多。在城里尽管野生鳖的身价一增再增,我基本不食。说基本不食,是不刻意去买来食用。宴席上的,人家准备的红烧甲鱼或老鳖汤,我有时也吃几口,可不仅感觉不出什么滋味,还有戚戚感从心底萌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乡镇的捕鱼现场遇到了两只小鳖,旧五分硬币般大小,怜爱之意顿起。我费了些气力,弄到手拿回家喂养。我专门买了一个装酒的玻璃缸,搁在客厅花架上,两只幼鳖悠游在酒缸的清水中。我用瘦肉末儿饲养它们。它们开始当着人不食,逐渐当着人敢吃,直到后来等着我投食。长到一岁,它们都长到了小碗口那么大。有一天,我如常喂食,它们不抢,不食。我把肉末儿放在水底,隔两个小时来看,依然没食。它们逐渐躁动起来。病了?直觉让我把它们捞出来审视。原来白色的鳖腹各长了两个红色的肿瘤,铜钱般大小。我到水科所请专家开了药,由于它们不进食,无效。那段时间,我总觉得有两双小眼睛,哀哀地看着我。它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我,可我却没有一丁点儿办法,只能每天换水,把药撒在水里。我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终于在第十天上午,有一只鳖停止了呼吸;另一只鳖的两个肿瘤,在一天内相继溃口,随后就开始进食。这可应了老家一命保一命的说法。
三年后,这只鳖长到了三斤多重。饲鳖的酒缸我换了两次,搁缸的地方也从客厅花架移到了封闭后的窗台。越到后来,它显得越不安分,每年总有一段时间,要翻出酒缸,沿窗台、墙角,不停地爬动。夜深人静,它还会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又请教了水科所专家。他们笑着说:“你的鳖崽儿长大了,想结婚了。”恰好这年,有一位西藏的活佛到汉江仙桃码头放生,我请他帮我把鳖放生汉江。他说:“你还是抽点儿时间去汉口,把它放到归元寺放生池吧。”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这样于你于鳖都有好处。因为鳖缸养的时间久了,放到汉江有一个适应过程,而等在汉江边专捕放生物的人,不会给它这个过程。你与它有了感情,放了它马上又看见,或者预见它的悲惨下场,你会心里感到不安。”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精心地饲喂了肉末儿之后,驱车前往归元寺,把它放到了放生池。它的确通灵性,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久久不肯离去。这只鳖如果健在,怕也有二十九年鳖龄了。我在梦里还经常与它为伴。
那几只鳖,一直爬动在我的记忆深处。想起它们,就想起那一处绿树环绕的村庄,那一方荷叶田田的池塘,那一个温情脉脉的小院,以及生我、养我、疼我的父母,还有一众不能忘怀的亲人。
——猪肝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