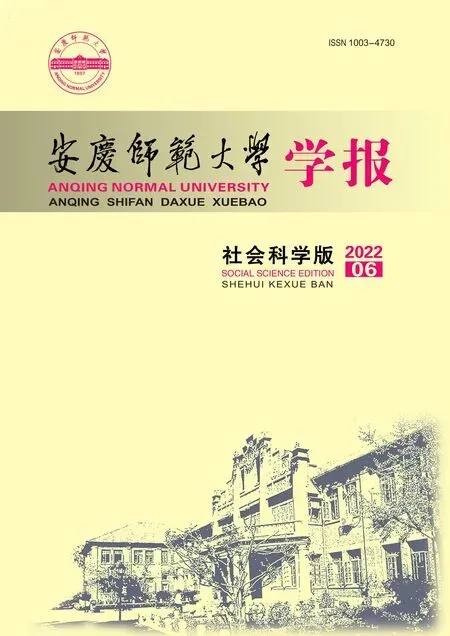“左联”东京分盟诗人群新诗现代性的域外实践
李 薇,杨 伟
(1.福建江夏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2.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重庆 400031)
近年,将左翼文学放置于“世界视野”下进行重新审视已成为相关研究的新范式,这种研究新动向折射出相关论者对中国左翼文学向世界范围内的文艺资源主动采借和联系的重视,以期透视其在东西方文化空间里互动与共振的面相,“描绘出中国左翼文学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1]。相关实绩可从鲁迅研究、华语左翼文学研究、欧洲左翼文学研究以及俄苏、日本左翼文学研究等获得佐证。回望左翼诗歌所走过的道路,其对域外文明的吸纳与模仿总是伴随在“新诗现代化过程”的认知和评价中展开。在诗歌审美评价日趋客观的当下,曾经被有意剥离或遮蔽的左翼诗歌现代性元素终于绽放新的色彩。
随着现代主义诗歌与左翼诗歌对现代性不同向度的探索日益受到论者的关注,人们正不断地对左翼诗歌呈现出的“另类”现代性追求作出更正和重新确认,“令昔日的狭窄视野变得宽阔”[2],以打破“单一现代性视野和现代主义思维模式”[3],力求对左翼诗歌实践做出整合性的认识和评价。然而,以左联东京分盟(文中简称东盟)为中心的左翼留日诗人域外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依然缺乏足够的目光聚焦,事实上其域外的诗歌创作乃左翼文学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本文拟以东盟左翼留日诗人的诗歌活动为参照,将左翼诗歌现代性追求放置在域外文化空间里做一较为系统的梳理,特别关注胡风、雷石榆、蒲风等人与日本左翼诗人以及东盟机关刊物《东流》《诗歌》的互动关系,由此对左翼新诗现代性的域外探索和艰难历程做出更为客观的理解,以便进一步全面认知左翼诗歌的整体风貌。
一、直视与同构:域外语境下的集体性想象
留日作家群普遍存在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时代使命,他们直面人生、力济天下的现实品格深刻地影响着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新诗的发展出现了政治倾向的多重变奏,文学与革命的结合已成为诗歌主旋律,时代的歌者追求着“和现实密切拥抱”,浪漫与感伤的梦中呢喃逐渐被大众抗战的呐喊声淹没。当新一代知识分子浸染了救亡图存的时代精神后,他们承载着动荡岁月的苦难,怀揣着澎湃的革命激情和真理之梦,或为求学或因政治压迫,相继汇聚到日本,再次开启了一幕幕探寻真理的异国体验。远离故土求索文明与进步背后的阴影没能遮蔽左翼留日诗人的感知世界,他们透过底层人民的生活日常注视着日本社会文明的镜像,把异国现实“纳入了注视者文化”[4],去思考、去评判这个社会现实。但是左翼留日诗人对日本形象的感知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新质,他们既满怀深情颂赞着岛国的风物人情,又以现实主义的直视目光审视着异国“文明”外衣下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悲苦。这种辩证的书写策略少了偏见与盲目,其间所展现的审视姿态和集体性创作指向更富有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左翼留日诗人的笔下,岛国的自然风貌和社会环境已逐渐褪去了往昔留日前辈们的审美色调。时代的风云与民族危机的多重挤压,使得左翼留日诗人已不再一味执着于凝视他者“纤纤的/蓝玉玉的寂寂的颤摇/覆着白纱的碧空中/”①《水飘》是穆木天早期浪漫主义诗作,全诗带有象征色彩,风格清新、邀远、深沉。转引自田源:《中国现代留日诗人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4‐128页。的海岸线,也不只流连于翻阅不忍池畔那道杨柳、街灯映衬下静谧无声的景致②冯乃超《不忍池畔》一诗所呈现的意象,相关诗句如“苍烟罩着病弱的杨柳,/寂寞的街灯饮泣在柳荫的衣袖”。转引自田源:《中国现代留日诗人笔下的日本形象》,《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24‐128页。,取而代之的是岛国那“萧条的农村”“疲乏的工厂”“倾斜的街道”以及“焦阳如怒”的郊野,即便是抒写故国家园的大陆和原野③相关诗句见胡风《仇敌底祭礼》:“‘丰沃的大陆’,/‘金黄的高粱地’……/极目无边的原野”。参见胡风.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7页。,也是为了以此鉴照日本侵华分子恬不知耻的贪婪面相。他者文明掩盖着的残忍暴戾与贪婪无耻扯碎了印留在左翼留日诗人心中原有的审美镜像,那种曾经代表着先进、现代的岛国文化大厦在留日者的群体注视下轰然崩塌。这里,他者镜像与诗人的主体意识悄然互换,衍生为了留日诗人集体性审美感知和时代意识的嬗变。同时,这种感觉更加强化了左翼留日诗人沉重的时代使命,他们开始更加理性地关注现实、观照人生,或站在贫苦大众的立场,写故国的饥荒④如雷石榆发表于《(中国)台湾文艺》第二卷五月号的日文诗《饥馑》,该诗后被雷石榆译为中文。参见张丽敏编著.雷石榆诗文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11页。、人民的爱与敌人的憎和岛国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压迫人民的苦难⑤如雷石榆发表于《(中国)台湾文艺》第三卷第三号的《磨碎可怜的灵魂》、发表于日本左翼刊物《文化集团》第二卷8月号的日文诗《非上帝的女儿》和发表于《诗精神》第一卷第十一号的日文诗《咖啡店》等。参见张丽敏编著.雷石榆诗文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或萃取一束“朦胧的红绿灯光”、一阵“窗下流涎似的滴滴音响”、一幕“纷纷撇下闪闪发光的/纯白的粉末”的夜空⑥如收录在雷石榆发行于日本东京的第一部日文诗集《沙漠之歌》中的《初雪》。参见张丽敏编著.雷石榆诗文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页,第3‐4页。,共构出“喘息”在日本社会底层的悲苦世界。经由诗人个体生命域外体验的阐释,异国自然与社会的种种感官景象已浮出象征层面转而内化为诗人别样的审美评判,从而将岛国的所谓文明置于一个框定的虚假影像中,映照出掩藏在黑暗社会阴影下的真实面影,将左翼的现实主义追求显露在域外自然万象的律动里,并在东盟诗人群体的直视与共构下,形成了左翼域外诗歌的现代性书写策略。
左翼留日诗人执着于书写日本平民与友人,并用平视的眼光连接起一个生息同脉、相携与共的世界,日本形象也因之增添了时代新质。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留日诗人的域外创作,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留日诗人胡风、陈子鹄、林林、蒲风、林焕平、雷石榆等均有意识地将日本平民、友人与日本侵华军队、政府截然区分,复合着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思潮的话语模式,巧妙地将反侵略反压迫以及人类联合抗争的现代意识融进“追求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视野”[5],在文本世界里合力共构出一个命运与共的集体性想象空间。如:
你们终要明白的:/这三军的威力,/飞机、大炮、机关枪、毒气/没有一样是你们的,/它们不过是暂时交到你们手里,/去屠杀海那边的和你们一样的兄弟,/为他们打出江山来,替他们建筑新的王位。/他们胜利了——/在你们底应该为了友爱的把握而伸出的手上,却已染上了和你们同命运的海那边的兄弟们底鲜血⑦节录自胡风.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7页。!
在讽刺和对比中,胡风对日本形象体验显然有了辩证性,暴虐的侵略者与日本友人、平民之间的有意区别,在“你们、我们、人们、咱们、大众、兄弟”的高频率出现的集合性称谓中,厘定了对他者的个体性区分,试图唤起日本普通市民的道德良知和反战良心。类似的书写策略也在《别离祖国》⑧原为日文诗,发表于日本左翼刊物《文艺》1935年8月号,并作为当年最佳作品收入日本前奏社出版的《1935年诗集》,1980年代该诗被作者自译为中文。参见张丽敏编.雷石榆诗文选.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7页。、《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①任钧1931年12月17日创作于东京的一首诗,标题为《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献给全日本的勤劳大众》。参见卢莹辉.诗笔丹心——任钧诗歌文学创作之路.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给异国的同胞们》②收录于冯宪章的诗集《梦后》,诗人通过梦前梦后区分理想现实,反映出时代青年的痛苦,旧社会的罪恶,以诗歌形式探讨社会真正的出路,探讨工农的出路。等诗篇中得到反复印证,甚至许多译自日本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歌,如《给妹妹》《妈妈》③收录于胡风的诗集《野花与箭》。参见胡风.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575页。、《记念》《现实的砥石》④原诗作者为小熊秀雄,雷石榆译,曾以中日文对照诗的形式发表于《日文研究》1936年第6期。参见小熊秀雄著,雷石榆译:《现实的砥石》,《日文研究》1936年第6期,第42‐43页。等,也可清晰地看出留日诗人所选择或重构的日本形象序列被赋予了时代新质,跃动着日本平民和友人们的“‘反战’良心”及其“对‘天下同是受苦人’‘同志之爱’的呼唤”[6]。这里,“我们”“咱们”跨越了民族边界,改变了词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化合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共同语的表征。可见,“九·一八”事变后,战争与侵略进一步炼铸了留日诗人为时代而歌的气魄,他们开始理性地重新认知自我,已然褪去了前辈们习惯于正面观看他者的纯粹,尤其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虚伪或隐或显地浮于纸面,如:“他们用万万千千的说谎来神圣化这可耻的流血”[7]。日军野兽般的野蛮与奸诈与留日左翼诗人的人性与道德之美形成反差性对照,曾经被认为进步的异国文明在“他者”无耻的面影里被重新界定,中日两国文明位置似乎也悄然得以转换。尽管这可能只是留日诗人的主观念想,但也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被唤醒的显证,表征为“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调整”[8]。
可见,左翼留日诗人经历了异国现实的耳濡目染后,一定程度上已经滋长了自身的人道精神,坚定了革命理想。这种相似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理想,使得左翼留日诗人在继承和超越前辈域外文学创作的范式时,借助新的语境及东盟集体化力量衍构出的诗歌文本具有着崭新的域外特征。
二、反观与对话:译诗与日文诗的艺术创化
东盟留日诗人心怀家国理想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因子,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历史节点注视着“他者”,他们用诗歌与文字的“真实叙事”讲述着自我经历,少了20世纪20年代之前留日诗人的那种迷恋或狂热。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很年轻,却具备了现代的世界视野,超越了传统偏见,更为准确地把握真实的日本形象。正如巴柔所说的他者与自我之间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共在关系,即“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言说了自我”[4]。随着国内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相继蓬勃发展,文学与革命紧密结合,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新文学的主体性精神。东盟重建之前,左联对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介绍,主要是从日文转译。可以说,没有日本这座文化桥梁,“左联”不可能完成中国诗歌现代性变革的历史使命。
对于诗歌创作而言,无论是新诗本身所沿袭的理论向度还是其承传的时代使命,诗人们往往选择依托先进文化,踩着“巨人的肩膀”快速成长。因此,对于东盟留日诗人来说,日本无产阶级诗人的作品、西方和俄苏进步诗人的日译作品等无疑成为了他们审美借鉴的最佳选择。为了追逐诗歌的时代精神,东盟留日诗人除了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写作外,还翻译了大量的日文诗歌和日本无产阶级诗歌理论,一方面配合国内左翼诗歌运动,另一方面让这些译作成为国人鸟瞰世界的窗口。译诗在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左翼诗歌发展亦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诗歌及其理论的滋养,大量地由日文转译世界无产阶级诗歌也侧面反映了东盟留日诗人诗歌创作的现代性诉求。尽管大部分译者的日语水平还比较低下,“特别是诗歌,译起来更加吃力”[9],但他们在不断的翻译中反观自我,力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诗歌接轨,努力地在他者先进文化的审视和借鉴中完成初步的自我构建。如:胡风的日文译诗《给妹妹》⑤原作为日文诗,作者京山爱子。中文译诗参见胡风.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1‐572页。、日文转译诗《给黑人女郎》《长工》⑥兰斯顿·休士著,胡风译。参见胡风.胡风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76‐577页。等;发表于《日文研究》第三号登载的魏晋日文译诗三首;林林将海涅的日译诗歌《决死的哨兵》《投弹兵》转译为中文寄到上海《世界文学》发表;任钧翻译日文诗《在劳动旗下》并转译日文译诗《叶赛宁诗三首》等。通过译诗,不仅让译者更深入理解他者文化,并让其在译诗过程中对世界视野下的诗学审美建构进行反思和自我更新。译者还将自身的诗学精神凝注于笔端,把自己或同人的中文诗歌译为日文刊登在域外杂志上,如雷石榆发表在《诗精神》第二卷9月号的自译日文诗《诗人的自杀》和发表在《日文研究》第五号上的中日文对照诗《给灾区逃亡的人们》等。在译诗影响下,东盟诗人不断拓新诗歌交流形式,让中文诗与译诗共同建构起了域外左翼诗歌创作的现代性品格,正是这种现代色彩的创新性实践为中国左翼诗歌发展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域外推动力。
东盟诗人还借助诗歌创作或诗歌活动等方式同日本文艺界进步作家密切交往,他们认为“对日本的学习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寻”[10]。与他们密切交往的日本左翼作家主要有江口涣、新井彻、秋田雨雀、北川冬彦、小熊秀雄等。同他者建立阶级友谊,使左翼留日诗人拥有了最为直接的学习对象。中日两国诗人均盛行以诗歌为载体进行吟和赠答,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时期,中日两国诗人能够以唱和等方式进行诗歌交流,尤为难能可贵,其中小熊秀雄和雷石榆用心灵的话语共同完成的“往复明信片诗”无疑“是一个醒人眼目的例子”[11]。小熊与雷石榆的往复明信片诗不同于日本传统的“连歌”,也不同于鹜逐欧美趣味的被称为“Renga”的联诗,他们不刻意追求文学书写的新形式,而是诗的对话,是两人同心交感、意气相投间共同创构的“心灵话语”。该诗作共37篇,其中雷诗18首、小熊诗19首,除作品第一号(9首)外,第二(8首)、三(8首)、四号(12首)均为雷石榆首先发出。如作品第四号的(5)(6):
雷(5)你啊,骏马的主人
给我以活力
注入生命的挥发油
你工要是驰遍
那边的大陆
那里高耸云霄的群山之峰
也许颤巍巍的要崩倒吧,
不,冷冷清清的诗坛沙漠上
会轰响夏天的雷鸣吧!
但是现在迫切地
期待着我们的
首先尽快地
两个民族的普罗诗人
紧紧地携起手来!
小熊(6)中国的诗人啊,
你的日本语格律走了调
可你在文字上如此
漂亮地道破了真理
在日本也有骄奢的诗人
牵着字眼儿打转转
倒算得是天才,
但并不痛快的说出人世间的真实,
侧耳倾听风吹草动
稍懂得暴风雨的势头也还好,
他们却象那在
烧热的平底锅上爆跳的油星
乱哄哄的叫嚷:
没有立脚之地哟!
嘲笑地、冷静地歌唱吧,
那说不上叫人可怜,
倒是花炮一类货色。
以上两首往复对话诗原为日文诗,二位志同道合的革命诗友用日文展开的身体经验世界的激情对话,在冼练的日本语中尽显中日两国诗人相互鼓励、携手战斗的革命憧憬。而以下的雷(7)(9)与小熊(8)(10)则在前者提出迎接历史空前巨变的爆发和担负革命使命的呼吁中以高度的艺术手法描写“处在叛逆的黎明前”的景象,以“母鸡”分娩的形象写出经过“新的苦痛”后艰难地诞生新的“革命”,并分别表明“向新的时代尽瘁献身”“向人们的生活予以冲击”的决心,诗句间洋溢着“特异的无与伦比的诗歌艺术”[12]。而雷(11)与小熊(12)运用浪漫的笔法道出中日两国诗人彼此革命的“战术”,飞扬着政治理想的光芒。从作品开始到第四号相隔只有10余天,对于还未充分掌握日语表达技巧的雷石榆来说,“在那日子里接续写出诗来,那种精神相呼应的姿态,更令人吃惊!”[11]而木岛始教授在《日本语中的日本》一书中更是将这种富有开创性的文化合作与交流提升到“几乎具有改写昭和文学史的作用”[11]的高度。且不说蕴含其中的里程碑意义,雷君与小熊氏的这场跨越国别的对话拓展了中国左翼现代诗歌的言说方式,使左翼留日诗人新诗现代性建构上具有了未来性和世界性的视野。在此,不管是他者的诗意建构还是自我的审美表达,其中的理想主义、底层情怀被放置于更空阔的文化语境下重新界定,使诗歌真正得以超越语言界限演绎出在场合一的同声合唱。对于青年留日诗人而言,更是巧妙地将诗情生发的共鸣点设计在他者文化的语境里,通过他者与自我的反复回应,让彼此对理想和艺术追求的共同旨趣获得某种确证。
三、坚守与拓新:诗学精神的域外延伸
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内外压力交困下艰难行进,左翼留日诗人却凭借其“前卫的眼睛”,在中日两国反动势力的多重挤压下撕开了一条裂口,构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左翼诗歌域外话语链。“左联”东京分盟的盟员大都是留日青年学生,诗学和外文水平不高,但服膺一身革命文学的热情,怀揣着“对文学阶级性的捍卫与坚守”[1],吸纳着世界视野下的左翼诗学资源,“发掘他们与域外思想之间所发生的互动与共振”[1],使中国左翼诗歌现代性追求更笼上了世界性色彩。
首先是超越文本的实践精神。东盟的重建及其相关机关刊物的创刊,离不开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支持与帮助。期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退潮期,左翼文化界遭受严重破坏,但东盟留日诗人关注日本文坛的国际眼光丝毫未曾暗淡。他们借助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资源,踏着“日本”这座容身其间的域外“桥梁”,担负起了时代使命,使中国左翼文艺思潮涌向新的文化空间,拓宽了国际视野。一方面,他们在江口涣等的建议下以合法的方式创建《东流》《诗歌》等刊物。在当时的中国,左翼诗歌运动几乎停滞之际,“藉由《诗歌》等刊物的创刊而死灰复燃”[13]。《诗精神》和《诗歌》友好交流,彰显着中日两国诗人的国际主义情谊。《诗精神》同人出席“东盟诗歌社”相关活动,为《诗歌》义务刊登广告进行宣传,转载原刊于《诗歌》的短诗《盐》(诗作者为林林,译者为台湾留日诗人吴坤煌),培植了《诗歌》与《诗精神》同人及台湾进步诗人间“拥有共同价值的友谊”[14]。另一方面,他们以诗歌为载体,以《东流》《诗歌》《诗精神》《文化集团》《台湾文艺》等为阵地,不但将众多的留日学生汇聚于中日左翼团体,吸纳留日诗人作为《诗精神》同人①《诗精神》为日本左翼同人杂志,创刊于1934年2月,是日本无产阶级诗人组织“前奏社”创办的机关刊物,也是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最后的战斗堡垒,成员有新井彻夫妇、远地辉武、雷石榆、吴坤煌等同人34人。参加各种文艺活动,而且经常同时刊发鲁迅、郭沫若、周扬、台湾地区留日学生及日本进步作家的作品,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特别是两岸文艺界的团结和交流,书写了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页。此外,在国内左翼联盟内部分化、相关刊物被查禁停刊乃至左联集体解散的背景下,东盟诗人们对左翼域外文化阵地的坚守,一定程度上同国内左翼文学运动形成了时间接续上的某种契合,使左翼诗歌创作活动在国内左联解散后却在海外获得必要的承续。基于此,左翼留日诗人这种善于融合域内外文化资源的实践精神无疑是蕴含在诗歌文本之外的一种别样的“精神诗性”[15],潜埋着左翼留日诗人们对个己生存状况、民族终极问题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垂询。当这种精神内化为诗歌创作主体的时代使命,有关左翼诗学集体层面的探索便拥有了世界视野下的实践美学色彩。
其次是诗学审美的多重复合。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诗歌常被解读为政治的有效配合体,认为他们因深度介入政治功利完全失去了个体精神的坚守,诸如此类的否定使左翼诗歌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一度被学界所忽视。但是,任何一个诗歌流派的创作实绩均可被认为是由多重合力综合促成的结果。对于左翼留日诗人而言,尽管他们留日时间较短,其诗风受到他者文化语境的影响不尽相同,但通过其域外创作可以看出,无论是试图借助诗歌对抗处身域外的日常悲苦还是通过个己情怀的抒唱或诗歌理论的探寻以展现时代审美的姿态,都促使我们换用新的眼光来重新评判。其实,即便处身域外的左翼逐“梦”者革命的初心不改,不同于国内的文化语境总会多多少少影响着他们各自的创作态度。一方面,他们围绕东盟创建、重建和解散这一时间轴,将左翼诗歌的美学精神和革命文学的权力语域延伸至域外,文本实践中明显带有着较为浓郁的乌托邦气息;另一方面,这些诗歌虽然弥漫着左翼诗人的“阶级意识”和权力话语范式,但亦充斥着“富有艺术个性的孤单、寂寞、独语”,文字间的柔软与真实印证了左翼留日诗人们在政治图说之外,也在现代性审美中展开诗意言说。如陈子鹄《春(二首)》之一:
春——/据说从青草中来,/从一阵风轻,/从一片翠绿的树林,/……/然而我看不见春,/我的心窝仍是一个严冬;/包含着一个坚忍,/一阵北风的残酷;/我感到粗梗的手掌有些痹麻,/又似乎仍是凝冻。/我看不见春天!/我没有春!/并不是在做梦!/我只有愤怒疾恨,/和一个沉痛①节选自陈子鹄《春(二首)·街头的春》,原诗收录于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诗集《宇宙之歌》。参见陈子鹄.宇宙之歌.东京:东流文艺社,1935 年版,第13‐15 页。!
这是东盟“东流文艺社”刊行的第一本诗集《宇宙之歌》中的诗句,短短的诗句间六次出现抒情主体“我”,异国的“街头之春”不断叩击着“我”对“春”无尽向往的心扉,“青草”“轻风”“绿树”交织的幻象里裹满了“我”焦灼的期待。诗人把自我毫不掩饰的浓重情绪沉潜入众多富有象征蕴味的意象里,并在所见所感的对立反差中将现实的疾恨与沉痛溶解进春的梦幻里。这里,没有左翼式的战叫和呼喊,却有着传统与现代诗学的融合,并在物境与心境的映射下完成了一次自然与心灵的诗学交换。另一方面,不同于国内左翼诗歌的“革命范式”,左翼留日诗人不满足于对以往革命文学之批判的摄取与研究,也不机械地陷落在普罗诗创作方法论的泥淖,其诗歌言说方式和文本制作更显自由多变。他们或高唱“模糊的血肉下会建造起明朝”的跫音,或低吟着“离别的路绵长得没有终点”的惆怅,或静听“窗下流涎似的滴滴音响”,或憧憬着“紫霞洞的淡雾,/陵谷寺的清幽,/那山野道旁的桃花”所氤氲的故园山野的轮廓,或在“起来呵,海这边的奴隶/起来呵,海那边的奴隶”的战叫声中让“全世界的奴隶”献上反侵略的祭礼。他们站立在域外的生存现场回望“过去的轮廓”,或以想象力重建家园记忆,或直面域外的所见所思,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新的言说秩序。这样,多维时空言说的书写策略不仅成为了左翼留日诗人打开中日两国双重文化空间的技术手段,也为其另辟了一个“更新生命体悟的重要观察点”[16],使左翼留日诗人的诗歌创作拥有了“多重性的打开和更为宽阔复杂的言说自由”[16]的可能性。
最后是诗学建构的视域融合。伽达默尔认为视域(Horizon)是“包含从一特定角度所能看到的全部东西的视觉范围”[17],当诗人作为读者身份向世界资源进行采借时,其与文本之间存在时间距离,要实现对文本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必须达到双方视域的融合。但“视域融合”(Horizon Fusion)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地理解“某个”文本的浅层含义,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为“文本”创造出新的内涵。该理论认为,平等对话是各方视域真正得以融合展开的必备条件,因为“只有秉持这样一种平等、开放的心态进行,真正的视域融合才得以可能”[18]。由此审视左翼留日诗人,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广采博纳,广泛聚集中日进步作家开展诗歌座谈会和作品批评活动,借助日文翻译、述介各国无产阶级诗学理论。除了东盟机关刊物外,他们还在《诗精神》《文化集团》等日本左翼刊物上发表大量诗论,以平等的姿态介入无产阶级诗学建构。但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方向和视轨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关注和期待。”[19]左翼留日诗人们或与日本《诗精神》同人友好交往,一同开展诗歌理论研讨活动,或充当“中日文学的桥梁”,将中日诗坛的近况分别客观地绍介给两国读者;或汇聚域外留日诗人致力于新诗大众化、国防诗歌实践,或与(中国)台湾文艺联盟留日诗人吴坤煌等一同探寻“现在的(中国)台湾诗坛”和“诗的创作问题”,历史性地在两岸视域下链接起大陆和台湾的现代“诗精神”;抑或在左联解散的背景下依然坚持办好《诗歌生活》《质文》,并协同非左翼刊物《文海》《日文研究》等成员继续在海外传播左翼文学,与日本左翼文学界联手打造中日文学史上少见的逆潮而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他们提倡讽刺诗、诗歌大众化、新写实主义,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从内容和形式上挣脱传统桎梏;他们还致力于日译诗、日文诗论的翻译和日文诗创作实践,试图用日文架起中日诗歌对话的桥梁,找寻着世界视域下无产阶级左翼诗学的融合点。如:中日诗友们认为日文诗集《沙漠之歌》《中日往复明信片诗》中的诗作“感情的深度具有抱拥性”“与已经日本化了的中国诗人所写的日文诗不同,与日本无产阶级诗人的诗歌(严格、无亲和力)也不同”[20]41“首创了文学史上无先例的‘往复明信片诗’,永留日本文学史册”[20]83。正是这种创新性的对话与吸纳才最终融合为中日两国从未有过的左翼诗学景观,凸显了中国左翼歌者在世界视野下的诗学精神与文本创新的域外表征。再如:中国现代长篇叙事诗首创之作《六月流火》②参见蒲风.六月流火.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的出版亦展现出了左翼留日诗人顺时代而作的诗学诉求,全诗虽存在诸多缺点,但它开辟了长篇叙事诗的写作新领域,多向度融合了传统诗歌的写作技法,采用“客家山歌的表现形式”“以‘对唱’‘轮唱’‘合唱’等民间歌谣的传统手法,创造了‘大众合唱诗’这一新形式”[21]。这里撇开左翼大众化诗歌现代性建构的缺失问题,显然当时的蒲风已经在有意识地创构多元取向下的民族化的诗歌形式,体现着左翼留日诗人正努力以传统为参照,寻找着大众诗学建构的某种“平衡”与“融合”。总之,正是“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22],使得视域融合下留日诗人的诗学建构获得了历史确证。
四、结 论
综观左翼留日诗人新诗现代性追求所做出的努力,不难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红色浪潮下,左翼留日诗人冲破中日两国反动统治,通过创建或重建东盟,创办盟刊,开展诗歌座谈会,同鲁迅、郭沫若、周扬及日本无产阶级诗人密切交流,并与国内左翼诗歌运动积极呼应,提倡讽刺诗、朗诵诗和诗歌大众化,利用域外日文语境拓新诗歌新形式,尤其是日文诗集、中日往复明信片诗集、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等的出版或创新性开掘,为中日文学史增添了一笔浓重的现代性诗学色彩。尽管他们在诗艺水平、审美选择、个体特质挖掘等方面存在缺失,创作实绩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他们立足域外全新的文化语境,以诗歌为媒介,用平视的眼光在世界范围内采借和融合着无产阶级文学资源,创构着富有时代审美新质的诗歌文本,拓宽了左翼诗歌的审美视域,为左翼诗学增添了新的景观。反观20世纪30年代诗歌整体风貌,固然现代主义精于个体特质纵深的探索,“执着于诗艺,获取了艺术真理”[23],但就当下诗歌发展现状来看,左翼诗人“对苦难的承担、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正视”[23]的创作姿态无疑依然值得人们深思。总之,“世界视野下”左翼诗学精神的研究还需不断深入展开。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