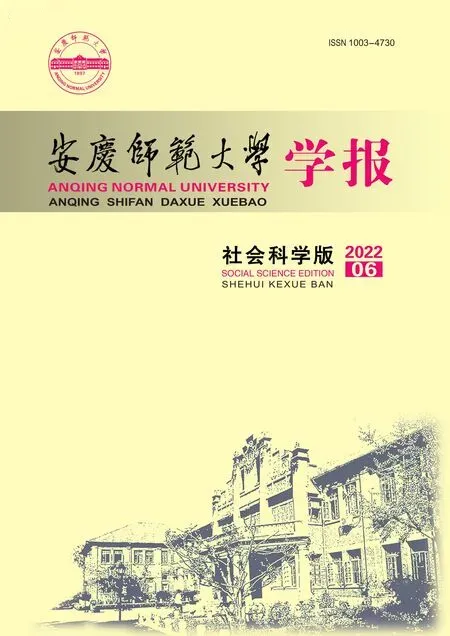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主要特征与官方应对
杨 帆
(巢湖学院 旅游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巢湖流域东南濒临长江,西接大别山脉,北依江淮分水岭,东北连接滁浦丘陵,位于安徽江淮之间,既为长江水系一部分,又形成以湖泊为中心的完整体系。从地理位置看,明清时期为庐州、和州下辖区域,大体包括合肥、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和州、含山7州县。从行政沿革看,明清时期变化小,境域相对稳定,便于长时段疫灾的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疫灾频发期,对当时社会经济、公共卫生诸方面产生重大冲击,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其中,在明清安徽灾害史和大区域疫灾研究中对巢湖流域疫灾特点有所提及①参看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王艳红:《明清时期皖江流域乡村水旱灾害及应对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尹阳硕:《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疫灾与医疗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单丽:《循海而来:清代霍乱大流行的地域分布与变迁》,《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胡兴涛:《公元前887年—公元1911年长江流域水、疫害灾时空分布特征研究》,《长江科学院院报》,2022‐05‐13。。有关这一时期巢湖流域疫灾应对研究体现在国家荒政救助、疫情奏报、防疫制度变迁、官员救疫和具体皇帝执政时期的疫灾应对等问题探索中②参看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林乾:《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何欣峰:《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研究》,《中州学刊》2020年第12期;张剑光:《直面与应对:中国古代地方官员抗击疫病的作为》,《东南学术》2020年第5期;姜文浩:《晚明南直疫灾:“大变迁”下的环境脆弱与社会拯救》,《农业考古》2022年第1期;李孜沫:《康熙年间疫灾流行的特征与应对》,《医学与哲学》2022年第1期。,缺少专文论述。基于此,笔者通过整理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史料,试分析其主要特征,并尝试探讨明清时期官方应疫行为。
一、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主要特征
带有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的灾害史料,是灾害与社会互动的呈现。笔者主要根据《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祥异、禨祥、食货、人物、义行等卷目中疫灾史料,广泛收录正史、实录、政书和时人笔记等关联记载,归纳分析这一时期巢湖流域疫灾主要特征。从整体看,明清两朝是中国古史上疫灾高峰期,明代277年,巢湖流域疫灾年份9年,疫灾频率3.26%;清代268年,疫灾年份27年,疫灾频率10.07%,清代巢湖流域疫灾年数和频率是明代3倍之多。其中,明代巢湖流域疫灾自弘治朝始,集中在中后期嘉靖、万历、崇祯朝,其它13朝暂未发现相关记载,以崇祯朝疫灾频度(11.76%)为最高;清代几乎每朝都有疫灾记载,以咸丰朝(27.27%)为最。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一)疫灾高发时段集中
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到弘治十五年(1502),巢湖流域暂无明确疫灾记载;弘治十六到十七年(1503—1504),合肥饥疫。之后,疫灾集中在嘉靖二到三年(1523—1524)、万历十六到十八年(1588—1590)、崇祯十三到十四年(1640—1641)3个高发时段。
嘉靖二到三年(1523—1524),大疫遍及巢湖流域内所有州县,与水旱灾和饥荒相关。时值南直隶疫灾,庐州、怀远、霍邱、全椒、怀宁、宿松、潜山、太湖、桐城、望江、安庆、扬州、江都、淮安、山阳15府州县大旱,民因饥疫而死。嘉靖庐州知府龙诰《请蠲赈疏》记录:“庐州一带地方连岁凶荒,劝民趁时布种,不料穷民命薄,瘟疫流行,乡市人家,不问官民老少,悉皆传染。”[1]229‐230他在比较嘉靖、弘治朝疫灾时,写道:“臣访之父老,询之士夫,佥谓弘治十六年,庐民亦尝染疫而病死者数万,未尝如今岁之既染疫而复重之以灾也。”[1]229‐230与弘治朝庐州有染疫病死者比较,嘉靖初年疫病达到“复重为灾”程度。庐州、和州方志分别记:“嘉靖二年夏旱、秋淫雨,并饥,斗米千钱,死者枕籍,三年春大疫”[2]470、“嘉靖二年大旱,自二月至六月不雨,秋大饥,斗米三百钱,死亡无算,三年大疫”[3],县志中亦有“巢县春大疫,死者枕籍”[4]460“舒城春大疫,民多丧亡”[5]37等记述,直到嘉靖三年(1524),秋大熟,民始生。
万历十六到十八年(1588—1590),特大疫遍及巢湖流域内各州县。疫情从万历八年(1580)山西鼠疫始,时任吏部员外郎邹元标感叹:“时人皆知救荒却不知救疫。”[6]万历十六年(1588),舒城旱疫,庐州郡属大旱饥,升米百钱,人相食。[2]471之后,万历十七年(1589)冬和十八年(1590)春,庐州疫灾;万历十七年(1589),含山大旱大疫。巢湖流域疫灾延续3年,主要受旱饥与外来鼠疫病菌综合影响。
崇祯十三到十四年(1640—1641),与大旱、蝗虫、战争裹挟而来的特大疫遍及巢湖流域。疫情在崇祯十一到十七年(1638—1644)遍及安徽长江一带。通过《(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中“庐州郡属旱蝗,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于无为,数日毙”[2]472和《(嘉庆)无为州志》中相关记载,推测原因为气候连旱化导致“旱-蝗-疫-饥-人相食”灾害链[7],惨状是鼠疫爆发,战事浩劫,民食草木树根,疾疫缠身。
清代共历10朝,其中9朝巢湖流域有疫灾,高发时段集中在康乾时期和晚清,并存在与更大区域疫病同灾现象。
康乾时期,巢湖流域有3个疫灾高发时段:(1)康熙四十七到四十八年(1708—1709)。巢湖流域在历经11年旱荒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冬大水,庐江、巢县、无为疫灾;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饥夏旱,疫区扩大到江苏山阳和安徽庐州、和州、含山、安庆、太湖、潜山等地。学界认为大范围高强度自然灾害是康熙朝疫灾第三时段(1688—1708)广度波动上升的主因[8]。(2)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夏间,受长江大水、黄淮交漫、饥荒谷贵等影响,舒城、庐江、无为、扬州、高邮、兴化、如皋、阜宁、山阳、天长、来安、望江等地同时瘟疫。(3)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夏雨水多,灾后疫气交作,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和州、六安与临近的阜阳、来安、怀宁、定远、宿州、霍邱等江淮州县皆有疫情报告。以上3个高发时段也是全国范围内疫灾密集期。
清代后期,咸同之际(1856—1863)巢湖流域疫灾流行,并与大区域疫病同灾。咸丰六年(1856),长江南北州县大旱,庐、凤、颍、六州县蝗甚;咸丰七年(1857),庐江、舒城夏旱蝗疫,周边诸县亦大饥,秋大疫;咸丰八年(1858),舒城、六安一带,夏秋又有疫情。同治元年(1862),庐江饥疫交迫,和州蝗害疫灾;第二年春,含山大疫。受战、疫、旱蝗灾等多重影响,民生疾苦。
(二)疫灾密集区域变化
在疫灾高发时段统计中,深入分析发现,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区域有一定密集性,并呈阶段性变化。
明代,从大区间范围看,巢湖流域隶属南直隶,而南直隶为当时全国疫情爆发频繁地,舒城、合肥又为该流域疫灾密集区。若将舒城疫灾置于舒城开发与人地关系演变中思考发现,明以前,舒城多良田,“昔之仕于此者率能兴水利以利民,故其田之所产视他邑加倍”[9]。明清时期,舒城旱涝频发,除与明清寒冰期气候变迁和地势地貌有关,也与巢湖流域上游水系之开发活动相关。随着流域经济发展与人口激增,攫取新耕地的比较利益导致人地关系紧张,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型生态失衡凸显,即疫灾前受灾风险的不均衡分布状况及其产生的社会源已形成,表现为自然灾害加剧并催生疫情。考察万历朝疫灾原因时发现:“仅万历朝大水8次、旱灾6次,而万历十六到十八年是水旱灾害连续爆发年”[10]。洪涝灾害加上米价涨,民众饥肠辘辘,疫情相伴而至,集中表现为万历十六年(1588)小疫,十七年(1589)冬疫重发,到十八年(1590)大疫。合肥疫灾和当时疫灾高发时段整体环境、交通便捷、人口流动、经济发展与人口密集等易发疫灾的脆弱性社会环境相关[11]。二者共同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对疫灾的综合影响。
清代康乾时代,巢湖流域疫灾密集区域在无为县疫灾共有11次,其中8次与水灾有关:康熙四十七年(1708),大水,圩田尽没,冬疫、来年春疫共2次;雍正五年(1727),五至七月前后大雨,圩尽没,岁饥,民食草根树皮殆尽,来年春疫;乾隆六到七年(1741—1742),江潮大涨,民多疫;乾隆二十年(1755),连绵雨水,没圩几尽,冈田虫伤,春饥酿成死者无算,来年大疫;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五月倾盆大雨始,临江及二坝相继破,江水横入圩田。乾隆三十四年(1769),淫雨,圩田、堤岸尽沉。水灾连续5年,在此期间,乾隆三十年(1765)、三十三年(1768)疫灾;乾隆五十一年(1786),先奇旱致疫,秋又大水,拖延疫情。无为也是清代安徽疫灾年数最多州县[12]。清中后期,疫灾密集区在庐江一带,仅道光末年到咸同之际,庐江疫灾5次,后清军与太平军战地从安庆往南京、芜湖迁徙,途经和州、含山,这两地各历疫灾1次。寻因可见,流域内两军的拉锯战、饥饿和流民等加剧了社会环境脆弱性,加之旱蝗灾形成的脆弱自然环境,两相交叠,瘟疫流行。
从明清巢湖流域疫灾高发时段与密集区域变化看,疫灾主要发生在自然灾害频发与战争时期。巢湖流域处于长江水系,明清时期饥疫、兵疫、水疫、旱疫、冻饥疫、旱饥疫、水旱疫、旱蝗疫、水饥疫等组合形成长江流域人口死亡事件多元关系链[13]。疫灾和其它灾害多相伴而生,又与其它灾害共同冲击百姓安全。
(三)疫灾危害表现凸出
疫灾本为生命灾难,又带来后续危害,不仅造成人口减员,而且扰乱原有经济秩序与生活状态,百姓疾苦。
人口减员。疫灾对人体生命健康危害大,疫灾高发期与密集区存在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明代嘉靖二年(1523)、三年(1524)、十八年(1539)和万历十八年(1590),方志记“大疫,死者枕籍于道”,尤以嘉靖初期,庐州疫灾“一门之内多者十数口,少者三五口,甚有举家染病,无人炊爨,阖门就死,无人殡葬者”[1]229为最惨;崇祯十四年(1641),“巢县夏大疫,死者万余人”[4]461;康熙四十八年(1709)、雍正六年(1728)以“流离死亡者甚众”书之;乾隆二十一年(1756)、三十年(1765)、三十三年(1768)和咸丰八年(1858),言“疫饥死者无算”;乾隆五十一年(1786)复记“大疫,死又十之三”[5]41、“大饥而疫死者弥望”[14]413,以上年份流域内人口死亡率高,可见疫灾当为生命体之首位灾难。
米价不稳,影响民生。疫灾引发对最紧缺物资——粮食需求的心理恐慌,导致米价及生活物资价格飞涨,经济秩序也间或不稳。嘉靖二年(1524)、万历十七年(1589)、咸丰八年(1858)和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斗米百千钱,民之死者不可数计,经济不稳冲击了民众生存保障。尤其是咸丰十一年(1861),庐江秋,“贼以安省克复遁走,境内肃清。冬大雪平地数尺……斗米千钱,饥疫,野兽食人”[15]603。多灾之下,百姓遭饥成疫。
破坏原有生活秩序。疫灾与人口流亡,最大程度破坏农耕生活,有的因人口死亡,土地无法耕种;有的因人口流离,土地荒芜;有的不得已加入匪贼之列,诸如此类非常态或失范行为,极有可能成为社会危机“助燃剂”。民众生活艰辛,只能靠树皮草根度日,如“康熙四十八年,无为春洊饥,饥民采草根树皮以为食,继大疫”[14]411。激烈动荡中,原有社会伦理被破坏,弘治十七年(1504)、嘉靖二到三年(1523—1524)、万历十七年(1589)、崇祯十四年(1641)等年发生了“洊饥,人多相食”的悲剧。还有咸丰年间,舒城、六安一带“夏秋大疫,幸存者率挈妻女逃他州县,鬻之以获口”[16]。人食人(尸体)既为疫之因,又为疫灾之人伦惨剧,还有卖儿鬻女、抛妻弃子等,冲击了原有生活秩序与伦理道德。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所带来人口减员、米价不稳、生活失序等危害,一定程度上激发了遏制之法的出现,也势必需要官方的及时应疫。
二、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的官方应对举措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频仍,尤其在疫灾高发期和密集区所引发的社会公共安全危机,亟待各级政府做出回应,建立各级政府和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疫灾防御体系。结合明清时期疫灾记载,就当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应对巢湖流域疫灾的举措作一探索。
(一)增设地方医疗机构
明代设中央医疗机构,有向瘟疫发生地遣医治疗的任务,但主要负责皇室与京师救疗,地方上增设府州县惠民药局,遇岁疫病,派遣医官,施药救治。洪武三年(1370),地方设惠民药局,授主管掌全面事务,授副训科员管药政,授内外科官医提领治疗疾疫,后太宗、宣宗、宪宗多有诏令发挥地方药局作用。明中后期,医疗建设式微,惠民药局多有废止。但疫灾时期,朝廷令医生开局于城隍庙施药,地方官会在旧址发放药物,有时大臣也会奏请重开药局以遏瘟疫。万历十五年(1587),南直隶特大疫,南京礼科给事中朱维藩“奏复药局以救荒疫,报可”[17],后庐州、和州开药局救疫。实际运作上,药局工作人员的稀缺与亟待救助的民众群体形成极大反差,有限的医疗资源难以权衡和有序化分配,明中后期惠民药局大多为疫灾时紧急开局施药,疫情一旦结束即被忽略,直待疫情再发,其逐渐从原有医疗机构演化为荒政社会救灾的临时机构。
清代承袭前制,疫灾之际,中央太医院派医官诊治疫病,地方设医学署以遣医赠药,刊刻医书,普及疫病救疗知识。从现有疫灾高发时段资料看,康熙帝对天花等瘟疫的重视、雍正帝要求必须精通《伤寒论》方为医官、乾隆帝大量的救疫投入等体现清前期皇帝的“仁本”思想以及个人意志对朝廷救疫政令的影响[18]。但制度性卫生防疫机制缺失,就地方医学署应疫能力看,其在强大民间医学、清廷式微和战乱不已等压力下日益衰弱。直到光绪末年,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西方医学双重因子促推下,国家方才建立政府主导、着力于富强的卫生防疫机制,推行新官制,专设“卫生掌检医防疫,建置病院”[19]3452“军医掌防疫、治疗,兼司军医升迁教育”[19]3459,标志着卫生防疫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出现,推动了近代卫生防疫事业发展。
总之,面对地方疫灾,中央太医院等虽有大疫期间社会救助之任务,但主要通过地方医疗机构遣医施药、编防疫方书以防疫灾等,其与规模庞大的服务统治阶层之太医院相比,力量相形见绌。这一时期,整体医疗水平有限,预防疫灾措施少,防疫机制缺乏,防疫意识薄弱,临阵裁方多,医疗队伍亦有失位,救疫大多由地方社会承担,这为民间医学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设仓积谷,力防饥疫
除医疗救助外,在中央政府“设仓备赈”统一要求下,设立仓储为灾民提供粮食是灾荒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在中央政策要求下,巢湖流域建立常平、惠民、预(裕)备、济农、社、义、营仓等整套仓储制度。洪武初年(1368),合肥设惠民、永丰和内仓,为本府预备仓,选耆民运钞籴米,以备赈济。清初,改为常平仓[20]77。嘉靖年间,诏令各抚按设社仓,合肥立本仁、宏济、广义、济惠、博爱和社仓,年饥上户不足者量贷,岁稔还仓[20]77。明代和州设预备、济农、益民仓,清代在中央直省州县卫所立仓以备赈要求下,设常平、和丰、预备、社、东、西、南、北、州、梁仓和尹家廒,含山亦设常平、社仓[21]190‐191。庐江预备仓,弘治年间知县胡阳合建于南门桥外,嘉靖知县汤彬移建马神祠前,万历知县章远重建。顺治年间,庐江知县孙宏喆重修,又增建东仓7间、西仓5间[15]65,后屡修扩建。
清前期,庐州府常平仓额储捐积米74 000石,储备仓储米麦谷35 000石,社仓储谷28 900石;和州常平仓额储捐积米31 000石,储备仓储米麦谷20 000石,社仓储谷14 300石[22]834。可见仓储有粮,各府县在饥疫之际有一定能力开仓救济,自康熙朝“每岁秋收,劝谕官民,捐输米谷,照例议叙,到嘉庆年间,虽遇水旱灾害,民无艰食也”[20]77。康熙四十七到四十八年(1708—1709),疫灾高发,巢湖流域各州县“动常平仓谷,赈济”[23]170。雍正四年(1726),望江、无为、铜陵、宣城、芜湖、繁昌、贵池等被灾州县,将社、常平、省仓捐还漕米,并安徽截留漕米内动用,设厂煮赈[22]835。清前期,仓储备荒是国家救灾重要一环,学者认为乾隆大旱,在备荒、平抑粮价、救助贫民之时,仓储粮食充足,政府救灾用款约占全部财政支出25%。而光绪初年,粮食储存寥寥无几,大旱发生时,仓储无力救灾[24]。鸦片战争后,财政危机加诸白银赔款,仓储救灾有限,使得救疫时捉襟见肘。
明清时期,设仓积谷内化为灾疫之际国家常规制度,积谷防疫成为国家荒政防御体系一部分,但两朝后期,受国家财力制约,救饥防疫能力有限。
(三)紧急救疫,上下发力
疫灾之际,其与水旱蝗灾所引发的灾害危机受到各级政府关注,紧急救疫既是家国一体化观念下对中央朝廷的考验,同为地方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从中央政府看,首要任务是启动紧急救疫相关办法。明清时期,从上到下形成备灾、报灾、救灾、赈济、安抚整套救助体系,官员严察灾情,及时报告,形成防疫首道屏障。朝廷要求官员及时查明成灾轻重和蠲免分数,对失职者予以严厉处罚这种责任追究和及时报告制度逐步成为应疫基本制度。其次,组织救疫人员。中央政府一般不直接参与地方疫病救治,但严选疫情勘灾人员,前往疫区指导并监督地方查灾,向地方提供赈疫物资,减免赋税徭役。嘉靖初期疫灾高发,流民四起,朝廷特派专员席书前往巢湖流域各州县救疫。同时,为保证疫灾时地方政府职能运作,中央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使其专心于地方救疫。正德帝曾下令各处被灾地方,许抚按官预先勘实具奏,疫灾期间免其正官朝觐。再次,组织医生前往灾区救疫,防止疫情扩散。朝廷规定当地医生要第一时间投身救疫,附近医生也会接到诏令,援助疫灾地。救疫奖励制度亦不可少。无论常规措施还是灾后应对,体现了一定的制度化管理,要求地方官照章办事,将官吏救疫救灾行为与其黜陟结合,把办赈好坏作为评估官员政绩标准之一,保证地方官办赈救疫时尽心尽力。
地方政府是地方疫灾应对的主体。明清时期,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地方政府通过协调粮药等物资开展直接应疫。一是实施煮赈。时人深知:“煮粥虽号为救荒下策,然济急实为最切”[25]232。粥赈有利于增强民众抵抗力,减低染疫率。嘉靖初年,疫灾多发,《(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光绪)庐江县志》《(嘉庆)舒城县志》和《(嘉庆)无为州志》等记载了朝廷命户部侍郎席书在庐州、和州赈济,地方抚按会同赈粥之事。万历十七年(1589),舒城民多饿死,邑令林材设厂赈粥存活万人[5]38。无论当地灾民还是流民,都是赈粥对象,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保存了劳动力。二是发放救疫药物。疫灾爆发后,中央政府统一收集药材资源,由地方政府免费发给疫区百姓。发放形式多样,有时通过官员直接上门发放,如正德二年(1507),庐州大疫,知府杨璲请祷,遍给医药使民活。嘉靖二到三年(1523—1524),庐州瘟疫,知府龙诰“逐村施药,既给之姜茶,又赈以食米”[1]229。也有组织疫苗接种,康熙帝曾谕旨地方组织种痘预防天花,抗疫费用由朝廷负担,一定程度上体现上下两级政府的互动。还有煮赈发药,《荒政全书》收录清人陆曾禹所见:“粥厂亲申贫民,收养流民,散给药饵。”[25]429‐430时人也发现粥厂附近高密度、低免疫力人群是疫病传染源,建议集中杀菌,“多置苍术,醋碗,熏烧以逐瘟气”[25]18。三是施棺椁墓地。染疫尸体处理不妥会使疫情恶化,逢大疫,埋尸骨,助棺葬成为地方政府及官员救疫行为之一。洪武年间,中央设义冢制度,由地方官府负责“以义地收瘞之”,诸多地方官如和州黄鹤鸣、庐州沈玮、董史、周良会等。也加入疫灾时“埋枯骨”“施棺掩骼”中,还有驱疫祈禳,也为政府采用以安民心。
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应疫主要责任人。换句话说,各级政府应疫责任伦理最终通过地方官落实。疫灾之际,他们常奉国家诏令,深入疫区,鼓励民间力量救疫,安排物资,勘疫与赈恤民众等。万历八年(1580),查志文任无为同知,掌州事,“岁值旱潦疫疠,亲巡郊野,施粥布泉,给药饵,赈种具,拊循拯恤,无不具备”[23]261。地方官亲临疫区,行为本身危险,却有利于疫区民心稳定。崇祯十四年(1641),舒城大疫,王朝岌岌可危,人多相食,翰林胡守恒仍设赈救民。同朝代的左瑛,知和州,“崇祯辛巳、壬午间,岁大饥,劝募赈济,多所全活”[21]435,救饥成效明显,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饥疫灾害。雍正九年(1731),和州旱疫,黄鹤鸣和州知州,“浚市河,埋枯骨,筑青云坝,捐卖籍田,详准滁南减捆入地丁征收,分款批解,群黎霑惠”[21]436,后迁镇江知府,“去之日,百姓泣留三日,阖郡建清正亭于州之东”[21]436,应疫行为妥帖,得到朝廷与民众双重认可。大多地方官对救疫的信心以及深入疫区之快速行动使其处于官方救疫之关键位置[26]。巢湖流域地方官行为体现了“仁民爱物”道德素养及其对职业岗位的浸润,这一精神的延续也深刻影响地方官应疫观念与实践。
(四)赈济蠲免,恢复生产
古代疫灾大多为自然灾害之伴生灾害,故其与水旱灾一起被勘定成灾分数,等候赈灾。赈济蠲免,助民耕种,是古代荒政社会疫灾后恢复社会发展的基本举措。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常用赈灾手段:一是蠲免,免除全部钱粮杂税,对灾疫严重区实施;二是缓征,对于灾疫轻微区适用,也有贷借钱粮、种子、农具和鼓励农耕等政策。现结合康乾时期流域内疫灾高发时段论述。康熙四十八年(1709),安徽大疫,巢湖流域水旱饥疫同现,清政府对安徽蠲免赈济,“四月,以潜山、宿松、宣城、铜陵、石埭、当涂、芜湖、繁昌、望江、贵池、青阳、南陵、无为、和州、含山、建平、泾县、巢县共十八州县,……蠲免地丁银七万五百二十一两有奇,米豆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八石有奇”[22]834,之后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疫灾广度降低,受灾区分布稀疏,说明这次疫后蠲免行之有效。乾隆二十一年(1756)疫灾多发,第二年,蠲免安徽之前所积欠未完地丁银,在《直隶和州志》《(嘉庆)无为县志》中有记。乾隆三十五年(1770)上谕:“安徽各属上年因春夏雨多,或江湖泛涨,被有偏灾,著再加恩将怀宁等十四州县被灾九十分之极贫加赈两月……八十分之极贫俱加赈一月”[22]841,有“合肥全免本年钱粮”[20]79“庐江免丁地起存钱粮”[15]110等附记,并有和州疫灾,“蠲免安徽应输漕米一次,又于普蠲各省钱粮内输免钱粮一次。”[21]186乾隆五十到五十一年(1785—1786)疫灾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上谕:“去年春夏雨水稍多,又灾后疫气交作,民间元气未能遽复,若令新旧并征,小民输将未免拮据,庐州府属之舒城,和州并所属之含山等十六州县,去年应征旧欠及历年灾缓钱粮、借欠本折籽种口粮等项,俱着缓”[22]843。以上年份,巢湖流域先有灾疫后获蠲赈。清代救疫救灾投入在乾隆后期之前,基本与灾况保持,康乾时代蠲赈占比最高,而后财政困难,灾况上升,蠲赈下降,嘉道之后,仓粮亏空,赈资欠缺,疫病流行,这也说明国家财政在应疫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上看,水旱疫灾后,中央政府诏令蠲赈并由地方付诸执行,给予了民众恢复生活的信心,嘉庆皇帝曾赞扬苏皖地方官救灾行为:“两省被灾严重,业经降旨蠲缓赈恤,不惜亿万帑金以全民命,当此嗷嗷待哺之时,全在地方官实心实力经理得宜,不使一夫失所”[22]138。然而,当时政府尚没有将救疫从灾荒救助中剥离。
(五)建立恤所,间接救疫
恤所建立并非都与疫灾有直接因果关系,但现实运作中,荒政救济理论是恤所建立的思想基础,灾疫频繁是其建立的环境因子,建成后成为拯救疾疫、接受贫老弱病残的慈善救济场所。所以,恤所救济为疫灾救助的间接行为之一。
在中央政府倡导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建立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局、广益局等恤所,功能大抵为扶弱济贫,留养幼孤老疾。清前期,诸帝多次诏令要求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庐州府广益局平时即有“设医药以轸疾病,施棺施茶,掩骼埋胔,收检字纸,并备救火器具”[2]239,不难想象疫灾时其救疫行为。巢县、舒城、和州、庐江皆有类似机构,大疫之际救治疾疫,收纳和救治贫苦无依疾疫者,为染疫者施医送药成为其社会责任。然而,恤所多以城市为中心而建,除因饥荒等流入城市的乡民,大多乡民无法享受救助。
综合而论,面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疫灾,官方应疫举措表现在增设地方医疗机构、设仓积谷、紧急救疫、灾后赈恤等方面,中央政府在具体应疫行为、相关政策落实和紧急物资给予中通过地方政府践行,又借力地方官主动性强化应疫效果,但各级政府应疫举措仍是古代灾荒社会救助行为的一部分。官方应疫举措总体上纾缓了疫情,虽有流民现象,但维护了地方社会的整体稳定。随着两朝末期政务废弛,腐败严重,战事频繁,又加以财政危机,接连旱蝗大疫,鼠疫与霍乱等再添救治难度,官方应疫实效并不尽如人意。
三、结 语
疫病流行既是国家治理之重大危机,也是完善治理系统与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契机。从疫灾官方应对看,责任伦理贯穿应疫救灾始终。明清统治阶级遇灾逢疫,必颁罪己诏以示责任担当,又通过救疫行为表明“民本”立场,并在天人感应思想架构下,认为居高位的帝王与天之间有更直接联系,应承担更多责任,进而将疫灾救治逐步内化为政治责任。政府抗疫的责任韧正通过治灾救疫实践不断淬炼。与此同时,抗疫时政府行为的下沉,地方官员救疫的责任担当等也在历史演进中不断砺炼,这些既是中华民族抗击疫病精神的写照,也是与疾疫抗争的重要力量来源。通过明清时期官方疫灾应对的表现,我们应当肯定并汲取其中的积极内涵。
当然,限于当时生产力和医疗水平,对明清时期官方应疫成效也不宜高估,对其存在的问题应予以关注。从理念上看,因疫灾与水旱蝗灾常伴生而来,故救疫仍被视为灾荒社会救助的一部分,然而疫灾传染性强、破坏性大、救助过程复杂,显然不同于救济灾荒。随着医疗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当代已然高度重视疫灾救助,并与自然灾害救助区分开来。同时也应注意思考防止多元灾害的叠加效应,尤不可完全割裂旱涝灾害与疫灾之关联,努力反思并建构生态、灾害与生命的和谐关系。从具体应对举措看,有的受医疗水平限制发病过快又不及医治而丧命,有的因医疗资源不足与财政困窘,诸多救疫措施临时、临事被动,这些为疫情当下及后疫情时代,加强常规医疗体制建设以防非常规、保有紧急医疗资源以防不测、重视应疫防御体系建设等提供了历史教训与灾害教育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