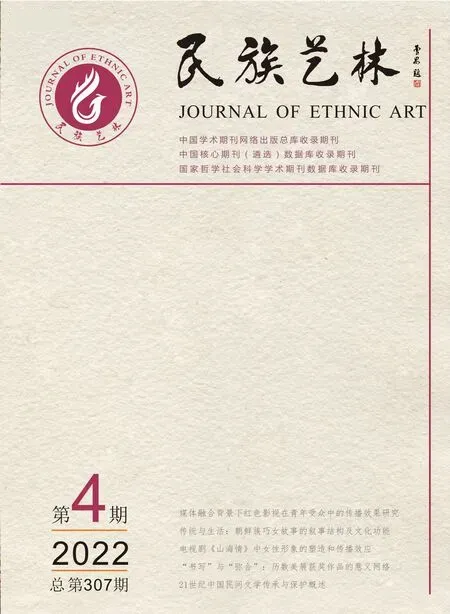《饮膳正要》体现的饮食文化交融
付皓田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呼和浩特 010020)
一、《饮膳正要》所体现的元代宫廷饮食变化
有元一代,领土疆域之大、通商往来之广在历史之上实属罕见。《元史·地理志》中描述为:“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在陆上,横贯亚欧大陆的诸汗国,保障着丝绸之路的再度畅通,四面八方的各类物产随之大量进入元朝;在海上,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高度开放,使得南亚、东南亚等地物产进入元代人民的生活。
元代饮食文化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逐渐发生变化,在保留其固有饮食喜好、传统食材、烹煮方式的同时,享用由海路、陆路输送而来的各类珍馐美味也渐成常态。随着食材来源的复杂化与多元文化的影响,元代社会对于奇珍异物的态度与认识也在发生改变。在《饮膳正要》开篇即言明:“伏睹国朝,奄有四海,遐迩罔不宾贡。珍味奇品,咸萃内府,或风土有所未宜,或燥湿不能相济,倘司庖厨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概于进献,则食之恐不免于致疾。”[2]以忽思慧为代表的饮膳官员,面对物产丰饶所带来的膳食新变革,不免有所担忧。同时,自北方草原南下入主中原的统治集团,因气候的调适以及日趋复杂的膳食需要,对忽思慧的工作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忽思慧等人历时多年精心编修,结合前代流传的饮食宜忌与汉唐本草医学,终于在元文宗天历三年进呈《饮膳正要》一书。书中不仅包含当时元代社会所常见的饮食材料、烹煮方式,而且以膳食为切入点,在言明诸般食材性味补忌的基础之上,倡导饮食调和、五味相谐。在饮食理念中,杂糅本草医学知识,借鉴西域诸族的饮食文化,形成了更适宜蒙元社会喜好的饮食文化实用性指南。
饮食的一面是生存所需,另一面则是口腹之欲。虽然忽思慧等人在食谱中收入各色酒水肉食,但是仍良言劝诫饮者应饮酒适度、不可大醉伤身。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以饮食为喻,婉言劝导君主应以前代世祖言谈举止为模范,“昔世祖皇帝,食饮必稽于本草,动静必准乎法度”,审慎地提出对于君主饮食的客观劝诫。
在《饮膳正要》的饮食调配中,不单注意常人所好的各色饭菜,其目光与着眼点更为深远。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基础上,兼顾疗养医疾之需要,形成药膳相合的膳食方案,对不同病症所需注意的饮食进补与膳食禁忌逐一言明。由此可见,编修者考虑周备、用心良苦。该书从日常膳食实践出发,以养生延寿为目标。调和搭配日常所见的各类食材,并斟酌选用适宜的烹煮方式,关注元代饮食的新变化趋势,在实践基础上吸收不同饮食文化优长,进而以实践总结理论经验,再次指导实践工作。
二、异域食材与烹煮再造
《饮膳正要·卷三》参考前代医家本草著述体例,逐一将当时膳食所常用的食材归为七类,即: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这七大类食材中,既有中原各地物产,也有不少域外之物。书中行文用语虽以汉语为主,但仍会使用部分食材的音译名词,可窥见其渊源与流传。
尚衍斌在《忽思慧〈饮膳正要〉不明名物考释》[3]《忽思慧〈饮膳正要〉不明名物再考释》[4]《忽思慧〈饮膳正要〉识读札记》[5]等文中对《饮膳正要》中的菜品、料物几大品类中所见的名物加以考释,如必思答、莳萝、哈昔泥、马思答吉等。同时,根据饭食炊煮的做法与物料,探讨元代社会多元族群文化的交融影响。
《饮膳正要》所载诸般食材的来源驳杂、品类繁多,产地横跨南北、并容东西。如产于东南亚、南亚的象肉、西北地区的驼肉,东北一带所产的阿八儿忽鱼、乞里麻鱼也进入视野,还有果蔬菜品中的八檐仁、必思答、沙吉木儿等物。
《饮膳正要》一书中,单列“料物”一类,其中所收的马思答吉、咱夫兰、哈昔呢、荜茇等物,并不在传统饮食常用料物之内。这些料物的运用,应该是随着饮食文化因素与食材的改变,传统料物的滋味难以与其相符,是为显其性味而与食材一并传入的。
《饮膳正要》所收的菜品不拘地域,烹煮技法也一应收入,如撒速汤、八儿不汤(文中称其系西天茶饭)。从文中所言各类菜品的渊源可以发现,在元代饮食文化的形成中,大批奇珍异物被纳入日常饮食,并且此后随着本土化的种植推广而渐入寻常百姓生活。同时,域外的烹饪技术也相伴而来。在长期的往来交流中,烹煮技法的传入进一步促进了饮食的多元性与风味的多样性。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物料的丰盈程度往往受交通、气候等条件所限变数颇多,而技法则因地制宜,在民众生活中落地生根,在民众饮食生活中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
在上述所记诸物中,可以发现元代饮食有其明显偏向,对于西域各地的物产投以相当关注。这也进一步说明,随着帝国的稳固,中亚、西亚等地再度因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与中国相连接。随着交流的稳定与繁盛,不仅使大量物产涌入,而且也带来了语言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再度传播。在东西密切的往来中,元代社会吸纳各类物产丰富饮食,接受烹煮技术、语言文化等潜在影响。多元文化如一颗颗种子随着通商往来的道路向四方播撒,在时间的长河中孕育生长,逐渐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心理与行为习惯。
三、《饮膳正要》中的劝谕
丰富多样的食材反映了统治集团在数十年东征西讨后所控制的横跨亚欧、世所罕见的疆域。但是,这也对统治者提出了新的考验。在版图基本奠定之后,军事征服的方式不再适用。统治集团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亿万民众,需要极大的智慧与策略来维持社会的运行。
《饮膳正要》一书虽从膳食出发,但是全书编纂的目的不单是为满足口舌之欲,而是以膳食为题引出对统治者的劝谕与引导。以忽思慧为代表的编纂者,不仅长于膳食、精于本草,通晓多种语言,而且深明儒家文化的修身治国之道,希冀以此书来尽人臣之责匡扶君主。
《饮膳正要》开篇序言征引元世祖遵从《周礼》、行依典故,进食“调和五味”“饮食相宜”,最终得以“圣寿延永无疾”的例子。在作如此铺垫之后,转而关切君主,盼其遵依祖宗定制以保其“圣躬万安”。文末忽思慧等人言辞恳切,尽表心意之忠坚。从元代历史来看,元代国祚虽短但是君主更迭频繁。对于一个偌大朝代的运行而言,这无异于是个极大的隐患。面对严峻残酷的现实问题,忽思慧等人恪守人臣之道,编纂修书以期上可辅佐君主治国理政,下可护其身体无恙,以此延续国家运行与长期稳定。明代景泰帝曾称许忽思慧“其执艺事,致忠爱,深于圣贤之道者不外是也”[6]。
忽思慧对当时宫廷饮食习惯中喜酒嗜肉之风表示担忧。《饮膳正要》以本草之要旨,不因宫廷贵人喜食肉类而投其所好,而是在肉食餐点中多佐以果蔬、米谷,以期调和膳食性质。对于时人好酒易醉之风,忽思慧认为饮酒过多会影响脏器与筋骨,甚至“多饮损寿伤神,易人本性”。在书中罗列的十三种酒品中,十种为药用滋补酒,余下三种为小黄米酒、阿剌吉酒、速儿麻酒,言明其性质,不置褒贬但其用意自明。
元代国祚虽短,但是在相对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之下,依然促生了时人学习多元文化并且对之积极实践的风尚。以忽思慧为代表的元代医疗、饮食官吏,善于接纳新食材、学习新烹煮技术,并努力促使其与传统饮食相调和。同时,面对饮食文化的变革,坚持以调和五味、延寿强身为要旨。不仅强调以饮食预防未病,而且希冀实现以君王之所安实现天下百姓之所安的宏大愿景。
四、文化交融下的饮食观念
(一)元代医学发展与饮食文化
《饮膳正要》一书的编纂者虽多,但是首功当推忽思慧。对于忽思慧其人史载甚少,生平经历也不甚详细。因此,《饮膳正要》中涉及的诸多细节,则为后人提供了些许参考。今人对其族别的考证本文不再赘述。从书中不难发现,忽思慧应当通晓多种语言,长于博物辨识。
《饮膳正要》以膳食为纲,但是明显偏重北方、西域的饮食风尚,反映出当时元朝宫廷饮食的偏好与习惯。书中并未局限于博物学的考证与烹煮调配,而兼唐宋以来本草医药与传统医学理论,甚至不乏宋代儒医的理念贯之其中。
元代建立之初,元世祖仿效《周礼》的记载设掌膳太医四人,专管膳食安排与餐具选配,并且对日常饮食随时记录以观后效。世祖之后,对于膳食官员的培养与任用,大体延续这一惯例。而后随着东西方往来通商的密切与更深层面的互动,关于饮食与医疗的关系也越发复杂。这也就要求饮膳太医一职不仅善于宴饮膳食的统筹安排,同时也必是精于医学、熟悉本草的医者,才可以应对新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元代医家创立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三皇祭祀。传统认识中,三皇具有“开天建极,创物垂范”的巨大影响,借此使医学、医生的社会地位较之前代有所提高。同时,元代医学教育置于三皇庙内传习讲授,如《全宁路新建三皇庙记》提及各地“立庙建学”,反映了元代医学以“庙学合一”的模式普及医学教育。而在实际教学中,虽分科传授相应内容,但是诸科讲习皆有《素问》《难经》以及本草。而对医学生的考核过程,不仅要求熟悉经义,而且要明识药性。
同时,医学授业不仅学习医书典籍还囊括儒学经典。这反映了宋代以来医家逐渐扭转前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偏见,儒士习医、从业者数量众多,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而涌现出诸多重要的医学典籍与医家。在这一过程中,医家的自身儒学修养随着其授业、成书影响开来,进而影响后世医家的思想观念,那就是不单以治愈疾痛为其目标,更以宏大的社会责任为己任。
因此,忽思慧不仅在饮食上格外注重膳食宜忌,而且强调饮食者的身行端正、心神相合。对于饮食者的各类不当行为都加以规劝。书中不乏明言直指各类行为不当所造成的祸患,特别是饮酒过甚最为忽思慧所强调。
在书前序言中,忽思慧自述其奉职时间,从中可以推断忽思慧身份不显、官爵不高,然而其历经元仁宗、英宗、泰定、天顺、文宗、明宗六位君主,见证了元朝的极盛之时也目睹了其未来的危机。由此,忽思慧晚年虽以年迈卸职,但是依然编修此书,希望可以为元朝的长治久安尽最后一份力。因而,忽思慧进呈《饮膳正要》一书,蕴含着他的政治理想与实现自身价值的二重含义。
(二)因势利导,调和本草
以忽思慧为代表的饮膳官员虽出身各异、族别不同,但是其履历大体相近,基本为元廷内侍近臣。作为宫廷膳食的首要责任者,如何满足众多食客的饮食需要并且调配各类食材,以期实现“以食为养,以食为医”的目标,是最为直接且重要的任务。
虽然忽思慧等人熟悉本草、见多识广,但是对于各类食材的选配依然慎之又慎。在《饮膳正要》中,常见于医家配伍的各类矿物均不见于食谱之内。而作为滋补之物,则多是选择蔬菜、肉食为大宗,滋补效果相对温和、平缓,避免势强过猛的食补菜色。元人久居北地,饮食风尚不同于中原南土。因此在《饮膳正要》中,南土菜色并不占优势,而西域菜色、北方饮食最为多见。食材之中,鱼品数量远逊于兽品,烹调制作也相对单调。这说明,忽思慧在考量编纂内容之时,对于中原、南土菜色或者鱼虾之属有所扬弃,着重考虑元廷内府的饮食习惯,在审慎思考之后方才撰写此书。
《饮膳正要》极为看重滋补之效,因为羊肉既能满足饮食之需又可补中益气,并且获取便易,所以书中所列食谱以食羊最为大宗。基于游牧民族对羊的了解,书中更为细致地按照毛色品类对羊群详加分类,以便于作不同用途。忽思慧针对元廷喜食羊肉的习惯细加应对,虽然以羊肉为主料的菜色可以迎合多数人的喜好,但是只用羊肉又稍显单调,在饮食中不足以做到膳食调和,因而,忽思慧在烹煮羊肉的各类技法中,佐以米谷、蔬菜来平衡膳食。
庞杂的各色肉类,对于烹调者是个巨大的考验。不仅要明晰其食忌、性味,更要在审辨其质性的基础之上,熟练引入各类料物,以调和肉类自身所带的腥膻异味。《饮膳正要》所见的各类料物来源庞杂、用法不一。相比于传统汉文化饮食的料物,其性味更为浑厚强势,多适用于对肉食的烹煮。唯有善使料物,通晓烹煮之道的庖厨,才可发挥料物之妙用,祛肉品腥膻促其鲜美。
而对于各类肉食副产,诸如头蹄内脏此类,在《饮膳正要》中并未对此视而不见,而是指出要精心烹煮、佐以各类料物,最大限度利用可用之物。食谱之内详细列出羊血、羊心、羊肝、羊骨、羊髓等食材的功效与烹煮技法,最大限度做到不弃一物。在草原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多以奶食、米谷为重,屠宰牲畜意味着产奶、繁殖的下降,所以屠宰的牲畜务必充分利用、不可浪费。这体现出草原民族对于食物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
饮食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从不同侧面使我们思考认识了元代饮食文化的多元包容。一方面,其在广泛吸纳异域诸方各类食材的同时,革新改进烹煮技术,尝试接纳与其相合的各类料物;另一方面,又在立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之上进行推广实践。
(三)以食为引,善寓明理
前文所述,忽思慧等编纂者的族属虽非汉族人,但是其饮食思想中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影响印记。全书循序渐进,以饮食着眼,系统性地剖析了元廷在不同文化交互影响、海内外诸多奇珍异物的冲击下是如何建立其饮食文化并付诸实践的。
《饮膳正要》的卷一即以三皇圣纪为开篇,叙说上古圣贤明天道、食有据、行有度,所以称为之圣贤。试图阐释饮食行为与世人修身养命的道理,以此作为下文的立论之基,证实书中所言并非杜撰空言。而后随即阐述“食禁”的各个方面。劝诫饮食需要审慎小心,在养生、妊娠、乳母、饮酒四个方面,进一步细致说明“食禁”之道。对于饮膳之人,不单需要注意口腹之欲,更要注意情志、道德行为的端正,防范饮食可能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
细究其理,忽思慧在面对当时元廷内的饮食习惯渐变、食材种类繁杂等现实问题,唯有抓住其主要矛盾,方可解决实际问题。首先,言明“食禁”、防微杜渐;其次,依照不同身份、不同需要单列所禁;最后,推及最为严肃的问题,即饮酒过甚。由此形成了其饮食思想的基础:知禁。
卷二是忽思慧编纂《饮膳正要》的核心所在,不仅总结、编排大量饮食的做法,考量菜色的搭配与其性质,而且在其中言明“以食为养,病以食医”的饮食理念与原则。
从平常易得的各类饮品到神仙服食的诸般异物,反映了《饮膳正要》既有其设计的社会现实,又希冀以修仙长生来影响他人效仿;而四时所宜与五味偏走,则遵照汉文化的经典理论认为饮食当四时五味相谐调和,方才最为适宜滋补疗养;而食疗诸病一节,详细论及各类病症服药之时当有所忌,不可因口舌之快使病症难消。卷二的内容广收多引,对时节宜忌、病患修养提出全面细致的说明阐述,意在使饮食发挥功效。由此,完成了其饮食思想的进阶:明养。
卷三开列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七类。每类中各样食材均以传统医籍中本草形式写出,将前两卷所见的各类食材加以细说,言明其特性,强调了饮食烹调的核心:识材。
从前两卷看过来,卷三内容尤为简明易懂,对于实际工作更具指导性。将这七类置于末尾看似前后倒置,实则别有深意。一般而言,应是先熟知各类食材,次之烹煮加工,最后由技入道。然而,《饮膳正要》反之而行,说明忽思慧等人的饮食思想并不局限于制作珍馐美味,还希望传达核心思想,希望后人在阅读前文之后掌握其中的奥妙。
忽思慧见证了元朝的辉煌。他在数十年里广学博闻,经手各类食材的宝贵经历,催生了其作为医家,书本草未尽之事的责任感。他深知不论是食材还是烹煮技法都会改变,食材搭配更为复杂、无法穷尽,所以在最后尽其所知,阐明各类食材的质性,留给后人去审视与尝试。
五、结语
在元代,随着亚欧大陆商道再兴与多元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丰饶物产与异族文化相伴进入中国。饮食虽不及治国理政重要,但却是诸多矛盾的集合,不可避免地处于时代漩涡之中。以忽思慧为代表的编纂者,直面这一时代与社会的问题,他们凭借自身学识与能力,试图从中调和诸般矛盾。一方面借力于汉文化的医学药理、儒学思想;另一方面吸纳异域诸方各色食材,并且不背离固有传统饮食文化,在此基础之上促生《饮膳正要》的编纂。作为系统性的饮食文化,全书不仅实践可行,而且更希望以饮食文化为导引,关注身心健康,进而推及国家的长治久安。长期以来,虽然《饮膳正要》流行不广、声名不显,但是其价值意义不可小觑。书中虽不可避免地存在神仙服药的内容,但是其保存记录了众多烹饪技法与异域食材。更为可贵的是,它为我们面对多元饮食文化冲击的当下,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与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