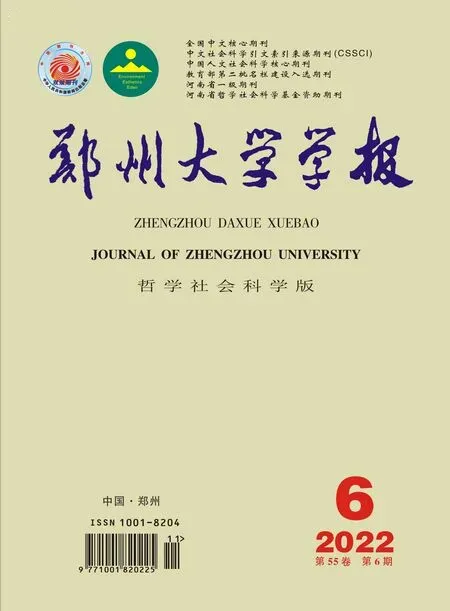论二里头文化龙崇拜及其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意义
袁 广 阔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1977年,中国考古学会在河南登封召开了“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邹衡先生发表了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的新观点,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认识因此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1983年与二里头近在咫尺的偃师商城发现后,多数学者放弃二里头遗址为西亳的看法,认为偃师商城才是西亳。后来偃师商城小城的发现又加强了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的认识。正如郑杰祥先生所说:“偃师商城处在原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区,显而易见,它应是商人灭夏以后在这里建立的一座重镇,用以巩固商初西部边防并镇压夏人的复辟。”[2]但由于二里头遗址缺乏文字资料,以及相关文献记述零散匮乏等原因,整个史学界还有一些学者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持怀疑态度。2002年二里头遗址大型绿松石龙发现以后,杜金鹏[3]、王震中[4]、朱乃诚[5]、王青[6]、李德方[7]等学者纷纷著文进行探讨,一致主张二里头的龙形象与夏文化关系密切,龙应代表夏部族对龙图腾的崇拜。可以说,龙主题遗存代表了夏部族对龙图腾的特殊崇拜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笔者发现,龙纹遗物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土,而二里岗文化早期遗址中几乎不见,其中与二里头遗址临近的偃师商城中龙图案或类似龙图案都没有发现,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古代文献中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很多,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就显示出从龙崇拜视角研究二里头文化性质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因此,本文旨在阐释对二里头遗址龙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与新认识,并拓展至夏商文化发展及时间节点问题。
一、二里头遗址的龙文化遗存
二里头遗址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始调查发掘,到现在已超过半个多世纪,该遗址出土了众多遗物,包括陶器、玉器、铜器、石器以及骨角器等。遗址中发现的大量与龙相关的遗存尤其引人注目,这些龙遗存多出土于墓葬及与祭祀有关的遗迹中,按照反映载体可以分为青铜器、漆木器、陶器和玉器四类。现举要如下。
1.青铜器上的龙纹
二里头遗址铜牌上的绿松石变形龙纹最为典型。如V区M4中出土3件绿松石铜牌饰(81VM4∶5、84Ⅵ M11∶7、87ⅥM57∶4),平面均呈长圆形似盾,中部呈弧形束腰状,两侧各有二穿孔钮,凸面(正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组成变形“龙”纹。铜牌正面浮雕式的兽面纹用绿松石片镶嵌而成[8]。此外,海外博物馆及私人藏有 12 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造型与二里头遗址出土者极为相似,有学者曾论证过这些器物之间的演变序列,认为它们或出自二里头遗址,后来流失于海外[6]。
圆鼎上也应有龙纹存在。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出土一件陶范,范内有阴线刻划出的龙纹,龙的嘴部和左前肢尚有保留,龙口大张带尖齿,利爪[9](图版七:1)。廉海萍推断这件陶范残块可能是鼎形铜器外范[10]的一部分。
2.漆木器上的龙纹
二里头遗址出土漆木器上的长条形龙造型独特。如2002年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一座墓葬(编号02VM3)中清理出一龙形器,系用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分龙头和龙身两部分。龙头为方形,臣形双目,龙眼用圆饼形白玉做成,龙鼻用蒜头形绿松石粘嵌,鼻梁和额面中脊用青、白相间的玉柱排列成纵长条形。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形状,象征鳞纹的绿松石片分布全身。清理时整个龙形器及其近旁发现多处红色漆痕,因而发掘者推测绿松石龙形器与其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应为一体[11]。
3.陶器上的龙纹
陶器上的龙纹可分为陶塑、雕刻两类,内容包括“龙与兔”“龙与龟”“龙与蝉”“龙与鱼”等组合图案。
“龙与兔”。位于透底器(ⅤT212⑤:1)上,龙形象为一首双身,头朝下,眼珠外凸,在龙的头部附近饰有云雷纹;在龙的身体上面有对称小兔,仰卧,四足朝上,兔眼眶内涂有翠绿色,雕刻精细,形象神秘。杜金鹏首先发现这件标本是透底器的残片,并将龙头两侧的云雷纹视为勾云纹,指出该纹饰构图有“飞龙在天、腾云驾雾,指探月宫之意境”[3]。王青经过研究复原认为该图像应是以一首双身龙为中轴,左右对称分布,纹饰可以分为两层,上层是分开的龙身及对称卧兔和回纹,下层龙头两侧为卷云纹[6]。
“龙与龟”。纹饰所附陶器残片疑为透底器(V·ⅡT107③:2),1959年出土于2号宫殿基址南部,陶片上刻划纹饰保留不全,保存部分上刻画有龟纹和龙纹,龟体的一半已残,龙为蛇形,只存头部,为龙的俯身形象[12]。
“龙与蝉”。位于透底器(VT210④ B∶3)上,出土于一号宫殿基址西南部,陶器上刻划的图案由龙、蝉、神像和双头小龙组成,主体为一长龙,细线刻纹饰,龙首残缺但可辨龙眼,龙身弯曲,长尾飘起,身下似有一爪[13]。
“龙与太阳”。纹饰附方形鼎(仿铜陶器)上,如陶方形鼎(83YLⅣH20:1),鼎的一面饰有太阳纹,另一面饰有一兽形纹。内壁刻画有龙头,龙口大张,露尖齿,前肢粗短有利爪,发掘者将其解释为“龙神像”[3]。
“龙与鱼”。纹饰所附的陶盆(03ⅤG14:16)为大敞口,口沿内侧有一条蛇形龙盘踞,龙头向上弯曲,圆目外凸,首尾相接,龙尾位于龙头的正下方,龙身饰有清晰的鳞纹,龙的首尾有小鱼相伴[13]。
“多龙聚会”。纹饰位于陶透底器(92YLⅢH1)上,器壁有菱形纹饰,其上塑出三条小龙,小龙体呈弯曲状,三角形龙首向上。92YLⅢH2 陶透底器雕塑六条小龙,形象生动[14]。
4.玉器上的龙纹
牙璋上的龙。邓聪认为:“二里头牙璋的扉牙实际是龙的侧面形象,并以长方形张嘴龙头为特征,它是牙璋龙化一种信仰神力的添加。”[15]这一认识深刻揭示了牙璋与龙的关系。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境内,毗邻的陕西、湖北、山西也有少量分布。河南境内经过正式发掘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40余处,考古调查的遗址约100余处,其中洛阳盆地的伊河、洛河流域,郑州一带的索须河流域,漯河、平顶山地区的淮河支流流域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而且在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荥阳东赵、平顶山蒲城店、新郑望京楼等都发现了城址[16]。二里头文化的众多遗址中,唯独二里头遗址出土大量与龙文化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其它的城址如大师姑、望京楼等虽然发掘出较大规模的城邑,但没有发现与龙有关的遗物,这充分说明龙在当时的神圣性和都邑的专有性。
二、龙文化在夏商分界研究中的意义
1.龙文化与夏商葬俗
二里头遗址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数量多,随葬品丰富。据研究,二里头遗址已有不下10座墓出土了各种镶嵌牌饰,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有8座,占当时已发现的18座中型墓的一半[17]。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纹遗物有相当一部分出土于墓葬,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为代表,且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多属于大中型墓葬,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较高。以Ⅵ区M57为例,该墓为长方形,墓底有2—3厘米厚的朱砂,有木质葬具。随葬品除绿松石铜牌饰外,还有铜器、玉器、陶器和漆器等。可见,二里头遗址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葬都具有较高的规格。
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墓葬目前已发现2座。其中02VM3埋葬在3号大型建筑基址南院内,属二里头文化二期。墓主为成年男性,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形器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绿松石龙形器放置在死者的肩部至髋骨处。龙身中部还置一铜铃,正位于墓主腰部。已探明3号建筑基址长达150余米,宽约50米,有三重庭院,主殿的夯土台基宽6米余。朱乃诚认为:“3号大型建筑基址可能与王室或‘王’者有关。反映出02VM3墓葬主人与王室成员或‘王’者是有某种联系的。”[5]王青认为:“02VM3墓主那位使用仪仗性法器镶嵌龙形器的祭司很可能是这隆重仪式的主祭,而使用各种小型佩挂式法器镶嵌牌饰的祭司很可能是仪式的辅祭。”[17]
早商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两城址都清理出二里岗期墓葬上百座。其中郑州商城河务局家属院内的M6位于宫殿区,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内葬3具人骨架,2号骨架为墓主人,位于中间,是一成年男性,上下铺撒大量朱砂,颈部挂一串饰,1、3号骨架的身份应为殉人。该墓随葬品达142件,有青铜器、玉器、骨器、蚌器等[18]。墓葬的位置和规模与二里头遗址02VM3接近,随葬品也很丰富,但郑州商城遗址M6没有与龙相关的遗物。
偃师商城内目前发现的早商墓葬正式发表了79座。墓葬多分布于大城城墙内外两侧,宫城北部和内城建筑群内也有少量墓葬。虽然这些墓葬部分随葬有青铜器,但无任何与龙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出土[19]。
早商最具代表性的遗址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清理出二里岗期墓葬上百座,均无龙形遗迹遗物出土,不见随葬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随葬品的礼器组合也与二里头文化完全不同,这反映出二里头和二里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2.龙文化与夏商礼器
二里头文化遗址已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中型墓葬中,因此可能还无法代表当时青铜冶铸的最高水平。《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作者总结二里头文化青铜冶铸业的成就时指出:“第一,(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型专业青铜作坊与青铜器工业中心出现。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相当大,延续时间长。迄今的发现,主要限于与铸造有关的设施和遗物。上述用于浇铸的工场、可能用于烘烤陶范的陶窑、预热陶范的房子,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的专门化。第二,铸铜技术水平提高与青铜礼器的初创。二里头文化由多块内、外范拼合而铸造的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在中国古代金属铸造工艺史上是个飞跃,为商周灿烂的青铜文明的形成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20]
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器类有鼎、爵、盉、斝等,鼎上的纹饰最具特征的是龙纹。如上述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出土一件陶范(鼎),范内即刻有龙纹。
在陶礼器方面,二里头文化陶礼器主要是酒礼器和祭祀用的透底器等。酒礼器主要是盉、鬶、觚、爵、豆、杯等,此类礼器多为素面,一般饰简单的弦纹、凸弦纹、圆点纹等。
祭祀用的专有礼器——透底器所刻绘或雕塑的龙纹最为特殊。
早商时期青铜器数量大增。青铜器表面常见的纹样有乳钉纹、弦纹、卷云纹、兽面纹(饕餮纹)、云雷纹、人字纹、斜方格纹、龟纹等。商代前期的青铜器纹饰以兽面纹为主,一般呈带状饰于器物的颈部和腹部,多为无底纹的单层装饰,纹饰多平雕,饕餮纹通常由两个夔纹组成,采用粗犷的曲线,突出眼和嘴。一般取左右对称之式,或进行分解突出眼和嘴,直鼻大口,双目突出,兽角略小,身、首连成一片。整体形象抽象而富有变化。另外,还有乳钉纹、雷纹等一些简单的几何纹饰。早商白家庄期,青铜器上出现浮雕兽面纹,兽目十分突出。此期的兽面纹多以云雷纹为地纹,兽面的主干和地纹都不明显。纹饰多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龙纹头部和躯体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如郑州商城城外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都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商城的青铜器祭祀坑(也称窖藏坑),其中不少器物应为王室重器,但也没有发现饰有龙纹的,可见龙纹在早商时期的地位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早商时期的陶礼器如斝、觚、爵、簋等多饰云雷纹、兽面纹、涡旋纹、圆圈纹等,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文化祭祀礼器透底器在二里岗文化中也有发现,但也不刻划龙纹。
需要说明的是,早商时期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青铜礼器、陶礼器都流行兽面纹,这些兽面形象应当为虎,如郑州商代二里岗上层出土的“人兽母题”纹饰。图案出现在陶簋腹部残片上,“左侧为一个刻有面、眼、鼻、口、耳的人头像,头下有颈,颈下有肩;在人头左侧刻有一只形似作跪立状的侧面虎,口大张,目前视,作欲吞噬人头状”[21]。这与商代后期青铜器上常见的“虎食人”图案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
总之,兽面纹(饕餮)是早商时代最主要的铜器纹样,占据着主要地位。兽面纹样与器形浑然一体,以神秘和恐怖的形象示人。二里头文化的龙纹则占主要地位,二者比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由此可以看出早商文化阶段,商文化已经完成了对夏文化的吸收,二者在器物种类和风格上都有一定的继承性。其中各种材质的工艺美术品,如绿松石制品、象牙制品、金制品、玉制品、骨制品、蚌制品等表现得更为明显。但二里头文化采用了刻划、雕塑、镶嵌和铸造、镶嵌兼施等多种创作技法创造的龙纹,在随之而来的二里岗文化中不见踪迹,说明龙纹在夏商分界方面具有独特意义。
三、古代文献中夏与龙的关系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盘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开启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建设。夏人不仅认为龙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认为龙与自身的存亡有着密切关系,这在文献记载中有明确表现。
1.夏人养龙驯龙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驯龙的历史可追溯至帝舜之时,以后帝舜氏世世代代均有养龙者。而夏代国君孔甲尤其好龙,“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记述:“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这段话说明夏室衰微与孔甲的淫乱食龙有关,同时也道出了龙对夏的重要性。夏人有尊龙、养龙的官职,龙与夏室的兴亡紧密相关。朱乃诚曾提出二里头遗址幕葬中佩带绿松石龙形器者是当时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或许当时确曾有驯养“龙”的专门人才。结合文献看,我们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
2.夏王朝的开创者与龙有关
夏王朝第一代君主禹的父亲死后化身为黄龙的故事史籍屡有记载。如《归藏·启筮》云:“鲧(禹之父)死……化为黄龙。”《归藏·开领》篇云:“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夏人也即龙之后。考“禹”之字义,学界已有颇多成果。《说文》中直言:“禹,虫也。”而古人认为“龙为鳞虫之长”。进一步考证,有学者认为“禹”字的本义即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运动中的蛇”[22],龙与蛇的特征则更为接近。因此“禹”的字义本身就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以其为名的君王很可能就是龙的化身。在文献中还可见到有关夏有龙瑞的记述,如《竹书纪年》:“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史记·封禅书》:“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我们若以后世阴阳家之五德论比附之,或可说夏王朝是有“龙德”“龙瑞”的,龙之于夏王朝的兴衰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再看一则有关夏王朝第二代君主夏启与龙的记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人珥两龙,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启)。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故事也可见夏人与龙的关系密切,以其为坐骑,乘龙上天。可见,夏王朝的开创者鲧、禹、启都与龙关系密切。
3.夏代巫师祭祀的舞蹈与龙有关
祭祀在中国古代是一件大事,并往往要举行各种仪式,舞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榖梁传·隐公五年》有云:“榖梁子曰:舞夏。” 此句道出了“舞”与“夏”有关。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榖梁传》:“舞羽谓之舞夏。”那么这与龙有什么联系呢?关于二里头遗址2002VM3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用途,杜金鹏和何弩曾提出过相近的观点,即是在宗庙祭祀时,相关管理者或参与者所执仪式之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绿松石龙形器的随葬位置,正好被墓主揽在怀中,而且还配一铜铃,这应该也反映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方式。何弩进一步论证这种仪式可能就是“萬舞”,绿松石龙形器是禹的化身仪仗,而在后世的发展中,所用的道具有所变化,包括会用到禽类之羽。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并且这一观点与夏人驯龙和“禹”之字义都有关联,相互不相矛盾,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龙在夏人生活中的丰富含义。
4.夏王朝的旗帜与龙有关
旗帜是一个群体的重要标志。《礼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緌。”郑玄注:“夏后氏当言旂。”旂即是旗帜。《周礼·司常》记载:“交龙为旂。”可知夏人有以交龙为旗的制度。这在《释名》中描述得更为清楚:“交龙为旂倚也。画作两龙相倚状。”此外,类似的标志物或装饰物还有舀酒的礼器——勺。《礼记·明堂位》记载:“夏后氏以龙勺。”以此可窥见龙在夏人礼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结语
从考古发现看,二里头文化龙纹的直接源头应是新砦期文化。在河南新砦遗址一件陶器盖上刻出的龙纹,与二里头文化的龙纹如出一辙[23]。但与新砦期的龙纹相比,二里头文化的龙纹更加抽象化、图案化。河南已经发现大量二里头文化遗址,但出土龙相关的遗存仅限于二里头遗址,说明龙与当时的王都有关。二里头遗址出土相关的龙形遗物,多在大、中型墓葬或宫殿区祭祀遗存中,显示其高等级的特殊地位,平民生活区几乎不见,这充分说明龙在当时的神圣性和都邑的专有性。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是夏人尊龙、崇拜龙的反映,可以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二里头遗址应是夏朝都城,龙为夏民族的图腾是可信的,龙是夏代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另一种方式向我们证明了夏人的信仰。二里岗文化为商文化,商人崇拜鸟和虎,早商考古发现的大量兽面纹应是尊虎的反映。
从夏崇拜龙和商崇拜虎(兽面纹)以及大型宫殿的布局方向上的差异反映出夏商两种文化在社会信仰和政治体制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继夏代之后,龙纹在中商阶段(郑州白家庄期)才又开始在青铜构件上出现,可以说龙文化在夏商之间曾有一个低谷或断裂期。商人对龙的信仰有一个接受并发展的过程,在商代后期热忱逐渐加大,甲骨文中也有不少对龙的祭祀。龙经历夏商周数千年的创造、演进、融合与涵育,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文化标志和情感纽带。基于龙形象的考古发现,归结到目前“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上,目前学术界多认为的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或一到四期早段为夏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或四期早晚段之间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夏商文化族属之间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学术界重新思考,这也是龙文化在夏商分界中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