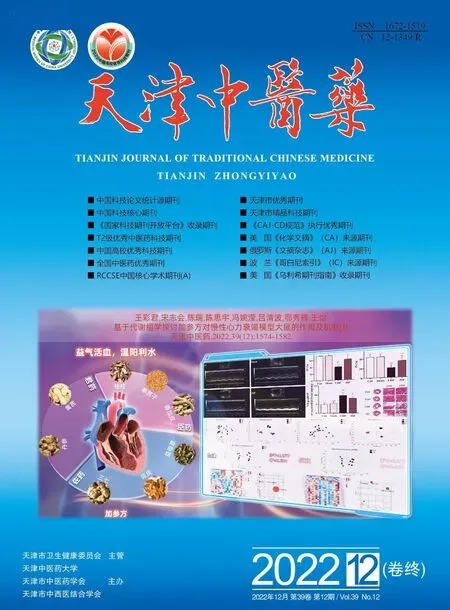基于卫气营血辨治功能性低热*
范顺 ,张小凡 ,张海宁 ,唐景潇 ,王毓言 ,吴秋君 ,王金贵
(1.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拿手法生物效应三级实验室,300193)
功能性低热又称为神经性低热、反复低热或无名低热,可能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体温调定功能障碍的结果,多见于年轻女性患者,其病程达数年,一般情况良好,门诊或住院系统的全面检查仍未发现阳性结果[1]。该类患者体温在正常体温之上1.0℃左右,24 h温差在0.5℃左右,晨起或上午正常,午后或傍晚升高(不因体力活动而升高)[2]。长期以来,功能性低热被视为现代医学治疗的难点问题。在排除继发于器质性疾病的低热之后,而无法使用退热药及抗生素,恐有不良反应,目前尚无行之有效的治疗措施。
本文基于卫气营血论述了功能性低热的辨证论治,并结合王金贵教授动态辨治夜间低热验案1则,以飨同道。
1从卫气营血辨治功能性低热
本病属中医学“内伤发热”范畴,中医学对其认识滥觞于先秦,其基本病机为气血阴阳亏虚,病理演变多虚实夹杂[3]。亘古通今,中医学对于本病辨证论治的归纳已较为全面,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具有明显的优势。临床中基于卫气营血辨治本病,在卫气分有湿遏热伏、脾胃气虚,在营血分主以邪伏阴分。
1.1 湿遏热伏 吴鞠通[4]云:“内不能运水谷之湿,外复感时令之湿。”湿温初起,或由外感,或由内生,外感之湿,阻遏卫阳,内生之湿留扰气分,湿胜则阳微,故见身热不扬,患者多表现为自觉身热,而体温不高,医者以手扪于尺肤片刻,可感微热。湿阻上焦,肺失宣降,不能正常输布津气,郁于三焦,症见周身酸楚、疼痛。湿遏热伏证,当以三仁汤之法,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在此基础上多佐藿香、防风,有芳香祛浊、风能胜湿之意。
1.2 脾胃气虚 《素问·调经论》[5]言:“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饮食劳倦,内伤脾胃,而元气不足,中虚而生内热。李东垣在此基础进而发挥为“阴火论”。患者表现为面色少华,低热,或伴汗出,泄泻便溏,周身乏力。治疗效法李东垣,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少佐甘寒之品,西洋参、玄参健脾益气,以泻阴火。
1.3 邪伏阴分 《素问·调经论》云:“阴虚则内热。”《素问·评热论》[5]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邪伏阴分证,温病后期,邪热渐入营血分,暗耗其阴,伏于阴分之证。患者多表现为夜间低热,或伴有盗汗,能食而形瘦。以青蒿鳖甲汤中“先入后出”之法,养阴清热,透邪外出,继而再调治气分之症。
2 典型病案
患者男性,60岁,2020年8月22日初诊:主诉间断夜间低热、汗出3月余。患者自述3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夜间汗出,未予重视,后间断出现夜间低热,测体温最高37.8℃,白天体温正常。曾就诊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经全面检查排除感染性发热及继发于其他器质性疾病所引起的发热,建议医学观察,变化随诊。患者为求进一步诊治,就诊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刻下症见:夜间低热,最高体温37.8℃,口干,口渴欲饮,盗汗,气急易怒,纳呆,寐欠安,夜尿频,平均5~6次,大便调。舌红苔白,左脉弦数,右脉细、关弱。西医诊断为“功能性低热”,中医诊断“内伤发热”,辨证属邪伏阴分,阴虚邪恋,治疗以养阴透热,疏肝健脾为法。处方:鳖甲20 g(先煎),生地黄 12 g,知母 10 g,牡丹皮 12 g,青蒿 12 g(后下),柴胡 12 g,白芍 12 g,当归 12 g,茯苓12 g,炒白术 12 g,炙甘草 6 g,7 剂,水煎服,每日1剂。
2诊(2020年8月29日):患者诉服药7剂,发热次数较前减少,仍有凌晨发热现象,盗汗减轻。现仍口干欲饮,夜尿频,平均4~5次,舌红苔白,脉弦数。继前方去疏肝健脾之逍遥散,加入透热转气之药,着重透解营血分之邪,处方:鳖甲15 g(先煎),生地黄 12 g,知母 10 g,牡丹皮 12 g,青蒿 12 g(后下),水牛角 20 g(先煎),金银花 12 g,连翘 12 g,玄参 12 g,黄连 10 g,竹叶 12 g,丹参 15 g,麦冬 12 g,3剂,水煎服,每日1剂。
3诊(2020年9月9日):患者诉服药3剂,盗汗已无,遂自行抓药7剂,继服7剂后,无发热症状。现纳可,寐安,舌红苔薄白,脉弦。继上方加活血利湿之品:王不留行10 g,黄柏12 g,炒苍术12 g,红花12 g。2020年12月10日(3个月后)随访,患者诉未见夜间发热症状。
3 讨论
3.1 审证求因,无失气宜 患者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夜间汗出,后夜间低热显著,常规问诊难寻病因,王金贵教授认为:“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5]欲厘清病因,可参运气理论,方能无失气宜。
庚子之年,少阴君火司天,3个月前正值小满,三之气主少阳相火,君相火旺,多暑病。患者年近花甲,平素情绪急躁,纳少,左脉弦数,右脉细、关弱,两关不和,知其肝气郁结,横犯脾土,加之恣食瓜果饮冷,困脾生湿。患者久居北方高燥之地,外感暑邪,鲜有挟湿者。暑热发于阳明气分,煎熬津液。“古人所谓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6]又因肝气郁结、中焦湿阻所致气机闭塞,暑热不能外达,内迫趋里,渐入营血分,暗耗其阴,乃成邪伏阴分之证。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5]曰:“夏伤于暑,秋必痎疟。”该患者恐为感受暑湿,则发暮热早凉之疟。由此感悟,探究疾病起因,有利于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方面的优势。在治未病时,当燮理病者身之阴阳,合于四时五脏,避虚邪贼风。
3.2 谨守病机,各司其属 患者以夜间低热为主诉就诊,询问现病史,排除继发于器质性疾病的发热。现代医学则考虑属“功能性低热”中“夏季低热”一型,即每年夏季出现低热,伴乏力、头晕、食欲下降等症状,天气转凉后低热可自行消失,亦俗称“连夏”。与现代医学对本病预后的认识有别,中医学认为本病属“内伤发热”,参析运气之后,为温病中“伏暑”病,故至秋仍可持续存在,而无夏去病愈之说。吴鞠通[4]尝谓:“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霜未降而发者少轻,霜既降而发者则重。”王金贵教授认为单纯感受暑热,其邪炎上易散,而不易伏藏。若为阴虚之体则易恋邪;或感受挟湿之暑;或暑与内湿相合者,如油入面,难以解散,诚如陆延珍[7]所云:“伏暑恶寒发热……此暑必挟湿。”
本病病机以气血阴阳亏虚为本,临床多夹实邪合而为病。吴鞠通[4]常谓:“夜行阴分而热,日行阳分而凉,邪气深伏阴分可知。”患者夜热早凉为邪伏阴分之象,其阴分内伏暑湿之邪,煎熬阴血,每致卫气夜行于阴,两阳相劫,故见夜间发热。阴虚火旺,津液失养,则发口干欲饮。内热迫津外泄则盗汗,血分有热则见舌质干红。患者平素性情急躁,肝气不舒,故见脉弦,阴虚内热,便有细数之象。“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久则不欲饮食,右关细弱。
3.3 时相思维,动态辨治 王金贵教授认为辨证大体分为空间性辨证和时相性辨证,空间性辨证不外脏腑辨证、六经辨证,时相性辨证则有卫气营血辨证。本病属“内伤发热”,亦属温病中“伏暑”病,故以卫气营血辨证为主。王金贵教授的每诊辨治思维无一不遵循温病发展规律,以立法遣方。
王金贵教授将本病辨为邪伏阴分,阴虚邪恋,属血分证,当以凉血散血。据此以青蒿鳖甲汤养阴透邪,青蒿鳖甲汤出自《温病条辨》,用于治疗少阳疟源于暑湿者,与该患者症机相通。王金贵教授认为欲除阴分中有形之邪,当“令药气至病所为故,勿太过与不及也。”[8]本病已有3月之久,“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木不能见效”[9],故以血肉有情之品鳖甲领诸药入阴分,《神农本草经疏》记载:“鳖甲主消散者以其味兼乎平,平亦辛也,咸能软坚,辛能走散。”[10]辛咸之性能搜剔血络中交混之邪。牡丹皮助生地黄益阴凉血清热。青蒿味苦、辛,性寒,其气芳香,善领湿热之邪由少阳达外,《本草新编》[11]有“青蒿能引骨中之火,行于肌表”之说。知母崇水,清热止渴,以利鳖甲、青蒿成搜剔达邪之功。王教授观其脉两关不和,纳谷不馨,再以逍遥散疏肝解郁,抑木扶土。
患者复诊诸症缓解,但夜间低热、盗汗症状仍在。王教授认为阴分之邪已有外解之象,病属营血两燔,师吴鞠通“祛邪务尽,善后务细”[4]之训,继青蒿鳖甲汤中加入清营汤。以水牛角清解营分之邪热,麦冬清热养阴生津,玄参清身中浮游之火。温邪病及营分,故用金银花、连翘、竹叶宣畅气机、透热转气,以达四两拨千斤之效,此叶天士所云“入营尤可透热转气”[12]之意。
患者3诊盗汗、夜间发热已无。继上方加王不留行、红花活血通经,防前药寒凉留瘀之弊,亦遵叶氏“凉血散血”之诫。阴分邪热已透解,但肝郁仍在,郁热与脾湿交结于气分,当用二妙散清热燥湿以收工。
4 小结
临床中卫气营血辨治功能性低热,在气分,当辨虚实,实则宣上利湿,虚则甘温除热,渐入营血分后,当养阴清热,透邪外达,再依邪之所居,循病之发展,随证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