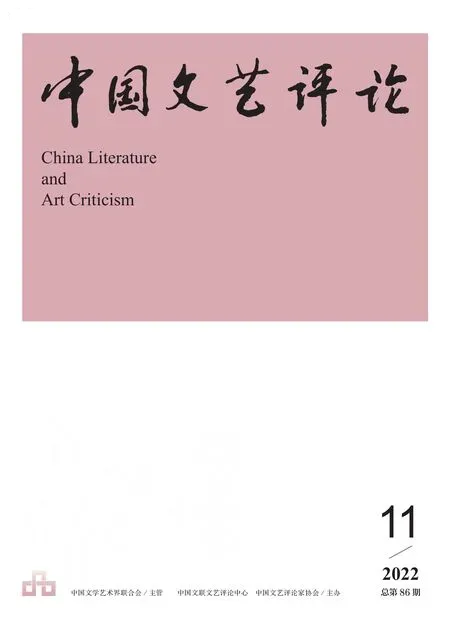中国大学校歌歌词与民族形式建构初探
■ 梁振华 张 熹
中国大学校歌的创作与传播肇始于清末民初,经历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学运动、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到“新启蒙”思潮至流行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尽管“歌词+旋律”的复合型艺术形式与校园的特定应用场域让校歌在传播与受众上并不拥有主流文学作品那样显著的优势,但就校歌歌词本身而言,无论在创作思想、呈现面貌还是深层内涵上,都具备不亚于其他文学类型的鲜明历史特征与研究价值。更重要的是,身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大学,校歌歌词的字里行间承载着知识分子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交织、融合与分裂、博弈。这都是值得把校歌歌词单独提出并予以梳理和分析的理由。
当下,歌词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使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边缘走向文艺史书写的大雅之堂。就歌词的性质而言,“诵诗从歌诗当中分离出来,又经常补充着歌诗。歌诗在诵诗上面产生出来,又最后演变为诵诗。二者同时存在,并行发展,又互相影响,不断转化”[1]公木:《歌诗与诵诗——兼论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第51页。。歌词本身即为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其当下意义来说,“现代歌词一直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一方面与歌词的经典化程度没有完成有关,一方面也与精英知识界对歌词的‘排斥’心理有关。……歌词与时代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诗歌。如果是这样,优秀的歌词创作就有理由进入当代文学史”[1]孟繁华:《声音的中国——当代歌词入史和经典化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页。,运用文学手段探析歌词是合理的。立足当下、回望过去,校歌歌词还可以作为贯通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发展史的基本抓手和主要线索。推动校歌歌词经典化的过程也是探讨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几次大变革之间深层互动关系的尝试。
以现有不同大学历代校歌歌词为研究起点,学术界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初步开拓:一是校歌创作者本人的自述或各校校史型研究,包括词作者在创作前后针对作品本身的论述[2]参见汪鸾翔:《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清华周刊》1925年第353期,第8页,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5-269页。与部分学校的校歌发展历史的回顾与解析[3]参见魏书亮、姜文:《旧音新韵同唱育人兴邦曲——北师大校歌的历史沿革》,2017年11月20日,http://sdxs.bnu.edu.cn/xsyj/yjcg/242777.html。;二是把校歌作为一种宏观概念,如从教育学方面探讨校歌的思想政治功能[4]参见张洪泰:《以大学校歌为载体的高校精神文化建设探究——基于组织文化的视角》,《教育探索》2021年第2期,第58-62页。,或从语言学方面研究校歌歌词的语言、辞格、词汇[5]参见曹师一:《中国大学校歌中的转喻及其教育含义》,《现代大学教育》2014年第6期,第9-13页。;三是对同一时期或同一地区的校歌进行横向对比的共时性研究[6]参见邹加倪、王文杰:《文以载道 歌以咏志:民国时期高校校训及校歌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39-47页;吴叶林、崔延强:《歌以载道:大学校歌与战时大学精神论析》,《重庆高教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0-121页。,主要涉及民国与抗战时期的校歌或着眼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高校群。
尽管前人在研究过程中总是有意识地运用各学科相关知识,以彰显研究的独特性或创新性,但大多数文献的后半部分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校歌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的探讨,且结论同质化倾向比较明显,皆为对校歌歌词提倡爱国、求知等共性的简单概括。另外,即使部分研究出现了从动态变化角度把握校歌发展的可贵思路,大多数也仅把时间当作连接历史阶段与校歌歌词的单向尺度,较少考虑到不同时期之间的相互影响。
要想全面认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必须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加以审视。前者有利于把握历史细节,后者重在梳理引发流变的动力。两者结合,可以为当下仍在进行的文艺创作提供现实启示。就校歌歌词而言,这一切都要从明确其发展的几个阶段开始。
一、鉴往知来:中国大学校歌歌词简史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大学校歌是创作于1897年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院歌《警醒歌》。学术界倾向于把这首清末民初的歌曲置于学堂乐歌的谱系中来考察。这暗示了学堂乐歌与大学校歌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承续关系。
(一)“五四”文学与大学校歌萌蘖
中国大学校歌第一次集中出现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五四”时期,学堂乐歌的创作逐渐走向低潮,李叔同、沈心工等一批学堂乐歌创作者纷纷另寻他路,现代新型大学的密集建立为他们提供了机遇。这批专业音乐人进行校歌创作的出发点,除了有为相应大学创设独特文化符号以外,还倾注了更多的思考,即借歌曲传唱以开启民智、促进社会变革。因此,处于萌蘖时期的大学校歌歌词一方面更强调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业性、技术性与知识性,另一方面也将学堂乐歌与生俱来的鲜明社会指向继承下来,将学习知识与改造国民性格、推动国家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言白话之争是“五四”语言革命的核心话题,其先导性事件是新诗运动。在这背后,学堂乐歌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学堂乐歌大多就西洋旧谱创作新词,而西乐节奏与汉语字符的不完全贴合为叠词、口语等白话文因素的产生创造了空间[1]参见谢君兰:《近代学校音乐教育背景下的学堂乐歌——以白话新诗的发生为考察维度》,《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5期,第20-26页。。与之相对应,“五四”校歌采取“西曲新词”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大多数大学校歌歌词并没有在文白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过渡特征。它们大多数沿用了古典文学中随处可见的“起兴”手法,在歌曲开篇首先点明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传统或学校人杰地灵的文化氛围;在歌曲中,常能见到并不十分严格的对仗句;在部分校歌歌词中,“嗟尔”“兮”等文言助词也散见于字里行间。“起兴”是为了强化学校特色、凸显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运用对仗的原因在于令歌曲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其他文言要素的出现,既是有传承经典形式、保留民族底色的考虑,也是创作者为了凸显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庄严感的刻意安排。
(二)延安文艺与两类大学校歌的划分
抗战爆发,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自开创以来的首次大变动。时局所迫,部分在民国初期已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作出西迁的决定,这其中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为典型,它调寄《满江红》词牌而创作的校歌流芳后世。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领域另外一个新动向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大学。这一批主要位于陕北的大学,作为战时部门为民族解放战争输送了大量军事政治人才,同时,作为知识机构又汇聚了很大一部分此前向革命根据地靠拢的知识分子,为延安文艺的诞生作好思想和理论准备。
“回顾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的革命文学是从1942年之后的延安文艺开始的。”[2]刘勇、汤晶:《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7页。抗战时期,五四运动中“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中的“救亡”得到了最大的凸显。无论是西迁的大学还是党办的大学的校歌,词作者都把爱国救国思想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具体而言,西迁的大学在主题有所侧重的前提下,基本遵循了“五四”校歌的发展脉络,加之校歌样本数量不多,变化不太明显,这一时期校歌歌词更关键的转变体现在党办的大学上。审视党办的大学校歌歌词,不但能发现它们与“五四”校歌及上文所述西迁的大学校歌的显著区别,而且能认清它在延安文艺的建构与实践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学校歌开始以独立的身份参与民族形式建构,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相较于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党办的大学生源包括工农、士兵,更为丰富多样;教学内容也更具思想政治性和战时实用性[1]参见吴付来、杨子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特点探析》,《中国高等教育》2017年第19期,第50-52页。。经根据地整体和党办的大学个体两方面条件的促成,郭沫若、成仿吾等作为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学校管理和校歌创作中。为了适应学员水平、便于在较短时间内传播开来,党办的大学校歌在歌词语言上实现了彻底的白话化,文言要素近乎不存;嘹亮激昂的旋律下,爱党爱国、热爱劳动、融入人民成为唯一落脚点。
党办的大学校歌是延安群众歌咏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在铺天盖地的歌咏活动之中,军民的士气得到极大振奋。“从五四‘平民文学观’到延安文艺大众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条历史逻辑、社会逻辑和革命逻辑。”[2]刘勇、汤晶:《延安文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0页。延安文艺将“五四”“平民文学观”真正落到实处,由内而外实现了文艺的大众化。作为延安文艺一种特征鲜明的艺术形式,党办的大学校歌充分融入时代大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人民的文艺。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学校歌
延安文艺集中反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下文艺创作的核心取向,并从根本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创作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政治性和大众化立场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艺领域的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工业化建设的总方针下,高校的院系、专业设置和学制等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均以苏联的高等教育为参照,努力在较短时间内为我国工业化建设输送高质量人才。党和政府在对全国高等院校实行直接管理的基础上,基于人文社科和理工科两大学科门类,对“五四”时期综合性大学的专业院系进行了归类、外调与重组,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办的大学进行整合完善,并着手新建一批理工科大学。[3]参见刘蕴秀:《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事业百年历程——文献学视角的考察》,《教育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65页。
在时代文学风气与教育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五四”校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很少在学校或社会的公共场合被提起;在新建立的理工科大学中,校歌创作基本沿用了抗战时期党办的大学的语言形式,其中的民族矛盾话语被置换为工业建设与阶级斗争话语,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歌《永恒的东风》(1958)、《山东大学校歌》(1962)等。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校歌创作无论在数量还是新变上,较“五四”文学和延安文艺的两个高潮都大为缩小。
(四)流行文化下的“五四”大学校歌复用与新变
新时期以来,“五四”知识分子重回高等教育领域主舞台,知识界出现以人道主义、“寻根”思潮为核心的“新启蒙”思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南京大学)校歌》(1916)、《国立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校歌》(1924)、《复旦大学校歌》(1926)等多首沉寂多年的“五四”校歌被复用。该时期新创作的校歌开始在字里行间有意识地运用学生的口吻抒发对母校的主人翁意识与眷恋之情,其言语立场显现出向学生本位的下移,同时得以容纳学术国际化等更具当代教育特色的内容。
流行文化在中国本土的生根发芽,催生了别具一格的校园文化歌曲,对校歌在师生心目中的独尊地位构成了挑战。受到校园文化歌曲创作方式的启发,该时期的大学校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新时期老校歌复用潮的对象由“五四”校歌扩展到延安校歌,如《陕北公学(现中国人民大学)校歌》(1937)、《国立交通大学(现西安交通大学)校歌》(1943)等;二是以旧体形式为基础,运用现代歌词技巧创作新词,如调寄《临江仙》词牌的《东南大学校歌》(2000)、北京师范大学新校歌《巍巍师大》(2012)等;三是考虑到校歌作为一种历史文本资源的有限性,利用跨文本的互文共读,对既有文学作品进行谱曲作为校歌的,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仰望星空》(2010)为代表。[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仰望星空》歌词为国务院原总理温家宝2007年9月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的诗歌,后由沈阳音乐学院的刘晖谱曲。2010年5月,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式定为校歌。参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网“北航校歌”专栏,www.buaa.edu.cn/bhgk/jrbh/bhxg.htm。
通过概览,百余年来中国大学校歌歌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大致变化线索得以呈现。不难发现,每个阶段的校歌歌词并非只是对上一阶段的特征进行扬弃。具体而言,为何新时期校歌能“跨过”延安文艺这道巨大的里程碑,重拾“五四”校歌的原初面貌呢?在当下流行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主要历史资源的延安文艺,历经近一个世纪能否继续发挥其对校歌的本质性影响?这一切既要从不同时代的整体政治形势与文学风气中找到端倪,也必须在不同阶段涉及的共同文学话题与校歌创作主体等具象性指标中得出结论。
二、旧题新解:延安文艺对大学校歌歌词影响的再审视
延安文艺相对于“五四”文学的更大发展,就是在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上给予了更为坚定而确切的回答。形诸校歌歌词,最明显的是“五四”校歌的文白混用转变为延安校歌的彻底白话。
在“五四”校歌中,词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风起云涌的语言革新思潮及隐含其中的大众化诉求。但此时相对狭小的校歌受众往往受传统文化背景影响,在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上,他们往往倾向于在立意的构思与呈现上更下功夫。《清华大学老校歌》(1924)的词作者汪鸾翔说:“本校歌意在词旨隽永,故用文言发表。”[1]汪鸾翔:《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清华周刊》1925年第353期,第8页,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学校时期(1911-1928)》,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1938年,马一浮秉承“义与箴诗为近”“歌者听者咸可感发兴起,方不失乐教之义”[2]参见浙江大学官方网站“校歌”专栏,https://www.zju.edu.cn/574/list.htm。的创作宗旨,采用诗骚古体、兼取《尚书》文风,令创作的《浙江大学校歌歌词》呈现了“取雅正,寓教思无穷之旨”[3]同上。的面貌。竺可桢校长阅后认为,“马老作的歌词虽文理艰深,但含义深远,很能体现浙江大学所追求的求是精神。”[4]同上。传递主旨的强烈要求不仅盖过了对简明语言的提倡,甚至有时候需通过调整语言形式服务校歌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强调:“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1页。在延安文艺基本语言观的指导下,党办的大学校歌歌词作为延安歌咏作品中的一部分,在重视内容、贴近政治军事与群众生活的同时,语言尽力追求通俗口语化。
既然延安校歌对“五四”校歌的发展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为什么在新时期却出现了似乎是逆潮流而行的“五四”校歌复用现象呢?《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艺大众化主张,也极富远见地展望了文艺领域的状况:“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6]同上,第862页。《讲话》着眼的是“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7]同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群众普遍文化水平的提升,文言与白话之间紧张的态势得到缓解。在流行文化背景下,文学、影视、音乐多种艺术门类深刻交织,形式与内容的古今融合不再成为人民群众接受的障碍,在很多青年人眼中还成为了高雅艺术的象征,被认为是文艺作品走向精品化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众化”对象层次水平的提升为“五四”校歌复用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但它并非此现象出现的主要动力。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历史主题上是“救亡”相对于“启蒙”的凸显,对创作主体来说则是政治权力的强势介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领域“一体化”方针的先声。“一体化”意味着:社会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都归属到公职人员的编制,从而实现对社会(自然也包括文学界)的全面控制,作家、教师等都以“干部”的身份被纳入这一“体制”中……使作家的社会地位和对自身的角色认定也相应出现了重要变化。[1]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第138页。在这一时期的校歌歌词中,“学校”作为相对于“国家”的微观构成,处于主导地位的“求同”视野也取代了“五四”时期标榜学校特色的“求异”心态。1985年5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2]参见范惠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综述》,《高等农业教育》2002年第1期,第14-18页。“五四”校歌的复用实际上代表了知识阶层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对“五四”文学和延安文艺一次更科学理性的定位与认识。如果说“五四”校歌歌词在创作时提出重视专业技术、知识至上的归宿是服务民族危亡大局,那么此时复用校歌中的这些元素就经历了“再解读”。借助它们,能够强调知识阶层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供文化与智力支持的关键群体所拥有的主体地位。
大学校歌歌词创作主体及其言说立场(口吻)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家”这一介质展现的。但家“作为民族生命之源,它是亲情、温暖和归属所在,它规定着我们的身份,创造着民族的力量”[3]戴锦华:《隐形书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10页。。进入新时期,“家国新秩序”变成了“‘人性’修辞”的所指,“‘新时期’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有关‘家’的‘自然’伦理秩序的重建”[4]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5页。。复旦大学曾于1926年创作了该校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但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近乎销声匿迹,直至20世纪80年代被复用至今: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沪滨屹立东南冠,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声名满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大学校歌》(1925年)
全曲三段开头、结尾基本形成复沓。在涉及学校本体的叙述上,每段首尾对“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命名典故进行了回溯,引出后文“巍巍学府文章焕”“师生一德精神贯”“沪滨屹立东南冠”等一系列分别着眼历史、校内、校外的赞美。对待学术的态度是这一歌词反复强调的重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巩固学校维护国家”“作育国士恢廓学风”三句跨段互文,反对“政罗教网”“羁绊”,但并不否定“巩固学校”为“维护国家”之基础,发扬“先忧后乐”的文化传统意在实现“震欧铄美”之现代目的。在这里,“小家”与“大家”既可以象征学生与学校、学校与国家的关系,也可以涉及国家与世界的关系。词作者通过有机的穿插,尽力将这三组关系在三段歌词中艺术化地融为一炉,在“五四”校歌基础上挖掘出面对个人与时代重大命题的积极态度与世界胸怀。
如果说对“五四”校歌典型文本(如1925年创作的《复旦大学校歌》)中人道主义话语的再挖掘已依稀透露出“小家”复归的信号,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新创作的校歌则让“小家”成为了行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
百年沧桑,弘毅自强,根深叶茂育桃李,满园芬芳。
啊,美丽的珞珈山,多少雄鹰竞翱翔。
扬帆长江,奔向海洋,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德业并进,求是拓新,大同寰宇向未来,我创辉煌。
啊,心中的珞珈山,今朝多磨砺,明日作栋梁。
——《武汉大学校歌》(1998)
“珞珈山”上有“亲爱的学堂”,学堂是广大师生“成长的地方”。校歌进一步打破了“时代(国家)—学校—知识分子(学生)”自上而下的链条,对校史及校园环境的描述成为了以学生口吻发出的深情讴歌。相比于“五四”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创作的校歌,它给作为校歌言说主体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近一整段的叙述空间,并允许他们把这一空间下移至知识的接受者——学生身上。在20世纪80年代,校歌创作在“政治本位”向“学校本位”复归的基础上,实现了“学校本位”向“学生本位”的下移。
三、古今齐观:从大学校歌歌词创作到民族形式建构
校歌歌词创作不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领域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个例,更不只是主流文艺史的一个注脚。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作为歌曲,它在世纪之交大众娱乐事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之时,面临着比一般文学体裁更为重大的挑战;作为校园文化符号,它又随时接受着最具思想活力的青年群体的品评。
(一)大学校歌复用范围的扩大
新时期“五四”校歌重获新生的传奇已成历史,但它开创了相同校歌歌词的思想内涵在不同时代得到多次发掘与诠释的先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方式被迁移到一些大学非“五四”时期创作的老校歌当中。2019年,创作于1935年的《陕北公学校歌》取代了20世纪初的新校歌,被正式定为中国人民大学校歌。[1]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官方“学校简介”专栏:https://www.ruc.edu.cn/intro。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学习。
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要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头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在建校之初的抗战语境中,“祖先发祥之地”指的是位于黄河流域的陕北地区(黄帝陵所在地附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校址位于首都北京。“祖先发祥之地”的定义被泛化,传唱过程中逐渐成为受众对中华民族的宏观感知。与之类似,“民族的命运”“民族解放事业”“新社会的建设”也不再局限于抗战本身,而延伸到对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前途命运。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主体的自我指认与自我言说而言,其最为突出的问题始终是一份强烈的自我意识及价值与意义的中空状态。换句话来说,21世纪之初,中国崛起的议题中再度显影的中国文化自我的中空状态,并非“五四”文化裂谷于历史苍穹下再度横移,而是世纪之交又一次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2]参见戴锦华:《历史、记忆与再现的政治》,《艺术广角》2013年第1期,第12-13页。《陕北公学校歌》中的政治话语经历了岁月的涤荡,它在新时代下的复用,对内可以满足社会大众和知识界对一个冉冉升起的复兴大国的文化期待,对外则宣示了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坚定志向。[3]促成新变的另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媒介形式加入到校园文化的塑造和宣传中,降低了校歌的理解难度,从而提升了校歌的群众基础与传唱度。比较成功的例子有中国人民大学在复用《陕北公学校歌》前后排演的《陕北公学》话剧。
(二)校园文化歌曲与现代歌词技巧的融入
如果说校歌复用潮的扩大是20世纪末文艺领域动态留下的袅袅余音,那么真正标志21世纪流行文化进入大学校歌语境的事件,是在一开始被认为与校歌本身无关,甚至无助于校歌后续发展的——校园文化歌曲的集中出现。
校园文化歌曲并非当代歌曲史上曾经成为一种现象级热潮的“校园歌曲”或“校园民谣”。与广义的“校园歌曲”不同,校园文化歌曲仍由学校官方组织相关人员(包括专业音乐人、校友、学生等)创作,一般用于学校重大周年庆典或招生宣传中。与校歌相比,校园文化歌曲的歌词言说主体多为学生口吻,用词比较活泼多样,曲调也不是校歌中常见的庄严激昂的进行曲调,而选择通过民谣、爵士、古风乃至嘻哈、摇滚等流行音乐形式传递学生的思想感情,较为知名的有《山高水长》(1997,中山大学建校75周年纪念曲)和《海大颂》(2015,中国海洋大学建校90周年纪念曲)等。它们通过“你”“我”等人称代词及细致的描绘校园历史、校园环境,在话语上构建了更为切实的学生本位;同时在文白夹杂、仿古文体与政治叙事、家国情怀之间求得了平衡。经由传播,校园文化歌曲在师生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部分优秀作品甚至被称为“第二校歌”,大有赶超校歌独尊地位之势。
如何在不改变校歌相对正式用词与曲调的前提下,使其在被流行文化浸润的师生与社会大众之间拥有一席之地呢?校园文化歌曲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法。除直接为兼具庄严氛围与流行文化的诗词作品谱曲,并将其定为新校歌以外,大学新校歌词作者利用现代技巧对老校歌进行了改写:
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昌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1923年)
木铎金声世所崇。学为人师,教化从容;行为世范,砥砺无穷。国运昌,民智弘,育人兴邦肩任重。(分节歌1)
巍巍师大,兼济天下气如虹,巍巍师大,育人兴邦肩任重。(副歌1)
育才宏基千秋颂。学为人师,教化从容;行为世范,砥砺无穷。立天地,展鲲鹏,薪火相传志恢弘。(分节歌2)
巍巍师大,治学修身乐为公。巍巍师大,薪火相传志恢弘。(副歌2)
——《北京师范大学校歌》(2011年)
形式方面,新校歌延续了老校歌的工整对仗与语句间的反复,但语气词“兮”的省略、“在藐躬”“共矢此愿”等表达的改写,提升了歌词的流行感;内容方面,新校歌不仅继承了老校歌“师道”的论述核心,并把精神层面的培养目标落实为“木铎金声”这一切实可感的校园文化符号。
值得一提的是,就两首校歌的整体结构而言,《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歌》在歌词意义上是不成熟的,因为它是典型的“单一段体”,没有考虑到歌曲入乐的方便需求。这种体式“思想内容对比性不大,情绪比较平稳……表达出丰富的感情,还具有一定的难度”[1]尤静波:《歌词文化鉴赏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年,第41页。。而《北京师范大学校歌》则是更具流行气息的“带再现二段式”歌曲:分节歌1中的核心内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在分节歌2中得到了再现,帮助这一关键符号很好地利用了歌曲再现模块的强调功能。除复现的部分外,两段分节歌在内容上存在明显的递进式关系。“木铎金声世所崇”深情回忆这所师范大学始终笃信“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之古训的历史底色,“育才宏基千秋颂”着眼“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千秋大业。就副歌而言,歌词遵循了从分节歌“一领”到副歌“众唱”的情感上升规律,有利于引起歌唱者对创作者的心路历程产生共鸣。从副歌1到副歌2不仅是单纯的重复,“兼济天下”“乐为公”两词皆化用《孟子》之义,遥相呼应;“育人兴邦”“薪火相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使全曲表达丰富、摇曳多姿。
(三)大学校歌歌词模式化及其突破空间
“五四”文学、延安文艺和流行文化影响下的大学校歌歌词都形成了一定的时代共性。之所以没有把这些阶段特征称为“模式”,是因为校歌歌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形成十分稳定的态势。更重要的是,歌词中的每一个表述与总主题之间都普遍存在着有机关联,并无生搬硬套的板滞之感。以校歌开头普遍出现的校园环境或历史事件为例,在“五四”及延安时期,它们大多是与全曲的家国主旨有关的“起兴”之语。步入21世纪,这些相关元素往往被抽象成了“地素”。它们“通过反复使用,达到符号象征效果,得以大范围地流通……它占用了地素而不叙述故事”[1]陆正兰:《歌词艺术十二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然而,正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那样:“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2][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01页。校歌开头的“兴”辞如果只是单薄的套语,便不能“由感情所直接搭挂上、沾染上,有如所谓‘沾花惹草’一般;因而即以此来形成一首诗的气氛、情调、韵味、色泽”[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3页。。这一点在同一地区几所大学校歌中可以看出,开头往往高度雷同,且部分开头景语与下文事语、情语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除此之外,本文开篇提到的大多数校歌研究文献后半部分都不约而同地转向对校歌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的探讨,且得出高度同质化的结论,或多或少也是由部分新校歌按照从写景(一般为大学所在地区或城市之景)到言志(一般为报国)的固定模式创作所造成的。这不仅直接受到流行文化复制机制的影响,也表现出21世纪知识阶层在主流话语叙述方式选择上的惯性与疲态。
大学校歌歌词的研究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着眼创作的现实话题。如果说延安文艺追求的“知识群体与政治力量之间存在着”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4]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转引自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即政治性与大众化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全面理性的贯彻,以致20世纪80年代出现“精英文学开始从主流政治权威话语中裂变出来,获得了自身的话语权,并且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5]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思潮》,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的反弹现象,那么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则需要在进一步站稳人民立场的基础上,将宏大的意象主题落实到细腻的校园叙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既在国家权力体制之内,又具有很大的独立性”[6]同上,第35页。,如何把身份的独立性变成文艺叙述方式的独特性,每位校歌词作者都应有所思考和行动。
(四)大学校歌歌词与民族形式建构
经历了“五四”文学、延安文艺的开创与积累、新时期的反拨与调整,以及21世纪流行文化的刺激与启发,大学校歌歌词不仅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的一面镜子,生动鲜明地映照出中国现当代文艺创作领域几次大变革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还作为一种由高校知识分子直接创作的文艺形式参与到包括形式和内容在内的民族形式建构中。民族形式建构是一个贯穿中国现当代文艺领域并持续至今的重大命题,其内涵又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的大学校歌歌词基于上个时代所作的改造并不意味着“五四”文学、延安文艺或流行文化本身存在理论缺陷,而是立足新的历史阶段审视既有的理论成果,势必会因当下文化语境而生成新看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1]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贯穿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始终,知识阶层的爱国热情与使命担当在广为传唱的歌词与旋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大学校歌自学堂乐歌演变而来,其歌词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的活化石,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特色的原因所在。2022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身处民族形式建构问题首次被提出的关键历史时期,延安文艺既高度总结了“五四”文学的历史经验,也奠定了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的基本面向:人民群众。大学校歌作为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关键一环。大学校歌一经面世,其接受对象有校园师生和社会大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标准的执行既要考虑语言形式在文白之间的恰当尺度,也要兼顾歌词内容在党性、人民性与专业性、知识性之间的平衡。如何合理利用校歌歌词发展史中宝贵的文学与思想资源,有效克服当前校歌创作逐渐显露的同质化、模式化倾向,是每位校歌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经典文化、革命文化与新时代思潮的深入融合,让新时代校园文化乃至教育文化建设工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焕发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将是一件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也需要包括校歌创作者在内的每位文艺工作者付出辛勤的努力。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