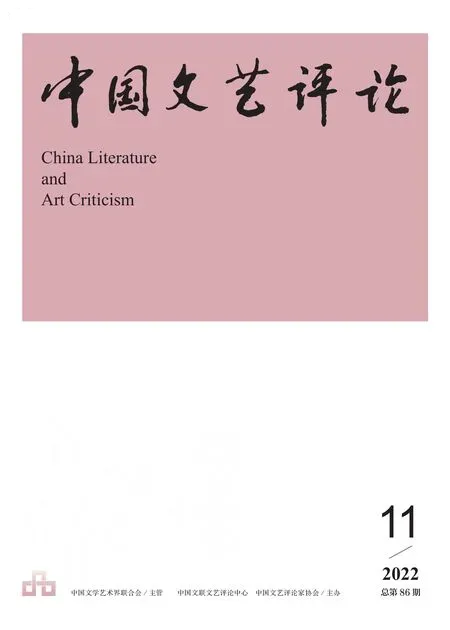中国当代小说在法国
——“汉学”主导下的翻译与接受
■ 张 珣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水平,已有不少高质量的研究。如新索邦大学教授、法国知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张寅德[1]参见张寅德:《中国当代文学近20年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1期,第58-71页;张寅德、刘海清:《莫言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第47-55页。、法国最著名的中译出版社“毕基埃”的前任主编陈丰[2]参见陈丰:《中国文学正融入世界文学体系——以法国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为例》,《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9月18日,第1、2版。、中国驻法大使馆前一等秘书尹丽[3]参见尹丽:《中国当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之路》,《中国文化报》2016年10月13日,第2版。等,都总结过以1988年和2004年(中法文化年)为分界的三个发展阶段,译介中国小说的四大出版社[1]译介中国当代小说最多的是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Philippe Picquier);创办最早的是弗拉马利翁出版社(Flammarion,1875年);中国蓝出版社(Bleu de Chine)由著名刘心武译作者安博兰(Geneviève Imbot-Bichet)创办于1994年,2010年被伽利玛(Gallimard)收购,但仍作为专栏继续由安博兰主持;对中国当代针对性最强的是南方书编 (Actes Sud,1978年),主编何碧玉是当代著名汉学家、作家,曾译介张辛欣、莫言、池莉等作家的作品。、两大书店[2]凤凰书店(Fénix)建于1964年,2009年荣获法国文化部“独立参照书店”称号。友丰书店(You Feng)建于1976年,在巴黎有两家分店。2005年凤凰书店的老板潘立辉荣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以及诸多法国译者[3]既做翻译又做研究的主要有安毕诺(Angel Pino)、何碧玉(Isabelle Rabut)、诺埃尔·杜特莱(Noël Dutrait)、马向(Sandrine Marchand)、安妮(Annie Curien)、尚德兰(Chantal Chen)、罗蕾雅(Marie Laureillard)、傅玉霜(Françoise Naour)、保尔·巴迪(Paul Bady)、魏简(Sebastian Veg)、邵宝庆、张寅德、金丝燕、徐爽等;只做翻译的有杜碧姬(Brigitte Duzan)、林雅翎(Sylvie Gentil)、贝施娜(Emmanuelle Péchenart)、雅格琳·圭瓦莱(Jacqueline Guyvallet)、普吕尼·高赫乃(Prune Cornet)、克洛德·巴彦(Claude Payen)、伊冯娜·安德烈(Yvonne André)、斯特凡·勒维克(Stéphane Lévesque)、帕斯卡尔·吉诺 (Pascale Guinot)、奥利维耶·比亚勒(Olivier Bialais)、维罗妮卡·瓦伊蕾(Véronique Woillez)、金卉(Brigitte Guilbault)等。的成果和翻译理念,各知名作家的接受状况学界也多有总结。概括起来: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确实成果丰富。法译本语言质量非常优秀,文学思潮的转折、各潮流的代表人物和主流外的小众作品,在法国都有及时的呈现和愈发连贯的追踪。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文学界关注不足,小说批评几乎都出自汉学家之手,文学家鲜有参与;学术期刊论文较少,学位论文也较少;对知名作家的评述“标签化”,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常被作为第一特征;过度聚焦中国的社会历史,而遮蔽了小说的“文学性”等。
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成败得失,在笔者看来都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传统汉学”思维主导“当代文学”翻译。先辈汉学家“切入”中国的视角、方式和情感——尤其是“深刻度”,都成了当今汉学界建构中国文学面貌的“无意识标尺”。
前文提到四大中译出版社,主持者都是汉学家;主导译介工作的“阶段性推进”、确立当代文学“视野”的,也是汉学家;研究中国小说特色的“主力军”,仍是汉学家。虽有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但“汉学圈”事实上居于中国小说推介的主导地位。而法国汉学在文学翻译方面的立场却比较微妙。一方面,相比其他国家汉学的“多领域开花”,法国是最强烈地主张回归文本、专注语言的;对中文水平的要求也最为严格。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就称“接受了专业学科训练的法国汉学学派早已超越了其他任何人”“(法国)汉学是汉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言)写成的早期文本的研究”[4]薛爱华:《何为汉学、如何汉学》,《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第9、6页。;但另一方面,发端于传教士札记的法国传统汉学,对中国文本的关注却几乎从来就不是“文学性”的,而是“法式人文主义”的。他们在中国文本中寻找的议题包括:宗教理念能催发何种社会结构?该结构又滋生何种人格气质、自我意识和人伦观念?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是否体现了另一种“文明进化模式”?异于西方文明的这条路径,将会把“人类命运”引向何方?等等。
对文学性隐晦的偏离,加上语言文化修养上严格的自我要求,使法国汉学的“自我认知”产生了一种奇异的错位。一方面着力强调“贴近中国”、力图让中国形象具备超卓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又越过文本跨入抽象,固守“人文主义”本位而不自知。饱含激情与热爱的人文主义视角和寄寓在中国身上的“自我文化反省”“异质文明比较”,就是传统汉学所追求的“深刻”,正是它们树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标尺。匹配前辈水准,是当代汉学家下意识的自我要求。传统汉学建立了“深刻的”古代中国、社会中国;那么以同样的严谨度、建立同等深刻的当代中国和文学中国,就成了当代法国汉学界的隐形目标,甚至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传统汉学标尺的尊崇,体现在当今中国小说“翻译”和“研究”的方方面面。首先,当代汉学家对“中文”语言特质的思考和翻译技巧的总结,基本没超越传统翻译理论的视野和深度。如“雅化”的尺度;出发语(langue de départ)与到达语(langue d’arrivé)间的关系;中文的风格化、陌生化;翻译应服务原作者还是读者等问题。法国学界对中国当代小说的探讨几乎是在重复传统汉学家的话语。如杜特莱提出直译需要“避免陷入异国情调、神秘、或可笑之中”[1]Noël Dutrait, “Quelques problèmes rencontrés dans la traduc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In Nicoletta Pesaro ed., The Ways of Translation:Constraints and Liberties of Translating Chinese.Venise: Cafoscarina, 2013, p.110.,就几乎只是转述德理文的“文学翻译介于直译和改编之间”[2]D’ Hervey-Saint-Denys, 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Paris: Ernest Leroux, 1885, pp.10-11.“汉语相对欧洲语言具有特异性”“直译常增添或怪异、或粗俗的情调”[3]D’ Hervey-Saint-Denys, Six nouvelles nouvelles, Paris:J Maison neuve, 1892, pp.6-7.等理念。对当今中文蕴含的潮流信息,如“网络热词”“流行梗”等,并无太多的针对性研究。
其次,对抽象的“民族性”问题,聚焦方式还是如出一辙。传统汉学最关注的“孝亲义务(devoirfilial)”,至今仍主导着研究中国武侠的思路。《远东远西》2012年发表《金庸小说及中国当代武侠小说中的父亲形象》[4]Nicolas Zufferey, “La figure du père chez Jin Yong et dans quelques romans d’art martiaux Chinois contemporain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 Occident,no.Hs, (January 2012), pp.219-244.,讨论焦点就是武侠伦理中的“孝道”。对中国“社会”的切分,也几乎依循固有的几个“深刻主题”,专注于“毛主义影响”“革命叙事”“国际工人运动”“极权问题”“社会意识觉醒”[5]前两个标签的总结来自加拿大汉学家胡可丽,参见Claire Huot, Mille ans de souci et soutain le printemps,Paris:l’aube,2004.后三个来自三位汉学家为同行罗兰·鲁的《共产主义中国:真实社会与自我觉醒》作的序。参见Guilhem Fabre,Jean-Jacque Gandini&Angel Pino, “Avant-propos des étideurs, ” L’Homme et La Société, Vol.2-3, No.172-173 (Mars 2009), p.11.等。
这些“守旧”的缺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学主义。似乎是某种西方优越感下滋生的“中国刻板印象”,在主导着汉学界对当代小说的体验。但吊诡的是,当代主流汉学家似乎并不缺“去刻板化”的自觉。毕基埃出版社着力寻找中国当代画家与当代小说契合的作品,来改变出版界长期以来随意用中国古画当封面的传统,于最直观处摆脱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干扰;于连(François Julien)则呼吁“用文学角度看待今天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像传统汉学那样将之“视为纯粹的文献”,或仅仅“当作证词、标记、指数或症候”[1]Noël Dutrait, “Traduir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au début du XXI e siècle, une question de choix,” In Paul Servais:La Traduction entre Orient et Occident, modalités, difficultés et enjeux, Belgique:Louvain-la Neuve, 2011, p.83.;杜特莱要求专注中国作家“笔下的艺术灵性及叙述方式”[2]杜特莱:《跟活生生的人喝着咖啡交流——答本刊主编韩石山问》,《山西文学》2005年第10期,第6页。;何碧玉被问及关注中国伤痕文学有无东方主义动机时,也立刻申明:“与其说是东方主义,不如说是对地道的、多样化的中国文化现象感兴趣。”[3]唐利群:《何碧玉教授访谈录》,《国际汉学》2010年第2期,第24页。
其实当今汉学家们研究方式的“刻板”与他们追求的“反刻板”,并不矛盾。正是同一个目标——维护中国的深刻性,让他们既高举传统汉学标尺,又力图排斥那些消解中国崇高性,使中国形象片面化、肤浅化的因素。描绘“古代中国的现代性”、挖掘“当代中国的古旧性”,呈现出时代的断裂、发展的迂回、文明的冲突,是法国汉学界“升华”中国的方式。中国的古老对法国汉学界而言,是一个充满诗性的矛盾意象。一方面它具有时间的力量感和历史的传承感,充满了对人类启智的欣悦、对天人和谐的向往、对早期文明的赞叹;另一方面又有发展的停滞感和传统的挟持感,唤起对文明传续的忧虑和对未来发展的迷惘。相比其他流派或诗歌散文,“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率先杀出重围、吸引了法国的关注,就是因为它们“挖掘社会深层迷失、呈现时代内部裂痕”的宗旨,符合法国汉学界“迷恋深刻中国”的口味。向先锋小说迅速转向,也是因为法国极为期待看到时代的下一个节点,“后现代”会在他们心目中“反现代”的中国身上制造出怎样的矛盾张力。
笔者认为这种法国汉学专属的“诗性”,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歧视”或“民族主义贬损”,更多是出于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和出于对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文意象”的深爱。是汉学界发现了这个神奇而丰富的文明,剖析了它的深刻蕴涵;是汉学家在本国文化土壤中,一手建立起中国的文明价值。总体来讲,法国主流汉学界是爱中国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作者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曾在工作手记中写道:“作为耶稣会传教士,追随我们17世纪的伟大先驱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的传统,我渴望努力使中国和我们的世界会合,让我的同胞了解那些使我受益无穷的人们。”[1]转引自安毕诺、何碧玉、王耀文、韩一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汉学》2007年第12期,第38页。这份手记没有发表,并无沽名钓誉意图,是真挚的内心剖白。法国汉学界建立的这种“深化中国”的方式里,其实饱含赞叹,充满深情地描画着文明发展之艰辛、社会动荡之深刻、性灵进化之苦难、人类精神之坚韧和战胜时代之勇气。但这种“深刻”,往往遮蔽了中国文学的时代性、多样性和生动性,无意间迫使“中国评述”返归“刻板话语”。
当代法国翻译界始终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是“国家智力与精神的历史”,时刻不忘在文学作品中搜罗“理解中国精神状态的迹象”[2]安毕诺、何碧玉、王耀文、韩一宇:《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现代文学》,《国际汉学》2007年第12期,第42页。。他们在介绍阿乙的悬疑小说时,在封底强调作品揭示了“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的裂痕”[3]A Yi, Le jeu du chat et de la souris,trans.Mélie Chen,Paris: Stock, 2017, p.4.。安毕诺夫妇力主看到中国小说的“文学性”,但两年前发表的《当今中国的怀旧商业》[4]参见 Angel Pino&Isabelle Rabut, “Le Commerce de la nostalgie dans la Chine d’aujourd’hu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no.44, (January 2020), pp.17-40.,仍不自觉地把余华和贾平凹的文本当作社会现象的注脚,来佐证商业领域的贩卖情怀,痛心疾首地感叹当代中国轻慢、甚至糟蹋了古代的丰富蕴涵和传统美感。对“古老中国”的迷恋和“古今断裂”的遗憾,渗入了对当代小说的审美模式。对“中国”意象被“商业化”、甚至哪怕只是被“生活化”的问题,当今汉学界都是警惕且抗拒的。商业出版社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国当代小说译介中,汉学家们未必乐见。何碧玉就曾对翻译《狼图腾》的理由仅仅是“在中国发行了两千万册”表示鄙夷,而忽略商业化在事实层面对提升流行度的助益。
当今法国的译者们似乎尚未察觉,他们追求的“中国深刻度”,是一种有碍于“当今中国文学面貌建构”的过度激情。传统汉学内部酝酿的学科情怀,对于当今的真实中国来说,已是“爱之适足以‘碍’之”。但不同的两种文化,必有不同的两种感性。法国译介中国小说,不仅是一方建构另一方的文学面貌,更是两国跨越自身感性、互相触摸文化“质地”的过程。要使法国穿透自身“感性屏障”、体验到中国文化情感下的小说魅力,尚需时间。但如果从法国本土视角出发,公允考虑到翻译界建构“一国全貌”的能力与节奏,考虑到学术圈传承的研究习惯,就会认同法国一直在积极地、稳步有序地铺陈具有当代视野的“文学中国”,并已取得可观成果。
1.保持进步的“译介意识”。首先在时间上,法国努力把中国文学的“当代”从“近现代”中独立出来。这看似是基本要求,但对沉迷古代、专注社会学领域的法国来说,能意识到自身关注点的偏狭,主动将注意力移到当代,把文学剥离出社会学,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清醒。1988年,法国文化部以官方立场表明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重视,邀请陆文夫等多位“寻根文学”“伤痕文学”代表作家赴法访问。出版界对文化部塑造“当代”的意图心领神会,开始将目光从“鲁郭茅巴老曹”转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活跃作家。同年出版的《中国短篇小说集》[1]参 见 A Cheng(阿 成 ), 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s:nouvelles de Chine (1978-1988), Aix-en-Provence:Édition Alinea, 1988.就以1978年为起始,盘点中国“当代”,有意识搁置“近现代”作品,聚焦与法国“共时”的中国文学。这种视角转换的努力是持续的,1994年伽利玛出版社也发行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2]参见Annie Curien, Anthologie de Nouvelles chinoises contemporaines, Paris:Gallimard, 1994.,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东方语言文化中心(Inalco)附属图书馆(Bulac),将“中国现当代数据库(fond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以1949年、1978年为转折,划分为三大目录。1949年至1978年的收录比例(28%)远多于新中国成立前(7%),更多聚焦最新一代小说(1978年之后作品占比65%)。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区分现当代并非法国的学术习惯,这种细腻的区分体现了对中国学术标准的关注。保留法国学界将1978年视为转折的习惯,也是在有意识地呈现本土研究的“阶段性”。
其次在文化概念上,“中国”在逐渐摆脱“东方”和“亚洲”等模糊标签。对欧洲来说东方曾是一个模糊的整体,中国走出“神话”和“含混”,历时三百多年。[3]从马可·波罗1275年来到中国并将她描述给欧洲人起,中国就是一个和“神话”相浑融的乌托邦。直到1585年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欧洲才确定中国是地理上存在的一个国家,与传说中的丝人国、鞑靼、满洲一脉相承。基于这种笼统性,传统汉学研究中国时,常把其他亚洲国家兼收并蓄。“亚洲”“远东”“东方”,都算“中国”含糊的同义词。如1923年介绍道家思想的作品,标题是《东方哲学——印度、中国、日本》[4]参见René Grousset,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Inde-Chine-Japon, Paris: Nouvelle Librairie National,1923.。受此汉学传统的深刻影响,介绍中国的丛书往往保留着“东方一体”的烙印。如20世纪80年代的“远东文学”[5]Lettre d’extrême Orient是弗拉马利翁出版社的亚洲系列丛书,是法国最早开始译介中国当代小说的丛书之一。“认识东方”[6]Connaissance de l’Orient是伽利玛出版社两大系列丛书之一,专门介绍亚洲文学。另一个是七星丛书(Pléiade),介绍法国文学。,都把多个亚洲国家古今拉通、穿插介绍;关注中国的学术期刊《远东远西》,也把中国作为远东的有机部分。但当下将“中国”剥离出来的意识已日益清晰,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有了独立分类。南方书编直接以《中国文学系列》(lettre de Chine)命名,中国蓝、毕基埃等都有独立的中国类目。瑟耶(Seuil)未按国别分类,但在官网能直接用“中国小说”检索到全部译作。伽利玛仍将中国文学寄居在“亚洲大陆和非阿拉伯近东”中,但检索“中国小说”,会看到该官网甚至为中国建立了交叉目录,包括“认识东方—书籍版”“认识东方—口袋书”和“中国蓝”。从收购“中国蓝”的举动也可看出伽利玛建构独立中国之决心。
在文学面貌的铺陈上,法国“作家名单”和“作品群”的译介批次,也体现出明确的推进逻辑,即“主要流派—流派内主要作家—流派内小众作家—无派系自由写作”。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在我国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同一时期,刘心武、张贤亮、张辛欣、韩少功、白桦等,就走入了法国视野。90年代主要增加了沈从文、冯骥才、贾平凹、汪曾祺、苏童、余华、莫言、李锐、马健等,从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法国译介对“寻根文学”的关注仍在继续,但已开始跟随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流变,将注意力转向了现代派和先锋派。2000年后逐渐不再以流派为依据,女性写作开始受到关注,王安忆、池莉、张欣欣、李昂、张爱玲、迟子建等都有较成体系的翻译。更年轻、更具现代意识的作家,被有序发掘,如废名、寇曹、梁鸿、李洱、范稳、小白、李娟、李敬泽、冯唐、张炜、阿乙等。2010年后,法国出版界在不断完善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刘震云、王刚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谱系时,还发掘了更多新锐作家,如戴思杰、李敬泽、黄蓓佳、金宇澄、张贵兴、崔子恩、薛忆沩、黄锦树、盛可以、曹文轩、季大海、周云蓬等。从作家、作品的“批次性”,明显可看出法国译介对当代思潮的追踪,对经典作品体系的完善和对“新生代”的关切。
2.新千年后,中国当代小说在法国的译介出现了一些喜人的新趋势。首先,最明显的是流行度大增,普通大众对中国小说愈发好奇,对中国的书商和出版社的关注明显增多;其次,作品形式多样化,网文、漫画、动画、戏剧齐头并进;最后,“当代文学”的构建视角日益宏大,小说种类趋于完备、“译介地图”扩张。
我们可以认为如今的法国普通读者,已被培养出阅读中国当代小说的“自发兴趣”。绝大多数当代作家在法至少拥有一本译作;法国相当于“当当网”的图书销售网Fnac,总结了最畅销的193部中国小说,前20位中13部是当代小说[1]参见Fnac官方网站https://Livre.fnac.com.目录按Roman et Nouvelles - Roman étranger - Romans Chinois - Meilleures ventes Roman Chinois(中国最畅销小说)。;相当于豆瓣的读书网站Babelio上,能找到很多普通读者写的当代小说书评;不少知名作家拥有了固定的粉丝群,池莉小说最低销量都有四五千册,余华的《兄弟》累积销量更达五万多[2]该数据通过出版统计网站EDISTAT(http://www.edistat.fr/)查询,这个网站的数据来源是书店、大商场的实际销售,而非出版社所宣称的销售情况。。中国小说逐渐“畅销”的趋势,吸引了更多出版社加入译介大军,早不再是“四大出版社、两大书店”独力支撑的状况。河流出版社(Fleuve)和黎明出版社(l'Aube)较有针对性地译介“80后”作家、华裔作家;一些小众出版社,如明书(Ming Books),翻译了不少刘震云和格非的作品;“非”出版社(FEI)专注于当代儿童文学;祖玛出版社(Zulma)翻译了张爱玲、张悦然和洪子诚;一贯只译介道家思想的阿勒班·米歇出版社(Albain Michel),2000年起也陆续翻译了华裔作家山飒的《女皇》《尔虞我诈》和《裸琴》[3]参见Shan Sa, Impératrice, Paris: Édition Albain Michel,2003;Shan Sa, Les Conspirateurs, Paris: Édition Albain Michel, 2005; Shan Sa, La Cithare nue, Paris: Édition Albain Michel, 2010.。
影视化也是流行趋势。2017年费米娜奖得主、戴思杰的电影作品《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以动画片的形式上映。[1]Dai Sijie, Balzac et petite tailleuse Chinoise, produced by FUTUROPOLIS, Paris, 2017.10.12.2020年改编自张爱玲小说《海上花列传》的电影《海上花》也在法国上映。[2]Les fleurs de Shanghai,Directed by Hou Xiaoxian,Produced by Paris:Carlotta films.2020.7.22.台湾的“80后”作家许俐葳[3]又名godwind Hsu,61 Chi,神小风。由此人可见当今法语翻译的一个小弊病:各搜索平台未能及时将多个笔名关联为同一作者。如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用Godwind Hsu搜索能找到作品,用61Chi和本名却没有任何结果;Babelio则是61Chi能搜到作品,其余名字皆无结果。的两部作品《房间》《少女与食梦貘》[4]参见Xu Liwei, Elle se laisse dévorer, Versailles:Édition H, 2020; Xu Liwei, Room, Versailles:Édition H, 2021.、香港女作家安静的小说《爱在灯火熄灭时》[5]参见Annie Lam, Un rayon de lumière dans la cité des ténèbres, Paris:Édition Gope,2020.,都出版了法语版漫画。
当代中国小说的类型铺设也基本完成,各类小说中最时兴的作品基本都被及时译介。
侦探悬疑类小说:何家弘的五部小说在黎明出版社已共有八个版次[6]参见 He Jiahong, Le mystérieux tableau ancien(神秘的古画),La Tour D’Aigues: L’Aube, 2013、2016、2022;He Jiahong, Crime de sang(血之罪),La Tour D’Aigues:L’Aube, 2011 ;He Jiahong, L’énigme de la pierre Oeilde-dragon (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La Tour D’Aigues:L’Aube, 2011 ;He Jiahong, Crimes et délits à la Bourse de Pékin (股市幕后的罪恶),La Tour D’Aigues: L’Aube,2005;He Jiahong, Crime impuni aux mont Wuyi(无罪谋杀),La Tour D’Aigues: L’Aube, 2013、2014.;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由库存出版社(Stock)2017年出版,视点出版社(Points)2018年再版。蔡骏的《生死河》由XO出版社2018年出版。2021年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暗黑者》由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社出版。
武侠类小说:经典作者如古龙、金庸等,前者在法国已有至少十个译作;2017、2018两年,金庸的译作也密集出版了八种。《远东远西》2012、2015年,均在第一期发表过分析金庸美学特点的论文。最新仙侠网文如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于2021年由马勒(Maned)出版社出版;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也在同年由纳兹卡(Nazca)出版社出版。
科幻类小说:刘慈欣的13部译作共有17个版本,由多家出版社如南方书编、德勒古(Delcourt)、海勒·塔森堡(Heyne Taschenbuch)等合力涵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录了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慈欣作品集》中文版。雨果奖得主郝景芳的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2018年由河流出版社出版,《流浪苍穹》2017年由沃尔特(Rowohlt)出版,《看不见的星球》2016年由特书(Tor books)出版。
网络小说:2017年,中法小说爱好者共创“元气阅读Chireads”[7]“元气阅读Chireads”的网址为:https://chireads.com。网站。该网站与起点中文网合作,取得版权方授权,专译中国畅销的武侠、玄幻、修仙、神魔等网络小说。该平台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甚至积累了不少本土之外的法语区用户。论坛月均活跃人数近百万。
儿童文学与女作家译介:毕基埃和“非”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曹文轩和黄蓓佳的作品,杨红樱更由前者出版了六部作品、14个版本;HO出版社也出版了沈石溪《狼王的梦》(2013)和《残狼灰满》(2019);“民”出版社(Minedition)2020年出版了于虹呈的《小黑鸡》。对女性作家的关注更是持续而强烈。截至2017年,法国已翻译了80位当代中国女作家的作品,王安忆、池莉、张欣欣、李昂、张爱玲、迟子建、残雪等都有十个以上的译本。[1]参见周蕾:《中国当代女作家在法国的翻译和接受(1978-2017)》,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学系,2018年,第16-26页。旅居国外的女作家艾米、郭晓橹、山飒等也有涉及。
地缘性构建日益全面,港澳台地区和少数民族作家的译介有序进展。如香港的安静、西西、周蜜蜜,澳门的廖子馨,台湾的李碧华、孟瑶、施叔青、苏伟贞、朱天文、朱天心等,在法国都有译作。安毕诺夫妇合著《台湾现代小说典藏选集》,囊括1920年至今的32位台湾作家,前两卷已在2016年出版。文学作品“形式”扩展到绘画领域,出现了漫画译作(如郑开翔:《街屋台湾》,2021年,艾莉缇出版社)或小说漫画化。少数民族作家也被有意识发掘。20世纪90年代介绍了知名作家如扎西达瓦、张承志等;世纪之交后,更能看到一种“发掘主流视野外作家”的努力。“中国蓝”2001年出版了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银狐》;伽利玛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回族作家李进祥《女人的河》;友丰书店2019年出版了藏族作家阿来的《空山》和《尘埃落定》、2021年出版了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小说集《僧舞》。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作家虽没有法译本,但已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建目介绍,并收藏其中文版作品,如仡佬族女作家王华,满族作家关仁山、朱春雨等。对少数民族写作的视野在有意识扩张。
3.学术研究条件改善,新一代研究人员成长。中国当代小说相关研究较少,但并不全是关注缺失。更主要的限制原因有二:“圣伯符主义”传统和比较文学学科要求。
圣伯符以“结合作者生平、理解作品内涵”为核心的研究方式[2]即圣伯符(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在其代表作《星期一漫谈(Causeries du Lundi)》中表现出的对历代法国作家的点评方式。,对法国的“作家研究”影响深远。文本批评往往需要现象学式地罗列生平,分析童年关系和成年经历对其人、其文的影响。脱离作者经历,在法国批评界看来缺少必要的“人文厚度”。
而中国当代作家拥有法语传记的极少,法国研究者很难了解他们的详细经历。对学术研究来说,缺少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料类型。这常使学者对研究深度丧失信心、放弃主题。但“当代华文中短篇小说网”[3]“当代华文中短篇小说网”的网址为http://chineseshortstories.com/。的出现,或将改变这一状况。该网站由汉学家杜碧姬与研究中国的学术期刊《亚洲新声》合创。用“姓氏首字母”和“地域”的交叉索引,介绍了数百位当代中国作家,其中不乏小众写手。不仅以数千字篇幅介绍作家生平、文坛地位和作品体系,还翻译了很多作家剖白内心、阐述理念的讲稿[1]例如张欣欣于2018年7月16日写的《我的中文处境》,徐则臣于同年3月10日写的《我写中篇,因为我有疑难》,以及2021年阎连科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的发言《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帮读者了解中国作家的精神世界。该网站梳理作家“人生轨迹”的转折,为法式“现象学生平梳理”提供了线索,很好地填补了这种研究资料的“类型性”缺失。
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要求,则沿袭了索邦学派在语言方面的苛刻。要做关于中国小说的学位论文,导师与学生都需要精通汉语,至少也需被研究对象具备成体系的作品译本。这样一来,导师基本局限在汉学圈,研究条件成熟的作家也有限,有研究能力的学生就更少。但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了中国小说研究在法国本土的“代际传承”:汉学家们的弟子不再以中国学生为主,法国弟子亦开始纷纷将博士论文贡献给中国当代研究。如安毕诺的学生奥勒良(Aurelien Boge)研究莫言(2021);杜特莱的学生弗朗索瓦(Francois Dubois)研究莫言(2017)、保罗(Paolo Magagnin)研究郁达夫(2010);何碧玉的学生梅(Mei Mercier)研究王小波(2016)、苏菲(Sophie Coursaul)研究韩东(2018)等。[2]括号所注为答辩年份。按作者名和答辩年可在法国博士论文网theses.fr上找到相关论文。另有很多尚未答辩的论文。研究界语言水平整体提高尚需时间,但博士论文的增多意味着懂汉语的“下一代”学者正在成长。
学术期刊对当代小说的兴趣也在加强。较常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期刊,主要有《比较文学评论》(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通讯》(Communications)、《远东远西》(Extrême-Orient Extrême Occident)、《亚洲新声》(Jentayu)和《中文世界》(Monde Chinois)。前两者最关心当代作品、关心中国文学的时代特质;《远东远西》涵盖古今,对当代文学也有所涉猎;《亚洲新声》专门译介当代中短篇小说或长篇节选;《中文世界》则关心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近几年各大刊物研究当代作家的文章明显增多。如《远东远西》2015年、2020年都有分析盛可以的文章,前文还是中法合著。[3]参见Xu Shuang&Ariadna de Oliveira Gomes: “Le corps souffrand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puis la nouvelle période(1979-2015),”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o.39, (January 2015), pp.145-176.2020年第一期更有三篇文章专题讨论“中国意象”与“怀旧”问题[4]参见Angel Pino&Isabelle Rabut, “Le Commerce de la nostalgie dans la Chine d’aujourd’hui,”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No.44, (January 2020), pp.17-40 ;Isabelle Charleux,Matthias Heyek&Pierre-Emmanuel Roux, “Le passé à vendre:commercialise l’histoire en Asie,”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o.44,(January 2020), pp.5-16; Clémentine Gutron, “L’Usure du passé, Marché du souvenir et mirage d’histoire,”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no.44, (January 2020), pp.209-220.;《通讯》也在2016年、2020年分别发表金宇澄批评,2019年还发表了王宁教授的《中国文学后现代性概览》[5]参 见Wang Ning, “Cartographie de la postmodernité chinoise,” trans.David Bartel, Communications, no.60, (April 2019), pp.104-119.。但总体来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论文的译介并不多,这与国内学界争先恐后译介法国理论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至少说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进入法语世界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也对我们精通法语并直接用法语著述和发表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纵观法国的中国当代小说译介史,会发现“外部世界”对中国文学,自有其接受逻辑、消化方式和认知节奏。那么要想摆脱法国“汉学情怀”对中国文学的遮蔽,中国学者能做些什么?这是值得当代学者深思的问题。如何帮助法国汉学界出离自身、意识到“法式感性”在筛选中国文学时的“主观”?如何向外国读者传达有细节、有温度的“中式感性”?要跨越意识形态分歧,还需漫长的时间和大量实践经验的累积;促进文学沟通,中法两国的学者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国当代小说在法国的译介,总体来看的确发展可喜,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