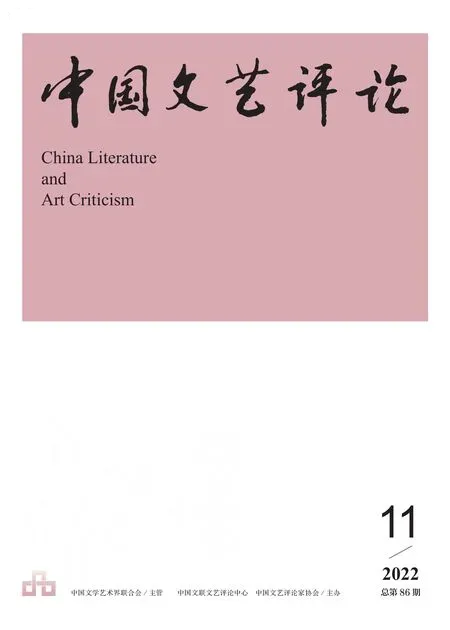论文化创意实践的美育属性
■ 王文革
“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10月1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基于美育在人才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育已经被列为国家教育方针,成为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重要方面,在各级各类学校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广泛深入开展。当前,“创意”一词广泛流行,创意活动广泛开展,创意实践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意特别是文化创意的属性,与美育十分契合。将文化创意实践与美育结合起来、融合起来,让文化创意实践发挥美育的功能,让美育充满文化创意,是进一步提升美育实效的一个重要路径。
一、作为一种审美活动
“创意”是现在相当流行的一个高频词。“创意”一词古已有之。如汉代王充 《论衡·超奇》曰:“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东汉]王充原著:《论衡全译》,袁华忠、方家常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8页。这里的“创意”,大约是创立思想的意思。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2]王国维:《人间词话 人间词》,谭汝为校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第27页。这里的“创意”大约指的是创立思想情感。这些“创意”有创新思想、创立内容的意思,都还不是现在人们所使用的“创意”。
现在使用的“创意”,应当是随着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而兴起的一个词,一般认为与英语的creative(a.)或create(v.)对应。就“创意”一词来说,“创”与“意”均可分别解释、分别理解,即:创,创新、创作、创造、创立;意,主意、观念、智慧、思维。“创意”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创意”,即其字面意思:创立一个新的主意。这个“主意”也往往被俗称为“点子”。张京成认为:“创意就是创立一个新主意。创意的属性有两个:第一个是新颖性,第二个是原创性。”[3]转引自王文革主编:《文化创意十五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狭义的“创意”着重于意念的创新、创立。这个意义上的创意,大约包含着不仅是提出一个新的主意,而且是这个主意与众不同、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的意思。广义的“创意”,则指各种富有新意的、体现奇思妙想的发现、发明、创造活动。而文化创意则往往与广义的“创意”相关,其所指范围也十分宽广,大凡与文化、与精神有关的发现、发明、创造的活动,都可以称为文化创意,如文学创意、创意文学,广告创意、创意广告,活动创意、创意活动,等等,以至“创意”一词的使用也十分广泛,成为人们使用频繁、一致认可的一个褒义词。如叶朗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文化时代,就是创意的时代,就是追求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时代”[4]叶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光明日报》2011年12月7日,第11版。。可见,现在的“创意”一词,已与从前的“创意”一词大不相同。
文化创意的本质特征是求新、求变、求好、求妙;文化创意活动是创意者按照个人意愿、循着相关要求和目的、发挥个人智慧能力、付出一定努力、创造出一个作品或产品的实践活动。与一般的实践、劳动、工作比起来,文化创意不是机械重复性的。它没有现成答案,它需要经过艰苦的脑力甚至体力劳动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作品或产品,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活动。因而这种活动对创意的环境、创意主体都有一定要求。但创意活动具有很强的自由性、主体性,创意的过程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充满新异性的过程,因而创意活动也是很有魅力、很有趣味的活动。与一般的知识技能的学习比起来,创意实践不是被动的接受,不是一旁的围观,而是主动的创造、积极的改变。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在创意活动中,面对创意要求,如果你不主动、不积极投入创意活动,你将一无所获、一事无成。不管是独创还是合创,创意者都要尽其所能地投入到创意活动中,这样才可能产生创意、获得创意的成功。
创意的过程不免存在一个“受困”“受阻”的环节,也就是遇到思路堵塞、一片空白、不知所措、没有选择或难以选择等困境。但一旦思路打开、新的思想不断出现的时候,那种豁然开朗的情景则令人欣喜不已。经过这一段“困”“阻”之后,终于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方案、作品甚至是文创产品,创意者所获得的愉快也是难以言表的。文创方案、作品、产品,同样是创意者智慧、体能的实现,是其辛苦劳作的结晶。在创意中,创意者不仅要考虑新颖,也要考虑适用,还要考虑美观和可行,体现了对美善的极尽所能的追求。比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火仪式的设计,总导演张艺谋考虑过各种方案,但都觉得不满意,不能完美地体现“简约、安全、精彩”的办会目标,最后忽发灵感:火炬手跑到处于巨大雪花镂空中的主火炬台后,面向观众、顺手将手中的火炬插到台上,完成主火炬的“点火”仪式。这个方案在实际完成中很自然、也很顺手,而且还很有寓意。但这个方案也是在提出各种方案、否定各种方案之后才得到的,十分来之不易。这个创意也让北京冬奥会的主火炬点火仪式与此前的历届奥运会点火仪式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文化创意实践是一种审美活动,但与一般的审美活动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
二、创造不一样的审美对象
我们认为,广义的文化创意可以是一种新情景的“发现”,也可以是一种新事物的“发明”。
创意是“发现”。柳宗元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1][明]王阳明:《传习录》,阎韬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萨特也说:“我们的每一种感觉都伴随着意识活动,即意识到人的存在是‘起揭示作用的’,就是说由于人的存在,才‘有’(万物的)存在。”[2][法]让-保罗·萨特:《萨特文学论文集》,施康强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94页。他们都强调人对外物的发现与照亮。从创意的角度来说,已经发现的和人人都能发现的就不是创意,只有那种见人之所未见、道人之所未道的,才属于创意。所以,“发现”也要强调新颖性、原创性。像杨万里的《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又如朱熹《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的诗作,与其说是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诗人的“发现”。诗人发现了这一清新可爱的美景,将它用诗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谓是照亮了这一清景,化瞬间为永恒。
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发现”的潜质、潜能,只是这种潜质、潜能被压抑、被束缚了而已。正如朱光潜在《谈美感教育》中所说:“美感经验并无深文奥义,它只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时某一境特别新鲜有趣而加以流连玩味,或者把它描写出来。这句话中‘见’字最紧要。我们一般人对于本来在那里的新鲜有趣的东西不容易‘见’着。这是什么缘故呢?不能‘见’必有所蔽。我们通常把自己囿在习惯所画成的狭小圈套里,让它把眼界‘蔽’着,使我们对它以外的世界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囿,有所蔽,许多东西都不能见,所见到的天地是非常狭小,陈腐的、枯燥的。”[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48-149页。人们确实会因各种现实的原因而看不见生活中的美。怎样才能看见这些美呢?朱光潜说:“诗人和艺术家所以超过我们一般人者就在情感比较真挚,感觉比较锐敏,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我们‘见’不着的他们‘见’得着,并且他们‘见’得到就说得出,我们本来‘见’不着的他们‘见’着说出来了,就使我们也可以‘见’着。像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他们‘借他们的眼睛给我们看’(They lend their eyes for us to see)。”[2]同上,第149页。借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来“见”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但用自己的眼睛来“见”却显得更加重要。文化创意实践也是“见”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实践,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有趣的对象。比如,直着切开苹果,见到的是一个剖开的苹果核;但如果突发奇想、横着切开苹果,就可以见到一个五角形的苹果核。这时我们也许要感叹自然造物的谨严认真了。
创意是“发明”。文化创意的“发明”,是“无”中生“有”。“文化创意的所谓‘发明’,就是依据各种文化材料创造出本来没有的文化产品、文化成果;而这个‘发明’,可以是一部鸿篇巨制,也可以是一个小品涂鸦;可以是多年劳作的结果,也可以是一时妙手偶得;可以是众人合作的作品,也可以是个人独自完成的成果。”[3]王文革主编:《文化创意十五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6页。文化创意的“发明”弹性极大,不过,还是要体现出新颖性、原创性以及奇思妙想的特性。像故宫文创产品对“朕”的使用,将“朕”与日常生活关联起来,产生诙谐、可爱的效果,这是原来没有的,可视为一个成功的文创“发明”案例。又如利用汉字元素的创意作品,也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如鲁迅设计的北京大学校徽,图案中的“北大”,如同一位大人托着两个小人,将北京大学人才培养的使命进行了形象化呈现;又如中国工商银行的标志、永久牌自行车的商标、中国铁路的标志、北京冬奥会的会徽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
创意的“发明”可以灵活多样、自由发挥,但创意的结果却并非无理性、非理性。创意的“意”,作为创意的结果,要么合情,要么合理,虽然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入于情理之中。好的创意,常常令人不可思议,以为是神来之笔。如齐白石的画作《蛙声十里出山泉》,是一篇“命题作文”。老舍请齐白石根据清初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一幅画,要用水墨画出蛙声来。齐白石根据老舍的提示,创作了这幅作品。[1]参见舒乙:《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中国艺术报》2013年5月6日,第8版。在画中,一条溪流从山中汩汩滔滔流淌出来,溪中清晰可见六只蝌蚪顺流而下。于是,画面上没有蛙而蛙声可闻。
朱光潜在《谈美感教育》中说:“在艺术创造中可以把自然拿在手里来玩弄,剪裁它、锤炼它,从新给以生命与形式。每一部文艺杰作以至于每人在人生自然中所欣赏到的美妙境界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2]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51页。他说的是艺术创造,其实文化创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广义的文化创意,甚至也包含着艺术创意和创造)。文化创意也是把“自然”作为材料进行“剪裁”“锤炼”,赋予其“生命与形式”,从而创造出新的“作品”。而在这个过程中,创意者不仅见到了一个不同的“自然”,而且也见到了一个不同的自己。
在这里,“发现”也可以说是“发明”。当你把你的“发现”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个“发现”就成了“发明”。如王国维的词句“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3]王国维:《人间词话 人间词》,谭汝为校注,北京:群言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朱颜”“花”都是短暂的美好之物,而“镜”“树”也都成了美好之物不能留驻人间的见证者。这是“发现”。但整个词句不仅文字精巧,而且设喻也很新颖。这又是“发明”。“发明”也可以说是“发现”。所有的“发明”,也都不过是对事物间原本就存在的关联的“发现”与应用。就如朱熹所认为的:“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又说:“阶砖便有阶砖之理。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还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是物也。”(《答刘叔文》,《文集》卷四十六)[4]转引自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96-797页。冯友兰也持相同看法。他在《新原道》第十章《新统》中说:“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借用旧日中国哲学家底话说:‘有物必有则。’”[5]同上,第808页。另外,冯友兰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未有飞机之前先有飞机之理。”[6]转引自杨建民:《相知相得两哲人——记张岱年与冯友兰的交谊》,《人民政协报》2013年5月2日,第7版。这个“理”,如果是指事物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规律、关联,朱熹、冯友兰的说法还是相当深刻的。对于文化创意来说,“发现”与“发明”都是事物间关联的生动形象的、有效的呈现。
不论是“发现”还是“发明”,都是创造出一个新颖的、原创的作品或对象。可以说,这种创造往往具有审美的属性,与审美创造相同或相通。
三、塑造心“灵”的学习主体
文化创意并非高深莫测。但对很多人来说,创意是相当困难的。他们更愿意接受现成的东西,不愿意改变、也不知道怎样改变已有的现实和对象。他们受到了各种有形无形的压抑,如“已有知识、经验的压抑”“心理的压抑”“功利性的压抑”“文化传统、文化氛围的压抑”“语言的压抑”“信息的压抑”等。[1]参见王文革主编:《文化创意十五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36页。它们都有意无意地束缚着人们的创意。有必要提高对文化创意的素养的认识,为人们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创造有利条件。概而言之,文化创意的素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创意思维。创意思维是一种力求改变现有关联、建立新的关联的思维。创意思维是一种灵活的思维,其意识的关注点、兴趣点、兴奋点能灵活迁移,思考的方式、角度、方法能多面转换,观念不固执、不僵化、不保守,内心保持开放性、包容性、敏锐性,如同苏轼所说的“静”“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这种“静”“空”,是对日常生活、日常思维的一时淡忘,也因此才能有所突破、有所超越。这种思维特别善于发现事物间隐藏的关联,从而建构起新的关联。这种思维具有自由想象的能力,所谓“迁想妙得”(顾恺之语)、如有神助。这种思维不认为当下的事物关系就是唯一的、不变的,甚至也不认为现有关系是最优的、最美的。
创意意识。创意意识是指具有创意的自觉性、习惯性的意识。它能用改变的态度看待对象,不把对象看成是一成不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是一种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意识。同时,现实的、现有的生活一定是不完满的,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足的,要通过创意来不断完善它。还有就是相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好”是对“最好”的超越。另外,对“新”的追求也体现了人的本性,正所谓“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兰亭诗》)。不满足于现有、已有的东西,具有强烈的改变对象、创造出更完美对象的意识,就是创意意识。在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有一个《闪亮的雪花》节目特别感人:当众多小朋友举着闪闪发光的“和平鸽”欢快奔跑的时候,有一只“小鸽子”掉队了。正当这个“小鸽子”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小姐姐迅速过来,牵着她回到队伍。这个情节被网友称为“一鸽都不能少”。这个情节十分真实、自然。扮演“掉队的小鸽子”的小朋友叫徐书元。她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闪亮的雪花》呈现的“寻找掉队小鸽子”的感人片段,就源自她排练期间真实的“落单”经历。徐书元说,当时排练时,她要找到的位置距离比较远,“我的速度也比较慢,走着走着就发现大家已经进去了,我就落在了外面,幸好有一个姐姐看到了我,把我拉到了队伍当中。”后来导演就根据她的这次“落单”经历,完善情景之后作为了开幕式中的那场“一鸽都不能少”的情节。[1]参见沈杰群:《排练中的意外 成就感动全网细节》,《中国青年报》2022年2月6日,第3版。如果导演没有创意意识,徐书元排练中的那次落单经历也就得不到提炼和升华。
创意动力。创意动力来自追求改变、追求美善的意愿,来自创意过程的情感体验,来自创意目标达成的满足期待。在很多情况下,不改变现状、满足已有的现状、“躺平”,也是可以的。但创意者往往要追求更善的善、更美的美,由此甚至不满足已有的结果,从而克服困难、不断开展创意活动。比如,乔布斯对苹果手机“一键”式的近乎强迫症的追求,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还有我国文学史上那些“一字师”,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对文字的反复推敲,也是这种务求完美的精神的体现。
创意方法。创意无法,创意也有法。创意可以是灵感式的,妙手偶得、直接达成;也可以是推演式的,不断推进、直到满意;也可以是选优式的,在众多方案中寻找最优方案;也可以是修改式的,对已有方案不断打磨完善,等等。像一些创意专家提出的头脑风暴法、鱼骨图、思维导图法、文字联想法等,都对创意方案的产生、提出有所助益。
产生创意的一条有效路径,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嫁接、融合。叶朗说:“美国《福布斯》网站发表文章《乔布斯可以教给我们的十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最永久的发明创造都是艺术与科学的嫁接。’乔布斯指出,苹果和其他所有计算机公司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苹果一直设法嫁接艺术与科技。”“这就是乔布斯这位天才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启示:艺术和科学的融合,艺术和高科技的嫁接,乃是创意的灵魂。”[2]叶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时代》,《光明日报》2011年12月7日,第11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就是艺术与科技的完美融合,充满了各种美妙的创意。如,倒计时中的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都是一幅美妙的中国画,极富诗情画意。而且,2月4日恰逢立春,二十四节气,第24届冬奥会,形成一种天然巧合。这个场景将中国人的诗意与浪漫生动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那些奇思妙想的场景,给世界观众带来惊喜。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性、自由性、情感性,而科学的特点是抽象性、概念性、严谨性;艺术“及人”,科学“及物”;艺术合目的,科学合规律,艺术与科学的融合能对创意思维的发展、创意意识的培养、创意动力的蓄积起到良好作用。至于创意方法,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本身就是创意的方法。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也与“全人”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
王夫之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俟解》)[1]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王夫之对不能“兴”的人进行了很生动的描述。这样的人,就是被各种实际目的所控制而不能有所创意超越、有所兴发感动的人,他们“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而开展文化创意实践,正可以让这样的人“兴”起来,让他能“见”到被遮蔽的事物本性,让他的心“灵”起来。开展文化创意,是人的创意思维、创意意识、创意动力、创意方法等的综合体现。文化创意要动脑、动情、动手。而这些“动”,都与人的主体性、生命性息息相关。它要调动人的各种能力,它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它是“创造”,是个人体能与智慧的体现和实现。它也是一种劳作,但这种劳作不是那种被动性的、机械重复式的劳作,而是主动的、打破现实、寻求新意的劳作。它也不同于一般的学习。学习是对新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对学习者来说,学习的内容固然是新的,但学习的过程还是接受性的。创意的过程则是创造性的。因此,文化创意能充分释放感性要素,具有相对充足的感性特征、自由开放的性质以及突显个体生命性的作用。
四、美育改进的一个重要路径
美育的实施,是因为人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理性,并使理性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感性却被压抑被束缚,这样就导致人本身的片面发展。美育所要改变的,是人的片面发展;美育所要达成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美育的根本特性是感性,以及与感性密切相关的方面,诸如感知觉、直觉、情感、想象、潜意识、经验、体验等方面。现在美育在学校得到广泛开展,但在对美育的这种感性特征的把握方面,还存在研究不够、重视不够的现象。正如杜卫所说:“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教育界虽然也开始意识到知觉、想象、情感、直觉等感性素质具有重要价值,但对人的感性素质的研究不够,在整体上重视更不够。许多人还是停留在‘文以载道’的观念上来看待美育,有意无意地把美育作为以艺术的形式灌输抽象道德的途径。……人们对于美育的价值,总希望在‘动之以情’之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晓之以理’。殊不知,美育追求的就是‘动之以情’本身。”[2]杜卫:《美育三义》,《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1页。美育本身是为了培养、解放人的知觉、想象、情感、直觉等感性的方面,但如果它使用的还是抽象概念的方式、“功利实用”的方式,那么一定程度上就会导致目的与手段的背反。
杜卫提出美育要发展人的“丰厚的感性”,而“丰厚的感性”涉及下面五个主要方面:“首先是生存的具体性”“其次是肉体性”“第三是生命活力”“第四是以体验为核心的一种心理能力”“第五是体现于直观形式中的观念意识”。[1]杜卫:《美育三义》,《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第12页。笔者以为,作为感性的教育,理想的美育应该在这五个方面都能有所达成,但实际上现实的美育离这五个方面的达成还有相当距离。以教学为主、以美学知识传授为主的美育,要在这五个方面使学生的感性得到良好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种美育方式下,学生所获得的往往是美学的知识和审美的技能。即使是看起来感性十足的欣赏一类的课程,其所呈现的方式还是逻辑性的、秩序性的描述,这就与美感的直接的体验性、创造性、直觉性有一定距离。实际上,在我们不少的美育教学中不仅存在“文以载道”的现象,即追求抽象的概念性的“道”,缺乏丰富的感性体验的现象,也有“坐而论道”的现象,即以传授美学的知识技能为主,缺乏审美、创美的实践的现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美育实施主要载体的美育课程,本身也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希望通过这个载体通达审美之境,是有困难的。有必要对这个载体本身进行改进完善。
美育的感性化还涉及一个美育与生活的“距离”问题。在现有的美育教学中,学生往往是接受性的、旁观性的,是听众、是观众;美育与学生、与学生的生活关联度不高。这可能导致学生对美育的热情不高,学生的主体性在美育教学中没有得到有效体现。生活本身是感性的,也是感性的生动显现。王德胜认为,美学越来越概念化,“生活现实的蓬勃生动与美学介入的实质性缺位,成为长期困扰美学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他说,“美学应该而且可以‘活’起来,而‘活起来’的根本,在于摆脱自身对生活现实的游离及其知识化构造,具体进入人的生活并同时向人的生活开放。”[2]王德胜:《重建美学与生活的关系》,《光明日报》2016年9月28日,第14版。他说的是美学,其实对美育也是适用的。美育同样存在这种“具体进入人的生活并同时向人的生活开放”的目标,让人觉得外国不再遥远、古代不再陌生,让外国的东西、古代的东西能向我开放,或我向它们开放,相互敞开,相互照亮,也就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美都能进入我的生活。这是美育应当追求的理想的目标。如果不顾及学生本身审美经验的缺乏,用一种高阶的美育面向学生,就可能导致美育与学生的“隔”或“距离”。另外,人们往往用“美”的非功利性、非目的性以及审美的距离等来看待美育,以为不关注生活、不介入生活,似乎才是美育的本质属性。于是,美育就如同艺术中的“阳春白雪”,与生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成了凌空蹈虚、难以触及的东西。其实,美育本身应该与生活保持密切关联,既关联生活,又超越生活,这样的美育才可能取得良好成效。这里的生活,当然不是抽象的生活,而是具体的生活,是个体的当下的生活。我们的美育在让美育“生活化”方面显然还存在不足。歌德有句名言:“所有理论都是灰色的,生活的金树长青。”[1][德]歌德:《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0页。美育如果不与现实、不与生活密切关联起来,也会如同理论一样变成灰色的。而美育一旦与现实、与生活密切关联起来,也将变得生动和具有生气。
从美育的根本特征、根本目标来考虑,仅使学生有爱美之心是不够的,还应该使学生能够认识美、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应当探索实施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与美学知识的传授、经典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表演、各种活动的参与等既有联系但又不同。这种教学方式具有充足的感性特征,具有自由开放的性质,能突出个体生命性的内在要求,且与学生当下生活息息相关。文化创意实践就具有这样的美育特点。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就提出:“在学生掌握必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素养,帮助学生形成艺术专项特长。”[2]《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2020年10月15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0-10/15/content_5551609.htm。这里把“创意实践”与“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等列为同等重要的核心素养之一。笔者以为,“创意实践”既是一种审美核心素养,同时也是美育实施的一种有效路径。创意实践,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主要体现为文化创意实践。
五、让美育课堂“活”起来
文化创意是一种自觉的活动。创意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目标是明确的;也知道自己如何达成目标,路径是清楚的;最重要的是能将自己的设想付诸行动,实现从意念到设想、再到行动、最后到作品的完整的创意过程。
文化创意实践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蔡元培当年给美育所下的定义是:“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美育》,1930年《教育大辞书》条目)[3]蔡元培原著、金雅主编、聂振斌选编:《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蔡元培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人们似乎对其“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有所误解,将其理解成了在教育中开展美学理论的教学。很多美育教材往往是美学理论的通俗普及版本。课堂教学也往往是美学理论的讲解传授,“文以载道”、“坐而论道”,“说”的多、“做”的少,而“说”中又是说理传道的多、引导感受体验的少。这种课堂教学方式最大的不足,就是缺乏实践性,就是缺少学生的动手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朱光潜也很强调实践:“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4页。我们认为,与其让教师“说”十堂课,不如让学生“做”一堂课。认识活动是如此,审美教育也是如此。让学生进行一种“作品”的创意活动,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技能的培养、发挥,更主要的是一种创作过程的经历、体验。古人讲“道不远人”。“道”就在日常的事物中。通过这种创造活动,学生可以更有效地感受美。经过反复实践,学生就能很好地感知、了解对象,形成一定的经验和技能,正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1][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714页。。
文化创意具有很强的激励性。文化创意活动较之一般课堂教学的区别,在于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有效的体现和实现。学生要独立开展创意活动,独立完成创意方案、创意作品。这是对学生知识能力的考验和运用。在创意过程中,学生体验到“困惑”“困窘”“阻塞”甚至紧张、焦虑、挫折等情绪。这样的体验与知识技能的学习、理解、接受过程是大不一样的。这种看似负面的情绪对于学生的成长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能激发学生的“斗志”,培养学生的意志,深化学生对知识技能的理解。经过“困惑”“困窘”“阻塞”甚至紧张、焦虑、挫折的情绪低谷,学生一旦提出合理的方案、完成满意的作品,那种成就感和快乐、轻松将是无以言表的。这里的情绪体验是先抑后扬、先阻后通、先塞后达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2]参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8页。都属于学习中的“困惑”“困窘”“阻塞”状态。孔子的意思是说,学生还没有这种状态,就不去启发他、不去开导他。而学生在创意活动中对知识技能的运用,则体现着“举一反三”的教学原则。
文化创意具有很强的体验性。从创意的要求来说,创意活动合乎个人的意愿,因而学生或创意者将在创意活动中追求尽善尽美的目标。追求尽善尽美也是人的内在要求。看起来文化创意活动是个人的发现、发明、创造,是个性的发挥和体现,但学生或创意者往往以自身、以人为尺度,以合乎人的需求为目标,按照事物的规律进行创意。这种“无中生有”,追求合目的、合规律,不就是一种美的创造吗?而学生在创意过程中对对象的“触摸”,是一种深刻的感知行为;在创意过程中从“困窘”到豁然开朗、从紧张到突然放松,是一种真切的情感体验;创意活动从“无”到“有”,是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生动实现。文化创意活动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创造出现实中本来没有的东西,从而丰富现实生活、创造新的生活,并激发对生活的热爱。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我常想,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趣味,莫过于种花。自然界的美,像山水风月等等,虽然能移我情,但我和他没有特殊密切的关系,他的美妙处,我有时便领略不出。我自己手种的花,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简直并合为一,所以我对着他,有说不出来的无尚妙味。”[1]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夷夏编:《梁启超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页。梁启超在这里用种花比喻教育,这种情感的体验在文化创意作品上的体现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文化创意作品也相当于创意者亲手种出的“花”。另外,文化创意活动还具有情感逻辑和自由表达的特点[2]参见李思屈:《审美经济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本质特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8期,第100-105页。,兹不赘述。
总体来说,文化创意实践要遵循善的原则和美的尺度,文化创意实践因而能使学生或创意者成为善的表现者、美的创造者。文化创意通向审美之境。
另外,文化创意实践还具有很强的实施性。与“创意”属于同一语义场的词有“创新”“创造”等。“创意”与“创新”“创造”不同的是,后者是单一的动词性的动词,而“创意”则是动宾式的动词,也即作为动作的“创”是有对象的。这就使“创意”一词比“创新”“创造”具体,不像“创新”“创造”那么“大”、那么抽象。比起“创新”“创造”,“创意”更可行、更现实。一个小小的改变可以称为“创意”,但不能称为“创新”“创造”。如,将英语单词impossible变成I’mpossible,只加了一个标点符号,其意思就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称为“创意”,但不能称为“创新”或“创造”。因为“创意”的这种形而下性,相对于其他教学或生产活动来说,文化创意具有高度的可行性。所谓“生活无极限,创意无极限”,学生或创意者可根据自身条件或意愿进行力所能及的文化创意。这里,力所能及在创意活动中就体现得比较明显。创意活动不像其他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活动有很高的门槛。创意活动的主题、题材、体裁、载体等都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或喜好来选择、确定。因而创意活动本身是适合学生特点的。我们的教学实践也表明,文化创意性质的教学活动是很受学生欢迎的。
六、结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3][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都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具有伟大的创造力的人物。对此恩格斯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叶朗指出:“恩格斯的‘巨人’的概念,首先是说‘思维能力’,接着说‘热情和性格’,接着说‘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这就使我们的眼光从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专业知识和技能来说,美育、人文艺术教育的直接帮助好像不明显,但从思维能力方面,从热情和性格方面以及从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这正是美育、人文艺术教育的独特功能,这是从孔子一直到蔡元培所一贯强调的。”叶朗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也应当培养巨人。[1]叶朗:《大学当培养巨人》,《光明日报》2017年1月3日,第13版。其中,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这段话,此前通行的译文为: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文化创意实践对于培养造就恩格斯所说的时代“巨人”所需要的“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均是契合的。因为创意实践可以广泛开展,因而创意实践具有普遍的提升创新创造能力的作用。创意也许很小,创意也许很生活,创意看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创意的特性,如前所述,是新颖性、原创性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创意都具有改变现状、改变生活的作用。日积月累,积小胜为大胜,从量变到质变,从个体到整体,这种提升、这种改变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基于文化创意实践的易于实施,文化创意实践的广泛开展可以为实现“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陶行知语)的教育理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文化创意实践通过个体的创造,不断实现着个人的力量,不断完善着现实的生活,也为个体克服生活的同质化、“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