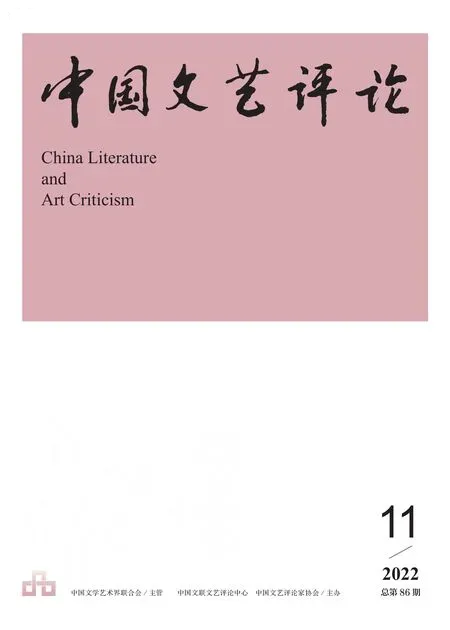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国际学界的对话
■ 刘 康
中国学术界今天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近现代以来知识、思想与学术的中西交汇、交流的“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双向脉络。中国话语、中国理论、中国学术在今天这个时代,将如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成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之中举足轻重、引领潮流的重要一翼?近年来,我与中国和欧美多位学者合作,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个角度,来参与当今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我们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和欧美不同语境下的中英文学术平台上展开的双语讨论。西方理论、中国问题,从字面上看就必然涉及中文和其他多语种,在单一语言的语境中讨论,也一定是跛足的。所以我们把多语种语境作为讨论的一个重要前提,以开展国际学界的对话。国际学界的一个现状是英文依然是主导性的通用语言,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对话平台扩展到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日文、俄文、阿拉伯文等多语种。但目前这类真正的多元、多样、多语种的学术平台尚不具备,所以我们还是从双语语境的讨论做起。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语境(context)问题,是要强调多语种并不等同于多语境。换言之,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之内的单一语境中,都可以用多语种发出声音,这可以称之为“对外传播”“对外交流”。但这跟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不同语境的交流和对话不是一回事,因此还称不上真正的多语境多语种的交流和对话。多年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中国文化、学术“走出去”的思路,乃至今天的“中学西传”话题,似乎都对于传播与交流的不同语境的问题有所忽略。这种思路认为只要有了多语种的工具和平台,以及掌握不同语言的人才和渠道,思想和学术就可以开展国际的传播和交流了,却忽视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语境下的交流与对话。不同语境中蕴含了不同的规范、习俗、价值观,没有对这些多元差异的不同语境的深刻理解,只靠工具化的多语种“对外传播”或“走出去”,实际上还是单向度、独白式(或卡拉OK式)的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即使这种自言自语是以多种语言形式来表达的。
因此我们开展的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把是多语种还是多语境的对话与交流视为一项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思考还是从对话的具体实践上,我们都予以高度关注。本文拟回顾数年来就此问题的思考、探索与实践,以就教于学界同仁。通过回溯西方理论中国问题这个话题的缘起、关注的要点、讨论的主要过程,希望围绕着多元多样的语境中如何展开思想和学术的对话与交流这个问题,与同行们进一步展开讨论和争鸣。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学术对话中道与术的问题,也即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价值观这个根本性的“道”的问题,以及不同规范、习俗、方式的“术”的问题。道与术的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学术对话和交流的目的和意义。我们为什么要开展国际对话?我们能否就对话和交流的道即价值观达成某种共识,即所谓求同存异中的“同”?亦或在今天这个相对主义、价值多元论盛行的时代,以谋求确立新的话语中心、价值主导为目标,其真实意图并非求同存异,而是“否定之否定”,以我为中心,取彼而代之?这种思路当然既不符合历史,也与现实背道而驰,更违背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但在我们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中,这个问题愈发变成一个时刻环绕着我们、令我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讨论的缘起和重点
中国近现代知识、思想和学术的出现、形成和建构,是一个跨越了几个世纪的、持续的、现在进行时的历史过程。19世纪末(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大致上是一个转折点。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1]转引自葛兆光:《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上的象征意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3-485页。现代中国思想先驱者之一的严复,在1895年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和《原强》等檄文,认为中国要应付这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保存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唯有接受西洋现代化的途径,当年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尚未付印就不胫而走,书中的“物竞天择”,似乎是在向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告别,同时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成为这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导。此前种种中西的体用之争、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之战,虽未偃旗息鼓,但中国开始以“世界的中国”的眼光来看待自身,重新认识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构想在世界之中的未来。这种眼光和构想是随着梁启超的四千年之大梦、严复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对历史的认知不断变化、拓展和更改的。20世纪以来,相对于几千年的古代文化,从“五四”以来逐渐形成了现代文化的“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就是一个中西冲撞、转换、融汇的现代传统。在此意义上,这个现代传统本身就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知识、思想和学术的又一个新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人文学界成为社会思潮的中心,在哲学、文学、历史和美学等领域内开始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大讨论,很快就演变成全社会热烈关注的文化反思、文化热。从历史上看,堪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媲美。80年代的中国译介了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把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话语体系。在21世纪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对中国、对世界、对历史的一个新的判断。在这个判断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梁启超、严复在一百多年前的思考的呼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和认识上的超越。在中国,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是“世界与中国”,而非“世界的中国”。前者蕴含着中国与世界平行而不相交的观念,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却确凿无疑地将中国置于世界变局之中,来思考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四十多年来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历程,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过程,也是“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的过程。近年来,我与中国及欧美多位学者关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是想从思想史、学术史的角度,聚焦中国的文艺理论来思考和把握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开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声音的新时代。[1]主要中文论文包括刘康:《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詹姆逊与詹姆逊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刘康:《中国遭遇西方理论:一个元批评角度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12月,第27卷;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个思想史的角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兼论研究方法、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话语体系的转换》,《中国比较文学》 2021年第4期;刘康:《美学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主要专辑包括《“批评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朱立元、曾军、刘康等:《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理论对话的新视角(座谈实录)》,《上海文化》2019年第8期;《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笔谈》,《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朱立元、王宁、曾军、刘康:《世界中的中国和西方:“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对谈》,《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曾繁仁、谭好哲、杨建刚、刘康:《美学与“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笔谈》,《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参见Wang Ning and Marshall Brown eds., Special Issue o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 (2018),其中收录了王宁、张江、朱立元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以及刘康、米勒(J.Hillis Miller) 与德汉(Theo D’ Haen)三位国际学者的评论与对话文章。Liu Kang ed, Special Issue of 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20, No.3 (2018); Liu Kang ed, Special Issue of 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22, No.5 (2020).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学术的肇始,现实和历史的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动态现实,从历史角度来予以把握和反思却极其困难。一方面40年的历程距离当下太近,而且还在不断演进中,思想史的总结和评判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虞。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与知识界是以历史的反思,尤其是对“文革”这个时间距离最近的时间段的反思为滥觞的。历史的角度、反思的角度,以及从大量译介的当代西方的思想中提炼的方法论、认识论,由此形成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高度自觉,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思提供了反思历史、着眼当代的主导模式和问题意识。这个历史/现实高度融合的反思模式与理论的自觉,也是所着力追踪依循的,或可称之为理论的历史化、历史的理论化的路径。
我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化”“元批评”的概念,并时常借用法国现代思想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以及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的“历史的多元决定”“症候式阅读”等观念,来探索方法论、认识论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希望以这些方法论和认识论所提供的思考路径,来反思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我提出的“历史化”“元批评”是一种双向、双重的思考路径:我们思考的对象或主题是理论的话语,所以既是方法论、认识论层面的思考,又是历史与现实问题层面的思考。从方法论、认识论层面来讲,就是对历史的理论化思考;同时要思考理论中蕴含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也就是理论的历史化思考。所谓历史化的角度,就是要把理论话语置放在历史的语境中,追溯来龙去脉,考察思想的形成与历史现实的互动。这是一个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理论的构成的角度,是对于理论的自我反思,也即元批评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文化批评和美学领域形成的各种理论话语,是讨论的对象和主题;其大历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多重背景或语境,是讨论要通过历史化和元批评方法加以把握和反思的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我们的讨论聚焦中国的文艺理论、文化批评和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话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现当代中国的知识、思想和学术体系中最重要的话语,我多年来一直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理论的中国化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美学理论在中国的历史脉络。这一学术研究的大背景当然是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而直接的学术背景是欧美的中国研究。我从1983年到美国迄今,始终在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中国研究这两个大的学科框架和话语体系下思考、写作、教学。欧美的中国研究多年来忽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发展,乃是一个重大的缺失与遗漏。对我来说,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中国研究这两个许多年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领域,反倒成为学术思考的两大支柱,并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的历史关联。我的研究始终聚焦广义上的“美学”(aesthetics),即感性、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问题。1995年开始写作、2000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Aesthetics and Marxism(中译《马克思主义与美学》) 一书中,我试图从一个国际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思想。多年以来,这个思路始终是我学术思考的一条主线。美学、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该书讨论的内容,但主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跟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文化思想和理论。这是我研究思想史的一个角度或出发点,以中国为案例,分析了美学与现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了中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之间的关联、平行与差异。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关系。从美学这样一个专门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分析这样一个大命题,可以说是“小题大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重大的命题缩微在美学的这个学术视点, 通过对美学思想的分析来思考、考察这个大问题,也可以说是“大题小做”。
为什么要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谈话语范式?因为人文学术的话语与范式,本身就是文论研究的对象。伽达默尔对于人文学术的范式有经典论述,其名著《真理与方法》(1960)讲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溯源、文本解释、元批评等方法,来认识人文思想的范式,探索与找寻真相(真理)。文艺理论或 “文艺学”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研究对象包括了各种文艺理论模式或范式,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中国的文艺学研究主导范式是黑格尔式(泰半经由苏联改造的)抽象思辨,以论述理论概念为主,鲜有从思想史和知识谱系学的角度来研究理论的历史演变。将理论(具体到文艺理论)作为思想史来研究,是我们讨论的双重目标之一。
我们的讨论始终是在国际多元学术语境下进行的对话与合作。多年来,我的思路始终是“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在英语学术界,我重点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将之置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作比较。在中文学术界,我则一直与中国学者就西方理论保持对话,写过有关不同西方理论的中文专著与论文。从21世纪初开始,我来回穿梭于中美之间,在许多中美高校与学界同仁交流,其中,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上海大学曾军教授领衔的“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重大课题,跟我们的主题高度吻合,许多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同时也参加了我们的写作团队。从2018年起,我与中美多位学者合作,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工作坊,并在诸多中英文学术期刊上组织发表了专辑、专栏文章,探讨这一主题。我欣慰地看到,世界各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界朋友关注、参与到这个话题之中。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The China Question of Western Theory)其中的“问题”用英文表述是question,也就是提问、质疑的意思。英文与中文“问题”对应的常用词有“question”和“problem”,两词含义不同。Problem往往是跟麻烦、困难、难题等有关。“What is your problem”含有“你有啥麻烦/毛病/困难要解决”的意思,常常出现在医生与病人的对话语境中,而“What is your question”则指向提问和质疑、寻求回答和对话的语境,更多出现在教学和学术讨论的语境中。而提问和质疑,乃是知识、思想和学术探索的第一要义。所以我们的双语讨论英文选择了China Question,而中文使用了“中国问题”,比起“中国话题”“中国主题”等貌似中性的概念更加准确。我曾写道:“‘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 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反之亦然,西方理论对于其产生发源的欧美而言,是内在的。但一旦进入中国而产生变异转换,则成为相对西方的外在问题了。”[1]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一个思想史的角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61页。我同时进一步强调,“‘西方理论’涵盖了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至今三百多年的思想理论,或可称为现代性思维或理论。哈贝马斯将黑格尔视为现代性思维的枢纽人物,上接康德以来的启蒙理性主义,下连尼采、海德格尔以降的当代欧洲思想,当然包含了哈贝马斯自己所主要承继、认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一个思想史的角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第161页。
参与这一讨论的中外同仁们正在不停地拓展研究的范畴和领域。我们的讨论包括了以下几个话题(有些谈论已经完成,专辑论文陆续发表或正在发表):1.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话语体系的转换;2.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方式、方法与问题;3.中国美学话语的沿袭与拓展;4.翻译与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 5.西方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中国问题;6.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外国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的范式,等等。
道与术:国际对话的回顾
关于国际学术对话的“道”与“术”的关系,是我们的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的缘起是美国重要文学与理论期刊《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主编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与王宁在2018年联合发起编辑的专辑“中国遭遇西方理论”(China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这个专辑收录了六篇论文,分别由王宁、朱立元、张江三位中国学者撰写,并由美国文学理论家、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比利时鲁汶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主编德汉(Theo D’ Haen)和我本人作为三位国际学者,分别对三位中国学者的文章作出评论。这一期专辑正是国际学术对话的重要案例,讨论的主题就是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关系,可作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讨论的一部分。专辑的英文标题“China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把“中国”与“西方理论”作为两个意义概念不同的范畴,“中国”是一个范围很大很泛的实体,跟“西方理论”是不对等的范畴。但这种说法跟中外学术界多年流行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有没有关联?冲击—反应模式强调了西方的主动进入和影响、中国的被动接受和运用;而 “遭遇”(encounter)这个动词,似乎弱化了谁是主动谁是被动、谁是主体谁是客体的关系。“对话”(dialogue)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让我们把理论的思辨与讨论中的内在/外在、主体/客体、主动/被动等二元对立的关系,置换成更具包容和多元的对话关系。推动国际学术对话并不能仅仅凭借某个机构或组织的安排,而主要是靠学者的力量,要靠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深厚功力的学者不遗余力的努力。几十年来,王宁教授为推动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的国际学术对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在国际学术平台发表了大量英文论文和讲演,而且筹划、组织了大量的学术会议、论文专辑,让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展开卓有成效的国际学术对话。[1]近年来王宁在重要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表的论著包括:Wang Ning,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Wang Ning, “Humanities Encounters Scienc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 European Review, Vol.26, No.2 (2018),p.344-353; Wang Ning, “World drama and modern Chinese drama in its broad Context,” Neohelicon, 46(2019), p.7–20; Wang Ning, “From Shanghai Modern to Shanghai Postmodern: A Cosmopolitan View of China’ s Modernization,” Telos 180 (2017), p.87–103.
MLQ专辑就是王宁教授组织的大量学术专辑和平台之一。包括他在内的三位中国作者,讨论的主要是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影响,而三位国际学者的回应就更具自我反思和元批评的意味:中国学者讲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者则要思考西方理论本身在遭遇中国时的种种问题。三位国际学者其实是四位,专辑主编之一也是刊物的主编布朗的意见,都表达在专辑前言中。当然我在其中的身份更为复杂。布朗在前言中指出,西方学者“很少开始反思和自我反思他们的文化立场,但专辑的中国作者有力地传递了他们的意见并引发了西方作者的回应”[2]Wang Ning and Marshall Brown, “Introduction,”Special Issue of China Encounters with Western Theories,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9, No.3(2018), p.246.。对于三位“西方作者”中的一员,前言也提到我的身份:“刘康在中国出生,在上海交大担任重要职务,但自从1982年(有误,应该是1983年)来到威斯康星大学读博士之后,一直以美国为基地。”[3]同上。这个说法甚为含糊,跟前面把我归类为“西方作者”的说法显然前后矛盾。在当今这个认同或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时代,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实际上我在专辑里的文章对于我的身份问题有所讨论。身份政治是今天欧美(尤其是美国)知识界的焦点话题,也是当代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无法回避,但需要从中国的语境出发来思考。就我们关于中西方文艺理论的学术讨论这个具体的语境而言,所谓认同/身份(identity), 当然包括了参与者的种族肤色等生物标志以及出生地和工作地等社会标志,但这种标志在今天这个多元多样化的世界,并非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是多重多元的。就我个人而言,思想、学术的认同和身份就是多重多元的。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这是我的思想和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根本的认同与身份。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有利于学术对话的。
MLQ的讨论后来在中文平台上继续展开。《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发表了王宁的论文《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我的论文《中国遭遇西方理论:一个元批评角度的思考》,就MLQ英文专辑的讨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辨析。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国际学术对话的“道与术”的问题,并以我在MLQ专辑上的英文论文所聚焦的詹姆逊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作为不同平台学术对话的案例继续解读。我认为国际学术对话的“道与术”的问题至关重要:“专辑的文章显示出英文(国际通用语言)语境与中文语境的异同。这些论文规范、话语形式,透露出中西不同学术传统与范式的差别。这里反映的既是术的问题(传播方式与习惯),也是道的问题(思维定式或范式)。术反映的是道,元批评须兼顾术与道的两面。”“在中西理论对话中,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倾向?以专辑为例,我认为对话中流露出的“影响的焦虑”挥之不去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遭遇西方理论(或我所说的“西方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历程中较为突出的现象。”[1]刘康:《中国遭遇西方理论:一个元批评角度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98页。除了道与术的问题外,我还提出了“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存在于中国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或遭遇中,其实在交流对话中也依然存在,MLQ专辑就是一个例证,“焦虑”显然是情绪、情感、态度方面的表现,道与术问题则更强调的是学术研究、对话与交流中的理性原则、学术规范等。但理性和感性因素的交织纠结,在人文研究中其实是题内之意。在社会科学领域也同样如此,只是社会科学更倾向以科学理性为指导原则和研究范式,强调客观与理性,对于主观性明显的情绪、情感等因素,往往刻意在研究中予以贬低和遮蔽。
MLQ专辑的三篇中国学者的文章受到三位欧美学者加上我共四位回应者主要关注的,在我看来并非仅仅是西方理论的中国解读接受中呈现的各种问题,更包括了学术研究的思路、方法、范式,也即“道与术”的问题。美国学者米勒、欧洲学者德汉对学术话题(文学研究、文学理论)非常热情,尤其专注学术规范。他们的回应文章虽篇幅有限,但都反复强调细节和证据,列举大量文本的证据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米勒在他短短的回应中对朱立元的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与朱立元展开了热烈的辩论商榷,是因为朱立元和米勒的文章,都是重细节、重证据,在学术规范上相通。德汉的每个观点,也都列举了详细论据,细致入微,不厌其烦。我的回应文章主要分析詹姆逊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转换的个案,举例甚多。没有大量的具体例证,没有对例证的精微分析,就无法提出任何一个观点。毫无疑问,学术论文的灵魂是明确无误的思想观点,而不是材料或论据的堆砌。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论据中建立严谨的逻辑关联,来论述支撑思想观点,就涉及到学术论文的基本规范、话语表述形式等。传播方式与习惯即是术,也是道,也即思维定式或范式,涉及价值观。术与道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归根结底,“术”后面蕴含的“道”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道”的问题不仅仅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跟思想、知识和学术的目的、方向密切相关的大话题。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中,就“道”的问题做了许多阐述。兹体事大,这里我还是要重提一下。2017年底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我有幸参加,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提出:“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1]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习近平总书记用了两个段落来表达“远离恐惧、远离贫困”的理念。现场来自世界各国政党的代表们对于这个理念心领神会,立刻联想起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人类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著名理念。这些著名的理念不仅仅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理念,还成为后来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石,被写进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之后在一篇特稿文章中强调,“今天习近平在向全世界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中国全球战略和世界蓝图的时候,重申远离恐惧、远离贫困的理念,这一世纪回眸,是对人类共同价值观基础的高度认可。”[2]刘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全球文化战略》,《国际传播》2018年第1期,第3页。我们要讲的“道”,就是要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高度,来思考和论述如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这不仅仅是从宏观的国际战略的层面来理解“道”,也是从国际传播的“术”的层面来理解。就文学理论的国际对话与交流而论,我们也应该循此道来思考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的问题,与世界知识界、学术界对话。
理论与现实的对话:走出影响的焦虑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国际对话的目的和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想和愿景的完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也要有现实主义的理性。我们讨论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就包括了情感和理性、抽象理论与复杂现实的多元融汇和互动。近年来参与这个话题的学术讨论,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状况中开展的。学术史乃是与大历史、思想史三种维度的互动中的一维,我们对于学术研究中的种种动向和趋势,也要有三维互动的清醒认识。我们的讨论中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西交流的不对等、不平衡——播散、传播的不对等,以及如何解读中国、理解中国的问题。这里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解释的困惑,另一个是伴随困惑而来的情绪的焦虑,或影响的焦虑。在MLQ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等多个平台上,我都重点关注了影响的焦虑问题。在本文结束时,我希望再度提出这个问题。首先是解释的困惑。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从康德、黑格尔到韦伯,都不断地思考和解释中国问题,以为启蒙的理性主义知识体系可以涵盖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然而启蒙理性主要依据的是西方的历史经验,许多方面是与中国历史、现状背道而驰的。其次是伴随着解释上的困惑,情绪上的焦虑也随之而来。近现代以来西方并不认为中国可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所以对中国的焦虑不太多。反观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对世界、对现代化的态度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情绪化。有时是忧心忡忡,有时是慷慨激昂。总而言之,往往是情绪的焦虑与理性的困惑相互交织。
而近年来,西方也充满了关于中国的焦虑情绪。现在的西方不再认为中国影响不了世界大局,反而关于中国的困惑和焦虑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对于世界也同样有理性的困惑和情绪的焦虑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蔓延,往往是大众的态度、立场的情绪化表态,受到社交媒体、数字媒体传播的重要影响。民族—民粹主义情绪涉及意识形态和情感、情绪、欲望等,是当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感性(aesthetic即中文的审美)领域的问题,理所当然是从事文艺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人们的情绪、态度、立场等在一个后真相的时代是如何被操控的,又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现实真相的判断和理解的?我们对于这些情绪、情感、态度的理性分析,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影响的焦虑、解释的困惑与焦虑的反思。这些现实问题,正是我们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要关注的重大话题。如何走出影响的焦虑?这对于我们的理论思考和国际对话来讲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