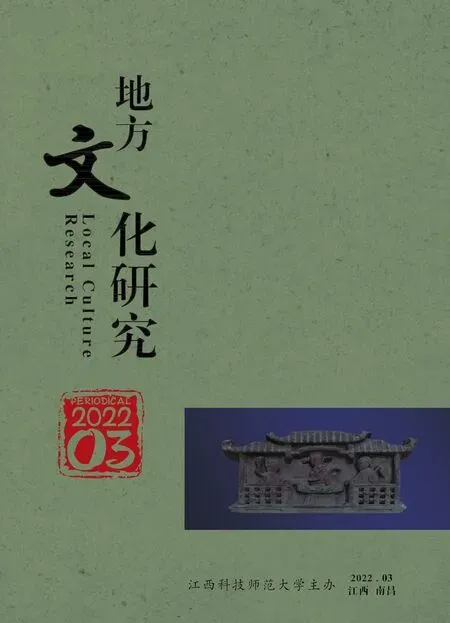清代学术嬗变中的徽州乐学
——以江永、汪绂为中心
张成儒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230039)
中华素称礼仪之邦,“华夏文明”亦被称为“礼乐文明”,自周公“制礼作乐”始,礼与乐便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此后《乐》经亡佚,关于“乐”之记载只得散见于《尚书》、三《礼》以及先秦诸子等著作,因此乐学思想的保存与发展较礼学思想更为坎坷。徽州作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是“12—18世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典范之区”①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导言》,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徽州文化博大精深兼容并包,徽州乐学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徽州学人在重视礼学研究的同时,也致力于乐学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②孙知:《以琴谱为视角论明清徽州琴人对古琴的贡献及影响》,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孙晓辉:《乾嘉音乐学术论略》,《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3期;石林昆,赵振宇:《清代乐律学家地理分布研究》,《中国音乐学》2017年第2期;袁建军:《乾嘉朴学家礼乐思想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
在清代众多徽州乐学家中,江永和汪绂(初名汪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二人乐学思想的差异,使得此时期的徽州乐学呈现出了两个发展方向,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针对江永的探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其乐律学贡献③李一俊:《江永<律吕阐微>整理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红:《江永乐律学思想初探》,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石林昆:《论江永对朱载堉乐律学思想的继承与进一步实证研究》,《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4期;黄敏学,叶键:《朴学宗师之承接——江永的音乐史学研究》,《学术界》2013年第5期;翁攀峰:《江永对新法密率的赞同及其律学思想变化过程分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针对汪绂的探究则多聚焦于乐学思想特征④黄敏学:《汪烜乐学著述及其音乐思想述评》,《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吴志武:《汪绂<乐经或问>中的诗乐谱研究——兼及<乐经律吕通解>》,《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张航晨:《清汪烜<乐经律吕通解>与<乐经或问>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针对两人的比较研究则从时代学术背景出发,揭示二人乐学思想异同的表现以及对中国礼乐思想的意义⑤袁建军:《复古与变通:清中叶礼乐诠释的两种路向——以汪烜、江永为中心》,《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江永与汪绂的乐学思想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然而目前的研究视角多以音乐学为主,研究方法侧重于个案分析,在二人乐学思想差异之复杂成因、随之产生的历史影响方面,仍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此外,通过对二者差异原因的解构,亦可为清代学术嬗变中学人们治学取向的变化情况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江永、汪绂乐学思想之异同
江永,字慎修,号慎斋,婺源江湾人,常年在家乡坐馆授徒,为塾师型学者,在清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乐学思想主要集中于《律吕阐微》《律吕新论》两部专著,其他著作亦间或涉及。汪绂,字灿人,号双池,婺源段莘人,治学方面“博览群书,博综儒经,其学以宋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张载五子为归”①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23页。,其论乐专著有《乐经律吕通解》《乐经或问》《立雪斋琴谱》三部。此二人生同时、居同乡,俱是清代大儒,并都在乐学领域成就颇多,对徽州乐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两人的乐学思想却同中有异,特点分明。
1、乐理层面的比较
“乐理”即指声音器数、发明律吕②孙晓辉:《乾嘉音乐学术论略》,《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3期。,在此方面江永和汪绂的相同之处是都意识到自身所处时代声音器数、律吕之学存在问题,并试图解决。
江永的乐律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而展开,他在二部乐学专著的序言部分将所处时代的乐理弊端进行总结,针对这些弊端开启了自身的乐学研究,其中便指出了“三分损益法”存在的问题③李一俊:《江永<律吕阐微>整理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三分损益法”最早可见于《管子·地员篇》,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生律方法,江永不仅指出了其问题的具体表现,还溯其源流认为“三分损益说”即朱熹误解了《国语》中“纪之以三”的意思,“管子盖春秋战国间人,撰自此以前未有三分损益之说,唯《国语》伶州鸠之言有‘纪之以三’一语,朱子疑其谓三分损益,然韦昭解此以三为天、地、人,则亦未必其果如朱子之说也”④(清)江永:《律吕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4页。。由此从根本上推翻了此法的合理性,同时也开启了对新生律方法的探究。
汪绂在声音器数、律吕之学方面亦用力颇深。汪绂所处年代,宋明理学已兴盛数百年之久,社会上弥漫着知识分子重谈义理而轻践行的风气,呈现出士大夫只知空谈理论而不懂器数与律吕,伶人只知乐器演奏却不通乐中义理的尴尬局面,目睹了此种情形的汪绂发出了“无闻学士高谈乐理而不娴器数声容,不娴器数声容则虚而鲜据,而理亦未必其尽安。伶人役于声音而不通乎义理,不通乎义理则流而忘本,而声乃日逐于淫荡……中正和淡之实已亡矣”⑤(清)汪绂:《理学逢源》,《汪双池先生丛书》第31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451-452页。的哀叹。汪绂为改变现状,在对《乐记》和蔡元定《律吕新书》进行注解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乐学观点,并辑纂《立雪斋琴谱》二卷以示践行,琴谱收录了其改编后的九首传统古谱和七首自制新谱,充分展现了扎实的音乐实践能力。
二人乐理层面的相异之处是江永运用数理计算推动中国古代乐律学的发展,而汪绂更偏向于维护古代圣贤旧说,保留了过多传统守旧的底色。
江永在论证了“三分损益法”的问题后,面对黄钟音无法还原的现实提出了“今律”理论,采取均匀截取管长的方法来实现“旋相为宫”的目的。“黄钟半律之容分,既当一岁之日,则其生大吕以下十一律也。亦以四寸有半均匀截之,以应月之中气。每律截去三分七厘五毫,其中容分三十分有奇”⑥(清)江永:《律吕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0页。,江永认为黄钟正律的长度为九寸,黄钟半律则应为四寸五分,每次截取部分为三分七厘五毫,按此等差方法便可避免“三分损益法”带来的问题,从而使得黄钟顺利还原。但“今律”亦存在一定问题,按此方法虽可确保各音对应正确的数值,但实际音程却比较混乱,只能实现形式上的“返宫”⑦翁攀峰:《江永对新法密率的赞同及其律学思想变化过程分析》,《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因此江永晚年开始转向信服更为科学的“新法密率”,并依据数理知识通过补充方圆相函列律图、补求夹角、水银代黍量律、求圆周率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此律法,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乐律学的发展。
汪绂在具体生律方法的认识上与江永有较大差异,他认为律吕之学本身并无深奥之处,至今几乎成为绝传之学,完全是由于士大夫高谈阔论,伶人又只知演奏而不通义理造成的。基于“非律吕之别有精微、别有法度也”①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86页。的观点,其依然钻研乐律旧说,对于朱熹和蔡元定的律学思想大多选择继承,关于落后的“候气飞灰”说依然执着坚持,“顾候气灰飞又有未能即据者,四方之气候有迟早,地势之高下有寒燠,王者之修德以召天和者有顺逆,假如冬而震电、夏而冰雹,则灰飞岂必应律”②(清)汪绂:《双池文集》,《汪双池先生丛书》第40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255页。,并认为江永论证律制的行为是轻议古人③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88页。,如此用王者修德来验证律音的方法,使其乐学思想沾染上了守旧与神秘主义色彩。
2、乐本层面的比较
“乐本”即指博通礼乐经学④孙晓辉:《乾嘉音乐学术论略》,《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3期。,中国古代将礼乐教化作用于国家治理和个人修养过程中,儒家尤其注重此功效,《荀子·乐论》载:“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⑤(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381页。梁漱溟先生指出:“儒家极重礼乐仪文,盖谓其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必情感敦厚深醇,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后人生意味绵永乃自然稳定。”⑥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7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由此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谈礼乐则必谈乐本。
在乐本方面,江永和汪绂的相同之处是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中国的乐教传统由来已久,或尤胜于礼教,刘师培指出:“古人以礼为教民之本,列于六艺之首。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⑦刘师培:《刘师培全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48页。儒家学者向来是论“礼”必谈“乐”,谈“乐”必论“礼”,礼乐对世道人心有着规范和塑造的作用,如若礼乐不彰则将产生严重危害。江永在此方面承袭了二程的观点,认为“古礼既废,人伦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有歌咏以养其性情,声音以养其耳目,舞蹈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⑧(清)江永:《近思录集注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472页。如此强调乐教和个人成材的联系性,无疑是对乐教具有明道济世作用的重要肯定。
关于重教化,汪绂继承了周敦颐的观点,亦认为“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⑨(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25页。,音乐从视、听、貌、言多方面对人进行塑造,于个人修养具有重要作用,圣人制乐的目的是为促使社会达到政善民安的状态,但时至今日圣人所作之“雅乐”逐渐流失反而“淫乐”当道,使得“贼君弃父”“轻生败伦”的事情屡禁不止。基于乐重教化的理念,汪绂力求改变现状促使“雅乐”回归,并希望能以此恢复政通人和的理想状态,但如何才能使具有教化作用的圣人雅乐恢复呢?对此,汪绂将其归因于人的情欲没有得到节制,并继承和发展了周敦颐的观点,认为“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燥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⑩(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22页。,简言之,则是追求乐的“淡和”性,以“淡”抚平“欲心”,以“和”消释“燥心”,如此一来雅乐便得以回归,政善民安的状态即可达到。
在乐本方面二人的相异之处是江永偏向于包容变通而汪绂偏向于保守极端。事物总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随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有新的乐曲和乐器被创作发明出来,当新乐与古乐相混杂时,学者们则需要面临判断与取舍。在此问题上江永秉持了包容变通的态度看待音乐的发展,其态度具体表现为三方面主张:乐曲方面主张“声音自有流变”,认为不察觉音乐的变化而高言复古的行为是不知时、不识势的表现;乐器方面主张“乐器不必泥古”,通过具体事例论证了演奏中只需选择适宜的乐器,不可一味泥古;雅俗方面主张“俗乐可求雅乐”,从谱、律、声三方面考察俗乐与雅乐之间的共同点,指出多数士大夫用异样眼光看待俗乐并鄙夷伶工不屑与之交流,仅囿于在自己领域空谈理论的通病①(清)江永:《礼书纲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1页。。
与此相反,汪绂面对音乐的发展这一事实表现出的态度更多是保守与极端。具体来看,在对待与雅乐并存的大量民间音乐时,他指出“昆腔妖淫愁怨,弋腔粗暴鄙野,秦腔猛起奋末,杀伐尤甚,至于小曲歌谣则淫亵不足言矣”②(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24-325页。,将中国地方民间曲乐中的优秀代表以及由广大民众长期口口相传的小曲歌谣全部加以贬斥,并进一步主张“凡天下之习俳优者宜尽禁止之,取杂剧之书而悉焚之”③(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35页。。汪绂以上对民间俗乐秉持的看法以及欲将其铲除殆尽仅留宫廷雅乐的主张,直观地体现了其乐本思想中保守极端的特征。
二、江永、汪绂乐学思想差异之原因
江永与汪绂生同时、居同乡,皆著作等身,俱可称为一代大儒,彼此间亦有过数次书信往来,二人之间的相同点不可谓不多,但在乐学思想方面出现的差异亦不可谓不大,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又在何处?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多注意到了学术风向改变对二人乐学思想的影响④张航晨:《清汪烜<乐经律吕通解>与<乐经或问>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袁建军:《复古与变通:清中叶礼乐诠释的两种路向——以汪烜、江永为中心》,《音乐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第94-104页。,这无疑是正确的探索方向,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到两点问题,其一是当时的学术环境是清代朴学之法正在发展,宋明理学之风尚有余存,此时期经学虽已有掩理学而上之势,但依然处在转变期,其变化过程是微妙、剧烈且动态的,且最终定式仍未形成⑤林存阳:《汪绂与江永之书信往还》,《徽学》第六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因此,对二人治乐取向的考察不能仅以理学或朴学的概念进行简单划分,更需要把握住此过程中二人学术偏向性的具体情况。其二是学术风向的影响只是部分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二人乐学思想差异的原因,在注意外部学术大环境的同时,也需着眼于二人各自生活与学术发展的历程。基于此,笔者试从学术思想形成环境、对西学的运用以及治学路径三个方面对其差异原因作进一步探究。
1、学术思想的形成环境不同
江永与汪绂虽生同时,居同乡,同为塾师型学者,但其生活环境却有较大差异,尤其在学术成长环境方面则更为不同,此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江永乐学思想偏向于包容变通而汪绂偏向于保守极端。
江永和汪绂虽都为塾师型学者,但江永在家乡坐馆授徒,而汪绂迫于生计选择前往浙江枫溪坐馆。由于江永常年在家乡进行学术活动,其名声渐起,于乾隆四年(1739)被时任徽州知府杨云服敦请校刻《朱子经济文衡》,并于此时结识了共同参与此事的三礼馆编修程恂。借此机缘,江永于翌年转至程恂处任塾师,此后程恂不但同江永探讨学术,还为其扩大学术交往圈。乾隆五年(1740)江永跟随程恂至京师访学三礼馆,同方苞、吴绂、梅瑴成等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据载“三礼馆总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负其学,及闻先生,愿得见,见则以所疑士冠礼、士昏礼中数事为问,先生从容置答”⑥(清)戴震:《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页。,同时,与其他学者就相关问题也进行了交流。此次江永入京,得以同当时一流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在此后依然与之保持联系,这意味着江永的学术思想不再局限于乡野塾师的层面,而是已经接触并融入到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圈,此后虽长期身处徽州,也不妨碍其感知到全国学术风潮的发展情况。
相较之下,汪绂为保障生计不得不长期坐馆于浙江枫溪,由于常年离家,使得汪绂在家乡影响力较弱,如此状态下无法获得江永这般机遇。从汪绂年谱记载中看,其日常形象是“与族众不习”“寡言笑”,交往对象多是亲属与学生,由此推测汪绂的社交能力应当不强,社交范围相对狭小。汪绂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探讨也多限于此范围,从年谱记载的学术交流、往来书信看,除江永外,金斗望和余元遴是门人,洪腾蛟为私淑,梅庵系亲属,再结合其“终生未尝一日从师”的情况,可知汪绂的学术思想形成环境是较为闭塞的,其学术成就多源于发掘古书和自身思考,外部交流与学习的机会极少,一定程度上视之,汪绂是处于当时主流文化圈之外的学者。
基于以上情况综观之,江永因其家庭环境尚可,得以留在家乡授徒治学名声渐起,进而结识名流,获得接触并融入主流文化圈的机会,自身学术思想在学习、思考与交流商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因此其乐学思想具有包容变通的特征。相比之下汪绂的家庭环境较为糟糕,不得不常年外出谋生,学术研究方面主要依靠自学,自身性格加之外部环境使其周边并无多少知名学士,较难从交流与探讨中获得提升,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形成的乐学思想容易偏向于保守极端。
2、对西学的运用不同
江永在乐学研究中借用西方算学知识求取律值,而汪绂则依然坚持传统旧说测算音律,这直接导致在乐律研究方面,江永比汪绂更为科学和准确。
江永治学兴趣广泛,西学亦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入京访学三礼馆期间又得以同梅瑴成交流,因此西学功底较为扎实,《翼梅》为其代表作。江永晚年的乐学研究主要是对朱载堉“新法密率”进行补充与发展,其中多处运用到西学。譬如,为求出更加精确的圆周率,江永借鉴西学方法进行计算,“西人分周天为三百六十度,一度又析为六十分,是分大圆为二万一千六百边也。八线各有相当,正弦与余割相乘,与半径全数自乘等积。查表一分之余割线,三四三七七四六八二,因此求得一分之正弦。二九〇八八八二〇四五〇一,以二万一千六百折半,为一万〇八百乘之,得三一四一五九二六〇八六一八。正弦是直线,圆周是曲线,几与之等。而曲者必稍赢,是以比圆周稍朒焉。故径一则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最密之率,宜用之”①(清)江永:《律吕阐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6页。。按其方法江永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5,同时这也是当时中国人能计算出的最精确的圆周率。此外,在测量律值时,江永也采用了西法,“先量黄钟正律,查立成图,黄钟正律实积九万八千一百七十四毫七七,用西人三率法算之,斗容一千二百为一率。一斗水银重若干毫为二率,黄钟九万八千一百七十四七七为三率。二率与三率相乘为实,一率一千二百为法除之,求得四率,为黄钟正律容水银之重。”②(清)江永:《律吕阐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2页。通过以上过程便可以测得黄钟的数值,其他各音也可按此法进行测算。
汪绂在探求音律时并没有运用到西方算学知识,而是依然坚持“候气飞灰”法,其具体操作过程是设置一个三重密闭的房间,在最内间布置上缇缦,用十二个木案对应十二音律,按照内底外高围成圆形,将十二个木案的首端涂上葭灰并覆盖上缇素,之后便静待气来灰去即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有“如气至,则吹灰动素,小动为和气,大动为君弱臣强专政之应,不动为君严猛之应其升降之数,在冬至则黄钟九寸”③(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11页。。除黄钟外,其他各音也有相对应的节气与律长。汪绂通过此种依据节气变化阳气上升的方法测算出了各音,并将其部分现象比附于君臣关系,此外还用阴阳关系强行解释了“三分损益法”出现问题的合理性。以上行为可以看出汪绂对音律的研究并未采取科学的方法与求实的态度,而是主要依靠无逻辑关系的主观推导而得来。二者相较,江永在乐律研究中运用西方算法而汪绂采取“候气飞灰”,此基础方法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二人乐学思想的差异。
3、治学路径的不同
江永为皖派朴学的开山,治学路径是由“道问学”而达“尊德性”,运用考据探析义理;汪绂为朱子学之余绪,治学途径是“尊德性”重于“道问学”,义理阐发压过实际考据。
江永的乐学思想并非一朝便成,而是有着长时段的完善过程,此过程中显著体现了江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考据学精神。对于流传已久的“三分损益法”,江永不因其是上古流传、圣人论述就奉若真理,反将其与节气、琴徽、日岁相互印证,得出此法为近似之法存在问题的认识,“古人见其数之近似也,遂立为成法,不知小有不合,则法已非真”①(清)江永:《律吕新论》,《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2页。。这种面对圣人观点能存疑证伪的做法,直观地体现了江永“不以人蔽己”的考据精神。江永乐学的探索过程中对“新法密率”的态度曾发生过重大转变,其早年由于对此法了解未深,在著作中曾持反对态度,直至晚年在研读朱载堉《乐律全书》后,其态度始发生改变,从“犹是旧法,如朝四暮三实无异也”转而变成“夫理数之真,隐伏千数百年,至世子乃思得之”②(清)江永:《律吕阐微·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未载此序,转引自李一俊:《江永<律吕阐微>整理与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在此转变过程中,江永并未因自己此前错误的论断以及朱载堉的“新法密率”比自己提出的理论更高明便对之抱有否定态度,反而表现出了极大地赞赏之情,这无疑是践行了“不以己自蔽”的考据精神。
江永为学治乐并不局限于“道问学”,考据手段的运用是为了达到探析义理的目的,但部分世人对此却多有误解,对此方面余龙光做过相应评价,“大约江先生崇尚汉学,沉潜精密参互理数,融会沿革。论者推为郑康成后一人,非过誉也。至其学及身而显,世每谓彼时士大夫竞尚考据,又得其高第弟子戴庶常震东原,揄扬师说,以故海内家有其书……其揄扬江先生者,不过举其偏以标一时之名,而其背畔江先生者,早已忘其全而没一生之实”③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凡例》,《双池先生年谱》,光绪九年刻本,第2-4页,天津图书馆藏。。由此视之,余龙光认为江永治学的本心是探求义理,只是由于后世崇尚考据的学术风气兴起,再加上弟子的推崇,渐渐地掩盖住了江永为学的本心。
关于汪绂的治学路径,后世学者对此已多有总结,徐世昌认为“双池居贫守约,力任斯道之传。其为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不废考据,而要以义理为折衷,恪守朱子家法”④徐世昌:《双池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40页。,徐氏意为汪绂虽进行考据但本质上更偏重于义理。对此,钱穆则更为直白,指出汪绂是“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而所治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则门路与江氏相似”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34页。。具体到乐学思想方面,汪绂主要表现为偏重承袭宋儒理论,对《乐记》、二程和朱熹部分观点进一步肯定,极度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著作中不乏有对“理”“欲”的表述,并将《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⑥(清)汪绂:《乐经律吕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42-43页。进行延伸与拓展。当然其乐学思想虽重义理阐发但也进行知识考据,《乐经律吕通解》的自叙部分载:“器数声音又不容以不考也。因是合《乐记》及西山书,疏通其意,复上采《周礼》《考工》,下及儒先注疏,以考其器数声容之略”⑦(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5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2页。,由此得见汪绂对器数声音的研究是基于对古代典籍和先儒注疏内容的考察而进一步得出。究其内容,第一卷对《乐记》原文进行了字音、音调、生僻词意的详细考证和注释,第四卷的“八音考度”,考证了八音乐器的源流、形制、演奏方法,整体特色是近则采文献,远则征故实,推本溯源,锱铢必较,其扎实的考据功底显露无疑。
综观之,汪绂为学治乐中表现出的特征确是义理阐发压过实际考据,并且义理阐发多在宋儒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因此造成传承重于创新的现象,也同时导致了其乐学研究中保留了不少如“候气飞灰”“禁绝俗乐”等传统守旧思想,限制了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影响力。
三、江永、汪绂乐学思想之影响
江永与汪绂的学术思想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考察二人学术影响时,不能以理学与朴学的分界而轻易判定二人学术思想孰优孰劣,至于江永身后多弟子,汪绂离世少传人的原因,钱穆将其归因于时代风向所导致,“有清一代尚实之风,群流所趋,莫能独外耳”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35页。。在此基础上余英时教授作了进一步阐述,采用“内在理路说”视角将宋明理学转至清代朴学看作是继承与发展,是学术演进的内在要求在清代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并不是后者全然反对前者②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因此在探析江永和汪绂乐学成就影响时,应秉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既要结合全国学术风潮嬗变的背景,又要坚持以二人乐学思想内容为中心进行探究。
江永的乐学思想是在全国学术风向由理学转向朴学的背景下,西学在国内传播的过程中形成的,其成就与研究方法对传统礼乐思想及后辈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江永的乐学研究善用西学,注重考据,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了等差思想、等比思想、函数思想等数理知识,以数字的精确性确保了音律的准确性。此外“俗乐可求雅乐”和“学士大夫不能胜工师”的观点,一改前人对俗乐与伶人的贬斥,主张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对待,一定程度上将雅乐与俗乐、士大夫与伶人等同视之,言辞中透露出音乐不应存“理”灭“情”的倾向,提出此后音乐发展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士大夫与伶人相互交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乐学研究,“乐必与工师谋,犹之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非可以虚理胜也”③(清)江永:《律吕阐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5页。。对于士大夫阶层空谈声律义理,完全凭借主观意愿来发挥想象的情况则力主摒除。
江永通过西学数理知识和严谨的考据学方法对此前的谬误进行纠正,推动了我国古代的乐律学研究的进程,其乐学思想具有包容与求实的特征,为处在传统王朝高压统治状态下的礼乐思想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更为重要的是对后辈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成就较大者甚多,譬如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等。以戴震为例,戴震在礼乐研究中,继承了江永考据的方法与求实的态度,进一步肯定民间俗乐,为“郑卫之音”做出辩解,认为“郑卫之音,非郑诗、卫诗;桑间濮上之音,非桑中一诗,其义甚明。南、豳、雅、颂,用之于乐,然而乐章也,非乐也。乐者,笙、籥、琴、瑟、钟、鼓之属也。是故雅诗非雅乐也。器之所奏者乐也,音声也。乐与音则又有辨矣”④(清)戴震撰,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1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36页。。戴震摆脱雅乐的局限性,转从广大的市民阶级的角度为俗乐正名,强调“情”“欲”“知”都根植于人的本性,是自然合理的存在,现实情况中“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⑤(清)戴震:《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情和理无法对立看待。依照戴震的探索方向,“情”的合理性一旦被发掘出来,民间俗乐存在的合理性便有了稳固的基础,新的礼乐思想一旦可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情感需要、能够规范引导广大民众的行为习惯,礼乐思想发展的合理道路即被找到,而在此条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江永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绂的乐学思想是儒家传统礼乐在清代高压统治环境下的进一步发展,其对中国传统礼乐发展的影响可分为消极与积极两部分看待。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于对待民间俗乐的问题上,汪绂认为,昆曲、弋腔、秦腔充斥着妖淫、粗鄙、杀伐之气,歌谣小曲亦是淫亵不堪,梨园杂剧动辄伤风败俗、费财生祸,这些音乐与雅乐相斥仅会产生扰乱作用而已,进而主张完全崇雅禁俗,不允许民间学习乐舞谐戏,杂剧书本全部予以焚毁,将懂音律的俗乐从事者收归为宫廷服务并仅允许演奏雅乐⑥(清)汪绂:《乐经吕律通解》,《汪双池先生丛书》第2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335页。。在对待音乐发展问题的态度上,汪绂比朱熹更加保守,朱熹尚且认为古礼、古乐与当下现实情况已有脱离,合理做法应当是对现行礼乐进行完善,使其不违义理能涵养人内心即可,“夫三王制礼,因革不同,皆合乎风气之宜,而不违乎义理之正。正使圣人复起,其于今日之议,亦必有所处矣。”⑦(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25-1326页。对于俗乐,朱熹亦用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在与学生的交谈中,胡泳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朱熹答:“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⑧(宋)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94页。由此可见,汪绂虽是以朱子为依归,但其部分礼乐主张较朱子更加保守和极端。
汪绂乐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礼乐发展的积极影响为虽重守旧但也有创新,在诗乐谱方面,既延续一字一音的传统,也加入变律以助歌余,各章处理上也与其他谱有所区别①吴志武:《汪绂<乐经或问>中的诗乐谱研究——兼及<乐经律吕通解>》,《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在乐观方面,将周敦颐“淡和”乐观加以发展,认为“淡”应在“和”之上,乐音只有具备“淡”的属性才能达到“和”的效果②张航晨:《清汪烜<乐经律吕通解>与<乐经或问>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西安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袁建军:《汪烜礼乐思想特点及意义》,《音乐研究》2017年第4期。。并在此理念的指导下辑纂了《立雪斋琴谱》,在小引中明确表示,如不符淡和思想则不予辑录,“其间篇什酌以淡和,或怡然自适,或凄以哀思,或远杳清冥,或和平广大,而要必以祗以庸,约乎中正。如或音调靡漫凶过,稍乖和淡者,皆置不录”③(清)汪绂:《立雪斋琴谱》,《汪双池先生丛书》第46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8页。。因此综合来看,汪绂的礼乐思想是在传统王朝中央集权发展到顶峰之时,泰西之学已在中国传播的背景之下形成,其治乐道路是依然沿着传统礼乐的方向继续发展,重视教化作用,强调纲常伦理,比此前宋儒更为保守复古,阐发角度更倾向于统治阶级,是传统儒家礼乐思想在清代中央集权到达顶峰状态下的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统王朝时代儒家传统礼乐思想发展的最终阶段,与此同时其乐学思想中包含着的保守、复古、脱离现实生活等因素,也预示着传统礼乐思想即将面临的困境。
四、结 语
通过对江永与汪绂二人乐学思想异同的表现、差异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直观地呈现出了清代徽州乐学的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在时代背景发生转变的情况下选择与时俱进同最新的学术思想结合进而延伸出新的发展方向;另一条是坚持旧有的发展路径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与阐述。二条发展路径的方向虽有不同,但江、汪二人的乐学思想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中都表现出了重要的时代价值,同时对其差异的探究也为观察中国传统学术风向由宋明理学向清代朴学转变时学人们治学取向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