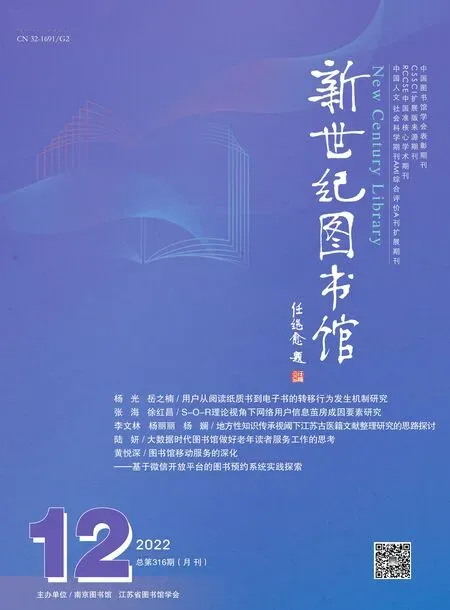图书馆学大家是怎样炼成的*
——从《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谈起
刘时容
收到快递“图情好书《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1]时,让人眼前一亮,沉甸甸的精装本,疏朗的文字排版,正是我所喜欢的装帧款式;翻开目录,“青少年时代、文华时光、执教大学、难忘的留苏岁月、学成归来、那些日子、科教春天、砥砺前行的八年、六秩之后”九个章标题将一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的成长奋斗史即刻呈现,探索欲瞬间爆棚。经过一番酣畅淋漓的阅读,更是点燃了笔者的言说激情——原来图书馆学大家就是这样炼成的。
1 “读书至上”乃家风使然
通常认为,家风是指一种由父母或祖辈提供并能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2],因其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功能和一定的规束作用而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在普罗大众间广泛流传。然而,知与行总是存在一定的距离,知行合一并持之以恒者乃是少数。湖南省汩罗市弼时镇樟树桥村的彭氏家族便属于这少数之列,彭斐章先生(以下简称“彭老”)便是彭氏家风“读书至上”的集大成者。
1.1 饱读诗书的伯祖父厚爱有加
彭老出生于1930年,自小受到伯祖父彭伯樵的疼爱,有三事为证:第一,亲自取名。给孩子取名是一门颇有难度的学问,取的名字既要响亮好听,又要意蕴深远,因而是一个费心、费脑的活,非至爱亲友者一般不会为之。彭老是家族同辈男孩中最大者,伯樵老人十分看重,遂亲自从《论语》中寻找灵感,给侄孙取名“斐章”,寓意“斐然成章,入圣之门”,希望他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第二,形影不离。“伯祖父对他家自己的孙女、孙子基本不怎么管,但是我记得,他无论走到哪里,总喜欢带我一起。”[1]5耄耋之年,彭老回忆与伯祖父的相处时光时,依然清晰记得儿时与伯樵老人出行“折腾”伯祖父半路回家取鞋一幕,足见祖孙情深。第三,润物无声。伯樵老人舞文弄墨时,总是不忘把侄孙叫到身边,让他牵对联、研翰墨。正是在与伯祖父的朝夕相处中,彭老受到家风熏陶,在教育尚不发达的年代,五岁半便进入了彭氏好古小学幼稚班读书。家族对其培养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2 乐善明理的父母言传身教
彭老的父亲彭育奇先生,乐善好施,为人正直,平易近人;母亲任淑身女士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妇女,他们共同养育了六个孩子,长大后有四个从事教育。成就这样一个教育世家,显然与父母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人们也可以从高家坊村老年协会自发撰写的《彭育奇先生生平简介》中窥见一二。彭老父母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却都读过书、识得字,对子女教育既严格又开明,尤其崇尚读书至上,这其中就体现在对彭老的教育上,“小时候我基本没做过农活,主要是读书学习。父亲对我很器重,要求也格外严格,尤其是写字,他总是对我说字是门面,你必须要努力练好。”父亲严格的教育,不仅成就了彭老一手好书法,而且在抗日战争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彭老的学业也没有荒废,从初小、高小到初中、高中,直到初出茅庐开始工作,担任小学教师、小学校长,父母依然认为“我应该继续上学,要多读书,要考大学”[1]39。如此恒力和眼光,可不是一般父母都具有的。
1.3 亦师亦友的叔父悉心教导
在彭老的求学过程中,有两位叔父对他的影响较大。一位是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彭俊明先生,中学时曾教授彭老数学、物理等理科科目,因其讲课逻辑性强、语言幽默、言简意赅、喜欢学生提问而深受学生喜欢,也直接培养了彭老对理科课程的兴趣,以至于高考录取时彭老被调剂到“图书馆学”这个文科专业后还曾一度产生“为什么不把我分到一个理科类专业”的困惑。另一位是学识渊博、古文功底深厚的彭卣簧先生,中学时曾教授彭老语文和历史,寒、暑假彭老也常到卣簧先生家学习国文,阅读“四书”“五经”等古典书籍,这为他后来从事古典目录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长大后,叔侄间多有书信往来,逢年过节、盛事喜事和诗作赋亦是常事。正是在亦师亦友的两位叔父的悉心教导下,彭老既具有严谨的理科思维,又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
2 与图书馆学结缘:从纯属偶然到爱我所选
2.1 求学文华:纯属偶然
“我怎么就学了图书馆学这个专业?是我从小就热爱这个专业?其实不然,这一切纯属偶然。”[1]43在“文华求学”一节的开篇,彭老明确告诉大家,他与图书馆学的结缘并不是他的主动选择,而是因为高考填报志愿“服从分配”导致的学校和专业调剂的结果。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的图书馆学专业从诞生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然而其招生靠调剂的尴尬局面却依然存在。在图林耕耘四十年的包头师范学院王龙先生对此深有体会,他直言不讳地说:该校图书馆学本科专业自2006年开始招生以来,始终没有摆脱第一志愿录取率最低、被迫调剂到本专业者最多、录取分数线最低、转专业率最高的窘境;“图书馆学专业”这个名称既不光鲜,也不体面,甚至还有点窝囊[3]。“相比牛气专业(如高分子材料、金融学、建筑学等)学生‘横着走路’的霸气,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毫无专业自豪感,他们走路更愿意贴着墙角慢慢挪,生怕被人问起什么专业”[4]。因此,如何扭转图书馆学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受待见的学科地位,是一个值得所有图书馆人思考的课题。也正因为如此,彭老及其弟子们始终将提高图书馆学学科地位当成自己的一种学科使命[5]。
2.2 “土改”溢出效应:思想转变
既然彭老最初与图书馆学结缘是一种无奈的被动接受,那么,他又是如何将其转化为一种主动作为的呢?在“土改经历”一节里,彭老将其归因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开展的土地改革”[1]57。土改期间,彭老负责管钱和管粮,在管钱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首饰丢失”[1]59-60事件,地方干部认为,对于那个捡到首饰就换钱的老实农民,用了的钱就算了,只要把剩下的钱交回来就行,不必深究,其体现的是一种人文情怀。彭老则从理科思维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钱物等价,把花了的钱也追回来。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处理实际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触动了彭老的内心,让他对“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有了更深的体会,从而对自己所学之专业思想开始改变。用当下的话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巩固了专业思想。事实上,这样的大局意识在许多“大家”身上不乏体现,例如,因国家需要由化工机械专业转学核动力专业的核潜艇专家彭士禄、为国选专业的科学家竺可桢(从土木工程专业转学农学专业再到气象学专业)、以国家需要为专业的科学家钱伟长(涉猎16种不同的专业领域)等。老一辈科学家们这种将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的精神,无疑值得当下一些追逐功利的年轻人学习践行。
2.3 文华精神的熏陶:爱我所选
“精神”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任何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都离不开精神的支撑。那么,什么是文华精神呢?文华图专毕业生毛坤先生将其概括为创办人精神、维持人精神、学生之精神;程焕文教授将这三个层面浓缩为“图书馆精神”,认为其内涵可用文华图专的校训“智慧与服务”进行阐释,并将其具化为“爱国、爱馆、爱书、爱人”之行为[6]。彭老是文华图专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又是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之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首批教师,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将文华精神提炼为“自强不息,团结奋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这三个方面、六个关键词。彭老曾说:“我热爱武大,热爱学院,热爱学科,爱我所选,无怨无悔”[1]257。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100周年之际,彭老捐赠100万元,设立“武汉大学彭斐章图书馆学发展基金”,以支持图书馆学系学科专业发展和师资队伍建设,可谓一爱终生。这种大爱精神,直接发源于文华图专,也与毛泽东主席寄希望于青年人的教导密不可分(彭老留学苏联时曾在莫斯科大学礼堂现场聆听毛主席教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130。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属于彭老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之歌。
3 留学深造:世界是“你们”的
3.1 从选拔考试到选择专业
所谓“厚积薄发”,是指人要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准备和积累。青年正是厚积之时,当去苏联留学的机会降临到彭老身上时,24岁的他为此做了全面细致的准备:首先,收集专业课程复习资料迎接选拔考试。“‘中文编目’很可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的刘国钧教授出题,‘参考工具’估计是王重民教授负责。于是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写信请求邮寄这两位教授的讲义。”[2]79-80正是这种对学术前沿的精准把握和有针对性的准备,让彭老在众多学子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了留学选拔考试。其次,专业选择请教名师。彭老基于自身对目录学课程的兴趣,请教了武汉大学的徐家麟先生、吕绍虞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的王重民教授。三位老师都认为,中国的古代目录学成果突出,但现代目录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而一致建议彭老去苏联学习现代目录学。这种基于兴趣和国家需要的专业选择在“留学热”的当下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再次,为语言交流做准备。听、说、读、写是学习任何一种语言都必须掌握的四项基本功。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国家专门成立了留苏预备部,就俄语口语、阅读、写作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以确保留学生出国后能够很快进入学习状态。最后,储备常识性知识。知识青年出国留学,既要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理念,又要担当起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因而有必要储备一些常识性知识。“学习苏联礼仪,了解国家的时事政策,懂得艺术鉴赏与评价,参观北京十大名建筑”[1]81,这是留苏预备部为当时的留苏学子定制的常识性知识套餐。在出国留学快速走进寻常百姓家的当下,有志留学的青年学子更有必要对留学国家政策法律、文化习俗、规章制度、教学方法、安全保护等方面的知识加深了解,同时对本国的传统美食、风景名胜、文化艺术等方面也要熟知,最好还能掌握一门才艺,自觉扮演好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角色。
3.2 读书、读人、读世界
上大学,究竟读什么?有学者用“读书、读人、读世界”来回答,可谓睿智。彭老留学苏联所读的也可以用“书、人、世界”来概括。先说读书吧。政治理论、哲学课,教育、心理、历史、外语等文化教育课,图书馆学和目录学专业课是彭老留学时上的三类课程,课程学习的主要方法是自学,老师出列书单。图书馆作为书籍的藏身之所,自然成了读书的主阵地。“我们每个研究生在那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位置,座位上有一盏台灯,桌子下面有抽屉,我们的书等都放在里面。”[1]108这是莫斯科图书馆学院科学图书馆为每一位研究生提供的贴心服务。可是,这样的贴心服务在国内一些过分强调“平等服务”的图书馆却被贴上了“区别服务”的标签,其实大可不必。读者群体在知识结构上是有层次区分的,因此读者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图书馆在确保基础性服务“公正、平等”的同时,应该为知识精英提供这种有如“特权”般的贴心服务,因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大与知识精英的贡献和推动高度相关。列宁图书馆有如“住馆读书”式的新书展览、图书借阅、休闲餐饮以及“每3栋住宅楼设立一个图书点为民众提供照看孩子、指导阅读学习”的苏联服务模式,即使是在当下的全民阅读环境中仍然具有生命力。就读人而言,“导师”应该是每一位研究生都需要仔细阅读的人物。彭老从其导师苏联著名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教授身上读到了“严”“导”“爱”三个关键词,诸如师生一起拟定学习计划、定期汇报学习情况和研究进展、共同确定毕业论文选题、为学生调研提供方便、并肩散步了解学生生活、安排博士答辩、去车站为学生送行等,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如此极品导师,不仅让学生铭记终生,还会实化为行动向下传承并发扬光大。对于留学生来说,参加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更是品读异域世界的一条捷径。为此,彭老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文化休闲活动,还踊跃报名大使馆和莫斯科共青团委组织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通过活动,既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吸收精彩异域文化,自觉充当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
3.3 “大家”初成
四年严格规范的研究生训练后,获得教育学副博士学位的彭老回到祖国,重回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目录学教研室主任,开始学以致用。科研方面,彭老接受领导安排,全面调查武汉大学图书馆的情况,撰写调查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许多建议上升为规章制度被师生遵照执行。教学方面,彭老担任目录学、苏联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图书馆目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并和同事一起代表武汉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目录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同时参与高考招生,尝试开放办学,去全国各地函授站进行现场授课和辅导,展现出了“大家”初成的魄力和胸怀。
4 执教大学:世界是“我们”的
4.1 教书育人:甘为后人梯
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科教的春天,也开启了彭老教书育人的新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培养本科生。在无教材可用的高考恢复之初,彭老给定参考资料指导学生阅读,后又组织编写教材努力让本科教学步入正轨。他还鼓励优秀学子出国留学,关注毕业学生的社会发展。学生发表的文章他会剪辑收藏;出差会去看望学生,为学生纾解困难,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学子们心中,珞珈山岩高千丈,也难及恩师待己情。第二,招收硕士研究生。彭老是武汉大学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从1978年的第一届到2006年的最后一届,共计有35人师从彭老获得硕士学位毕业,他们的姓名、研究方向、硕士论文题目、入校和毕业时间,彭老都一一记录在案。不仅对全日制研究生了如指掌,非全日制研究生班的学生在彭老心中也同样有位。他继承自己苏联导师“严”“导”“爱”的教育风格,指导学生查找资料、撰写文章并推荐发表,且从不以导师自居,习惯从学生角度考虑问题,从而收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带出来的学生个个德才兼备。学生们编辑出版的《春华秋实——贺彭斐章先生执教56周年暨80华诞》纪念文集便是对彭老的赞美。第三,指导博士研究生。彭老从1991年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现代目录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一共带了18届,总共30人。“做人要谦虚,治学要严谨”是彭老对博士生们的纲领要求。他不仅严于律生,也严于律己,和学生一起制订培养计划,一起开展科学研究,鼓励他们树立高远目标,勇于创新,走到世界本学科的前沿。人们可以从30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和18名国内外访问学者的信息清单中窥见彭老教书育人的用心和细心[1]263-266。
正如彭老所言:“作为一名老师,只有甘为人梯和引桥,才能让后来者走得更顺畅”。学生们也不负师望,倪晓建、柯平、陈传夫、肖希明、郑建明、王新才、司莉等一大批弟子,个个都成长为图情界的翘楚,挑起了当下图情事业的大梁。“平生最觉开心处,喜看桃李结满枝。当听到学生取得成绩、获得奖励、晋升职称的时候,我最开心,最感光荣和骄傲。”正所谓“学生是老师的理想”,彭老这番肺腑之言,天下所有为师者都是如此吧,也应该如此。
4.2 学术研究:开创新高地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高校教师应该以学术为业,“学术人要满怀热情地欲求对人类知识作出原创而持久的贡献”,并通过严格的专业化,使学术人在学术研究的世界里“获得那种确实感到达成某种真正完美成果的意识”,从而成就并持续这样的学术热情[7]。彭老既具有这样的学术热情,又通过了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从而让他在学术研究领域开创出了新高地。如彭老为促进学科发展,开展学术交流,推动成立湖北省图书馆学会和中国图书馆学会。从古至今,目录学都是人们读书治学的一个门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彭老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一身都致力于目录学研究,所参编的《目录学概论》 (1982版)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先后印刷七次,发行十余万册,被誉为“书林新葩,学海津梁”。此外,彭老出版专著、主编、参编、译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8],可谓著作等身。彭老为了推动我国图书馆学发展曾率领图书馆界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苏联、保加利亚、美国并参与国际图联大会,推动海峡两岸图情界专家互访。每次访问回国,他都要撰写详细的考察报告提交给上级政府部门,为系部师生做关于访问的学术讲座,并整理成文公开发表。正是一大批如彭老般敬业的学者们的沟通、互补与合作,才促进了中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快速发展。
4.3 执掌“图情”:跻身世界前列
根据中国现行的退休制度,人们通常认为,55岁后即便在岗工作,也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然而,彭老从54岁到62岁,却是其砥砺前行的八年。正是这八年的努力付出,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跻身世界前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彭老是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首任院长,他将坚持多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的办学方法,扩大研究生、双学位学生的招生规模作为学院的发展方向,将培养高质量人才、推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教材作为学院的改革目标,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付诸行动。第一,花大力气狠抓教材建设。彭老多次利用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会议的机会,力推二十余种图书情报学专业教材出版,同时还组织编写教学大纲、教学参考资料,为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资料保障。第二,重视人才建设。彭老尊重人才自身意愿,支持人才自由流动,从而间接推动了全国图情事业的均衡发展。第三,发展函授教育。在各级各类人才紧缺的20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继承文华图专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传统,将图书馆学全日制教育与业余教育相结合、专业教育与双学位教育相结合,实行异地办学,在全国各地设立函授站,彭老亲赴各函授点授课。第四,摈弃门户之见。彭老十分爱才,又能海纳百川,只要德才兼备,都在其“后人梯”之列,由此赢得了学界的赞誉,也成就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科的迅速发展并取得了辉煌业绩。第五,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学位授权点建设既是学科建设的产物,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彭老在全面调查了国外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情况后,多次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写申述报告,终于促使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在1990年有了自己培养高端人才的博士学位教育。
正是因为以彭老为首的领导团队抓住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成立”这一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机,才有了美国西蒙斯大学林瑟菲教授两次访问武汉大学对比之后“三个不相称”和“三个没想到”的巨大变化,也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科于2017年跻身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全球第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告诉人们:杰出的领导需要有敏锐的嗅觉,高校图书馆应该抓住学校人事调整、升本评估、审核评估、学位点建设等关键节点,公共图书馆应该抓住城区改扩建、评估定级等关键节点,变挑战为机遇,下大决心、花狠力气全面提升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及科研水平。
5 耄耋之年:享誉海内外
1992年,彭老请辞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职务,全力指导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他将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在治学与为人两方面都高标准、严要求。为人方面,彭老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坚持道德高于学术并寓德于教;治学方面,推崇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四个关键词,师生关系则遵循“严、导、友”三个关键字。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彭老以其“高学”和“正身”受到了后学及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戴。2000年彭老七十寿庆,学生们相聚武汉大学,召开了“彭斐章教授寿庆学术研讨会”,并为恩师出版了论文集《当代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论集》;2009年彭老八十寿庆之际,武汉大学专门举办了“彭斐章教授执教五十六周年暨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还设立了“彭斐章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专栏;2013年武汉大学又举办了“彭斐章教授执教60周年庆祝会”;2019年彭老九十大寿之际,武汉大学再次隆重召开了“彭斐章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一书的策划、整理和出版便是其弟子柯平先生以及弟子之弟子刘莉女士向彭老九十大寿和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院庆的献礼。2004年,彭老被评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他的许多珍贵照片、重要证件、聘书、获奖证书、代表性论著及著述目录、媒体评价与报道等资料被“武汉大学名人档案”收录;2010年入选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并为其拍摄了纪录片,其个人信息被大型社会科学人物画传《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收录;还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杰出成就”奖章,可谓享誉海内外。
6 结语
彭斐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图书馆学大家,他的成就来自于家风熏陶、学校教育、自强不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阅读传记,文献整理编纂家王云五、顾廷龙,经营服务拓展家柳诒徵、袁同礼,学科理论创建家杜定友、刘国钧等图书馆学大家的炼成亦无不如此。《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一书对于教育史研究、图书馆学史研究、现代目录学研究、留苏历史研究以及武汉大学校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详实的页下注为读者了解20世纪图林概况提供了便捷通道与方向导航。与此同时,一大批与彭老同时代的中外图书情报专家,如皮高品、谢灼华、周文骏、庄守经、严怡民、孟广均、吴慰慈、沈宝环、王振鹄、胡述兆、兰卡斯特、斯图亚特等,他们的名字于当下普通图书馆员而言虽如雷贯耳,却总感遥不可及,但因其与彭老发生过交集而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在该书中随文字插入,就如同本人活生生站在读者面前。目睹他们的儒雅容止,就像圣人走下了神坛,走进了普通图书馆员的心间。因此,对于广大图书馆员而言,《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亦是开阔眼界、培育图书馆职业精神、实现快乐充电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