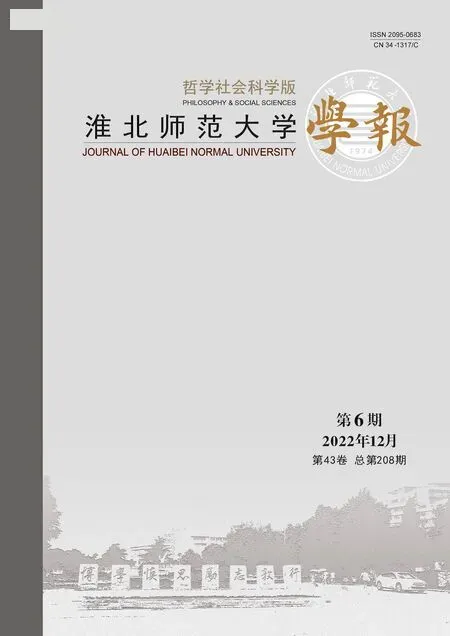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的鲁迅杂文书写及其变迁
古大勇
(绍兴文理学院 鲁迅研究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国新文学史的写作已经有百年时间,胡适发表于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的末尾,提到五四新文学,因此,这可以算是一本“附骥式”文学史。1933年出版的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则是“第一部具有系统规模的中国新文学史专著”,[1]自此之后,中国大陆以及台港地区暨海外产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百部之多。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中,对于鲁迅的杂文,或一笔带过或被忽略,不被重视。如1943年出版的李一鸣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中,鲁迅的杂文被划入“议论、批评、讽刺的散文”中,[2]只是简单提及。而有的史著中,鲁迅杂文则干脆不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王瑶、丁易、刘绶松等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鲁迅杂文的重要性才被凸显出来,在文学史版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此后,杂文就大致成为与小说、散文等文体同等重要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历史阶段的新文学史的版图中,鲁迅杂文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并且其面貌的嬗变与时代紧密相关,鲁迅杂文在台港地区暨海外学者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也具有独特的书写逻辑。探讨中国新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杂文书写及其变迁,一方面是为了在鲁迅学的层面,通过文学史的“窗口”和切入点,观照七十年来鲁迅杂文接受的一般规律,深化对于鲁迅杂文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文学史撰写的层面,以“鲁迅杂文”的文学史书写为研究个案,总结中国新文学史写作的经验教训。
一、“毛泽东时代”“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与政治阐释视角
“毛泽东时代”指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的这一段时间。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等人撰写的新文学史著作。由于特定的时代影响,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多表现出“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以及对于政治阐释视角的重视。例如在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第六章“鲁迅(下)”专论鲁迅杂文。该章各节的一、二级标题分别是:第一节“总论”,二级标题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第二节“鲁迅前期的杂文”,二级标题为: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韧性战斗”的策略、光辉思想的跃进;第三节“鲁迅后期的杂文”,二级标题为: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于文艺思想的指导与斗争。通过这些标题可以看出,该著基本是从思想内容的层面来进行分析,艺术成就仅仅在“民族的形式”小节中作简单介绍。“重思想、轻艺术”的阐释倾向在该时期其他人的史著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而在对于鲁迅杂文思想内容的阐释上,又偏重于政治的视角,多强调鲁迅“革命的”“战斗的”的一面,同时刻意挖掘鲁迅后期杂文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马列主义”的内涵,以及鲁迅后期与中国共产党乃至毛泽东的关系。王瑶的史著凸显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特色,他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十年中,是鲁迅先生战斗精神最健旺和他领导左翼文学运动的时期,而他的杂文正是表现这种战斗精神的工具和结晶”;[3]284鲁迅的杂文是“新文学血肉战斗的历史中不可分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3]290-291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书写的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史,该著强调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政治性”:“(鲁迅)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他写小说,写杂文,其目的都在于从事文化思想的斗争、进行革命教育。……在他的杂文中,战斗者的鲁迅活现着”;“鲁迅赋给(杂文)这种文体以新的特质:高度的政治性;形象性;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多方面的、及时的反映和抨击”。[4]184
如果说用“战斗性”一词来定义鲁迅杂文的内涵符合鲁迅作品的思想实际,那么,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阐释鲁迅杂文内涵则显然是有意的政治性“拔高”和勉强“附会”了。如丁易竭力挖掘鲁迅前期杂文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他认为鲁迅前期散文中就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因子:“发展的进化论的观点,唯物论的成分,和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相结合,这就构成了他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宇宙观的桥梁,这就是鲁迅前期杂文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5]200而后期杂文则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特征:“鲁迅迅速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个思想上的伟大发展,充分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后期杂文中,……他这一时期杂文全部辉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火焰。这些伟大辉煌的杂文,奠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初的一块基石,并引导了中国许多进步作家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上迈进。”[5]200-201丁易甚至将鲁迅杂文所体现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相提并论,他认为:“总体看来,这一时期,鲁迅杂文中所表现的思想,其博大精深的程度,往往和毛泽东同志思想相接近,在一些基本观点和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上,也和毛泽东同志思想有一致的地方……,鲁迅的思想确是充满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因而鲁迅在中国文化战线上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鲁迅的光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5]225-226
无独有偶,刘绶松也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词来阐释鲁迅杂文的内涵:“鲁迅后期杂文是真实地、具体地在革命的发展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特征,而且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教育和鼓舞了中国广大人民的,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最基本的特色。……在后期杂文中,鲁迅坚持而且体现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的伟大原则,在中国人民与反动统治者作殊死斗争的时候,这些杂文发挥了无比强烈的战斗作用”。[6]在这里,刘绶松不但刻意强调鲁迅后期杂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征,还认为它符合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似乎鲁迅的杂文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其他如蔡仪也认为部分鲁迅后期杂文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7]张毕来认为,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中国新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滥觞”,“而鲁迅本人也是从此出发后来终于变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现实作家的”。[4]48
在五十年代的文学史家中,王瑶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期浸淫于民国时期自由主义风气之中,受到清华学风和朱自清等人的影响,形成他特有的自由主义气质,但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受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影响,自觉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例如,王瑶也在史著中特意援引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只有人民的领袖才会这样理解和推崇鲁迅的”。[3]123不过王瑶与丁易等人区别的地方在于,他在强调鲁迅杂文思想性的同时,对于鲁迅杂文的艺术性也比较重视,相关评价文字较为充分,这也可以视为这位具有自由主义潜在人格的文学史家对于主流话语潜意识中有几分不自觉抗拒吧。
二、新时期以来“思想与艺术并重”与多元化解读的阐释趋向
新时期以来,大陆的新文学史编撰进入了繁荣期,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数量远远逾百部之多。1979年6月,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第一卷问世。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部新文学史,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后两卷陆续出版。该史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较大影响。总体看来,该史著一方面已经具有了新时期的时代特征,但另一方面也留有从“毛泽东时代”到新时期的过渡性特征,“意识形态”的烙印没有完全消失,“毛泽东时代”思维的影响没有完全摆脱。例如对于鲁迅后期的杂文,作者认为:“从一九三〇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9]唐弢刻意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鲁迅对共产主义的拥护等,不难看出其立场与50年代的文学史家有潜在的一脉相承之处。当然,唐弢不像50年代的文学史家那样“重思想、轻艺术”,他同时对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也花了不少笔墨。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出版于1984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与唐弢史著类似的特征,如强调鲁迅后期“已能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10]287“三十年代鲁迅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杂文在思想高度上和色调上便与‘五四’和二十年代期间的有所不同”。[10]292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产生的新文学史著作,“毛泽东时代”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阐释现象逐渐消失,总体上呈现出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在评价鲁迅杂文的思想艺术成就时,一部分史著不再把鲁迅的杂文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是将前后期的杂文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进行论述,从整体上肯定鲁迅杂文的价值。例如,严家炎认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和文学价值在于:它具有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具有浓烈真挚的感情色彩;具有幽默风趣的深长韵味和高超出众的讽刺才能。[11]钱理群则在整体性视野中指出鲁迅杂文“跨学科”的知识视野、“跨文体”的文体试验以及先锋性特征:“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的、散文的、绘画的,以至音乐的……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的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试验;在这个意义上,‘杂文’又确实是具有某种先锋性的。”[12]钱理群同时又从整体上指出鲁迅杂文五个思想和艺术特质:一、批判性、否定性的特色;二、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三、杂文思维中的“个”与“类”;四、主观性与诗性特征;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朱栋霖和孔范今等人的史著也分别从整体上评价鲁迅杂文的杰出成就,如朱栋霖认为:“现代杂文正因鲁迅的积极倡导和大力实践而得以踏入文学殿堂,成为新文学园地中的一枝奇葩”。[13]262孔范今认为:“鲁迅的杂文,是民族性和现代性兼具的创造性文体,无论其认识价值还是其艺术价值,都堪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高标”。[14]417
当然,也有一部分史著作者仍然把鲁迅的杂文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但一般不再强调后期杂文在思想内涵上、特别是政治思想上超越前期杂文,不再强调鲁迅后期杂文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再强调鲁迅后期杂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素与“马列主义”内涵,而分别阐释前后期杂文在思想内容上的不同表现。
其次,区别于“毛泽东时代”的史著“重思想、轻艺术”的阐释倾向,新时期的史著表现出“思想与艺术并重”的阐释趋向,并加大阐述鲁迅杂文艺术成就的文字内容。通观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著作,绝大部分在阐释鲁迅杂文思想内涵的同时,又以较为充分的篇幅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进行多维度的细致阐释,并高度评价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论证鲁迅杂文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杰作。例如,朱栋霖在介绍鲁迅前后期杂文的不同内容之后,强调了鲁迅杂文的主要艺术特点:“一、诗与政论的结合;二、从‘贬痼弊’的立意出发,塑造出否定性的类型形象体系;三、幽默讽刺和冷峭曲折的语言”;“鲁迅杂文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其文体形式丰富多样”。[13]264-265孔范今高度评价鲁迅后期杂文的艺术成就:“一、以具体的现实生活现象来形象地引出或涵纳整体的社会思考,得出切实的思想及对社会历史的深入认识。二、形象性与理性原则的内在统一,两者彼此融汇。巧妙地用暗示、借喻和关联的手法,寓理性判断于形象事例之中,使理性逻辑获得形象地展开,而不是硬性地塞给读者。三、强烈的感情、鲜明的道德倾向与深湛的理性思考融为一体,互为促进。……四、现实战斗精神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统一。”[14]416-417
最后,在阐释的具体内容上,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史著更强调鲁迅杂文的“政治性”和“战斗性”,那么,新时期以来的史著则更重视鲁迅杂文的文化批判性和启蒙性意义,对于鲁迅杂文艺术特征的阐释更加多元化。朱寿桐《汉语新文学通史》①《汉语新文学通史》的主编是澳门学者朱寿桐,该著2010年由内地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著作主要内容完成于作者在内地工作时期,所以将之视为大陆的著作,而不是港澳台著作。从“汉语新文学”的新视角,认为鲁迅的贡献在于两点:首先是“开创了批评本体的新文学传统”,其次是“鲁迅的文体贡献”,即文体的开创之功。作者在具体论述时,没有专门谈鲁迅杂文或某种其他体裁的贡献,而是将鲁迅多种体裁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性现象进行观照,认为它们作为一种“合力”和综合性因素共同建构了鲁迅的“批评本体”传统和开创性的文体。所谓“批评本体”,即鲁迅的批判性传统:“鲁迅愿意将文学当作批判的武器,展开深刻而且强烈的社会批判,以此发扬新文化精神,并直接开创了新文学的伟大传统——批评本体的文学传统。”[15]99这种“批评本体”传统不但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同时体现在杂文等体裁中。作者又从“语言革新”“古代文学文体革新”“从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借鉴角度,以恢弘的视野进行文体创新”等三个方面谈鲁迅的“文体贡献”,例如,肯定鲁迅创造性地突破古代散文而创作现代杂文、成为现代杂文之祖,以及其杂文“四不像的白话”“语言杂糅”的文体特征等。[15]101-104黄修己也肯定了鲁迅对杂文文体的贡献:“由于他(鲁迅)的倡导和实践,杂文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树立起艺术的丰碑,确立了与新诗、现代小说相互颉颃的新文体地位”,[16]并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论述了史著的成就。唐金海探讨了鲁迅杂文的中外文化渊源,例如就西方文化渊源而言,作者认为,《我之节烈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与鲁迅读过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托尔斯泰《复活》“在创作思想上都有着相通的脉络”;[17]126《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灯下漫笔》则“明显地融入了进化论思想”;[17]128鲁迅笔下的三种人——“真的人”(《狂人日记》)、“完全的人”(《热风·随感录(二十五)》、“觉醒的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精神渊源与尼采、托尔斯泰等确是一脉相承的”。[17]128吴福辉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在介绍鲁迅杂文时,运用了几幅插图来进行辅助性阐释,起到直观形象的效果。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凸现了鲁迅杂文的高人一等之处,如把李大钊和鲁迅五四时期的杂感相比,认为它们的风格“都属白话中的文白搭配纯熟”,但鲁迅的“文言味要淡了”,“文言句式融合得也是很好”,[18]166-167也就是,鲁迅的杂文融汇了文言句式,但已经看不到文言的明显痕迹,文言水乳交融地进入到白话文的表述中。在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和周作人都分别写了纪念文章,但鲁迅那样“寓伟大深邃精神于沉郁,激愤的文字”,是周作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18]167
三、台港地区暨海外学者新文学史著作中鲁迅杂文书写的变迁特征
如同大陆学者史著中的“鲁迅杂文”书写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新时期”两个阶段,台港地区暨海外学者新文学史著中的“鲁迅杂文”书写也可分为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戒严”时期)和冷战之后(台湾国民党“解严”之后)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台湾国民党“戒严”时期),大多数台港地区及海外文学史家对于鲁迅杂文的总体评价持否定意见,认为鲁迅的杂文不算文学作品,而是政治的工具。周丽丽说:“他(鲁迅)创造了杂文的典型,但也带给了散文长远的厄运”;“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给予真正散文最大打击的是杂文,罪魁祸首乃是鲁迅”;[19]72“杂文的性质不是文学的,完全是政治斗争的工具”。[19]73周锦认为:“中国新文学中的散文,一开始就遭到厄运,那是鲁迅在无意中惹下的,鲁迅的‘随感’杂文,曾经威风八面,……嬉笑怒骂都可以成为文章,固然为刊物和读者所喜爱,但不是创作,不能算做文学作品”。[20]李牧认为鲁迅杂文“行文的路线,却完全以中共的好恶为依据”。[21]陈敬之认为鲁迅的杂感是“仇世嫉俗与造谣惑众之作”。[22]美国夏志清在其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也有对鲁迅杂文的阐释,虽然夏志清在局部内容的评价上,不否认有客观公正之处,但总体上对鲁迅杂文充满“偏见”,评价较低。例如他认为,“他(鲁迅)十五本杂文给人的总印象是搬弄是非、啰啰嗦嗦”;[23]39他否定鲁迅后期的杂文,认为后期鲁迅“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在他转向之后,杂文的写作更成了他专心一意的工作,以此来代替他创作力的衰竭”。[23]38夏志清耿耿于怀于鲁迅后期创作力的“衰竭”或“消失”,言下之意就是鲁迅后期杂文创作不是好作品。当然,也有极个别文学史家对于鲁迅杂文评价较高,如李辉英认为:“鲁迅的散文是自成一家的,特别是他的杂文”;[24]87“鲁迅的杂文从最初开始,就涉及了宽广范围,用他的严肃的态度,加以指摘、攻击所有社会上的缺憾,浩然的正气,恰好使章士钊一类人物为之而敛迹,而他的那些杂文,原本都是些杂感的,……鲁迅的杂文,依然保持过去的精神,战斗到底的”。[24]151李辉英肯定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文明批评的特色。
冷战时期的台港地区暨海外文学史家为何对鲁迅杂文的评价普遍较低?这一定程度上受到全球化的“冷战思维”的影响。冷战时期,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阵营,处于相互对峙的状态,文学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服务于两大集团的战略需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备受毛泽东推崇、并在大陆享有崇高地位的鲁迅,则被处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台港地区暨海外的文学史家视为“共产作家”的代表,因此,他们在评价鲁迅的杂文时,则容易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而贬低鲁迅。
相对于冷战时期,冷战之后台港地区暨海外学者文学史著作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则较高。顾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1915-1927)”这一节,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共分五小节,其中第二节以“救赎的文学:鲁迅(1881-1936)和《呐喊》”为标题,专门论述鲁迅,可见顾彬对鲁迅及其《呐喊》的重视。同时顾彬以较为充分的篇幅阐释了鲁迅杂文的特征及其价值,他肯定鲁迅杂文“有着一种在中国无以伦比的现代性”:“(1)作为新闻文体的固定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现代的文学体式。(2)它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实存(Existenz)的表达和手段,这种实存要求对一切领域的一切事物做出直接的反应。要言之,杂文就是:现在。(3)这种散文以积极干预的姿态登场,它具有道德性。它要迅速介入,直截了当地促成变化。(4)它是片断式的,没有固定的形态。由于它似乎能同时兼容所有的形式和思考内容的东西,因此是一种‘无体的自由体式’”。[25]然后顾彬阐释了鲁迅杂文的几个特色:批判的特色、多疑性、引申性、双层性、语言特征等。
美国的王德威肯定了鲁迅后期杂文的存在价值及其独特的艺术特征:“1926年起,鲁迅大半放弃了创意写作。杂文——一种短小的论辩散文——成了他写作的主要形式,并以此捕捉生命最后十年的所见所闻。杂文同时也成为他捍卫自己和阐释自身写作动机的一种手段……鲁迅巧妙结合他对中外文学文本的渊博知识,他娴熟运用文言和白话语汇的技能,以及辛辣的讽刺。他精心组织的论述彻底反驳了对手。在机智、说理和表达方面,他的对手难以望其项背,极少人能在他的反击下全身而退。”[26]447王德威对鲁迅后期杂文的肯定与夏志清对鲁迅后期杂文的偏见形成鲜明对比。
台湾地区马森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开辟了专节“鲁迅的杂文与诗化散文”,可见其对鲁迅杂文的重视,在第十七章《匕首与投枪vs.幽默小品》中又提到鲁迅杂文。马森肯定鲁迅对于作为散文“次文类”的杂文文体开创性的贡献,“由于鲁迅文笔的出众,杂文遂成为那一代散文中极重要而不可忽略的一项”;[27]448早期杂文“文辞犀利”,“笔战的演习把鲁迅的一枝笔磨练得十分犀利、辛辣,形成了鲁迅独有的风格,也是那时杂文的典范”。[27]339认为鲁迅后期杂文具有拼贴性质的“后现代”特征,“扩展了杂文的形式”。[27]463马森同时指出鲁迅杂文对台湾地区柏杨杂文创作的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皮述民等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评价鲁迅散文时,认为“散文(不包括杂文)风貌,色块沉重灰黯,表现了深刻的与悲悯”。[28]整部文学史将鲁迅的杂文排除在外,反映了该史著对鲁迅杂文的严重偏见,当然,这种极端现象也是个别的。
结语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史著作演进历程来看,鲁迅杂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史著作中不被重视。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受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鲁迅一锤定音式评价的影响,鲁迅的崇高地位得以确立。在毛泽东、周扬等政治家的宏观指点下,王瑶、丁易、刘绶松等文学史家主动配合,推波助澜,积极建构以鲁迅为榜首、“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新文学史秩序,共同推动完成了“鲁郭茅巴老曹”文学大师的命名工程,[29]于是,“鲁郭茅巴老曹”成为公认的国之经典,鲁迅更成为当仁不让的经典之首。自此之后,鲁迅杂文改变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文学史著作中那种被忽略的状态,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重要内容。总体来说,大陆文学史著作的鲁迅杂文书写,从“毛泽东时代”到“新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政治阐释视角为主到多元化阐释视角、从“重思想、轻艺术”到“思想与艺术并重”的阐释演变过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和冷战时期的台港地区暨海外,文学史中的鲁迅杂文书写都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大陆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政治话语来解读鲁迅杂文的内涵,而台港地区暨海外则表现为基于“冷战思维”或反共目的而贬低鲁迅的杂文。其中也有个别文学史家不为政治气候、时代风潮所裹挟影响,对鲁迅杂文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体现了一个文学史家的胆识和史德。“冷战”之后,这种对于鲁迅杂文“意识形态化”解读基本消失了。除个别外,海内外文学史家对鲁迅杂文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较为客观公正,对鲁迅杂文的整体评价表现出一致性倾向,即都对鲁迅的杂文评价较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外因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内因则是由鲁迅文学“巨人”地位所决定、由鲁迅杂文本身不可复制的文学价值和卓越品格所决定。鲁迅杂文具有深广的思想内涵和高超的艺术价值,就思想内涵而言,它是一部表现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内容的巨型“百科全书”,它的广泛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它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开掘、对中国文化的感悟,堪称独一无二,无人能出其右,“迄今为止,鲁迅杂文还是了解中国特别国情的最可靠的文字,最深刻的文字”。[30]鲁迅杂文在艺术上,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情、理、趣的统一,并且能自由运用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鲁迅杂文卓越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应该为“冷战”之后的海内外文学史家所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