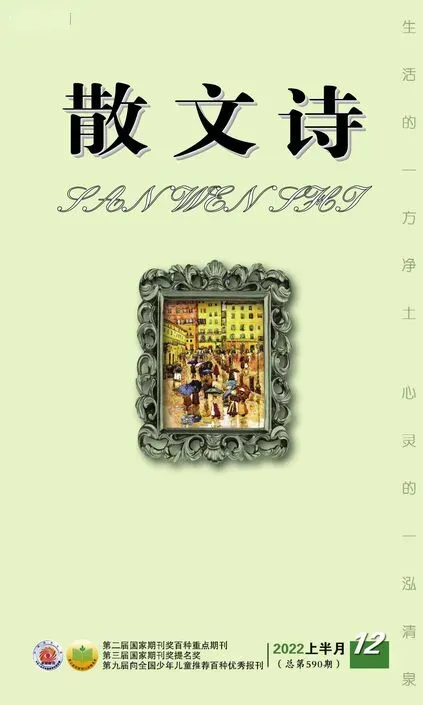没有融化的旧糖厂(外一章)
2022-02-09 01:48:21刘喜良
散文诗 2022年23期
◎刘喜良
面对时光,高大厂房的风窗,像望眼欲穿的眼睛。
糖的名字还在,甜的记忆还在,生锈的机器却像钙化的胃,异常安静。
当年滚烫的空气冷却下来,一层一层剥落,时间受伤以后,残留的糖渣,终于结痂了所有的疼痛。
再硬的铁,也经不住光阴的锈蚀。
再甜的日子,也抗不住人生的苦恋。
只有回忆,是化不开的糖。
旧糖厂,固化为一个时代的甘苦总结。
泊在乡愁里的乌篷船
乌篷船,如流动的画。
划一双桨叶泊进码头;沾一船水墨泊在洞庭;装一舱诗韵泊在江南。
乌篷船,也曾是漂泊的渔家。
一网,捞出柴米油盐,过滤春秋冬夏。乌篷,藏不住船尾的烟火;一支渔歌,洗不净人世间厚重铅华。
乌篷船,你已经摆渡完所有的命运。
泊,是下一个轮回的阐释。
泊在褪色照片,泊在陈列馆角落,泊在时光的反刍中。
乌篷船,终于泊在了万缕千丝的乡愁里。
猜你喜欢
故事作文·高年级(2023年10期)2023-10-23 11:21:36
中国矿业(2021年12期)2021-12-15 09:34:04
少儿美术(2020年6期)2020-12-06 07:37:18
文苑(2020年5期)2020-06-16 03:18:22
阅读与作文(小学高年级版)(2019年8期)2019-10-16 04:46:50
音乐教育与创作(2019年9期)2019-05-16 09:34:10
中国三峡(2017年4期)2017-06-06 10:44:22
北方音乐(2017年4期)2017-05-04 03:40:00
创新作文(小学版)(2016年30期)2016-02-28 18:25:15
工矿自动化(2016年12期)2016-02-22 08:3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