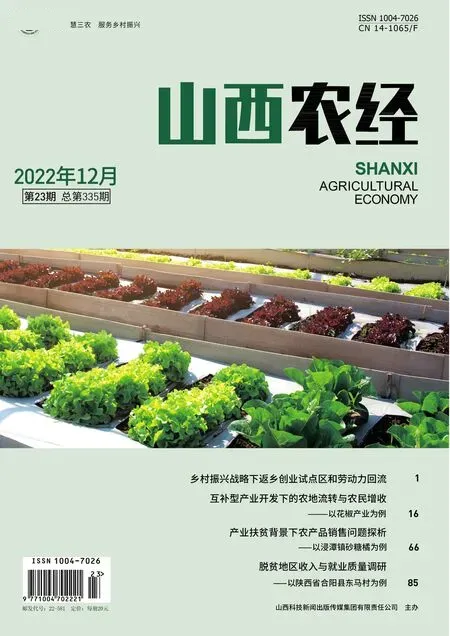互补型产业开发下的农地流转与农民增收
——以花椒产业为例
□邓文辉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要求“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当前,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农村就是发展最不充分的地方。2018 年6 月,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讲话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在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后,过去高度依赖城市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动力已经减弱,其所造成的城乡分离和差距已成为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梗阻。乡村产业振兴能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解绑农民对承包地的依赖,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助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和提质增效。
1 农民收入结构分析
狭小的耕地面积和微薄的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农户的生计与发展,农民除经营农业之外,还需要赚取“兼业”收入,才能维持和改善生活。
自2015 年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4 600.3 元)超过了经营净收入(4 503.6 元)。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是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农村住户家庭经营活动按行业划分为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文教卫生业和其他家庭经营。从定义和范围来看,家庭经营收入来源包括所有农业和非农业行当。把打工和其他非农业经营可统称为“兼业”。从这个范围来看,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源于农业经营的收入规模和比例更小,源于“兼业”的收入规模和比例更高,可见农业经营早已不是农村居民的第一收入来源,“兼业”收入已远超农业经营,成为农村居民的首要收入来源。
从增长速度来看,工资性收入增长要快于经营净收入增长,2013—2017 年,工资性收入增长了1 846 元,经营净收入增长了1 093 元,见表1。“兼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位贡献,既反映农地经营收入及其增长有限,又凸显出农民对劳务输出和非农经营的高度依赖。这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问题,所以不能局限在农业生产内寻找出路。

表1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2 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增收
截至2017 年底,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0.92 亿hm2,承包经营户共2.27 亿户,全部或部分流转出土地的农户超过7 000 万户,面积达到了0.34 亿hm2,占家庭承包地总面积的37%。照此推算,2017 年实际经营农地的农村家庭,平均每户的耕地规模为0.6 hm2。美国210 万个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为170 hm2,是中国的240 倍;欧盟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是18 hm2,是中国的25 倍[1]。
由于我国农村户均耕地十分狭小,相对于土地而言,农村劳动力过剩。这既限制了农民增收,又限制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改革开放以来,为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民工潮。随着昔日乡镇企业热潮退却,农村工业衰落,农民就地非农兼业创收机会锐减,继续务农的农民已经被纯粹化为“种养农”,仅从事农业产业链当中的种植、养殖、采收等直接生产环节,这个环节恰恰是被资本所淘汰的环节。大资本的明显优势已占据利润更高的加工、销售等环节,把小农户纯化为初级农产品供应方。由于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村人才、人力跨地区和跨城乡流动,导致家庭离析、农村社会解构等问题。2018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13.95 亿人,其中农村常住人口5.64 亿人,城镇常住人口8.31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这16 个百分点的差距意味着有2.27 亿农业户籍的人口虽已在城镇居住和生活,但尚未落户城镇[2]。
面临历史形成的巨大城乡差距,少数农村精英和青壮年有机会、能力进城,离开贫弱的农村。这种撕裂式的半进城模式下,大多数家庭老幼成员仍留在农村,甚至不少进城者年老力衰后被迫返乡。如果城镇化率提高至70%,我国仍会有超过4 亿人居住在农村,这比人口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的总人口(3.32 亿人)还要超出近1 亿人。
要解决好这么多农村常住人口的生活与发展问题,需要发展乡村产业,通过农村产业振兴为农民开辟“第三就业空间”——通过产业融合和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为农民在乡村提供不依赖于单纯农业的就业岗位[3]。2016 年,我国农村土地总面积6.45 亿hm2,其中耕地1.35 亿hm2,林地2.53 亿hm2,草地2.19 亿hm2,见表2。在耕地资源和用途受限的约束下,引入适合林地、草地开发利用的产业,发展经济作物,更符合商业资本对周期短、收益快、附加值高的经营需求。中国人民银行达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18)调查显示,213 家调查企业中仅有6%的企业投资于传统粮食生产,工商企业更多投资于农产品加工、经济作物种植、乡村休闲旅游等领域[4]。互补式产业开发,不仅能减少“耕地非粮化”和“农地非农化”风险,而且能为农民提供本地就业和增收渠道,减少农民异地迁徙成本,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粮食安全、维持农村经济社会的完整性和秩序。

表2 2016 年全国农用地总面积 单位:亿hm2
3 互补型产业开发——四川省花椒产业项目
2017 年底,四川省花椒种植面积达32.96 万hm2,年产干花椒8.36 万t,综合产值62.7 亿元,3 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18 年5 月30 日出台《关于推进花椒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川办发〔2018〕34 号),提出总体目标:到2022年,全省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600 万亩(40 万hm2),其中现代花椒基地突破300 万亩(20 万hm2),花椒果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0%,建成亿元级加工企业10 个、省级以上花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10 个、省级以上花椒产业特色优势区10 个,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知名品牌20 个,实现综合产值300 亿元,主产区椒农人均年收入达到3 000 元,努力把四川省打造成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研究和开发水平领先、综合效益显著的花椒产业第一省。
2018 年底,调研了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一带的花椒产业项目,内江市东兴区新店乡已建成万亩九叶青花椒示范区,一人多高的九叶青花椒树植满了山头坡坎,花椒林与良田耕地毗邻共处。荒草野山转变成了整饬的花椒林。区内建立了花椒烘干厂房、办公楼,并设置了相应了管理服务机构等。万亩九叶青花椒示范区建设是东兴区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举措。
四川省花椒产业的经营主体和经营组织方式都已多元化。在商业资本主导的规模化花椒产业项目运行中,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发掘和适宜地块的搜寻是项目成功的起点。“市场土地两适宜”是农村产业项目盈利的基本要求。企业家凭借专有信息、技术、市场渠道以及综合的个人才能,发掘产业机会和锁定落地地块。花椒具有耐寒、耐旱、耐瘠薄以及固土能力强等特点,四川省多山地、林地、荒坡,多数地区适合花椒种植。花椒项目在四川省落地,满足了土地适宜的条件。花椒是一种特色经济树种,单价高于一般粮食作物。花椒在食品、香料、化工、药用、养生等方面广泛应用,其产业链更长,市场和目标用户更趋多元化,有巨大发展潜力和较广阔的市场前景。四川省本身也是花椒消费大省。因此,发展花椒种植与加工产业是市场适宜的。
规模化经营花椒产业需要占用大量农地种植花椒,具体的种植方式可以是“企业+农户”的合作形式,也可以是基于农地流转的企业自主经营。成功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是企业自主经营的必备条件。大规模的产业开发和土地流转要遵法合规,并符合各方的经济利益。
花椒产业开发项目涉及的法律规章要求主要是“农地用途改变”的限制及“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花椒种植对土地条件要求较低,不必占用粮田,不会危及粮食自给安全。花椒林能加强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因而花椒产业项目项下的土地流转基本不会受到法规限制。文章将着重分析四川省花椒产业项目对当地农民和农业的互补增进效应。
4 花椒产业开发中的互补增进效应
4.1 流转地块与主营地块的互补效应
流转地块与主营地块的互补关系表现在主营地块的经营权、用途、农时、市场等方面没有被流转地块的经营活动挤占。花椒项目的土地流转基本都是草坡、林地和其他抛荒地块,这些地块可以被称为“外围地”,不挤占农民耕种的主营地块。主营地块的经营活动不会因为土地流转交易而中断或挤占,农户的主营生产活动不受干预。在用途方面,流转地块用于种植花椒,农户主营地块的原有作物一般为花椒以外的作物,二者用途迥异[5]。
流转地块与主营地块在农时、市场方面都有很强的互补性,替代关系较弱。由于以上互补关系,土地流转基本不影响农民的主营活动和经营规划。流转对农户的生活及经营活动影响是边际的,而非根本性。因而,在项目方与农户沟通和达成流转意向的过程中,农户面临的动荡和不确定性较低,流转活动交易成本较低,效率较高。同时,互补性产业开发可以减少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和挤出效应,避免严重扰动粮食生产,稳定粮食生产供给,还有利于维持农村经济社会完整和秩序[6]。
4.2 流转地块经营给农户带来增量收益
流转地块与主营地块的互补关系使流转地经营在不消减农户原存量收益的基础上,给农户带来增量收益,农户收入处于稳中有增的良好态势。
四川省花椒产业项目对土质的要求不高,山头、坡地、林地、撂荒地等“外围地”都满足花椒种植需求,流转“外围地”获得高出原用途的流转收益,且不减损原主营地块的收益。花椒项目恰恰拓宽和增加了“外围地”的用途,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效益,顺便把撂荒、无偿或低价非流转的零碎地块也纳入正规稳定的流转范围。
花椒产业项目运行中的就业机会创造和外溢使该项目产生持续富农、兴农效应,增强了项目的生命力和造富功能。由于花椒种植项目基本不占用良田耕地,原务农村民继续在原有耕地上务农,且有较多的农闲时间。由于花椒和该地其他农作物的农时有明显差异,花椒种植项目流转农地的拓荒、开垦和日常劳作经营。大多雇佣当地农民,农民可以就地兼业务工,获得一份工资性收入,这提高了劳动力利用率,也提高了家庭收入和家庭保障。
5 花椒产业开发项目的政策启示
乡村产业振兴中,如果引入的产业需要占用大量农地,则引入产业与当地主营产业之间在土地占用方面产生的竞争或互补关系将对项目的交易费用、成本以及对当地农民生产经营和福利等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
5.1 基于用途提升的“外围地”流转交易成本更低
“外围地”的原用途收益低,不属于农户的主营地块,其向外流转不影响农户的主营业务和收入,对农户生产经营和生活的影响较小。如果有适合“外围地”质的产业项目,则项目方与农民就土地流转进行沟通并达成协议的交易费用较低,达成流转意向的概率更高。中等地和优等地可能都是农民的主要经营地块及主要经营收入来源。当农民面临是否流转主营地块的抉择时会考虑更多。如果家庭事先没有外出务工或经营的想法,出让主营地块而“净拿”流转收益意味着家庭劳动力将赋闲;如果农户不出让土地,通过“自我雇佣”投入劳动从事农地耕作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很可能高于“净拿”额。流转出让主营地块对农户的影响更大,显然更难以达成流转意向。
此外,中等地和优等地的原主营用途收益较高,土地流入方要支付更高的流转价格,这会提高项目成本,提高对项目的经营要求。
5.2 挤出效应小的产业项目更适合当下农村实际
通过走访内江市东兴区花椒产业基地可以看出,花椒产业基本都是利用荒坡、林地等,没有挤占主营农地。花椒作为一个新增产业植入农村机体,原来的农业生产经营未受花椒产业排挤。这种“拾遗捡漏”+“拓荒”式的土地利用没有侵占当地农户的主营农业用地,不会造成农民“失地”“离地”问题,也不会危及粮食安全。农民不仅获得“流转收益”,还可以因为花椒产业的就业创造和溢出效应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花椒项目与原农业生产经营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既保证了农民和农业的稳定性,又增加了农民流转收入和务工收入。即便项目有失败或终止的风险,但对农民的影响也是边沿性的。当前我国农民创收渠道有限,社保制度发展滞后,大规模流转主营土地会造成对农民的排挤,造成农民“失地”“离地”,一旦项目不可持续,会引发大面积社会动荡。因此,花椒林这种“拾遗捡漏”+“拓荒”的土地流转模式是在隔离和保留主营地块用途基础上的提升“外围地”用途,是温和、渐进的土地流转推进路径,是我国当前农村经济社会状况和人地关系下的一种安全、稳妥的土地规模利用和土地用途提升途径。因此,这种互补型产业开发项目在当下更有生命力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