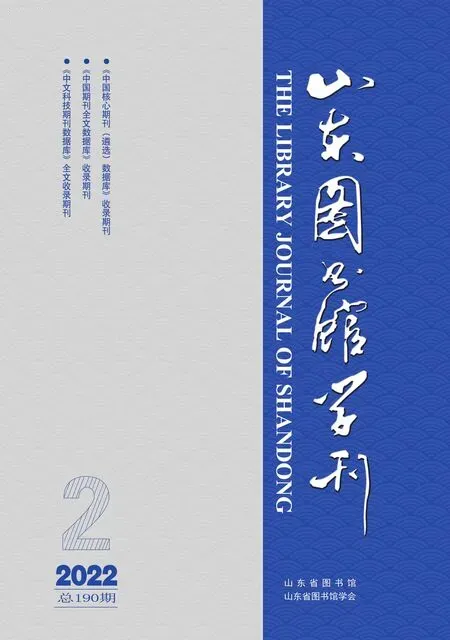伦明“续书楼”藏书源流考*
钱 昆
(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1 引言
伦明(1878-1943),字哲如,一作哲儒、喆儒、节予,广东东莞人,出身重视文化教育的伦氏家族。少年时期即好藏书,及至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已经逐渐积累起丰富的书藏经验,在京亦开设“通学斋”促进书藏,于藏书研究、藏书实践等方面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反对贵远贱今、重视清人著述、每书版本齐备、藏书意欲为公等,这些藏书观念在晚清民国时期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伦明的藏书处所称为“续书楼”,其藏书不仅能供伦明读书治学以自用,同时还能惠及友人并泽被后世。
2 “续书楼”的由来
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里开篇即说“续书楼者,余钤书所自署也。余居京师二十年,贫无一椽之栖,而好聚书,聚既多,室不足以容,则思构楼以贮之。其所聚书,尤详于近代,意谓书至近代始可读。自乾隆朝命儒臣纂四库书,撰提要,裒然大观矣,由今视之,皆糟粕耳。则思为书以续之,此续书楼所由名。”[1]可见伦明抱有续修《四库全书》的宏愿,因此意欲把自己的藏书构楼以贮,命名为“续书楼”。然而得书不易,建楼亦不易,纵观伦明一生的活动轨迹,“续书楼”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景,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书楼,而是由众多分散的小型藏书处所集合而成的一个概念,而非实体。这些分散的藏书处所包括伦明位于广州的小东门寓所、南伦书院,位于北京的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因此伦明才说“然而楼未成也,书亦不备,志之云尔。”[2]
1937年伦明南归扫墓,适逢卢沟桥事变,滞留广州,直至1943年去世再没回过北京。滞留广州、东莞期间,他的书斋也称“续书楼”。伦明毕生是以续修《四库全书》为志业的,所以当后人提及伦明的藏书处所时,一般都以“续书楼”称之,如王謇的《续补藏书纪事诗》、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皆以“伦明·续书楼”称之。
3 “续书楼”藏书来源
伦明少年时期曾随父就读于江西崇仁县衙斋任所,平时生活所得零花钱皆用来购书,深得伦父喜爱。伦父好书,叮嘱伦明藏书的同时也要善读,伦明以此为庭训。可见伦明少年时期即有志于藏书、读书,但是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书藏基础,则是在其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时期,此后通过其从学、从商、从教和短期从政的经历,以购书、抄书、建通学斋促进藏书等方式,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书藏。
3.1 购书
1902年(壬寅),伦明初到京师,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当时正值庚子(1900年)之乱后,一些王府贵家的藏书开始散出,伦明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接,每到傍晚便载书满车回寓。1907年(丁未)伦明返粤,逢南海孔氏(孔广陶)三十三万卷楼藏书散出,鹤山易氏(易学清)、番禹何氏(不详)、钱塘汪氏(不详)所藏亦散,伦明皆得择而购之。1911年(辛亥)伦明再至京师,自武昌事起后,都人仓皇奔避,纷纷贬价售书,此次伦明得到同邑叶灿薇的资助,尽力购之,载四大簏。时与伦鉴、伦叙、伦绰兄弟四人一同寓京,相约南返,无奈车站人流众多,携带书簏更是不便,伦明“誓与书同行”,选择独自留下观察情况以备后动,其余兄弟三人先行至天津等待,伦明往返车站数日,发现人流渐稀,遂从容携书簏上车,至天津与兄弟同行南返。由此可看出伦明求书若渴,护书心切。
伦明久居京师,自然明白京师之地对于藏书家来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在京为官者,大都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即使清季变法废除科举,但因新式高级学校相继建立,负笈而来者众多,所以京师书业甲全国。辛亥以后,达官武人雅慕文墨,视蓄书亦为挥霍之豪事之一,同时大学图书馆的建立以及私人藏书家的需求,都使得京师之地的藏书供不应求,于是出现众多搜书之人,始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次江浙、闽粤、两湖,又次川陕甘肃,先通都大邑,次穷乡僻壤,远者一年往返一次,近者一年往返三四次。伦明慨叹此种做法如竭泽而渔,不出十年,故书尽矣。结果访书愈来愈难,书价愈来愈贵,伦明书资有限,亦不喜“陈陈相因”之书,因此其求书之法颇重版本。
伦明一生历经多省,或从学、或从教、或从商、或从政,每到一地,一有机会便去访书,只为实现其续修四库之志。伦明游迹所至,上海、天津经过最频,苏州、杭州各一次,南京、武昌各两次,居河南三年游怀庆、卫辉、清化诸地,皆有所获。以上所列诸处为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所述,但不是每一次游历都有迹可循,后世史料亦少。
3.2 抄书
伦明好藏书,藏好书,但其本身既不是富商大贾,也不是达官显贵,因此常因书资而捉襟见肘,甚至有时养家之用也要让位于购书,伦明曾有《买书》诗云:
平生丝粟惜物力,独遇奇书不论钱。
书坊质库两欢喜,只有妻孥饿可怜。[3]
“有抄之图书馆者,有抄之私家所藏者,又有力不能致,而抄之坊肆者,有抄自原稿本者,有抄自传抄本者,又有猝不易得,而抄自自刻本者。”[4]可见伦明设法通过多种渠道抄书以丰富所藏,其中有亲自抄录的,也有请人抄录的。
3.2.1 亲自抄录
伦明就读京师大学堂时始识曾习经(伦明《辛诗》里为其做诗传),曾氏嗜书,癖过伦明,每当有客拜访偶谈及书,便神态飞动、手舞足蹈,口亦不停,边谈边从书架上取书作证,客人感到疲倦之时亦不休息,客人欲走之时又再三劝留而不得去,久而久之,相熟之人皆互相告诫不要与曾氏谈书,而伦明却最为喜欢。当时伦明在京居烂缦胡同,曾氏居绳匠胡同,相距不过百步,便于伦明造访,粗茶淡饭之后,二人时常谈论古今,赏奇析疑,直至深夜伦明乃归,其时必挟书数册,或读、或抄、或校,再访时归还,如此数月,直到伦明迁居东城。伦明自己曾说:“余壬寅来京师,多从君借书读。君喜读书本,暇则偕游琉璃厂,随所见谆谆指示,余之癖于此,由君引之也。”[5]可见伦明的“书癖”与曾习经的熏陶引导有密切关系。
孙殿起记云:“某岁津门书贾以重值购入清翁覃溪方纲未刻稿数种,先生得知亟赴津往观,以其价奇不可得,乃设计携归旅邸,尽三昼夜之力摘其切要而还之。”[6]可见伦明抄书之功用力颇深,有《抄书》一诗记云:
不爱临池懒读书,习劳聊破睡功夫。
异时留得精抄本,算与前贤充小胥。[7]
3.2.2 请人抄录
伦明常年雇佣三名抄工,随时为之抄写。有王志鹏者,系邃雅斋弟子,练就一手抄书、修补绝活。“抗战前大学者伦明、建国后酷爱收藏的李一氓。都曾把他请上门,帮助抄书、修书,结下深厚的友谊。”[8]后来伦明在京城的“通学斋”也是在一魏姓的补书匠的建议下设立的。伦明与这些抄书之人、补书之人经常打交道,甚至常年雇佣为其抄写、装补,沿袭了古代藏书家重视抄校的传统,虽不至满门尽抄书,但也见其用功之深。
伦明曾说“抄书不难,而抄之先借书难,抄之后校书难,校书之事我为政,借书之事人为政,故借书尤难焉。”[9]这段话深刻总结了藏书家的访书之难,因为抄书不难,甚至还可以请人抄录,而校书对于“读书治学以自用”而非“束之高阁”的藏书家来说,虽然也算是难事,但毕竟在自己学识能力范围之内,只有借书不可控,因为首先要知书籍来源,然后才能确定是否能得见、得抄或得借,这些有关人事,并非一厢情愿就可以,因此伦明才感慨借书最难。对于校书,伦明亦有诗记云:
一字辛勤辨鲁鱼,益书益己竟何如。
千元百宋为吾有,眼倦灯昏搁笔初。[10]
3.3 建“通学斋”促进藏书
伦明亦有《卖书》诗云:
货值仍然不离儒,本来稗贩笑吾徒。
长门赋价今时贱,不卖文章改卖书。[11]
1915年,伦明三至京师,决心定居北京,本意将所藏书籍全部北运,因运资问题不能全部随行,只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寄存在南伦书院,另一部分随行入京。伦明初入京时赁居在莲华寺,随行书籍残破待装补者众多,于是雇佣一书匠魏氏,月资十五金,魏氏觉得要是将伦明所需装补的书全部整理完毕,没有二十年的时间是完不成的,于是建议伦明开设书肆并遍数益处,即“装书便一也,求书易二也,购书廉三也”[12],伦明深以为是,遂于1918年在南新华街路东七十四号开设了“通学斋”书店。通学斋始设,魏氏告病,伦明聘用会文斋的伙计孙殿起(耀卿)帮助经营。伦明南归后,通学斋逐渐转到孙殿起名下,但伦明尚有股份(以书入股),当时伦明之子伦绳叔留在北平读中学,常上通学斋或孙殿起家里取学费和生活费[13]。伦明1943年去世后,孙殿起一直经营通学斋,直到1956年因公私合营而并入中国书店。
对伦明自身藏书建设来说,通学斋是伦明搜集图书的主要渠道,也是“续书楼”藏书的主要来源。伦明虽是东主,但如果需要自藏,也要按规记账,雷梦水曾在《孙耀卿先生传略》一文中回忆说:“时伦哲如虽为通学斋东主,然按书铺惯例,私人购书也要上账,履行手续,伦君严以律己,诚可敬也。”[14]经过伦明与孙殿起二人独具慧眼的收书、藏书、校书、售书的一系列经营,使得通学斋名噪京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往来的主要场所,亦是当时中国古旧书业的主要代表之一。
3.4 得书心得:以俭、以勤、以恒[15]
伦明通过自己买书、抄书、建立通学斋以促书藏的做法,不断丰富自己的藏书,在晚清民国时期的藏书家中算是规模比较宏大的。伦明把自己的得书经验概括为“以俭、以勤、以恒”六字,并进一步阐释说,“俭以储购书之资,勤以赴遇书之会”,而“恒”则体现了伦明以续修四库为目标的求书毅力与决心。从少年时期开始,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伦明不遗余力收书、校书,尤其在京日久又逢群籍集中之时,日积月累,最终达到了“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在这样的藏书动力驱使下,伦明的藏书规模究竟如何呢?前有述“续书楼”者,是后世称呼伦明藏书处所的一个代称,实际伦明有构楼贮书的愿望,但未能实现,他的藏书分散在广州的小东门寓所、南伦书院和北京的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据孙殿起记述“他在北京所储藏的书,写记目录凡两次。二十年代奉派杨宇霆、郑谦为张学良抄过一次,因故中辍;1938年他眷属南归,又抄一次,计十余册,每册五十页。由他的眷属携归,经友人借阅佚去数册。”[16]可见伦明曾为储存在北京的藏书编有书目,可惜稿本未刊行,现存于上海图书馆,题名为《东莞伦氏续书楼藏书目录》,凡十三册,红格十六开墨笔稿本。此书目稿本先经叶恭绰索要收藏、后经顾廷龙借阅抄录,据张宪光考察,“这份目录的编撰,以箱为序,大体将经、史、子、集同类书籍装于一箱,却又很不严谨,时有错杂的现象。目录十分简明,仅记书名册数,偶尔标注稿本、钞本、铅印、不全、未装订、明刊本等字样,几乎未标明作者及其他信息。”[17]据张宪光粗略统计,该目共收书一百五十七箱,总计约一万三千种、四万三千册左右。今就东莞图书馆所编《伦明全集》第五册之《东莞伦氏续书楼书目》观之,除前述一百五十七箱之外,还多出四十七箱,约三千种、近一万册左右。这样伦明“续书楼”的藏书规模大概有一万六千种、约五万余册藏书,这在晚清民国时期不可谓不宏富。
4 “续书楼”藏书管理
4.1 广州藏书管理不善
前述伦明“续书楼”里的藏书,实际分散在广州的小东门寓所、南伦书院、北京的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粤地卑湿,书亦生蠹,伦明藏书较多,不易整理,残缺较多。己酉(1909年)夏,西江水上涨发水(时伦明正辗转于两广之间),越门而入转瞬二三尺高,广州小东门寓所内的书藏因仆辈收拾不及而损失惨重,但因害怕伦明斥责而刻意隐瞒,后待伦明翻检书籍时才发现,但已经无法挽回了。伦明出游时有部分书藏寄存在族中南伦书院(伦氏宗祠),院内有一贩卖破铜器的无赖,私下里把书橱铜钥挖掉变卖换钱,及至转为盗卖院中所藏书籍,若不是伦明友人在书肆中见有书籍似为伦明所藏,并据之以告,伦明尚且不知自己的书已经被盗卖!后伦明虽将此人驱逐,但已有不少书籍被盗卖,可惜可叹矣!1920年冬,伦明曾回过广州一次,时伦明已定居北京近五年时间,此次回广州因时间仓促,对南伦书院的藏书顾不上整理,返回北京后才得知因修马路南伦书院被拆的消息,藏书在迁徙中流失,无人知晓下落。这部分流散之书或许曾归于粤地公私藏书中,但因伦明藏书从不钤印(或有批校、题跋可供辨识),基本已无迹可寻了。
4.2 北京藏书管理完善
北京气候干燥适宜藏书,并且“京师书业甲全国”,便利求书,这应该也是伦明决心“弃乡土”而定居北京的原因之一[18]。伴随伦明治学中心的转移(续修《四库》)和“士而商”的选择(在京开设通学斋),伦明迁居北京先后入住东莞会馆和东莞新馆。伦明在北京的藏书,一部分来源于其入京时自广州带来的部分藏书,一部分来源于定居北京后自己不断求书所得。同时在经营通学斋的过程中,亦有孙殿起帮助搜访,伦明书藏益富。通学斋亦有抄书匠、补书匠等专职打理,伦明的藏书管理较广州书藏完善一些,但没有足够的空间藏书又是一大问题。孙殿起曾回忆说其北京藏书“拥书数百万卷,分贮箱橱凡四百数十只,书房非有十楹屋宇,不得排列。”[19]虽空间有限,但相较于粤地而言,在气候与管理方面改善很多,这也是伦明在北京的书藏最后能够归公于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原因。
5 “续书楼”藏书去向
伦明于1943年去世后,陈垣、冼玉清、袁同礼等一批学者为伦明“藏书归公”的遗愿而奔走努力,所幸终偿其所愿,但仍有部分书藏散佚,现大致归纳伦明藏书的几个去向。
5.1 归公于图书馆
1947年春,在伦明去世三年后,其藏书终于归公于北平图书馆,当时通学斋店员雷梦水告知邓之诚该批藏书近以一万万元归北平图书馆,邓之诚评言:“此价在平世不及万元,得值仅十之一耳!无异掠夺。”[20]从伦明的藏书数量和学术价值来看,虽为“卖”但无异于“捐”。伦明藏书归于北平图书馆的交接经过,伦绳叔有过一段记录:先生一生从事学术,除著作外,当以所存之书籍闻著于社会,命之曰伦氏续书楼。然吾辈后生不得保守,乃决议让与北平图书馆。此乃八姐伦慧珠由港与袁同礼氏商洽而定。今由图书馆派人帮予同整理目录(前目录遗失,仅余五册目录),迄今已告完毕矣。[21]
在《藏书家伦哲如》一文中,魏隐儒曾言“伦氏卒后,将广州藏书全部让于广东省图书馆。北京所藏部分,于1947年全部归北京图书馆。”[22]归公于北京图书馆的说法上文已述,归公于广东省图书馆的说法目前查无实证,尚不可考。
5.2 捐赠给学校或友人
伦明八女伦慧珠于1947年将已逝丈夫张荫麟留在东莞会馆的藏书捐给了浙江大学,这批藏书中可能夹杂有伦明的藏书;伦明曾将广州的一部分藏书转让给在广东从事教职的弟弟伦叙做教学用,后来伦叙的孙女伦德仪又在“土改”期间将这批藏书捐给了广州文化事业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望牛墩散存的图书“被迫”捐了出去。伦明病重期间曾嘱托好友张伯桢捐书给北平图书馆(除了张伯桢之外,陈垣、冼玉清、袁同礼等人也致力于伦明书藏归公的努力,如上文所述,伦明去世三年后,其藏书终于归公于北平图书馆),他同时也列出一个书单,让张氏自选,送给他部分藏书。
5.3 伦氏后人散卖
伦明后人中有一子略识版本,但因吸食鸦片,在伦明去世后曾偷卖过父亲的藏书;1947年伦明在北京的书藏正式归公之前,迫于生活困难,伦氏后人亦散卖过一些藏书以贴补家用;及至归公于北平图书馆后,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北平图书馆和中国书店为广泛搜集古书,还曾去伦家找书,陆续翻出一些散本,伦家后人以十元二十元的价钱零卖出去。
5.4 通学斋学徒散卖
1947年伦明藏书归公于北平图书馆的时候,通学斋孙殿起的大徒弟李书梦帮忙守书,大部分书藏被北平图书馆用卡车装走,还剩下一些散页、散本(因伦明的书藏特色之一即是版本齐全,集中在一起价值较高,分散析出后价值变低),其中当然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如书信、手稿之类。由于装运的图书太多,无人留意这些散本、散页,这些散存的书藏、资料便由李书梦陆续零散卖出。
5.5 辗转遗失不知所终
冼玉清《记大藏书家伦哲如》云:“先生(伦明)久欲编印《续岭南遗书》,其弟子李棪劲庵允经纪其事,并允向粤督陈济棠措款,先生尽以所藏粤人著述秘籍授之。李君来香港执教,以书寄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先生来书嘱咐李君求交代,李君唯唯。其后邓之诚文如教授亦有函来,嘱转告李君速为处理。今李君远适异国,秘籍之下落如何?中心耿耿。”[23]可见这批粤人著述是伦明用来作《续岭南遗书》的,但已无从可考且不知所终。
6 结语
伦明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其藏书处所称为“续书楼”。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爬疏资料,从藏书来源、藏书管理和藏书去向三个方面进一步厘清伦明“续书楼”的发展源流,希望能为晚清民国时期私家藏书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