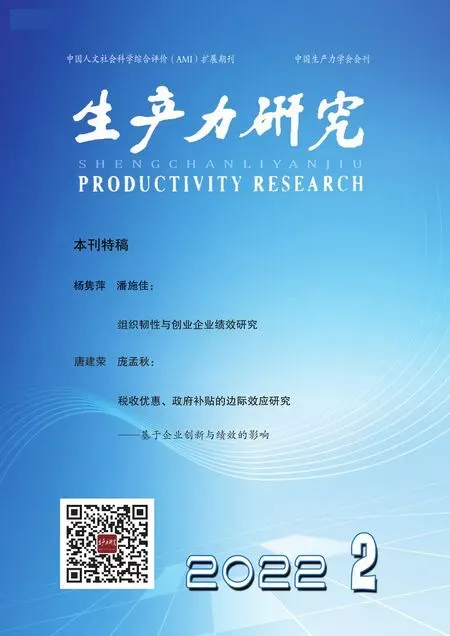区域制造业优势和特色发展研究述评
邓如梦,钟书华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Manufacturing i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regional economy,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is the top prior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manufacturing advantages in China,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reviews.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dvantages,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and the selection of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on this basis,expound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trends.
一、引言
在全球垂直专业化深化发展的背景下,发展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就是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产业,并取得持续效益的过程。因此,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形成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优势产业可通过区域内产业专业化的转型激活,为区域经济识别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增加区域实力。制造业作为区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优势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要重塑产业竞争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需要指出的是,竞争力的分析一般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次的竞争力涉及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微观层次的竞争力体现在企业层次的竞争力。随着产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作为中间层次的产业竞争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三个层次的竞争力侧重点各不相同,但又相互融合。区域制造业优势发展需要考察区域、产业和企业三个层次的交互发展。因此,本文基于区域优势、竞争优势、比较优势等理论,从区域优势发展、产业竞争力构建、企业特色选择三个层次出发,对区域制造业优势和特色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综述。
二、区域优势发展
国内学者以区域优势理论为基础,主要从差异化能力评价、要素贡献程度和产业集聚升级三个方面分析区域制造业的优势发展。
(一)差异化能力评价
由于区域间产业结构同质化及恶性竞争的存在,立足区域差异能力和定位,结合行业发展潜力,兼顾规模优势,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为识别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重点行业的发展方案,方大春和王婷(2019)[1]通过产业结构超前值、区域熵、产业结构相似系数等三个指标,考察了区域间产业同质性和差异化发展潜力。彭智敏和冷成英(2015)[2]使用区域熵和产业集聚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制造业的集聚强度和差异优势进行测度。武慧敏(2014)[3]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变化,以摸清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
在具体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上,张世龙等(2011)[4]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各区域医药产业差异竞争能力进行评价,并按主因子及综合竞争力得分进行排序和聚类分析,揭示各区域医药制造业的特点和优势。李廉水等(2014)[5]运用基于FAHP-熵权组合赋权的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制造业差异化竞争能力进行横向和纵向评价。李琳和王足(2017)[6]提出了包括绿色发展表现力、绿色创新驱动力、绿色环境支撑力3 个评价层27 个评价因子在内的区域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1 省市制造业绿色竞争力进行动态比较和评价。张文宇等(2018)[7]概括了包括环境规制、经济水平、创新投入、创新组织、创新产出和创新扩散在内的6 个层级31 个指标的评价体系,以评估各区域制造业差异化的绿色创新能力。
(二)要素贡献程度
区域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多源性特征。王图展和张跃(2018)[8]认为,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制度因素、规模经济、集聚效应都是区域制造业显性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毛海丹(2012)[9]分析了制度因素、要素禀赋、R&D 投入、规模经济、出口结构、产业特征等6 个影响因素对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影响,其中,规模经济、R&D 投入、出口结构是推动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最重要的力量。刘航(2013)[10]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因素出发,研究了制度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机制和实效。
各要素贡献程度不一,同时也会随着比较优势的演化而呈现新特征。冯梅(2012)[11]揭示了制造业比较优势演化中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外资注入、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动态变化特征。其后,冯梅根据相关要素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确定了指标体系,将指标体系与制造业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回归分析,测算上海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中各要素贡献程度。结果表明,资本对于上海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贡献最大,技术也是提高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针对要素不断演化特征,石奇和孔群喜(2012)[12]进一步刻画了我国产业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的发展态势。同时,作者进一步认为,应基于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来构建新式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实施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应当围绕现有产业的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来展开。
(三)产业集聚升级
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的新特征,是影响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变量。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产业优势越明显。有学者认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格局演变呈现出“四化”特征,即高新技术化、重型化、集群化、相似化。毛琦梁等(2014)[13]进一步认为,一国之内产业格局变化主要得益于集聚外部性的作用,而不是区域间比较优势变化。产业集聚度低,不仅制约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提升,还挤出了产业融合竞争优势的提升效应。
关于产业集聚作用,学者们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制造业集聚能够有效推动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提高,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率的提升。例如,陈雁云和邓华强(2016)[14]运用区位商指标,对长江经济带11 个省市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效果差异较大。韩中(2010)[15]指出,制造业空间集聚使生产要素不断流动,加速了区域技术进步和创新,抵消了技术效率下降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加。相反的,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扩大区域差距的负面影响。徐盈之和朱依曦(2010)[16]进一步区分,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存在区域化和城市化两种不同作用机制,区域化经济对航天航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城市化经济对其起着负作用,且各区域不同集聚经济呈现相异的显著作用。
三、产业竞争力构建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为产业竞争力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国内学者对于制造业竞争力构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竞争优势依托、优势动态变迁和服务化转型三个方面。
(一)竞争优势依托
知识是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是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经历规模优势、产业集群、网络化制造等过程,获得市场竞争性地位。为了探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优势依托问题,李国英和陆善英(2019)[17]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阐述了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交易效率优势和综合优势四类优势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综合优势影响作用最大,且存在路径依赖;要素禀赋优势对处于价值链低端产业的影响作用更大;创新分工优势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作用更明显。未来高技术制造业优势发展可依托要素禀赋优势、创新分工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动态迭代。
具体到不同行业,其竞争优势依托也有所不同。曲玥(2010)[18]认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具有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因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是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宏和陈圳(2018)[19]关注中国优势制造业竞争力发展状况。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具有明显优势。相对于低技术和新兴制造业,中、高技术行业更具显著竞争力。以核电、航空和高铁为代表的高技术和新兴制造业,主要依靠国内增加值的中间品出口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而代表低技术行业的纺织业,依靠融入全球价值链,来保持全球同行业竞争优势。在全球垂直专业化背景下,我国优势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和价值链攀升具有依靠国内增加值质量提升的内化特点。
(二)优势动态变迁
比较优势的多源性和动态性决定了竞争优势的动态变迁。李晓华(2011)[20]华指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经历从价格优势到规模优势,再到创新性制造优势的演变过程。耿伟和战楠(2006)[21]进一步揭示,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模式的演变具有固化性特征,而部门干中学和国际知识外溢是固化特征的主要动因。所以,需要关注综合优势的动态培育,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也有学者将比较优势变迁与要素代替、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偏向性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内容联系起来,以探析其与比较优势变迁的关系。郑猛和杨先明(2017)[22]指出,要素代替弹性的提高能够推动比较优势动态转变,自主创新和技术模仿型技术进步是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变迁的两条有效路径。未来中国制造业应突出要素代替的资本积累效应,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技术进步向生产率转化程度,更快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转变。李强(2016)[23]通过构建CES 生产函数,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会交互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需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服务化转型
制造业可通过服务化转型,增加产品中知识型服务要素的密集度,增加产品种类,同时降低价值链各环节间的协调成本,提高利润水平。实现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变,制造业服务化是形成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新来源。基于金砖国家和其他典型国家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情况,胡昭玲等(2017)[24]发现,发达国家以金融保险、信息通讯、专业科技服务化为主;发展中国家以运输仓储、批发零售服务化为主。低端服务融入低技术制造业,高端服务倾向于融入高技术制造业。
随着学者更多地关注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服务化能否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等问题得到不断探讨。王娟(2019)[25]研究了企业服务化战略能否促进行业技术进步,以及以何种方式促进技术进步等问题。结果表明,优势企业采取的面向产品服务化和面向客户服务化战略均能有效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具体而言,面向产品服务化战略主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小。而面向客户服务化战略,虽然能有效带动行业整体技术创新效果,但投入服务要素本身的特点对企业自身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可能会弱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胡昭玲等(2017)[24]的研究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可通过技术创新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高端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远大于低端服务化。
四、企业特色选择
企业是市场中最具活力的主体之一,区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企业优势发展。国内学者对企业特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导向评价、影响因素识别和“专精特新”策略三个方面。
(一)特色导向评价
由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多源性,企业竞争优势的度量一直充满争议。汪金祥等(2014)[26]将企业竞争优势划分为成长性、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并使用这三种不同指标度量企业竞争优势。结果表明,不同发展目标企业可依赖的竞争优势皆有所不同。成长性企业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扩充现金持有量和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竞争优势;以获取创新综合优势为目标的企业可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产品差异化战略和提升品牌商誉等提高优势;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可通过成长性企业和获取综合优势企业采取的所有五类措施提高竞争优势。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迫切需要评价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制造企业发展状况,其中以小巨人企业、“隐性冠军”企业较具代表性。孟祥芳和夏来保(2015)[27]首先界定了“小巨人”企业的概念,采用BSC 方法和AHP方法设计了“小巨人”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天津市装备制造企业对指标的适用性进行验证,为开展“小巨人”企业的评价和认定工作提供了参考。沈红丽(2015)[28]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了科技“小巨人”企业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总结了科技小巨人这一类特色企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徐天舒和朱天一(2017)[29]以苏州200 家“隐性冠军”企业为样本,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和层次分析方法,提炼了“专精特新”企业的主要评价指标。
(二)影响因素识别
构建持续企业竞争优势,需识别并判断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区域软环境作为外部环境的组成部分,对企业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影响。有学者系统分析了六大区域软环境要素对企业竞争优势各要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同时,黄培伦等(2010)[30]指出,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是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前因,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对人力资本、关系资本、结构资本等要素的获取和培育。吴松强等(2018)[31]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是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变量,网络结构特征的网络稳定性、位置中心度和利用式知识搜索,均对企业竞争优势有正向影响。
赵杰等(2013)[32]进一步解释了竞争优势影响因素的分布特征。他指出,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交互影响企业竞争状态,呈现二元制结构。外生要素具有不可控性,内生要素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路径,即培育包括组织文化、互补资产和动态组织能力为基础的内生竞争要素。具体表现为:锤炼组织文化,统一企业价值观,实施长远战略;凝结互补资产,提炼组织惯例和隐性知识;提升动态组织能力,构建产业战略同盟。程仲鸣和陈荣剑(2017)[33]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竞争优势的影响,发现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存在倒U 型关系。同时,市场机遇、企业家才能、产品、资源和资源交换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获得竞争优势的五个关键要素。
(三)“专精特新”策略
面对“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专精特新”战略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专精特新”是一种发展理念和模式,其强调企业在用人结构、机制创新、新兴业态等方面进行差异化发展。其基本特征是:行业或产品战略专一化、研发精深化、产品或服务特色化、业态或经营模式新型化,其能在产品、技术、业态和经营方式上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建设“专精特新”型中小企业是把握中小企业中的精华和最具成长潜力的部分,发挥其在自主创新创业、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张兵等(2014)[34]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法规、战略定位、资源应用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质控能力对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管理柔性对其有一定正向影响,社会环境对其没有显著影响。佟岩和贾成龙(2015)[35]分析了政府支持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和内部资金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中小企业研发人员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也有学者通过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调研发现,中性无偏的政策支持,即强调产业政策的中性化、去地方政府化、竞争化、协调与统一的趋势,能营造更好的市场氛围,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五、述评与展望
(一)述评
从以上综述来看,关于区域制造业优势和特色发展,主要以区域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为理论依据。已有研究成果从区域、产业和企业三个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制造业优势发展进行阐述。针对区域宏观层面,研究集中在差异化能力评价、要素贡献识别以及产业集聚升级助力区域优势发展,但对区域优势发展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机理尚未找到最为贴切的理论剖析。中观层面集中在产业竞争优势依托、优势动态变迁,以及服务化转型助力产业竞争力提升。微观层面集中在特色导向评价、影响因素识别和“专精特新”策略助力企业特色发展,但产业或企业竞争优势影响因素的差异程度无法识别,无法掌握哪些具体因素对不同产业和企业的影响程度,且缺乏大量结合实地调研产业和企业的实证研究。结合新兴的智慧专业化理论和,研究区域制造业优势与特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展望
第一,完善和拓展竞争优势要素和依托对区域制造业发展的结果机制研究。现有文献研究仅仅停留在识别哪些因素会影响区域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因素对制造业发展的因果机制,研究较为松散,很少研究系统地讨论优势影响因素在宏、中和微观层面上产生的作用,而该问题的研究能够为管理实践提供实际参考。未来研究应积极探索竞争优势影响区域制造业特色发展的结果机制,系统地识别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因素作用下的差异化结果。
第二,深化智慧专业化理论的融合研究。智慧专业化理论是“欧盟2020”战略的主要框架,OECD出版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智慧专业化》将其定位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框架”,其强调区域进行优势领域定位,发挥区域和产业特色,实现区域包容性发展,这与区域制造业优势与特色发展的目标高度契合。目前中国情境下智慧专业化理论发展较为薄弱,在制造业这一重要行业的研究则更少。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智慧专业化理论,完善智慧专业化战略在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开发更多适合中国制造业特色发展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