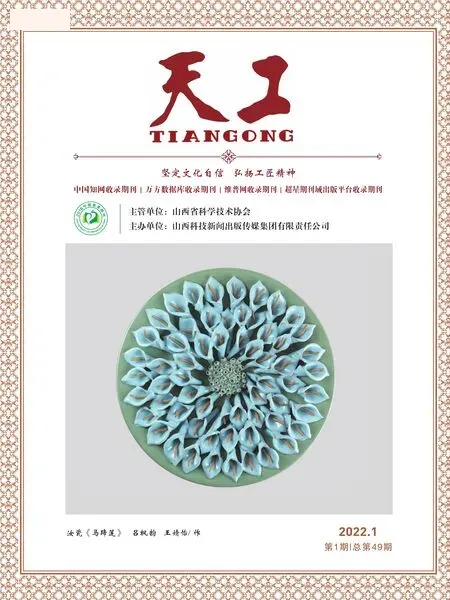禅意入瓷
——论禅宗美学对清前期陶瓷山水画的影响及二者的结合
高 颖 景德镇学院
禅宗美学对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发展影响至深,这其中包括对中国陶瓷山水画的影响,虽然并不能因此使陶瓷山水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也使得陶瓷山水画审美发展波澜起伏。陶瓷山水画发端于唐代,其后经历了非常缓慢的发展,直至晚明时期才真正兴起,而禅宗美学也开始发挥其影响力。晚明之后的整个清前期可以说是禅宗美学对陶瓷山水画影响最为显著的时期。清前期大致包括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从乾隆时期开始审美发生转变,乾隆及其后为清中后期。清前期的陶瓷山水画显著地受到禅宗美学的影响,并呈现出鲜明的契合于禅宗美学思想的意境。对清前期禅宗美学思想影响陶瓷山水画的路径和表现进行深入研究,将使我们更清晰地认知与理解清前期陶瓷山水画所体现出的审美面貌与精神。
一、“南北宗论”与清初陶瓷山水画禅意的盛行
从陶瓷史的发展来看,清前期指清顺治时期至清康熙早期。这一时期的陶瓷发展实际上是与明末时期联结在一起的,陶瓷史上将明末清初称为“转变期”。由于清初的景德镇官窑在明万历后期停产以后并没有得到恢复,因而此时仍处于民窑主导时期,是明末民窑的自然延续,二者的审美特征十分相似,这在陶瓷山水画中表现也颇为突出。因此,要研究禅宗美学对清初陶瓷山水画的影响,就必须从明末谈起。
从明前中期的情况来看,以“海浪仙山”为主要题材,满布的海浪纹和山崖构成了一种庸俗不堪的气息,与禅宗美学思想所追求的空灵简洁的意境相距甚远。从明代万历后期开始,社会逐渐陷入动乱当中,在连绵不断的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宫廷对民间的控制力不断弱化,禅宗思想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趋于活跃,特别是江南文人集团参禅之风日盛。而此时,在江南文人集团中出现了一位重要人物,即董其昌。作为禅宗虔诚信徒的董其昌,创造性地依据禅宗的南宗和北宗流派的划分,将山水画也划分为南宗和北宗,即“南北宗论”,他指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1]并且采取抑北崇南的态度,将山水画与禅宗思想直接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将禅宗的美学意境作为山水画的审美标准。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加深了禅宗思想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实际是发出了当时占中国文化艺术主流的江南文人集团共同的心声。
与此同时,景德镇瓷工也奋起抗争,发起了反抗税监潘相的暴动,直接导致官窑停产,民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迅猛扩张的明末民窑以江南文人集团为主要消费群体之一,而为迎合其审美需求,陶瓷山水画迅速崛起,并以文人审美观为核心,从而出现了显著的文人化倾向。由于明末江南文人集团普遍视禅宗美学为评判艺术境界高下的标准,“南北宗论”成为共同奉行的审美标准,因而明末以青花为主要类型的陶瓷山水画也就很自然地将禅宗美学意境作为审美发展的主流方向,并且属于董其昌所倡导的南宗画风,显现出非常浓郁的、富有文人化的禅意境界。
清初时期,虽然明朝已经灭亡,但是江南的抗清斗争却此起彼伏,江南文人士大夫群体普遍以不合作的态度对抗清廷,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出家为僧,隐逸山林,因而清初的江南明朝遗民的禅宗思想不是消退了,而是在山河破碎中进一步发展。此时,有四位僧人将禅宗思想融入中国画创作中,即“清初四僧”,画风纵横,不守绳墨,各具风采,成就卓然。他们均为明朝遗民,甚至是明廷皇族,分别是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弘仁。此时的景德镇瓷业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官窑体系还没有复兴,陶瓷山水画工匠同样感受着悲凉的亡国之痛,在延续着晚明文人禅意风格的同时,融入“清初四僧”的画风,更接近于追求清冷孤寂的禅宗美学意境,因而他们笔下的陶瓷山水画继承“南北宗论”,并与“清初四僧”画风非常相似,尤其是与弘仁的山水画风最为接近。弘仁为徽州(即新安地区)人,是新安画派的创始人,清顺治四年拜禅宗的曹洞宗大师、古航道舟禅师为师,其山水画作充满了禅意思想[2]。景德镇紧邻徽州,从事陶瓷绘画的艺人大都为徽州籍人,深受新安画派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初不少陶瓷山水画作品与弘仁山水画作颇为相近,在国破家亡的愤懑中展现出清寂空灵的禅意境界。例如,清顺治青花五彩山水盖罐上的画面一派山河破败、百木凋零之景,与弘仁山水画禅意审美境界显然是相通的(如图1)。

图1 清顺治青花五彩山水盖罐
二、“清初四王”与清康熙陶瓷山水画禅意的正统化
进入清康熙中期时,天下战乱基本平息,国家重新实现了统一,景德镇御窑厂得到重修,官窑的确立终结了民窑自由发展的时代。官窑陶瓷山水画以帝王意志为主导,而民窑则效仿官窑,从此中国陶瓷业进入清代宫廷主导时期。清康熙宫廷山水画以“清初四王”艺术风格为主导,而清康熙中晚期的陶瓷山水画则在“清初四王”的基础上,开启了陶瓷山水画新的发展篇章。
清初时期的“四僧”以禅意入画,达到非常高的艺术成就,但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以及画作中所隐含的反清意识使他们的画作不可能成为清宫山水画正统,清宫中占据山水画正统地位的则是另一个群体“清初四王”。“四王”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因四人风格相近且姓氏均为王,故而得名。实际上,“四王”与“四僧”同属于董其昌“南北宗论”的追随者,追随董其昌画风,并以宋元以降南宗山水画家为宗,只是他们并没有隐逸山林,特别是其中的王原祁还曾官至户部侍郎,为康熙帝创作了不少山水画作。“四王”和“四僧”虽均为董氏追随者,并在山水画作中多蕴禅意,但与“四僧”荒寒冷寂、空灵奇崛的禅意相比,“四王”风格则显得温柔平和、中正敦厚,也正因如此,与“四僧”相比,“四王”画风得以成为清宫山水画正统。
由于“清初四王”当时的正统地位,康熙中晚期官窑陶瓷山水画均以具有“清初四王”风格的山水画为蓝本,而民窑又效仿官窑,因此,康熙中晚期陶瓷山水画几乎完全是“四王”画风的移植和再现。例如,清康熙青花山水盖罐与“四王”山水画在构图、笔法、风格上如出一辙(如图2)。清康熙陶瓷山水画在汲取“四王”山水画风的同时,将其画作中所蕴含的禅意也一并引入作品当中,因此,康熙中晚期的陶瓷山水画同样深受禅宗美学的影响。不过,与清初陶瓷山水画效仿“四僧”风格而形成的空灵孤寂、纵横恣意的境界相比,康熙中晚期陶瓷山水画则在笔法上趋向严谨拘束,画面也较为繁复,稍显沉闷而缺乏灵动之气。

图2 清康熙青花山水盖罐
“四王”南宗山水画之所以能够入主清宫而成为山水画正统,取代了青绿山水画作为正统的地位,主要还在于康熙帝本人的审美趣味。康熙帝信奉佛教,并尊其中的喇嘛教为国教,但对禅宗也颇感兴趣,并将其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甚至几乎每天都要抄写《心经》,并曾经出资对普陀山的普济禅寺和法雨禅寺进行大力修缮,表现出对禅宗的热情与推崇。[3]与此同时,康熙帝对文化艺术亦表现出极高的热忱,对董其昌的书画作品格外器重,这也是“四王”得以成为正统的关键原因,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康熙帝与董其昌禅宗思想的相通性。康熙帝还对陶瓷艺术极度关注,亲自监督指示官窑陶瓷的制作,使之契合于自己富有禅意的审美观。也正因如此,清前期陶瓷山水画得以在康熙时期延续其禅意表达并成为审美主流。
三、“超等宗师”雍正帝与清雍正陶瓷山水画的禅意浓厚
进入清雍正时期,与清康熙帝的理性化对待佛教的态度所不同的是,雍正帝对禅宗的热爱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雍正帝自幼喜读诗书,对禅宗思想尤为感兴趣,对文人隐逸生活充满了向往。即位以后,雍正帝大力推行禅宗思想,优渥禅宗僧人,并自认为禅宗修养极高,以禅宗的“超等宗师”“人间教主”等自居。雍正帝将偌大的紫禁城当作了禅堂,而将百官当作了法友,常常宣讲禅法,并严厉打击非议禅宗的大臣,同时,他还插手全国的禅宗事务,为禅门宗派纷争定夺是非,以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显示出其文化专政的本性,这在历代帝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4]正是有了雍正帝的直接参与和管理,雍正时期的禅宗之风达到极盛,然而也因雍正帝的过度管控,导致禅宗思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与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对陶瓷艺术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直接关注并参与到皇家陶瓷的生产活动当中来,因而与清康熙时期一样,雍正时期也同样是陶瓷发展的黄金时期。从陶瓷山水画的发展来看,雍正时期的陶瓷山水画以粉彩以及珐琅彩为主导,完全颠覆了康熙时期以青花和五彩为主导的格局。粉彩、珐琅彩于康熙晚期时初创,但其真正成熟则在雍正时期,初创的康熙粉彩与珐琅彩中并没有山水题材,而在清雍正时期则出现了令人称道的粉彩、珐琅彩陶瓷山水画。在“超等宗师”雍正帝的亲自干预下,清宫珐琅彩陶瓷山水画和景德镇御窑厂粉彩陶瓷山水画得其艺术思想精髓,呈现出浓重的禅意审美风格。
清雍正时期的陶瓷山水画虽然与康熙陶瓷山水画一样具有浓厚的禅意,但是因皇帝性格特征的不同,二者显现出显著的审美差异。康熙帝具有阳刚之气,而雍正帝则具有阴柔之气,因而在构图上雍正帝并不喜康熙陶瓷山水画的顶天立地、重峦叠嶂的磅礴气势,而更倾向于山势平缓,江渚舟横的清新疏朗之景,而与此同时,雍正帝也并不喜率意粗犷之作,而更侧重于细腻内敛的笔法。例如,清雍正珐琅彩山水碗画面清丽平和、简洁荒疏,于细腻笔法中又注重水墨韵味,设色浅淡,整体呈现出柔淡纤细的阴柔美,颇清新雅致、禅意浓厚(如图3)。

图3 清雍正珐琅彩山水碗
清雍正帝的禅宗美学追求之所以能贯彻于陶瓷山水画之中,与著名督陶官唐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唐英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值养心殿,侍奉雍正帝,雍正六年时被派往景德镇担任督陶官。一方面,唐英来自清宫内廷,曾长年侍奉雍正帝左右,对雍正帝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对于雍正帝在禅宗方面的痴迷也是熟谙于心,所以能够更好地揣摩雍正帝下达的旨意,因此这个时期在陶瓷山水画创作中,既蕴含一定的宫廷青绿山水画的细腻工整,又融入水墨风格以充分迎合雍正帝的禅意喜好;另一方面,唐英本人自幼饱读诗书,对文人皆好的禅宗思想自是了然于心,身为朝廷官员,却以“陶人”自居,其本人也具有非常浓厚的禅宗思想,这在其大量留传后世的诗篇中即可窥见一斑。如他的一首《秋日偶成》诗:“宦兴天涯半未删, 半官半野半忙闲。半生鞅掌风尘吏, 半在庐山栗里间。”[5]体现出浓厚的宦隐思想,充满了禅意。正是由于对雍正帝审美思想的理解以及内心思想与禅宗的接近,唐英得以在监造陶瓷山水画时更好地将禅意融入作品中,从而使雍正陶瓷山水画成为清代陶瓷山水画发展的又一高峰。
四、禅宗美学影响下的清前期山水画审美意境
意境是中国艺术中的核心审美概念之一,它的提出与禅宗美学有着莫大的关联。意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唐代诗人王昌龄所提出来的,自“意境说”提出以后,号称“诗佛”并对禅宗思想有颇深造诣的唐代诗人王维即将意境付诸其山水画创作当中,将意境与禅境相融合,而在其后的发展中,历代文人山水画家皆将意境与禅境相结合。纵观山水画意境的发展史,可以说中国文人山水画中的意境与禅境基本上是相通的,所包含的美学追求也基本是一致的。从陶瓷山水画的发展来看,清前期之前,陶瓷山水画受到的禅宗美学影响还比较微弱,而在清前期,受到帝王及当时山水画风的影响,禅宗美学思想被大规模地融入陶瓷山水画的创作当中,从而使清前期陶瓷山水画的审美意境中包含着浓郁而丰富的禅意,与当时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意境表达并无二致。
清前期陶瓷山水画呈现出一种简约的审美意境。禅宗修行与其他宗教的修行方式不大一样,其简便易行,因此,简约是禅宗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清前期陶瓷山水画吸收了禅宗美学简约纯净的特点,在构图布局上多采用简洁疏朗的方式,在笔法运用上则简约写意,画面中的各元素描绘均不要求工细严谨,简练的线条勾勒和明快的晕染、点缀,有的作品甚至不着一树一木、一屋一宇,简洁明快,纯净自然,充满了简约的禅意境界。
清前期陶瓷山水画还呈现出一种清静的审美意境。禅宗在修行中非常注重内心的平静,认为只有在内心平静的状态下才能够不受外部世界的干扰,安心修行,禅宗修炼者多追求生活朴素,强调保持内心的清静与淡泊,清静之境亦是禅宗美学意境的重要特征之一。清前期陶瓷山水画吸收了禅宗美学对清静之境的审美追求,画面中多营造出一种恬静淡泊的审美意境,画面平淡舒缓,不以强烈的视觉效果为目的,从而带给观者一种宁静平和的审美感受。
清前期陶瓷山水画也呈现出一种冷逸之境。事实上,禅宗修行并非人们所想象的具有神秘之感,它非常讲求一种平淡之境,注重内心的清冷,以放空自我,寻求精神解脱,追求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冷逸之境。清前期陶瓷山水画汲取了禅宗美学对冷逸之境的审美追求,画面中多采用素雅的冷色调,大多表现的是一种万木萧瑟的深秋或寒冬之景,给人以一种异常清冷的感觉,而这正是禅宗美学所追求的心境表达。
五、结语
清前期是中国传统陶瓷山水画发展的巅峰时期,青花、五彩、珐琅彩、粉彩等传统陶瓷山水画的主要类型在这一时期都得到充分发展并完善。传统陶瓷山水画在清前期达到鼎盛的原因有很多,而禅宗美学融入陶瓷山水画并对其施加深刻影响是关键原因之一,正是禅意入瓷,使得此时期的陶瓷山水画在工艺与审美上都发展至新的高度。而清雍正以后,因乾隆帝喜爱奢靡华丽的艺术品,禅宗美学对陶瓷山水画的影响迅速消退,也使陶瓷山水画盛极而衰。近年来,随着陶瓷艺术界回归传统潮流,作为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一的禅宗美学重新对陶瓷艺术发挥重要影响,禅意也重新回归陶瓷山水画领域,我们看到陶瓷山水画已经开始摆脱乾隆遗风,审美品位不断得到提升,因而,就未来的发展而言,禅意入瓷仍是一个重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