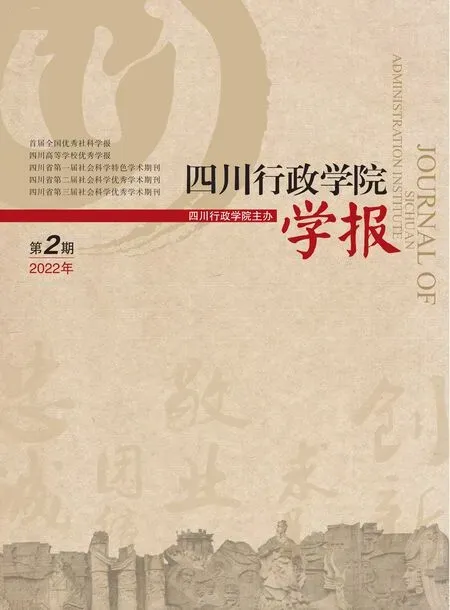数字化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问题思考
——基于浙江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的实践探索
文/缪关永(中共衢州市委党校,浙江衢州 324003)
内容提要:以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是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道路上,浙江衢州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动力,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重构,打造“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治理的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为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创新、融合、赋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为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为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从而推动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直以来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党建引领、重心下移、科技赋能,不断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随着数字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等社会新形态的不断涌现,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也得以深度重塑,革命性、系统性、全局性的变革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当下,传统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滞后化等问题在传统治理中日益显著,如何有效破解此类问题已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新课题。鉴于此,本文以衢州市“三通一智(治)”实践探索为经验基础,从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入手,寻求“以治理模式系统重构破解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优化路径。
一、文献回顾与实践评述
数字化改革是当下地方政府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衡量地方治理效能如何的重要呈现。国外学者对此侧重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理论研究,具体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公共行政学视角的数字化治理而言,数字化治理因其自组织、灵活创新和整合社会优势,能有效避免传统行政管理僵化模式所带来种种弊端,因此哈特利、马什等人提出网络治理是传统行政管理的重要补充部分,是打破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僵化的新举措。[1]基于此,盖里认为数字治理已经打破传统公共行政学视野下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元分离,形成了一种更为符合时代发展方式所需的政治化公共行政,并以数字化技术对治理进行回应性重构。[2]第二,从制度主义视角的数字化治理而言,福柯认为数字治理的多元化主体构建绝非在制度真空下产生,而是在一套新的制度视域下运行,并受其影响;[3]从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而言,数字治理有着双重价值,在克服新公共管理制度和组织上的碎片化同时,为互动模式的全面推进提供了现实依据。第三,从组织学视角的数字化治理而言,普罗文等人将数字治理分为共享参与、领导组织、行政组织等三种类型。
国内研究者更为重视微观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研究,侧重于数字化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探索研究,具体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基层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思考,学者更多围绕“思维—平台—机制”模式进行探析。李建宁认为数字思维是基础,数据平台是保障,体系机制是支撑;[4]文宏认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改革,因此需持续优化政府数据管理体制机制,提升转型实效[5];黄璜提出“平台驱动的数字政府”论,提倡数字政府建设应转向“平台驱动”模式,为决策科学化、执行高效化和监督立体化提供新动力。[6]第二,社会治理数字化重构中的技术赋能与制度重塑关联分析,孟天广在政府数字转型中提出“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向驱动能有效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构;[7]张廷君、李鹏在对数字机关事务治理模式研究中指出,数字机关事务治理是基于技术与制度不断双向调试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制度重塑。[8]第三,社会治理数字化需从数字形态生产关系本身介入,通过技术、行为、组织三个层面系统架构来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建设,[9]从而破解数字治理就是平台治理,数字治理就是技术赋能的狭义理解。基于此,“整体智治”“全域数治”等社会治理理念也得到不断提倡和拓展。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发展数字化推进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理论探索和实践指南,对此,本文将数字化社会治理理解为,社会治理通过技术手段支持,助力不同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服务集成、数据共享、要素统筹,最终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的行为模式。换而言之,数字化社会治理就是借助数字技术,创新治理机制,通过互动智慧平台,构建治理主体、治理要素、治理领域的有效协调模式。衢州市通过“三通一智(治)”平台构建运行,已较好走出一条社会治理智慧管理、智慧治理、智慧服务的新路子。
二、衢州市“三通一智(治)”实践、效应及逻辑
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线上操作平台是在衢州城市大脑2.0基础上,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领域及基层治理数智创新领域的场景应用,是以“最多跑一次”为核心目标,以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为核心业务,以“邻礼通”“村情通”“政企通”为核心架构,贯通省市“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借互联网之力,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2019年以来,衢州全面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公共服务、公共场所、社会治理等领域延伸扩展,持续发动改革的撬动裂变效应,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提质增效升级。以“邻礼通”“村情通”“政企通”为核心架构,衢州“三通一智(治)”智慧线上治理平台体系逐渐形成。
(一)“三通一智(治)”衢州实践
1.“邻礼通”衢州实践。“邻礼通”是一款定位于物业费收取、物业评价、小区网格治理为核心功能的小区综合治理线上平台,是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探索。2019年3月,基于老旧小区物业管理老大难问题,衢州市柯城区信安街道率先探索开发“未来社区”微信小程序。同年10月,在衢州市“红色物业联盟”专班的推动下,该小程序更名为“邻礼通”,并在柯城区6个街道19个小区开展试点,经过半年多的实战检验、迭代升级,于2020年5月正式向市级进行推广升级“邻礼通+红色物业联盟”模式。
2.“村情通”衢州实践。“村情通”源于衢州市基层党支部的探索创新。2016年由衢州市龙游县东华街道张王村尝试将村情民情电子化、信息化,设计开发应用“村情通”综合信息化服务管理平台;2017年,衢州市龙游县在此平台基础上进行迭代升级,全县推广;2018年,衢州市各县(市、区)在此基础上推行了本地化的“村情通”式智能平台,柯城区“点点通”、衢江区“钉格通”、江山市“一家亲”、常山县“慢城百事通”、开化县“三民工程”E掌通全部上线运行;2020年4月,衢州市按照“主题教育主阵地、乡村振兴主平台、基层治理主载体”和打造乡村振兴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系统集成平台的功能定位,将“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理念向基层延伸拓展,市县一体,在整合各地现有涉农平台的基础上,统筹开发“乡村振兴讲堂·村情通”平台。
3.“政企通”衢州实践。“政企通”是为解决疫情期间复工复产惠企政策知晓难、兑现难的“两难”问题,2020年2月,由衢州市营商办牵头搭建、信安数智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以五在线一专区”(政策在线、服务在线、监管在线、互动在线、招商在线、定制化专区)为整体架构,重点突出政策兑现、融资服务以及咨询投诉三大主体功能,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综合集成,为政企建立起更简便、快捷、高效的服务线上办事平台。
(二)“三通一智(治)”实践成效
1.“邻礼通”实践成效。截至2020年12月,“邻礼通”已经覆盖全市300多个小区,登记入驻16.2万户、涉及约40万人,入驻率95%。“邻礼通”接收的2612件报修事项全部处理完毕,其中96.9%在社区内部解决。“邻礼通”有效把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居民串联在一起,构建起点线面相结合、防管控相贯通的治理通道。
2.“村情通”实践成效。“村情通”目前已实现衢州全覆盖,实名认证用户达135.9万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共受理诉求4.9万件,回复率100%,96%以上在村内解决,实现农民办事“一机在手、一呼而应、一点就通”。推进“民主协商”,让广大村民对村级重要事项、热点问题进行表决,有效解决群众参与村务决策和监督难的问题。“村情通”将涉农补贴、村播卖货、农业技术指导项目上网公开,便于村民了解和一键申请,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
3.“政企通”实践成效。截至2020年12月,“政企通”总浏览量达503万,覆盖全市23万余家企业。通过平台累计兑现政策9.02亿元,融资贷款239.24亿元,8635家受惠主体受益,并与浙江省经信厅对接上线至企业码衢州市专区,作为衢州市特色服务,通过“亲清直通车”线上提交,线下“组团联企”工作专班,负责问题收集和交办落实的方式,收集企业诉求2730条,已解决2724条。“政企通”作为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的主平台、主抓手、主战场,推动政策在线兑付、诉求在线直达、服务在线落地,为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改革再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三)“三通一智(治)”架构逻辑
衢州市“三通一智(治)”以数字化技术为基层治理新举措,建设数字化智慧治理平台,通过城市智慧大脑实现多重数字治理体系的协同联动,实现治理单元在智慧治理平台上的公共服务生产、供给、使用、反馈等多个环节的互动交流,从而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1.架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发展为逻辑,系统重塑社会治理模式。围绕城市社区管理、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乡村振兴农村发展办事难等现实问题,衢州市坚持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坚持“制度+技术”,以打破部门界限、打破条块分割、打破信息孤岛为基本要义,打造了“邻礼通”“村情通”“政企通”“三通一智(治)”平台,从而实现资源共享、整体联动、协同服务、便民利民。“三通一智(治)”通过互联网的力量,使得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其中,既大幅度减轻基层负担,更让企业、群众办事更为便捷,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打下扎实基础。
2.架构主体:精准定位,创新引领,提升智慧治理效能。“三通一智(治)”作为政府和社会信息服务有效协调联动数字治理平台,其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各方参与其中,在信息相互联动中已构建一个网络空间、多方参与的社会命运共同体。在复杂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数字化技术赋能各参与主体的精准如何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衢州市在城市社区治理方面,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为核心,以构建红色物业联盟、“邻礼通”平台为载体,精准定位,实现了城市社区治理线上线下双互动;在企业服务方面,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以行政服务中心为线下载体,按照“机制集成、政策集成、服务集成”和数据赋能的理念,打造“政企通”企业线上办事平台;在乡村治理方面,以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乡村振兴为导向,以乡村振兴大讲堂和“村情通”互为基层服务载体,更好落实落细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
3.架构方式:服务下沉,数字赋能,助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社会公共服务从社会协同治理而言,需有效将各类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与官方链接,形成协同联动的治理格局,而以往传统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以供给者自居,由此导致“服而无所求”“服而不易享”的尴尬处境。衢州市“三通一智(治)”将公共服务进行数字化集成,从需求侧入手,全面推动数据迭代更新,同时通过“三通一智(治)”平台实现数据“跑路”替代传统的“多地跑”“跑多地”的办事模式。“三通一智(治)”社会治理的精准性、智慧性、接地气性,有效推动了数字化时代衢州市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三、数字化改革推动下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路径
与西方国家所认为数字化社会治理使得“政治与行政的二元分离”路径截然不同,较组织学视角下数字治理共享参与、领导组织、行政组织三种类型又有所突破。衢州市“三通一智(治)”社会治理体现了一种社会治理模式系统重构,着力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下沉为载体,实现政府、企业、市场、群众互为命运共同体的系统重构治理模式。
(一)价值重构,提升社会治理精准化
社会治理中政府在传统公共管理学属于权威主体,与公民、企业之间形成“命令—服从”的关系。[10]在“命令—服从”模式运行下,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社会主体的公民、企业则处于服从状态,由此形成社会治理是“自上而下”单向性,并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行为。
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新公共管理学提出政府是一个服务性“产业”,是一个以国民为顾客又关系到国家兴衰的服务性“产业”。[11]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服务型”主体,则需从曾经“命令—服从”模式演进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协调联动模式,而如何打破传统约束,科学构建高质量服务型政府也已成当下社会治理的热点话题。
服务型政府构建,形式在服务,关键在价值。对此,衢州市围绕社会服务下沉如何高效、精准,如何实现社会服务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如何深层次实现政府从“我要供给”向“要我供给”转变等问题,进行社会服务价值重构,从而构建了以“三通一智(治)”数字化平台为重要依托,以社会服务下沉为主要内容,以社区、企业、乡村参与者实际所需为基本导向,打通“自上而下”的互动渠道,打破传统“自上而下”单向的服务理念,构建社会治理更为高效、精准、满意的“上下”协调联动社会治理模式。
(二)职能重构,推进社会治理高效化
从政府社会治理而言,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是其重要职能之一。衢州市社会治理曾存在社会服务体系和机制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分散,公私部门协调难、整合难等问题,导致公共服务职能无法较好适应广大人民的根本需求。对此,职能重构成为衢州推进社会治理高效的重要因素。
衢州市“三通一智(治)”以职能重构为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对政出多门、协同不力等问题,打破层级和部门壁垒,通过服务集成、数据共享和要素统筹,构建“一网智治”治理模式,如“三通一智(治)”“政务通”将市场监管、人力社保、不动产、电力、税务等20多个部门社会服务数据打通,由此实现“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由“最多跑一次”向“不用跑”、由“企业跑”向“政府跑”转变。另一方面,以需求驱动为导向,激发基层自治,围绕深度构建“自智”协同的数字化治理模式,从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三通一智(治)”的“邻礼通”就是以基层自治为主要动力,以“红色物业联盟+小区支部党员+志愿者”的联防形式为主体,以数字积分为激励举措,从而全面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公益服务,烦琐的日常社区生活小事已从曾经的“老大难”变为当下的“邻礼睦”。“邻礼通”俨然已成为衢州市人民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为衢州不断推进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新内涵。
(三)技术重构,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治理[12]理念提出,意味着我国社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创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传统以管控为主的单一式社会管理模式已无法全面诠释当下社会发展中群众参与、多元主体、社会赋权等相关思想。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向往已从更高的物质生活需要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向同步推进,对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3]因此,利用数字技术工具提升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也已是当下发展重要之举。
衢州市“三通一智(治)”正是基于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数字平台建设推进社会治理方式革命性变革,以实现闭环管理、自动化流转、联动式协同、智慧化分析,构建了社区、企业、乡村治理需求相匹配的“三通”应用,从而推动了衢州市社会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管理手段的创新,激活了政府与企业、社区与居民、村务与村民服务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式服务网络。
综上所述,在数字化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衢州市“三通一智(治)”通过价值、职能、技术多维度的重构,实现了行政型治理向服务型转变,推动了社会治理服务供给的改革与创新,主动式、集约式和精准化的服务供给打破了传统被动式、碎片式、粗放式的服务供给,从而为全面推动衢州市市域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创了良好新局。
四、数字化改革推动下社会治理系统重构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数字改革有效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但同时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困惑和挑战。何为真正意义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数字化治理模式真的是“平台即数字,数字即平台”吗?数字化改革与“德治、法治、自治该如何协同推进,是简单在“三治”基础上叠加“智治”的“四治”模式还是其他,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出现,有待在社会治理研究中进一步厘清和解答。衢州市“三通一智(治)”创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各个领域社会治理的效能,为数字化改革推进下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供了现实借鉴。
(一)党建引领是数字化社会治理改革的核心要义
打造全方位的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需坚持党建引领,保障数字治理改革方向正确,目标明确,坚持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数字化社会治理要坚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市场协同,由此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共享社会治理数字化改革红利,实现数字化改革的最终目标。衢州市“三通一智(治)”构建也正是基于此:“邻礼通”,党建引领下的红色物业联盟;“村情通”:党委政府支持引导下的两委架构;“政企通”,党委政府发起下的企业响应。衢州市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数字化社会治理,打造如“三通一智(治)”等相关数字应用平台,从而全面提升了市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创新、融合、赋能是数字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模式重构的选择路径
相对于治理模式从线下到线上线下同步推进而言,多而散的数字化应用平台给社会治理带来便利,同时也带来了烦恼。数字化社会治理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提供治理便捷同时,更需做好平台多元化的融合治理、精准治理,由此赋能社会治理才是高效、便捷,人民更为满意的治理模式。衢州市“三通一智(治)”打造正是以“创新”“融合”“赋能”“三维一体”系统推进,围绕治理对象复杂性、差异性,创新性打造相应平台;对于“邻礼通”“村情通”“政企通”三平台“多而散”问题,进行“一智(治)”融合;随后集成服务、精准赋能现实所需,从而获得社会高度认可。
(三)行政主导转向服务优先是数字化改革下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效能的基本逻辑
推进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改革,要义在人民,核心在人民,如何提升治理精准性是数字化改革亟须破解的重要课题。数字化社会治理与传统公共治理模式下的行政服务供给有所不同,其社会治理模式重构起点是提升群众参与度、市场协同性,以及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最终构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对此,社会治理模式需由传统行政供给驱动的单向架构模式转化为人民群众实际需求驱动为主体,以行政供给为回应的互为协调的双向型架构模式。双向型架构模式的构建,能精准了解人民群众之所需,企业发展之所想,乡村振兴之所往。同时数字化治理平台流程操作相关的数字反馈信息一定程度能督促政府的社会治理行为,促使其社会治理服务向更为高效、更为让人满意方向发展。
(四)社会“智治”回归到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内在要义
数字化改革被誉为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它是从技术理性向制度理性的跨越。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中,数字化被等同于智慧化、智能化,因此较多学者提出了社会智治。从治理而言,若平台即数字,数字即智能,那么服务集成、数据共享和要素统筹的社会治理模式可谓社会智治模式。如此而言,衢州市“三通一智(治)”是衢州社会治理中的一种“智治”创新,但是对于社会治理内在要义而言,如何提升治理效能关键是治理主体是谁,治理信息源于谁,治理方式为谁服务等。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倡导要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共享,并以此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这意味着社会治理核心要义在于“自治”。
随着数字化改革不断推进,数字化技术参与社会治理越发普遍,越来越多学者及地方政府将社会治理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社会治理模式发展成为社会治理“四治”(“德治、法治、自治、智治”)模式。但是从衢州市“三通一智(治)”探索实践而言,“智治”的关键是有效激活了衢州社区、企业、乡村的“自治”热情,让更多社会群体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中,此可谓“智治”赋能于“自治”,全面提升“自治”能力,为推动衢州市域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直接动力保障。由此可知,社会治理数字化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自治”能力,而非简单的治理要素模式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