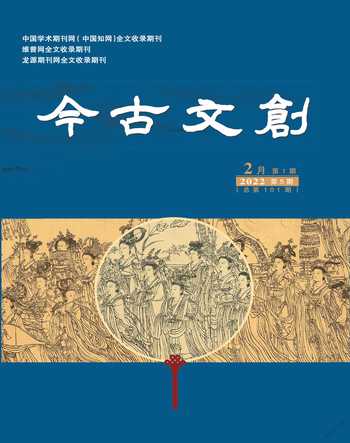浅析《我的姐姐》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王涵 李慧君
【摘要】 女性主义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在其发展到影视领域后,便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批评话语之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通过对文本与意识形态的批评,逐渐将女性“他者”的身份進行改变。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相关理论,通过对影片《我的姐姐》中女性主体形象的建构、男性形象的缺席及潜意识解读三方面的探讨,分析女性编导视角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展现女性困境的同时对女性解放前景进行展望。
【关键词】 女性形象;自我意识;男性形象;潜意识
【中图分类号】H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5-0095-03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一种说法“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性更合适”,因为男性总是“通过描写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来表达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其价值仅在于解决了将女性问题从男性话语中脱离出来的基本问题;而女性则是更为私密层面探究女性内部世界的自我挣扎,是由表层向内层的深层次发展” ①。近期上映的《我的姐姐》便是女性导演殷若昕和女性编剧游晓颖在女性的立场上深层次地探讨女性主体地位与话语的问题,其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和社会性话题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我的姐姐》讲述了生活在“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安然,因一场车祸失去了双亲,却要被迫抚养尚还年幼的“陌生”弟弟,围绕着姐姐安然亲自抚养弟弟而放弃去北京求学还是送养弟弟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这一矛盾展开,将人生经历的温馨、痛苦、迷茫与人性的复杂揭露出来,使观众收获的不仅有感动,还有随之而来的关于女性困境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以安然和姑妈为例的两个女性形象自我意识的觉醒,武东风、安子恒和父亲的男性形象的解构,以及针对安然梦境的解读三方面入手,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现代女性形象的建构、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以及在既存秩序下女性想要实现平等仍面临的困境。
一、女性主体形象的建构
在经典好莱坞叙事电影中,女人被先在地派定在绝对被动的、客体的位置上:作为男性行动的客体与男性欲望的客体。而经过20世纪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体意识逐渐树立起来,这种主体意识包括女性的社会意识与女性的自我意识。其中,女性的自我意识,指的是女性作为个体的人,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极力争取应有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从福柯那里获得启示,她们认为:话语即权力。女性要想改变“他者”的“被看”地位,就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新的真理和权力。
女性的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最好尺度。在当今中国社会,女性的权利保障程度以及女性的地位相较于之前有很大的提升,在这个倡导男女平等的时代,女性形象崛起的案例在影视领域也遍地开花。影片《狗十三》中的李玩尽管最终向父权低头,但仍在青春期的路途上向自身主体的发掘进行了挣扎;《春潮》中郭建波不依附任何男性形象,向男权社会重拳出击,体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送我上青云》中的盛男不隐晦于对于性的表达,以期实现自身主体的完整。而在《我的姐姐》中,安然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形象,不依附男友、独立清醒,有着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人生方向,即便生长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家庭里也在不断地反抗着,最终达成了自我主体意识的凸显。
影片《我的姐姐》中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以姑妈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代表着“第二性”的转变的安然这一角色。安然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为了生男孩,向街道办申请安然的残疾身份,以获得再生育的权利,而当街道办发现安然并不是残疾人之后,父亲生二胎的希望破灭,狠狠地殴打“有过失”的安然。传统的父权制度在这个家庭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就是在那时安然的自我主体意识开始慢慢地觉醒,想要摆脱家庭的束缚,自力更生。安然在影片中对于弟弟安子恒的排斥源于两方面:一是安然与弟弟没有感情基础,仿佛是两个没有关系的陌生人;另一方面则是安然潜意识里对于弟弟的存在心有不平——父母的宠爱只给了弟弟一人,她连出现在家庭合照的机会都没有。
家庭对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专制的父亲、懦弱的母亲是安然一开始对弟弟如此偏激态度的根源。原生家庭对安然的影响使她在对待弟弟时与其他“姐姐”的做法不同,也让安然在工作和感情中独当一面。面对工作上的歧视和感情上的无力,她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追逐梦想、选择结束恋爱关系。在医院,她对已有两个女儿却还冒着生命危险生儿子的孕妇怒吼:“儿子就那么好吗?”这句怒吼不仅是安然“话语”的表达、情感的宣泄,也是众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姐姐”发声口。女性主体性的建立源于社会关系中女性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女性为实现自我救赎选择走上自我意识觉醒的道路,安然便是典型的代表,她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掌握自身的命运。
除了安然这一反传统、反父权压制、反“第二性”的女性形象存在,还有与之产生对比的姑妈这一女性形象,姑妈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付出型”女性:小的时候半夜醒来听见自己的母亲只让弟弟吃西瓜却无奈接受;上学期间因家庭条件有限把继续就读的名额让给弟弟;长大后想出国创业结果被要求回来看弟弟的孩子;弟弟去世以后虽自己家庭重担很大还要再兼顾弟弟的两个孩子:安然和安子恒。在这一过程中,她或许是想过反抗的,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我是姐姐,生下来就是”的思想使她变成了一个“失语者”,只能默默接受照顾弟弟及弟弟一家的设定。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的设置:姑妈安顿好自己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照顾好安子恒入睡后,累沉沉地坐在椅子上,仰头看天花板上的水晶灯。水晶灯上已经蒙有很多灰尘,但依旧璀璨华丽。就宛若姑妈的人生,如若没有被自己的母亲要求退学让弟弟先上学,姑妈或许会就读西师俄语系,拥有一段璀璨的人生。这一场景的设置为姑妈日后自我意识的觉醒做下铺垫,此时的她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或许当时狠心反抗家庭的束缚,现在的生活会有很多的不同。姑妈的思想真正发生改变与俄罗斯套娃这一意象紧密相关,她告诉安然,“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从一开始强烈的要求安然抚养弟弟,到最后鼓励安然不要走自己的老路,做出自身的选择。这一思想上的转变寓意着姑妈最终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完成了自我主体的建构。
二、男性形象的解构与缺席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中指出:女性在电影中只作为一个能指的符号,作为男性幻想中的理想自我,电影中的男性中心人物则推动故事,男主人公控制事件、女人和情欲的凝视。且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消解了女性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与焦虑之源的双重功能所形成的困境。这种凝视、快感以男性为中心,将男性的力比多在观影过程中释放出来,消解了被阉割的焦虑。
相比于很多电影中女性形象是“在场的缺席者”,在《我的姐姐》中的男性形象大都为“缺席者”,这与近几年中国出现的女性主义电影相似:影片文本中的男性都是以女性的视角被叙述或者直接以“缺席者”的姿态出现的。例如:电影《春潮》中郭建波的爸爸始终在纪晓岚和郭建波两人的叙述中出现,所以观众对于郭建波父亲的认识是不同的,而郭晓婷的父亲直到影片结尾都不曾出现,始终是“缺席”的;《送我上青云》中刘光明、李平以及四毛的形象都具有扁平化的特征,且他们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突出主人公盛男的形象;《我的姐姐》中也是如此,武东风、安子恒以及从未出现却一直“在场”的父亲,都是将男性的形象符号化的表现,流露出女性为“发声者”的态度。
在女性导演的视角下,为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女性角色身上,防范影片中女性沦为从属角色或杜绝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她们更倾向于解构或者重建女性眼中的男性形象。殷若昕导演将影片中的男性角色重新解构,纨绔无能的舅舅、体弱不能自理的姑父、没有主见的男友、有话语权却早逝的父亲、年幼无知的弟弟,这些男性角色没有了昔日的光环,不得不依附着女性。
安然的舅舅武东风在文本中有三种角色,一是安然、安子恒姐弟的舅舅,在这一角色设定下,安然无论做什么都会得到武东风的支持和维护,安然要考研复习也有舅舅帮他照顾弟弟,尽管舅舅可能更多的是贪图房子和钱财。舅舅对安然来讲是一个温暖的形象,就好像安然在影片中说的那样:“有时候觉得舅舅更像我的爸爸”,是对武东风舅舅这一形象的肯定;第二个角色则是可可的爸爸——一个不被女儿接受的父亲形象,武东风为了见女儿偷跑去女儿工作的地方却遭到了众人的驱逐,女儿结婚时也没有邀请他。这一角色下,武东风作为一个父亲是失败的,女性不再依附男性而存在,武东风的男性形象因而被解构。除此之外,武东风还有一个隐藏角色——武东凤的弟弟。武东风没有固定的职业,天天打麻将,穿着上有一种小资本家的样子,与麻将馆的其他人格格不入。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武东风是在姐姐以及全家人的庇护下成长的,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中被惯坏的“弟弟”形象。
从武东风三个角色的剖析来看,男性在影片中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不是作为叙述主体展现“看”与“被看”的关系,更不是依据男性主体建构女性形象和意义,导演对于男性角色的设定是为了更好地突出女性的内心世界。
除了舅舅武东风的形象外,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是弟弟安子恒,初期的安子恒是叛逆、唯我独尊的,他仰仗着先前父母的溺爱,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家里的东西都是我的,你必须听我的话”,如若不是父母的离世,安子恒或许也会成长为某一个家庭中的霸权形象。但这一人物相比于老一辈的父亲和舅舅来说,他是新时代成长的男性形象,是在与女性進行情感、话语的交流而成长起来的,他的出现是对两性地位平等不失衡的充分展现,体现了导演对男女地位平等、两性个性充分展现的呼吁。
而关于父亲这个形象,影片以他的车祸、葬礼开始,他从未在影片中直接出现,相反他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是一位“缺席的在场者”。他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孩子有两种态度,对安然是经常打骂,对安子恒则过度宠爱。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对待,激发了安然内心自我意识的觉醒,让安然在经济和人格上逐渐独立。
三、创伤及被压抑的潜意识
“潜意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愿望、某种冲动或者某种幻想。这些愿望、冲动或是幻想虽然被压抑于潜意识中,但其并非是死寂状态,其会构成我们内心世界的冲突,并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左右着我们的梦和我们的内心世界” ②。梦是潜意识建构的关于欲望的满足,童年的记忆和创伤是形成梦和潜意识的重要来源。对弗洛伊德来讲,所谓释梦,是将梦作为某种欲掩盖其真相和真意的表象系统来予以分析,以发现掩藏于其下的愿望与童年的、或创伤性的记忆内容和意义。梦一旦经过释梦解析后,便成为、还原为表达多种愿望、记忆的话语结构。
影片《我的姐姐》中,安然在慢慢接受了弟弟的存在后,做了这样一个梦:童年时期的她开心地骑着单车吃雪糕,父母在她面前擦肩而过,她怎么追赶都无济于事,此时长大的她也出现在梦境里凝视着当时的自己;另一个场景里,父母与小时候的自己在游泳池里开心玩耍,长大后的安然看到这一场景也幸福地笑了,然而当童年时期的自己在水下练习憋气快要溺水时,父母在远方冷漠地注视着她而不施救,是现在的自己跳下水救了梦境里童年时期的自己。梦境的存在对于人物的成长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揭示了安然的潜意识,即:安然与父母有过美好的回忆,但父母为了有机会生二胎不惜眼睁睁地看她溺水身亡的过激场景成为了安然的噩梦。梦境中,成年后的自己跳下水去救溺水的童年自己也暗示了安然潜意识里认为只有自我主体意识强大、不依附别人后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安然梦境的出现与童年时期经历的父亲暴打她的创伤记忆紧密关联着,在得知弟弟一直备受宠爱,反观自身获得的来自父母的爱微乎其微,童年时期留下的创伤又在夜晚不受控制的无意识中爆发出来。在后续的场景中,安然打理好父亲留下的皮衣、在寺庙为父母弟弟烧香祈福、在父母墓碑前进行内心倾诉,这些都体现了安然内心里已达成与父母的和解,也流露出她想要获得父母认同的愿望。安然逐渐接受了自己在父母面前不被重视的现实,在父母墓碑面前撕掉自己的残疾证明也表明她心结终于得到纾解。安然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第二性”的角色,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心的创伤仍会在潜意识中难以消解。
四、结语
影片结尾,安然似乎与弟弟达成了和解,这一结局引发观众的热议。观众更倾向于看到姐姐送养弟弟,追逐梦想,而不是在弟弟的感化下被迫接受抚养弟弟。但是人性本来就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个体的选择永远与家庭、社会有着干系,三者的关系值得深思。作为一部女性题材的影片,《我的姐姐》由女性主导主编或许更能改变女性被看的地位,许多女性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它很好地揭示了女性所遭受的某种话语缺失、地位不平等的困境,对于女性自我意识成长与女性关于家庭与工作的自主选择提供了思考与展望。近几年,女性题材电影在中国逐渐显现并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实证明,只有部分女性觉醒向传统父权社会反抗是远不够的,在女性视角下,消解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身份,强调男女两性的同一性,而不过分削弱男性角色,高举女性大旗,置身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通过建构两性和谐关系、谋求两性共同发展来解决女性困境” ③,中国的女性主义电影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才能为中国女性寻得自我意识觉醒的道路。
注释:
①黄珞、李明德:《再现、互构、生产:中国都市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89-94页。
②陈文婷:《〈盗梦空间〉:诺兰之梦照进现实》,《名作欣赏》2015年第27期,第172-173页。
③郭丹青:《吕乐电影女性意识的嬗变与建构研究》,华侨大学2020年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张阿娇.岩井俊二电影中的女性意识研究[D].陕西科技大学,2020.
[3]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休·索海姆,索海姆,艾晓明等.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李杨.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导演在女性视角下的创作特征[D].山东大学,2015.
作者简介:
王涵,女,山东德州人,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
李慧君,女,山东寿光人,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文化与影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