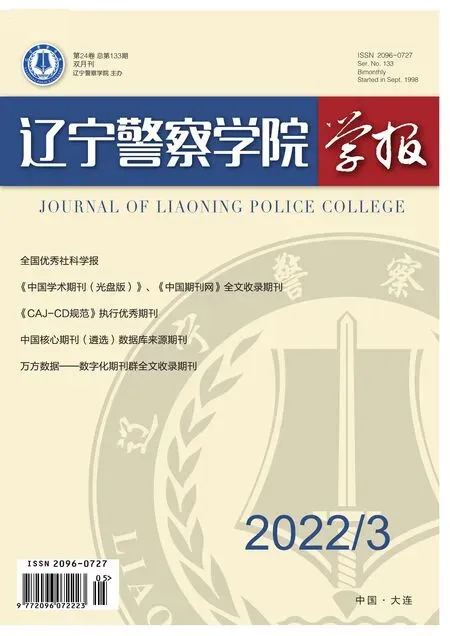韩非子法制思想实证主义分析及现代启示
王楚雅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0)
西方一些国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是问题也逐步显现。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能一味照抄西方,很多学者强调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1]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固有观念的历史渊源,可以反思一些本来无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倾向。陈金钊认为“固有的文化传统使来自西方的法理有了中国意义。人们所接受的法理学知识、原理和价值本身就是与中华文化相契合的内容,因而也是人们所能接受的东西。”[2]梁启超也曾论证传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在学习新思想、新制度时必须考虑“多世遗传共业”对国民意识的影响,所以“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针砭洗炼。”[3]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正是被多世遗传下来的共业之一,他的很多观点跨越千年,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思想。对这种传统加以识别和反思,才能更好地实现具有本土色彩的现代化法治。
一、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区分事实与价值
就目前对韩非子的研究而言,大部分是以历史学、政治学的视角展开,法学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法学研究提炼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如“务实务力社会观及其价值取向”[4]。这种研究的理由和结论无可非议,强调法要适应时代变化是韩非子反对儒家的一个有力理由。但这种思想倾向古今中外都是存在的,如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因而提炼特点的研究方式难以为实践带来启发。还有研究关注了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韩非子思想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5]但是现有研究没有对韩非子法制思想进行一个基本的区分:事实与价值。“概念分析与价值立场相联结”的研究方法有两个缺陷“削弱了权利概念的交流、媒介功能”以及“妨碍人们准确地把握权利概念的学术传统”[6]。简单来说,如果不区分事实与价值,那么采取不同价值立场的人将无法进行交流;对于没有明显价值立场的概念无法进行理解。
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来说,韩非子采取的价值立场与当今人们普遍的价值立场并不相同。韩非子的价值立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一篇给秦王的献言中,韩非子多次以“霸王之业、天下可有”来形容其理论的实践效果。韩非子的理想是否为一统天下并不确定,毕竟《初见秦》是献给秦王的文章,一统天下可能是对秦王理想的猜测,在文章中这样说可以促使秦王接受自己的谏言。对于韩非子理论的终极目的,郭沫若认为“荀子还侧重人民,韩非子则专为帝王,他们纵然有过师徒的关系,但他们的主张是成了南北两极的。”[7]宋洪兵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举《问田》中“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等为例证,认为韩非子“赋予君主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政治责任”[8]。然而这种观点仍然不够准确。韩非子确实认为法术是利民萌之道,但“四封之内,执会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职受事名曰萌”(《难一》)。也就是说,韩非子所追求的为民,不是为了每个个体的人民大众,而是由官吏掌管的民众的事务,也就是作为一个集合体的“民”。联系《难一》的上下文中“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这里不管是天下还是一国,都是一个集合体的形象。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韩非子虽然主张立君为民,同时又主张不人道的重刑思想,因为他并不重视作为个体的民。因此,笔者认为韩非子采取的价值立场是传统的集体主义,其理论的终极目标确实是在追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种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立场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并不相同,因为现代的集体主义观点大多是以个体为基础和前提的,认为每个作为个体的人都是十分重要、应当被考虑的。康德认为“每个人都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他完全不是作为手段而任由这样或那样的意志随意使用。”[9]这是现代法治区别于传统法律的根本特征,即认为每个个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或尊严。如果不区分韩非子法制思想中的事实部分和价值部分,那么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由于韩非子提出的法制服务于君主的统治,因此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内容。这种结论看不到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切断了我国当代法律与传统法律的联系,好像我国当代的法治是完全的舶来品。因此本文以法理学为视角,将韩非子所有关于“法”的论证根据两条线索进行重构:第一,他提出的法制是什么;第二,为什么应当实施这样法制。
二、对韩非子法制概念论的重构
根据历史学研究,秦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法律问答、式、例、文告;内容包括农业经济、刑罚、程序、治安等[10],这些法律体现出实证的倾向,也符合韩非子对法的定义。韩非子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定法》)。这个定义直观地指出了法是官府颁布的、适用于民众的规范,与奥斯丁提出的法律命令论有异曲同工之处,“所谓法律,就是主权者或其下的从属者所发出的,以威胁为后盾的一般命令。”[11]76命令论因不能解释现代法律多样性等缺陷已经被否定,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理论工具并结合《韩非子》的其他篇章,对韩非子的法制概念进行深入分析。
(一)法律是可化约为命令的行为规范
首先,韩非子认为法律是用来衡量事物的标准,这表示法律是作为行为规范而存在的。在《有度》中他提出“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换言之法律是用来衡量人们行为对错的标准,就像墨绳是用来衡量木头曲直的标准。而且这种行为规范普遍地适用于所有人,无论贵、智、勇、大臣、平民都不能违反法律:“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其次,认为韩非子给出的法律定义可以进一步化约为命令,主要是因为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君主对于臣民,是命令与被命令的关系:“贤者之为人臣……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世治之民……专意一行,具以待任”。这意味着,臣民对于君主所下达的行为规范,不能有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缺乏内在观点,只能静静的等待命令。而且对命令的服从是绝对的,君主提出的行为标准,不仅不能达不到,也不能超出:不当名也,害有甚于大功(《二柄》)。
(二)法律的服从以赏罚为后盾
奥斯丁认为服从法律的动机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习惯,而韩非子却给出相当不同的答案。韩非子在法的定义中强调赏罚,是因为他认为赏罚是人们服从命令的原因或动力: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赏罚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誉和毁。韩非子对服从法律的动力的判断,是基于对人性的认识,认为利弊计算、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也即所谓性恶说。所以君主掌握赏罚就可以驱使臣民: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制分》)。基于这样的论证,韩非子认为赏罚是十分有效的驱动人们服从法律的工具。在《六反》《饬令》中,这种驱使人们的方法被推理到极端的状态,比如提出重刑少赏、不要让民众过于富有否则赏会失效。除了赏罚能驱动人们服从命令之外,势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势是一个模糊的、只可意会的概念。势最开始来源于地位、可利用的资源,但是会根据赏罚的权力是否集中产生变化,权力集中威势会更大。韩非子认为人性会服从于势: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六反》)。
(三)法律是社会中唯一的行为规范
韩非子认为要实现法制,就要把法律作为社会中唯一的行为规范: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
韩非子论证这一观点的理由包括:第一,如果允许人们考虑道德等其他行为规范而违反法律,民众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对错: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饰邪》)。从而民众会对法律产生怀疑。第二,韩非子认为公私是相对的,立法就是为了存公去私。凡是不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言论、对公利没有贡献而得到的赞赏,都是匹夫之美。韩非子在《五蠹》中提到“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人们就会失去遵守法律的动力,所以私利应当被禁止。第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君主赏罚的权力和威势是人们服从法律的动力,所以韩非子特别害怕君主的权势被分散。一旦权威被分散,法律就有不再被遵守的危险,所以君主要集中赏罚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威势:威不贰错,制不共门(《有度》)。由于强调权力和威势的集中,有学者由此认为“成文法始终是为维护‘君权独尊’的地位服务的”[12]。如果从韩非子提出的法律概念的角度出发,就会对这一问题产生不同理解。因为权和势的集中并非为了讨好君主,而是命令论的法律概念所必然导致的。
(四)基于法律(命令)的法制
基于前文论述,韩非子提出的法律概念是这样的:君是立法者,臣民是服从者,臣民服从的动力是趋利避害的本性和畏惧威势的心理。为了保证法律服从的动力,必须将法律作为唯一的行为规范,并将权势集中于君主。君主的根本利益就是公利,即让国家这一集体变得更好:君之情,害国无亲(《饰邪》)。
需要补充的是,如果从对君主服从的角度来说,臣民并没有区别,那么韩非子的法制只要分成命令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两方即可。特别强调“臣”的原因在于君主不可能一个人治理国家,必然要借助臣的帮助。臣既是法律的服从者,又是法律的执行者,然而臣子并不像君主那样只有公义,“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饰邪》)。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臣子很容易分散君主的权力和威势,转化为私权和私威,从而追求自身的利益。一旦权威被分散,人们服从法律的动力就会减弱,君主就会被臣子所威胁,这也意味着公利被私利所侵害:大臣官人,与下先谋比周,虽不法行,威利在下,则主卑而大臣重矣(《诡使》)。所以为了确保臣的权威都来自于君主授予,达到有贵臣而无重臣的效果,除了用法律来治理之外君主还要使用术来锄奸。若其无法令……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问辩》);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定法》)。
加上“臣”这个要素后,韩非子的法制构想就变得复杂了。君仍是命令的发出者,但命令不再是向民面对面发出的,而是借助臣为媒介。为了保证命令的传达,君不仅要用法来规制臣的行为,还要用术来识别和铲除奸臣。“法和术的关系,是君主对官吏讲明法律,令其依法治理老百姓。君主则依靠术驾御官吏。”[13]韩非子对自己提出的法制理论非常自信。他批评儒家的贤治,认为儒家期盼的、像尧舜禹那样的贤君千世才出一个,而使用自己提出的法制,就能让占大多数的平庸君主治理好国家。
三、对韩非子法制价值论的重构
如前文所述,韩非子的终极目标是追求一个国家的强大。这种强大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这一判断从韩非子提出的措施上就可以看到:“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六反》)。要实现“天下可有”的理想,就要实现国富兵强,也就是法家一直看重的耕战。而要实现国富兵强,必须通过“民用官治”。“民用官治”描述的不仅是一个互不侵犯的有秩序的社会,而是一国之人步调统一地朝着一个目标走。换言之韩非子认为耕战是民用官治的目标,同时耕战也是实现国家强大这一终极目标的措施。最后要实现民用官治,就必须用法制:“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他虽然主张法术势的结合,但术和势是作为法的补充和辅助而存在的。[14]
首先,法律作为行为的标准具有客观性,行为是否符合标准普通人就能作出判断,君民不易被蒙骗。韩非子的思想有着务实的特点,他不仅强调以功用为目的,而且认为必须使用客观标准加以检验:不以仪的为关,则射者皆如羿也(《外储说左上》)。这种务实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韩非子法制思想对当时宽漫无边、闳大迂阔的德治思想具有纠偏作用。”[15]在《显学》中,韩非子还举出孔子、区冶、伯乐的例子,说明离开客观标准聪明人也会被骗,有了客观标准普通人也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最终得出“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的结论。而且正因为普通人也能识别客观标准,所以使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更有效率: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有度》)。
其次,法律是普遍适用的行为标准,能够达到统一臣民行为的效果。韩非子提出的法制建立在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之上。他认为像孔子、老子那样的圣人是很少的,像盗跖那样纯粹的坏人也是很少的,大多数都是普通人,而法制就是为普通人而设置,“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守道》)。因为法律是规制普通人的,所以法律的内容也是基于人的本性,不会强人所难,“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大体》)。这也是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差异,法制之下的社会是整齐平一的,甚至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平等,而儒家构想的则是有差异有等级的。[16]所以有法律就能统一人们的行为: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
最后,法制具有稳定长久的优点: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忠孝》)。韩非子在《难一》中批评管仲死前向君主献言除掉三个奸臣的做法。他认为除掉这几个奸臣,还会有其他奸臣,根本的做法是建立好的制度。没有制度而惩罚某个奸臣,就像没有目标地胡乱射箭,即使射中猎物也不能称为善射。因此,韩非子得出结论: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显学》)。
四、对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韩非子理论的重构,可以看到他对于法律作为客观标准被严格执行的强调,这是重视形式公平的体现。对形式公平的重视在我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因为我国历史上除了短暂的秦代以外,从来就不赞成严格法治,思维方式的骨子里就不讲逻辑,习惯于用整体性思考和辩证法来看待问题。”[17]因此重新关注韩非子的思想,可以矫正一些为了追求实质公平而抛弃形式公平的观点和实践,前提是对韩非子的理论进行适当的扬弃。
(一)对法律服从动力的认识
韩非子法制理论的第一个问题在于他对法律服从动力的理解。“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奸劫弑臣》)”。韩非子追求民众被迫服从法律,认为这种“不得不”的态度能够最稳定地保证法律被遵守。他不但追求被迫服从,还排斥主动遵守:“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显学》)”。因为如果民众不恃赏罚,那么他对法律是否遵守是不确定的,所以对韩非子来说自善之民是不确定因素,是要除掉的对象。“韩非子承认,极少数人可以发自内心地超越利害、追求道德,但他们是国家制度的破坏者,不应推崇。”[18]在这种法制之下,民众的形象不但愚昧,而且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愚戆窳堕之民,苦小费而忘大利也(《南面》)”,愚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利益,更无权提出异议,一切由君主替他们决定。这种错误的动力源导致韩非子的法制理论走向极端化。由于法律的服从者对法律没有内在认同,法律的实施完全依靠权和势,所以权势越大越好、越集中越好。因此韩非子的理论以及在这种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产生了许多荒谬的观点,如重刑少赏、民智不可用、连坐相告、牧臣、文学与行义无用、百姓不能过于富有等等。
对法律服从动力的理解,暗含着对服从法律的人的认识与理解。韩非子将服从者理解为基于计算的人,认为民众服从法律的动力是被动的、不得不的态度,因为经过计算服从法律是利大于弊的选择。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服从者的形象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多样。在现代社会,不管是抽象的法律法规还是具体的司法裁判结果,民众对之不仅有理解而且有评价,也就是哈特所说的内在观点,“凡规则存在之处,违反规则的行为,不仅仅构成预测敌对反应或法院制裁的基础,而且也是这种反应和制裁的理由或证立。”[11]146简单来说,很多情况下,人们服从法律不是因为预测到违法后的惩罚(当然也存在这种情况),而是因为他本身就认为行动应当符合规则,规则是行动的标准。比如红灯停的交通规则,有人基于不想被罚款的理由遵守,也有人认为“就应当这样”,后者就是内在观点。关键在于,基于内在观点的法律服从是更加稳定和长久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法律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是衡量人们法律意识的强弱,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19]这提示我们在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关注服从法律的内在观点,即重视民众对规则的认同。
(二)对规则治理的认识
韩非子主张用法律规制人们的行为,却没有将这种规制贯彻到底,导致其理论的根本目的“公利”无法实现。韩非子的理论建立在对社会的观察和对人性的判断之上,他认为社会中大部分人是普通人,普通人是有私心有欲望的,因而认为相比于德治,用法律这种客观的、外在的规范来规制臣民的行为更有效。从韩非子对法制价值的论证中可以看到,韩非子的法制与儒家的贤治针锋相对。
同样地,韩非子认为“治世者不绝于中”,然而他却没有提出用法律对君主进行规制,对立法者的行为停留在教导和劝说的层面。因为公权力集中在君主一人,所以君主成为“利害之轺毂”,也就是全国利益的中心。因此,君主要学习“术”进行自保;要时刻提防周围的人(《八奸》);不能有私心、私情和爱好(《十过》)。如果这些限制都实现,那么君主完全没有了自我,不禁让人感叹:法制与君主谁是工具?不仅如此,由于君主决定一国的方向,因此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当了解天道人情以便制定正确的法律。且不论立法者能否做到这些要求,这一立法者的形象已经与韩非子所说的“平庸的君主”大相径庭,没有外在约束的普通人是无法做到的。没能对君主提出外在限制,就无法保证立法者完全代表公利,导致韩非子“抱法处势则治”“治千而乱一”的设想无法实现。这对我们反思传统法律文化提供了另一个重要启示,限制权力的思想正是韩非子法制思想和我国法律传统所缺乏的,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