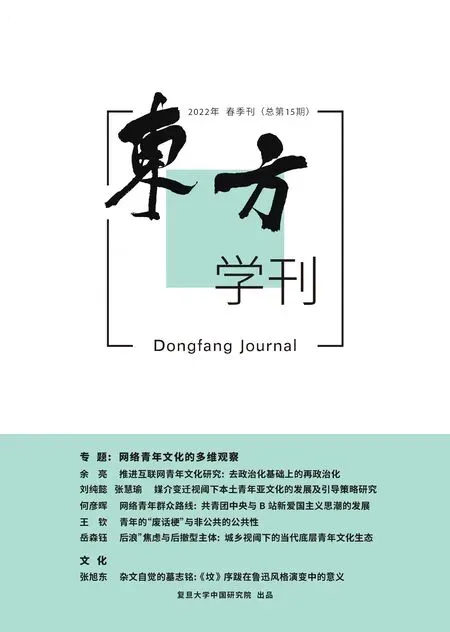媒介变迁视阈下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及引导策略研究*
刘纯懿 张慧瑜
第一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第二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青年亚文化对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是西方的“舶来品”,1980 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国内青年群体从政治青年向文化青年转变,使青年亚文化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纵观国内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发展变化,不管是从文本之内的内容、形式,还是从文本之外的生产机制、传播模式、消费方式等都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重点关注青年亚文化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下,其具体表现形式和所负载的文化意涵是如何变迁的,以及在新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网络青年亚文化又具有哪些新特征,结合这些特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引导青年亚文化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有效的公共对话和社会整合。
一、青年亚文化的历史缘起和本土语境
亚文化(subculture),从其语词构成“sub-culture”来看,就是一个以对“他者”的否定而完成反身定义“自我”的文化,具体来说,亚文化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凭借批判和反对主流文化而形成的具有自我风格和集体认同的附属性、边缘性、次要性文化。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亚文化的前缀sub 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对应。”①[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281 页。
“青年亚文化”这一概念源于芝加哥学派对青年越轨群体的研究,其面对的社会语境是在20 世纪初,美式资本主义和欧洲工业化相结合发展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径,在这条发展道路中,欧洲工业化社会所强调的共同体与美国的移民社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文化冲突,而这个冲突在芝加哥地区显得尤为典型和突出,于是青年亚文化就成了一种与主文化群体之间进行对抗和调控的文化形态。到了1960 年代,伯明翰学派取代了芝加哥学派成为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导力量,并将研究群体从芝加哥学派聚焦的“越轨群体”转变为工人阶级青年群体,并对青年群体面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霸权时的抵抗行为进行深度挖掘。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到来,青年亚文化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研究范式的创新,后亚文化理论试图突破立足于以种族、性别、阶级为框架的文化研究式的亚文化研究范式,更多从身份认同、文化资本、符号消费等方面重新刻画亚文化群体的内在动力,以及探讨与商业文化之间除抵抗之外的更多张力关系。
可见,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发展及其研究话语和框架是有其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的,也正因如此,当亚文化理论伴随着1990 年代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入中国时,用西方的亚文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的青年文化现象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实际上,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形成的时间较西方而言要晚得多,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年文化一直是作为集体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在1950 至1970 年代以人民文艺和群众文化为主基调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青年文化始终保持着和主流文化同声唱和,青年群体的主体意识也并不体现在对“主流”和“官方”的反叛与抵抗层面上,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新青年”的召唤之下生产和享用着共同的文化意涵。
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才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文化形态,然而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初现并不是一个自在和自为的过程,而是一个与大众文化发展和国外流行文化传入同步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来自欧美、日韩等的消费文化传入中国,其中包括影视、音乐、动漫、游戏等诸多内容。1980 至1990 年代,摇滚乐在我国音乐市场盛行;海外动画作品也随着电视传媒体制改革得到引进和播出;游戏厅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青年活动场所以及个人游戏机也逐渐进入了家庭空间……这些现象均构成了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最初样态。
在青年亚文化扎根中国的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关键作用。如1990 年代国内动漫杂志《画书大王》的创刊成为日本漫画传入本土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成了国内早期二次元文化群体跨地域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另外,源于日本的以动画(animation)、漫画(comic)、游戏(game)、小说(novel)为代表的ACGN 亚文化不但借由杂志和书籍等纸媒进行传播,还在电视上完成了更大范围、更广受众的扩散。同时,源自西方的带有1960 年代反文化传统的摇滚乐也在这一时期经由最早一批思想激进的青年所接受,并借助磁带、录像带、碟片等媒介将这些带有极强政治隐喻和反叛态度的摇滚音乐植入一代青年的成长历程。再加之以荧幕空间中的“都市热”和第六代导演作品中的城市边缘青年,“愤青”和“顽主”成了这一时期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脸谱化勾勒并呈现在大众媒体之上。
中国本土青年亚文化由于缺少自觉性、自发性和自主性发展的土壤,因此在亚文化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与商业、资本和官方主流话语的交织与合谋。2005 年电视综艺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这场由大众媒体造就的青年亚文化景观,为我们展现了青年群体充满个性的、极具颠覆性和反叛性的主体特点,也揭示了这种反叛性的力量如何被商业资本所利用,成为传媒集团、经纪公司和广告商进行市场扩张和资本积累的有力工具,同时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也完成了一次从“决裂”到“协商”、从“文化的垮掉”到“文化母体的揭示”的转变。青年亚文化也由此展现出与主流文化的均质化、同频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互联网时代愈发显露出来。
在传统纸媒时期,亚文化常常作为被污名化和边缘化的“他者”而存在,文字更是青年亚文化群体无法掌握的一种“权力”,大众媒体的发展给了青年亚文化自我表达的契机,即使这份表达中必然带着主流文化的规训意味。电视媒体的出现是亚文化群体的福音,音画相较于文字更易于被亚文化群体利用和接受。1990 年代的青年,借由广播、磁带、光盘、电影、电视等媒介收听或观看青年亚文化的种种文本。但是,在大众媒介时代,青年亚文化主要呈现为两个特征:一是青年更多是作为文化的接受者,很少参与到文化创作过程中;二是青年亚文化更多是作为主流文化的抵抗一方而存在,然而这些特征在互联网时代则发生了变化。
二、青年亚文化的数字化转向及其本土特征
1990 年代末到21 世纪初,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起步和发展,个人电脑进入家庭,网吧成为中下阶层青年的主要社会活动空间,青年亚文化迎来了一个较为蓬勃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呈现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织共存。第一代互联网时期的网络游戏就具有较强的外来输入性,像《红警》《反恐精英》《魔兽世界》等游戏都是以国外公司作为开发者,国内也因此涌现了一批游戏代理公司。与此同时,本土青年亚文化也呈现出一些更具本土特征的自主创作型的文化内容和形态,比如网络文学。以榕树下、红袖添香小说网、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为代表的一批文学网站成了网络小说爱好者的生产和消费聚集地。与此同时,网络论坛的出现也加速了以趣缘关系为主要连接纽带的网络文化社群。这些网络论坛成为在第一代互联网时期青少年获得身份认同和集体认同的主要空间,也成为亚文化得以传播、扩散和再创造的主要场所。
随着网络论坛的建立,一些解构、重组、拼贴主流作品的网络恶搞作品也随之兴起。2005年12 月,一个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电影短片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在这部20 分钟的短片里,创作者胡戈以电影《无极》《中国法治报道》以及上海马戏城表演的视频为素材重新剪辑加工,其网络下载率甚至超过了《无极》电影本身。除了恶搞视频,网络论坛中的一个帖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发酵成为热点事件。2009 年,百度贴吧的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引发了几十万的回帖和上千万的点击量,此后人肉搜索、网络恶搞、网络歌曲等接踵而至。孤立地看这些视频和帖子其实并不足以构成一种亚文化,但是大量网民的围观、跟帖、讨论以及大量仿制和挪用就构成了一种聚合性的亚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将网络上分散的群体迅速召唤和集结,彰显着青年们的集体创造性和对文化的解构性,同时这种解构性也具有短暂性和瞬时性的特点。
第一代互联网媒介环境所塑造的网络亚文化的特点,在新媒体时代或称Web2.0 时代得到了延续和继承,同时也有所突破和革新。延续性在于网络亚文化的拼贴、重组与解构性在媒介技术的发展之下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图像处理、视频处理软件的发展,为亚文化群体进行了技术赋能,使许多青年亚文化爱好者从最初的传播者和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和创作者。2007年和2009 年Acfun 和Bilibili 两大以“二次元文化”为主题、以“用户生产内容”为核心机制的视频网站伴随着ACGN 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和在地化发展应运而生,并开发出实时弹幕、鬼畜视频等更具有仪式狂欢性意涵的网络亚文化新形态,也正因如此,在网络亚文化的研究领域中更多展现出对“传播仪式观”理论的倾向和表达,即将传播看作“共同信念的表达”而不是“告知信息的活动”。①[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 页。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人们以更加浸入式的姿态投入网络空间,并被赋予更多的网络话语权,青年亚文化也借助新媒体的交互技术而使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活动都成为一种“仪式”,这种传播仪式观使传播主体的传受二元论因此被消解,每一个主体都是传播的平等参与者。②蔡骐、黄瑶瑛:《新媒体传播与受众参与式文化的发展》,《新闻记者》2011 年第8 期。在这种新型的文化生产机制之下,网络亚文化群体也同时拥有了另一个新的身份——“产消者”(prosumer)。生产者即是消费者是当前网络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表征,用户生产内容也被按照媒介类型、信息价值、原创程度、独立程度、作品类型等标准分类,①张小强、郭然浩:《媒介传播从受众到用户模式的转变与媒介融合》,《科技与出版》2015 年第7 期。这种在媒介融合之下从受众传播模式到用户产消模式的转变也反过来型构着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时代下的新特征,即积极受众背后的主体性以及这种主体的有限性。
至此可以看出,在青年亚文化的数字化转向和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今日语境下的亚文化切实地经历了两重“告别”。
第一重“告别”,是与文化研究占据亚文化研究主流范式时代所携带的对立结构的告别。当伯明翰学派试图借助工人阶级文化来争夺以往精英所长期霸占的文化定义权和话语场时,青年亚文化自然地同时也是历史地携带有新文化对旧文化、新权力对旧权力的抵抗和更替,在这个语境下,青年亚文化约等于工人阶级的文化,而这个背后是在英国的社会语境中特有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明的对立关系,是阶层分化极为严重情况下所产生的“highculture”和“lowculture”的泾渭分明和极端两立。然而,当青年亚文化移植至中国之后,它失去了所诞生的空间中截然二分的两种文化的对立状态,事实上,在中国历史语境下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并非截然分明和不言自明,更多情况下是存在诸多中间地带和难以言明的空间的。这也导致了中国的青年亚文化先在地失去了一种清晰可辨的反抗姿态,再加上1950 至1970年代占据社会主流文化场域的群众文艺的遗产延续,就使这种携带有特定社会结构的反抗性文化顿时失去了可参照的“他者”,因此也难以进行自我的反身定位而难免有“言之无物”之嫌。
第二重“告别”,是与传统媒介下的亚文化生产和亚文化群体组织方式的告别。在经历了1970、1980 年代文化产业化的浪潮之后,“受众”代替“大众”成了资本市场用来规避投资风险而进行精确化细分化文化产品生产的关键参照。伴随着新媒介革命和商业互联网的发展,“受众”一词逐渐被“用户”所代替。然而,“用户”这一概念并非“天然地”指向“参与者”这个单一内涵,而是具有多重分类——从文化的视角,用户可分为接受者和参与者;从经济的视角,用户可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从劳动关系的视角,用户可分为业余者和专业者。②José van Dijck,“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generated Conten”,Media,Culture &Society,2009,31(1),pp.41-58.对“用户”一词的解读很好地解释了如今网络亚文化群体的行为方式——一方面,网络亚文化群体(或称网络亚文化用户)被平等地赋予了网络主体的身份,在文化民主的互联网承诺之下自主生产内容;另一方面,以流量为准则的新媒体赋权,强化了网络亚文化群体的消费者身份,于是网络亚文化又极易被作为资本的帮凶,正如有学者所言,“其本质是商业与技术的合谋下媒介对用户的控制与宰制”③党明辉:《“流量”准则:算法机制下的新媒体赋权——基于两种对立观点形成过程的分析》,《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8 年第2 期。。
通过对今日青年亚文化的历史化、语境化、媒介化和在地化的再定位,可以看出青年亚文化早已跳脱出旧有的“抵抗-收编”范式,与此同时也不完全等同于“游牧民”“文本盗猎者”等文化民粹主义的分析。在新时代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下,一方面,网络亚文化对青年的主体认同、心理构建和基于生命周期意义上的成长经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网络亚文化又与资本、权力、政治互相勾连在一起进而成为多方力量的谈判场。因此,对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文化治理就显得极为必要,然而对网络亚文化治理路径的提出就必须建立在对新时代网络亚文化的双重面向的清晰认知之上,方能有所效用。
三、新时代网络亚文化的双重面向和治理路径
(一)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双重面向
1.消费主义面向
在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时代下,网络亚文化作为一种青年进行自我身份标榜和完成自我个性认同的文化品类很快就受到了资本与平台的注目,进而成为互联网平台用以完成平台用户积累和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细描的“文化工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以青年亚文化为题材和主要内容的网络自制综艺节目以及短视频和网络直播。
随着移动终端的市场普及和多屏互动时代的到来,腾讯、爱奇艺、优酷这三大互联网视频平台纷纷加强内容生态布局,构建自己的“互联网+文娱”产业链,其中一个动作就是平台向内容制作这个产业链的上游进行开发。纵观网络综艺近五年的发展,2017 年成为网络综艺的井喷之年,有多档以网络亚文化为主题的综艺节目,比如,以嘻哈文化为主题的《中国有嘻哈》、以粉丝文化为主题的《明日之子》、以吐槽文化为主题的《吐槽大会》等。在互联网视频平台依靠资本和技术占据综艺节目市场时,青年亚文化的意义和内涵也在被平台、资本和技术重构着,在青年的消费活动中,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脱离了小众、边缘的意味,而成了消费主义文化中最为“流行”的流行文化。
与网络综艺视频几乎同期发展的是网络直播和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天然地带有亚文化中反权威、反中心化的抵抗与反叛色彩。不管是借由直播进行传播的“草根文化”还是短视频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品类“土味文化”,都体现出一个与大都市青年具有异质性的乡土青年的形象,与前者相比,这种乡土青年的面向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具有中国经验。据2019 年快手数据研究院联合《中国青年报》发布的《2019 小镇青年报告》显示,每年约2.3 亿小镇青年活跃在快手平台,发布视频28 亿条以上,视频播放总数超过26000 亿次。①《2019 小镇青年报告:2.3 亿小镇青年的真实世界》(2019 年5 月6 日),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905/06/t20190506_32008333.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2 月20 日。当占据中国更广阔土地的“小镇青年”基于凸显个性和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渴望而生产和消费这些亚文化产品时,亚文化内容也反过来根据青年用户,诸如点击、浏览、点赞、转发、再创造的网络行为,将这种个性化的话语类型化进而成为可以进行批量复制和生产的产品进行利润的攫取。因此,在消费主义作为逻辑内核的网络亚文化中,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力量在资本与市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而对资本力量的外显化和正视就是对网络亚文化进行治理的关键一步。
2.爱国主义面向
抵抗性范式之所以无法再继续解释今日的本土网络青年亚文化,除了消费主义对这种抵抗的弱化之外,还有一个更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亚文化发展路径,那就是:中国本土的网络亚文化始终是与网络爱国主义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和媒介平台的快速发展,亚文化群体开始突破原有的小众圈层,参与到更为广泛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其中,伴随着“大国崛起”的声音和“中国经验”的传播,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网络亚文化也呈现出爱国主义的主流化倾向。比如,2015 年,改编自网络同名漫画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在网络平台播出,该动画熟练运用ACGN 的媒介和文化语法,成功地用二次元偶像询唤着作为青年亚文化个人主体的“我”和作为国家主体的“我兔”,实现了个体身份和国族身份的整合和重叠。《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作为一部军事题材的爱国主义漫画,巧妙塑造了一个具有国族身份的二次元动漫偶像,并将二次元群体和网络民族主义群体整合为一个数量庞大、持续性强的粉丝群体——“兔粉”,这一过程被研究者称为“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①林品:《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2 期。。
借助《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一个更为普遍的亚文化与爱国主义交织的脉络显影开来,即B 站从ACGN 亚文化视频平台到如今的爱国主义和左翼思潮传播主阵地的转型。B 站2020 年的跨年晚会极具代表性:晚会选择了被称为央视段子手的朱广权担任主持人;现场的交响乐团在演绎《中国军魂》之余还跨界演奏了动漫组曲;既有主旋律电视剧《亮剑》的演员出场带来“80 后”“90 后”的电视剧回忆杀,也有洛天依等二次元偶像引领亚文化的发展潮流。这场晚会获得了8000 万次的观看量,外界将其评价为“最懂年轻人的晚会”。然而,这场晚会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迎合了年轻人的喜好,而是从这种迎合的行为之中,我们可以窥见青年亚文化与爱国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相互靠拢。
(二)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治理路径
1.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鉴于中国本土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独特的爱国主义特征,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与网络青年亚文化逐渐呈现出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一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借助拼贴、鬼畜、盗猎等后现代文本生产手段表达属于“Z 世代”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也日益展现出对青年亚文化的靠拢姿态,通过更新自身话语体系来完成对青年群体的意识形态的询唤。近年来,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更新自身话语,逐渐找到了和青年沟通的新姿态。比如:央视主持人康辉以vlog 的形式拍摄习近平主席出访希腊、巴西的新闻视频;公安、消防等部门的宣传视频采用爆红的嘻哈歌曲《野狼disco》进行改编填词;《新闻联播》主持人拍摄短视频,熟练运用时下流行语传达时事热点。
其实纵观近些年共青团所开展的网络工作可以看出,官方一直致力于探索出一套符合新媒体传播特征的且与青年群体同频互动的话语体系。2016 年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布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提出要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以“智慧团建”和“青年之声”为重点,建设工作网、联系网、服务网“三网合一”的“网上共青团”,形成“互联网+共青团”格局,实现团网深度融合、团青充分互动、线上线下一体运行的指导意见。②《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国共青团》2016 年第8 期。因此,近几年共青团的青年思想宣传工作时常和粉丝文化、嘻哈文化、御宅族文化黏连在一起,以亚文化形式为“瓶”,装主流意识形态之“酒”,然而在进行形式创新之时不可一味地套用和挪用,而要注意亚文化“瓶”之本身就携带有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的“旧酒”。
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常常借用饭圈文化之势以使思想工作更广泛、更有效地抵达青年群体之中。然而,在借用流量明星和饭圈文化的过程中,官方不能只注重饭圈所外显出的传播效果,比如转发量、点赞量和评论量,而是更要注重这些传播效果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本质特征。实际上,当今本土的饭圈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承袭着日韩文化工业的特征,本土粉丝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机制也仿照着日韩的应援文化和打投逻辑。因此,当主流意识形态借助流量明星的“流量”之时,实际上挪用的是被称为“数据劳工”的饭圈粉丝的数据劳动,在上万的点赞、评论、转发背后是粉丝们为了彰显自家偶像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所进行的数据生产和传播。而由于饭圈文化是一种群际鲜明的“圈地自萌”式的网络文化,因此这种数据生产和传播往往呈现出一种“自娱自乐”的倾向,即限定在特定的粉丝群体内部而难以抵达更广大的、饭圈文化群体之外的青年受众之中。
因此,与青年对话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还要注意在借由既有亚文化的优势之时,同时思考每一种亚文化携带的潜在问题和历史语境。与其单纯照搬形式,不如自我生长。依旧拿主流意识形态和饭圈文化的结合来作为例子,单纯借用流量明星吸引青少年群体注意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度难免会落入流量之困,然而如果采撷饭圈文化中的精髓,即“为爱发电”这一特性,而弃其数据化、圈层化、对立化的弊病,则会事半功倍。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以王冰冰为代表的新青年偶像的塑造和推出。王冰冰本身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拥有长时间的从业经验并积累起令人敬佩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态度,伴随其甜美笑容的外表特征,收获了一批青少年粉丝群体的青睐,王冰冰的采访视频一度成为B 站的“流量密码”,“这周的青年大学习有王冰冰”等词条也曾登上微博热搜。可见,对王冰冰之“爱”逐渐转化为对王冰冰所参与的新闻活动的关注,也逐渐转化为对王冰冰所传达的思想、价值的认同。与流量明星的站台和宣传相比,王冰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青少年的“黏合剂”具有更加鲜活的个体形象和更加深刻的传播内容,同时也减弱了饭圈文化机制中所藏匿的危机。
2.重视新媒体传播的情绪偏向和共时语境
主流意识形态在运用亚文化语法时不仅要注意对创新形式保持警惕,还要对社交媒体的实时情绪和共时语境怀有敏感。在大众媒介转向互联网媒介的今天,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特征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中,“情绪”成为活跃在新媒体传播活动中甚至左右传播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Web2.0 时代的兴起使每个个体成为传播的重要节点,在人人都是传受一体者的变化之下,个体情绪通过网络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转化为公共情绪、社会情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有研究指出,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下,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呈现出“弱信息,强情绪;讽正面,捧负面;速度快,范围广”这三大特征。①隋岩、李燕:《论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 年第12 期。因此,在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引导和发展时,与社会情绪的同频与否往往成为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在忽视社交媒体实时传播情绪方向和共时语境的情况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和亚文化的结合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意外效果。2020 年年初,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推出虚拟偶像“红旗漫”和“江山娇”就遭到了网友的抵制,反对的声量巨大以致直接逼退虚拟偶像下架,甚至围绕“江山娇”还引发了一场以微博为主阵地、以女性生存困境为议题的社会舆论发酵。除此之外,同样在2020 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期间,在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中,官方平台给救灾挖掘机起名为“铲酱”“叉酱”“呕泥酱”并进行线上打榜活动,也遭到了网络争议和论战。这两次借用御宅族亚文化失败的案例恰恰是与社会情绪背道而驰的结果。
在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推出虚拟偶像“红旗漫”和“江山娇”之时,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是防疫女性工作人员被剃发、防疫女性生理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等新闻,因此在关于性别议题再一次成为社会热点之时,拥有性别特征的官方虚拟偶像的推出则为网络性别困境的讨论再一次增加了情绪素材,于是以“江山娇你也会来月经吗”“江山娇你也会遇到职场歧视吗”等为代表的上万造句涌来,被视为本土网络空间中的一次“MeToo 运动”。同理,在全社会初面新冠疫情之时,社会情绪正处于一种面对严肃危机时的紧绷状态,并且持有一种同仇敌忾式的抗击疫情的共同情感,更需要提及的是,在抗疫初期官方和民间本就处在一种需要调和与紧张的状态之下,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对救灾挖掘机进行御宅族式的幼化处理和饭圈应援式运营则会引起受众对官方态度的不满情绪。
由此可见,不由分说不分场合地与青年亚文化结合并不会使青年群体为此买单,相反,还可能带来主流媒体和国家机关的声望下降。事实上,不管是共青团虚拟偶像还是“铲酱、叉酱”事件,其不当之处在于一味追求文化形态上的新颖化和年轻化,而忽略了每种特定的网络青年亚文化背后特有的文化意涵,以及这种文化意涵是否可被主流意识形态借用。这就涉及对青年亚文化在地化的重视,而所谓在地化,不仅是将中国本土的文化经验囊括进去,更重要的是要将每时每刻的网络情绪走向和共时语境囊括进思想传播的考量之中,方能达到官方和民间的同频互动与情感共享。
3.增强社会共享价值和意义场域的建设
伴随着平台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受众的类型化和群体化成为各大平台将用户进行数据商品化售卖的关键一环,因此圈层传播已然成为平台主导下新媒体传播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亚文化圈子就是互联网时代下基于网络空间中人际互动而产生的超越血缘、业缘等传统关系的圈层文化,这种网络亚文化通过圈层内部成员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来塑造其文化边界和风格。由于网络亚文化形成之初是在圈层内部自发产生的,鲜有外部控制力量,因此文化模因在圈层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文化模因在亚文化圈子里意味着独特的视觉符号、语言风格和文本特征,它像某种密码成为圈内人标示身份的暗号而外人却难以知晓,因此文化模因就为不同的文化圈子划定了一条明确的边界。①胡泳、刘纯懿:《现实之镜:饭圈文化背后的社会症候》,《新闻大学》2021 年第8 期。
网络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趣缘文化,以不同的文化趣味形成了社会区隔,正如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a)在《区分》中着重论述了“趣味”是如何作为一种阶级划分的标志而存在的。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坐标场,人们拥有的资本标出了其社会空间位置,个人的资本和所在场域决定了其鉴赏趣味。在消费社会中,文化资本愈发成了标志个人社会地位和进行社会区隔的关键参数。②参阅[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而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亚文化资本”的概念。在桑顿看来,亚文化内部并非只被布尔迪厄的阶级秩序引导,而呈现出另类的亚文化资本秩序。①Sarah Thornton,Club Cultures:Music,Media,and Subcultural Capital,Hanove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6,pp.116-160.青少年通过青年亚文化完成了对父权秩序的短暂逃离,在这个过程中亚文化也进而实现了对主流文化的暂时性解绑。由此,就可以解释当前网络围绕不同文化所形成的特定话语符号,以及每一种亚文化符号对自身藩篱的捍卫和对自身文化阵地的固守,以此逃避成人世界的文化钳制,标榜自我的个性化身份。
如此形成的网络亚文化圈层化对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造成了冲击。以趣缘和圈层化为特征的网络文化机制决定了它在维护文化多元性方面、在公共领域形成理性讨论方面以及营造一个开放的网络文化氛围方面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公共性就造成了公共价值的缺失,同时也就对形成共享的社会意义、维系健康的社会情感结构带来了威胁。学者彭兰曾指出,出于抱团取暖、利益交换等因素考虑,多数个体很难完全脱离圈子存在。圈层化一方面对个体产生了各种约束,另一方面导致各种群体间的隔阂增加,公共对话与社会整合变得更为困难。②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编辑之友》2019 年第11 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不同圈层人群的交流和对话,对于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必要的,所以增强社会共享价值也意味着对公共传播重要性的强调,即多元主体在不同属性媒介构成的开放式传播网络中,围绕公共议题进行信息发布与沟通对话。
四、结语
纵观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发展,与西方亚文化不同的是:本土亚文化从未真正脱离于主流文化而独立生长,本土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从来不是单纯的反叛和抵抗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互为缠绕、互为补充和互相借重的关系。本土青年亚文化同时具有消费主义和爱国主义两大面向,因此本土青年亚文化的在地化发展需要创生出一套不同于西方亚文化的研究范式,并且总结出一套更具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本土实践经验。伴随着近五年共青团中央的网络转向和青年转向,也产生了一些借重青年亚文化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循环的有效经验,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杂糅着一些偏差和失误。在总结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结合的工作经验之下,笔者认为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依然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与此同时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意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在地化特点和网络青年的情感经验,更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网络传播环境和传播方式的新变化,从而才能突破圈层传播之下所形成的文化隔阂进而推动社会共享价值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