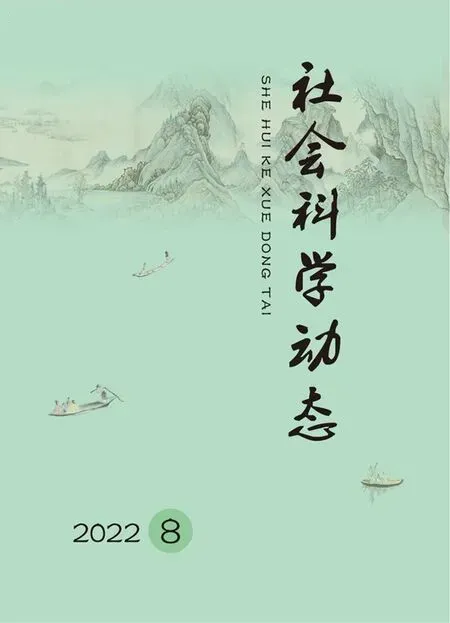《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记录》读后感
方 竹
2002年,父亲80岁,开始用电脑,南方人,“得、特”尤其“呢、勒”不分,但他想方设法学会拼音打字,上网成为他的最大快乐。
每天早起,父亲先在振动仪上站半小时,据说相当于走五公里,血液流通后开始洗漱,然后吃早饭,大约八点左右,就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神清气爽地端坐电脑前,接收邮件。与朋友联系,交流思想,是每天当务之急,然后浏览网页,迅速处理完,约早九点左右开始写文章,天天乐此不疲。其实那时他整天头痛,他笑说:“唉,浑身觉得重得不得了,换了别人,早躺下不起床了。”
询问医生,也只是说年纪大了,血管老化,拿回一大堆疏通血管的药,他认为吃了药就没事了,于是一切照旧,工作照旧,从不向人诉说病情。2003“非典”那年,父亲终于肺气肿病发作住院,他又笑说:“哎呀,平生第一次住院。”那口气仿佛旅游似的。就这次出院后,邵燕祥先生向父亲推荐了吴永平先生的文章,说是细致深入。父亲初次读过后表示果然如他所说,只凭材料说话,凭事实说话,于是很钦佩,说吴永平是胡风研究领域内第一只燕子。
以前曾有某些人不是纯粹想了解事实,对事实也不想探求,带着预设的观点而来,想套取某些更适合他预设观念的信息,完了还发文歪曲。这样的人父亲不再接待,而父亲与吴永平治学理念一致,都在切实地谈问题,不是先入为主,所以他们通信了。不巧我当时眼睛做手术,不敢看电脑,父亲也因身体越发虚弱没精力复述通信内容,我就没和父亲对此交流过。
真没想到,如今这些通信出版了,《我和舒芜先生的网聊纪录》(以下简称《网聊》)是吴永平先生写作《舒芜胡风关系史证》一书时与父亲的通信结集,于2021年9月由花木兰出版公司出版。我当然惊喜莫名,如获至宝。那些我没看到的,父亲在世最后几年,被吴永平激发而保留下来的文字、彼此交流才引发的思想、一个个问题的考证、史实逐一的筛查,那么一丝不苟,反复推敲,无数的细节需要核实,双方争分夺秒,刚回完信,新的信又来了,父亲笑着感慨:“电脑真是方便,以前邮局寄信,多则十天少则六七天,现在和吴永平有时一天往返七八个来回,能多讨论很多问题,要是过去不可想象。”
那是父亲在世最后几年最宝贵的思想啊,如今都保留在书里,打开即见,多么幸运,多么意外之喜,对我有如奇迹。
想到父亲当时身体艰难,行动不便,硬撑病体坐在电脑前打字,又看到父亲对吴永平说:“舒芜致胡风信,我已经输入电脑,略加注释,没有完工就病了。从医院回家后,恢复极慢,没有精力继续这项工作。但最近即由于与先生的通信,感到此事必须在我有生之年完成,决定立即继续工作,从目前情况看,还要努一把力才行。”我就感到一种无声中的悲壮,平凡中的无畏,它来自知识分子已融化在血液中的使命感,衰老病弱之身蕴藏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考虑安逸养生,只考虑责任、义务。而吴永平,以十年寒窗苦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整理搜集资料,详实地阅读,严格地梳理历史的各条脉络,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仁”,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学问,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浸于斯,思于斯,至死终身不渝。
吴永平的治学理念是极扎实的,他穷追每个历史细节,力求字字有来历,父亲关注事实出入与措辞分寸。这里要提一句,对父亲的意见和批注,吴永平要经过分析加材料核实才决定是否采纳,以致父亲说:“十分惊佩先生的科学精神,督促我纠正了一些推断与记忆错误,也重新肯定了一些不错的判断。”
对自己,父亲曾有一句很重的话:“对舒芜,该贬则贬,不予回护,以昭大公。”在吴永平为胡风说话时,父亲立场鲜明:“为胡风说话一处尤好,很必要。”
父亲既是当事人,又从旁观者审视者第三方的角度把握分寸。吴永平也一样,既把父亲当长者学者尊敬,又当作研究对象用事实去考量,只对其著作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双方都遵循公正严肃无我规则,这种态度下的交流就不再是简单网聊,而是严肃认真又有情怀的学术对话,这奠定了《舒芜胡风关系史证》的基调。
自接到吴永平惠赠的《网聊》,我每天就想赶快吃完饭,好踏踏实实地读,迫切想知道父亲都说了什么,吴永平回复了什么。
父亲这样评价吴永平的治学方法:
您与他们的区别,我看是在于“细读”与“粗读”的区别,其实“粗读”就是“不读”,就是不具体研究胡舒关系的实际,从抽象的“耶稣与犹大”概念出发,粗枝大叶地下结论。
粗读就是不读。
粗枝大叶地下结论。
真是言简意赅,还有点幽默,典型的父亲的语言。
和朋友提起,他大叫:“哎呀,粗读就是不读,一听就是方老的口气,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别人不会有。”他说过父亲是文体家,这就是了。我爱读父亲文字,准是开卷有益,必然开卷有益。
父亲抓住吴永平研究的最大特点“细读”,没有杂念,不受干扰,只取事实的细读;以坚韧的考证精神细读,点出做研究最重要一环。
父亲还说到另一关键:“尊作以细读胜,细读必有充分资料,此特点万不可失。”
吴永平说:“我认为研究要从最基本地方开始,史实没弄清的情况下不能进入研究阶段,着手基础工作时,考据的功夫必须下到极致。”
真是高度契合,两人都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其实,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细读”的,“细读”必要具备某些素质,才、学、识三者兼备,才能驾驭庞杂的资料,推出正确的史学结论。
在长期的资料爬梳工作中,吴永平发现,胡风早舒芜一年引舒芜信秘报中央,这是以前没任何人提过的。他还考证出:
自舒芜加入《希望》作者队伍,为《希望》贡献了七分之二稿件,使《希望》从纯文艺刊物一跃成为思想文化类刊物,大受读者欢迎,销量大增,昆明黑市以十倍价抢购。胡风借助舒芜的理论阐明自己的观点,恰恰是舒芜在《希望》发表文章,使胡风有了领袖群伦的风范。这真是新发现,用舒芜对《希望》杂志的贡献,对胡风威望提升起的作用,以此来看舒芜对胡风的重要,就纠正了许多以前想当然的说法,比如“恩师说”。
吴永平得出自己的结论——“胡风与舒芜更像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不是师生关系。”
他还依据双方全部文章,认为舒芜与胡风在文化观念、学术知识结构、学术趣味追求上均有很大差别。“舒芜的学问体系和兴趣范围不是胡风的‘文艺理论’所能范囿的。”这么看舒胡二人的分开,就是很正常的文化原因,用相互印证的材料否定了“道德说”。此观点以前也有人提及,但不像吴永平将结论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上,这就为正确认识胡风与舒芜的关系提供了有事实依据的新视角。
父亲也补充了分开的另一原因,是自从和胡风相识,发现宗派气息浓厚,问“我们是不是太孤立”,即被胡风痛批,此念只好埋藏心中,表面附和,思想并没解决。1949年后总爆发,写文还是只反宗派,确是其一贯思想。
我了解父亲,相信他的话。他认准的理论一经确定就百折不回,没想到天降大难。而一般人只知拿道德去套,就是不想真把问题弄清楚。只信“凡有错必源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必源于投机”,而拒绝从思想认识这一角度更深地探讨问题。我也试着从非亲非故的角度审视,都没看到“将叛者其辞惭”“失其守者其辞屈”的味道。
吴永平能有别于他人的,是他把材料全部摊开后细细地从中找原因,这样得出的结论,才禁得起历史的检验。
《网聊》汇集了丰富的思想史料。可以说,读了所有目前已出版的关于该冤案的文章著作后,还没机会读《史证》和《网聊》的研究者,若有机会看这两部书,会有很多意外收获,它无疑是必备参考书。
对我来说,意外收获更凝结在一些小的史实上,它们曾很让我迷茫,这回因吴永平的真诚、客观,终于让懒于澄清的父亲出面澄清了。
下面这个细节曾让我耿耿于怀:
1954年胡风在“万言书”中说:“北京打电报要他(舒芜)来北京参加讨论我的思想,他动身之前告诉人,‘北京没有办法了,我这次去是当大夫,开刀’。”
这流言一出就广为传播,我在很多人文章中见过,甚至较严肃的学者也引用,不可谓影响不大。每见此,我就心里“咯噔”一下。
结果,竟然是这样——父亲说:“这话不知从哪来的,莫名其妙。说我是‘动身之前’告诉人,那么是在南宁说的了,可是南宁谁与我谈这个呢?即使谈了,胡风又怎么知道呢?绿原说我过武汉时找曾卓谈的,我在武汉转车时间那么匆促,能找谁呢?我与绿原的关系比与曾卓的关系密切得多,绿原尚且无暇找,如何有时间找曾卓呢?此虽仅一小细节,也可见事情叙述多么出入了。”
随即查出当年日记:夜十二点半到武汉,次日早六点火车离汉去京。深更半夜,哪有时间找人,可见根本不可能有的事!
这太让我吃惊了,我一直对它将信将疑,但起码我信了一半,对父亲的不解也存在心上,没想到完全子虚乌有,手法真巧妙,两句话,一个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大显身手的打手形象就跃然纸上,形象令人侧目,编造的人真煞费苦心。不由我联想,关于舒芜的许多“定罪”,似是而非,又有几个是源于事实?
还有傅国涌的《吕荧是一面镜子》,说中国文人几十年后回顾吕荧先生当年对胡风的仗义执言,依然丑态百出:“……舒芜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称吕荧站出来‘不过是个小插曲,蛮有戏剧性的’。显然带有‘看戏’心态……”
父亲说:“我不记得在哪里向谁人说过这样的话,傅文似乎说我是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不记得谁来采访,采访记录也没给我看过……”
时间,地点,采访人都没有,就用微言大义的手法虚构。从何说起?
还有化铁说父亲1947年就对路翎和朋友们冷冷地不发一言,作协前秘书长张僖说父亲找冯雪峰汇报胡风秘密活动。结果,父亲证明全是没有的事。
是吴永平介入胡风研究,诸多精心编造的谎言才得以澄清,对我来说这种澄清事关重大。
父亲曾笑诵陆游的诗:斜阳古道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没想到今天我把它和父亲联想起来了。
父亲既是这起冤案当事人,还是学者,《网聊》里除了史料的丰富,思想的精湛,还谈为文之道,看了真让人有如步苍穹而望云霞。比如,父亲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他认为,(庄子《齐物论》)三个层次,作为言论策略,极为高明。韩愈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进学解》)其实孟子的好辩,如“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类,反给孔道带来很大损失,韩愈的卫道“人其人,火其书,盧其居”之类,更不成话也。足下以为如何?
用圣贤之道论学,真有黄钟大吕气象。
孔子“暮春者……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怡怡然。
孟子:“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令人莞尔。
从孔子读到孟子,的确从悠悠气象变成雄辩滔滔。
吴永平回复:
先生:
这样的为文之道,过去从来没听人讲过。在学校里,老师教的与这完全不同,根本就没有说过治学为文还有“存”“论”“议”这三个层次。即使听说过,当时也不一定会认为高明。
我所受的教育与先生不一样,从小接受的是崇尚斗争的教育,从会读鲁迅起,学习的也只是他的“横眉”,而不是其他。从学习古典文学起,便爱读那些“善辩”之文。从学习写文章起,讲究的就是如何把别人驳得“体无完肤”。从来没有想过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没有想过应平和地去建设什么。
看到“讲究的就是如何把别人驳得体无完肤”的文字,我笑出了声,我受的教育也是如此,写辩论文章也老琢磨着怎么把人驳得体无完肤。还羡慕有的同学那么厉害,谁都说不过她,为自己软弱不会和人斗而郁郁焉。对“存而不论,论而不议,议而不辩”更是闻所未闻。我忽若有所悟,父亲很少为自己辩护,除了记得鲁迅的“辩”本身就居于下风外,是否也遵庄子之道?
总之,《史证》与《网聊》,呈现了那么多历史真相,都在吴永平持之以恒的细读下浮现,他像史官在写史,“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迄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文心雕龙》)父亲随后病重去世,这两部书就成为对历史资料最后的搜集和抢救,其珍贵、难得、独特不言而喻。
吴永平先生与父亲共同完成了这项艰苦巨大工程,“秉笔荷担,莫此之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