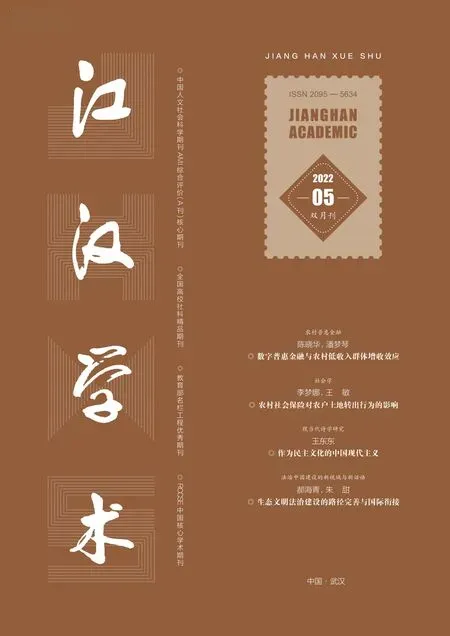中国歌剧“咏唱范式”的建构及其戏剧性因素
王 楠,徐敦广
(东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长春 130024)
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歌剧已有百年的发展历程,逐渐在外来文化的移植运用与自我文化的继承发展中形成多元、独立的文化品格。歌剧作为音乐的戏剧,演唱是其重要实现途径。在西方歌剧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咏唱”已成为表现人物情感的固定艺术样式。中国文化中“咏”的释义是“曼声长吟”,意指通过诗词来描写景物及抒发感情。随着西方歌剧文化的融入,“咏唱”在中国歌剧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曾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对某一时期某一专业做仔细的历史研究,就能发现一组反复出现而类标准式的实例,体现各种理论在其概念的、观察的和仪器的应用中。这些实例就是共同体的范式。”[1]范式是在科学实践中产生的,同时也为实践提供模型,形成一种传统,科学共同体也因此得以维系。库恩的“范式”概念首先在科学史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它将历史的维度带入科学史研究中,打破了科学研究以追求唯一正确陈述为目标的固有认识。库恩的文字有较大的阐释空间,其“范式”概念后来逐渐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并且在这些领域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
“范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也可以被引入音乐领域。音乐学家波维曾说:“当我们‘音乐学家’讨论作品时,通常指讨论乐谱。我们很少关注表演实践,更不用说围绕这创造一种新的音乐声音的表演文化了。”[2]音乐表演中的“范式”形成于集体内的某种共识,被音乐学家用于指涉“典范模式”与“范例”的意义,即由艺术家共同体构筑的文化模型。“范式”也被赋予了方法论意义,有助于音乐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演唱范式”这一概念是在歌剧创作—表演—接受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戏剧性的表现为基础,以演员的歌声为载体,以观众的认可为条件,形成了多种典范与传统。中国歌剧从诞生至今不过百年时间,有关“演唱范式”的建构一直是业内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文化命题。它打破了作品宣叙调、咏叹调、重唱与合唱等声乐体裁的限定,打破了美声、民族、民美结合、戏歌综合等唱法分类,打破了高音、中音、低音声部与抒情、戏剧、花腔等人声类型的划分,完成了从“乐谱”到“声音”的视域转换,是从表演实践出发对作品解读的新的理论模型。中国歌剧的“咏唱范式”是建立在中西音乐文化交融双重视野中的演唱范式类型,是百年发展进程中艺术家共同体对外来范式移植运用与自我文化探索挖掘的成果,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歌剧演唱艺术的主导范式。
一、中国歌剧“咏唱范式”的发展历程及其戏剧性内涵
关于“咏唱范式”的概念在此前中国歌剧的研究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但构成范式的基本要素早就存在于典型西方风格的作品之中。居其宏将中国歌剧分为民族歌剧、正歌剧、先锋歌剧、歌舞剧、歌曲剧[3]几种类型,其中将具有典型西方歌剧特征的正歌剧与先锋歌剧合称为“严肃歌剧”。这部分作品被李吉提命名为“中国西体歌剧”①,这些作品是中国歌剧“咏唱范式”得以建构的主体。姚亚平提出“戏唱式”“咏唱式”与“歌唱式”的概念,他将“咏唱式歌剧”视为具有西方化、学院气的作品:“它更接近西方歌剧本身的内在特点,更希望与国际通行的‘歌剧’这个概念靠近,考虑到的不仅仅是中国观众,也考虑中国歌剧的国际化影响。这种歌剧中,咏唱(宣叙、咏叙)性的歌唱占有更重要的位置,它一般会有意识避免太多歌曲化的唱段,与歌唱式歌剧这类更大众化、更通俗易懂的歌剧保持距离。”[4]然而,这些西体歌剧作品内部演唱形态较为复杂多样,并不能以“咏唱”单一而论;另一方面,一些走中间化发展路线的“歌唱式歌剧”也具备“咏唱”的特征因素。所以作为歌剧演唱艺术的主导范式,“咏唱范式”的实践建构和理论挖掘都成为中国歌剧亟待探索的命题。
对于任何艺术品种而言,范式的建构都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中国歌剧的“咏唱范式”历经1920 年代的黎锦晖歌舞剧、严肃歌剧《秋子》(1942 年)、《草原之歌》(1955 年)、《望夫云》(1962 年)等作品的早期探索,在1960 年代“戏唱”的辉煌和“文革”的影响下进入沉寂,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引发的歌剧观念更新中迎来复苏,诞生了如施光南的《伤逝》(1981 年)这样的经典作品。1987 年,由作曲家金湘创作、曹禺女儿万方改编,万山红、孙健、孙毅主演的歌剧《原野》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首演,并于1992 年被美国媒体评为“第一部叩开西方歌剧宫殿大门的东方歌剧”[5]。《原野》形成于“主导动机”贯穿发展的音乐结构中,通过跌宕起伏的旋律线条、张弛有序的力度变化、动静结合的节奏变化、错落有致的声部交织构成人声戏剧性张力的模式,历经多次复排成为中国西体歌剧的经典之作,为中国歌剧的“咏唱范式”建构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新时期以来,在多部西体歌剧中,“咏唱范式”得到了探索和发展,如1996 年获第六届文华作曲奖的歌剧《苍原》、2007 年的歌剧《雷雨》以及国家大剧院的多部原创歌剧作品。大部分作品采用名著或民间故事改编而成,将西方歌剧音乐与民族音乐元素相融合,探索中国歌剧与国际歌剧接轨的新样式。近年来,几部优秀剧目的出现为中国歌剧“咏唱范式”的建构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郭文景的《骆驼祥子》(2014 年)和张千一的《兰花花》(2017 年)最具代表性。这些西体歌剧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展现出极强的人文内涵,并运用戏剧化的音乐语言呈现了原著的内在意蕴,扩展了原著人文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咏唱范式”建构的典范。
显然,声乐的发声方法与演唱形式等外在因素不足以阐释“咏唱”作为范式深刻而复杂的意义内涵,而歌剧的本质是“以音乐承载戏剧”[6],戏剧性因素是“咏唱范式”得以建构的重要依托。歌剧音乐的戏剧性包括“抒情性、叙事性、冲突性”[7]三个方面。“抒情性”是纯音乐本身特有的感性特质,以长线条旋律的起伏跌宕、曲调的高低错落与乐句间的气息舒缓宽广为常见特征,带给人们梦境、幻想与憧憬,呈现出与力量相反的特点。歌剧中音乐的抒情因“符合特定人物在特定戏剧情境下特定情感状态的表现要求”[7]。歌剧音乐的叙事是戏剧的叙事,比纯器乐音乐叙事更具体,比文学叙事更直观,其叙事的手段、情节的推进与人物性格的呈现在特定的叙述结构中展开,音乐承担着叙述事实、交代动机和推进情节的戏剧功能。冲突性是狭义的戏剧性,是“歌剧音乐的旋律进行和声部交织法的方式含有明显的乃至强烈的对比和矛盾冲突,有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性,或者与人物急速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动作相吻合的那种特性”[8]。歌剧的情感推动、情节推进与冲突运行中的戏剧性因素是“咏唱”得以成为范式的原因。《原野》《骆驼祥子》《兰花花》是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歌剧作品,这三部歌剧戏剧性因素的表现较为突出,在中国歌剧“咏唱范式”的建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原野》中人物唱腔的“表情性音调”
“表情性音调”是歌剧音乐戏剧性中抒情的重要因素,是“内心活动在语音上的情绪反应”[9]。纯音乐具有表现情绪的能力,但其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具有隐喻的特征。“音乐可以展现各种力量、活力、紧张和松弛,但所有这些都只能在象征的意义上来理解。”[10]歌剧音乐中由旋律带来的情绪体验通过歌词象征意义与戏剧情节进行呼应,通过上下行、速度、力度、音色变化与人物的情绪状态和性格特征形成某种对应关系,构成人物的某种音乐性格特征和某种特定情感的外在表现形式,形成演唱中兼具音乐元素与戏剧元素的“表情性音调”。
在音乐音调与语言音调的关系问题上,卓菲娅·丽莎认为:“音乐音调并不是语言音调单纯的模仿。”[11]1980 年代也有关于音乐音调对人类基本情绪运动状态同步性的论述,认为“音乐音调完全能表现具体情感……语气与音乐音调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姐妹关系”[12]。歌剧音乐的抒情是戏剧的抒情,歌剧歌词是音乐化的剧词,音乐与歌词的联觉对应产生能够表现情感的“表情性音调”。歌唱家通过“表情性音调”把握角色的情感特质,使谱面文本得以音响化、视觉化呈现,以牵动欣赏者对音乐音响事件的期待。在威尔第的歌剧中,绝美的花腔女高音和辉煌的男高音将源自灵魂深处的力量注入歌唱之中;在普契尼的歌剧中,旋律的大线条与强力度的内化,构成倾泻的情感与迸发的冲突等强烈的戏剧张力,实现了歌声对戏剧化情感的承载和表达;瓦格纳的歌剧中,由无终旋律带来连绵不绝的声音效果,带来情感体验的震撼与升华……西方歌剧中的“咏唱”通过“表情性音调”给听者带来“期待(expectation)”:“剧中的女主角才能顺理成章地为那些本来空洞无谓的元音带来必要的意义,将角色的性格特质以及情绪氛围注入其中。”[13]这是一种对音乐事件的期待,其强于对戏剧事件的期待,构成音乐时间的延展与戏剧叙事时间的延长或暂缓,甚至是完全暂停。
首先,“表情性音调”由歌词语气与乐句的旋律走向结合而成。《原野》中焦大星的乐句以下行的旋律线为主,形成叹息语气与乐句走向的对应。咏叹调《哦,女人》中,用断续的节奏和下行乐句展现大星的失落。作曲家通过连续的上行抒展的旋律表现大星对金子热情的爱,通过连续的下行旋律带来标志性的叹息语气。模仿性的乐句构成旋律的平稳下行,用于陈述曾经美好的设想;情绪化的短语结合三连音的节奏与音程的大跳,构成语气急迫的表述。二度下行与连续的纯四度、纯五度下行旋律结合,带来速度的渐慢与力度的渐弱,用于表达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金子的音乐通过音程的大跳表现内心的激动与愤怒,表达了在封建社会压抑下人性对自由的渴望。《哦,天又黑了》中下行的旋律音调表现了低落的情绪,通过半音连接表现叹息的语调,波浪式的级进表达人物哀怨的心绪;调性色彩的变化带来情感变化,完成了从低沉向明亮的音乐色调转变。《啊,我的虎子哥》中,旋律上行大跳带动情绪的大幅度攀升,起句多组四度与七度的音程上行跳进来表现金子获得爱情的喜悦心情,大开大合的旋律线带来情感酣畅淋漓的宣泄。
第二,“表情性音调”由歌词语意与音乐节奏结合而成。当金子面对焦母的压迫表现出极强的反抗情绪,如在《你们打我吧》中,将语句动词置于节拍重音位置,快速唱出“逼”“打”“做”“偷”“养”等,表现了金子面对死亡和压迫的无所畏惧,带出了人物情绪的极致愤怒。借鉴戏曲中“紧打慢唱”的表现方式,运用三连音的节奏型打破原节奏的平衡,剧烈的节奏变化配合大跳音程,展现出毫不畏惧的呐喊。在重音推动下,休止带来突然静止,构成情绪迸发前的阻碍和准备;弱低音表达斩钉截铁的态度,最后爆发出压抑多年的怨恨与屈辱,意味着向整个封建社会的黑暗宣战。“每行音节的数量、重读的音节位置,都可以决定演唱的节奏和音乐的和声结构。”[14]歌词语意与音乐节奏之间情绪上的对应将强拍的突出性与语句重音相结合,带来动力感,激发听者心中对节奏内在律动的反应,从而引发情感的共情。“节奏正是通过戏剧动作、情节、冲突等所有这些要素来显现自身。”[15]
歌唱家的二度创作是舞台的动态文本,也是“表情性音调”在时空中赖以形成的基础,是“咏唱范式”得以建构的重要环节。以1987 年的首演版本为例,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从出场时的热情泼辣、面对爱情时的温柔缱绻到面对恶婆婆时的激烈控诉,通过其过硬的技巧和精湛的情绪把控力,展现出金子敢爱敢恨的性格,表现了封建社会压抑下人性对自由的渴望。男中音歌唱家孙健演绎出仇虎在复仇和爱情的双重抉择中复杂的内心纠葛。男高音歌唱家孙毅塑造出焦大星懦弱的形象。尤其是在三人的冲突性重唱之中,三个声部旋律与唱词交织并前后呼应,将同一时空不同角色的状态同时呈现,为戏剧矛盾的揭示带来立体化、交响化的表现,使“咏唱”在声部之间营造出强烈的悲剧氛围,将悲情复仇故事背后的人性问题以及黑暗社会对人心灵的摧残展现得淋漓尽致,引发欣赏者的怜悯与崇高的审美愉悦感。
当然,“表情性音调”不只存在于《原野》之中,《骆驼祥子》通过大跳的旋律配合直白的唱词展现虎妞豪放泼辣的性格;《兰花花》通过大跳的旋律与动力性的节奏展现兰花花的反叛精神,运用优美如歌的抒情旋律展现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定追求。这些让音乐不明确的情绪性体验转化成演唱中具体的情感体验,对人物的抒情形成范式的意义。“表情性音调”是由作曲家以情感表现为目的之创作、歌唱家以演唱经验为基础的阐发和观众以情感体验为目的之欣赏共同形成的共识与传统,在西方现代派音乐技法与民族音乐元素融合的旋律外衣和美声唱法“大开大阖”的张力审美中成为“咏唱范式”独具特色的戏剧性因素。
三、《骆驼祥子》中演唱叙事的“间离效果”
“间离”②是源于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的一种陌生化手段,指戏剧表演中运用特殊技巧展现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件,使观众对舞台表演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让观众既看戏又不完全融入剧情,消除舞台幻觉和戏剧共鸣,从而看清事物的本质,以形成清醒的认识和批判性思考。但是,相较于戏剧中文学叙事通过哲理性思考引发情感体验,歌剧更注重由直接的视听觉感受带来情感上的共鸣。歌剧中谈及“间离”更多指通过音乐的多种手段来触发观众在欣赏过程中对戏剧内涵的独立思考,让观众不断从感官体验中深入思考戏剧中蕴藏的人文精神,它同时也是歌剧叙事性的一种体现。“间离”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视听幻觉,如同传统戏曲中的程式化和虚拟化表演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当观众习惯后,它就变成了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
《骆驼祥子》是国家大剧院2014 年的原创歌剧,由郭文景作曲,徐瑛编剧,易立明导演,孙秀萎、韩蓬、宋元明等歌唱家主演。原著因其“自由”的核心观念在西方以众多英译本形式广泛传播,“正因为这种文化的‘异质性’与‘同一性’相互交融,才使文化间的传播、交流、借鉴成为可能”[16]。在改编的歌剧中,作曲家将交响音乐与老北京音乐元素结合,通过美声的咏叹调与重唱、合唱,展开多样化的立体音响,将汉语的腔调与曲艺元素融汇,打通了中西文化的审美差异,展现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他写人性的挣扎、黑暗与活泼,总会折射出某些悲剧性的光芒。”[17]在人物的演唱形态上,歌唱家通过“咏唱”与“念唱”相结合的演唱方式来塑造艺术化的舞台形象,诠释了老舍原著的悲剧美学精神。小福子以“咏唱”为主,音乐主题由民歌《小白菜》的核心音调构成。下行小三度和大二度形成五声性的哀叹旋律,描绘性的音乐表达了歌词中凄婉哀怨的情感内容,离调手法带来了和声色彩的变化,展现人物的情绪变化,营造戏剧情境。“小白菜”的音乐主题赋予小福子形象悲剧性的特质,暗示了人物的宿命,让人物经历一系列抗争之后的毁灭更具悲剧美感。虎妞与祥子的“咏唱”则穿插在“念唱”之中,在推进情节的过程中舒展情怀。歌剧中戏剧化的音乐语言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构成演唱叙事中独具特色的“间离效果”。
“间离效果”的第一个层面是人物间音乐情绪的分离。这种间离广泛存在于各种题材的歌剧重唱中,实现对同一场面、同一时空中不同人物心理状态的描述。《骆驼祥子》第三场的“勾引”情景中,虎妞的旋律起伏、强势主动,通过跳进并拉宽的旋律线展现性格的嚣张跋扈,而祥子则唯唯诺诺、躲躲闪闪,唱的内容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不是与虎妞的对话,这种“打背躬”③的技巧构成两人心理空间的各自揭示。声音强弱的力度对比展现了虎妞的进攻和祥子的躲避。祥子历经从无精打采、惊恐万分到忐忑不安的情绪转变,在几杯酒的引诱下开始动摇,极强的力度将内心的紧张推到了顶点。
第二个层面的“间离效果”表现为声乐情绪与器乐情绪的分离。大部分歌剧中器乐声部与声乐声部的情绪是一致的,呈现出对声乐声部情绪的“迎合”“衬托”和“补充”。乐队与声乐表演一起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是故事中的一员,但很多段落中声乐与器乐声部形成情绪的分离,乐队形成独立的思维,在演唱中埋下伏笔和隐患,预示着故事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命运,具有隐喻义和暗示义。音乐成为了故事的看客,成为拨弄全局的操盘手。《骆驼祥子》第五场第三曲的“结婚”中,乐队音乐与人物演唱的结合展现虎妞最初的兴奋情绪,乐队随着她的力度渐强,但小提琴却下行跳进渐弱,带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祥子的咏叹调则通过半音阶呈现出无奈的心境,与高音唢呐交替,唢呐由强到弱,衔接祥子的无奈。祥子力度渐强,刚推起的情绪被唢呐的渐弱消解,调性继续模进向下。祥子终于愤怒,乐队也随之力度渐强,二人声部汇合在对唱中。虎妞的调性是光明的大调,祥子的旋律则以不协和的和弦搭配,二人声部汇合成旋律与节奏一致的重唱。民间乐器唢呐的引入映衬了祥子的凄凉处境,使原本热闹的婚礼场面在敲锣打鼓的迎亲音乐中显得悲凉。一方面由主人公打背躬的演唱构成人物情绪的间离,另一方面唢呐与管弦乐队形成不和谐的音响对峙,表现出人声与器乐音乐情绪上的间离效果。
第三个层面的“间离效果”表现为音乐情绪与场面情绪的分离。这是由现代派音乐技法与民间音乐元素融合形成的独特的戏剧效果。在第六场“庙会”场面中,一首充满烟火气息的合唱“硬面儿饽饽年糕坨”展现出京城百姓的生活样态。中段群众以密集、重复的节奏唱出“可了劲儿吃,可了劲儿喝,可了劲儿玩儿,可了劲儿乐”,通过“吃、喝、玩、乐”重音的强调不断推动音乐高潮。合唱运用北京方言、胡同吆喝、杂技、相声贯口④等民间元素描述了热闹的民间生活情景。转调模进的手法在民族音乐元素的发展中可层层推进音乐张力,增强音乐谐谑的色彩。但乐队音乐却与群众演唱和表演的喜悦不同,营造出一种与场面氛围相反的凝重且悲壮的气氛,与场面中的群像形成情绪上的间离。色彩性场面通常用于展现轻松愉悦的民间生活,为矛盾的发展提供缓冲。音乐情绪和场面情绪的分离让人在看热闹场面时形成悲剧的预感,呼应了祥子与场面情绪的不相适应和虎妞得知刘四爷变卖车场跑路的崩溃状态。
“歌剧音乐最大限度地承载了剧本的精神内涵,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歌剧应有的意外、矛盾、冲突、消解等戏剧张力,这是该部歌剧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该剧中,每一处音乐都能找到自身的内在戏剧性意义,而非外在程式性的夸张的音响轰鸣。”[18]《骆驼祥子》中的“咏唱”不仅追求由乐队与人声交织形成外在的音响张力,更重要的是演唱叙事内在的戏剧张力。不同于原著中文字叙事的含蓄,歌剧更发挥了现代派音乐营造戏剧“间离效果”得天独厚的优势。如第三场通过表演动作与“咏唱”结合还原了“勾引”的真实情景,呈现出西方19 世纪末与20 世纪西方歌剧追求感官刺激的戏剧性特征。这种“艺术化的真实”在某种视角下具有“程式化”的表演特征,让观众不断在庞大的音响张力中产生“看戏”的审美感受。
“间离效果”同样蕴藏在众多作品的重唱之中。如《原野》中第三幕仇虎与焦母的对唱,表现为由泛调性与多调性技法形成的人物音乐情绪的分离。焦母吟诵“菩萨,菩萨,求求您,我家藏着鬼和怪……”,而仇虎用一段民歌旋律唱出心中的悲凉和冤仇,“初一十五庙(哎嘿)门(呀个)开(呀得儿喂呀),牛头马面两边排,两边排(呀哈)。”二人重唱形成“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双重调性展现出二人各自的心理和情感。作曲家张千一在谈到《兰花花》的第三幕的“入洞房”情景时,对赶羊与兰花花两人之间心态也用了“间离化”的解释,其重唱带来同一时空下不同人物心理状态的描摹,这与刻画《骆驼祥子》的“结婚”场面相似。“间离效果”这一戏剧性因素在作曲家、歌唱家与欣赏者的理解中被赋予不同于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的意义,逐渐成为对演唱叙事中音乐情绪差异性的判断和对舞台上音乐事件之间联系的认识,对“咏唱范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四、《兰花花》中冲突运行的“人声交响化”
矛盾冲突是戏剧性的核心要素。歌剧中的冲突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人物立场、阶级、观念不同引发的显而易见的外部冲突,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二是更深层的人物内心冲突,是引发外部冲突的根源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力量,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界限。歌剧中由对唱、重唱与交唱的演唱形式带来矛盾冲突的推进,其声部间交织形成的“人声交响”是“咏唱”运行冲突的重要戏剧性因素。
《兰花花》是2017 年国家大剧院的原创歌剧,由张千一作曲,赵大明编剧,陈薪伊导演,赵丽丽、薛皓垠等歌唱家主演。该剧冲突运行的“人声交响化”具有典型范式,表现为通过音乐的多声性思维构建声部间联系,形成人物内心冲突与外部冲突的交织;在多种演唱形式中运用调式、和声、复调等多种音乐技法构成声部间庞大的音响张力;通过模仿性复调表现嘈杂的人声,塑造出“乌合之众”的乡民群像。作曲家在传统民歌《兰花花》中提取核心音调作为主导动机,结合西北音乐特有的四度音程,使民歌音调成为具有符号意义的音乐语汇,通过快慢、强弱、松紧等对比形成主题音调对某种情绪的指示性意义,赋予了民歌更丰富的情感色彩。歌唱家赵丽丽对兰花花角色的诠释从最初的不屈、无奈到最后因绝望而走向死亡,将人物情感状态的心如刀割和生死两难表现得淋漓尽致。听众感受到“兰花花”民歌的影子,却不是它原本的旋律形态,这是由技法与审美转变带来的范式转向。
《兰花花》探索了民族音乐元素的戏剧化呈现与民族音乐文化的当代表达方式。分曲概念的弱化使人物演唱围绕着情节发展自然地衔接和推进,构成声乐声部间交织的冲突推进模式。全剧以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作为故事的线索,围绕兰花花与其他主要人物的关系设定了“兰花花与大”“兰花花与周老爷”“兰花花与赶羊”“大与周老爷”几组核心的矛盾冲突,通过外部冲突呈现、内外冲突交织共同推进至戏剧冲突的高潮场面,形成人声交响化的戏剧性效果。
第一幕主要呈现兰花花、骆驼子与乡民之间的外部冲突,表现自由爱情与封建观念的矛盾。合唱、重唱《赶脚的外乡人》是群像引发冲突的开始。乡民通过声部间的交错对位表达愤怒的情绪,赶羊在其中劝阻,媒婆阻拦赶羊,造成多方冲突混乱的场面调度。羽音和角音构成的简单旋律主线塑造了赶羊淳朴善良的音乐性格,男低音和男高音声部间旋律的错位营造出嘈杂且充满愤怒情绪的音响效果,大跳的旋律展现了乡民粗犷的音乐形象。突然闯入的强音“滚蛋”打破了赶羊的歌唱性旋律,形成赶羊与乡民的冲突。乡民们激动的情绪在力度上形成压倒赶羊抒情性旋律的强势气焰,进入合唱《教训他》。乡民歌唱中运用了不稳定的5/8 拍子,节奏上具有极强的进攻性,由“教训他”三个字构成的声部间交错式旋律持续推动着乡民们的愤怒。在力度到达顶点时,伴随兰花花极强的一声呐喊,《别打他》迎来全剧第一个冲突的高潮场面。众人惊讶地看着兰花花,合唱声部中兰花花的民歌旋律第一次完整再现,乡民们从故事的评判者和矛盾冲突的推动者摇身一变成为故事的看客。在领唱、重唱《要走咱们一起走》及合唱《还有王法吗》中所有主人公重唱形成了声部间的交织。“大”的旋律位于高音区,“天呐”的强音从极强的愤怒转为急促下行的反复咒骂。周老爷的旋律代表乡民在兰花花和骆驼子的旋律之间低声吟诵,赶羊四音音列的旋律重复加剧了场面的混乱,下行的羽音、角音的音程大跳和切分音的节奏表达了焦急的劝阻。兰花花与骆驼子的坚定表态后,进入乡民群情激愤的合唱,在巨大的声浪中结束第一幕。
第二幕与第三幕展现了冲突的交织。第二幕的二重唱《我(你)不嫁》爆发了兰花花与“大”激烈的冲突。“大”的念白引起“嫁与不嫁”的对立,兰花花八度的大跳渐强唱出誓死不嫁的立场,复调重唱与“大”之间形成剑拔弩张的戏剧效果。“要么死要么嫁”伴随着“大”的歌唱力度突然加强,二人在对峙中愈发激动。演唱中借鉴了戏曲的“紧打慢唱”的技法,节奏与旋律间快慢的律动与对比推动矛盾冲突进入白热化。第三幕的《累了吧》中,赶羊与兰花花随着节奏与力度的对比矛盾逐渐激化,兰花花的短促节奏昭示了惊恐,而赶羊同样快速的节奏体现出欢喜,冲突被短暂弱化。赶羊旋律的大幅度下行,直至低音区的力度渐弱。二重唱《你不明白》中兰花花与赶羊复杂内心矛盾在复调中交织。真正冲突的爆发点在于“怀上了”,节奏大幅度变化,赶羊由两个全音构成的四音音列形成急速下行的音阶,在不协和的增四度与增八度中收束,愤怒之意油然而生。兰花花的旋律与赶羊形成不协和的四度叠置的和声特征,两次重复的七度音程伴随节奏的愈发紧凑营造了张力极强的音响效果。兰花花与周老爷的对唱《你?是周老爷》中,全音呈现周老爷的阴险,二人的矛盾上升到顶点,旋律越推越高,冲突不断增强,兰花花的八度大跳从惊讶和惊恐转为愤怒,造成二人强烈的对峙。
在人物间内外冲突的层层铺排下,第四幕迎来矛盾冲突爆发的高潮场面。周老爷以全音阶上行公布真相,引发了群众的惊叹。在合唱的烘托下,“大”发出天旋地转般反复的呐喊“天呐天呐天呐”,不断下行的旋律表现了内心的崩溃。周老爷则在保持音上平稳上升,气势咄咄逼人,唱腔中的八度滑音显得阴阳怪气。赶羊强烈的愤怒与指责伴随着群众交错式的喧嚣加剧场面的混乱。随后兰花花的爱情主题与赶羊的主题音调再现,赶羊以强音下行高呼对欺骗羞辱的愤怒,在重复的语句中失望地质问苍天。音程大跳直至小字三组d,高音延长在乐队强有力地推动下形成极度崩溃的情绪宣泄,赶羊疯癫地跑下场。“大”的自言自语、周老爷的强势逼人与兰花花的满腔愤怒交织在一起,兰花花的全音下行和同音反复的全音模进爆发强烈的怒斥,“大”的全音下行带来最后的呐喊,在疯癫的“天呐”中气绝倒地。此时群像由麻木的看客变为充满人性温暖的乡亲,流露出对兰花花的悲悯。乐队半音滑奏配合唱腔中的陕北“哭音”形成内心绝望的极致表达。兰花花旋律由舒展到紧密,拉宽的全音下行宣誓对爱情坚定的信念,演唱张力犹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音程大跳形成渐强的高音延长,满腔激情喷涌而出。伴随休止的阻碍又一次蓄满力量,第二次复音程大跳形成中弱到极强的力度变化,在小字三组d 的高音延长中完成生命的绝唱。最后,合唱完整再现兰花花的民歌旋律,歌颂爱情,赞美人性,在恢弘的气势中将悲剧美感转变为震撼人心的悲壮感与崇高感,升华了作品的悲剧主题。
“大”临死前崩溃中的大喊与威尔第的《奥赛罗》中主人公昏厥时所唱“手帕”的情感表达方式极为相似,表现出人极端情绪下巨大的声音张力和情感冲击力。作曲家张千一提出:“既要用音乐完成一种中国式的表现,又要与世界歌剧舞台接轨,尤其要符合歌剧艺术规律,具有真正意义的、全方位的音乐戏剧性。”[19]从乌合之众的“乡民群像”、民歌的戏剧外延形式到主人公“发疯”时的情感状态,《兰花花》构成冲突运行的人声交响模式,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戏剧表现冲突方式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歌剧对西方大歌剧范式的追求。作品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双重视野,为中国歌剧“咏唱范式”的建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余论:中国歌剧“咏唱范式”建构的难度与可能性
“咏唱”具有对情与理、爱与恨、生与死等复杂的哲学命题深度挖掘的能力,从而也具有形成范式的典型性。新时期以来,由民间故事与文学名著改编的中国歌剧贯彻着对西方歌剧通过咏唱展现人物极致情感状态与复杂矛盾冲突的戏剧性诉求。从1980 年代的《原野》的反复重演到近年来《骆驼祥子》《兰花花》等新作品的创新探索,中国歌剧在艺术家共同体的努力下逐渐打破中西音乐的文化差异,探索了歌剧艺术与中国戏剧音乐语言融合的新方式,塑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歌剧形象,建构了以“歌声”承载戏剧的文化模型。“中国艺术强调情理交融,一方面提倡以理节情,另一方面提倡以情融理。在情与理的关系中,中国艺术较西方艺术好些,西方艺术重情而无理,中世纪重理而无情。中国艺术将二者结合,主张情理交融。”[20]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的差异使中国歌剧产生了与西方歌剧不同的情感表现方式,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了感染人心的力量,是因为主人公面对情感的复杂纠葛与生死抉择时通过“咏唱”进行了独特的中国式表达。正是中国文化中所蕴藏着的深厚能量使歌剧“咏唱”的艺术形式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中心领域具备范式建构的长足空间。
一个艺术品种范式的建构是迂回曲折的发展历程。当一部作品经历了当下的评判与历史的洗礼成为经典被留存,未来的作品方能在对原有模式的打破与创新中实现进一步探索,从而促进艺术品种的发展和繁荣。西方歌剧四百多年的辉煌依靠经典作品在世界歌剧舞台的传播,每一部经典作品无疑均兼具国际视野与民族情怀,其范式的典型性对中国原创歌剧有启发意义。在这个方面,中国歌剧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从演唱范式的建构之路可以看出,“戏唱范式”已然随着歌剧文化的时代发展走向衰落,“念唱范式”在专业圈层初现端倪,唯有“咏唱范式”在当代成为演唱范式的主导,肩负着这一文化重任。
“咏唱范式”的建构反映出中国歌剧面向世界歌剧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诉求。这种双重诉求不是简单的“国际接轨”和“民族特色”,而是以民族特性为基点,对西方歌剧文化加以学习与转化,使其与民族音乐文化、戏剧文化深层次地交融,将民族情感通过音乐的专业手段转化为戏剧化的情感,通过“咏唱”构建民族化与国际化相互依存、互相融合的文化模型。这是艺术家共同体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实践命题,也是中国歌剧“咏唱范式”建构所要长期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2018 年,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21]在“双创”强国的精神推动下,在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之中,中国歌剧正处于最好的发展阶段。不断打破常规、转化中国本土音乐资源、吸收西方歌剧优秀成果,创作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展现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扩大中国歌剧的受众范围、引领并提升观众审美是中国歌剧“咏唱范式”建构的未来趋势。
注释:
① “中国西体歌剧”作为与“民族歌剧”相对应的概念,是以西式美声唱法和管弦乐队音乐形式呈现的歌剧类型,它全方位地继承和借鉴了西方歌剧的音乐技术,采用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等多种歌剧声乐体裁,同时注重发挥交响乐队在前奏、间奏和戏剧进程中对转换时空、营造气氛、刻画人物等方面的能动性作用和音响音色优势;调式、调性、和声、复调技术的多方位展示和整体化、立体化表现的歌剧音乐类型。参见李吉提的文章《中国西体歌剧音乐创作的得与失》,刊于《中国音乐学》2021 年第2 期。
② 间离是由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创造的一个表演艺术概念。布莱希特在1936 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中国表演中的异化效应》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该词,他在文中将其描述为“演戏的方式阻碍了观众对剧中人物的简单认同”。
③ “打背躬”指剧情发展中有两人以上同时在场,其一人在暗自思考或评价对方言行时,用来表达其内心活动的唱、念或表情、身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 页。
④ “贯口”是相声中常用的手段,特点是要求多个句子一气呵成,如“报菜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