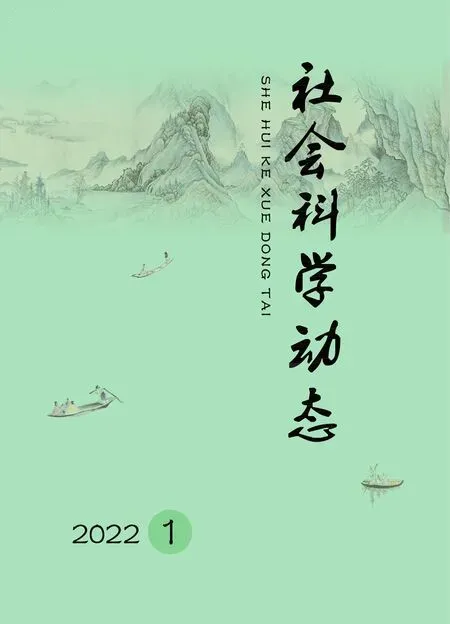《圣伯丁年代记》探析:兼论加洛林年代记的特点
陈素娟
《圣伯丁年代记》 (The Annals of St-Bertin)作为加洛林时代的代表性史书,记载了9 世纪中期以后加洛林王朝尤其是西法兰克王国的历史,内容涵盖范围从830 年到882 年,是有关9 世纪法兰克王国尤其是秃头查理统治下西法兰克王国历史的重要资料。西方历史学界对这一史料进行过大量的考证和辨析,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英国著名女历史学家简内特·L·纳尔逊 (Janet L. Nelson)教授。1986年,她发表题为 《圣伯丁年代记》的论文,从历史的角度讨论了史学界关于这一史料的争议,重新构建了历任作者尤其是普鲁登提乌斯和兴克马尔的写作背景、意图及写作特点,认为 《圣伯丁年代记》并非加洛林统治者用于政治宣传的工具,其目标读者并非同时代人,其对后世历史学家的作用远比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力更大。①此后,纳尔逊教授又发表两篇论文 《两位王子的故事:加洛林王朝年代记中的政治、文本与意识形态》与 《兰斯的兴克马尔论国王的形成:以 〈圣伯丁年代记 (861—882)〉为中心》,探讨 《圣伯丁年代记》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实践。②1992 年,纳尔逊教授将 《圣伯丁年代记》译成英文并撰写长篇序言,梳理其产生的背景、作者、内容、编著方式及版本信息,该著成为中世纪史研究者探究这部史料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西方学界受到高度评价。③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部史料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2021 年初,东北师范大学王晋新教授发表 《〈圣伯丁年代记〉探微》一文,梳理了这部史书的基本面貌,认为它是 “一部私人著述与教会著述两种特性兼具的历史文献”,并从基础性与和核心性、权威性、独特性等方面总结了其史料价值。④2021 年8 月,暨南大学李云飞教授出版 《圣伯丁年代记》中译本,介绍了这份史料的名称、作者、不同部分的特点、写作方式,探究其可信度,对不同抄本、编译本和译本予以说明,并在译著中还对 《圣伯丁年代记》做了大量的批注。⑤另外,在一些论及中世纪早期西欧史料与史学的文章和著作中,这部史料也时常被提及,如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在 《西方史学通史 (第三卷):中世纪时期 (公元5世纪至14 世纪初)》⑥一书及论文 《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形式及其价值》⑦中,将其作为加洛林时代史学的一种形式进行介绍。东北师范大学朱君杙副教授在《从王室宫廷到大主教区——论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修撰中心的转移》与 《加洛林时代历史文献的政治倾向性》文中,分析了 《圣伯丁年代记》写作地点的转移以及写作中体现出的政治倾向性。⑧
本文试在国内外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 《圣伯丁年代记》这一历史文献的书写与作者立场、宗教氛围、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论及加洛林时代年代记写作的特点,以期深入探索加洛林王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丰富对中世纪早期西欧历史的了解。
一、《圣伯丁年代记》作者与基本内容
(一)书成于众家之手
《圣伯丁年代记》因其最初版本的发现地而得名,是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 (Royal Frankish Annals)的续篇之一,与描述东法兰克王国历史的《福尔达年代记》 (The Annals of Fulda)比肩而立。其所载内容起于830 年,终于882 年,时间跨度长达52 年。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写作者先后有三位:虔诚者路易王朝宫廷牧师富尔克 (Fulco)、特鲁瓦主教普鲁登提乌斯 (Prudentius of Troyes)和兰斯大主教兴克马尔 (Hincmar of Reims)。
第一任作者富尔克写作了830—835 年间的年代记。虔诚者路易统治初年,负责年代记写作的是宫廷首席牧师希尔杜因 (Hilduin),富尔克曾在他的手下接受相关训练。830 年,一批加洛林贵族发动反对虔诚者路易的叛乱。因为支持叛乱,希尔杜因被革职,由富尔克继任为宫廷牧师,同时续写年代记。833—834 年,法兰克帝国贵族发动反对虔诚者路易的叛乱,富尔克选择效忠虔诚者路易。835年,莱姆大主教艾博因为参与叛乱被撤职并投进监狱,富尔克继任莱姆教区大主教。 《圣伯丁年代记》拉丁文版的编者列维兰结合语言风格、人名地名的使用,认为835 年是富尔克写作的截止时间。⑨纳尔逊教授认为,830—835 年间 《圣伯丁年代记》也可能并非富尔克一人所作,而是由其领导的团队完成。⑩
特鲁瓦主教普鲁登提乌斯是 《圣伯丁年代记》的第二任作者。学者们根据其语言特点与写作风格,普遍认为他写作了836—861 年间的条目。普鲁登提乌斯出身西班牙,最初作为难民来到法兰克。820 年左右,他进入虔诚者路易宫廷,接受时任梅斯大主教兼任宫廷牧师的德罗戈的委任,承担起年代记的编修任务。因为长期身居宫廷担任要职,与很多教俗贵族结交,普鲁登提乌斯掌握了绝佳的信息来源,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帝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其写作内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普鲁登提乌斯的写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围绕统治者虔诚者路易进行,记载路易的征战、功绩、与诸子的关系等;后期由于作者在政治、地理以及个人关系上远离查理宫廷,其所记述的核心内容逐渐发生转移。
兴克马尔是 《圣伯丁年代记》的第三任作者。他是西法兰克王国的超级大贵族,早年也曾在希尔杜因手下工作,后成为秃头查理的主要支持者和宫廷重臣。因为身居特殊的政治地位,兴克马尔亲自见证了西王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能够便利获得重要的国家和教会文件,其叙述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861 年,普鲁登提乌斯去世,其包括 《圣伯丁年代记》在内的个人财产被转移到秃头查理手里。兴克马尔因此获得机会, “第一次阅读普鲁登提乌斯所撰写的年代记”⑪,随后他向秃头查理借阅该书进行抄录并决定续写。学者多认为兴克马尔的写作始于862 年。针对这一看法,剑桥大学著名中世纪史教授罗莎蒙德·麦基特里克 (Rosamond Mckitterick)提出了不同看法: “虽然兰斯的兴克马尔在《圣伯丁年代记》中提及特鲁瓦的普鲁登提乌斯何时停止写作,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兴克马尔是在862 年开始写作的。”⑫关于续写 《圣伯丁年代记》的原因,纳尔逊教授认为:其一,早在跟随希尔杜因工作之时,兴克马尔应该就看过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及富尔克所作的 《圣伯丁年代记》,对于前辈所记载的岁月充满了怀旧之情;其二,兴克马尔于861 年完成两部重要的作品,续写 《圣伯丁年代记》成为其新任务。⑬
(二)基本内容
作为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续作, 《圣伯丁代记》继承了前者的写作传统,以记载 “国王的事迹”为中心,记述了830 至882 年间半个多世纪加洛林王朝的历史发展。841 年以后,主要集中记载西法兰克王国尤其是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的历史,兼及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王国的一些信息。历任统治者的更迭、国王的巡游、重大节日的庆典、大会议的召开、礼物的分发等,都是 《圣伯丁年代记》所关注的主要内容。
作为当时西欧基督教世界中心法兰克的史书,《圣伯丁年代记》也关注本国与周围异教邻国之间的关系,历任作者都颇费笔墨地记载了北欧维京人对法兰克的侵袭,以及法兰克人对此所作出的回应等。在841 年后的年代记中,只有874 和875 年的条目未曾提及维京人的活动。此外,基督教会受到《圣伯丁年代记》作者们的关注。西欧基督教会的发展,罗马教廷与法兰克君主及世俗贵族的往来,法兰克内部教区划分、教职变化及教会贵族的升迁和贬谪等,都在年代记中有所涉及,其中还保留了很多与教会事务相关的信件和文件。
可以说, 《圣伯丁年代记》既关注加洛林王朝上层的状态、政治制度的发展、政治结构的变化,也书写了包括金钱、市场、外交、船只、蜂蜡等在内的普通人日常生活。相较于以东法兰克王国为中心的 《福尔达年代记》而言, 《圣伯丁年代记》信息量更大,甚至涉及对国王统治政策的批评意见。这些宝贵的资料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西欧历史,尤其是加洛林王朝社会状况、政治发展、外交政策和教会发展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
二、《圣伯丁年代记》的写作特点
(一)当代人写当代史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年代记起源于基督教的复活节表,由撰写者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件,其写作时间常常较为接近所描述事件的发生时间,有些甚至是对同一时期事件的记载,因而具有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特点。加洛林王朝早期,通常由皇室的宫廷牧师负责收集和整理书面文件,进行年代记的编写。在交通、通讯条件极不发达的中世纪早期,这项工作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在加洛林皇室巡行制度下,统治者巡行时,其家人及宫廷官员包括宫廷牧师以及皇家档案也随之迁居。虔诚者路易从822 年开始,抛弃其父亲查理曼的传统,不再固定在亚琛过冬,而是频繁巡行。客观上,皇室活动的流动性增加了年代记作者的写作难度,他们只能主要依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他人的口述材料,进行写作。
与早期的小年代记相比较,作为大年代记代表之一的 《圣伯丁年代记》更加详细具体,对于事件的记载亦有了轻重之分,尤其对于重大事件的记载非常详尽。其记载的视界以整个加洛林宫廷和整个帝国为主,帝国分裂后则集中于西法兰克王国。843 年,普鲁登提乌斯调任特鲁瓦主教,远离秃头查理宫廷,其写作内容也不再集中于王室宫廷,而是记载作者更为熟悉的事务。兴克马尔接续后,详细记载皇室的巡游、重要节日的庆祝、大会议与宗教会议的召开、外交活动的开展,以及主要官员的升迁。其原因在于,作为西法兰克高级贵族、秃头查理的近臣及高层教士,兴克马尔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能够接近别人所无法接触的信件和文件,掌握别人无法掌握的资料,使其写作内容更加详实具体。就文本长度来说,9 世纪20 年代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每年条目大约有2.5 页,普鲁登提乌斯所著年代记中每年1.5 页,而兴克马尔写作的长度达到每年5.5 页,远超前人。⑭
(二)从宫廷著史转变为私家作品
年代记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和宗教偏见,使人们通常将其归于 “官方修史”。 《圣伯丁年代记》最初也是由法兰克国王的宫廷牧师在宫廷里完成的,但随着历史发展,其写作地点逐渐转移到宫廷之外,年代记也便逐渐从宫廷著史成为私人作品。
751 年,加洛林王朝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编写年代记传统的影响下,欧洲大陆年代记的写作逐渐流行起来。查理曼在位期间,曾经组织一个宫廷神职人员团队专门进行年代记的写作。794 年以后,亚琛逐渐成为皇室驻地,皇室宫廷也成为年代记的写作中心。虔诚者路易统治时期,宫廷皇家牧师一直负责编写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富尔克写作和普鲁登提乌斯写作的前期也都是在宫廷完成的。可以说,初期的 《圣伯丁年代记》,即便算不上是正宗的 “官方史著”,也离不开宫廷资助。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年代记的写作逐渐远离宫廷。844 年,普鲁登提乌斯升任特鲁瓦主教,其写作随之远离秃头查理宫廷。同时,普鲁登提乌斯对异端神学家哥特沙克的同情立场、与兴克马尔因为后者在特鲁瓦所拥有的教堂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使得离开查理宫廷的普鲁登提乌斯一改往日“以王室及君主为中心”的特点,更多地表达了其个人立场,甚至表露出与君主秃头查理不同的观点。例如858 年,西法兰克贵族温尼洛密谋邀请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入主西法兰克,普鲁登提乌斯就选择了支持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温尼洛。
这种个人化观点的体现,在兴克马尔的写作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或事极尽讽刺之词。例如,他曾批评图卢兹人 “一贯背信弃义”⑮;将对路易二世影响力巨大的贝加莫主教哈甘诺描述为 “既狡猾又贪婪的意大利主教”⑯;甚至在写秃头查理的妻叔康拉德伯爵时,兴克马尔也极为直白地讽刺他 “为人傲慢,对世界的了解极其肤浅。这对他本人毫无益处,对别人更没好处”。⑰对于前任作者普鲁登提乌斯,兴克马尔的评价也不高。他写到: “特鲁瓦的主教普鲁登提乌斯……因为一些痛苦事情的刺激,他坚定地维护他 (哥特沙克)的异端思想,反对先前与他们一起反对异端邪说的主教。他到死都在胡编乱造一些明显违背真理的东西。”⑱纳尔逊教授认为,兴克马尔性格中最重要的特点是评判别人的行为,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就是他引用大量 “官方”材料,也都是为了证明自身行为的合理性。⑲可以说,地理位置、宗教及政治立场以及个人情感,促使 《圣伯丁年代记》的作者们逐渐远离了当时的统治中心,继而使其写作体现出更多个人情感倾向。
(三)兼具教会著史与私人著史的性质
年代记是西欧中古早期历史记载的主要形式,是研究中世纪早期历史最基本的文献资料。年代记来源于教会的复活节表。中世纪早期,教会普遍认为人类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上帝的启示,教会人士是社会中的主要知识阶层,所以年代记的作者多为教士。⑳《圣伯丁年代记》的历任作者都出身教士,这必然使其作品受到教会史学的影响。以兴克马尔为例,9 世纪20 年代,他是圣丹尼斯的一名年轻教士,经常陪同希尔杜因一起出入宫殿。虽说希尔杜因不曾亲自执笔撰写,但是编修年代记是其责任所在。续写 《圣伯丁年代记》可能是兴克马尔缅怀故人的一种方式。在他看来,神学和历史是相互联系的,错误的神学观念会导致对于过去的误读。作为当时法兰克的高级教会贵族,他有责任和义务,也有自觉,维护基督教正统。所以,他借阅了普鲁登提乌斯的年代记,希望以此了解普鲁登提乌斯的宗教立场以及他对历史的描述。
尤其是当9 世纪70 年代以后,兴克马尔与国王秃头查理的关系趋于恶化,失去君主宠幸的兴克马尔在年代记的撰写中也流露出这种情绪。在876年的条目中,兴克马尔记载了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去世之后,秃头查理试图夺取其部分洛塔林吉亚领土,因而与其侄儿——日耳曼路易的儿子小路易对峙于安德纳赫 (Andersonnach)。战役爆发前,小路易在 “军队面前进行了神判法:十人接受热水神判法;十人接受热铁神判法,还有十人接受冷水神判法。每个人都祈祷上帝能够做出裁判:小路易是否有权利拥有其父亲留给他的那块疆土,就是那块他父亲在其弟弟查理同意和庄严宣誓下所获得的疆土。所有接受神判的人都没有受伤”㉑。在中世纪西欧,神判法的结果通常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代表了受审事务的合理性。此处,小路易一方30 人分别接受三种不同的神判,结果 “所有接受神判的人都没有受伤”,还向叔父查理和世人表明了自己诉求的合理性。作为当时唯一记载该程序的史料, 《圣伯丁年代记》此处的记载显然表达出兴克马尔支持小路易一方的立场,这无疑是其与恩主秃头查理关系交恶后,个人情绪与立场的自然流露。㉒
王晋新教授认为: “对加洛林时代各类史著性质判定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作者所持之立场,即作者是秉持宫廷立场对时事加以所谓的 ‘客观’的记述,还是出自于自己之内心,独立地记录、阐释对过往和当下诸般事务的主观认知。”㉓参照这一标准, 《圣伯丁年代记》的诸位作者尤其是普鲁登提乌斯和兴克马尔,虽然出身教士,但是在其写作中因为各种原因日益流露出个人情绪。可以说, 《圣伯丁年代记》是一部 “私人著述与教会著述两种特性兼具的历史文献”。㉔“其作者的观点是宫廷教士和主教的,而非普通僧侣的,关注的中心是世俗统治者和大主教的事迹。然而,尽管关注公共事件,但主要代表的是个人的观点。该年代记并非受任何统治者之命而作,并不是 ‘官方历史’,也不具备官方宣传性。”㉕
三、《圣伯丁年代记》评述:兼论加洛林年代记的特点
(一)史家著史意识日益凸显
早期的年代记常将大小事情混杂在一起,进行简单描述,没有轻重、详略之分。包括最古老的《圣阿曼德年代记》在内的早期法兰克年代记,其形式更像大事年表,语言简洁,内容随意,涉及的通常是政治、经济、军事、气候等,极少有作者主观意识的体现。后世史家常据此批判其缺乏历史意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因为 “年代记作者往往只是满足于描绘那个世界,而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平凡的现象经过他们的挑选,也会产生意义,出现解释和发展的意识”。㉖
认真考察 《圣伯丁年代记》写作背景就会发现,在其产生过程中,诸位作者的著史意识在不断提升,这一点在普鲁登提乌斯和兴克马尔身上尤为突出。例如,普鲁登提乌斯在年代记写作中逐渐凸显出其个人意识。在840—843 年加洛林家族三兄弟的纷争中,普鲁登提乌斯支持秃头查理,因此将洛塔尔一世描绘成内战元凶和祸首,将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兄弟描写成和平爱好者,认为他们只是在兄长洛塔尔步步紧逼下,才不得不卷入战争。840 年条目如此记载: “洛塔尔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立即打破成例,离开了意大利,冲进高卢。他对皇帝的头衔垂涎已久,因此纠结了手下大部队,反对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两位皇弟,先后对他们发动战争,但是都未曾取得成功。无论他多么虚荣自负,曾经多么无情,事态终究暂时朝向好的一面发展。然而,洛塔尔并未停止对兄弟们的阴谋诡计。由于他贪婪与残忍的本性,他依然时刻准备谋害他们。”㉗这段记述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家尼特哈德在 《历史》一书中的记载不谋而合,但与体现东法兰克王国立场的 《富尔达年代记》大相径庭。后者如此记载: “从意大利来的时候,洛塔尔姗姗来迟。法兰克人推选他为统帅,继任皇位。法兰克人们都说:已故皇帝弥留之际,指定洛塔尔为统辖王国之人,并将象征君主的权杖和皇冠也授予了他。但是洛塔尔的兄弟们却并不认可这一安排,他们筹划发动了对洛塔尔的叛乱。首当其冲是他的兄弟日耳曼路易,他率领强大的东法兰克军队,前来夺取莱茵河以东的王国领土。”㉘同一时代的两部年代记对同一历史事件迥然不同的记载,恰恰体现出作者政治立场的差异。普鲁登提乌斯支持西法兰克王国和秃头查理,其写作必然站在西王国立场上。然而,教职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与宫廷生活的疏离、与兴克马尔在教产方面的矛盾、对教会异端的同情以及与秃头查理政见的不同,都使得普鲁登提乌斯在写作中日益体现出本人的情感倾向与个人观点。纳尔逊教授评价说: “毫无疑问,普鲁登乌斯编撰年代记的方式由其个人的政治忠诚和关系决定,而非抽象原则决定。”㉙正因如此,858 年西法兰克王国贵族森斯的维尼洛、布鲁瓦伯爵,密谋邀请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取代秃头查理入主西法兰克王国时,作为其中一员,普鲁登提乌斯在记录此时事却并未提及涉事贵族的名字。㉚
作为秃头查理倚重的大臣之一,兴克马尔的政治地位及其与君主秃头查理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决定了其无法做到真正的 “秉笔直书”。对材料的任意剪裁,记载中的前后矛盾,恰恰是其个人立场的反应。例如,当秃头查理的侄儿洛塔尔二世试图跟原配妻子离婚、立情妇为后时,兴克马尔坚持基督教关于婚姻不可解除的教义,坚决反对洛塔尔二世离婚再娶;而当秃头查理本人希望儿子结巴路易离婚另娶的时候,兴克马尔却选择避而不谈。㉛由于神学观点和个人立场的不同,兴克马尔甚至可能篡改了前任作者普鲁登提乌斯的作品。849 年的年代记条目中,强烈谴责了异端哥特沙克,说他 “因为学识而自我膨胀,沉溺于错误的信条”, “在虔诚的动机掩盖下,远赴意大利,却在羞辱中被驱逐”㉜,这既不同于普鲁登提乌斯的写作风格,也与其对哥特沙克的同情立场相悖。此外,行文中还赞许地提到此次谴责哥特沙克的宗教会议是由 “受人尊敬的兰斯大主教兴克马尔主持的”㉝。结合普鲁登提乌斯与兴克马尔之间的矛盾,有理由推测,兴克马尔对普鲁登提乌斯的原文做出了篡改,使其更加符合本人的意思。因此,纳尔逊教授评价他: “指控他人伪造的人,本身就是一名伪造者。”㉞
应该说,某种程度上,篡改恰恰是著史意识的体现。在评价兴克马尔的写作时,纳尔逊如此写到: “虽然查理曼支持写作,但是宫廷教士们更是为自己写作当代史。正如时人所言, ‘任何有学识的人都不会怀疑,将做过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写在年代记中,供后人学习,是一种最古老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这里强调的是 ‘有识之士的著史意识,而不是国王的价值。’”㉟“我们阅读兴克马尔的年代记时,不能将其当作一个坏的历史作品来读。它是对当时的政治事件的一系列主观或者瞬间的感知与反应,兴克马尔本人或多或少地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㊱南安普顿大学中世纪史教授蒂姆·罗伊特 (Timothy Reuter)也认为,以年代为框架组织起来的事件内容,不再仅仅是备忘录,已经演化成为一种复合型的历史叙述,它们记载各类事件,对其进行评价,甚至试图对其加以解释。㊲
(二)年代记书写受到政治的影响
正如麦基特里克教授所言: “如果对700—900年的认识完全依赖于这个时期的史书,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法兰克人的夸耀和赞美,并将其作为8—9世纪研究的中心点。他们极力标榜加洛林社会统治精英的自信与伟大,赞扬其在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中的活力。”㊳年代记是法兰克时期重要史著形式之一。加洛林时代是年代记编撰的高峰时期,数量增多、内容丰富、主题范围广泛,其书写显然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统治者的推动是加洛林年代记迅速发展的原因,也是王室宫廷一度成为年代记编写主要阵地的原因。因此,年代记明显有维护王朝的统治权益、美化统治者的政治目的。 《梅斯年代记》的编撰目的是荣耀加洛林家族,阐释加洛林家族取代墨洛温王朝、掌握政权的合理性。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写于宫廷之中,由宫廷教长或者其下属撰写,其内容以王室或者王家为中心,记载的王室的征战、政绩、贵族对王室的忠诚等,体现出法兰克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具有更为清晰的官方属性。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对矮子丕平篡夺王位虚构和不实的记载,目的也在于证明其夺权是军事成功、教皇支持和法兰克人选举的结果,进而说明751 年加洛林王权确立具有合法性。㊴
有论者认为, 《圣伯丁年代记》 “并非在君主要求下产生,其作为政治宣传的功用很小。虽然其关注的是公共事件,但是它们主要代表的是个人对事件的反应”。㊵这一观点强调的是 《圣伯丁年代记》的 “非官方性”,但不能就此认为年代记的写作不受政治影响。年代记反映出政治兴衰、统治的延续和中断,其写作势必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富尔克在写作初期,原本遵循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的传统,按年份顺序记载每一年发生的事件。但在832—833 年却,集中叙述了虔诚者路易与其儿子们之间的纷争,而忽视其他事件的记载。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833 年加洛林帝国爆发了反对虔诚者路易的叛乱,国内形势紧张,国王虔诚者路易与诸子之间的斗争成为备受瞩目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混乱的政治形势给年代记的撰写带来了客观的困难,也可能是年代记作者难以判断当下局势对立的优劣,不好下笔。等到叛乱被镇压后,833—834年的年代记便恢复了相对完整性与连续性。834 年的条目中,作者表达出对于虔诚者路易的同情,“这位皇帝一直被囚禁在亚琛,他始终没有得到丝毫人道主义对待。相反,他们正变本加厉地、残暴地对待他,妄想通过昼夜不停地身心折磨,摧垮皇帝坚强的意志……”。㊶虔诚者路易恢复统治后,836—839 年的年代记更是体现出令人惊讶的完整性,对于宫廷的关注更加清晰。
840 年虔诚者路易去世,加洛林三位王子展开权力之争。一时间,战事不明, 《圣伯丁年代记》的写作反映出这种形势:几乎没有记载从虔诚者路易去世到丰特努瓦战役爆发之前的历史。究其原因,可能是丰特努瓦战役之前,在与长兄洛塔尔一世的对峙中,秃头查理与日耳曼路易处于劣势。动荡不安的时局自然也无法为普鲁登提乌斯提供稳定的写作环境,必然会影响其写作。当丰特努瓦战局胜败已现时,在相对稳定的政局下 《圣伯丁年代记》的写作才得以继续。
(三)体现出宗教服务于世俗政治的功用
中世纪年代记是在基督教历史和基督教神学背景下形成的。㊷加洛林年代记的兴起,最初是由于统治者希望复兴拉丁文化,但是其写作更多是由于教士阶层的兴趣,而不是皇室的热情。㊸早期年代记的记载简洁扼要,通常只涉及到修道院生活。㊹加洛林时期,大多数年代记撰写者是神职人员,因此基督教信仰及基督教史学传统大大地影响了其写作。最显著的表现是,重要的基督教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以及各类宗教活动,频繁地出现在年代记中。在 《法兰克王国年代记》中,从759 年到808 年,几乎每年都提到统治者庆祝复活节、圣诞节的地点、方式。同时,年代记中大量史事体现出神意的作用,将加洛林统治者塑造成理想中基督教国王的形象,认为法兰克人作为罗马帝国的后继者是上帝的选民。他们也一再强调,上帝是法兰克王国的庇佑者,多次显示奇迹襄助了法兰克人,从而使加洛林王朝的篡权具有宗教上的合法性。陈文海教授评价,这是 “以显性的方式将加洛林法兰克历史置于基督信仰的框架之中……将加洛林法兰克的发展旅程与基督诞生后的线性时间链条捆绑再一起,也就意味着加洛林法兰克是基督家族的组成部分,支持加洛林君主、匡扶法兰克国家也就成了上帝的分内之事”。㊺早期的基督教史家们曾反对史学写作依附于世俗政权并为世俗政权服务的倾向。但是,从包括 《圣伯丁年代记》在内的加洛林年代记中可以看到,神职出身的加洛林史家们违背了早期基督教教父们的教诲,将个人著述建立在服务世俗统治的目的之上。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世俗王权来说,这一时期基督教会的权力较为弱小,世俗君主牢牢控制着教会的各个方面,各个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的选任、调迁都掌握在世俗君主的手中。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加洛林时代的史家们不得不以自身服务的政治派别作为判断标准,其史学写作和评论也必然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从而使得加洛林时期的史学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因此,加洛林史学也注定无法脱离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
综上所述, 《圣伯丁年代记》在其撰述过程中,经历了从宫廷著史到私家作品转变,反映出其撰写者作为中世纪早期史家著史意识的逐渐凸显。同时,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斗争,对于这一时代年代记的产生与写作发挥了重要影响。虽然以现代观点来看,加洛林时代的年代记缺少历史批判精神,但由于其写作时间接近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年代记作者通常是事件的亲历者,因此,这些看似零散的记录实则为后人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和宝贵的资料,并按照年代顺序记载历史的方式,为后人研究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探索王朝政治,提供了极大便利。
注释:
① ⑬ ⑭ ⑲ ㉙ ㉞ ㉟ ㊱ ㊸ Janet L. Nelson, “The Annals of St. Bertin”, Politics and Ritual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London and Ronceverte: The Hambledon Press, 1986,pp.173-194, p.186, p.185, p.186, p.182, p.190, p.174, p.190,p.191.
②Janet L. Nelson, A Tale of Two Princes: Politics,Text, and Ideology in a Carolingian Annal, Studies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y 10, New York, 1988, pp.105-141; Hincmar of Rheims on King-Making: The Evidence of the Annals of St. Bertin, 861-882, Coronations: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onarchic Ritual, Ed. Janos M. B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1990, pp.16-32.
③⑩⑪㉕㊵Janet L. Nelson, Introduction, The Annals of St-Bertin: Ninth-Century Historie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anet L. Nel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9, p.7, p.10, p.2, p.2.
④㉓㉔ 王晋新: 《〈圣伯丁年代记〉探微》, 《古代文明》2021 年第1 期。
⑤ 李云飞译注: 《圣伯丁年代记》,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
⑥⑳ 赵立行: 《西方史学通史 (第三卷):中世纪时期 (公元5 世纪至14 世纪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06—108、108 页。
⑦ 赵立行: 《加洛林时代的史学形式及其价值》,《贵州社会科学》2012 年第9 期。
⑧朱君杙: 《从王室宫廷到大主教区——论加洛林时代大年代记修撰中心的转移》, 《历史教学》2016 年第18 期;朱君杙: 《加洛林时代历史文献的政治倾向性》,《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5 期。
⑨ 转引自: Janet L. Nelson, Introduction, The Annals of St-Bertin: Ninth-Century Historie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anet L. Nel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
⑫Rosamond McKitterick, Charlemagne: The Formation of a Europea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5.
⑮⑯⑰⑱㉑㉒㉗㉚㉛㉜㉝㊶Janet L. Nelson (trans. and annotate), The Annals of St-Bertin: Ninth-Century Histories,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1991, p.105, p.106, p.103,p.94, p.196, p.196, N.26, p.49, p.88, p.106, p.67, p.67, p.28.
㉖Erne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Modern 2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102.
㉘ Timothy Reuter (trans. and annotate), The Annals of Fulda: Ninth-Century Histories, Manchester: Th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8.
㊲Timothy Reuter, Introduction, The Annals of Fulda: Ninth-Century Histo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
㊳Rosamond McKitterick, Introduction: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II c.700-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3.
㊴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Illusion of Royal Power in the Carolingian Annal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2000, 115, p.4.
㊷Rosamond McKitterickR, Carolingian Culture: Emulation and Innov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9.
㊹ Rosamond McKitterick, The Frankish Kingdoms Under the Carolingians 751-987, New York: Longman Inc.,1983, p.3.
㊺ 陈文海译注: 《法兰克王家年代记》,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 64—6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