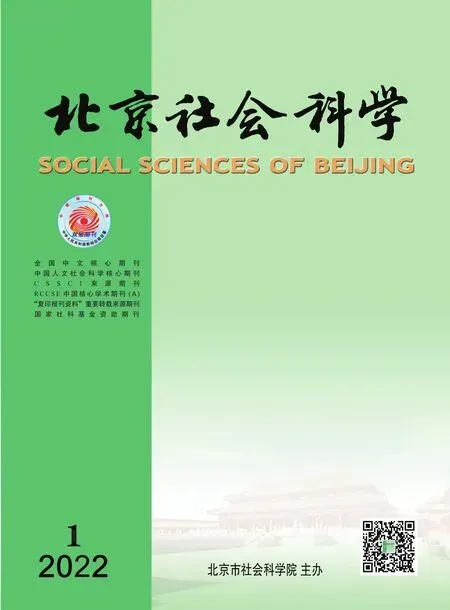“阳国北门”居庸关的地理叙事和审美空间
吴 蔚
一、引言
“文学景观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又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在所有的文化景观中,又以文学景观的意义最为丰富,因为文学景观是可以不断被重写、被改写的。”居庸关正是一个不断被重写、具有多重内涵的文学地理景观。它是万里长城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关塞之一。早在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篇就有记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谓九塞?大汾、方城……居庸”。其地理位置又十分独特,自古以来,无论是燕都、蓟城,还是辽南京、金中都,或是元大都、明清北京,这些都城的相伴都为它增添了无限的历史底蕴和人文色彩。此地著名历史事件众多,文人墨客常有出入,文学名家之作品多有留存,例如唐代高适、宋代汪元量,明代郝经、徐渭、李贽,清代顾炎武、朱彝尊等。“中国北方关塞甚多……也没有哪个关口曾经走过那么多的……文学家。”因此,居庸关这一地理景观具有深厚的文化意义,有待今人进一步挖掘、整理。
一般认为,最早书写居庸关的诗篇出自唐代边塞诗人高适之手。此关在唐代被称为“蓟门关”。查询《全唐诗》中包含“蓟门”的诗歌共有34首,但没有一首有“蓟门关”之名,唐人通常用“蓟门”“蓟北门”来泛指蓟丘、蓟城,而非指长城关隘。比如边塞诗人高适在开元十八年有《蓟门行》五首,诗中的“蓟门”就没有指向“蓟门关”。其中第四首提到了长城,诗曰:“茫茫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虽然已写道“长城外”,并且提到“空塞”,但只是泛化的描写,并没有出现塞垣、城关等具体地理景观。可见“蓟门关”在唐诗中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而高适另有《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反倒出现了“居庸”的名称,说明在唐代,“居庸关”与“蓟门关”之名是同时存在的。这首组诗是描写居庸关的滥觞之作,也就是居庸关作为文学景观的开始。诗歌写于唐天宝九载之秋,作者得制科仅授封丘县尉一职,心中怀着郁闷,去给青夷军(在今河北怀来境内)送兵。诗中有“古镇青山口,寒风落日时”“莫言关塞极,雨雪尚漫漫”的描写,对居庸关的边塞苦寒做出描绘,也有“登顿驱征骑,棲迟愧宝刀”“绝坡冰连下,群峰雪共高”之句,不失盛唐边塞诗人之骨力,奠定了居庸关诗篇怨愤悲凉的感情基调。此后历代均有众多歌咏居庸关之佳作。仅据李德仲《居庸关》和徐红年《八达岭长城古诗咏》所搜集的居庸关古诗词就有177首左右,共13000余字,碑刻、石刻文30000余字。这些成为居庸关文学景观研究的丰厚基础。
目前对长城关隘文化的研究,以山海关、嘉峪关、雁门关,或以内三关、外三关为关键词的较多,如许海军的《长城诗歌反映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象的重构——以嘉峪关为例》、杨怡的《论外三关长城的美学价值》等,对居庸关的研究则比较欠缺。本文试对此做一弥补。
二、地理意象:抵御外侮的“阳国北门”精神
“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一个客观物象由于古代诗人的反复运用,经常会固定地带上某种意蕴,如梅花是清高芳洁的象征。
居庸关在人们的心目中首先是一道天然的分水岭。居庸关“大体上仍是……气候的分水岭,生产、生活方式的分水岭,由此也自然成为了文化上的分水岭”。关南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关北则大多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关南是京西平原、华北平原,关北是塞上草原;关南是农耕文化,关北是草原文化。自然和文化的分隔也往往形成政治统治的屏障。“天设居庸险,乾坤此北门”。这里山岭阻隔、悬崖深谷的地形可以极大地限制往来出入,是大自然用来隔离南北、划分内外的天然门户。
而作为地理意象,居庸关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元代郝经“阳国北门”的说法更为明确地表征。在《居庸关铭序》中,他说:“居庸关在幽州之北,最为深阻,号天下四塞之一……中原能守则为阳国北门,中原失守则为阴国南门。故自汉唐辽金以来,尝宿重兵以谨管钥。”这个说法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并略加考证。历史上在西周时期曾有一个姬姓小国称为“阳国”,地理位置在今山东沂南县南,后为齐桓公所灭。这个“阳国”与长城相距甚远,且没有一个“阴国”与之相对应,与郝经文章中的阳国应该没有关系。而从“中原能守”“中原失守”来看,郝经序文中的“阳国”明显是指中原国家、汉族统治的政权,“阴国”指塞外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权。
阳国和阴国的说法又显然与古代阴阳数术有关。据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金星占》所述“(金星)从西方来,阴国有之;从东方来,阳国有之”,“上旬为阳国,中旬为中国,下旬为阴国”,这里是说当太白经天的时候,从东方经天为阳国,从西方经天为阴国,而书中还明示不同的天象预示着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动乱。阴阳为两极,“阳国和阴国是相对而言的。越、齐、韩、赵、魏,是秦、荆的阳国;齐国,为燕、赵、魏的阳国;魏国,韩、赵的阳国”,展开战国地图,大致可见,位于东方者为阳国,位于西方者为阴国。汉族政权相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在东南方,故而称为阳国;反之,游牧民族在汉族政权的西北方,故而称阴国。结合南北分水岭的内涵,“阳国北门”的说法就有了双重的空间意识,一是居于东方之国,二是南北之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北方长城上的关隘都可以叫做“阳国北门”或“阴国南门”,其地理意象的基本文化意蕴是类似的。
历史上的居庸关长期为“阳国北门”,但自从辽金以来作为“阴国南门”的时日也渐长,最后或成为“国中虚门”。三者之间的文化内涵有着显著的差异。“阳国北门”与“阴国南门”是相对立的、具有战争因素的地理意象,前者为防御性的,后者为进攻性的;“国中虚门”是和平的、安定的,但也不排除临时的内部的动荡因素。我们从居庸关大事记中,可看到大量有关战争的史料:汉代有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北齐侍御史桓彦范于河北断塞居庸以备突厥;五代有幽州节度使周德威以兵拒契丹于居庸关之西;明代有也先攻大同,英宗亲征,度居庸关“北狩”;清代有圣祖仁皇帝率八旗官兵讨葛尔丹,幸居庸关;等等。而其中涉及“阳国北门”题材的文学作品才最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明代《建罗公表忠祠记》表彰了御史罗通抵御瓦剌的英勇事迹。土木堡之变后,边警日急。正统十四年十月,也先、脱脱不花率三万众急攻居庸关,危急关头罗通稳住阵脚。当参将想要出关护卫的时候,他冷静地分析,关北已经失守,幸而还有居庸关,不守住居庸都城就不保。在决定固守居庸关后,他立下“此身与关共存亡”的誓言。战斗开始,他显示出机智与勇敢并存:先下令在关西南布帐迷惑敌军;又令军民老幼浇水冰城,使地冻滑不得靠近;又忽开门冲出重围大战三个回合,俘虏斩杀敌人无数;最后敌军逃遁而去。这些众志成城、守卫国土的书写,让人热血沸腾,给后世子孙无穷的力量,正是北关锁钥“阳国北门”精神的体现。
而作为“阴国南门”和“国中虚关”时,也不缺少人文书写,但相形之下,通常显得缺乏较为深刻的感人力量。例如郝经的《居庸行》叙述了金朝被蒙古人所灭的过程,“清夷门折黑风吼,贼臣一夜掣锁降”,本是蒙古人的侵夺战争,被叙述成扑灭乱臣贼子,总是让读者心生犹疑。又如清玄烨所写《居庸叠翠》“凯奏捷书传朔塞,欢声喜气满人寰”,所谓“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这类诗歌总体而言显现出典雅或秀丽的诗风,骨力则大不如从前。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以为,历代对于居庸关的文学地理书写是以“阳国北门”这一意蕴为核心的,或者说居庸关意象的核心象征意蕴是“阳国北门”。因为长城主要是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工事,其功能重点为防守,只有“阳国北门”的意蕴才更具有抵御外侮、守卫和平的文化意义。也只有当其表现为“阳国北门”之时,那些人文书写才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家国情怀和悲情意识,才显得更为感人,更有风骨。
需要指出的是,“阳国北门”“阴国南门”或是“国中虚关”,主要不是从历史阶段来区分,而是从人文意蕴来探讨的。“阳国北门”是长城人文书写中的一种心理,一种情结,是居庸关作为文学地理意象的较为固定的意蕴,即守卫家园、捍卫和平的情怀。这种情怀并没有因为居庸关功能的改变而失落。就像清代的居庸关用来抵御外侮的意义已经不太大,但乾隆皇帝仍有诗曰“居庸天险列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也就是说即便居庸关的防御功能早已弱化,“阳国北门”精神却一直作为居庸关地理意象的主要文化内涵沿袭下来,成为国人隐藏在头脑深层的集体记忆。
三、地理叙事:战争苦难的“复奏”与民族融合的“变奏”
地理叙事是“指文学作品中以地名、地景、地理影像与地理空间建构为主要的叙事方式,是指向文学作品的艺术传达问题”。不仅在小说等叙事文学中,“在许多诗歌作品里,其实也存在一个‘地理叙事’的问题”,“在诗歌作品里存在地名现象,就具有地理叙事的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学景观的书写离不开地理叙事。虽然“阳国北门”精神是居庸关地理意象的核心象征意蕴,但围绕这一地景的地理事象是丰富而多样的。具体说来其地理叙事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战争苦难的多重“复奏”,二是民族融合的“变奏”。
所谓“多重复奏”是围绕边塞、雄关、战争,风沙、严寒、苦难,怨愤、悲凉、愁苦,荣辱、责任、生死等的地理叙事,是指对自唐代高适以来所形成的怨愤悲凉之情反复而多样的书写,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居庸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既目睹了外族入侵中原,也经历了民族矛盾或内乱纷争。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无论是何种战争都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常具有强烈的悲情色彩。居庸关作为战争灾难的意义已经成为恒久的历史记忆,即使在和平年代也是其地理叙事的主流。元代萨都剌的《过居庸关》云:“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昼击云雷张。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按说元代已是“华夏于今共一天”的时代,但诗人们对于雄关的记忆仍是战火纷飞、尸横遍野的景象。这首诗中描绘了居庸关作为古战场“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的凄惨情景,叙述了一位八十岁还在扶犁锄的老翁对战争的苦痛记忆。诗歌借居庸关表达了对蒙古贵族发动战争的痛恨,对百姓的同情,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后呼告“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
伴随着对战争灾难的思考,居庸关作为雄关的意义也一再得到反思。事实上,前文所述《居庸关铭》最终要表达的主旨也并非赞美居庸关的关隘险要。其言:“天险地险,莫如人险,兵力相须兮。刻铭岩,用告仆夫,当戒覆车兮。”这是告诫人们国家的永固与否关键不在于关隘是否牢固,而在于兵力,在于人。类似的表达还见于元代刘秉忠的《过居庸关》:“函关不谓平如地,蜀道无如险似天。万里挥鞭犹咫尺,谁能掌上保幽燕。”意思很明确:函谷关也好,蜀道也好都是天险,但也难保不被攻破,万里的距离挥鞭即到犹同咫尺,谁又能说居庸关能保住幽燕之地呢?这些诗文都对关隘保家卫国的历史作用做出了深沉的思索。“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再险要之关隘也抵挡不住腐败的朝廷和无耻的官员。明代张宁在《居庸关》中写道:
羽书昨夜报居庸,百万雄师下九重。
天子垂衣临大漠,群臣端笏扈元戎。
禁中已乏回天策,阃外谁成辟地功。


而居庸关作为分水岭的意义,也随着南北的对峙,在生与死、荣与辱的考验中被极度放大了。当居庸关已是辽、金、元国土的一部分,汉人来到此地往往不再是建功立业或是游览山水,而是伴随着屈辱与羞耻。南宋汪元量作为宫廷琴师,被俘入元随太皇太后北行,亲身经历三宫北上的过程。其《出居庸关》曰:
平生爱读书,反被读书误。今辰出长城,未知死何处。下马古战场,荆榛莽回互。群狐正纵横,野枭号古树。黑云满天飞,白日翳复吐。移时风扬沙,人马俱失路。踌躇默吞声,聊歌远游赋。
诗中突出了“出长城”这一地理事象的特殊的生命意识,并对居庸关外的古战场进行地理叙述,群狐纵横、野枭哀号,黑云漫天、风沙肆虐,人马失路的景象是这一文学景观典型事象的再现,但比高适诗中的边塞描绘更为阴惨和沉郁。诗中的苦难不仅仅是边地的苦寒和战争的残酷,更是对南宋王朝懦弱无能的无奈。宋、金时期的宇文虚中是一个庾信式的人物。他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出使金朝,写下《过居庸关》一诗。当时宋将姚平仲大胜金军,钦宗却害怕得罪大金,于是派时任资政殿大学士的宇文虚中前往金上京调停请和。诗的结尾写道:“花已从南发,人今又北行。节旄都落尽,奔走愧平生。”这里的南北分界是居庸关地理意象的典型特征,南北在此已经开始带有象征意义:南方花开,象征家园,行向北方,象征他乡。它与汪元量诗中“今辰出长城,未知死何处”一样,深切表现了身在异国他乡的苦楚和对故国的眷念。
所谓“变奏”是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在传统主题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书写:不再是苦难,而是和平宁静的生活;不再是民族的对抗,而是民族的融合。
居庸关在太平年代作为交通关口和民族融合的地理叙事,可谓人们对该地理意象的一种变奏,所谓“有事则席卷燕赵之兵以为犄角”,“无事则坐享长河之利以为转输”。长城上的关隘是通过长城的通道,是联系关内、关外的关口,居庸关是蒙古高原通向幽冀平原的咽喉,正如山海关是东北通向华北的要道,嘉峪关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节点。和平时期,关门洞开,察出御入,抽取捐税。元代揭傒斯《居庸行》描绘道:“关门西向当天开,马如流水车如雷。……昔不容单车,今马列十五。”他表达了“圣人有道关门开”的思想,最后满怀豪情地抒发盛世情怀,希望“关门开,千万古”。元代黄溍《居庸关》曰:“……圣人大无外,善闭非键钥。车行已方轨,关吏徒击拆(柝)。居民动成市,庐井互联络。幽翕白云聚,石磴清泉落。地虽临要冲,俗乃近淳朴。政须记桃源,不必铭剑阁……”诗中突出了关隘除了军事之外的重要功能,描绘了和平时期关内外居民相互往来联络,市井繁忙、民风淳朴的景象。歌颂太平盛世,世外桃源,从而否定战乱。尽管这不是居庸关文学地理意义最为主要方面,但也是地理叙事的重要内容。
“复奏”和“变奏”本是音乐叙事的专有名词,笔者借用来表达不同时期地理叙事的主题变化。多重复奏是不同时期居庸关战争灾难叙事的重复而又多样性的书写;变奏则是关隘互通、民族融合叙事的和平之音。这两类文学作品在艺术美感上也是不一样的,前者充满怨愤之音,以悲为美,后者多为平和之音,以和为美。居庸关地理景观的文学意义就在这种多样的地理叙事中趋于丰厚。
四、审美空间:外险内秀一统于壮丽雄关
“在文学中,地理已非现实空间,而是一个美学场所。”作为北关锁钥的居庸关,其雄伟之势自古以来为文人所称道,它和嘉峪关、山海关一样也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美称。古代文人墨客莫不称颂其天然形势、歌咏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奇崛。明代哲学家李贽过居庸关时也不由地赞叹:“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清初顾炎武曾到居庸关进行实地考察,也感慨:“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古人将居庸关与其他著名的雄关险隘相比较,以突出其雄伟,如“形式嵯峨压剑关,两崖突出白云间”,“蜀道之难不为难,险莫险于居庸关。出关入关仅百里,千回万转羊角盘”,“雄峻莫夸三峡险,崎岖疑是五丁穿”,分别以剑门关、蜀道和三峡来突出居庸关的雄伟险峻。“长城横塞白,叠嶂逼天青”则用夸张的手法形容雄关直逼青天。
然而这些似乎只突出了居庸关地理景观美学意义的一个方面,即整体的审美蕴含。居庸关其实还包含着诸多“微地理”景观,其美学意蕴也是多方面的。明代修筑的居庸关本身又包含3道关防,除关城外还有南口、北口、上关,其中北口即著名的八达岭。因此,说居庸关实际已经包含了八达岭。居庸关又有居庸八景之美誉,即玉关天堑、石阁云台、叠翠连峰、双泉合璧、汤泉瑞霭、琴侠清音、驼山香雾、虎峪晴岚,说居庸关时也都将这些美景涵盖其中。书写居庸关的诗文常常包含关内、关外两方面的描写和抒发,若从“阳国北门”与“阴国南门”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其对立统一的两面的审美特质。关外代表的苍凉悲慨和关内代表的苍翠秀丽都统一在这一道雄关之中。
如同所有的边塞诗歌一样,关外之景往往是“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的苦寒,是“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的苍凉。元末明初李延兴《过居庸》一诗描述了躲避兵灾的普通百姓出关感受到的环境的恶劣:
岁莫候,风凄凄,车中行客胡不归?一车南,一车北,南来北去何时息。车行欲近关上头,鞭牛不前吁可愁,须臾摧挽在平地,车中儿女欢且讴。短褐萧萧风雪里,山径荒寒多虎兕。呼儿取火伙晚炊,瓦铛黍米和沙煮。黄昏露宿官道旁,茅店鸡鸣载行李。殷勤起谢车中人,万岭千山多苦辛。严风吹霜皮欲裂,一身只有筋骨存。安得筋骨化为山下土,填却万岭千山无险阻,尽使行人免愁苦。
这首歌行体诗歌以傍晚时分凄凄风雪为背景,以“鞭牛不前”引领对关外苦寒景象的描写,突出一个“愁”字。无论是山径中“多虎兕”,充满着威胁,还是风沙大到“瓦铛黍米和沙煮”,“严风吹霜皮欲裂,一身只有筋骨存”,身着短褐的行人,黄昏露宿官道边,或是栖身于简陋的茅店之中,清晨又要载上行李匆匆赶路,都给人以慷慨悲凉的审美体验。最后仿效杜甫发出呼告:“安得筋骨化为山下土,填却万岭千山无险阻,尽使行人免愁苦”,呼应了开头的“愁”字,再次突出了凄怆悲苦的美学特征。类似这样写居庸关外苍凉悲慨之险恶景象的诗篇在有关人文书写中占了多数。
然而居庸关又有另一面。“中国北方关塞甚多,但很少有像八达岭那样集险与翠于一身的关口。”翠是“居庸叠翠”,早在金代明昌年间(1190-1196)金章宗钦定燕京八景之一,将“居庸叠翠”列为首位。明代永乐年间该景致被列为北京八景。清代乾隆皇帝曾亲笔题写“居庸叠翠”四字。狭义的“居庸叠翠”之景在关城东南;而广义来说,不能仅仅局限于东园附近或居庸关附近,应该将整个关沟作为“居庸叠翠”的欣赏对象。《燕京八景图诗序》中称:“居庸关之中延袤四十里,两山对峙,一水旁流,关中有峡曰弹琴,道旁有石曰仙枕,两崖峻绝,层峦叠翠,故曰居庸叠翠。”翠表现为一种秀美,但不仅仅是实指夏天的林木繁茂,山林翠绿。明代画家王绂《居庸叠翠图》有行人乘船过关悠然自得的景象。元代陈孚《居庸叠翠》有“征鸿一声起长空,风吹雪低山月小”之句,描绘这里的冬景,意境既有壮美的一面,又有秀丽的一面。清代奕詝的《居庸叠翠》颔联“雉堞高依秋月静,螺峰浓带塞云环”,“雉堞高依”为雄,“秋月静”则为秀;“螺峰”为雄,“塞云环”则为秀,颈联“画屏掩映层峦秀,石径萦纡一线攀”,上句为秀,下句为险。诗中的审美体验无不是险与秀的结合。
在书写居庸关的诗篇中,关外的险与关内的秀又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地理空间审美对比,使得作品充满了张力,从而让人回味无穷。“是关也…… 关景咫尺,南雨北雪,天造地设华夷之界限也。”清代尹会一《居庸关》诗曰:
莽莽关山起暮愁,乱云层叠隐危楼。
雕弧控满清霄月,画角吹残紫塞秋。
旅梦无端空索莫,归心何事更夷犹。
燕南碧草还飞蝶,已见桑干带雪流。
这首诗大概写于1337年作者到京师入觐之时,反映了作者浓重的羁旅之情、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人生的无尽感慨。诗中颈联由桑干想到燕南,居庸关的深秋已经开始下雪,而家乡燕南还是碧草飞蝶,通过南北两地的对比,进一步加深了居庸关深秋的悲凉气象。
对于出关作战的将士来说,关外的苦寒景象是残酷战争的象征,关内的春光则是家乡温馨和平生活的代表。在诗文中,作者常常借景抒情,融情入景,在两种风景的对比中寄托对战争的忧惧、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渴望和人生的痛苦。清代徐兰《出关》写道:“凭山俯海古边州,旆影风翻见戍楼。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此诗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帝统兵征讨葛尔丹,作者随安郡王出塞之时。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称这首短小的七言绝句“几于万口流传”,其妙处就在于地理空间对比手法的运用,和“回头”这一细节的捕捉。马后桃花与马前雪的对比(实际上就是关内与关外的对比),使得诗歌带有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巨大的张力,也展现了出征将士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既是铮铮铁汉,但又柔情似水。他们并非只会行军打仗,而是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舍弃小我而求大义。
关内、关外的不同感知是和南北的物候紧密相连的。因此出现关南暑多、关北寒凉,马后桃花盛开、马前飘洒白雪,燕南碧草青青蛱蝶飞舞,关北桑干河上雪花飘舞的情形。物候的巨大反差更加引起文人强烈的生命感知与对生命的珍惜。他们思念家乡,归心似箭,“旅梦无端空索莫,归心何事更夷犹”。出关一步三回头,将军此去也许还能封侯,广大士卒也许就是战死沙场,因此教他们“何心肯逗留”。对于战争期间的汉人,出关就意味着向死亡跨出了一步。
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文学景观,居庸关的文学空间又由雄关以及关内、关外等“微地理”空间组成。所谓“微地理”主要就是指一个相对具体而微小的“地理场”,它包括场地、场景和场合等三个方面。不同的微地理场所呈现的审美空间是不同的,但又能在雄伟壮丽的色彩中得到统一。
五、结论
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布朗所说:“我们将地理景观看作一个价值观的象征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地理景观就是解读阐述人的价值观念的文本,地理景观的形成过程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通过地理景观得以保存和巩固。”通过对居庸关的文本解读,我们能够窥见一千多年以来人们寄托在这一地理景观中的复杂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
作为长城关隘的典型代表,居庸关的文学地理意义是多重的。首先,从地理意象来看,其比较固定的意蕴是“阳国北门”的意义,即守护国家安危的存亡之门。长城关隘也许曾是“阳国北门”“阴国南门”或者“国中虚门”,而最能代表长城关隘精神的则是“阳国北门”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顽强抵御外侮的精神。其次,从地理叙事看,主要为战争灾难的多重“复奏”与民族融合的“变奏”。动荡年代,“阳国”与“阴国”,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南与北,家园与异乡都在这道门的两边。出关与入关,对于个人仿佛就在死生之间,对于国家就在存亡之间,具有浓郁的生命意识和悲情色彩;和平时期,关口的开放与融通也大大地促进了民族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做出了贡献,此又为安乐之音。整体上看,以忧愤愁苦为叙事的主要旋律,而和平之音也是人文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从审美空间上看,关外的苍凉悲慨、关内的苍翠秀丽也被涵盖在同一道雄关之中,是复杂的统一,多样的和谐。审美空间的对比所形成的反差往往是居庸关诗篇最为动人之处。
整体而言,这三个层面又是相通的。地理意象是精神,地理叙事是血肉,审美特征是风格。精神需要统一,血肉需要饱满,风格往往是杂糅的。文学景观的意义多具有这三个层面的特征。我们以往对文学景观的探讨常常有两种倾向,或者罗列各种文化意义,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贪多求全;或者只举一端,不及其余,只顾主体景观,不及微观地景。这两种倾向都有失偏颇。
今封四海为家日,居庸关内外别样而多元的景致成为北京城的一张美丽的名片;其丰富的地理事象也成为讲好城关故事的资源宝库;它的地理意象所具有的不畏艰险、自强不息、抵御强敌、守卫和平的“阳国北门”精神更存留在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警醒着人们,感染着人们。居庸关是长城关隘景观的代表,其文学地理意义也是长城的文化意义。虽然长城上的各个关隘早已失去了军事价值,但所代表的长城精神却永远保留下来,化为中华民族的血脉,生生不息。以居庸关为代表的长城文化从来都是以反对欺凌、追求和平为核心的,其文化价值恰恰在于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相互依存,实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无论是“阳国北门”还是“阴国南门”,只要是和谐之门,就永远洞开,如古人云“关门开,千万古”。这也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和谐共生精神的体现,是符合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而广之,世界需要和平,追求开放、融通、和平的精神理应成为当下这个时代居庸关文化也是长城文化的主流。在北京冬奥即将召开的今天,这个话题显示出特别的意义。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长城的背景下,欣赏冬奥会运动的力量与美感之时,他们必将感受到长城文化作为中国国家文化的厚重与魅力。
① 见曾大兴教授《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六章第二节“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识别标准”。
② 见陶礼天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十周年·江西高端论坛”会议论文《微地理与文学空间若干问题新思考》提要。